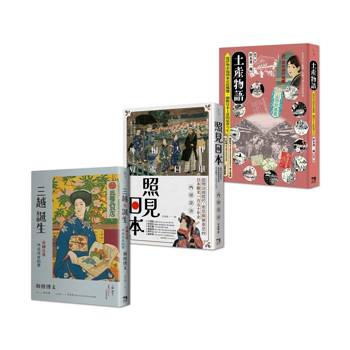《土產物語:從伊勢赤福到東京芭娜娜,細數日本土產的前世今生》
第一章 鐵道與近代土產的登場
序章中提過,近世偏好的是不會腐壞、不佔空間的土產,畢竟當時交通尚不發達,將食物或笨重且龐大的物品當成土產並不可行。
而鐵道的出現則為此帶來了革命性的轉變。已有許多研究指出,鐵道不僅改變了社會經濟,對人們的生活型態與時間概念等文化層面也造成了強烈的影響。由於名產與土產兩者和旅行有極為密切的關係,自然也遭受到鐵道帶來的直接衝擊。
本章將探討鐵道這項近代交通設施的出現,使近世以後名產與土產的意義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又如何轉變成符合近代需求的型態。
清河八郎的「土產宅配」
事實上,即使是近世,也並非完全沒有辦法運送笨重又龐大的土產。
安政二年(一八五五),著名的幕末志士清河八郎與母親一同前往西國旅遊,探訪伊勢、東海道、金毘羅、宮島等近世具代表性的名勝古蹟,並將行程詳細記錄在《西遊草》這部遊記中。翻閱《西遊草》會發現,清河非但在旅遊地點購買了陶器、人偶等大量「笨重又龐大的土產」,更直接寄回家鄉,據說運費並不貴,而且這種作法相當普及。現代人常用來寄送土產的宅配服務,或許可說就是源自清河八郎的土產宅配。
不過,清河畢竟是出羽國清川村出身的富裕鄉士,在這趟旅途中他還包下了一整艘船由四國搭往本州,連番的奢侈行徑連諸侯也為之遜色。由此可見,當時要寄送體積龐大的土產回鄉,或許不像現代這般容易。
鐵道開通與名產的演變
鐵道的開通改變了前述狀況,其中最為劃時代的發展,便是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東海道線全線通車。這使得東京到大阪、京都的交通時間大幅縮短,也大大改變了生鮮食品的運送模式。
東海道線全線通車後,人們享有交通之便,早晨在大阪飲酒,晚上就得以享用東京佳餚。因此,今年許多民眾將大阪產的海鰻寄到東京當新年禮物,國內的運輸公司不斷湧進貨物,配送員也極為忙碌。
儘管引文中的情況與本書列舉的土產不在同一個討論範圍,其時的輸送系統其實也無法在當日完成運送,不過東京往返京都與大阪所需的時間大幅縮短,確實可能為食品的贈送與答禮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鐵道的開通也促使新名產誕生。舉例來說,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京都二條到嵯峨之間的京都鐵道開通後,沿線的嵐山、嵯峨野等自古便十分知名的景點,就開始販售「勝花糰子」及「櫻餅」等名產。
勝花糰子據說是模仿隅田川的糰子製作,鐵道開通後來訪的遊客增加,各家業者競相販賣這種糰子,於是成為嵐山的名產之一。櫻餅也是在京都鐵道通車的明治三十年前後由奧村又兵衛開始販賣。兩者都是鐵道開通後新創的名產,但其型態仍保有近世以來的傳統,以當場食用為前提。
明治三十六年(一九○三)京都鐵道發行的沿線旅遊指南中,將勝花糰子與櫻餅放在「美食」單元,看來是以當場食用為前提(土產單元則有櫻樹手杖、竹硯等手工藝品,以及天龍寺納豆、香魚煎餅等便於保存的食品)。當然,其時並非完全沒有食品類土產的需求,只是尚未有證據證明這些食品在保存性與容器包裝上已獲得改良。
以當場食用為前提的名產,不僅銷路有限,業績也難以大幅提升。為了拓展銷售版圖,就必須擴張銷路,並克服保存期限短與攜帶不便等問題,將名產發展為土產。此外,像嵐山這樣歷史悠久的地方,一般都會給名產加上歷史典故,然而,「勝花糰子」與「櫻餅」卻欠缺這些要素,難免給人美中不足的印象。嵐山自古就是知名的賞櫻景點,將商品取名為「勝花糰子」可說韻味十足,只是如今似乎已經銷聲匿跡。可見一項名產能否成為主流,背後確實存在前述的因素。
安倍川餅與醃山葵
東海道不僅連接京都與江戶,也是前往伊勢神宮參拜的必經街道,乃近世主要的交通幹線,沿途曾有許多名產問世,同樣是廣為人知的事實。
其中,安倍川餅自近世開始便是知名的東海道名產。顧名思義,當時的安倍川餅是安倍川畔的茶屋所販售的點心,關於它的起源,則流傳著這麼一段說法:
慶長年間,德川家康赴御用金山井川笹山巡視時,一名男子製作了麻糬進獻。家康詢問這款麻糬的名字,男子假安倍川與金山的金粉答稱「這是安倍川的黃金粉餅」,家康聞言大喜,之後便將這種點心稱為安倍川餅。
安倍川餅自此成為名產,然而明治以降卻隨著東海道線的開通「逐漸沒落,僅餘石部屋一家商店尚在販賣」。
在靜岡車站有一家販售鐵路便當的加藤便當店,店主加藤鶴對這種情況憂心忡忡,便開始在車站內兜售安倍川餅。安倍川餅因此成為靜岡站的名產,甚至只要「列車停靠靜岡站,叫賣『名產安倍川餅』與醃山葵的聲音便此起彼落」。
值得注意的是,改為在靜岡站販賣的安倍川餅與之前銷售的近世東海道名產安倍川餅,並非只有販賣地點不同。
近世以來,安倍川畔的茶屋所販賣的安倍川餅,是撒上黃豆粉的麻糬;至於靜岡站販售的名產安倍川餅,用的其實不是麻糬而是求肥。
求肥是用水溶解白玉粉或餅粉,再加入砂糖、水飴攪拌後製成的一種和菓子材料,主要特徵是口感柔軟,且比一般麻糬的保存期限更長。事實上,近世的麻糬名產之所以能成功轉型成近代土產,求肥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使用求肥製作的安倍川餅一直以來都受到「似是而非的假貨」、「欺騙世人」等批判。然而,安倍川餅原本是以在茶屋現場食用為前提的名產,若要轉型成在車站就能隨手購買的土產,就免不了這番脫胎換骨的過程。
此外,靜岡站還會販賣另一種極具代表性的土產──醃山葵。關於其起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據說最晚在幕末時期就已經有了醃山葵的雛形。不過,基本上在「東海道鐵道開設前,醃山葵並非出奇之物」。
到了明治三○年代,醃山葵已經躋身「鐵道開設以來備受東西往返旅客喜愛的土產,靜岡車站每日銷售盛況驚人,稱得上本市首屈一指的特產」,在靜岡車站內販售,成為醃山葵這項土產大為風行的開端。
明治初期的醃山葵主要由田尻屋製造販賣,鐵道開通之後,小泉樓與田丸屋的商品也加入了站內販售的陣容。其中田丸屋還由壽司桶得到靈感,開發出盛裝醃山葵的桶狀容器,據說「與普通的容器不同,別具雅趣,因而大受讚賞,後來業者也參與各種共進會、博覽會,大大宣傳了一番」。如今,靜岡車站等處有許多商店會販賣田丸屋的醃山葵,可見積極的商品改良與擴大銷路是其主導醃山葵市場的關鍵之一。
《照見日本:從明治到現代,看見與被看見的日本觀光一百五十年史》
2 旅行導覽手冊問世
【知識分子必讀的旅行導覽手冊】
歐美人到底對日本的哪些面向感興趣?想要知道答案,只要看看他們所出版的日本旅行導覽手冊就行了。為了能在日本國內旅行無礙而由歐美人統一蒐集資訊、撰稿、編輯及發行的旅行導覽手冊,打從明治時代前期便已存在,挑選的內容都是歐美人心中認定「值得一看的景點」,在手冊中所占的篇幅比重也就與其價值呈正比。舉例來說,假如一本旅行導覽手冊共三百頁,介紹京都的篇幅占了五十頁、日光占了二十頁,就代表歐美人認為京都值得觀光的景點多於日光。若是在同一個地區,例如淺草寺在東京的介紹文裡占了五十行、鹿鳴館的建築只占了五行,則可以合理推論編纂者推薦遊客前往淺草寺更勝於鹿鳴館。有些旅行導覽手冊還會以星號來表示這方面的評價,例如淺草寺三顆星、鹿鳴館零顆星等。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的旅行導覽手冊與現在書店裡陳列的有相當大的差異,如果以現代的概念來想像當時的旅行導覽手冊,可能就太小看當時的外國人對日本所抱持的求知欲及好奇心了。以下舉個例子。
明治三十四年(一九○一)十二月,因日本文部省的命令而在倫敦留學的夏目漱石寫了一封信給正準備動身前往英國留學的茨木清次郎──茨木後來曾歷任東京音樂學校(東京藝術大學的前身)校長與東京外國語學校(東京外國語大學的前身)校長。
他在信中簡單扼要地條列了留學英國的七個建議事項,包含打包行李的重點、怎樣在倫敦尋找住處,以及如何粗估生活費等等,其中有一項是:
「務必隨身帶一本貝德克爾的倫敦導覽手冊。」
那個時代在日本的西洋書店就買得到貝德克爾出版社所出版的一系列旅行導覽手冊,在對西歐有所了解的知識分子之間,「貝德克爾」幾乎已經成了旅行導覽手冊的代名詞。
這封信中的另一個項目提到從日本帶去的東西越少越好,連衣服也只要準備一套,剩下的到那邊再買就行了。換句話說,夏目漱石建議茨木帶到英國的,只有一套衣服以及貝德克爾的旅行導覽手冊。
他在寫給妻子鏡子的信中曾描述倫敦的馬車、鐵路及地下鐵「有如蜘蛛網一般錯綜複雜」,「一個不小心就會迷路,被帶往陌生的地方」。剛到英國的日本人幾乎都會因為搞不清楚方向而迷路,所以必須隨身攜帶一本囊括交通路線圖及介紹文的旅行導覽手冊。貝德克爾的《倫敦》導覽手冊除了簡單明瞭地記載這些資訊,還提供關於倫敦歷史、風俗、氣候及自然的豐富知識,如果不是知識分子,要全部讀通恐怕不容易。既然要到倫敦留學,就得把這些基礎知識記到腦海裡──這應該也是夏目漱石想要傳達給茨木的訊息吧。
現在的日本書店所販售的旅行導覽手冊大多不脫「好玩」、「好吃」的工具書範疇,甚少提及當地的歷史、文化、自然地理、藝術、文學、動植物等相關知識,就算有,往往也只是寥寥數行。但是在昭和末期之前,如果是針對日本國內旅遊的旅行導覽手冊,作者通常是地方上的文史工作者、地方性報紙的文化記者、高中教師或大學教授,因此介紹景點時也會囊括一些歷史知識;如果是針對國外旅遊的旅行導覽手冊,作者則會是在該領域極具權威的大學教授等,這不僅是明治時期以來旅行導覽手冊的特色,同時也承襲了歐美出版社所發行的旅行導覽手冊的傳統。如今在歐美國家所發行的旅行導覽手冊──例如著名的《米其林綠色指南》,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會詳細介紹各景點的歷史及文化。
曾任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館長的歷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在一九六二年的著作中提出了以下看法:
「想要知道在人們的觀念裡『應該觀賞什麼』或『什麼比較重要』,不妨參考旅行導覽手冊。我在前往法國、義大利旅行時,身上總是帶著貝德克爾。」「閱讀貝德克爾讓我樂在其中且獲益良多。」「這些內容非常有趣,而且都是很有用的研究題材。」(《幻影時代──大眾媒體所製造的事實》)
由此可知,即使在歷史學家眼裡,旅行導覽手冊的內容依然具有極高的價值,足以成為研究題材。
3 明治時期外國人心目中的日本景點排名
【比起餐飲,更重視的是如何對付蚊蟲及跳蚤】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薩道義及霍斯所編著的默里旅行導覽手冊第二版的一些內容(以下引用該書的內容皆出自庄田元男譯,《明治日本旅行案內》)。
這本書在介紹各景點之前,首先說明了整趟旅程的注意事項及各種必備知識,閱讀後便能稍微理解當時的外國旅客如何在日本旅行,又會面臨什麼樣的困難。
例如在飲食方面,書中提出了下列注意事項:
「旅客在絕大部分的內陸地區不可能吃得到西式餐點,因此吃不慣當地食物的話就只能自行攜帶糧食。」
另外書中也提到,在內陸的箱根宮之下、日光、京都這些地方,可以透過旅館取得魚肉、雞肉及雞蛋;酒類的話,符合個人口味的葡萄酒並不容易入手,因此最好自備;至於麵包,「如果隨從會烤麵包,那麼當地只要有麵粉就夠了,不難取得能代替烤箱的用具」。
接著又解釋所謂「代替烤箱的用具」,指的就是煮飯的鐵鍋,用鐵鍋代替烤箱製作麵包,這樣的方法可說相當獨特:
「以側面朝下的方式埋入地面,就是相當好用的烤箱代替品。生了火之後,可以用蓋子調節溫度。」
但也提到了以下的注意事項:
「旅宿老闆往往不願意拿他們的廚房用具烹調外國食物,因此要是能攜帶平底鍋及烤網就可以派上用場。」
好心將鐵鍋借給外國客人,對方卻將它埋入地面,旅宿老闆想必會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吧。光看這段敘述,便不難想像會造成多大的文化衝擊。
此外,就算是不排斥日本食物的旅客,書中也建議攜帶一些下面的食物:
「李比希公司的牛肉精、起司、德國的香腸豌豆湯、鹽與芥末、芝加哥的粗鹽醃牛肉、伍斯特醬、罐裝牛奶、培根、餅乾、紅茶與砂糖、果醬。」
另外亦提醒:「蠟燭、燭台、小刀、叉子、湯匙、杯子都是相當方便的隨身必需品,同時別忘了開瓶器及開罐器。」
肉類的部分,書中提到即便在大城鎮同樣很難買到牛肉,就連雞肉也不容易入手,但亦提及;「在主要驛道上的旅宿,應該能夠吃到非常美味的當地食物。」
西歐人的飲食習慣不盡相同,有些人可能會因為吃不慣日本的食物而傷透腦筋,不過薩道義等英國人在吃的方面似乎並不特別講究。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書中幾乎完全沒有提及食物的衛生問題,也只用寥寥數語提醒讀者不要飲用生水:「最好攜帶小型過濾器,有時能派上用場。水田裡的水絕對不要喝。」
事實上就算是日本人,也不太可能會去喝水田裡的水。另一方面,像是溪水、井水,或是東京的神田上水、玉川上水這類自來水,外國人似乎認為在飲用上不會有什麼問題。東京的現代化淨水系統(將水過濾後透過壓力輸送的供水系統)必須要等到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的淀橋淨水場通水後才漸漸開始普及,在此之前,日本人都是喝生水過活。不過就算到了現代,亞洲大部分國家的自來水依然不太適合直接飲用。薩道義在書中並未特別提及食物的衛生問題,可以看出當時日本人提供客人的餐點基本上都算乾淨衛生。
比起飲食衛生,更讓外國人感到困擾的是跳蚤及蚊蟲。伊莎貝拉.博兒在《日本奧地紀行》一書中也曾數次提及旅宿房間太多跳蚤,令人苦惱。《明治日本旅行案內》當然也針對這一點加以提醒:
「千萬別忘了帶基廷牌防蟲粉。每到夏天,旅宿房間裡的榻榻米及相當於床鋪的寢具上必定會有成群的跳蚤,如果沒做好預防措施,恐怕整個晚上難以安眠。最好的做法,就是在睡衣撒上大量防蟲粉,如果跳蚤實在太多,也可以直接撒在身上。在床單底下鋪一層油紙確實有防護效果,但難聞的氣味可能會引發頭痛,而一小塊樟腦有時也能發揮不錯的效用。」
當然若是投宿在箱根、日光等地專門接待外國人的旅店,就不太會有跳蚤問題;至於蚊蟲,外出時自不用說,如果是夏天,就算乾淨衛生的旅店也難以避免。書中介紹到箱根及草津時,一開頭就會提到「(這一帶)蚊蟲很少」,那是因為附近有硫磺溫泉,較不易孳生蚊蟲。這兩處溫泉勝地很早就廣受外國人喜愛,除了距離東京較近、適合避暑,以及溫泉水量豐沛外,旅行導覽手冊上標榜的「蚊蟲很少」,應該也是理由之一。關於這個部分,第三章還會詳述。
《三越誕生:帝國百貨與近代化的夢》
18 家庭相簿──一小時照片/彩色照片/輪轉印刷照片
促使三越吳服店脫胎換骨的要素之一──攝影部成立於一九○七年四月一日。《讀賣新聞》於同年四月十二日的報導〈新郎新娘的攝影棚(三越吳服店的新攝影部)〉中,提到攝影部除了攝影棚,還有化妝室,拍攝費用與「一般相館」無異,不同的是拍攝時能免費租借衣物。三越畢竟是吳服店,提供的服裝種類廣泛,報導提到「除了元祿風格等傳統服飾,還有中國、朝鮮的服裝,和扮裝用的衣物與歌舞伎服裝」。「婚禮」是兩人建立家庭的第一個典禮,也是家庭相簿的起點。當然,不分身分、不論目的,任何人都能來拍照。實際上,在讀賣新聞來採訪的前一天,農業大臣松岡與商工局長森田就已經來拍過照了。
駿河町三越,顧客紛登門,購衣又飽食,攝影棚留影。(劍珍坊)
三越攝影部,看見小倆口,兩人同合影,相簿又添頁。(桃仙坊)
前者在一九○八年一月號《時好》〈川柳〉欄獲選頭獎,描述客人來到三越吳服店買衣服、進餐廳吃午飯,然後在攝影部留下紀念照。對於立志轉型成為百貨公司的三越而言,看到這句川柳想必非常高興吧。後者則收錄於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讀賣新聞》所刊登的〈第四十二屆讀賣川柳會〉,描寫兩人婚後大概是為了紀念日來拍照,令家庭相簿又添了新的一頁。蕉雨生〈照片的故事(二)〉(《時好》,一九○七年)中提及,三越的化妝室裡有鏡子、香水、肥皂、白粉、化妝品與理髮工具,提供顧客自由使用,但也同時提醒讀者白粉塗多了,五官會顯得模糊;口紅塗多了,嘴唇反而會顯黑。
當時一般人還沒有相機,無法自由拍攝感興趣的人事物,因此所謂的家庭相簿,收藏的多是在三越攝影部與照相館所拍攝的紀念照,或是參加活動與旅行時購買的明信片。三越攝影部技師長柴田常吉在〈秋季最適合攝影〉(《三越時刊》,一九○九年九月號)中提到,近年來,社會大眾對攝影的興趣日漸高漲,可說是「攝影界革新」的時代,「嚴肅認真、有禮端正」的照片在大家看來已經過於單調,拍照的姿勢也出現了變化。〈開始銷售東都美女明信片──攝影部的新活動〉(《三越時刊》,一九一○年四月號)一文則表示過往的「明信片風潮」已經退燒,大家不再收集明信片、製作相簿,許多明信片商店因而倒閉。明信片熱潮降溫的其中一項原因,是市面上出現大量粗製濫造的明信片,三越因此推出「美人明信片」,由柴田負責攝影與印刷,並且使用「最新進口」的紙張。
至於紀念照則在一九一○年代前期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第一種變化是「一小時照片」問世,降低了民眾拍照的門檻。《三越》一九一一年八月號的報導〈推出一小時照片──破天荒的速成照片〉中介紹了「一小時照片」是指從拍照、顯影、印相到交給顧客,所有工時合計僅一小時,過往若是委託歐洲知名的「攝影師」在郊外的工房處理後再郵寄給顧客,約莫費時一週。在這之前,如果只有一兩位顧客,三越攝影部通常也能在一小時後交件,但客人一多便無法快速交件,於是進口了新型機器來解決這個問題,顧客拍照後就先去逛街,買完東西後恰好照片也洗好了。要是想將照片寄給遠方的親朋好友,在明信片大小的照片背後寫上地址與留言,貼上郵票,便能投進店裡的郵箱。
右圖收錄於一九一一年九月號的《三越》,影中人是巖谷小波,他在拍照一小時後領取照片,寄給了當時人在箱根的日比翁助。同一期雜誌刊登的報導〈一小時照片大受好評〉便提到一小時照片的服務始於八月一日,當天利用這項服務的顧客多達數十組,他們和巖谷一樣,趁著購物空檔回到攝影部,提筆寫下近況或是在三越拍攝一事,寄給親朋好友。曾有朝鮮牧師觀光團一行共三十五人前來拍照,即便人數眾多,三越依舊能提供空間拍攝團體紀念照,並在一小時後交件。
只是不見得所有人都會選擇拍攝一小時照片。柴田常吉在〈使用一小時照片〉(《三越》,一九一二年五月號)中便提到,許多消費者會期待攝影師發揮「高超技術」,因此傾向選擇一般的攝影方式,例如拍攝相親照的話,講究成果勝於時間,便會選擇一般的攝影方式。儘管如此,一小時照片還是在一個月內賣出了超過四百組,需求主要集中在從外地來到東京的民眾,他們想讓故鄉的親朋好友瞧瞧自己「健健康康的樣子」,於是來到攝影部拍照。另外到了報考官公立學校的季節,學生也會紛紛前來拍照,好把照片貼在報名表上,之後辦理入學手續時也會需要繳交照片。除此之外,更有每個月來拍一小時照片好幾次的「常客」。
一小時照片推出兩個月之後,也就是一九一一年十月一日,三越又推出瞬間攝影的彩色照片。同年十月號的《三越》刊登了行銷廣告宣稱:「過往的奧托克羅姆(Autochrome Lumière)彩色照片顯像技術需時三分鐘,拍照的人必須靜止不動,十分辛苦。本店技師利用一大發明,瞬間便能拍下原本的顏色,得以記錄真實的人物景色,萬無缺失。」彩色照片不受天氣影響,一小時便能顯影印相,雖然不是全新發明,但這樣的瞬間攝影的厲害之處,就在於「剎那間」即可結束。同一期雜誌刊登的另一篇報導〈推出彩色照片〉則強調「想要將真實的『自己』流傳後世,必定需要這種攝影方式」,這是構成「我」這個個人故事的嶄新片段,為家庭相簿增添了前所未有的真實色彩。
隔年一九一二年八月一日,三越再推出輪轉印刷照片。〈推出輪轉印刷照片──以及運用水中屏風〉(《三越》,同年八月號)中,讚賞輪轉印刷照片「是新穎的發明,使用一片感光版便能立刻印出八百張以上的照片」,根據該雜誌刊登的照片可知,這是在長長的紙上印了許多相同的照片。輪轉印刷照片的方便之處是運用在眾人群聚的典禮、宴會與園遊會等場合,大家先集合拍照,等到要回家時便能帶走方才拍攝的團體紀念照。只不過拍照後當然需要把底片送回三越顯影、印相,加上往返會場的時間,通常需要幾個小時。在這期雜誌發行前一個月的七月十九日,三越接受日本橋區委託,印製了一千兩百張照片送給新大橋落成典禮的出席人士,大受好評。至於文章副標題中的「水中屏風」,指的是玻璃做的背景,能讓人雖然在攝影棚,拍起來的效果卻像是站在淺灘上。
一小時照片問世的一年四個月後,也就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七日,三越攝影部又推出了一分鐘照片。右圖《三越》一九一三年一月號的廣告顯示一分鐘照片分為兩種,右邊是立框式,左邊是獎牌式,照片會鑲在金屬製的圓形相框裡。〈一分鐘照片廣受好評〉(《三越》,同年一月號)中介紹這樣的照片是以進口的機器拍攝,尺寸比一般照片小,鮮明的程度卻不相上下。只需一分鐘就能收到相片,這項服務因此大受好評,推出當天就有兩百二十名顧客上門,由於賓客盈門,材料一下子就用光了,所幸又收到了向國外追加下單的材料。雖然照片裝進相框裡就無法收在家庭相簿中,卻能放在桌上或架子上,輕輕鬆鬆為生活空間增添個人畫像。
一分鐘照片在當時蔚為話題,各家報社也爭相報導,例如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七日,《讀賣新聞》的報導標題便是〈一分鐘拍照〉,指出一分鐘照片在歐美大為風行,三越的技師兼攝影部主任泉谷氐一數天前才從柏林塔波公司(Talbot)買來機器與材料。只要拍照後按下機器的按鈕,感光版掉進顯像液箱中,約莫二十到三十秒便能完成顯像。根據〈德國最新流行的照片〉(《三越》,同年十一月號)一文報導,泉谷在七月下旬與妻子一同前往柏林,距離上次拜訪已經過了六年半,在考察柏林攝影界與電影界的現況時發現了一分鐘照片,於是把機器帶回日本。
對於日本的家庭相簿來說,最劃時代的革新或許是一九一三年八月三越開始販賣相機。〈照相機與進口鞋開賣〉(《三越》,同年九月號)一文報導,相機銷售部為業餘攝影師引進了美國伊士曼公司(Eastman)、德國哥茲公司(C.P Goerz)與福倫達公司(Voigtlander)的相機。部分相機──如伊士曼公司推出的柯達(Kodak)相機──體積小到可以放進口袋,至於腳架等配件,提供的是攝影部實際覺得好用的商品,顯影劑與混合鍍層液則由三越獨自調製販賣。同時三越也舉辦攝影比賽,所需的相關用品同樣一應俱全。要是人人都能擁有自己的相機,拍攝喜歡的對象,自行在壁櫥裡的暗室顯像,那麼家庭相簿的存在便會大幅改觀,不同於紀念照與明信片,家庭的歷史與回憶將會透過相機記錄在相紙上,得以反覆翻閱回顧。
第一章 鐵道與近代土產的登場
序章中提過,近世偏好的是不會腐壞、不佔空間的土產,畢竟當時交通尚不發達,將食物或笨重且龐大的物品當成土產並不可行。
而鐵道的出現則為此帶來了革命性的轉變。已有許多研究指出,鐵道不僅改變了社會經濟,對人們的生活型態與時間概念等文化層面也造成了強烈的影響。由於名產與土產兩者和旅行有極為密切的關係,自然也遭受到鐵道帶來的直接衝擊。
本章將探討鐵道這項近代交通設施的出現,使近世以後名產與土產的意義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又如何轉變成符合近代需求的型態。
清河八郎的「土產宅配」
事實上,即使是近世,也並非完全沒有辦法運送笨重又龐大的土產。
安政二年(一八五五),著名的幕末志士清河八郎與母親一同前往西國旅遊,探訪伊勢、東海道、金毘羅、宮島等近世具代表性的名勝古蹟,並將行程詳細記錄在《西遊草》這部遊記中。翻閱《西遊草》會發現,清河非但在旅遊地點購買了陶器、人偶等大量「笨重又龐大的土產」,更直接寄回家鄉,據說運費並不貴,而且這種作法相當普及。現代人常用來寄送土產的宅配服務,或許可說就是源自清河八郎的土產宅配。
不過,清河畢竟是出羽國清川村出身的富裕鄉士,在這趟旅途中他還包下了一整艘船由四國搭往本州,連番的奢侈行徑連諸侯也為之遜色。由此可見,當時要寄送體積龐大的土產回鄉,或許不像現代這般容易。
鐵道開通與名產的演變
鐵道的開通改變了前述狀況,其中最為劃時代的發展,便是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東海道線全線通車。這使得東京到大阪、京都的交通時間大幅縮短,也大大改變了生鮮食品的運送模式。
東海道線全線通車後,人們享有交通之便,早晨在大阪飲酒,晚上就得以享用東京佳餚。因此,今年許多民眾將大阪產的海鰻寄到東京當新年禮物,國內的運輸公司不斷湧進貨物,配送員也極為忙碌。
儘管引文中的情況與本書列舉的土產不在同一個討論範圍,其時的輸送系統其實也無法在當日完成運送,不過東京往返京都與大阪所需的時間大幅縮短,確實可能為食品的贈送與答禮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鐵道的開通也促使新名產誕生。舉例來說,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京都二條到嵯峨之間的京都鐵道開通後,沿線的嵐山、嵯峨野等自古便十分知名的景點,就開始販售「勝花糰子」及「櫻餅」等名產。
勝花糰子據說是模仿隅田川的糰子製作,鐵道開通後來訪的遊客增加,各家業者競相販賣這種糰子,於是成為嵐山的名產之一。櫻餅也是在京都鐵道通車的明治三十年前後由奧村又兵衛開始販賣。兩者都是鐵道開通後新創的名產,但其型態仍保有近世以來的傳統,以當場食用為前提。
明治三十六年(一九○三)京都鐵道發行的沿線旅遊指南中,將勝花糰子與櫻餅放在「美食」單元,看來是以當場食用為前提(土產單元則有櫻樹手杖、竹硯等手工藝品,以及天龍寺納豆、香魚煎餅等便於保存的食品)。當然,其時並非完全沒有食品類土產的需求,只是尚未有證據證明這些食品在保存性與容器包裝上已獲得改良。
以當場食用為前提的名產,不僅銷路有限,業績也難以大幅提升。為了拓展銷售版圖,就必須擴張銷路,並克服保存期限短與攜帶不便等問題,將名產發展為土產。此外,像嵐山這樣歷史悠久的地方,一般都會給名產加上歷史典故,然而,「勝花糰子」與「櫻餅」卻欠缺這些要素,難免給人美中不足的印象。嵐山自古就是知名的賞櫻景點,將商品取名為「勝花糰子」可說韻味十足,只是如今似乎已經銷聲匿跡。可見一項名產能否成為主流,背後確實存在前述的因素。
安倍川餅與醃山葵
東海道不僅連接京都與江戶,也是前往伊勢神宮參拜的必經街道,乃近世主要的交通幹線,沿途曾有許多名產問世,同樣是廣為人知的事實。
其中,安倍川餅自近世開始便是知名的東海道名產。顧名思義,當時的安倍川餅是安倍川畔的茶屋所販售的點心,關於它的起源,則流傳著這麼一段說法:
慶長年間,德川家康赴御用金山井川笹山巡視時,一名男子製作了麻糬進獻。家康詢問這款麻糬的名字,男子假安倍川與金山的金粉答稱「這是安倍川的黃金粉餅」,家康聞言大喜,之後便將這種點心稱為安倍川餅。
安倍川餅自此成為名產,然而明治以降卻隨著東海道線的開通「逐漸沒落,僅餘石部屋一家商店尚在販賣」。
在靜岡車站有一家販售鐵路便當的加藤便當店,店主加藤鶴對這種情況憂心忡忡,便開始在車站內兜售安倍川餅。安倍川餅因此成為靜岡站的名產,甚至只要「列車停靠靜岡站,叫賣『名產安倍川餅』與醃山葵的聲音便此起彼落」。
值得注意的是,改為在靜岡站販賣的安倍川餅與之前銷售的近世東海道名產安倍川餅,並非只有販賣地點不同。
近世以來,安倍川畔的茶屋所販賣的安倍川餅,是撒上黃豆粉的麻糬;至於靜岡站販售的名產安倍川餅,用的其實不是麻糬而是求肥。
求肥是用水溶解白玉粉或餅粉,再加入砂糖、水飴攪拌後製成的一種和菓子材料,主要特徵是口感柔軟,且比一般麻糬的保存期限更長。事實上,近世的麻糬名產之所以能成功轉型成近代土產,求肥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使用求肥製作的安倍川餅一直以來都受到「似是而非的假貨」、「欺騙世人」等批判。然而,安倍川餅原本是以在茶屋現場食用為前提的名產,若要轉型成在車站就能隨手購買的土產,就免不了這番脫胎換骨的過程。
此外,靜岡站還會販賣另一種極具代表性的土產──醃山葵。關於其起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據說最晚在幕末時期就已經有了醃山葵的雛形。不過,基本上在「東海道鐵道開設前,醃山葵並非出奇之物」。
到了明治三○年代,醃山葵已經躋身「鐵道開設以來備受東西往返旅客喜愛的土產,靜岡車站每日銷售盛況驚人,稱得上本市首屈一指的特產」,在靜岡車站內販售,成為醃山葵這項土產大為風行的開端。
明治初期的醃山葵主要由田尻屋製造販賣,鐵道開通之後,小泉樓與田丸屋的商品也加入了站內販售的陣容。其中田丸屋還由壽司桶得到靈感,開發出盛裝醃山葵的桶狀容器,據說「與普通的容器不同,別具雅趣,因而大受讚賞,後來業者也參與各種共進會、博覽會,大大宣傳了一番」。如今,靜岡車站等處有許多商店會販賣田丸屋的醃山葵,可見積極的商品改良與擴大銷路是其主導醃山葵市場的關鍵之一。
《照見日本:從明治到現代,看見與被看見的日本觀光一百五十年史》
2 旅行導覽手冊問世
【知識分子必讀的旅行導覽手冊】
歐美人到底對日本的哪些面向感興趣?想要知道答案,只要看看他們所出版的日本旅行導覽手冊就行了。為了能在日本國內旅行無礙而由歐美人統一蒐集資訊、撰稿、編輯及發行的旅行導覽手冊,打從明治時代前期便已存在,挑選的內容都是歐美人心中認定「值得一看的景點」,在手冊中所占的篇幅比重也就與其價值呈正比。舉例來說,假如一本旅行導覽手冊共三百頁,介紹京都的篇幅占了五十頁、日光占了二十頁,就代表歐美人認為京都值得觀光的景點多於日光。若是在同一個地區,例如淺草寺在東京的介紹文裡占了五十行、鹿鳴館的建築只占了五行,則可以合理推論編纂者推薦遊客前往淺草寺更勝於鹿鳴館。有些旅行導覽手冊還會以星號來表示這方面的評價,例如淺草寺三顆星、鹿鳴館零顆星等。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的旅行導覽手冊與現在書店裡陳列的有相當大的差異,如果以現代的概念來想像當時的旅行導覽手冊,可能就太小看當時的外國人對日本所抱持的求知欲及好奇心了。以下舉個例子。
明治三十四年(一九○一)十二月,因日本文部省的命令而在倫敦留學的夏目漱石寫了一封信給正準備動身前往英國留學的茨木清次郎──茨木後來曾歷任東京音樂學校(東京藝術大學的前身)校長與東京外國語學校(東京外國語大學的前身)校長。
他在信中簡單扼要地條列了留學英國的七個建議事項,包含打包行李的重點、怎樣在倫敦尋找住處,以及如何粗估生活費等等,其中有一項是:
「務必隨身帶一本貝德克爾的倫敦導覽手冊。」
那個時代在日本的西洋書店就買得到貝德克爾出版社所出版的一系列旅行導覽手冊,在對西歐有所了解的知識分子之間,「貝德克爾」幾乎已經成了旅行導覽手冊的代名詞。
這封信中的另一個項目提到從日本帶去的東西越少越好,連衣服也只要準備一套,剩下的到那邊再買就行了。換句話說,夏目漱石建議茨木帶到英國的,只有一套衣服以及貝德克爾的旅行導覽手冊。
他在寫給妻子鏡子的信中曾描述倫敦的馬車、鐵路及地下鐵「有如蜘蛛網一般錯綜複雜」,「一個不小心就會迷路,被帶往陌生的地方」。剛到英國的日本人幾乎都會因為搞不清楚方向而迷路,所以必須隨身攜帶一本囊括交通路線圖及介紹文的旅行導覽手冊。貝德克爾的《倫敦》導覽手冊除了簡單明瞭地記載這些資訊,還提供關於倫敦歷史、風俗、氣候及自然的豐富知識,如果不是知識分子,要全部讀通恐怕不容易。既然要到倫敦留學,就得把這些基礎知識記到腦海裡──這應該也是夏目漱石想要傳達給茨木的訊息吧。
現在的日本書店所販售的旅行導覽手冊大多不脫「好玩」、「好吃」的工具書範疇,甚少提及當地的歷史、文化、自然地理、藝術、文學、動植物等相關知識,就算有,往往也只是寥寥數行。但是在昭和末期之前,如果是針對日本國內旅遊的旅行導覽手冊,作者通常是地方上的文史工作者、地方性報紙的文化記者、高中教師或大學教授,因此介紹景點時也會囊括一些歷史知識;如果是針對國外旅遊的旅行導覽手冊,作者則會是在該領域極具權威的大學教授等,這不僅是明治時期以來旅行導覽手冊的特色,同時也承襲了歐美出版社所發行的旅行導覽手冊的傳統。如今在歐美國家所發行的旅行導覽手冊──例如著名的《米其林綠色指南》,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會詳細介紹各景點的歷史及文化。
曾任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館長的歷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在一九六二年的著作中提出了以下看法:
「想要知道在人們的觀念裡『應該觀賞什麼』或『什麼比較重要』,不妨參考旅行導覽手冊。我在前往法國、義大利旅行時,身上總是帶著貝德克爾。」「閱讀貝德克爾讓我樂在其中且獲益良多。」「這些內容非常有趣,而且都是很有用的研究題材。」(《幻影時代──大眾媒體所製造的事實》)
由此可知,即使在歷史學家眼裡,旅行導覽手冊的內容依然具有極高的價值,足以成為研究題材。
3 明治時期外國人心目中的日本景點排名
【比起餐飲,更重視的是如何對付蚊蟲及跳蚤】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薩道義及霍斯所編著的默里旅行導覽手冊第二版的一些內容(以下引用該書的內容皆出自庄田元男譯,《明治日本旅行案內》)。
這本書在介紹各景點之前,首先說明了整趟旅程的注意事項及各種必備知識,閱讀後便能稍微理解當時的外國旅客如何在日本旅行,又會面臨什麼樣的困難。
例如在飲食方面,書中提出了下列注意事項:
「旅客在絕大部分的內陸地區不可能吃得到西式餐點,因此吃不慣當地食物的話就只能自行攜帶糧食。」
另外書中也提到,在內陸的箱根宮之下、日光、京都這些地方,可以透過旅館取得魚肉、雞肉及雞蛋;酒類的話,符合個人口味的葡萄酒並不容易入手,因此最好自備;至於麵包,「如果隨從會烤麵包,那麼當地只要有麵粉就夠了,不難取得能代替烤箱的用具」。
接著又解釋所謂「代替烤箱的用具」,指的就是煮飯的鐵鍋,用鐵鍋代替烤箱製作麵包,這樣的方法可說相當獨特:
「以側面朝下的方式埋入地面,就是相當好用的烤箱代替品。生了火之後,可以用蓋子調節溫度。」
但也提到了以下的注意事項:
「旅宿老闆往往不願意拿他們的廚房用具烹調外國食物,因此要是能攜帶平底鍋及烤網就可以派上用場。」
好心將鐵鍋借給外國客人,對方卻將它埋入地面,旅宿老闆想必會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吧。光看這段敘述,便不難想像會造成多大的文化衝擊。
此外,就算是不排斥日本食物的旅客,書中也建議攜帶一些下面的食物:
「李比希公司的牛肉精、起司、德國的香腸豌豆湯、鹽與芥末、芝加哥的粗鹽醃牛肉、伍斯特醬、罐裝牛奶、培根、餅乾、紅茶與砂糖、果醬。」
另外亦提醒:「蠟燭、燭台、小刀、叉子、湯匙、杯子都是相當方便的隨身必需品,同時別忘了開瓶器及開罐器。」
肉類的部分,書中提到即便在大城鎮同樣很難買到牛肉,就連雞肉也不容易入手,但亦提及;「在主要驛道上的旅宿,應該能夠吃到非常美味的當地食物。」
西歐人的飲食習慣不盡相同,有些人可能會因為吃不慣日本的食物而傷透腦筋,不過薩道義等英國人在吃的方面似乎並不特別講究。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書中幾乎完全沒有提及食物的衛生問題,也只用寥寥數語提醒讀者不要飲用生水:「最好攜帶小型過濾器,有時能派上用場。水田裡的水絕對不要喝。」
事實上就算是日本人,也不太可能會去喝水田裡的水。另一方面,像是溪水、井水,或是東京的神田上水、玉川上水這類自來水,外國人似乎認為在飲用上不會有什麼問題。東京的現代化淨水系統(將水過濾後透過壓力輸送的供水系統)必須要等到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的淀橋淨水場通水後才漸漸開始普及,在此之前,日本人都是喝生水過活。不過就算到了現代,亞洲大部分國家的自來水依然不太適合直接飲用。薩道義在書中並未特別提及食物的衛生問題,可以看出當時日本人提供客人的餐點基本上都算乾淨衛生。
比起飲食衛生,更讓外國人感到困擾的是跳蚤及蚊蟲。伊莎貝拉.博兒在《日本奧地紀行》一書中也曾數次提及旅宿房間太多跳蚤,令人苦惱。《明治日本旅行案內》當然也針對這一點加以提醒:
「千萬別忘了帶基廷牌防蟲粉。每到夏天,旅宿房間裡的榻榻米及相當於床鋪的寢具上必定會有成群的跳蚤,如果沒做好預防措施,恐怕整個晚上難以安眠。最好的做法,就是在睡衣撒上大量防蟲粉,如果跳蚤實在太多,也可以直接撒在身上。在床單底下鋪一層油紙確實有防護效果,但難聞的氣味可能會引發頭痛,而一小塊樟腦有時也能發揮不錯的效用。」
當然若是投宿在箱根、日光等地專門接待外國人的旅店,就不太會有跳蚤問題;至於蚊蟲,外出時自不用說,如果是夏天,就算乾淨衛生的旅店也難以避免。書中介紹到箱根及草津時,一開頭就會提到「(這一帶)蚊蟲很少」,那是因為附近有硫磺溫泉,較不易孳生蚊蟲。這兩處溫泉勝地很早就廣受外國人喜愛,除了距離東京較近、適合避暑,以及溫泉水量豐沛外,旅行導覽手冊上標榜的「蚊蟲很少」,應該也是理由之一。關於這個部分,第三章還會詳述。
《三越誕生:帝國百貨與近代化的夢》
18 家庭相簿──一小時照片/彩色照片/輪轉印刷照片
促使三越吳服店脫胎換骨的要素之一──攝影部成立於一九○七年四月一日。《讀賣新聞》於同年四月十二日的報導〈新郎新娘的攝影棚(三越吳服店的新攝影部)〉中,提到攝影部除了攝影棚,還有化妝室,拍攝費用與「一般相館」無異,不同的是拍攝時能免費租借衣物。三越畢竟是吳服店,提供的服裝種類廣泛,報導提到「除了元祿風格等傳統服飾,還有中國、朝鮮的服裝,和扮裝用的衣物與歌舞伎服裝」。「婚禮」是兩人建立家庭的第一個典禮,也是家庭相簿的起點。當然,不分身分、不論目的,任何人都能來拍照。實際上,在讀賣新聞來採訪的前一天,農業大臣松岡與商工局長森田就已經來拍過照了。
駿河町三越,顧客紛登門,購衣又飽食,攝影棚留影。(劍珍坊)
三越攝影部,看見小倆口,兩人同合影,相簿又添頁。(桃仙坊)
前者在一九○八年一月號《時好》〈川柳〉欄獲選頭獎,描述客人來到三越吳服店買衣服、進餐廳吃午飯,然後在攝影部留下紀念照。對於立志轉型成為百貨公司的三越而言,看到這句川柳想必非常高興吧。後者則收錄於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讀賣新聞》所刊登的〈第四十二屆讀賣川柳會〉,描寫兩人婚後大概是為了紀念日來拍照,令家庭相簿又添了新的一頁。蕉雨生〈照片的故事(二)〉(《時好》,一九○七年)中提及,三越的化妝室裡有鏡子、香水、肥皂、白粉、化妝品與理髮工具,提供顧客自由使用,但也同時提醒讀者白粉塗多了,五官會顯得模糊;口紅塗多了,嘴唇反而會顯黑。
當時一般人還沒有相機,無法自由拍攝感興趣的人事物,因此所謂的家庭相簿,收藏的多是在三越攝影部與照相館所拍攝的紀念照,或是參加活動與旅行時購買的明信片。三越攝影部技師長柴田常吉在〈秋季最適合攝影〉(《三越時刊》,一九○九年九月號)中提到,近年來,社會大眾對攝影的興趣日漸高漲,可說是「攝影界革新」的時代,「嚴肅認真、有禮端正」的照片在大家看來已經過於單調,拍照的姿勢也出現了變化。〈開始銷售東都美女明信片──攝影部的新活動〉(《三越時刊》,一九一○年四月號)一文則表示過往的「明信片風潮」已經退燒,大家不再收集明信片、製作相簿,許多明信片商店因而倒閉。明信片熱潮降溫的其中一項原因,是市面上出現大量粗製濫造的明信片,三越因此推出「美人明信片」,由柴田負責攝影與印刷,並且使用「最新進口」的紙張。
至於紀念照則在一九一○年代前期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第一種變化是「一小時照片」問世,降低了民眾拍照的門檻。《三越》一九一一年八月號的報導〈推出一小時照片──破天荒的速成照片〉中介紹了「一小時照片」是指從拍照、顯影、印相到交給顧客,所有工時合計僅一小時,過往若是委託歐洲知名的「攝影師」在郊外的工房處理後再郵寄給顧客,約莫費時一週。在這之前,如果只有一兩位顧客,三越攝影部通常也能在一小時後交件,但客人一多便無法快速交件,於是進口了新型機器來解決這個問題,顧客拍照後就先去逛街,買完東西後恰好照片也洗好了。要是想將照片寄給遠方的親朋好友,在明信片大小的照片背後寫上地址與留言,貼上郵票,便能投進店裡的郵箱。
右圖收錄於一九一一年九月號的《三越》,影中人是巖谷小波,他在拍照一小時後領取照片,寄給了當時人在箱根的日比翁助。同一期雜誌刊登的報導〈一小時照片大受好評〉便提到一小時照片的服務始於八月一日,當天利用這項服務的顧客多達數十組,他們和巖谷一樣,趁著購物空檔回到攝影部,提筆寫下近況或是在三越拍攝一事,寄給親朋好友。曾有朝鮮牧師觀光團一行共三十五人前來拍照,即便人數眾多,三越依舊能提供空間拍攝團體紀念照,並在一小時後交件。
只是不見得所有人都會選擇拍攝一小時照片。柴田常吉在〈使用一小時照片〉(《三越》,一九一二年五月號)中便提到,許多消費者會期待攝影師發揮「高超技術」,因此傾向選擇一般的攝影方式,例如拍攝相親照的話,講究成果勝於時間,便會選擇一般的攝影方式。儘管如此,一小時照片還是在一個月內賣出了超過四百組,需求主要集中在從外地來到東京的民眾,他們想讓故鄉的親朋好友瞧瞧自己「健健康康的樣子」,於是來到攝影部拍照。另外到了報考官公立學校的季節,學生也會紛紛前來拍照,好把照片貼在報名表上,之後辦理入學手續時也會需要繳交照片。除此之外,更有每個月來拍一小時照片好幾次的「常客」。
一小時照片推出兩個月之後,也就是一九一一年十月一日,三越又推出瞬間攝影的彩色照片。同年十月號的《三越》刊登了行銷廣告宣稱:「過往的奧托克羅姆(Autochrome Lumière)彩色照片顯像技術需時三分鐘,拍照的人必須靜止不動,十分辛苦。本店技師利用一大發明,瞬間便能拍下原本的顏色,得以記錄真實的人物景色,萬無缺失。」彩色照片不受天氣影響,一小時便能顯影印相,雖然不是全新發明,但這樣的瞬間攝影的厲害之處,就在於「剎那間」即可結束。同一期雜誌刊登的另一篇報導〈推出彩色照片〉則強調「想要將真實的『自己』流傳後世,必定需要這種攝影方式」,這是構成「我」這個個人故事的嶄新片段,為家庭相簿增添了前所未有的真實色彩。
隔年一九一二年八月一日,三越再推出輪轉印刷照片。〈推出輪轉印刷照片──以及運用水中屏風〉(《三越》,同年八月號)中,讚賞輪轉印刷照片「是新穎的發明,使用一片感光版便能立刻印出八百張以上的照片」,根據該雜誌刊登的照片可知,這是在長長的紙上印了許多相同的照片。輪轉印刷照片的方便之處是運用在眾人群聚的典禮、宴會與園遊會等場合,大家先集合拍照,等到要回家時便能帶走方才拍攝的團體紀念照。只不過拍照後當然需要把底片送回三越顯影、印相,加上往返會場的時間,通常需要幾個小時。在這期雜誌發行前一個月的七月十九日,三越接受日本橋區委託,印製了一千兩百張照片送給新大橋落成典禮的出席人士,大受好評。至於文章副標題中的「水中屏風」,指的是玻璃做的背景,能讓人雖然在攝影棚,拍起來的效果卻像是站在淺灘上。
一小時照片問世的一年四個月後,也就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七日,三越攝影部又推出了一分鐘照片。右圖《三越》一九一三年一月號的廣告顯示一分鐘照片分為兩種,右邊是立框式,左邊是獎牌式,照片會鑲在金屬製的圓形相框裡。〈一分鐘照片廣受好評〉(《三越》,同年一月號)中介紹這樣的照片是以進口的機器拍攝,尺寸比一般照片小,鮮明的程度卻不相上下。只需一分鐘就能收到相片,這項服務因此大受好評,推出當天就有兩百二十名顧客上門,由於賓客盈門,材料一下子就用光了,所幸又收到了向國外追加下單的材料。雖然照片裝進相框裡就無法收在家庭相簿中,卻能放在桌上或架子上,輕輕鬆鬆為生活空間增添個人畫像。
一分鐘照片在當時蔚為話題,各家報社也爭相報導,例如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七日,《讀賣新聞》的報導標題便是〈一分鐘拍照〉,指出一分鐘照片在歐美大為風行,三越的技師兼攝影部主任泉谷氐一數天前才從柏林塔波公司(Talbot)買來機器與材料。只要拍照後按下機器的按鈕,感光版掉進顯像液箱中,約莫二十到三十秒便能完成顯像。根據〈德國最新流行的照片〉(《三越》,同年十一月號)一文報導,泉谷在七月下旬與妻子一同前往柏林,距離上次拜訪已經過了六年半,在考察柏林攝影界與電影界的現況時發現了一分鐘照片,於是把機器帶回日本。
對於日本的家庭相簿來說,最劃時代的革新或許是一九一三年八月三越開始販賣相機。〈照相機與進口鞋開賣〉(《三越》,同年九月號)一文報導,相機銷售部為業餘攝影師引進了美國伊士曼公司(Eastman)、德國哥茲公司(C.P Goerz)與福倫達公司(Voigtlander)的相機。部分相機──如伊士曼公司推出的柯達(Kodak)相機──體積小到可以放進口袋,至於腳架等配件,提供的是攝影部實際覺得好用的商品,顯影劑與混合鍍層液則由三越獨自調製販賣。同時三越也舉辦攝影比賽,所需的相關用品同樣一應俱全。要是人人都能擁有自己的相機,拍攝喜歡的對象,自行在壁櫥裡的暗室顯像,那麼家庭相簿的存在便會大幅改觀,不同於紀念照與明信片,家庭的歷史與回憶將會透過相機記錄在相紙上,得以反覆翻閱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