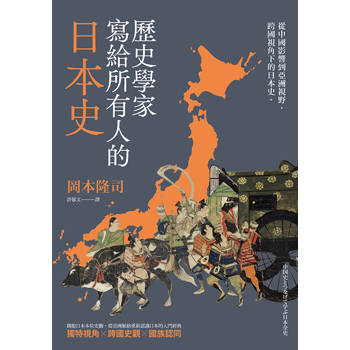從東洋史重新檢視日本史
全球化與「加拉巴哥化」
近年來,「全球化」、「全球主義」這類詞彙幾乎每天都在耳邊出現。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任何國家都必須與全世界接軌、交流與合作。即使有些國家想要奉行孤立主義或是鎖國政策,終究也無法如願。而這種情況,並不只發生在我們日本。
然而,若要問實際上日本的全球化程度有多高,恐怕答案會讓人陷入不安。儘管日本政府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實際上仍有許多方面落後於全球,至今仍未擺脫「加拉巴哥化」的刻板印象。
以上純屬個人觀點,不一定能反映日本的整體情況,不過,對於我最熟悉的學術界,在全球化方面的相關情況,或許我還能進一步提出較為具體且明確的說明。
第一點要提出的是,目前日本學術界的發展方向可說與全球化背道而馳,這點讓人感到憂心。由於學術研究重視獨創性,當然需要所謂的「加拉巴哥化」,也就是讓自己得以「自主演化」的意思。然而,在進入奉全球化主義為圭臬的時代之後,卻讓人不禁懷疑,原本應該發揮原創性的研究者是否已被全球化的浪潮吞噬,導致其研究與相關知識素養也變得平庸與同質化。簡單來說,雖然每個人的描述方式或使用的語言可能不同,但說的卻是差不多的話,甚至根本是相同層次的內容。這種學問一點都不有趣,而且這種換湯不換藥,把大家都已知的事情換個說法來講,根本就不算是學術研究。
若問全球化是否能讓人們擁有更開闊的視野,或是讓研究水準提升至世界的標準,答案當然不是。我發現許多研究領域正逐漸被世界所淘汰,而這就是負面的「加拉巴哥化」。而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或許變質最嚴重的學術領域,就是人文學科。
日本史的研究又如何?
日本史學恐怕也不例外。在爬梳一國歷史時,當然得了解其內部精細的史實,但光是這樣還不夠充分。必須進一步掌握該國與世界關係的變化,或是其對世界造成了哪些影響,這些面向的重要性絲毫不遜於對該國歷史本身的探究。
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內部與外部不是彼此分離的。要想徹底了解內部,便不能忽略與外部的關聯;而若不了解內部,就不可能真正掌握與外部的連結。國家也是一樣,只有同時了解內部與外部,才能知道國家的來龍去脈,以才能真正理解其發展脈絡及當前在國際社會中的定位。
但我發現,現行的日本史研究往往不是如此,總給人一種「以管窺天」的感覺,只將焦點集中在日本這個國家的內部,然後沿著歷史脈絡依序列出「曾經發生過哪些事情」而已。
筆者總覺得,這很像是在讀「履歷表」。任何人之所以能夠在這個世界出生,一定有父母親,也一定有祖先;而他會在學校學習,進入社會後從事某些工作,而在這段過程中,應該都會經歷過各種人際相遇、啟發與轉折。然而「履歷表」上完全不會記載這些內容,只會依序列出「畢業」或「任職」等人生大事,感覺就像這個人順理成章地一步步成長起來。至於履歷表的格式、撰寫方法、題材與內容也幾乎大同小異,趨於平庸,看不到「加拉巴哥化」的獨創性。
市面上的日本史也有同樣的問題,日本這個國家彷彿自古以來就理所當然地存在,各種事件也幾乎都只在國內發生與結束。若以這種方式書寫日本史,誰來寫都差不多,也的確比較容易順應當今全球化的潮流。
話雖如此,要研究日本史當然不能只把焦點放在日本。比方說,在「遣唐使」的歷史之中,就不得不提及中國的唐朝;在探討「元寇」的歷史時,就一定會涉及蒙古這個外國。然而,主題與主語終究還是日本,這些外國通常只被視為跑龍套的配角,很少有人深入外國本身的歷史脈絡,進而重新審視日本的歷史。
如果稍微轉換視角,的確可能從不同的角度來論述「遣唐使」或「元寇」的歷史,但我完全看不到有人真正關注這一點,這正是所謂「加拉巴哥化」的體現。
從本國史進入世界史
話說回來,日本人對「日本」這個國家或是歷史感到興趣,其實也不是什麼太久遠的事情。
若問最古老的史書是哪一本,根據日本東洋史學先驅內藤湖南的說法,應該是鎌倉時代初期的《愚管抄》或南北朝時代的《神皇正統記》。再往前推算的話,應該是《日本書紀》或六國史這類官方史書,但這類史書的刊行動機或關注重點並不相同,因此不包含在這裡討論的範圍內。
這些官方史書主要記載天皇家或相關人士的事蹟,算是宮廷史或王朝史的一種。再往後一點時代的史書,則有知名的水戶光圀著手編撰的《大日本史》,但說到底,這還是模仿中國史書編撰的作品,基本上還是王朝史。只有漢籍,也就是中國的史書,因此當時的日本人還未真正開始思考自身的歷史。
許多日本人開始從現代國家或現代社會的角度思考日本歷史,是在江戶時代中期的「國學」興起之後。另有一說認為,大眾之所以開始對歷史有一定程度的認知,是因為江戶後期的儒學者賴山陽所著的《日本外史》成為暢銷書的緣故。如果這種說法屬實,那麼日本人不過是從兩百多年前才開始關心自己國家的歷史。
進入明治時代之後,日本打著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的口號,企圖轉型為西方式的「nation state」(民族國家)。因此,日本人認為有必要效法西方,建立全體國民共享的國家歷史,也就是所謂的「national history」(國族史)。從此,日本開始發展出「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並依照這套學術體系教導國民歷史,以喚起對集體過去的認同,強化「我們是同一國的國民」的共同意識。
當時的英國有自己的國族史,德國也有屬於自己的國族史。直到今日,歷史學或歷史書寫雖然還是以本國為主,但是當時的歷史學可是毫不避諱地將本國置於敘述核心。因此,從過去到現在,幾乎每個國家的「國族史」都容易流於「自說自話」。畢竟這種書寫方式,本就是寫給「國民想要了解與分享的歷史」。然而,僅止於此難免流於狹隘,更無從掌握本國與外部世界的關聯,以及自身的國際定位,所以我們才需要關注超越本國的歷史,也就是所謂的「世界史」。
「東洋史」的誕生與衰退有何意義?
西方的世界史不僅涵蓋外國史,同時也構成了本國的歷史。比方說,要研究英國史就無法不提及法國史或日耳曼民族史,因為這些國家彼此交織,而且共享基督教信仰與文化背景,因此「西洋史」也就自然包容了各國的本國史,成為一套彼此連結的整體敘述。此外,由於西方列強曾經稱霸世界,所以「西洋史」也就順理成章地延伸為「世界史」。
因此,當西方國家討論本國史時,一定會納入世界史;因此本國史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世界史的一部分。從本國史、「國族史」緩緩過渡到鄰國史、外國史、西洋史,再擴展為世界史。以西方的歷史學而言,光是這樣的結構就已經相當充實。
然而日本的情況卻不是這樣。不管如何深入挖掘日本史,都挖不出宏觀的世界史,就算偶有外國登場,終究還是只會從日本角度加以描述,幾乎不重視對方的客觀脈絡。而在西方版本的「世界史」中,不僅未提及日本,甚至未提及整個東亞。
為此,內藤湖南等人創立了「東洋史學」這門學問。明治時期的日本人本就熟悉漢學,對中國史書與史實有相當理解,因此他們才意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套屬於東洋的「世界史」框架,用來區別以西洋為中心的世界史,藉此重新審視日本,並嘗試建構一個東西合壁的世界史。光是從這一點,不難窺見當時的日本人對於歷史學、世界史與日本史之間的落差有多麼苦惱,也多麼認真地的想要重新探究自身在其中的定位。
尤其是中國作為東亞舉足輕重的存在,不論從空間或時間上來看,若忽略了中國的歷史,就無法理解日本的整體定位。一直以來,中日兩國隔著日本海遙相對峙,不斷地彼此影響,從未斷絕。
如果能透過東洋史學來說明中國與東亞這個歷史世界,就能從這些關聯性中描繪出日本的樣貌,進一步的定位日本在整個世界中的位置。這正是當初許多學者在建構日本歷史學之際的共識。因此當時除了大學之外,在中等教育也設有「東洋史」與「西洋史」兩門課程,並重視它們與日本史之間的銜接。
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兩門課程被整併為「世界史」,導致東亞世界在中等教育中的比重明顯下滑。雖然「東洋史」在大學中勉強存續,如今也幾近崩解,更像是瀕臨絕種的稀有物種。換言之,日本人已慢慢淡忘前人構建的東亞視角,也正在失去連結日本與全世界的關鍵線索。前面提到的「全球化」與「加拉巴哥化」乍看之下互相矛盾,卻恰恰說明了當前日本人以及日本史學的現況。
以日本史的肖像畫為目標
話說回來,「國族史」這種史觀本來就很容易流於只從本國立場解釋自身國家的通病,一方面資料豐富、語言相通,另一方面則是貼近日常生活,充滿各種屬於冷知識的話題,當然更容易理解與引起共鳴。然而反過來說,這種史觀也很容易讓人劃地自限,逃不出自我封閉的象牙塔。
不過,就如「見葉不見樹、見樹不見林」的道理,若是所有注意力都被眼前瑣事與周遭細節所吸引,便容易忽略整體與全局。這種情況在日常生活中算是司空見慣,歷史學也不例外,尤其是日本史,這種傾向更是顯著。
其實這不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早在過去,內藤湖南就曾批評那些眼光短近、不顧外國歷史,只在乎日本國內瑣碎史實的研究者為「低能的國學者」。這種批評固然嚴苛,但是從他作為創立東洋史學者的立場來看,或許是因為自身的學術研究與重要性未能被理解所引發的焦躁與無奈。筆者身為同樣研究東洋史的後輩,實在是深有同感。
日本史不同於西方各國的歷史,背負著難以與世界史接軌的宿命。而鄰近的中國懷抱強烈的「中華意識」,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對其他國家可說是漠不關心。因此,日本史從一開始便由於這種結構上的限制,很難與鄰近的東洋史建立緊密連結,更遑論擴展到廣大無垠的世界史敘事之中了。
換言之,日本人若不付出額外努力,就難以理解中國對日本的觀點,也難以掌握世界對日本的定位。不管是學習日本史、東洋史還是世界史都是一樣的,如果不多提醒自己,不強迫自己跨出舒適圈,就會變得只在意枝微末節的瑣事,「加拉巴哥化」的問題也會變得更嚴重。正因為我們身處全球化的時代,更應該克服上述的「先天障礙」,如果一直停留在「低能」的狀態,就難以真正與世界接軌。
有時候,相較於精緻細膩的自畫像,筆觸粗糙的肖像畫更能準確捕捉模特兒的人物本質。對筆者這樣一位專攻東洋史的研究者而言,要描繪出日本史學者那種精細的歷史圖像,實屬不易。但或許,筆者反而能描繪出他們未曾描繪、或無法描繪的日本史肖像。而本書,正是以這樣一幅肖像畫為目標所完成的。
日本在外國、全世界的眼中是何等樣貌?雙方建立了何種關係?又是如何彼此影響?本書將從這種全球尺度的東洋史、中國史,乃至整體亞洲史為媒介,重新審視日本史的內容,逐步展開論述。乍看之下,這似乎是在繞遠路,但一如前述,這也是日本人避無可避的「先天障礙」吧。
正是透過這樣的嘗試,我們才能從客觀且俯視全局的角度,重新認識並描繪日本的樣貌,並重新審視至今仍存在摩擦的日中、日韓關係,反思過去、展望未來,放眼彼此的未來,這將有助於我們思考日本在未來的世界中應有的姿態與角色。
全球化與「加拉巴哥化」
近年來,「全球化」、「全球主義」這類詞彙幾乎每天都在耳邊出現。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任何國家都必須與全世界接軌、交流與合作。即使有些國家想要奉行孤立主義或是鎖國政策,終究也無法如願。而這種情況,並不只發生在我們日本。
然而,若要問實際上日本的全球化程度有多高,恐怕答案會讓人陷入不安。儘管日本政府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實際上仍有許多方面落後於全球,至今仍未擺脫「加拉巴哥化」的刻板印象。
以上純屬個人觀點,不一定能反映日本的整體情況,不過,對於我最熟悉的學術界,在全球化方面的相關情況,或許我還能進一步提出較為具體且明確的說明。
第一點要提出的是,目前日本學術界的發展方向可說與全球化背道而馳,這點讓人感到憂心。由於學術研究重視獨創性,當然需要所謂的「加拉巴哥化」,也就是讓自己得以「自主演化」的意思。然而,在進入奉全球化主義為圭臬的時代之後,卻讓人不禁懷疑,原本應該發揮原創性的研究者是否已被全球化的浪潮吞噬,導致其研究與相關知識素養也變得平庸與同質化。簡單來說,雖然每個人的描述方式或使用的語言可能不同,但說的卻是差不多的話,甚至根本是相同層次的內容。這種學問一點都不有趣,而且這種換湯不換藥,把大家都已知的事情換個說法來講,根本就不算是學術研究。
若問全球化是否能讓人們擁有更開闊的視野,或是讓研究水準提升至世界的標準,答案當然不是。我發現許多研究領域正逐漸被世界所淘汰,而這就是負面的「加拉巴哥化」。而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或許變質最嚴重的學術領域,就是人文學科。
日本史的研究又如何?
日本史學恐怕也不例外。在爬梳一國歷史時,當然得了解其內部精細的史實,但光是這樣還不夠充分。必須進一步掌握該國與世界關係的變化,或是其對世界造成了哪些影響,這些面向的重要性絲毫不遜於對該國歷史本身的探究。
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內部與外部不是彼此分離的。要想徹底了解內部,便不能忽略與外部的關聯;而若不了解內部,就不可能真正掌握與外部的連結。國家也是一樣,只有同時了解內部與外部,才能知道國家的來龍去脈,以才能真正理解其發展脈絡及當前在國際社會中的定位。
但我發現,現行的日本史研究往往不是如此,總給人一種「以管窺天」的感覺,只將焦點集中在日本這個國家的內部,然後沿著歷史脈絡依序列出「曾經發生過哪些事情」而已。
筆者總覺得,這很像是在讀「履歷表」。任何人之所以能夠在這個世界出生,一定有父母親,也一定有祖先;而他會在學校學習,進入社會後從事某些工作,而在這段過程中,應該都會經歷過各種人際相遇、啟發與轉折。然而「履歷表」上完全不會記載這些內容,只會依序列出「畢業」或「任職」等人生大事,感覺就像這個人順理成章地一步步成長起來。至於履歷表的格式、撰寫方法、題材與內容也幾乎大同小異,趨於平庸,看不到「加拉巴哥化」的獨創性。
市面上的日本史也有同樣的問題,日本這個國家彷彿自古以來就理所當然地存在,各種事件也幾乎都只在國內發生與結束。若以這種方式書寫日本史,誰來寫都差不多,也的確比較容易順應當今全球化的潮流。
話雖如此,要研究日本史當然不能只把焦點放在日本。比方說,在「遣唐使」的歷史之中,就不得不提及中國的唐朝;在探討「元寇」的歷史時,就一定會涉及蒙古這個外國。然而,主題與主語終究還是日本,這些外國通常只被視為跑龍套的配角,很少有人深入外國本身的歷史脈絡,進而重新審視日本的歷史。
如果稍微轉換視角,的確可能從不同的角度來論述「遣唐使」或「元寇」的歷史,但我完全看不到有人真正關注這一點,這正是所謂「加拉巴哥化」的體現。
從本國史進入世界史
話說回來,日本人對「日本」這個國家或是歷史感到興趣,其實也不是什麼太久遠的事情。
若問最古老的史書是哪一本,根據日本東洋史學先驅內藤湖南的說法,應該是鎌倉時代初期的《愚管抄》或南北朝時代的《神皇正統記》。再往前推算的話,應該是《日本書紀》或六國史這類官方史書,但這類史書的刊行動機或關注重點並不相同,因此不包含在這裡討論的範圍內。
這些官方史書主要記載天皇家或相關人士的事蹟,算是宮廷史或王朝史的一種。再往後一點時代的史書,則有知名的水戶光圀著手編撰的《大日本史》,但說到底,這還是模仿中國史書編撰的作品,基本上還是王朝史。只有漢籍,也就是中國的史書,因此當時的日本人還未真正開始思考自身的歷史。
許多日本人開始從現代國家或現代社會的角度思考日本歷史,是在江戶時代中期的「國學」興起之後。另有一說認為,大眾之所以開始對歷史有一定程度的認知,是因為江戶後期的儒學者賴山陽所著的《日本外史》成為暢銷書的緣故。如果這種說法屬實,那麼日本人不過是從兩百多年前才開始關心自己國家的歷史。
進入明治時代之後,日本打著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的口號,企圖轉型為西方式的「nation state」(民族國家)。因此,日本人認為有必要效法西方,建立全體國民共享的國家歷史,也就是所謂的「national history」(國族史)。從此,日本開始發展出「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並依照這套學術體系教導國民歷史,以喚起對集體過去的認同,強化「我們是同一國的國民」的共同意識。
當時的英國有自己的國族史,德國也有屬於自己的國族史。直到今日,歷史學或歷史書寫雖然還是以本國為主,但是當時的歷史學可是毫不避諱地將本國置於敘述核心。因此,從過去到現在,幾乎每個國家的「國族史」都容易流於「自說自話」。畢竟這種書寫方式,本就是寫給「國民想要了解與分享的歷史」。然而,僅止於此難免流於狹隘,更無從掌握本國與外部世界的關聯,以及自身的國際定位,所以我們才需要關注超越本國的歷史,也就是所謂的「世界史」。
「東洋史」的誕生與衰退有何意義?
西方的世界史不僅涵蓋外國史,同時也構成了本國的歷史。比方說,要研究英國史就無法不提及法國史或日耳曼民族史,因為這些國家彼此交織,而且共享基督教信仰與文化背景,因此「西洋史」也就自然包容了各國的本國史,成為一套彼此連結的整體敘述。此外,由於西方列強曾經稱霸世界,所以「西洋史」也就順理成章地延伸為「世界史」。
因此,當西方國家討論本國史時,一定會納入世界史;因此本國史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世界史的一部分。從本國史、「國族史」緩緩過渡到鄰國史、外國史、西洋史,再擴展為世界史。以西方的歷史學而言,光是這樣的結構就已經相當充實。
然而日本的情況卻不是這樣。不管如何深入挖掘日本史,都挖不出宏觀的世界史,就算偶有外國登場,終究還是只會從日本角度加以描述,幾乎不重視對方的客觀脈絡。而在西方版本的「世界史」中,不僅未提及日本,甚至未提及整個東亞。
為此,內藤湖南等人創立了「東洋史學」這門學問。明治時期的日本人本就熟悉漢學,對中國史書與史實有相當理解,因此他們才意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套屬於東洋的「世界史」框架,用來區別以西洋為中心的世界史,藉此重新審視日本,並嘗試建構一個東西合壁的世界史。光是從這一點,不難窺見當時的日本人對於歷史學、世界史與日本史之間的落差有多麼苦惱,也多麼認真地的想要重新探究自身在其中的定位。
尤其是中國作為東亞舉足輕重的存在,不論從空間或時間上來看,若忽略了中國的歷史,就無法理解日本的整體定位。一直以來,中日兩國隔著日本海遙相對峙,不斷地彼此影響,從未斷絕。
如果能透過東洋史學來說明中國與東亞這個歷史世界,就能從這些關聯性中描繪出日本的樣貌,進一步的定位日本在整個世界中的位置。這正是當初許多學者在建構日本歷史學之際的共識。因此當時除了大學之外,在中等教育也設有「東洋史」與「西洋史」兩門課程,並重視它們與日本史之間的銜接。
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兩門課程被整併為「世界史」,導致東亞世界在中等教育中的比重明顯下滑。雖然「東洋史」在大學中勉強存續,如今也幾近崩解,更像是瀕臨絕種的稀有物種。換言之,日本人已慢慢淡忘前人構建的東亞視角,也正在失去連結日本與全世界的關鍵線索。前面提到的「全球化」與「加拉巴哥化」乍看之下互相矛盾,卻恰恰說明了當前日本人以及日本史學的現況。
以日本史的肖像畫為目標
話說回來,「國族史」這種史觀本來就很容易流於只從本國立場解釋自身國家的通病,一方面資料豐富、語言相通,另一方面則是貼近日常生活,充滿各種屬於冷知識的話題,當然更容易理解與引起共鳴。然而反過來說,這種史觀也很容易讓人劃地自限,逃不出自我封閉的象牙塔。
不過,就如「見葉不見樹、見樹不見林」的道理,若是所有注意力都被眼前瑣事與周遭細節所吸引,便容易忽略整體與全局。這種情況在日常生活中算是司空見慣,歷史學也不例外,尤其是日本史,這種傾向更是顯著。
其實這不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早在過去,內藤湖南就曾批評那些眼光短近、不顧外國歷史,只在乎日本國內瑣碎史實的研究者為「低能的國學者」。這種批評固然嚴苛,但是從他作為創立東洋史學者的立場來看,或許是因為自身的學術研究與重要性未能被理解所引發的焦躁與無奈。筆者身為同樣研究東洋史的後輩,實在是深有同感。
日本史不同於西方各國的歷史,背負著難以與世界史接軌的宿命。而鄰近的中國懷抱強烈的「中華意識」,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對其他國家可說是漠不關心。因此,日本史從一開始便由於這種結構上的限制,很難與鄰近的東洋史建立緊密連結,更遑論擴展到廣大無垠的世界史敘事之中了。
換言之,日本人若不付出額外努力,就難以理解中國對日本的觀點,也難以掌握世界對日本的定位。不管是學習日本史、東洋史還是世界史都是一樣的,如果不多提醒自己,不強迫自己跨出舒適圈,就會變得只在意枝微末節的瑣事,「加拉巴哥化」的問題也會變得更嚴重。正因為我們身處全球化的時代,更應該克服上述的「先天障礙」,如果一直停留在「低能」的狀態,就難以真正與世界接軌。
有時候,相較於精緻細膩的自畫像,筆觸粗糙的肖像畫更能準確捕捉模特兒的人物本質。對筆者這樣一位專攻東洋史的研究者而言,要描繪出日本史學者那種精細的歷史圖像,實屬不易。但或許,筆者反而能描繪出他們未曾描繪、或無法描繪的日本史肖像。而本書,正是以這樣一幅肖像畫為目標所完成的。
日本在外國、全世界的眼中是何等樣貌?雙方建立了何種關係?又是如何彼此影響?本書將從這種全球尺度的東洋史、中國史,乃至整體亞洲史為媒介,重新審視日本史的內容,逐步展開論述。乍看之下,這似乎是在繞遠路,但一如前述,這也是日本人避無可避的「先天障礙」吧。
正是透過這樣的嘗試,我們才能從客觀且俯視全局的角度,重新認識並描繪日本的樣貌,並重新審視至今仍存在摩擦的日中、日韓關係,反思過去、展望未來,放眼彼此的未來,這將有助於我們思考日本在未來的世界中應有的姿態與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