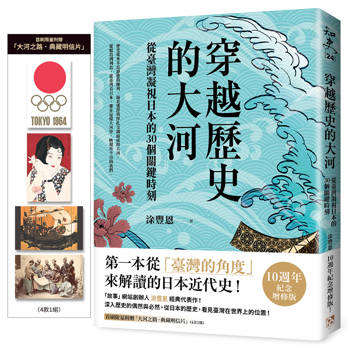三都
江戶、大阪與京都
如果活在德川時代,身為「江戶人」會是件光榮的事吧。
一六○○年,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中擊敗了對手,從此大權在握。三年之後,他選擇江戶做為執政的地點,在此地建立了幕府。儘管天皇還居住在京都,但所有重要的政策由幕府決定,江戶也成為實質上的政治首都。住在江戶,等於就是首善之都的居民。
不過,根據德川時代的說法,只有雙親都是出身江戶之人,才有資格稱得上是「江戶之子」。如果父母是從外地來的,就只能被稱之為「田舍子」;假如雙親只有一方是江戶人,則被稱之為「斑」。而真正的江戶之子,實際上只佔了人口的十分之一,反而是田舍子的人數高達了六成。但或許正因為人數稀少,江戶之子的身分才更加顯得稀罕。
江戶就是今天的東京。一八六八年日本經歷明治維新,天皇從京都遷居到此地,江戶才改名為東京。但早在德川時代,江戶就已經是日本的第一大都市,德川時代也因此經常被稱為江戶時代。
德川幕府上臺之後,日本經歷了一段天下太平的日子,沒有戰亂騷擾,經濟蓬勃發展,人口也隨之增加。到了十八世紀,江戶人口數估計已經超過了一百萬,和同一時間的北京不相上下,名列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巨大都市。同一時間的倫敦,人口大約只有六十萬,而巴黎只有五十萬。
當然,那個時代並沒有人口普查的機制,這些數字都是歷史學者推算出來的,並不見得精準,學者間也存在不同意見。但是江戶人口眾多這件事,倒是無庸置疑。因為人口爆炸,德川時代的江戶人已經感受到生活空間的狹小──跟今天東京人的煩惱一樣。
不過,德川家康上臺時,江戶不過是關東地區的一個小漁村。從十七世紀開始,它才開始成長、擴張,逐漸變成了德川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中心。
當時的日本,除了德川幕府能直接控制的勢力範圍之外,各地由兩百多個地方領主分別統治著。這些領主被稱之為「大名」,他們的領土則稱之為「藩」。大名擁有自己的軍事勢力,和德川幕府之間形成了微妙的關係。有些大名與幕府的關係良好,甚至就是德川家族的親屬,但是,並非所有大名都是如此。
如果大名的勢力太大,又對幕府缺乏忠誠,很可能會對中央政權形成威脅。雖然如此,江戶幕府並沒有因此打算要消滅這些大名。他們採取了另外一套方式穩固政權,也就是所謂的「參勤交代」。
按照這項制度,大名每隔一年必須到江戶定居。身為地方領袖的大名,當然不可能獨自行動,而是攜家帶眷,連同家中的武士和僕人,一同帶到江戶。有時同行的人數高達幾百人,甚至上千人,光是旅費就花去不少錢。
這還沒算在江戶安頓所需要的開銷。大名終究是國內的一方之霸,他們在江戶的居所也不能夠寒酸。勢力比較小的大名,居住的地方都至少有兩千坪,至於勢力大的大名,宅院的面積更超過十萬坪,其中所需要的花費可想而知。也因此,參勤交代為大名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但從幕府的角度看來,參勤交代讓他們得以就近監督大名,讓這些盤據一方的地方領袖不敢搗亂,同時還可以塑造自己高高在上的形象,一舉數得。
除了鞏固德川的政權外,參勤交代也有一些意外的結果。比如,各地的文化隨著大名的隊伍流入江戶,促進了日本國內的文化交流。此外,因為跟著大名來到江戶的,大多是擔任武士的男性,結果讓江戶裡頭的男性人口遠遠高於女性。
現代日本有所謂「單身赴任」的說法,也就是男性上班族因為工作所需,必須離開家庭,一個人到外地工作。德川時代來到江戶的武士們,跟這種情況有幾分類似,因而被一些人喻為單身赴任的前身。
江戶除了做為政治權力的核心所在,在交通與商業發展上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德川家康上臺之後,幕府修築了五條重要交通要道,起點都是江戶,因而形成了一個以它為中心、向外發散的交通網絡。
五條要道中,有兩條通往天皇所在的京都,分別是東海道與中山道。前者從江戶出發後往南走,沿著海岸線往西;後者從江戶出發後往北走,途中則經過內陸的山區,最後抵達京都。至於另外三條,則以路線的終點命名,分別稱為甲州街道、奧州街道和日光街道。
整頓後的交通幹道,不僅可以讓大名前往江戶,讓商人運送貨物,還可以讓小老百姓到各地旅行。在這五條幹道中,東海道因為沿途風光明媚,所以格外出名,成為旅行的代名詞,也刺激出不少藝術創作。
德川時代就有位作家十返舎一九寫了名為《東海道中膝栗毛》的作品,描寫在東海道上旅行的故事,內容趣味滑稽,大受讀者歡迎,結果一連出了好幾個續集,許多模仿之作也紛紛出爐。「栗毛」指的是馬,而「膝栗毛」則是用膝蓋代替馬匹,「東海道中膝栗毛」,也就是用雙腳徒步旅行東海道。
徒步旅行畢竟辛苦,幸好,當時在東海道已經設置有休息站,總共五十三個,被稱之為「東海道五十三次」,可以讓旅行者暫時歇息。
但德川時代的旅行者不能說走就走,而是必須先向地方領主申請許可,告知遠行的原因,得到同意後才能出發。當時最流行的理由,是要到各地的寺院參拜,最受歡迎的路線,則是巡迴四國地區的八十八間寺院──一直到今天都還是著名的觀光旅程。因為信徒人數眾多,市面上甚至出現了專門的導覽手冊。在這種風氣下,與旅遊相關的行業,也跟著發達了起來。
除了陸路之外,水路在德川時代也很重要。儘管幕府禁止一般船隻出海,但沿著海岸線,商船已經可以航行到國內各地,十分便利,幕府上臺之後也特別針對水運加以整頓。
有了完備的交通建設,商品流通就更加容易。當時的日本,已經有了名產或特產的概念,每個地方按照自然環境或文化傳統,生產不同的商品。比如位於關西的龍野,以釀醬油出名;姬路的棉布在市場上名氣特別響亮;至於說到日常生活必用的鹽,則大多出自瀨戶內海一帶。這眾多名產當中,有許多到今天還是地方的代表性商品。
至於人口眾多的江戶,吸納了來自各地的商品,就成為全國最大的消費市場。
在江戶日益興盛的同時,日本有另外一座都市也正在崛起,那就是位於關西的大阪。大阪的人口比不上江戶,但也聚集了數十萬人,遠遠超過德川時代的其他都市,就算放在世界平臺上比較,也稱得上是座大城市。
不過,大阪與江戶的「性格」很不一樣。
大阪原本是豐臣秀吉的根據地,他在這裡興建了一座富麗雄偉的城堡,有學者推算,如果按照今天物價,這座城堡造價將高達七百八十五億日圓。十六世紀的大阪,一開始就是圍繞著這座昂貴的城堡發展起來。只是,後來德川家康打敗了豐臣秀吉,城堡不幸在戰火中燒毀。之後,政治中心轉移到江戶,大阪更失去了原本的地位。
但危機也是轉機,遠離權力中心的大阪,在這之後改頭換面,以另一種姿態重新登上歷史舞臺。因為交通便利,大阪成為了全國的物流中心、最大的商品轉運站,各種生活必需品都會在此地匯聚、合流,再運送到其他地方。少了政治的紛擾,大阪變成了一座屬於商人、充滿自由與活力的都市。
大阪的興起,有賴於水運發達。除了天然的河流外,大阪內部開鑿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運河和水道,交錯縱橫,將整座城市變為水都。因為水道眾多,橋梁也成為了大阪的特色,因而出現了所謂「大阪八百八橋」的說法,相對於江戶的八百八町。
這些水道與橋梁很多已經消失了,但有些還在,比如今日繁華的觀光景點道頓崛,就是德川時代開通的運河之一。道頓崛附近的日本橋,也可以追溯到同樣的時代,不過最原始的橋梁已經不復見,只有名稱保留了下來。
在這些水道交會的地方,漸漸出現了大型的交易場所,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堂島米市場、天滿青菜市場,和雜喉場魚市場──從名稱中不難看出,其中所交易的都是人們日常飲食的必需品。
相較於江戶與大阪的崛起,曾經長期做為日本政治中心的京都,在德川時代似乎喪失了原本的重要性。不過,這座位於天皇腳下的城市,依然有著與眾不同的象徵意義。比如,江戶人前往京都,會說自己到了「上方」,「上方文化」也成為精緻文化的代名詞。
此外,京都聚集了許多貴族,和平民居住的江戶和大阪相比,生活氛圍還是不同。京都所出產的商品,也以其高品質而聞名。比如京都西陣一帶出產的織品,儘管價格昂貴,還是受到了許多有錢人的歡迎,直到今天,西陣織依然是日本傳統工藝品的卓越代表。
德川時代有位名叫廣賴旭莊的學者,曾經以簡潔的方式,點出了京都、大阪與江戶之間的差異,他說:「京都人細膩,大阪人貪婪,江戶人浮誇。」又說:「京都之人多矜氣,重土地;大阪之人多殺氣,重財富;江戶之人多客氣,重官職。」
不過,或許正是因為性格截然不同,這三座都市才能夠以各自的姿態,引領著時代的風騷。德川時代的經濟與文化,就在這些大城市的帶領下,像繁花一般盛開著。
江戶、大阪與京都
如果活在德川時代,身為「江戶人」會是件光榮的事吧。
一六○○年,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中擊敗了對手,從此大權在握。三年之後,他選擇江戶做為執政的地點,在此地建立了幕府。儘管天皇還居住在京都,但所有重要的政策由幕府決定,江戶也成為實質上的政治首都。住在江戶,等於就是首善之都的居民。
不過,根據德川時代的說法,只有雙親都是出身江戶之人,才有資格稱得上是「江戶之子」。如果父母是從外地來的,就只能被稱之為「田舍子」;假如雙親只有一方是江戶人,則被稱之為「斑」。而真正的江戶之子,實際上只佔了人口的十分之一,反而是田舍子的人數高達了六成。但或許正因為人數稀少,江戶之子的身分才更加顯得稀罕。
江戶就是今天的東京。一八六八年日本經歷明治維新,天皇從京都遷居到此地,江戶才改名為東京。但早在德川時代,江戶就已經是日本的第一大都市,德川時代也因此經常被稱為江戶時代。
德川幕府上臺之後,日本經歷了一段天下太平的日子,沒有戰亂騷擾,經濟蓬勃發展,人口也隨之增加。到了十八世紀,江戶人口數估計已經超過了一百萬,和同一時間的北京不相上下,名列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巨大都市。同一時間的倫敦,人口大約只有六十萬,而巴黎只有五十萬。
當然,那個時代並沒有人口普查的機制,這些數字都是歷史學者推算出來的,並不見得精準,學者間也存在不同意見。但是江戶人口眾多這件事,倒是無庸置疑。因為人口爆炸,德川時代的江戶人已經感受到生活空間的狹小──跟今天東京人的煩惱一樣。
不過,德川家康上臺時,江戶不過是關東地區的一個小漁村。從十七世紀開始,它才開始成長、擴張,逐漸變成了德川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中心。
當時的日本,除了德川幕府能直接控制的勢力範圍之外,各地由兩百多個地方領主分別統治著。這些領主被稱之為「大名」,他們的領土則稱之為「藩」。大名擁有自己的軍事勢力,和德川幕府之間形成了微妙的關係。有些大名與幕府的關係良好,甚至就是德川家族的親屬,但是,並非所有大名都是如此。
如果大名的勢力太大,又對幕府缺乏忠誠,很可能會對中央政權形成威脅。雖然如此,江戶幕府並沒有因此打算要消滅這些大名。他們採取了另外一套方式穩固政權,也就是所謂的「參勤交代」。
按照這項制度,大名每隔一年必須到江戶定居。身為地方領袖的大名,當然不可能獨自行動,而是攜家帶眷,連同家中的武士和僕人,一同帶到江戶。有時同行的人數高達幾百人,甚至上千人,光是旅費就花去不少錢。
這還沒算在江戶安頓所需要的開銷。大名終究是國內的一方之霸,他們在江戶的居所也不能夠寒酸。勢力比較小的大名,居住的地方都至少有兩千坪,至於勢力大的大名,宅院的面積更超過十萬坪,其中所需要的花費可想而知。也因此,參勤交代為大名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但從幕府的角度看來,參勤交代讓他們得以就近監督大名,讓這些盤據一方的地方領袖不敢搗亂,同時還可以塑造自己高高在上的形象,一舉數得。
除了鞏固德川的政權外,參勤交代也有一些意外的結果。比如,各地的文化隨著大名的隊伍流入江戶,促進了日本國內的文化交流。此外,因為跟著大名來到江戶的,大多是擔任武士的男性,結果讓江戶裡頭的男性人口遠遠高於女性。
現代日本有所謂「單身赴任」的說法,也就是男性上班族因為工作所需,必須離開家庭,一個人到外地工作。德川時代來到江戶的武士們,跟這種情況有幾分類似,因而被一些人喻為單身赴任的前身。
江戶除了做為政治權力的核心所在,在交通與商業發展上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德川家康上臺之後,幕府修築了五條重要交通要道,起點都是江戶,因而形成了一個以它為中心、向外發散的交通網絡。
五條要道中,有兩條通往天皇所在的京都,分別是東海道與中山道。前者從江戶出發後往南走,沿著海岸線往西;後者從江戶出發後往北走,途中則經過內陸的山區,最後抵達京都。至於另外三條,則以路線的終點命名,分別稱為甲州街道、奧州街道和日光街道。
整頓後的交通幹道,不僅可以讓大名前往江戶,讓商人運送貨物,還可以讓小老百姓到各地旅行。在這五條幹道中,東海道因為沿途風光明媚,所以格外出名,成為旅行的代名詞,也刺激出不少藝術創作。
德川時代就有位作家十返舎一九寫了名為《東海道中膝栗毛》的作品,描寫在東海道上旅行的故事,內容趣味滑稽,大受讀者歡迎,結果一連出了好幾個續集,許多模仿之作也紛紛出爐。「栗毛」指的是馬,而「膝栗毛」則是用膝蓋代替馬匹,「東海道中膝栗毛」,也就是用雙腳徒步旅行東海道。
徒步旅行畢竟辛苦,幸好,當時在東海道已經設置有休息站,總共五十三個,被稱之為「東海道五十三次」,可以讓旅行者暫時歇息。
但德川時代的旅行者不能說走就走,而是必須先向地方領主申請許可,告知遠行的原因,得到同意後才能出發。當時最流行的理由,是要到各地的寺院參拜,最受歡迎的路線,則是巡迴四國地區的八十八間寺院──一直到今天都還是著名的觀光旅程。因為信徒人數眾多,市面上甚至出現了專門的導覽手冊。在這種風氣下,與旅遊相關的行業,也跟著發達了起來。
除了陸路之外,水路在德川時代也很重要。儘管幕府禁止一般船隻出海,但沿著海岸線,商船已經可以航行到國內各地,十分便利,幕府上臺之後也特別針對水運加以整頓。
有了完備的交通建設,商品流通就更加容易。當時的日本,已經有了名產或特產的概念,每個地方按照自然環境或文化傳統,生產不同的商品。比如位於關西的龍野,以釀醬油出名;姬路的棉布在市場上名氣特別響亮;至於說到日常生活必用的鹽,則大多出自瀨戶內海一帶。這眾多名產當中,有許多到今天還是地方的代表性商品。
至於人口眾多的江戶,吸納了來自各地的商品,就成為全國最大的消費市場。
在江戶日益興盛的同時,日本有另外一座都市也正在崛起,那就是位於關西的大阪。大阪的人口比不上江戶,但也聚集了數十萬人,遠遠超過德川時代的其他都市,就算放在世界平臺上比較,也稱得上是座大城市。
不過,大阪與江戶的「性格」很不一樣。
大阪原本是豐臣秀吉的根據地,他在這裡興建了一座富麗雄偉的城堡,有學者推算,如果按照今天物價,這座城堡造價將高達七百八十五億日圓。十六世紀的大阪,一開始就是圍繞著這座昂貴的城堡發展起來。只是,後來德川家康打敗了豐臣秀吉,城堡不幸在戰火中燒毀。之後,政治中心轉移到江戶,大阪更失去了原本的地位。
但危機也是轉機,遠離權力中心的大阪,在這之後改頭換面,以另一種姿態重新登上歷史舞臺。因為交通便利,大阪成為了全國的物流中心、最大的商品轉運站,各種生活必需品都會在此地匯聚、合流,再運送到其他地方。少了政治的紛擾,大阪變成了一座屬於商人、充滿自由與活力的都市。
大阪的興起,有賴於水運發達。除了天然的河流外,大阪內部開鑿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運河和水道,交錯縱橫,將整座城市變為水都。因為水道眾多,橋梁也成為了大阪的特色,因而出現了所謂「大阪八百八橋」的說法,相對於江戶的八百八町。
這些水道與橋梁很多已經消失了,但有些還在,比如今日繁華的觀光景點道頓崛,就是德川時代開通的運河之一。道頓崛附近的日本橋,也可以追溯到同樣的時代,不過最原始的橋梁已經不復見,只有名稱保留了下來。
在這些水道交會的地方,漸漸出現了大型的交易場所,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堂島米市場、天滿青菜市場,和雜喉場魚市場──從名稱中不難看出,其中所交易的都是人們日常飲食的必需品。
相較於江戶與大阪的崛起,曾經長期做為日本政治中心的京都,在德川時代似乎喪失了原本的重要性。不過,這座位於天皇腳下的城市,依然有著與眾不同的象徵意義。比如,江戶人前往京都,會說自己到了「上方」,「上方文化」也成為精緻文化的代名詞。
此外,京都聚集了許多貴族,和平民居住的江戶和大阪相比,生活氛圍還是不同。京都所出產的商品,也以其高品質而聞名。比如京都西陣一帶出產的織品,儘管價格昂貴,還是受到了許多有錢人的歡迎,直到今天,西陣織依然是日本傳統工藝品的卓越代表。
德川時代有位名叫廣賴旭莊的學者,曾經以簡潔的方式,點出了京都、大阪與江戶之間的差異,他說:「京都人細膩,大阪人貪婪,江戶人浮誇。」又說:「京都之人多矜氣,重土地;大阪之人多殺氣,重財富;江戶之人多客氣,重官職。」
不過,或許正是因為性格截然不同,這三座都市才能夠以各自的姿態,引領著時代的風騷。德川時代的經濟與文化,就在這些大城市的帶領下,像繁花一般盛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