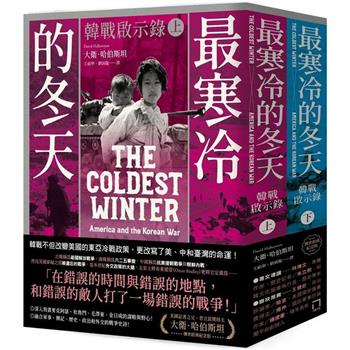試閱文章1:〈登陸仁川,攻克漢城〉
在仁川戰役中,麥帥可謂吉星高照,因為他的對手金日成絕對稱不上足智多謀。不知基於何種原因,對於美軍會在北韓大軍後方進行兩棲登陸這個說法,金日成根本就不以為然。但在仁川計畫實施前,北京就已經注意到大批美軍在日本集結。在一九四○年代末到五○年代初,日本對外國間諜活動不設防,各個港口的安全防衛形同虛設,加上日本的碼頭工人中有很多都是忠誠的共產黨員,因此中國早就得到風聲,知道這裡的許多裝備都是用來進行兩棲登陸的。早在八月初,毛澤東就為北韓進攻南方而憂心忡忡。金日成曾誇下海口說自己能迅速攻克南方,但是這個目標並沒有實現。毛澤東知道,從八月末到九月初,雖然美軍一直在加強對釜山的防禦,卻在日本保留了兩個師的精銳部隊,並進行兩棲登陸演練。顯然是有什麼大事即將發生。在毛澤東的一生中,敵人總是有更強大的武裝力量與軍事裝備,因此戰略戰術對他來說特別關鍵。中共軍隊只能避實就虛,為隨時隨地與外界斷絕一切聯繫來保存實力。毛澤東非常重視眼前發生的事,以及他預感即將發生的事。
八月初,也就是仁川登陸之前,他派自己的得力部將、同時也是周恩來的軍事祕書雷英夫進行研究,看看美國人在搞什麼名堂。這是一次徹底的軍事情報行動。這些中國的軍情人員認為這裡的情況顯而易見。不少美國軍人正在進行兩棲登陸的演練,日本的許多港口也都停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美軍與聯合國軍艦。之前在太平洋戰場上,麥帥曾不只一次採取兩棲登陸的戰術。雷英夫在認真推敲所有相關情報後認定,美國人已經為北韓軍布下天羅地網。他們準備出其不意在北韓軍的後方登陸。他相信,美軍不只是準備衝破釜山包圍圈,還準備利用兩棲登陸的戰術一舉打垮北韓的主力部隊。雷英夫仔細研究了地圖,並試圖按美國人的方式思考他們的行動。以麥克阿瑟野心勃勃的個性來看,在六個有可能進行兩棲攻擊的港口中,他極有可能選擇仁川。八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北韓軍最後一次進逼洛東江之前的一週(這個日子恰好也是麥帥在東京盟總進行精采絕倫表演的同一天),雷英夫向周恩來報告了自己的調查結果。周恩來聞訊大吃一驚,並立刻將這訊息轉告毛澤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雷英夫對這件事進行了一次極為詳細的匯報,並提交一份三頁有關麥帥生平、思維方式、性格特徵及慣用戰術的備忘錄。於是,毛澤東讓周恩來向金日成轉達美軍可能在仁川登陸的消息。同時,北韓的一些蘇聯顧問也提出了同樣的警告,但是金日成卻不以為然。這並不奇怪,因為他本來就不是在戰場上取得天下,而是依靠在殘酷的政治環境中艱難求生的能力以及對蘇聯人的態度。金日成能上臺執政,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蘇聯紅軍對他的慷慨幫助。因此,他奪權的方式與毛澤東和胡志明截然不同。
毛澤東根據自己的推測確信,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角色即將發生變化。北韓進攻的日子在八月中旬達到巔峰。八月十九日與二十三日,他兩度告訴蘇聯駐華大使帕維爾.尤金,如果美軍繼續向南韓增兵,那麼北韓軍很有可能會支撐不住,轉而向中國求助。八月末到九月初,毛澤東又數度會見北韓駐華代表李相祖。毛澤東歷數了北韓軍因為沒有聽從自己的建議而犯下的錯誤,以及遭遇的一次次失敗。例如,他們準備在如此寬廣的戰線上作戰時卻沒有足夠的預備隊;他們過度注重攻占城鎮,卻沒有對敵軍窮追不捨。此外,毛澤東還提到,在金浦這樣的地方建設空軍基地簡直不堪一擊,因此北韓應從這些難以防守的地方撤退並加強防禦。他甚至指著地圖對李相祖說,仁川是最有可能遭到攻擊的目標。然而出乎中國人意料的是,金日成對此滿不在乎,沒有在仁川港布雷。
中國很清楚前線正在發生的大事,但是北韓領導卻渾然不覺。在極權主義制度下,最大的問題就是壞消息很難從前線準確地傳回大後方。儘管民主國家同樣會發生類似的事,但是這一點在階級制度格外森嚴的北韓尤其明顯。不利的消息往往會在傳播過程中逐漸變成有利的訊息。因此,九月四日,當毛澤東的特使柴成文告訴金日成,戰事已經在釜山地區陷入僵持狀態時,這位北韓領導人並不相信。他告訴中國代表,他的重大攻勢才剛剛開始,勢必能迅速打破僵局。柴成文又提到,美軍可能會在北韓後方發動襲擊,但是金日成回答:「據我們估計,現在美軍不可能進行反攻。他們沒有足夠的兵力增援,更不用說在我們後方登陸。」十分詫異的柴成文在九月十日,也就是仁川登陸五天前回到了北京,但是隨即又返回平壤。周恩來讓柴成文轉告金日成,希望他能做戰略性撤退。「我從不考慮撤退。」金日成回答。周恩來對這個答覆十分不快。美軍幾乎是在毫無阻礙的情況下實施了仁川登陸計畫。三天後,即九月十八日,周恩來會見了蘇聯代表,再次建議北韓軍撤退到北方進行重組,並向西方國家宣稱中國或蘇聯會參戰。
※
一萬三千名美軍官兵穿越海堤與碼頭登陸,隨後向漢城迅速推進,這一切完全依麥帥預定的情況發展,完美得令人難以置信。作戰狀況出人意料地極為有利,美軍幾乎沒有遭遇任何抵抗。從地形看來,仁川港就像是半截大拇指一樣向外突出,往東大約十英里就是金浦機場,如果一切順利,從金浦再往東大約五、六英里就是漢城。第一陸戰團和第七團將首先拿下仁川,接著攻克金浦,然後向東越過漢江直搗漢城。這麼一來,他們很快就能與華克的第八軍團取得聯繫,後者屆時將突破洛東江包圍圈,迅速揮師北進。
一開始,陸戰隊的傷亡很小:在月尾島一戰中沒有人員傷亡,隨即打開了港口;在開戰的第一天,美軍只有二十名士兵陣亡。但是隨著聯合國軍不斷逼近漢城,北韓也加強了抵禦。同時,第十軍軍長阿爾蒙德與屬下第一陸戰師師長史密斯之間的摩擦也越演越烈。阿爾蒙德主張不惜一切代價速戰速決,而史密斯則認為,在這場愈發艱難的戰役中,海軍陸戰隊應避免無謂的犧牲。史密斯(以及陸戰隊大多數的將領)逐漸意識到,阿爾蒙德是不顧現實條件的指揮官,除了聽命於自己的上司,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指揮正確與否,也不在乎手下將士的存亡安危,更不用說聽取他人的意見了。這就為他們日後的各自為政埋下了禍根。從一開始,陸戰隊將官就覺得,毫無兩棲登陸經驗的阿爾蒙德不僅刻意忽略美軍可能遭遇的危險與困難,而且對自己的下級軍官及其需要置若罔聞。阿爾蒙德和史密斯本來就是兩種人:前者目空一切、剛愎自用;後者踏踏實實、低調敬業(事實上,史密斯還有個綽號叫「教授」,不過沒有人敢當面這麼稱呼他)。他們的摩擦也反映陸軍與陸戰隊本質的不同。陸軍規模龐大,所以陸軍將領與部下的關係往往異常疏離;陸戰隊規模較小,因此軍官與部下之間非常親密、感情很深。此外,史密斯比一般的陸戰隊將領更小心謹慎。一九四四年十月,當第一陸戰師在貝里琉登陸時,史密斯是副師長。那是太平洋戰場上最殘酷、代價最高的戰役之一。因為重大情報失誤,陸戰隊在登陸時才發現敵我力量的差距極為懸殊,自己即將面對的是九千多名在掩體裡嚴陣以待的日軍士兵。可以說,這麼一次遭遇可以永遠改變一個人的性格。
如果說這些將領從一開始就不和,那麼隨著戰爭的展開,他們的關係就更四分五裂了。他們之間的夙怨,借用陸戰隊歷史專家愛德溫.西蒙斯(Edwin Simmons)的話來說,可謂「一言難盡」。西蒙斯曾經是陸戰隊軍官,參加過仁川登陸與長津湖戰役。在他看來,這些人的摩擦與二戰期間將領之間的不和完全不同。在歐洲戰場,打擊德軍的美國陸軍火力極為強大,當德軍潰敗時,大批敵兵會集體繳械,只有少數人倉皇逃竄,因此使得部隊能立刻順勢推進、趁勝追擊。然而,太平洋戰場上的陸戰隊與陸軍官兵的戰鬥條件異常艱苦。當日軍無力還擊時,他們會慢慢撤退,因此部隊只能一步步向前推進,而且日本人極少投降。
史密斯曾警告阿爾蒙德,仁川登陸大獲全勝只是一種假象,美軍打敗的是敵軍的小股部隊,攻克漢城仍十分困難。他說,初步偵察結果顯示,守衛這座城池的是北韓精銳部隊的數萬名將士。史密斯的猜測一點也沒錯。之前,麥帥的情報處長估計,在仁川─漢城一帶有六、七千名敵軍官兵,但是仁川登陸結束後,金日成緊急調來兩萬大軍,即一個師外加三個獨立團的兵力增援漢城。因此,最後守住漢城的,是一支三萬五千至五萬人的大軍,雖然有些士兵毫無作戰經驗,個個卻異常勇猛。史密斯後來一針見血地指出,通往漢城的道路「在報紙上看起來平常,但在戰場上絕非如此」。處於人數劣勢的美軍只在武器裝備與火力上占有優勢。但是,漢城易守難攻。攻占這樣一座城市,巷戰必不可少,因此這場戰役打得極為辛苦,美軍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有時候,勝利甚至是一條街一條街地奪來的。因為美軍只能依靠自己的強大火力,所以交戰過後,這座城市的大多數地區都已被夷為平地。隨著美軍攻勢逐漸減弱,奪取每一寸土地都需要付出越來越高的代價。史密斯變得壓力沉重,而阿爾蒙德和麥帥的野心卻越來越大。阿爾蒙德對史密斯設定的進攻速度十分不滿。他開始以師長自居——在接下來的幾場作戰中也是如此——他搭乘自己的小型偵察機四處巡視,越過史密斯的師部不斷對其手下的團長、營長甚至連長發號施令。阿爾蒙德以傑出的戰場指揮官自居,凡其所到之處,不管下面是哪支部隊,他都會透過無線電發出指令。史密斯對阿爾蒙德越權指揮十分惱火。「你可以下達指令給我,由我負責執行這些命令。」有一次他對阿爾蒙德說。但是阿爾蒙德依然我行我素,繼續指揮史密斯的手下。最後,史密斯只好向自己的作戰處長鮑澤上校下達命令,如果沒有師部的認可,他可以拒絕執行任何命令。
在史密斯看來,切斷北韓軍的補給線能達到速戰速決的效果。然而,戰場上的重重壓力反映出麥帥總部對公共關係的過度迷戀以及對虛榮永無止境的慾望,這無疑會分散軍隊的注意力。但是,他的這種看法讓自己與阿爾蒙德的關係更加緊張。在這個問題上,東京與華盛頓出現了嚴重分歧。就史密斯、華克及在華府盛頓遠遠觀望的參聯會認為,最明智的方法就是繞過漢城,封鎖它,然後迅速往東與正揮師北上的華克部隊會合。他們希望,這個戰略不僅能讓美軍取得大捷,還可以合圍大部分的北韓軍。在他們看來,麥帥與阿爾蒙德對漢城的執著已經超出這次登陸的目的,如果照他們的想法去做,大批敵軍就能藉機逃之夭夭。但是他們知道,麥帥急於在九月二十五日之前或當天,也就是北韓首度越過三十八度線三個月以後這個別具紀念意義的日子裡,一舉攻克漢城。麥帥原本打算把攻克漢城的日期定在九月二十日,後來卻聽從阿爾蒙德的這個建議。史密斯認為,阿爾蒙德為了登上報紙頭條,不惜拿陸戰隊將士的生命去冒險。但是,他的那一套在史密斯這裡卻行不通,因為在他看來,那些東西只不過是騙人的把戲而已。
(本文節錄自:【第六章】扭轉乾坤:麥克阿瑟仁川登陸)
試閱文章2:〈保護臺灣〉
一九五○年秋天,當國會的兩黨議員,甚至那些曾經對蔣介石忠心耿耿的支持者都不願意為向中國大陸派兵承擔責任時,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夢想就化為泡影了。然而在白宮,這個反攻的夢想還具有相當的政治價值,不僅可以讓政客們反覆用來抨擊政敵,還受到國民黨駐美大使館的極大鼓勵。但是,當使館官員們得到那些可能對美國不利的訊息時,他們往往不會對自己的美國朋友直言相告。
在中國參戰的幾週前,大批中共軍隊在中韓邊境集結。對於這個動向,無論是臺灣的國民黨高層還是其駐美大使館的要員都全然洞悉,幾乎能肯定中共下一步會有什麼舉動。他們完全知道,當美軍、南韓軍直逼中國和北韓的邊境時,中共對北韓搖搖欲墜的局勢會有哪些反應,就像他們知道中共會對他們做出哪些反應一樣。然而,他們的情報並不只是基於自己的直覺。在中國內戰期間,當國民黨某個師向中共投降時,一些前國民黨黨員也被強行併入共產黨軍隊當中。這些人會透過無線電臺透露中共的某些作戰計畫。因此,國民黨往往能掌握一些相當重要的情報,不僅從那些共軍內部的前國民黨特務那裡,還從一些鐵路工人身上,甚至還能從舊政府的其他部分那裡得到這些情報。從聯合國軍越過三十八度線的那一天起,對於即將發生的事,他們具有某種強烈的預感,而且他們所得到的每一條情報似乎都在印證這些預感(有關這件事的部分電報後來被國民黨駐美大使館的一位異議人士公諸於世,因此才真相大白)。中國介入韓戰可能會引發的衝突正是他們亟待看到的事—只有等到新中國參戰後,他們才有機會返回大陸。這是他們唯一能反攻奪權的希望,因此他們並不急於提醒自己的美國盟友即將發生什麼事,否則美國就會極力避免可能發生的衝突。國民黨駐美大使館官員在美國問題上的態度遠比美國人在臺灣問題上的態度複雜得多。他們反覆告誡身在臺灣的國民黨高層要保持冷靜,不要讓這項訊息傳到美國人耳中。
國民黨駐美大使館的力量絕不可低估,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個個足智多謀,更是因為在美國的右派勢力中有一個極為重要的派別特別想支持國民黨。到一九四八年,無論國民黨政權是否能生存下去,他們在華盛頓的生存機率卻比在中國大得多。它的支持者是美國的政客和記者,而不是中國的平民百姓。國民黨政權最聰明的兩位代表人物宋子文和顧維鈞以高超的技巧活躍於華盛頓的政治舞臺上。一九四九年五月,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艾瑞克.薩瓦賴德(二戰期間曾擔任駐華記者)寫道:「國民黨政府已經土崩瓦解。如果說它還有一個真正總部的話,那麼一定是在華盛頓。在這裡,國民黨的說客及其美國支持者正拚命地四處奔走,想促成美國再次對國民黨進行大規模援助。」
引發美國與中國之間衝突的力量遠比大洋兩岸人民所以為的強大得多。很多美國人都沒有意識到,從蔣介石退守臺灣的那一刻起,臺灣就成為中美關係的癥結所在。當新中國成立以後,美國立刻斷絕了一切與之交流的可能性。當包括英國在內的重要盟友開始與中國對話時,美國仍拒絕承認新中國,孤立了中國,也孤立了自己。這無異於主動將中國推入史達林的懷抱。此外,在美國人看來,與蔣介石保持聯繫就意味著要保護他,而保護蔣介石就要保衛臺灣。在美國與新中國斷絕往來之前,參聯會認為這個島嶼對美國的國家安全無關緊要。一九四九年三月,麥帥也表示:「把臺灣視為我們的一個基地,毫無軍事根據」。他的這項聲明被國務院有意公開(這只會讓這位太平洋戰區司令在艾契森眼裡變得更加面目可憎)。然而,政策並非總是一成不變。但當這個政策逆轉,即美國決定支持蔣介石與臺灣時,卻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可以說這是美國對亞洲巨大變化所做出的相對較小的政策調適,但是在毛澤東及其擁護者眼中絕非如此。他們認為,這是一次公然的挑釁,阻礙了他們統一國家的發展。在美國切斷了一切可能與他們交流的管道時,事實上也是阻擋了他們徹底革命的發展。當時,雙方對於這一點都沒有太大的轉圜餘地。在華盛頓,杜魯門政府只是憑著自己的本能做出反應。美國官員以為,這只是對地緣政治的微調。然而在中國大陸的勝利者眼中,華盛頓的所作所為卻使解放全中國這個夢想成了泡影。美國的這項舉動立刻讓自己成為對方不共戴天的仇敵。
從蔣介石離開大陸的那一刻起,國民黨駐美大使館與「中國遊說團」所做的都是在阻止美國承認新中國。他們成功地讓是否承認新中國變成美國國內一個持久的論題,即使在時隔二十幾年之後,民主黨仍對這個話題噤若寒蟬。尼克森總統曾是一名勇於批評民主黨人對待共產主義過於軟弱的年輕政治家,人們以為他不會受到共產黨的紅色誘惑。不過,一九七二年二月,他首度打破堅冰,出訪中國。然而,除了尼克森以外,如果換成民主黨人出訪中國,那就會被指責為親共。同時,美國人不得不考慮這麼一個奇怪的問題:究竟哪一個國家才是中國?是那個有著五億、六億、然後又迅速攀升到七億人口的國家,還是那個遠離大陸、只有八百萬人的小小島嶼?對於這個問題,美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做出正確的回答。
政策問題更是至關重要:難道臺灣和蔣介石真的那麼重要,繼續支持他們會不會讓美國與一個初具雛形的亞洲大國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岌岌可危?難道對於那個曾經一次又一次地失信於民、對美國在軍事與政治經濟上的建議置若罔聞、卻又把自己的先進武器裝備拱手送給敵人的業已垮臺的領袖,美國真的欠他的人情?難道美國真的甘願把一個實力正在上升、有可能成為自己潛在威脅、將來一定會變得強大的泱泱大國逼入自己仇敵的懷抱?難道美國有必要印證毛澤東的信仰,證明自己是一個覬覦中國的新帝國主義列強?難道美國真的打算按照毛澤東的某種說法變得狂妄自大,從而進一步鞏固他對美國的敵視態度與敵對政策?這些都是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而每一個問題的答案幾乎都是否定的。但是由於事涉國家安全,當時人們對這些問題噤若寒蟬,而且較之於國內政治鬥爭,它們立刻顯得無足輕重。因此,最後美國還是決定繼續支持那個業已死亡的國民黨政權。
對於即將發生的衝突,沒有人比麥爾比看得更為清楚。這個中國通親眼目睹國民黨政府的垮臺,因此對很多事情他往往能採取更明智的舉動。麥爾比是一個傳奇人物。一九四五年,在哈里曼的力薦之下,他從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來到中國,然後又成為美國駐蘇聯大使,並受命密切注意該國政府的一舉一動。他很快就成為美國使館中重要的反蔣人物。他發現共產黨在中國受到擁戴並取得成功與蘇聯並沒有太大關係,而是因為他們積極回應了人民的呼聲與國內潛藏著的民族主義情結,從而變得堅不可摧。因此,麥爾比毫不懷疑,儘管美國與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之間的關係一定會十分艱難,但美國在處理這項關係時卻應當十分慎重。一九四八年六月,也就是蔣介石政權垮臺的前一年,就像是在預言即將發生的事情那樣,他在日記中寫道:「美國竭盡全力也無力阻擋亞洲的潮流,但是如果能集思廣益,我們完全能讓這股潮流變得比現在更加友善。」
在韓戰爆發後,美國立刻決定把第七艦隊調往臺灣海峽。然而美國人當時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做出了一個宿命的決定。毛澤東深知,他無法在海上和空中與美國軍隊抗衡,因此當他最終決定與美國一決雌雄時,那麼戰場一定是在韓國。中國規模龐大的陸軍輕易就能抵達北韓。毛澤東的軍隊能徒步穿越鴨綠江,但是美國軍隊卻無法游過臺灣海峽。如果美國膽敢在臺灣海峽劃定自己的界線,那麼毛澤東在北韓劃出自己的界線簡直是易如反掌。
(本文節錄自:【第六章】扭轉乾坤:麥克阿瑟仁川登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