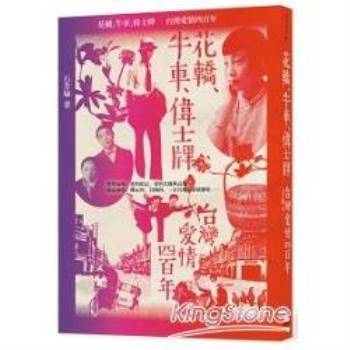【內文節選一】
從臺灣到滿州國:一代詩妓王香禪
文人與娼妓之間的交遊,一直是中國流傳以久的粉色文化。文人對娼妓的歌詠,不管是讚嘆其技藝或是美貌,抑或憐憫其身世,都為中國文學史留下許多纏綿的詩篇以及動人的愛情故事。
在臺灣,與文人交往密切的藝妓中,最為人所熟知的便是人稱「藝妲中的藝妲」王香禪。王香禪情路坎坷,交往的又多是知名的文人,在她一生中,便前後經歷了連雅堂、羅秀惠和謝介石等人,有些是傷感的感情生活,有些則是浪漫的想像。
王香禪出生臺北艋舺,原名罔市,因家境清苦,從小就被送給龍山寺婦人董仔治,在鴇母董仔治的調教栽培下,十六、七歲時開始大張豔幟。
香禪雖身在風塵,但極為上進。她性喜文藝,最初學北曲,略諳文字,並嘗試自己填詞。彼時艋舺詩人王子鶴見她頗有詩才,便介紹她到設於大稻埕的「劍樓書塾」學習作詩。
劍樓書塾的塾師趙一山是前清秀才,年近花甲、雙目失明,但熟讀詩書,講解仔細,且幫門生修改詩作,因此學生的詩藝進步很快。而香禪勤奮好學,不論晴雨,每天都從艋舺坐車到大稻埕,從未偷懶翹課,一如愛好文學的文藝少女。一年之後,她的詩詞略有所成,「詩妓」之稱便流傳開來。而各地紳士每有宴會,便不惜重金邀請香禪前去佐酒吟詩助興。
大約一年後(一八九五年),香禪轉入臺南「玩春園」(另一說法是在「寶美樓」)。在那個時代,藝妓在十四、五歲時,多半會隨著養母或養祖母南下各大城市,俗稱為「飲墨水」。在南部待上三、五年,人面熟了,客門也闊,於是在洽當的時間內返回臺北,整修藝妓間,高樹豔幟。
香禪到臺南時,「南社」剛成立,文人擔憂國事、感傷時局之餘,也經常寄情秦樓楚館之中。因為王香禪略解詩詞,也就結識不少文人雅士,其中包括了連雅堂以及煙花浪子羅秀惠。
連雅堂初識王香禪,便發覺她的詩學難能可貴,而願意加以指導,香禪的詩藝也就益加精進。年輕時的連雅堂風度翩翩,香禪對他可說一見傾心,可惜連雅堂早在二十歲那年便娶了臺南富商沈德墨的女兒筱雲,夫妻感情恩愛。據說香禪曾有意屈居側室,但連雅堂卻極力反對男人蓄妾,主張男女平等。他認為遺產與蓄妾是引起兄弟相爭、家庭不幸福的根源。香禪了解到連雅堂不可能改變他的信念,納她為妾,便只好深藏情感,轉化為友誼。
之後,王香禪遇到了風月名家、煙花浪子羅秀惠。羅秀惠雖惡名昭彰,卻也頗有才氣。在羅秀惠的追求下,兩人深交一段時日,便結了婚。可惜婚後的羅秀惠並未專情於王香禪,依舊流連於花街柳巷,而且又找到了新的攻獵目標,那便是赤崁女史蔡碧吟。
蔡碧吟不僅家世良好,且容貌秀麗、體態婀娜,王香禪得知夫君移情別戀後,心灰意冷,終於看開一切,主動提出離婚,隨後便離開臺南這傷心地,重回臺北。
結束這段不如意的婚姻之後,王香禪閉門獨居,長齋禮佛,同時也寫些詩詞在報上發表。就在這段時間,她得到大家的關懷,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火焰。而後經人撮合,三十開外的王香禪重披嫁裳,嫁給了謝介石。婚後隨著謝介石前往上海。
(中略…)
民國元年,雅堂先生遊滬,王香禪與夫婿在一次宴會中和連雅堂偶遇。相逢逆旅,香禪善盡地主之誼,與連雅堂朝夕相處,兩人品茶談詩,雅堂先生並指導香禪詩作,加深昔日情誼。此時連雅堂寫了一首〈滬上逢香禪女士〉:
淪落江南尚有詩,東風紅豆子離離;春申浦上還相見,腸斷天涯杜牧之。
而從「淪落江南尚有詩」的詩句中,足見連雅堂對王香禪的讚賞。
其後,謝介石受聘為吉林法政學堂教習兼治報務,遂與王香禪移居吉林。巧的是,連雅堂先生也受《新吉林報》之邀,遠赴東北,再次與謝氏夫婦相逢。
然而因《新吉林報》對時政多有批評,在袁世凱執政初期就被查禁。但連雅堂並未氣餒,又與日人兒玉多一共同創辦《邊聲》報。只不過《邊聲》發行三期又宣告停刊。不得已,連雅堂只好韜光養晦,閉門讀書。
在他閉門讀書這段時間,王香禪以女主人兼女弟子的身分陪伴他讀書賦詩、閒話家常,成為他朝夕相處的紅粉知己。而在連雅堂的詩作中,記載王香禪最多的,也是在這個時期。
在謝氏夫婦熱情款待之下,連雅堂待在吉林長達半年之久。然而吉林終究只是客居,臺灣的家人和文史工作依然召喚著他,即使離情依依,連雅堂還是做出堅定的歸鄉決定。
王香禪不捨分別,為此曾作詩挽留:
數株松竹繞精廬,絕色天香伴著書;
此味年年消受慣,秋風底事憶鱸魚。
然而連雅堂也作詩回應,表達他想回臺灣的心意:
小隱青山共結廬,秋風黃葉夜擁書;
天涯未老情未減,且向松江食鱖魚。
連雅堂這一別,與王香禪再不曾再相遇,兩人的故事就此畫下句點。
(中略…)
王香禪經歷了兩段波折的婚姻,與連雅堂之間亦師亦友又似戀人的往來留給後人許多想像,即便在《連雅堂全集》裡,由師古先生所寫的〈連雅堂先生
從臺灣到滿州國:一代詩妓王香禪
文人與娼妓之間的交遊,一直是中國流傳以久的粉色文化。文人對娼妓的歌詠,不管是讚嘆其技藝或是美貌,抑或憐憫其身世,都為中國文學史留下許多纏綿的詩篇以及動人的愛情故事。
在臺灣,與文人交往密切的藝妓中,最為人所熟知的便是人稱「藝妲中的藝妲」王香禪。王香禪情路坎坷,交往的又多是知名的文人,在她一生中,便前後經歷了連雅堂、羅秀惠和謝介石等人,有些是傷感的感情生活,有些則是浪漫的想像。
王香禪出生臺北艋舺,原名罔市,因家境清苦,從小就被送給龍山寺婦人董仔治,在鴇母董仔治的調教栽培下,十六、七歲時開始大張豔幟。
香禪雖身在風塵,但極為上進。她性喜文藝,最初學北曲,略諳文字,並嘗試自己填詞。彼時艋舺詩人王子鶴見她頗有詩才,便介紹她到設於大稻埕的「劍樓書塾」學習作詩。
劍樓書塾的塾師趙一山是前清秀才,年近花甲、雙目失明,但熟讀詩書,講解仔細,且幫門生修改詩作,因此學生的詩藝進步很快。而香禪勤奮好學,不論晴雨,每天都從艋舺坐車到大稻埕,從未偷懶翹課,一如愛好文學的文藝少女。一年之後,她的詩詞略有所成,「詩妓」之稱便流傳開來。而各地紳士每有宴會,便不惜重金邀請香禪前去佐酒吟詩助興。
大約一年後(一八九五年),香禪轉入臺南「玩春園」(另一說法是在「寶美樓」)。在那個時代,藝妓在十四、五歲時,多半會隨著養母或養祖母南下各大城市,俗稱為「飲墨水」。在南部待上三、五年,人面熟了,客門也闊,於是在洽當的時間內返回臺北,整修藝妓間,高樹豔幟。
香禪到臺南時,「南社」剛成立,文人擔憂國事、感傷時局之餘,也經常寄情秦樓楚館之中。因為王香禪略解詩詞,也就結識不少文人雅士,其中包括了連雅堂以及煙花浪子羅秀惠。
連雅堂初識王香禪,便發覺她的詩學難能可貴,而願意加以指導,香禪的詩藝也就益加精進。年輕時的連雅堂風度翩翩,香禪對他可說一見傾心,可惜連雅堂早在二十歲那年便娶了臺南富商沈德墨的女兒筱雲,夫妻感情恩愛。據說香禪曾有意屈居側室,但連雅堂卻極力反對男人蓄妾,主張男女平等。他認為遺產與蓄妾是引起兄弟相爭、家庭不幸福的根源。香禪了解到連雅堂不可能改變他的信念,納她為妾,便只好深藏情感,轉化為友誼。
之後,王香禪遇到了風月名家、煙花浪子羅秀惠。羅秀惠雖惡名昭彰,卻也頗有才氣。在羅秀惠的追求下,兩人深交一段時日,便結了婚。可惜婚後的羅秀惠並未專情於王香禪,依舊流連於花街柳巷,而且又找到了新的攻獵目標,那便是赤崁女史蔡碧吟。
蔡碧吟不僅家世良好,且容貌秀麗、體態婀娜,王香禪得知夫君移情別戀後,心灰意冷,終於看開一切,主動提出離婚,隨後便離開臺南這傷心地,重回臺北。
結束這段不如意的婚姻之後,王香禪閉門獨居,長齋禮佛,同時也寫些詩詞在報上發表。就在這段時間,她得到大家的關懷,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火焰。而後經人撮合,三十開外的王香禪重披嫁裳,嫁給了謝介石。婚後隨著謝介石前往上海。
(中略…)
民國元年,雅堂先生遊滬,王香禪與夫婿在一次宴會中和連雅堂偶遇。相逢逆旅,香禪善盡地主之誼,與連雅堂朝夕相處,兩人品茶談詩,雅堂先生並指導香禪詩作,加深昔日情誼。此時連雅堂寫了一首〈滬上逢香禪女士〉:
淪落江南尚有詩,東風紅豆子離離;春申浦上還相見,腸斷天涯杜牧之。
而從「淪落江南尚有詩」的詩句中,足見連雅堂對王香禪的讚賞。
其後,謝介石受聘為吉林法政學堂教習兼治報務,遂與王香禪移居吉林。巧的是,連雅堂先生也受《新吉林報》之邀,遠赴東北,再次與謝氏夫婦相逢。
然而因《新吉林報》對時政多有批評,在袁世凱執政初期就被查禁。但連雅堂並未氣餒,又與日人兒玉多一共同創辦《邊聲》報。只不過《邊聲》發行三期又宣告停刊。不得已,連雅堂只好韜光養晦,閉門讀書。
在他閉門讀書這段時間,王香禪以女主人兼女弟子的身分陪伴他讀書賦詩、閒話家常,成為他朝夕相處的紅粉知己。而在連雅堂的詩作中,記載王香禪最多的,也是在這個時期。
在謝氏夫婦熱情款待之下,連雅堂待在吉林長達半年之久。然而吉林終究只是客居,臺灣的家人和文史工作依然召喚著他,即使離情依依,連雅堂還是做出堅定的歸鄉決定。
王香禪不捨分別,為此曾作詩挽留:
數株松竹繞精廬,絕色天香伴著書;
此味年年消受慣,秋風底事憶鱸魚。
然而連雅堂也作詩回應,表達他想回臺灣的心意:
小隱青山共結廬,秋風黃葉夜擁書;
天涯未老情未減,且向松江食鱖魚。
連雅堂這一別,與王香禪再不曾再相遇,兩人的故事就此畫下句點。
(中略…)
王香禪經歷了兩段波折的婚姻,與連雅堂之間亦師亦友又似戀人的往來留給後人許多想像,即便在《連雅堂全集》裡,由師古先生所寫的〈連雅堂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