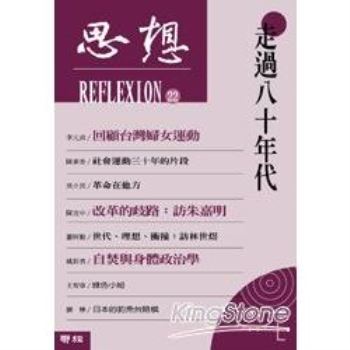播種與茁壯:回顧1980年代台灣婦運
李元貞
一、前言:1970年代的刺激
二戰後的台灣婦運,可以1970年代呂秀蓮的新女性運動為「拓荒期」、1980年代婦女新知等新興婦女團體的萌芽為「播種期」、1990年代後的多元性別運動為「開花結果期」。但要談1980年代台灣婦運,就必需交代1970年代影響我個人投入婦運的事情。記得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國民黨政府的威權受到挑戰,當紅的《大學雜誌》刊出一篇許信良等人所寫的〈台灣社會力分析〉,對當時剛入大學做講師的我影響不小。其文對舊式地主、農民及其子弟、知識青年、財閥、企業幹部及中小企業者、勞工、工務員等階層做了分析,並指出台灣社會已潛藏著實現現代化和民主政治的力量。另外1973年4月,晨鐘出版社出版歐陽子等人翻譯的西蒙 波娃《第二性》,後來我才知道她們只翻譯了第二卷,第一卷的理論部份沒有譯出,但此書已經明白寫出女性做為社會第二性的精神桎梏,給我當頭棒喝。不久,我的婚姻出了問題。我在1973年底離婚後,1974年,9月至美國進修戲劇,更多地接觸了美國婦運的資訊,發現並非特殊女人(我想做藝術家)才不適合婚姻;原來父權制的婚姻,其桎梏女人是普遍的婦女問題。因此在我1976年9月返台之後,除在淡江中文系繼續任教外,我一方面為蘇慶黎做總編輯的《夏潮》寫稿和做義工,另方面參加呂秀蓮的「新女性運動」,覺得台灣的民主化和兩性平權都是我要追求的目標。記得1978年還常去陳鼓應及陳婉真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台大附近的立委、國大競選辦公室,購買了一件背後寫著「民主大家來」的休閒外套,也去支援呂秀蓮的桃園國大選舉活動。那時,黨外的選舉聲勢頗大,到處看見一張握緊拳頭的人權傳單,但因為12月底美國與中共政府建交、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蔣經國總統宣布停止選舉受挫;不過這股受挫的新生代黨外力量,不久藉出版《美麗島》雜誌而壯大,並時時要求舉行民主選舉,終於導致1979年12月初的發生高雄美麗島政治事件,當局抓了許多人,呂秀蓮入獄,連我也被調查員約談,整個社會充滿了肅殺、壓迫、苦悶的氣息。
二、婦女新知雜誌誕生
然而黨外的政論雜誌繼續出刊,《亞洲人》、《暖流》、《縱橫》、《政治家》、《前進》、《自由時代》等等,警總查禁了一本,甚至到印刷廠扣押、搗毀,不久另一本又以新名稱面世,印刷廠也換來換去,黨外新生代不厭地與警總捉迷藏。暫停的中央民代增額選舉,在海內外不息的壓力下,終於在1980年底舉行,美麗島政治受難家屬幾乎全部當選,周清玉、許榮淑、方素敏代夫出征成功,安慰了黨外重傷的人心。黨外新生代這股不死的決心大大地鼓勵我,讓我潛藏心底的憤怒找到出口,面對這股台灣政治社會渴盼轉型的洪流,我體悟婦運也必須繼續下去。我發起「婦女聯誼會」,與吳嘉麗、薄慶容、簡扶育,李豐、鄭至慧、曹愛蘭、李素秋、黃毓秀、黃瓊華、莊素雅等人每月聚會討論婦女問題,商量有沒有人願意出來做婦運。幾次之後,我知道自己必須學習黨外來編雜誌發言做婦運。因為我從來沒編過雜誌,便去參觀殷允芃剛創辦的《天下》雜誌,發現《天下》雜誌社在台塑大樓的一角,辦公室很大,光是攝影師就有3、4位,還有廣告部門,我看了只得死心。後來認識編小開本(25開)《心靈》雜誌的王溢嘉,他告訴我都是他一個人在編寫,太太嚴曼麗幫忙編輯設計,一個月兩萬塊左右就夠出刊了。我算了一下我剛升副教授(淡江文理學院也剛改制大學)的薪水,每月3-4萬元,加上一點積蓄,再向朋友們募捐,應該可以試試。於是湊足戶頭30萬元,拜薄慶容先生柴松林的幫忙,向台北市新聞處申請雜誌(月刊)許可。許可很快就下來,社委們慷慨地每人每月捐助一千元,大家商量以「婦女新知」為雜誌名稱,未掛名社委的曹愛蘭,請她的堂兄曹昌明用毛筆寫出好看的樣字,並選了一張鳥巢裡有一顆蛋的圖片做封面,25開本、頁數不過30-50頁的小雜誌,就在1982年2月創刊了。社委李素秋向民生社區三一教會免費借了一間小房間給我辦公,我可以用他們的電話及在小房間放雜誌。記得顧燕翎曾經勸我不要辦雜誌,因為當時政府對出版品的管制甚嚴,所以流行一句話:「想要害誰就勸他辦雜誌」。加上我原來的人生志趣是文學及藝術創作,她認為我不如以寫作來傳達「女性意識」較好。但是當我決定辦雜誌以後,燕翎雖沒掛名社委,捐款和寫文章總是有求必應。黃毓秀除了捐款及支援文章外,知道我要找尋女律師以充實雜誌社內容,她透過律師出身的先生周弘憲將尤美女介紹給我。在《婦女新知》雜誌的第三期,尤美女便討論法律與婦女的關係,往後更開了與婦女相關的「法律專欄」,檢視法律裡的婦女問題。
簡扶育一開始就是《婦女新知》雜誌社的社委兼雜誌攝影師,第二期《新知》的封面就是她的「女子登山」照片,象徵著婦運的艱辛與理想。她在往後的雜誌中,還開闢「婦女生活攝影」及「攝影與詩」的專欄。稍後掛名社委的鄭至慧不久當上《婦女》雜誌的主編,百忙中抽空為《新知》從第二期起開闢「婦女新聞」這個專欄,讓《新知》一直沿用了25年。其夫台大數學系教授兼橄欖球校隊隊員張海潮,還用筆名在《新知》寫文章,以男性立場砥礪婦運。李豐醫師除供應稿源外,更介紹了不少女醫師訂閱《婦女新知》雜誌,如林和惠及孫啟璟醫師都慷慨解囊。孫啟璟、吳嘉麗與稍後加入的徐慎恕也在《新知》上提供「生活小常識」,推銷訂戶不在話下。「佳姿韻律世界」的分店老闆林邊,從第二期起就每期登廣告支援《新知》,一直支援至25開本的《新知》在兩年四個月後停刊為止。在《新知》出刊三期後,沒想到《新知》竟飄洋過海到了成令方的手中,她以一個讀者的身分寫信給我,除了鼓勵外還捐款及供稿,自《新知》第六期開始,就常常看見令方的「海外婦女報導」,給我極大的溫暖。此外,她又介紹郭美瑾、王瑞香給《新知》,兩人不用說都捐款及為《新知》寫稿,同時她們三人都提供不少《新知》應改進的意見。記得令方曾派在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的錢永祥到三一教會的小房間看我,帶來捐款及令方的關切。錢永祥後來與黃道琳(王瑞香的前夫)故意邀請我到三民所談婦運來抬舉《新知》。這些姊妹們及其男性親人和友人的熱情,使我在面對社會的冷嘲熱諷時,有足夠的力量對付。
本來大家實行輪流編輯,第三期後就取消了,因為沒有固定負責人會脫期,我既然掛名發行人,還是由我來負責。由於我要上課無法投入全部時間,淡大中文系的學生李燕芳就義務支援我。《新知》前半年的美編都是在美編自己家裡做,我與美編常約在咖啡室看藍圖。不久,我們從三一教會的小房間搬到羅斯福路三段的一家朋友介紹的漫畫社分租一間較大之房。從這時候起,《新知》美編可以在這間辦公室裡做,其慘澹經營可以想見。半年後我與漫畫社社長不和,就跟鄭至慧介紹的、也是婦女雜誌編輯林秀英合租基隆路二段12樓的一間公寓,公寓的客廳當做雜誌社,兩間房由林秀英及其男友石天威居住。記得在舉辦第二年「8338婦女週」的大活動時,華視「今天」節目記者來雜誌社訪問我,看見簡陋的公寓客廳就是雜誌社的辦公室,嚇得那位女記者花容失色,我也很尷尬,但只能強裝無所謂地接受採訪。一年後又與李燕芳姊妹一起將雜誌社搬到共租的通化街二樓,這期間有朋友提供光復南路一棟大廈的地下室免費使用,然而地下室雖大卻沒有窗戶,根本不行。讓我深悟,我決定辦雜誌而資金不足,實在太大膽了。好在經由社委黃瓊華與文大教授游麗嘉的牽線,我認識了當時美國亞洲協會(現稱亞洲基金會)駐台的代表謝孝同及其秘書王世榕,他們非常關心台灣政治、社會的發展,對女權運動很支持。沒想到我與亞協駐台代表謝孝同相談甚歡,竟可以《婦女新知》這麼小的雜誌,向亞協申請主辦第二年婦女節「8338婦女週」的大活動,申請到的經費是一萬美金(40萬元台幣),對當時《新知》而言真是一筆巨款!因為有亞洲協會做後盾,也說動了中國時報生活版與我們在師大合辦演講及宣傳;目前寫旅遊、美食的專欄名家韓良露也幫忙策劃主持「女性電影」,借到電影圖書館放映並討論。記得我去各單位洽談時,說明這是亞協補助的計劃就頗具份量,好似我的身分地位也因此抬高不少。其實,我對自己的社會不關心婦女問題有些氣悶,對我非要拉著老美(亞協)才能說服社會的情況也頗為失望,然而現實也只能如此做下去。
三、8338婦女週
利用第二年的三八婦女節,《新知》開始緊鑼密鼓地籌辦「8338」婦女週。活動從3月5日-10日七天,每天從早上10點到晚上9點,包括展覽、文藝活動、座談、演講及女性電影。前三項在主要的會場即在台北市復興南路的文苑,演講在師大綜合大樓,而女性電影分多場在電影圖書館放映。展覽有七項:家庭計劃圖片及婦科診療室展(林永豐、陳文龍醫師是顧問),有各種避孕器具的展出,相當吸引婦女的目光;台灣婦女雜誌大展(1982-1983年1、2月雜誌),在大本的彩色的美女封面雜誌前,《婦女新知》雜誌實在不起眼,只能說她是一顆女性意識的種子;還有簡扶育、許大雯的婦女生活攝影展及向中國女權運動者致敬等展覽。演講以李豐、李昂、林菊枝律師的聽眾較多,座談會以徐慎恕主持的「創造性的主婦生活」最多婦女參加,我與柏楊對談「男女如何互相學習」也吸引很多人,觀眾多半衝著柏楊而來。記得不少姊妹擔心我會講不過鼎鼎大名的作家柏楊,我安慰大家說,柏楊雖在某些方面擁有知識,但在兩性方面的新知絕對比不過我,對談之後大家不只放心還很興奮,因為柏楊口才雖好,兩性觀念平平,被我挑戰之處甚多。其實不只柏楊,當時一些進步的男作家如陳映真都不以女性觀念落伍為恥的,我也在《新知》第七期批評過李敖的「大男人主義」,我還特別將這本小雜誌寄給他,自稱大師的李敖卻完全不予理會。韓良露主持講評的三部女性電影:《兄弟姊妹》(性政治的呈現)、《失聲呼叫》 (女性被強暴的問題)、《後勤女工》(二次大戰時美國女性加入各類工廠,戰爭結束又後被解雇,帶出種族及性別歧視等問題),這三部租來的金馬獎外片,不只內容有女性的視角,也同時檢討電影形式的掌握與欺瞞問題。此時《新知》文章比較強調「女性意識」,但韓良露從電影的講評中卻帶出「女性主義」這個1990年代後開始在台灣社會流行起來的名詞。
《新知》雖然是不起眼的小雜誌,由於我也支持黨外的民主運動,與當時自立晚報社的許多人認識,自立晚報副刊主編向陽對我辦雜誌及「8338」婦女週活動很支持。自晚在這年的婦女節前一天及當天都製作女性專輯,3月7日由應鳳凰、鐘麗慧策劃在自立副刊三月號的「出版月報」報導了「出版界的十位傑出女性」:林海音、姚宜瑛、吳美雲、殷允芃、鄭淑敏、李元貞、柯元馨、李王秋香、嚴友梅、孫小英,且有照片登載。將我以「婦女新知月刊發行人」的身分介紹出來,竟可以與幾位國內女性大出版家一起現身,讓我既興奮又慚愧。3月8日自晚的11版以「女性們請站出來」為標題,藉婦女節介紹三位成功的現代女性:文建會第三處處長申學庸、實踐家專校長林澄枝、婦女新知發行人李元貞。申學庸的主張是「先齊家,再談其他」、林澄枝的主張是「工作時,忘記自己是女性」、我的主張是「自覺,走出傳統」,也有照片登載。有趣的是其他兩位的採訪記者掛本名,分別是楊淑慧、張慧英,我的採訪記者只掛筆名「悒攸」。中國時報答應與《新知》合作宣傳婦女週,展覽的報導不錯,《新知》辦公室電話響個不停,使《新知》月刊當年的訂戶達到800多名,這似乎是《新知》雜誌訂戶最多的一次。以後《新知》再怎麼努力,都只能保持500-600個訂戶左右,媒體的力量由此可見。《時報雜誌》發行人鄭淑敏說話算話,婦女節當期雜誌刊出楊美惠與我做封面人物,對台灣婦運做了傳承的介紹,我這才得知楊美惠曾與歐陽子合譯波娃的《第二性》,她又出過《婦女問題新論》一書,對我做婦運的思想啟發不少,往後更寫信鼓勵《新知》,我十分感謝。在報紙只能出三大張的時代,這些報導,加上《時報雜誌》的宣傳,讓我個人一時比《新知》還出名,對推展婦運確實有些幫助。
在8338婦女週活動中,不少婦女留下姓名、地址,5月我們開始組織「讀者聯誼會」,每月一次,由會員決定講題,也由會員輪流主講,家庭主婦參與者甚多,徐慎恕、林美絢、暢曉雁、余善如是骨幹,後來賴玉枝亦積極加入,「讀者聯誼會」也成為《新知》社內的進修活動,大家討論越多,感覺婦女問題的解決越迫切。慎恕在第二年的16期起開始做《新知》雜誌的編輯工作,林美絢也接下讀者聯誼會的主持工作,曉雁經常來《新知》做剪報、整理資料,必要時寫書評支援《新知》,賴玉枝也寫親子文章在《新知》發表。《新知》16期的封面人物是李素秋,討論的專題:「社會變遷中的主婦角色」,《新知》內文不但肯定家庭主婦的家務勞動,而且說明家庭主婦角色的複雜性:妻子、母親、女傭的三結合,其「無酬」的生產性與服務性卻被父權社會以「愛」之名遮蔽。再經過《新知》1985的「家庭主婦年」的婦女節活動,呼籲「家庭主婦再發展」,埋下徐慎恕1986創辦「新環境主婦聯盟基金會」的種子。同時,參與8338婦女週主持「互助的力量——離婚婦女聯誼會」座談的林蕙瑛教授,往後與許多離婚婦女聚會,在1985成立「拉一把協會」,是1988施寄青正式成立「晚情協會」的前身。同時亞協駐台代表謝孝同介紹姜蘭虹與我及燕翎認識,姜蘭虹也參加了8338婦女週活動,我們一起說動亞協支持成立婦女研究資料中心,希望婦女研究能成為婦運的後盾。1985《新知》積極幫助姜蘭虹召開「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在亞協的資助下姜蘭虹成立「台大婦女研究室」。可以說8338婦女週最大的影響是召喚了不少婦女關心自己切身的問題,產生積極組織新社團的興趣。
李元貞
一、前言:1970年代的刺激
二戰後的台灣婦運,可以1970年代呂秀蓮的新女性運動為「拓荒期」、1980年代婦女新知等新興婦女團體的萌芽為「播種期」、1990年代後的多元性別運動為「開花結果期」。但要談1980年代台灣婦運,就必需交代1970年代影響我個人投入婦運的事情。記得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國民黨政府的威權受到挑戰,當紅的《大學雜誌》刊出一篇許信良等人所寫的〈台灣社會力分析〉,對當時剛入大學做講師的我影響不小。其文對舊式地主、農民及其子弟、知識青年、財閥、企業幹部及中小企業者、勞工、工務員等階層做了分析,並指出台灣社會已潛藏著實現現代化和民主政治的力量。另外1973年4月,晨鐘出版社出版歐陽子等人翻譯的西蒙 波娃《第二性》,後來我才知道她們只翻譯了第二卷,第一卷的理論部份沒有譯出,但此書已經明白寫出女性做為社會第二性的精神桎梏,給我當頭棒喝。不久,我的婚姻出了問題。我在1973年底離婚後,1974年,9月至美國進修戲劇,更多地接觸了美國婦運的資訊,發現並非特殊女人(我想做藝術家)才不適合婚姻;原來父權制的婚姻,其桎梏女人是普遍的婦女問題。因此在我1976年9月返台之後,除在淡江中文系繼續任教外,我一方面為蘇慶黎做總編輯的《夏潮》寫稿和做義工,另方面參加呂秀蓮的「新女性運動」,覺得台灣的民主化和兩性平權都是我要追求的目標。記得1978年還常去陳鼓應及陳婉真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台大附近的立委、國大競選辦公室,購買了一件背後寫著「民主大家來」的休閒外套,也去支援呂秀蓮的桃園國大選舉活動。那時,黨外的選舉聲勢頗大,到處看見一張握緊拳頭的人權傳單,但因為12月底美國與中共政府建交、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蔣經國總統宣布停止選舉受挫;不過這股受挫的新生代黨外力量,不久藉出版《美麗島》雜誌而壯大,並時時要求舉行民主選舉,終於導致1979年12月初的發生高雄美麗島政治事件,當局抓了許多人,呂秀蓮入獄,連我也被調查員約談,整個社會充滿了肅殺、壓迫、苦悶的氣息。
二、婦女新知雜誌誕生
然而黨外的政論雜誌繼續出刊,《亞洲人》、《暖流》、《縱橫》、《政治家》、《前進》、《自由時代》等等,警總查禁了一本,甚至到印刷廠扣押、搗毀,不久另一本又以新名稱面世,印刷廠也換來換去,黨外新生代不厭地與警總捉迷藏。暫停的中央民代增額選舉,在海內外不息的壓力下,終於在1980年底舉行,美麗島政治受難家屬幾乎全部當選,周清玉、許榮淑、方素敏代夫出征成功,安慰了黨外重傷的人心。黨外新生代這股不死的決心大大地鼓勵我,讓我潛藏心底的憤怒找到出口,面對這股台灣政治社會渴盼轉型的洪流,我體悟婦運也必須繼續下去。我發起「婦女聯誼會」,與吳嘉麗、薄慶容、簡扶育,李豐、鄭至慧、曹愛蘭、李素秋、黃毓秀、黃瓊華、莊素雅等人每月聚會討論婦女問題,商量有沒有人願意出來做婦運。幾次之後,我知道自己必須學習黨外來編雜誌發言做婦運。因為我從來沒編過雜誌,便去參觀殷允芃剛創辦的《天下》雜誌,發現《天下》雜誌社在台塑大樓的一角,辦公室很大,光是攝影師就有3、4位,還有廣告部門,我看了只得死心。後來認識編小開本(25開)《心靈》雜誌的王溢嘉,他告訴我都是他一個人在編寫,太太嚴曼麗幫忙編輯設計,一個月兩萬塊左右就夠出刊了。我算了一下我剛升副教授(淡江文理學院也剛改制大學)的薪水,每月3-4萬元,加上一點積蓄,再向朋友們募捐,應該可以試試。於是湊足戶頭30萬元,拜薄慶容先生柴松林的幫忙,向台北市新聞處申請雜誌(月刊)許可。許可很快就下來,社委們慷慨地每人每月捐助一千元,大家商量以「婦女新知」為雜誌名稱,未掛名社委的曹愛蘭,請她的堂兄曹昌明用毛筆寫出好看的樣字,並選了一張鳥巢裡有一顆蛋的圖片做封面,25開本、頁數不過30-50頁的小雜誌,就在1982年2月創刊了。社委李素秋向民生社區三一教會免費借了一間小房間給我辦公,我可以用他們的電話及在小房間放雜誌。記得顧燕翎曾經勸我不要辦雜誌,因為當時政府對出版品的管制甚嚴,所以流行一句話:「想要害誰就勸他辦雜誌」。加上我原來的人生志趣是文學及藝術創作,她認為我不如以寫作來傳達「女性意識」較好。但是當我決定辦雜誌以後,燕翎雖沒掛名社委,捐款和寫文章總是有求必應。黃毓秀除了捐款及支援文章外,知道我要找尋女律師以充實雜誌社內容,她透過律師出身的先生周弘憲將尤美女介紹給我。在《婦女新知》雜誌的第三期,尤美女便討論法律與婦女的關係,往後更開了與婦女相關的「法律專欄」,檢視法律裡的婦女問題。
簡扶育一開始就是《婦女新知》雜誌社的社委兼雜誌攝影師,第二期《新知》的封面就是她的「女子登山」照片,象徵著婦運的艱辛與理想。她在往後的雜誌中,還開闢「婦女生活攝影」及「攝影與詩」的專欄。稍後掛名社委的鄭至慧不久當上《婦女》雜誌的主編,百忙中抽空為《新知》從第二期起開闢「婦女新聞」這個專欄,讓《新知》一直沿用了25年。其夫台大數學系教授兼橄欖球校隊隊員張海潮,還用筆名在《新知》寫文章,以男性立場砥礪婦運。李豐醫師除供應稿源外,更介紹了不少女醫師訂閱《婦女新知》雜誌,如林和惠及孫啟璟醫師都慷慨解囊。孫啟璟、吳嘉麗與稍後加入的徐慎恕也在《新知》上提供「生活小常識」,推銷訂戶不在話下。「佳姿韻律世界」的分店老闆林邊,從第二期起就每期登廣告支援《新知》,一直支援至25開本的《新知》在兩年四個月後停刊為止。在《新知》出刊三期後,沒想到《新知》竟飄洋過海到了成令方的手中,她以一個讀者的身分寫信給我,除了鼓勵外還捐款及供稿,自《新知》第六期開始,就常常看見令方的「海外婦女報導」,給我極大的溫暖。此外,她又介紹郭美瑾、王瑞香給《新知》,兩人不用說都捐款及為《新知》寫稿,同時她們三人都提供不少《新知》應改進的意見。記得令方曾派在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的錢永祥到三一教會的小房間看我,帶來捐款及令方的關切。錢永祥後來與黃道琳(王瑞香的前夫)故意邀請我到三民所談婦運來抬舉《新知》。這些姊妹們及其男性親人和友人的熱情,使我在面對社會的冷嘲熱諷時,有足夠的力量對付。
本來大家實行輪流編輯,第三期後就取消了,因為沒有固定負責人會脫期,我既然掛名發行人,還是由我來負責。由於我要上課無法投入全部時間,淡大中文系的學生李燕芳就義務支援我。《新知》前半年的美編都是在美編自己家裡做,我與美編常約在咖啡室看藍圖。不久,我們從三一教會的小房間搬到羅斯福路三段的一家朋友介紹的漫畫社分租一間較大之房。從這時候起,《新知》美編可以在這間辦公室裡做,其慘澹經營可以想見。半年後我與漫畫社社長不和,就跟鄭至慧介紹的、也是婦女雜誌編輯林秀英合租基隆路二段12樓的一間公寓,公寓的客廳當做雜誌社,兩間房由林秀英及其男友石天威居住。記得在舉辦第二年「8338婦女週」的大活動時,華視「今天」節目記者來雜誌社訪問我,看見簡陋的公寓客廳就是雜誌社的辦公室,嚇得那位女記者花容失色,我也很尷尬,但只能強裝無所謂地接受採訪。一年後又與李燕芳姊妹一起將雜誌社搬到共租的通化街二樓,這期間有朋友提供光復南路一棟大廈的地下室免費使用,然而地下室雖大卻沒有窗戶,根本不行。讓我深悟,我決定辦雜誌而資金不足,實在太大膽了。好在經由社委黃瓊華與文大教授游麗嘉的牽線,我認識了當時美國亞洲協會(現稱亞洲基金會)駐台的代表謝孝同及其秘書王世榕,他們非常關心台灣政治、社會的發展,對女權運動很支持。沒想到我與亞協駐台代表謝孝同相談甚歡,竟可以《婦女新知》這麼小的雜誌,向亞協申請主辦第二年婦女節「8338婦女週」的大活動,申請到的經費是一萬美金(40萬元台幣),對當時《新知》而言真是一筆巨款!因為有亞洲協會做後盾,也說動了中國時報生活版與我們在師大合辦演講及宣傳;目前寫旅遊、美食的專欄名家韓良露也幫忙策劃主持「女性電影」,借到電影圖書館放映並討論。記得我去各單位洽談時,說明這是亞協補助的計劃就頗具份量,好似我的身分地位也因此抬高不少。其實,我對自己的社會不關心婦女問題有些氣悶,對我非要拉著老美(亞協)才能說服社會的情況也頗為失望,然而現實也只能如此做下去。
三、8338婦女週
利用第二年的三八婦女節,《新知》開始緊鑼密鼓地籌辦「8338」婦女週。活動從3月5日-10日七天,每天從早上10點到晚上9點,包括展覽、文藝活動、座談、演講及女性電影。前三項在主要的會場即在台北市復興南路的文苑,演講在師大綜合大樓,而女性電影分多場在電影圖書館放映。展覽有七項:家庭計劃圖片及婦科診療室展(林永豐、陳文龍醫師是顧問),有各種避孕器具的展出,相當吸引婦女的目光;台灣婦女雜誌大展(1982-1983年1、2月雜誌),在大本的彩色的美女封面雜誌前,《婦女新知》雜誌實在不起眼,只能說她是一顆女性意識的種子;還有簡扶育、許大雯的婦女生活攝影展及向中國女權運動者致敬等展覽。演講以李豐、李昂、林菊枝律師的聽眾較多,座談會以徐慎恕主持的「創造性的主婦生活」最多婦女參加,我與柏楊對談「男女如何互相學習」也吸引很多人,觀眾多半衝著柏楊而來。記得不少姊妹擔心我會講不過鼎鼎大名的作家柏楊,我安慰大家說,柏楊雖在某些方面擁有知識,但在兩性方面的新知絕對比不過我,對談之後大家不只放心還很興奮,因為柏楊口才雖好,兩性觀念平平,被我挑戰之處甚多。其實不只柏楊,當時一些進步的男作家如陳映真都不以女性觀念落伍為恥的,我也在《新知》第七期批評過李敖的「大男人主義」,我還特別將這本小雜誌寄給他,自稱大師的李敖卻完全不予理會。韓良露主持講評的三部女性電影:《兄弟姊妹》(性政治的呈現)、《失聲呼叫》 (女性被強暴的問題)、《後勤女工》(二次大戰時美國女性加入各類工廠,戰爭結束又後被解雇,帶出種族及性別歧視等問題),這三部租來的金馬獎外片,不只內容有女性的視角,也同時檢討電影形式的掌握與欺瞞問題。此時《新知》文章比較強調「女性意識」,但韓良露從電影的講評中卻帶出「女性主義」這個1990年代後開始在台灣社會流行起來的名詞。
《新知》雖然是不起眼的小雜誌,由於我也支持黨外的民主運動,與當時自立晚報社的許多人認識,自立晚報副刊主編向陽對我辦雜誌及「8338」婦女週活動很支持。自晚在這年的婦女節前一天及當天都製作女性專輯,3月7日由應鳳凰、鐘麗慧策劃在自立副刊三月號的「出版月報」報導了「出版界的十位傑出女性」:林海音、姚宜瑛、吳美雲、殷允芃、鄭淑敏、李元貞、柯元馨、李王秋香、嚴友梅、孫小英,且有照片登載。將我以「婦女新知月刊發行人」的身分介紹出來,竟可以與幾位國內女性大出版家一起現身,讓我既興奮又慚愧。3月8日自晚的11版以「女性們請站出來」為標題,藉婦女節介紹三位成功的現代女性:文建會第三處處長申學庸、實踐家專校長林澄枝、婦女新知發行人李元貞。申學庸的主張是「先齊家,再談其他」、林澄枝的主張是「工作時,忘記自己是女性」、我的主張是「自覺,走出傳統」,也有照片登載。有趣的是其他兩位的採訪記者掛本名,分別是楊淑慧、張慧英,我的採訪記者只掛筆名「悒攸」。中國時報答應與《新知》合作宣傳婦女週,展覽的報導不錯,《新知》辦公室電話響個不停,使《新知》月刊當年的訂戶達到800多名,這似乎是《新知》雜誌訂戶最多的一次。以後《新知》再怎麼努力,都只能保持500-600個訂戶左右,媒體的力量由此可見。《時報雜誌》發行人鄭淑敏說話算話,婦女節當期雜誌刊出楊美惠與我做封面人物,對台灣婦運做了傳承的介紹,我這才得知楊美惠曾與歐陽子合譯波娃的《第二性》,她又出過《婦女問題新論》一書,對我做婦運的思想啟發不少,往後更寫信鼓勵《新知》,我十分感謝。在報紙只能出三大張的時代,這些報導,加上《時報雜誌》的宣傳,讓我個人一時比《新知》還出名,對推展婦運確實有些幫助。
在8338婦女週活動中,不少婦女留下姓名、地址,5月我們開始組織「讀者聯誼會」,每月一次,由會員決定講題,也由會員輪流主講,家庭主婦參與者甚多,徐慎恕、林美絢、暢曉雁、余善如是骨幹,後來賴玉枝亦積極加入,「讀者聯誼會」也成為《新知》社內的進修活動,大家討論越多,感覺婦女問題的解決越迫切。慎恕在第二年的16期起開始做《新知》雜誌的編輯工作,林美絢也接下讀者聯誼會的主持工作,曉雁經常來《新知》做剪報、整理資料,必要時寫書評支援《新知》,賴玉枝也寫親子文章在《新知》發表。《新知》16期的封面人物是李素秋,討論的專題:「社會變遷中的主婦角色」,《新知》內文不但肯定家庭主婦的家務勞動,而且說明家庭主婦角色的複雜性:妻子、母親、女傭的三結合,其「無酬」的生產性與服務性卻被父權社會以「愛」之名遮蔽。再經過《新知》1985的「家庭主婦年」的婦女節活動,呼籲「家庭主婦再發展」,埋下徐慎恕1986創辦「新環境主婦聯盟基金會」的種子。同時,參與8338婦女週主持「互助的力量——離婚婦女聯誼會」座談的林蕙瑛教授,往後與許多離婚婦女聚會,在1985成立「拉一把協會」,是1988施寄青正式成立「晚情協會」的前身。同時亞協駐台代表謝孝同介紹姜蘭虹與我及燕翎認識,姜蘭虹也參加了8338婦女週活動,我們一起說動亞協支持成立婦女研究資料中心,希望婦女研究能成為婦運的後盾。1985《新知》積極幫助姜蘭虹召開「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在亞協的資助下姜蘭虹成立「台大婦女研究室」。可以說8338婦女週最大的影響是召喚了不少婦女關心自己切身的問題,產生積極組織新社團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