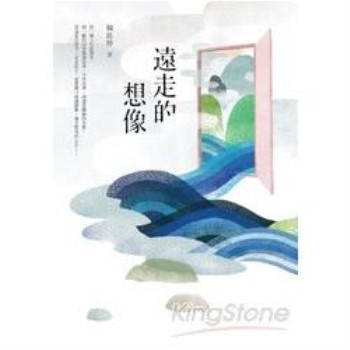雪見晴雨
遇見這美麗的名字,我便著了迷。雪見、雪見,念茲在茲。想像著一幅清新冷冽的圖景。見字超然輕盈,少了觀看的刻意,也沒有著意相望的機心,簡簡單單,僅是悠然而見。不沾染也不驚動,脫俗的意境在我的腦海中擴大蔓延,我翻查著雪霸國家公園的資料,計畫前往雪見的各種可能。
資料上說,雪見是雪霸國家公園繼武陵和觀霧後設立的遊憩據點,海拔兩千公尺左右,年均溫攝氏二十度以下。北起樂山、北坑山、東洗水山、東流水山稜線,往南延伸至盡尾山稜線的司馬限林道上,林相完整而原始。因為地勢和坡向使然,身在其中,能盡覽雪山和大霸尖山、小霸尖山連綿而成的「聖稜線」,乃至於往西南延展至火石山、大雪山、頭鷹山、中雪山、小雪山,峰峰相連迢接而成「雪山西稜線」。
看著書上羅列成串的山名,彷彿涉入另一世界的語彙。陌生巍峨的山名聳立面前,圈圍出高山仰止、山行艱難的神聖氛圍,一如世間常態,希絕的美,總帶著難以觸及攀越的遺憾。闔上書頁。停止對雪見之名的種種想像,如常走踏於熙攘街市。島嶼大山的壯景,想當然爾的感動,翻查檢索愈多,心中的負擔愈重,那儼然是一處遙不可及的夢土。
囿於現實考量後的結論,雪見之行如同冬日覆蓋在雪山諸峰上的皚皚白雪,天宮雲闕,遙遠而虛幻。一直這樣自我設限著。
是怎樣的心念流轉,如今也很難說清了。好似突然之間,有了不太在意結論的勇氣,心念很單純:就出發吧,去看看,看看而已,不一定非要怎樣。
我學著哄騙自己內心的不安。出發。那情境相當不真實,我確實在前往夢土的路上。
沿著太平、大坑、新社、東勢、卓蘭……,穿行小鎮,車途迢遠。鄉間道路,一貫的迂迴彎轉,放眼望去,農田果樹層出迭起,綠野盈疇,在車速中匆匆瞥逝。
一路駛至大安溪堤防。順著堤防曠闊的天景前行,路旁停放不少車輛,全是慕名而來。九二一大地震造成臺灣中部莫大損害,山迸地裂,無端震出大安溪河谷宛若美國大峽谷似的地貌景觀。荒石嶙峋,堆疊陡峭。遊覽車、小客車沿堤防依序停放,風景煞是熱鬧。
右往和平鄉,左往白布帆。過了大紅色的烏石坑橋,路標顯示進入了達觀香川部落。達觀部落像個花園,社區道路間,花木扶疏齊整。我被路旁的指標「達觀部落共同廚房」吸引,循路而去,在一處原木搭築的棚舍外停了下來。
該如何言述眼前所見?隨遇而安的走看,卻有意外發現。這是泰雅族人共作共食的廚房,供餐給當地住民搭伙,也接受遊客訂餐。共同廚房空間質樸簡易,木棚外連接著一片庭園花木。牆上有今日菜單、分工輪值表。櫃臺前年輕的泰雅男子斯文緬腆,「團體桌菜可以事先預定,打電話來。」牆壁上張貼工作守則、注意事項等,那些書寫得密密麻麻、字跡歪斜的紙片,扎在布告欄上,每一張都是共同廚房努力經營的證明。
山中部落,一些人共同做一些事,看來平凡,想來卻很動人。離開達觀部落,經桃山部落、泰安鄉士林村、象鼻村……,雪見遊憩區的指標時有時無,山路彎轉,曲行分岔,屢屢教人疑心是不是錯走迷途。
行至天狗部落,按捺不住心底的擔憂,車子快沒汽油了,雪見還不知道離多遠。我在梅園派出所前停下來,問值班員警:「哪裡可以加油?」不料,員警竟然回答:「最近的加油站在卓蘭啊。大湖那裡。大約三十多公里。」我聽了十分吃驚,要就此放棄,折返下山了嗎?我心有不甘,卻又無可奈何。僅剩的汽油量,連能否安然抵達卓蘭市區都不可知,何況是繼續朝雪見之路前行呢?
只能悻悻然下山了。
雪見初旅,大老遠的奔赴行駛,最終卻是徒勞一場。未竟的遺憾在心底積釀為一股堅決的動力,未完成的缺憾,隱隱發芽為一個待完成的心願。一定要再去,一定要抵達。
再訪雪見。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海上颱風警報剛剛發布,眼前天氣還很晴朗,山區天候路況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帶著戒慎忐忑的心情出發,我格外珍惜再訪的機緣,細細記憶著路途上的景觀。那些我不知道的故事,在地的、極為鄉土氣息的種作勞動,隨車速拂掠而過。之於鄉鎮日常,農林果樹,我又多認識了一些,理解了一些。
竹林派出所、摩天嶺甜柿專業區、達觀國小、桃山部落、士林大壩、麻必浩部落、梅象橋、天狗部落……,我牢牢指認途經之地,害怕記不住,辜負了這一路渾然樸實、不假雕飾的山地風光。
在梅園派出所辦理入山證。員警認出我來,笑著問:「這次有加滿油了吧?」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員警好意提醒:「小心開車,颱風可能會來。」
天色確實陰濛,雨的可能混雜山嵐氣息,草葉微腥的濕氣發散在空氣裡,像一張霉濕森鬱的臉。第二回合的遭逢,我怎能就此罷休?司馬限林道鋪展在面前,山壁聳立危峭,天和地順著路形蜿蜒盤旋,窄小路面密密披散著闊葉、落葉林木,我像是一瞬間被整片深邃的綠簇擁著,樟樹、櫟樹、油桐、臺灣赤楊……,胡亂辨認著少數幾種,滿眼的綠深淺濃淡,教人眼花撩亂。
林道中途,夾道松林密布,天地也隨之清朗。這是司馬限林道上,名為「二本松」的解說站。解說站周遭,步道通闊天然,蒼松挺拔入雲,布置出一片幽深靜謐的森林。
途中偶有雕塑臺灣黑熊、山豬等山林意象,加以泰雅族的雕刻和圖騰,空氣鮮涼冰透,讓人放鬆得渾然不知「二本松」,日治時期是一條警備道,今日的解說站,是當年的駐在所。為了監控、壓制的手段,大安溪畔河階平台更設置了丸田砲台。不只在霧社,這裡也有一頁泰雅族人和日警激烈交戰的史詩。
循山徑前行。山樹林木,高大茂密的枝椏葉脈,層層疊疊映襯著天空。幾乎是不見天的遮蔭。鳥語聲吱吱嘎嘎、嘰嘰喳喳,混著蟲鳴嘁嘁,蟬鳴噪鬧。露天立體聲響大鳴大放,東一陣、西一陣,分不出是此起彼落,還是彼落此起,身在其中,只覺得雙耳忙不來聽。大自然的交響如此震撼,而我踩踏前行的節奏,步履起落間,腳畔枯葉沙沙、細土碎石揚起滑動的聲響,也襯著鳥語蟲鳴,成為交響的底蘊。
拔地而起的香杉林,在二本松樹景裡,最為森然動魄。通往丸田古砲台遺址的小徑,穿行一片鬱鬱蒼蒼的古杉群。歷史的破口在哪裡,日治時期,日警用以轟炸、恫嚇原住民的大砲就藏覆在杉林密生的台地上。激烈的戰鬥,以血肉之軀抵抗火砲的故事,如今只剩這片廣袤幽閉的古杉林為證。
攀行至此,安靜聆聽周遭。靜。四方八面,靜得只餘下我的喘息和胸膛怦怦搥擊的心跳。我環視這荒蕪的台地,古砲台的遺址。古砲早已遺失了,歷史彷彿也靜了下來。古杉林人跡罕至,木本植物叢聚蔓生,遺址或將湮滅,裂隙或被修補了。
終於抵達雪見遊客中心時,心情反倒沒有想像中激動。也許是沿線鋪陳連貫的景致,沖淡了詫然和驚喜。情境中理所當然的安適、明白。雲端的雪見,不再只能仰望,蜿蜒攀升、匝繞盤旋,終也置身雲端之後,不再虛浮、懸空,抵達車行終站,有一種心安的究竟。
日光出奇得好。光影酡黃潑灑的氣勢,如烈酒,在透白天色中微微暈染一筆,就有令人醉倒的濃度。不到雪見,不知道晴朗的極致。我的視覺還沒從灰冷色調轉換過來,天幕卻一下子變出搶眼的夏妝。
看似平凡無奇的步道,低開發的原始山林感,相較於臺灣他處知名的步道景區,少了人工設施的干擾,素顏天成,山野林木的脾性都在,枝條披垂、順性擴長,泥徑上一落落深積的乾枝枯葉……,純天然的野生野長,沒有驚擾,也無須管理。
山林之妙,在於環境與天候交映下,無常變幻的景致。此刻行進,不同於二本松步道的森鬱。篩了金粉的日光,疊合不規則的樹影葉隙,灑下一閃一閃細碎晶亮的光芒。光影的魔法點染在樟樹林、櫟樹林之上,透光的樹葉是枝幹上薄薄的玉片,通透的翠,簡直是顯微鏡下的無瑕。
無瑕的還有大自然高深莫測的幻術。當我正仰著臉,瞇著眼縫細瞧那星星點點的陽光,豆大的、迅及的雨珠便叮叮咚咚霹靂啪啦落了下來。
日光都還沒撤場,急雨已經千軍萬馬趕到。我想仿效那不聽穿林打葉聲的超然姿態,在茂密林葉遮蔽下,文風不動深入前行。濃霧紛至,雨水和霧氣飄漫在空氣中,腳下泥水橫流,路形也愈見積溽模糊。我想著派出所員警的提醒,以及方才晴暖的天候,這大剌剌的暴雨,不知該說是意料之內,或意料之外。
雨中空景,我在泥漿路面屏息挪行。大雨打在臉上,冰涼醒腦。我小心避開泥濘中浸濕的落葉,那相當滑腳,稍不留神就會失衡跌跤。
今日,我該是雪見遊客中心裡,最狼狽的旅者了。當我從天然林道的滂沱暴雨中,走出,終於得以暫避於遊憩中心的木簷下。正嘀咕這雨來得太急,忘了找聖稜線啦。我下意識用手抓擰濕答答的長髮,彎身一瞥,玻璃窗內,穿著制服的替代役、巡山員正安安穩穩喝著咖啡,不經意看著我。西螺橋影
我想說一段橋的故事。在生命的此岸和彼岸之間,屬於舊時代,已漸漸湮沒的輝煌。像是追溯一座橋的身世,記憶那些途經片刻的印象,然後也藉此拼貼出我們的時代,在時間和空間的座標上,找到自己的歷史。
河面廣闊的濁水溪,向來是臺灣中部重要的分界河。十六世紀歐洲人繪製的臺灣地圖,甚至誤將臺灣分隔為南北兩島。濁水溪以南,屬熱帶氣候;濁水溪以北,屬亞熱帶氣候。就連政治認同的板塊劃分,也以濁水溪為界。
南北上下,空無的天際線接合著平廣曠漠的溪面,冬日溪水枯竭,夏日急流滔滔,西螺大橋橫亙在濁水溪之上,彷彿是一道溝通的彩虹,連結彰化縣溪州鄉和雲林縣西螺鎮。在公路初始的年代,壯闊簇新,猶如新時代的標誌,夢一般的通道貫串西部平原。
經彰化往雲林。鄉間農村的景致,路旁大面積的農地種作,構成綠的圖景。路樹野草,自生自長的天然與雜蕪,無人照管卻有在地的蓬勃生氣。鄉間道路,車輛不多,路形筆直,無遮蔽的空曠感,有一點貧乏的意味。
臨路偶見,舊朽的屋形,二、三樓水泥房宇,大多蒼老。破損的水泥牆,半漏餡的老磚塊,裂隙與水漬混著綠蘿似的藤蔓爬成壁面癌狀的年輪。臺灣小鄉鎮,相對困窮的農村,日昇月落、日復一日的種作勞動。偶然迎面見到一台鐵牛車噗噗而過,或是改裝的三輪貨車引擎聲嗶嗶啵啵,緩速通行。老者的面容,瘦?健朗的身形,這裡還是老臺灣、舊時光,不發達的單純日子。
光陰慢悠悠挪移。記憶裡的西螺,理所當然來自西螺大橋。童年時光,和阿嬤或父母到南部旅行時,遊覽車必經之地。那些民營公路休息站,婆婆媽媽爭相購買的特產,名號響亮的西螺蔭油,傳統道地。玻璃矸仔裝,祖傳祕方或黑豆或黃豆怎樣繁複釀製而成的純天然口味。進香團或老人會,各項名目組織而成的村鄰遊覽觀光團,西螺的名號響叮噹,沒拿它幾瓶半打蔭油豆腐乳,似乎就沒了坐遊覽車出遊的憑證。
幼年懵懂的印象裡,西螺是熱鬧的,比家鄉先進繁盛的商鋪市集、人車聲浪匯聚成一種仰望的高度。彷彿提到西螺,就與去哪裡遊覽劃上等號。西螺大橋是濁水溪的門戶,更是劃時代建設的里程碑。從阿嬤那一輩老人家口傳而來諸如偉大、厲害之類的形容詞,加上屢次自遊覽車司機口中聽來的名詞與掌故,濁水溪上的西螺大橋,全長一九三九公尺,是當時遠東第一大橋,世界第二大橋。北往南來,全台各地的遊覽車穿行在鮮紅色的鋼橋上,也有遊客要求在大橋前停車,專要與橋頭「西螺大橋」四字合影留念的。
翻查這座橋的身世,一九三七年開工興建,卻在一九五三年才落成。當時,地方人士成立「西螺架設濁水溪人道橋同盟會」向日本總督府上書陳請,當局批准後開始興建工程。然而,工程進行期間,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將鋼梁材料等轉供戰備使用,築橋的工程不僅停頓,隨著戰爭情勢的演變,復工之日也遙遙無期。
日本戰敗,臺灣光復。在中美友好關係的基礎下,美方援助購買橋梁鋼材的經費一百多萬美金,國民政府成立西螺大橋工程處,中斷多時的工程才又有了延續與開始。
日人架設的橋墩,美援購得的鋼梁,在動力機具匱乏的年代,由本國工程人員苦心研究、設計、組裝而成。沒有經驗可循,全憑一顆愛國的心,在那樣的年代裡,彷彿再困難的工程,只要咬緊牙關,都可以順利完成。
立大樁、排架、裝樁、鉚釘、油漆、橋面、調整拱度、拆架去樁等,每個步驟都是關卡;河床地質、氣象、水文、地震、機具、人工等,每個環節都是學問。橫跨在濁水溪之上的橋梁建築史,有日治時期的印記,有中美邦誼的證明,有臺灣人為家鄉流淌血汗、奉獻生命的光輝。
造橋鋪路,跨越的不只是濁水溪岸的距離,連接的也不只是溪州鄉和西螺鎮。拱型鋼構設計,新穎簡潔,橋面鋪以鋼筋混泥土,不論材料或工法都是世界級的先進指標。跨時代的連接,象徵著可預期的現代化繁榮,那是一個起點,南北貫通亟欲起飛的臺灣。
一座橋,有一個時代的縮影。幾代人殷殷企盼,在西螺大橋通車之前,南北兩地居民若要過溪,必須依靠船隻擺渡,每當夏季溪水暴漲,常處於涉險通行或大水阻隔的困境裡。長久以來,自然環境區隔出溪之南、溪之北,這一刻,以人的力量築成了鋼橋,穩固了島嶼內往來的基礎。
曾聽一名老司機轉述那場轟動全台的通車典禮,鑼鼓喧天、萬頭攢動的盛況,人人歡天喜地,熱鬧如同迓媽祖。父親也說,他的小學課本裡,有一課課文就是歌頌西螺大橋氣派恢弘的美景。當時新台幣十元紙鈔,正面印刷的圖像,就是西螺大橋的橋影。
我還記得阿嬤說起這座橋的鮮活口吻:「有一次神明生日辦活動,信徒們扶老攜幼,前簇後擁跟著神輦走,走著走著,火車突然來了,大家趕緊閃躲到一旁去,有人沒處躲了,乾脆跳到橋下沙洲去!橋下沙洲都種西瓜,西螺橋下種出來的西瓜,全臺灣最好吃的……」
西螺大橋的獨到處,除了雙向汽車道之外,南下車道還鋪有台糖小火車的輕便軌道,每當火車開上西螺大橋,南下車道上的人車得儘速避讓,形成汽車與火車並馳的奇景,乃至於阿嬤口中驚險逗趣,有滋有味的場面。
橋影彷彿。我佇立在橋邊,看這座有「遠東第一長虹」美稱的橋梁。鮮紅的漆色,在長期曝曬下,有些地方已經褪紅泛白。當年的輕便軌道,也因糖業運輸需求不再,加上每逢下雨軌道濕滑,屢屢造成車輛事故等因素,早在一九七一年拆除了。在陸續闢築中沙大橋、溪州大橋連接國道及省道後,西螺大橋的運輸地位,也由省級降為縣級,目前僅供小型車輛、機車、自行車通行。
曾經輝煌烜赫,對照之下的今日,確實是有點沒落寂寥了。
呼嘯而過的車輛很少。多是像我一般下車步行,沿著鐵橋順著欄楯縫隙朝橋外、往濁水溪底、溪水、溪岸四處張望閒看的遊人。
這裡並不是風景區,四周卻有一些走著、看著的人。我不知道他們在找什麼、看什麼?眼前無遮蔽的天景,在日色中透閃著赤藍的光影。天空亮得很純粹,幾乎是毫無保留的藍與空白。濁水溪岸在岩層、石壁、風化的想像裡,如層疊歧出異變的地殼地質。溪底泥石淤積為平整的埔地,崎嶙怪石,長草雜樹,混生其間,綠得幽幽閉閉,這裡那裡,掩映出泥地土徑。仔細一看,光影竄入竄出,幾名孩童光著腳丫子奔跑追逐,捉迷藏似地嬉鬧。
都說這座大橋該拆了。
每次維修的經費龐大,鐵橋在風吹、日曬、雨淋中,早就斑駁鏽蝕,老態盡出。若要再有天然的風雨災害,別說是抵禦不住,就算抵禦住了,只怕一身老骨幹也不堪修,總要封橋拆廢。
在經濟效益優先的聲浪中,屬於西螺大橋的光榮已經是上一代,乃至於更久遠之前的故事了。那存活於我記憶中,為之目眩絕美的紅橋夕照,在這當下,依舊鮮明燦亮。保橋運動,像是一件該做的事情,可是其中又有許多現實的無奈。
橋頭樹叢旁一條岔出的小徑,是新近規劃的自行車專用道。指標另一頭,指向親子戲水區,就在大橋周邊新闢的公路旁。「西螺大橋觀光文化園區」的名號,也許不是那麼容易架構起來。時空變異下,如何才能延續來自於土地的記憶和情感呢?
信步走向一旁鐵皮屋宇,一顆顆碩大肥綠的西瓜如石塊磊在牆角,剛從大卡車上傾倒下來的態勢,西瓜山似地堆了半屋子。我學著旁人點了一份西瓜,外帶。只見那個身形黑壯的男子,剁剁剁剁,飛快剖切瓜皮果肉,裝入塑膠袋,擲進竹籤。動作在一瞬間完成,又是下一份客人的西瓜剁剁剁。
陰暗簡陋的內室,擺放好幾張桌椅,牆上貼了許多紙片,有泛黃的報導也有名人留影的老照片。
回到橋頭。我在堤防邊等待今天的夕陽。想拍攝一張安靜的照片。看鏡頭裡的歲月,落日餘暉中的橋影。綠島光景
船身靠岸。從船艙內跨出,無遮蔽的透亮日光豔影閃動,螫得人睜不開眼。剛從連續漂蕩抖震的航行中踏上陸地,步履有點虛浮。碼頭邊熱絡繁鬧,待租賃的機車排列成規矩的歡迎隊伍,沿著海岸長堤展示著島嶼的觀光動力。處處都是等待船客上岸的業者,經營民宿或浮潛生意的店家,早把箱型車停靠在路旁,準備迎接登島的嘉賓。
小小的碼頭,人潮隨船期輻輳聚散著迎來送往的節奏:下行李、上行李,取機車、還機車。船隻靠港,遊客陸續上岸,岸邊準備登船的人龍,也早聚攏為長長一串。太陽的味道、此起彼落,招呼應答的人聲,沿海堤迆邐為一趟旅程的初始和終結。
都說這是一座火燒島了。可是島的景致卻很綠。
環狀公路沿海岸線闢築,島上的山景,島緣海上浮突的怪石礁岩,無邊際的太平洋,水色漫漫,我是鬱鬱熱風中騎行的旅者。方才碼頭、加油站前的人潮不知道哪裡去了,在這片空白的風景中,偶遇一二人跡,迎面擦身而去,有著奇特靜謐的基調。
幾艘船停泊在灣澳內,襯著海和天廣闊的藍與白,像一幅悠遠寫意的畫。
高地山巒,廢耕或是未開發的丘陵巨石上,覆蓋著各種綠色植被,野生野長,教人不知如何辨認起。最顯眼的是林投樹。沿海岸邊,到處都是。不尋常的荒野,蘭嶼土沉香、大葉山欖 、咬人狗、馬鞍藤、白榕、銀合歡、木麻黃……,滿眼的綠矮植物,叢聚為綠島強韌的地貌。
鼻頭角海岬邊,棉白雲絮勾勒著微藍的天景,白色的燈塔兀立在鮮綠的草坡上。情境太唯美休閒,而有布景道具般,拍戲現場的錯覺。綠島燈塔建築的意象,猶如天然畫面中簡潔明淨的標點。
我曾讀過燈塔的身世,那是一則船難救援的故事。當年美國籍油輪在綠島外海觸礁,美國人感念島民救災的義行,透過國際紅十字會捐獻建造而成。那時落海的婦孺老少,在海水中遽浮遽沉。島民的人力船、機動船在巨浪中設法奮進,冒險搭救。千鈞一髮,來自地球彼端,金髮碧眼、語言不通的外國人,在生死邊境,意外踏上這片原始純淨的土地,那是怎樣的心情?
我沿著燈塔外圍坡道步行。從島的視野望向海,又從海的視野回身,望向島。草坡的綠,在日光返照下,有著油油燦爛的光亮;海則是一面幽藍的鏡子,反射著午後天光,灼熱的白,鬱鬱的灰。不知覺便陷入了無可名狀的心情洞穴,反覆觀照的風景,突然轉換為內心沒有著落的空洞。空洞裡,只餘下薄薄的呼吸聲,也不思想,也不感性,卻有種不期然的新穎,如入無人之境。
沒料到可以獨享一方海色。無人跡的時刻,有種不真實感。礁石潮間帶,白色貝殼砂礫連綿延伸向海。那觸感極其潔淨,每一步履的起落,都能感覺到砂石於腳畔挪移唰動,卻沒有沙灘粉石裹滿腳掌的風塵。近灘海水,遠遠看是一泓綠色寶石,走近了俯看,卻清澈到可以晃動自己的影子。遠處一雙人影,蹲下身體,於水石交界處,細細摩娑腳邊的貝殼砂。像童心未泯的孩子,睜大眼搜尋貝殼石罅中,神出鬼沒的小蝦蟹。魚苗樣,肉眼可辨的游魚,在清淺的水光中游得滿地皆是,簡直是無涯際的魚塘。
熱愛潛水的友人,每年都來綠島。我曾看過他傳寄的海洋照片,熱帶海域中,珊瑚、水藻和鮮麗竄動的魚群,構成一幀幀內太空的奇彩。我喜歡「內太空」這個詞彙,相對於「外太空」,我們對海底世界的了解,確實同等貧乏。
天生莫名的懼水。我不曾嘗試過浮潛,但在這朗朗開闊,魚水粼粼的情境裡,卻興致勃勃想俯身而下,與魚共舞。
島上,租車行通常兼營潛水活動。我租機車的店家就是。返回機車行,穿上潛水裝備,隨教練來到浮潛區。「潛水就像呼吸一樣自然,不用刻意去想,你就會潛水啦!」教練的身材高而胖,是個熱情爽朗的台東人。「綠島這邊,大都是台東過來做生意的啦!來打工的也是。」他指了指一旁側肩抓著六七個救生圈男孩,男孩答腔「我都蘭來的,暑假來工作」。
男孩眼神溜溜,五官立體深邃。「綠島打工比較好找,暑假需要很多人手……」,我斷斷續續聽到男孩和同梯浮潛客的應答,「跟你們一樣坐交通船過來,住在這邊」。他個子不高,我猜想約莫是國中生年紀的孩子。等待浮潛前,我一直默默觀察他。
當我們走下潛水步道,隨著教練柔和的語調節奏,輕輕吸氣、慢慢吐氣,不疾不徐沒入海中。讓身體呈現無重力的漂浮狀態,海水溫柔的包覆著臉頰、身體,在手腳的舞動行進間,感覺海底寬闊廣袤,寧靜澄明的時空。
穿行於礁石間,各式各樣奇形怪狀的石珊瑚,拔尖隆起或凹突陷落,螢光色的魚群鑽竄嬉遊。這一刻,心領神會的悠游之樂,讓我胡亂想起莊子和惠施的濠梁之辯。若是身在這時代,能設身處地,親自體驗魚的快樂,說不定惠施也會愛上浮潛。
巨型的珊瑚,像是圖鑑放大了,立體投影於面前。遠近高低處,這裡那裡分不清是海葵或軟珊瑚,鮮麗燦目,觸手招搖。最容易辨認的就是小丑魚了,牠們也不怕人,列隊成群迎面泅來,像是被逗樂的孩童,在人類的身軀周遭好奇又貪玩地窺探竄動。
仰起頭,慢慢漂回灘頭,踏著坑突稜銳的礁石上岸。自海裡、海面、岸上,一路悠悠晃晃,有種時空錯亂,猶如隔世的恍惚感。
我還處在「沒想到這就是浮潛」、「我也會浮潛」的興奮裡,脫下裝備,也不覺疲累,興致高昂決定迎著微涼的風,騎行繞島。「孔子岩」、「哈巴狗與睡美人」、「牛頭山」,那些被模擬為俏皮情狀的奇岩怪石,想像力天馬行空,在黃昏溫煦的夕照中,彷彿有令人會心一笑的魔法,擬人轉態,如童話中的世界。
流連忘返,直至夜幕低垂。在戶外曝曬終日,身體倦渴灼熱,亟需靜止休息。可是民宿老闆的話太誘人了:「等一下門口集合,夜訪梅花鹿!」
不想錯過這精采好戲,匆匆吃了晚餐,熱血沸騰騎上機車,跟著民宿主人,浩浩蕩蕩往黑夜裡的公路騎去。在少有光害的島上,空曠廣闊的原野、丘陵、礁石、海岸,夜騎如盲騎,靠著車頭燈照路,尾隨前車煞車燈,天地黑得亂七八糟,海浪聲、風聲,那規律的潮汐湧動、伴隨著車速呼呼颳起的晚風,那麼清楚而徹底地環繞交響著。
車流一群一群,夜遊探訪,幾乎是每家民宿業者力推的行程。機車群掠過風裡,迎面交會,或是後來居上側出超車,夜的時分,恐怕是這座沒有紅綠燈的島,交通最繁忙的時刻。
我在車流中,小心跟著。在天地的黑,車燈閃滅,車引擎聲來去間,辨認天幕荒野和太平洋拍擊岸礁的潮水。黑烏烏的人權文化園區,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名字鐫刻在大理石版上,密密麻麻,成千成萬。海聲、風切,低吼嗚嗚共鳴,平坦的地勢,一無遮蔽的赤裸海景,抬頭是一盤星羅棋布的碩亮。
上車。往彎道騎行。「那裡!那裡!」領頭者語調興奮,語速急促,揮舞示意著:關掉引擎,靠邊停車。
狀況外的我,有點不明所以。跟著圍行在草叢旁,向公路坡崖邊,四面八方,張望搜索。「那裡!那裡……」領頭者改以氣音發聲,彷彿發現神祕,害怕驚動。「哪裡?哪裡?」黑暗中有人窸窸窣窣提問,有人指著約略方向提點。「啊。有!亮亮的!」公路彎轉低坡處,草叢裡一雙如探照燈,炯炯晶亮的大眼。側一點、再低一點,長草後還閃爍躲藏了好幾盞偵察窺伺的目光!
同行的人,一時間全都沉默了。與梅花鹿遙遙對視的瞬間,我在這座島的夜色裡。涼風吹來潮濕的海味,薄薄鹹鹹,混著澀澀的草香。周圍的人倡議著,夜涼,不如往朝日溫泉走吧!嚷動的人車聲漸遠,我在落後離去的暗黑中回望,草叢裡眼色流轉,熾熾閃亮,彷彿螢火星光。
遇見這美麗的名字,我便著了迷。雪見、雪見,念茲在茲。想像著一幅清新冷冽的圖景。見字超然輕盈,少了觀看的刻意,也沒有著意相望的機心,簡簡單單,僅是悠然而見。不沾染也不驚動,脫俗的意境在我的腦海中擴大蔓延,我翻查著雪霸國家公園的資料,計畫前往雪見的各種可能。
資料上說,雪見是雪霸國家公園繼武陵和觀霧後設立的遊憩據點,海拔兩千公尺左右,年均溫攝氏二十度以下。北起樂山、北坑山、東洗水山、東流水山稜線,往南延伸至盡尾山稜線的司馬限林道上,林相完整而原始。因為地勢和坡向使然,身在其中,能盡覽雪山和大霸尖山、小霸尖山連綿而成的「聖稜線」,乃至於往西南延展至火石山、大雪山、頭鷹山、中雪山、小雪山,峰峰相連迢接而成「雪山西稜線」。
看著書上羅列成串的山名,彷彿涉入另一世界的語彙。陌生巍峨的山名聳立面前,圈圍出高山仰止、山行艱難的神聖氛圍,一如世間常態,希絕的美,總帶著難以觸及攀越的遺憾。闔上書頁。停止對雪見之名的種種想像,如常走踏於熙攘街市。島嶼大山的壯景,想當然爾的感動,翻查檢索愈多,心中的負擔愈重,那儼然是一處遙不可及的夢土。
囿於現實考量後的結論,雪見之行如同冬日覆蓋在雪山諸峰上的皚皚白雪,天宮雲闕,遙遠而虛幻。一直這樣自我設限著。
是怎樣的心念流轉,如今也很難說清了。好似突然之間,有了不太在意結論的勇氣,心念很單純:就出發吧,去看看,看看而已,不一定非要怎樣。
我學著哄騙自己內心的不安。出發。那情境相當不真實,我確實在前往夢土的路上。
沿著太平、大坑、新社、東勢、卓蘭……,穿行小鎮,車途迢遠。鄉間道路,一貫的迂迴彎轉,放眼望去,農田果樹層出迭起,綠野盈疇,在車速中匆匆瞥逝。
一路駛至大安溪堤防。順著堤防曠闊的天景前行,路旁停放不少車輛,全是慕名而來。九二一大地震造成臺灣中部莫大損害,山迸地裂,無端震出大安溪河谷宛若美國大峽谷似的地貌景觀。荒石嶙峋,堆疊陡峭。遊覽車、小客車沿堤防依序停放,風景煞是熱鬧。
右往和平鄉,左往白布帆。過了大紅色的烏石坑橋,路標顯示進入了達觀香川部落。達觀部落像個花園,社區道路間,花木扶疏齊整。我被路旁的指標「達觀部落共同廚房」吸引,循路而去,在一處原木搭築的棚舍外停了下來。
該如何言述眼前所見?隨遇而安的走看,卻有意外發現。這是泰雅族人共作共食的廚房,供餐給當地住民搭伙,也接受遊客訂餐。共同廚房空間質樸簡易,木棚外連接著一片庭園花木。牆上有今日菜單、分工輪值表。櫃臺前年輕的泰雅男子斯文緬腆,「團體桌菜可以事先預定,打電話來。」牆壁上張貼工作守則、注意事項等,那些書寫得密密麻麻、字跡歪斜的紙片,扎在布告欄上,每一張都是共同廚房努力經營的證明。
山中部落,一些人共同做一些事,看來平凡,想來卻很動人。離開達觀部落,經桃山部落、泰安鄉士林村、象鼻村……,雪見遊憩區的指標時有時無,山路彎轉,曲行分岔,屢屢教人疑心是不是錯走迷途。
行至天狗部落,按捺不住心底的擔憂,車子快沒汽油了,雪見還不知道離多遠。我在梅園派出所前停下來,問值班員警:「哪裡可以加油?」不料,員警竟然回答:「最近的加油站在卓蘭啊。大湖那裡。大約三十多公里。」我聽了十分吃驚,要就此放棄,折返下山了嗎?我心有不甘,卻又無可奈何。僅剩的汽油量,連能否安然抵達卓蘭市區都不可知,何況是繼續朝雪見之路前行呢?
只能悻悻然下山了。
雪見初旅,大老遠的奔赴行駛,最終卻是徒勞一場。未竟的遺憾在心底積釀為一股堅決的動力,未完成的缺憾,隱隱發芽為一個待完成的心願。一定要再去,一定要抵達。
再訪雪見。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海上颱風警報剛剛發布,眼前天氣還很晴朗,山區天候路況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帶著戒慎忐忑的心情出發,我格外珍惜再訪的機緣,細細記憶著路途上的景觀。那些我不知道的故事,在地的、極為鄉土氣息的種作勞動,隨車速拂掠而過。之於鄉鎮日常,農林果樹,我又多認識了一些,理解了一些。
竹林派出所、摩天嶺甜柿專業區、達觀國小、桃山部落、士林大壩、麻必浩部落、梅象橋、天狗部落……,我牢牢指認途經之地,害怕記不住,辜負了這一路渾然樸實、不假雕飾的山地風光。
在梅園派出所辦理入山證。員警認出我來,笑著問:「這次有加滿油了吧?」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員警好意提醒:「小心開車,颱風可能會來。」
天色確實陰濛,雨的可能混雜山嵐氣息,草葉微腥的濕氣發散在空氣裡,像一張霉濕森鬱的臉。第二回合的遭逢,我怎能就此罷休?司馬限林道鋪展在面前,山壁聳立危峭,天和地順著路形蜿蜒盤旋,窄小路面密密披散著闊葉、落葉林木,我像是一瞬間被整片深邃的綠簇擁著,樟樹、櫟樹、油桐、臺灣赤楊……,胡亂辨認著少數幾種,滿眼的綠深淺濃淡,教人眼花撩亂。
林道中途,夾道松林密布,天地也隨之清朗。這是司馬限林道上,名為「二本松」的解說站。解說站周遭,步道通闊天然,蒼松挺拔入雲,布置出一片幽深靜謐的森林。
途中偶有雕塑臺灣黑熊、山豬等山林意象,加以泰雅族的雕刻和圖騰,空氣鮮涼冰透,讓人放鬆得渾然不知「二本松」,日治時期是一條警備道,今日的解說站,是當年的駐在所。為了監控、壓制的手段,大安溪畔河階平台更設置了丸田砲台。不只在霧社,這裡也有一頁泰雅族人和日警激烈交戰的史詩。
循山徑前行。山樹林木,高大茂密的枝椏葉脈,層層疊疊映襯著天空。幾乎是不見天的遮蔭。鳥語聲吱吱嘎嘎、嘰嘰喳喳,混著蟲鳴嘁嘁,蟬鳴噪鬧。露天立體聲響大鳴大放,東一陣、西一陣,分不出是此起彼落,還是彼落此起,身在其中,只覺得雙耳忙不來聽。大自然的交響如此震撼,而我踩踏前行的節奏,步履起落間,腳畔枯葉沙沙、細土碎石揚起滑動的聲響,也襯著鳥語蟲鳴,成為交響的底蘊。
拔地而起的香杉林,在二本松樹景裡,最為森然動魄。通往丸田古砲台遺址的小徑,穿行一片鬱鬱蒼蒼的古杉群。歷史的破口在哪裡,日治時期,日警用以轟炸、恫嚇原住民的大砲就藏覆在杉林密生的台地上。激烈的戰鬥,以血肉之軀抵抗火砲的故事,如今只剩這片廣袤幽閉的古杉林為證。
攀行至此,安靜聆聽周遭。靜。四方八面,靜得只餘下我的喘息和胸膛怦怦搥擊的心跳。我環視這荒蕪的台地,古砲台的遺址。古砲早已遺失了,歷史彷彿也靜了下來。古杉林人跡罕至,木本植物叢聚蔓生,遺址或將湮滅,裂隙或被修補了。
終於抵達雪見遊客中心時,心情反倒沒有想像中激動。也許是沿線鋪陳連貫的景致,沖淡了詫然和驚喜。情境中理所當然的安適、明白。雲端的雪見,不再只能仰望,蜿蜒攀升、匝繞盤旋,終也置身雲端之後,不再虛浮、懸空,抵達車行終站,有一種心安的究竟。
日光出奇得好。光影酡黃潑灑的氣勢,如烈酒,在透白天色中微微暈染一筆,就有令人醉倒的濃度。不到雪見,不知道晴朗的極致。我的視覺還沒從灰冷色調轉換過來,天幕卻一下子變出搶眼的夏妝。
看似平凡無奇的步道,低開發的原始山林感,相較於臺灣他處知名的步道景區,少了人工設施的干擾,素顏天成,山野林木的脾性都在,枝條披垂、順性擴長,泥徑上一落落深積的乾枝枯葉……,純天然的野生野長,沒有驚擾,也無須管理。
山林之妙,在於環境與天候交映下,無常變幻的景致。此刻行進,不同於二本松步道的森鬱。篩了金粉的日光,疊合不規則的樹影葉隙,灑下一閃一閃細碎晶亮的光芒。光影的魔法點染在樟樹林、櫟樹林之上,透光的樹葉是枝幹上薄薄的玉片,通透的翠,簡直是顯微鏡下的無瑕。
無瑕的還有大自然高深莫測的幻術。當我正仰著臉,瞇著眼縫細瞧那星星點點的陽光,豆大的、迅及的雨珠便叮叮咚咚霹靂啪啦落了下來。
日光都還沒撤場,急雨已經千軍萬馬趕到。我想仿效那不聽穿林打葉聲的超然姿態,在茂密林葉遮蔽下,文風不動深入前行。濃霧紛至,雨水和霧氣飄漫在空氣中,腳下泥水橫流,路形也愈見積溽模糊。我想著派出所員警的提醒,以及方才晴暖的天候,這大剌剌的暴雨,不知該說是意料之內,或意料之外。
雨中空景,我在泥漿路面屏息挪行。大雨打在臉上,冰涼醒腦。我小心避開泥濘中浸濕的落葉,那相當滑腳,稍不留神就會失衡跌跤。
今日,我該是雪見遊客中心裡,最狼狽的旅者了。當我從天然林道的滂沱暴雨中,走出,終於得以暫避於遊憩中心的木簷下。正嘀咕這雨來得太急,忘了找聖稜線啦。我下意識用手抓擰濕答答的長髮,彎身一瞥,玻璃窗內,穿著制服的替代役、巡山員正安安穩穩喝著咖啡,不經意看著我。西螺橋影
我想說一段橋的故事。在生命的此岸和彼岸之間,屬於舊時代,已漸漸湮沒的輝煌。像是追溯一座橋的身世,記憶那些途經片刻的印象,然後也藉此拼貼出我們的時代,在時間和空間的座標上,找到自己的歷史。
河面廣闊的濁水溪,向來是臺灣中部重要的分界河。十六世紀歐洲人繪製的臺灣地圖,甚至誤將臺灣分隔為南北兩島。濁水溪以南,屬熱帶氣候;濁水溪以北,屬亞熱帶氣候。就連政治認同的板塊劃分,也以濁水溪為界。
南北上下,空無的天際線接合著平廣曠漠的溪面,冬日溪水枯竭,夏日急流滔滔,西螺大橋橫亙在濁水溪之上,彷彿是一道溝通的彩虹,連結彰化縣溪州鄉和雲林縣西螺鎮。在公路初始的年代,壯闊簇新,猶如新時代的標誌,夢一般的通道貫串西部平原。
經彰化往雲林。鄉間農村的景致,路旁大面積的農地種作,構成綠的圖景。路樹野草,自生自長的天然與雜蕪,無人照管卻有在地的蓬勃生氣。鄉間道路,車輛不多,路形筆直,無遮蔽的空曠感,有一點貧乏的意味。
臨路偶見,舊朽的屋形,二、三樓水泥房宇,大多蒼老。破損的水泥牆,半漏餡的老磚塊,裂隙與水漬混著綠蘿似的藤蔓爬成壁面癌狀的年輪。臺灣小鄉鎮,相對困窮的農村,日昇月落、日復一日的種作勞動。偶然迎面見到一台鐵牛車噗噗而過,或是改裝的三輪貨車引擎聲嗶嗶啵啵,緩速通行。老者的面容,瘦?健朗的身形,這裡還是老臺灣、舊時光,不發達的單純日子。
光陰慢悠悠挪移。記憶裡的西螺,理所當然來自西螺大橋。童年時光,和阿嬤或父母到南部旅行時,遊覽車必經之地。那些民營公路休息站,婆婆媽媽爭相購買的特產,名號響亮的西螺蔭油,傳統道地。玻璃矸仔裝,祖傳祕方或黑豆或黃豆怎樣繁複釀製而成的純天然口味。進香團或老人會,各項名目組織而成的村鄰遊覽觀光團,西螺的名號響叮噹,沒拿它幾瓶半打蔭油豆腐乳,似乎就沒了坐遊覽車出遊的憑證。
幼年懵懂的印象裡,西螺是熱鬧的,比家鄉先進繁盛的商鋪市集、人車聲浪匯聚成一種仰望的高度。彷彿提到西螺,就與去哪裡遊覽劃上等號。西螺大橋是濁水溪的門戶,更是劃時代建設的里程碑。從阿嬤那一輩老人家口傳而來諸如偉大、厲害之類的形容詞,加上屢次自遊覽車司機口中聽來的名詞與掌故,濁水溪上的西螺大橋,全長一九三九公尺,是當時遠東第一大橋,世界第二大橋。北往南來,全台各地的遊覽車穿行在鮮紅色的鋼橋上,也有遊客要求在大橋前停車,專要與橋頭「西螺大橋」四字合影留念的。
翻查這座橋的身世,一九三七年開工興建,卻在一九五三年才落成。當時,地方人士成立「西螺架設濁水溪人道橋同盟會」向日本總督府上書陳請,當局批准後開始興建工程。然而,工程進行期間,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將鋼梁材料等轉供戰備使用,築橋的工程不僅停頓,隨著戰爭情勢的演變,復工之日也遙遙無期。
日本戰敗,臺灣光復。在中美友好關係的基礎下,美方援助購買橋梁鋼材的經費一百多萬美金,國民政府成立西螺大橋工程處,中斷多時的工程才又有了延續與開始。
日人架設的橋墩,美援購得的鋼梁,在動力機具匱乏的年代,由本國工程人員苦心研究、設計、組裝而成。沒有經驗可循,全憑一顆愛國的心,在那樣的年代裡,彷彿再困難的工程,只要咬緊牙關,都可以順利完成。
立大樁、排架、裝樁、鉚釘、油漆、橋面、調整拱度、拆架去樁等,每個步驟都是關卡;河床地質、氣象、水文、地震、機具、人工等,每個環節都是學問。橫跨在濁水溪之上的橋梁建築史,有日治時期的印記,有中美邦誼的證明,有臺灣人為家鄉流淌血汗、奉獻生命的光輝。
造橋鋪路,跨越的不只是濁水溪岸的距離,連接的也不只是溪州鄉和西螺鎮。拱型鋼構設計,新穎簡潔,橋面鋪以鋼筋混泥土,不論材料或工法都是世界級的先進指標。跨時代的連接,象徵著可預期的現代化繁榮,那是一個起點,南北貫通亟欲起飛的臺灣。
一座橋,有一個時代的縮影。幾代人殷殷企盼,在西螺大橋通車之前,南北兩地居民若要過溪,必須依靠船隻擺渡,每當夏季溪水暴漲,常處於涉險通行或大水阻隔的困境裡。長久以來,自然環境區隔出溪之南、溪之北,這一刻,以人的力量築成了鋼橋,穩固了島嶼內往來的基礎。
曾聽一名老司機轉述那場轟動全台的通車典禮,鑼鼓喧天、萬頭攢動的盛況,人人歡天喜地,熱鬧如同迓媽祖。父親也說,他的小學課本裡,有一課課文就是歌頌西螺大橋氣派恢弘的美景。當時新台幣十元紙鈔,正面印刷的圖像,就是西螺大橋的橋影。
我還記得阿嬤說起這座橋的鮮活口吻:「有一次神明生日辦活動,信徒們扶老攜幼,前簇後擁跟著神輦走,走著走著,火車突然來了,大家趕緊閃躲到一旁去,有人沒處躲了,乾脆跳到橋下沙洲去!橋下沙洲都種西瓜,西螺橋下種出來的西瓜,全臺灣最好吃的……」
西螺大橋的獨到處,除了雙向汽車道之外,南下車道還鋪有台糖小火車的輕便軌道,每當火車開上西螺大橋,南下車道上的人車得儘速避讓,形成汽車與火車並馳的奇景,乃至於阿嬤口中驚險逗趣,有滋有味的場面。
橋影彷彿。我佇立在橋邊,看這座有「遠東第一長虹」美稱的橋梁。鮮紅的漆色,在長期曝曬下,有些地方已經褪紅泛白。當年的輕便軌道,也因糖業運輸需求不再,加上每逢下雨軌道濕滑,屢屢造成車輛事故等因素,早在一九七一年拆除了。在陸續闢築中沙大橋、溪州大橋連接國道及省道後,西螺大橋的運輸地位,也由省級降為縣級,目前僅供小型車輛、機車、自行車通行。
曾經輝煌烜赫,對照之下的今日,確實是有點沒落寂寥了。
呼嘯而過的車輛很少。多是像我一般下車步行,沿著鐵橋順著欄楯縫隙朝橋外、往濁水溪底、溪水、溪岸四處張望閒看的遊人。
這裡並不是風景區,四周卻有一些走著、看著的人。我不知道他們在找什麼、看什麼?眼前無遮蔽的天景,在日色中透閃著赤藍的光影。天空亮得很純粹,幾乎是毫無保留的藍與空白。濁水溪岸在岩層、石壁、風化的想像裡,如層疊歧出異變的地殼地質。溪底泥石淤積為平整的埔地,崎嶙怪石,長草雜樹,混生其間,綠得幽幽閉閉,這裡那裡,掩映出泥地土徑。仔細一看,光影竄入竄出,幾名孩童光著腳丫子奔跑追逐,捉迷藏似地嬉鬧。
都說這座大橋該拆了。
每次維修的經費龐大,鐵橋在風吹、日曬、雨淋中,早就斑駁鏽蝕,老態盡出。若要再有天然的風雨災害,別說是抵禦不住,就算抵禦住了,只怕一身老骨幹也不堪修,總要封橋拆廢。
在經濟效益優先的聲浪中,屬於西螺大橋的光榮已經是上一代,乃至於更久遠之前的故事了。那存活於我記憶中,為之目眩絕美的紅橋夕照,在這當下,依舊鮮明燦亮。保橋運動,像是一件該做的事情,可是其中又有許多現實的無奈。
橋頭樹叢旁一條岔出的小徑,是新近規劃的自行車專用道。指標另一頭,指向親子戲水區,就在大橋周邊新闢的公路旁。「西螺大橋觀光文化園區」的名號,也許不是那麼容易架構起來。時空變異下,如何才能延續來自於土地的記憶和情感呢?
信步走向一旁鐵皮屋宇,一顆顆碩大肥綠的西瓜如石塊磊在牆角,剛從大卡車上傾倒下來的態勢,西瓜山似地堆了半屋子。我學著旁人點了一份西瓜,外帶。只見那個身形黑壯的男子,剁剁剁剁,飛快剖切瓜皮果肉,裝入塑膠袋,擲進竹籤。動作在一瞬間完成,又是下一份客人的西瓜剁剁剁。
陰暗簡陋的內室,擺放好幾張桌椅,牆上貼了許多紙片,有泛黃的報導也有名人留影的老照片。
回到橋頭。我在堤防邊等待今天的夕陽。想拍攝一張安靜的照片。看鏡頭裡的歲月,落日餘暉中的橋影。綠島光景
船身靠岸。從船艙內跨出,無遮蔽的透亮日光豔影閃動,螫得人睜不開眼。剛從連續漂蕩抖震的航行中踏上陸地,步履有點虛浮。碼頭邊熱絡繁鬧,待租賃的機車排列成規矩的歡迎隊伍,沿著海岸長堤展示著島嶼的觀光動力。處處都是等待船客上岸的業者,經營民宿或浮潛生意的店家,早把箱型車停靠在路旁,準備迎接登島的嘉賓。
小小的碼頭,人潮隨船期輻輳聚散著迎來送往的節奏:下行李、上行李,取機車、還機車。船隻靠港,遊客陸續上岸,岸邊準備登船的人龍,也早聚攏為長長一串。太陽的味道、此起彼落,招呼應答的人聲,沿海堤迆邐為一趟旅程的初始和終結。
都說這是一座火燒島了。可是島的景致卻很綠。
環狀公路沿海岸線闢築,島上的山景,島緣海上浮突的怪石礁岩,無邊際的太平洋,水色漫漫,我是鬱鬱熱風中騎行的旅者。方才碼頭、加油站前的人潮不知道哪裡去了,在這片空白的風景中,偶遇一二人跡,迎面擦身而去,有著奇特靜謐的基調。
幾艘船停泊在灣澳內,襯著海和天廣闊的藍與白,像一幅悠遠寫意的畫。
高地山巒,廢耕或是未開發的丘陵巨石上,覆蓋著各種綠色植被,野生野長,教人不知如何辨認起。最顯眼的是林投樹。沿海岸邊,到處都是。不尋常的荒野,蘭嶼土沉香、大葉山欖 、咬人狗、馬鞍藤、白榕、銀合歡、木麻黃……,滿眼的綠矮植物,叢聚為綠島強韌的地貌。
鼻頭角海岬邊,棉白雲絮勾勒著微藍的天景,白色的燈塔兀立在鮮綠的草坡上。情境太唯美休閒,而有布景道具般,拍戲現場的錯覺。綠島燈塔建築的意象,猶如天然畫面中簡潔明淨的標點。
我曾讀過燈塔的身世,那是一則船難救援的故事。當年美國籍油輪在綠島外海觸礁,美國人感念島民救災的義行,透過國際紅十字會捐獻建造而成。那時落海的婦孺老少,在海水中遽浮遽沉。島民的人力船、機動船在巨浪中設法奮進,冒險搭救。千鈞一髮,來自地球彼端,金髮碧眼、語言不通的外國人,在生死邊境,意外踏上這片原始純淨的土地,那是怎樣的心情?
我沿著燈塔外圍坡道步行。從島的視野望向海,又從海的視野回身,望向島。草坡的綠,在日光返照下,有著油油燦爛的光亮;海則是一面幽藍的鏡子,反射著午後天光,灼熱的白,鬱鬱的灰。不知覺便陷入了無可名狀的心情洞穴,反覆觀照的風景,突然轉換為內心沒有著落的空洞。空洞裡,只餘下薄薄的呼吸聲,也不思想,也不感性,卻有種不期然的新穎,如入無人之境。
沒料到可以獨享一方海色。無人跡的時刻,有種不真實感。礁石潮間帶,白色貝殼砂礫連綿延伸向海。那觸感極其潔淨,每一步履的起落,都能感覺到砂石於腳畔挪移唰動,卻沒有沙灘粉石裹滿腳掌的風塵。近灘海水,遠遠看是一泓綠色寶石,走近了俯看,卻清澈到可以晃動自己的影子。遠處一雙人影,蹲下身體,於水石交界處,細細摩娑腳邊的貝殼砂。像童心未泯的孩子,睜大眼搜尋貝殼石罅中,神出鬼沒的小蝦蟹。魚苗樣,肉眼可辨的游魚,在清淺的水光中游得滿地皆是,簡直是無涯際的魚塘。
熱愛潛水的友人,每年都來綠島。我曾看過他傳寄的海洋照片,熱帶海域中,珊瑚、水藻和鮮麗竄動的魚群,構成一幀幀內太空的奇彩。我喜歡「內太空」這個詞彙,相對於「外太空」,我們對海底世界的了解,確實同等貧乏。
天生莫名的懼水。我不曾嘗試過浮潛,但在這朗朗開闊,魚水粼粼的情境裡,卻興致勃勃想俯身而下,與魚共舞。
島上,租車行通常兼營潛水活動。我租機車的店家就是。返回機車行,穿上潛水裝備,隨教練來到浮潛區。「潛水就像呼吸一樣自然,不用刻意去想,你就會潛水啦!」教練的身材高而胖,是個熱情爽朗的台東人。「綠島這邊,大都是台東過來做生意的啦!來打工的也是。」他指了指一旁側肩抓著六七個救生圈男孩,男孩答腔「我都蘭來的,暑假來工作」。
男孩眼神溜溜,五官立體深邃。「綠島打工比較好找,暑假需要很多人手……」,我斷斷續續聽到男孩和同梯浮潛客的應答,「跟你們一樣坐交通船過來,住在這邊」。他個子不高,我猜想約莫是國中生年紀的孩子。等待浮潛前,我一直默默觀察他。
當我們走下潛水步道,隨著教練柔和的語調節奏,輕輕吸氣、慢慢吐氣,不疾不徐沒入海中。讓身體呈現無重力的漂浮狀態,海水溫柔的包覆著臉頰、身體,在手腳的舞動行進間,感覺海底寬闊廣袤,寧靜澄明的時空。
穿行於礁石間,各式各樣奇形怪狀的石珊瑚,拔尖隆起或凹突陷落,螢光色的魚群鑽竄嬉遊。這一刻,心領神會的悠游之樂,讓我胡亂想起莊子和惠施的濠梁之辯。若是身在這時代,能設身處地,親自體驗魚的快樂,說不定惠施也會愛上浮潛。
巨型的珊瑚,像是圖鑑放大了,立體投影於面前。遠近高低處,這裡那裡分不清是海葵或軟珊瑚,鮮麗燦目,觸手招搖。最容易辨認的就是小丑魚了,牠們也不怕人,列隊成群迎面泅來,像是被逗樂的孩童,在人類的身軀周遭好奇又貪玩地窺探竄動。
仰起頭,慢慢漂回灘頭,踏著坑突稜銳的礁石上岸。自海裡、海面、岸上,一路悠悠晃晃,有種時空錯亂,猶如隔世的恍惚感。
我還處在「沒想到這就是浮潛」、「我也會浮潛」的興奮裡,脫下裝備,也不覺疲累,興致高昂決定迎著微涼的風,騎行繞島。「孔子岩」、「哈巴狗與睡美人」、「牛頭山」,那些被模擬為俏皮情狀的奇岩怪石,想像力天馬行空,在黃昏溫煦的夕照中,彷彿有令人會心一笑的魔法,擬人轉態,如童話中的世界。
流連忘返,直至夜幕低垂。在戶外曝曬終日,身體倦渴灼熱,亟需靜止休息。可是民宿老闆的話太誘人了:「等一下門口集合,夜訪梅花鹿!」
不想錯過這精采好戲,匆匆吃了晚餐,熱血沸騰騎上機車,跟著民宿主人,浩浩蕩蕩往黑夜裡的公路騎去。在少有光害的島上,空曠廣闊的原野、丘陵、礁石、海岸,夜騎如盲騎,靠著車頭燈照路,尾隨前車煞車燈,天地黑得亂七八糟,海浪聲、風聲,那規律的潮汐湧動、伴隨著車速呼呼颳起的晚風,那麼清楚而徹底地環繞交響著。
車流一群一群,夜遊探訪,幾乎是每家民宿業者力推的行程。機車群掠過風裡,迎面交會,或是後來居上側出超車,夜的時分,恐怕是這座沒有紅綠燈的島,交通最繁忙的時刻。
我在車流中,小心跟著。在天地的黑,車燈閃滅,車引擎聲來去間,辨認天幕荒野和太平洋拍擊岸礁的潮水。黑烏烏的人權文化園區,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名字鐫刻在大理石版上,密密麻麻,成千成萬。海聲、風切,低吼嗚嗚共鳴,平坦的地勢,一無遮蔽的赤裸海景,抬頭是一盤星羅棋布的碩亮。
上車。往彎道騎行。「那裡!那裡!」領頭者語調興奮,語速急促,揮舞示意著:關掉引擎,靠邊停車。
狀況外的我,有點不明所以。跟著圍行在草叢旁,向公路坡崖邊,四面八方,張望搜索。「那裡!那裡……」領頭者改以氣音發聲,彷彿發現神祕,害怕驚動。「哪裡?哪裡?」黑暗中有人窸窸窣窣提問,有人指著約略方向提點。「啊。有!亮亮的!」公路彎轉低坡處,草叢裡一雙如探照燈,炯炯晶亮的大眼。側一點、再低一點,長草後還閃爍躲藏了好幾盞偵察窺伺的目光!
同行的人,一時間全都沉默了。與梅花鹿遙遙對視的瞬間,我在這座島的夜色裡。涼風吹來潮濕的海味,薄薄鹹鹹,混著澀澀的草香。周圍的人倡議著,夜涼,不如往朝日溫泉走吧!嚷動的人車聲漸遠,我在落後離去的暗黑中回望,草叢裡眼色流轉,熾熾閃亮,彷彿螢火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