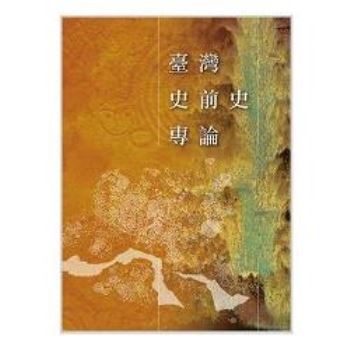遺址形成與土地利用──以鳳山隆起珊瑚礁為例
陳維鈞
一、前言
由於考古學的研究材料,在自然環境下,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營力和人為作用力的影響,而呈現不同程度的質與量的變化。此一現象,就是所謂的考古遺址形成過程,對於考古學的研究影響深遠。早期的考古學者以所謂的相關原理(correlate principle),將行為現象和物質在空間分布的現象相對應,認為物質文化是凍結的時空秩序組合,其最後堆積的情形,直接反映人類行為的最終歸宿。因此,認為從具有規律的器物組合關係模式,就可以用來推論過去的人類行為(Schiffer 1987)。這種考古學的推論過程,其前提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因為過去人類行為所產生的文化遺物和生態遺留證據,在自然環境中,明顯的受到無數次的多樣性文化和自然形成過程的影響。事實上,任何具有規律性的器物組合關係都是經過所謂的轉型過程(transformation)的結果(Schiffer 1975、1976)。因此,考古學者必須理解,並注意到考古遺址形成過程的理論,及其對考古遺址被發現機率的可能影響。不能只看考古遺址或文化遺物的外表或組合關係,就加以解釋過去人類的行為和文化,而應該審慎的考慮和完全的掌握有關的問題,例如考古資料是如何形成的,而形成過程又是如何影響考古資料、如何影響考古學者蒐集考古資料、以及形成過程如何影響到我們對考古資料的使用等。如此,考古學者才能理解考古資料的可能限制,繼而瞭解考古資料與人類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最後才能有效的針對考古出土資料,做出有意義的人類行為的解釋。也就是這個原因,考古遺址形成過程的研究,是各地學者,無論他們的學派隸屬是否相同,都必須正視的重要研究課題(陳維鈞 2000)。
考古學資料受到考古遺址形成過程影響的現象,在臺灣考古學發展的過程中,很早就被學者所提及。但是,有關遺址形成過程的探討與研究,卻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與重視。例如日治時期,宮本延人(宋文薰 1961:5)就曾提出東海岸史前遺址的分布比開發較早的西部平原為密集,是因為西部平原多已被開墾,遺址不易被發現之故。此一現象即說明了屬於文化形成過程範疇的人為擾亂過程,例如土地的開發行為,會破壞遺址,進而降低遺址被發現的機率。宋文薰師在〈臺灣的考古遺址〉一文中(1961),指出為何台南、台中、及台北諸平原上的史前遺址分布比較多,而嘉義、新竹、及宜蘭諸平地則較少,這是因為過去調查之細密或疏略所造成的緣故。此一觀察,很明顯的認識到考古田野調查次數的多寡、涵蓋範圍的密集程度、或調查方法對考古遺址發現機率的影響。調查次數愈多,調查方法愈密集者,則發現遺址的機率將愈大。另外,同文中,宋文薰師更指出由遺址的地理分布的情形來看,大致可以類推尚未被發現的遺址的可能所在,強調調查者應該對調查區域的現在及過去的地理環境變遷,以及其他自然背景知識有所掌握。例如台北盆地史前遺址多位於盆地邊緣;西海岸中部地方之史前貝塚遺址多位於后里、大肚、及八卦等台地的西側邊緣,距海不遠處;而台南地區之史前貝塚遺址多分布於台地邊緣,海拔約10公尺之高度上。這些現象,說明了自然形成過程對考古遺址的分布有絕對的影響。很可惜的,研究形成過程對考古學資料的影響,包括遺址的發現機率、遺址的保存狀況、乃至於考古學者對人類行為或文化的推論等,並沒有被深入的探討。僅偶而會出現在考古學的文獻中,以描述現象的方法,說出考古遺址或文化遺物可能遭受到的自然營力或人為作用力的擾亂(陳維鈞 2000)。
本文將以鳳山隆起珊瑚礁的考古遺址在時空架構下所呈現的考古學資料,來檢視考古遺址在空間上的分布情況,是如何受到考古遺址形成過程的影響?亦即根據遺址分布的時空關係證據,本研究試圖提出一套架構來解釋研究區內考古遺址分布的規律。基本上,由鳳山隆起珊瑚礁現有已知的遺址分布情形來看,並無法真正瞭解其中所包含的意義。因此有必要檢視其週遭區域的資料,例如高雄平原和屏東平原上同時期的史前遺址分布情形,如此才能有一個較為清晰的圖像。現有資料顯示,研究範圍區內的遺址分布多位於隆起珊瑚礁之上,雖然有少數遺址座落在丘陵前緣,或沖積平原較高的地帶上,但似乎多屬較為晚近的文化遺址。這種遺址在空間上不平均分布的現象,其造成的可能原因,也是本文想要探討的課題。二、遺址形成與土地利用
考古學這門學科的發展,可以被看成是對考古出土資料的理解和解釋的一種連續不間斷的研究過程。考古學的研究素材是人類行為所產生的物質遺留,包括了文化遺物和生態遺留,因此,對於物質文化所處的情境,有必要加以區分。基本上,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可以稱之為現生的系統脈絡(systemic context),它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動態行為系統;而考古脈絡(archaeological context)則表示當物質一旦進入考古體系中,就只和自然環境產生互動,基本上是屬於靜態的。在現生的系統脈絡中,物質文化的使用歷程,亦即物質文化的生命循環(life cycle),大致包括下列的幾個連續過程:首先是從自然環境中獲取所需的原料(procurement),然後依其工藝技術製造器物(manufacture),器物經過製造之後,再來就是使用階段(use),器物在使用的這段期間中,也可能會經過維修(maintenance),或被回收再製造(recycling),或再使用(lateral cycling),最後當器物損壞無法再使用時,則會被丟棄(discard),或可能在器物仍可使用的情況下,因為無意而被遺棄(lost)。當器物被丟棄或遭遺棄時,物質文化即不在屬於現生的行為系統,而進入了考古脈絡中,成為考古學的研究素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物質經由採集或發掘,在考古脈絡中的物質遺留將重新進入現生的系統脈絡。也就是說,物質可以在現生的系統脈絡和靜止的考古脈絡這兩種體系中來回的轉換(Schiffer 1972、1976:27-41)。
基本上,考古學的研究素材通常都是破碎、殘缺不全的物質遺留,當考古學者獲得之時,便思索著如何可以藉由實驗室的各種分析,歸納各項結果,從而進行人類行為,甚或社會文化的重建工作。換言之,就是想從靜態的考古脈絡中所得的資料,去探究這些物質遺留所反映的系統脈絡的動態行為體系。可以說是從所看到的物質遺留在空間上的聚集(或考古遺址的分布)的結果,而想辦法從這些物質遺留在所處地理環境所呈現的規律,如數量的多寡有無、類型的樣式變化、或分布範圍的大小等,去理解整個聚落系統。想要瞭解為何考古遺址會選擇在此地,而非彼地。也就是說,想從考古脈絡中的考古資料,思索著去回推到系統脈絡,進而試圖去重建和解釋人類行為的發展過程。考古遺址是考古學者研究的最基本單位,其定義可能因研究者的認知或研究旨趣,而略有不同。不過,基本上我們依然可以為考古遺址做一個簡單的定義:考古遺址就是一個物質遺留聚集的地點,而其物質遺留所提供的考古學資料,足以被用來判定人類行為與活動的性質。例如從遺址具有的功能可以區分為聚落遺址、狩獵遺址、作坊遺址、或墓葬遺址等。如果每一個考古遺址都是考古學者研究的一個樣本個體,那麼,考古學者的研究區域可以說就是研究的樣本空間(陳維鈞 2005)。在這個定義之下,本研究的樣本空間,即包括了鳳山隆起珊瑚礁,以及其緊鄰的高雄平原和屏東平原。
遺址地點的選擇,不論其類型是聚落遺址、狩獵遺址、作坊遺址、或墓葬遺址,在空間上的分布並不是隨機的(SARG 1974)。它反映了人類如何在土地利用上適應自然和社會環境的結果,尤其是聚落位置在空間上的選擇,更不是無義意的分布的,而是考慮人地關係和群際關係之後一系列選擇的結果。人類聚落的選擇不僅受到自然地理環境的限制,也受到人類本身創造出來的文化的制約。其中,自然條件的限制包括了地形(如坡度、高度、自然障礙等)、生業需求(如自然資源的多寡、季節分布、空間分布等,它包括了動、植物及原料等)、氣候(如溫度、濕度、日照、雨量、風向、風速等)、土壤(如所含養份的高低、適耕土地的分布)、水資源(如距水源的距離、多寡、和季節分布等)、以及其他(如生物種屬的競爭)。而文化的約束方面,則包括群際互動(如不同族群的競爭、合作)、族群認知(如對氣候狀況、環境狀況、資源使用選擇的知識,以及宇宙觀的認知等)、族群喜好(因文化選擇而有所不同,會表現在食衣住行上)、族群社會組織(如族群結構、社會組織等)、以及技術水平等(如工具的製作、資源取得、儲藏、運輸等方式)(參見Butzer 1982;Trigger 1968;Jochim 1981)。
就區域研究而言,聚落系統是由區域內一群不同類型的遺址所構成,每一個考古遺址,都是屬於該聚落系統的一個環節。所以說,在討論或者解釋人類行為的變異,以及社會文化的發展過程和變遷時,考古學者並不能,也無法只針對其中的一個遺址來做研究,而必需考慮到區域內聚落系統的每一個環節。也就是說,即使是研究區域內的某一個遺址,也應該整體考慮其所屬的聚落系統在自然環境下的空間分布,以及區域內各遺址之間相互關係的社會環境(SARG 1974)。
陳維鈞
一、前言
由於考古學的研究材料,在自然環境下,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營力和人為作用力的影響,而呈現不同程度的質與量的變化。此一現象,就是所謂的考古遺址形成過程,對於考古學的研究影響深遠。早期的考古學者以所謂的相關原理(correlate principle),將行為現象和物質在空間分布的現象相對應,認為物質文化是凍結的時空秩序組合,其最後堆積的情形,直接反映人類行為的最終歸宿。因此,認為從具有規律的器物組合關係模式,就可以用來推論過去的人類行為(Schiffer 1987)。這種考古學的推論過程,其前提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因為過去人類行為所產生的文化遺物和生態遺留證據,在自然環境中,明顯的受到無數次的多樣性文化和自然形成過程的影響。事實上,任何具有規律性的器物組合關係都是經過所謂的轉型過程(transformation)的結果(Schiffer 1975、1976)。因此,考古學者必須理解,並注意到考古遺址形成過程的理論,及其對考古遺址被發現機率的可能影響。不能只看考古遺址或文化遺物的外表或組合關係,就加以解釋過去人類的行為和文化,而應該審慎的考慮和完全的掌握有關的問題,例如考古資料是如何形成的,而形成過程又是如何影響考古資料、如何影響考古學者蒐集考古資料、以及形成過程如何影響到我們對考古資料的使用等。如此,考古學者才能理解考古資料的可能限制,繼而瞭解考古資料與人類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最後才能有效的針對考古出土資料,做出有意義的人類行為的解釋。也就是這個原因,考古遺址形成過程的研究,是各地學者,無論他們的學派隸屬是否相同,都必須正視的重要研究課題(陳維鈞 2000)。
考古學資料受到考古遺址形成過程影響的現象,在臺灣考古學發展的過程中,很早就被學者所提及。但是,有關遺址形成過程的探討與研究,卻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與重視。例如日治時期,宮本延人(宋文薰 1961:5)就曾提出東海岸史前遺址的分布比開發較早的西部平原為密集,是因為西部平原多已被開墾,遺址不易被發現之故。此一現象即說明了屬於文化形成過程範疇的人為擾亂過程,例如土地的開發行為,會破壞遺址,進而降低遺址被發現的機率。宋文薰師在〈臺灣的考古遺址〉一文中(1961),指出為何台南、台中、及台北諸平原上的史前遺址分布比較多,而嘉義、新竹、及宜蘭諸平地則較少,這是因為過去調查之細密或疏略所造成的緣故。此一觀察,很明顯的認識到考古田野調查次數的多寡、涵蓋範圍的密集程度、或調查方法對考古遺址發現機率的影響。調查次數愈多,調查方法愈密集者,則發現遺址的機率將愈大。另外,同文中,宋文薰師更指出由遺址的地理分布的情形來看,大致可以類推尚未被發現的遺址的可能所在,強調調查者應該對調查區域的現在及過去的地理環境變遷,以及其他自然背景知識有所掌握。例如台北盆地史前遺址多位於盆地邊緣;西海岸中部地方之史前貝塚遺址多位於后里、大肚、及八卦等台地的西側邊緣,距海不遠處;而台南地區之史前貝塚遺址多分布於台地邊緣,海拔約10公尺之高度上。這些現象,說明了自然形成過程對考古遺址的分布有絕對的影響。很可惜的,研究形成過程對考古學資料的影響,包括遺址的發現機率、遺址的保存狀況、乃至於考古學者對人類行為或文化的推論等,並沒有被深入的探討。僅偶而會出現在考古學的文獻中,以描述現象的方法,說出考古遺址或文化遺物可能遭受到的自然營力或人為作用力的擾亂(陳維鈞 2000)。
本文將以鳳山隆起珊瑚礁的考古遺址在時空架構下所呈現的考古學資料,來檢視考古遺址在空間上的分布情況,是如何受到考古遺址形成過程的影響?亦即根據遺址分布的時空關係證據,本研究試圖提出一套架構來解釋研究區內考古遺址分布的規律。基本上,由鳳山隆起珊瑚礁現有已知的遺址分布情形來看,並無法真正瞭解其中所包含的意義。因此有必要檢視其週遭區域的資料,例如高雄平原和屏東平原上同時期的史前遺址分布情形,如此才能有一個較為清晰的圖像。現有資料顯示,研究範圍區內的遺址分布多位於隆起珊瑚礁之上,雖然有少數遺址座落在丘陵前緣,或沖積平原較高的地帶上,但似乎多屬較為晚近的文化遺址。這種遺址在空間上不平均分布的現象,其造成的可能原因,也是本文想要探討的課題。二、遺址形成與土地利用
考古學這門學科的發展,可以被看成是對考古出土資料的理解和解釋的一種連續不間斷的研究過程。考古學的研究素材是人類行為所產生的物質遺留,包括了文化遺物和生態遺留,因此,對於物質文化所處的情境,有必要加以區分。基本上,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可以稱之為現生的系統脈絡(systemic context),它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動態行為系統;而考古脈絡(archaeological context)則表示當物質一旦進入考古體系中,就只和自然環境產生互動,基本上是屬於靜態的。在現生的系統脈絡中,物質文化的使用歷程,亦即物質文化的生命循環(life cycle),大致包括下列的幾個連續過程:首先是從自然環境中獲取所需的原料(procurement),然後依其工藝技術製造器物(manufacture),器物經過製造之後,再來就是使用階段(use),器物在使用的這段期間中,也可能會經過維修(maintenance),或被回收再製造(recycling),或再使用(lateral cycling),最後當器物損壞無法再使用時,則會被丟棄(discard),或可能在器物仍可使用的情況下,因為無意而被遺棄(lost)。當器物被丟棄或遭遺棄時,物質文化即不在屬於現生的行為系統,而進入了考古脈絡中,成為考古學的研究素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物質經由採集或發掘,在考古脈絡中的物質遺留將重新進入現生的系統脈絡。也就是說,物質可以在現生的系統脈絡和靜止的考古脈絡這兩種體系中來回的轉換(Schiffer 1972、1976:27-41)。
基本上,考古學的研究素材通常都是破碎、殘缺不全的物質遺留,當考古學者獲得之時,便思索著如何可以藉由實驗室的各種分析,歸納各項結果,從而進行人類行為,甚或社會文化的重建工作。換言之,就是想從靜態的考古脈絡中所得的資料,去探究這些物質遺留所反映的系統脈絡的動態行為體系。可以說是從所看到的物質遺留在空間上的聚集(或考古遺址的分布)的結果,而想辦法從這些物質遺留在所處地理環境所呈現的規律,如數量的多寡有無、類型的樣式變化、或分布範圍的大小等,去理解整個聚落系統。想要瞭解為何考古遺址會選擇在此地,而非彼地。也就是說,想從考古脈絡中的考古資料,思索著去回推到系統脈絡,進而試圖去重建和解釋人類行為的發展過程。考古遺址是考古學者研究的最基本單位,其定義可能因研究者的認知或研究旨趣,而略有不同。不過,基本上我們依然可以為考古遺址做一個簡單的定義:考古遺址就是一個物質遺留聚集的地點,而其物質遺留所提供的考古學資料,足以被用來判定人類行為與活動的性質。例如從遺址具有的功能可以區分為聚落遺址、狩獵遺址、作坊遺址、或墓葬遺址等。如果每一個考古遺址都是考古學者研究的一個樣本個體,那麼,考古學者的研究區域可以說就是研究的樣本空間(陳維鈞 2005)。在這個定義之下,本研究的樣本空間,即包括了鳳山隆起珊瑚礁,以及其緊鄰的高雄平原和屏東平原。
遺址地點的選擇,不論其類型是聚落遺址、狩獵遺址、作坊遺址、或墓葬遺址,在空間上的分布並不是隨機的(SARG 1974)。它反映了人類如何在土地利用上適應自然和社會環境的結果,尤其是聚落位置在空間上的選擇,更不是無義意的分布的,而是考慮人地關係和群際關係之後一系列選擇的結果。人類聚落的選擇不僅受到自然地理環境的限制,也受到人類本身創造出來的文化的制約。其中,自然條件的限制包括了地形(如坡度、高度、自然障礙等)、生業需求(如自然資源的多寡、季節分布、空間分布等,它包括了動、植物及原料等)、氣候(如溫度、濕度、日照、雨量、風向、風速等)、土壤(如所含養份的高低、適耕土地的分布)、水資源(如距水源的距離、多寡、和季節分布等)、以及其他(如生物種屬的競爭)。而文化的約束方面,則包括群際互動(如不同族群的競爭、合作)、族群認知(如對氣候狀況、環境狀況、資源使用選擇的知識,以及宇宙觀的認知等)、族群喜好(因文化選擇而有所不同,會表現在食衣住行上)、族群社會組織(如族群結構、社會組織等)、以及技術水平等(如工具的製作、資源取得、儲藏、運輸等方式)(參見Butzer 1982;Trigger 1968;Jochim 1981)。
就區域研究而言,聚落系統是由區域內一群不同類型的遺址所構成,每一個考古遺址,都是屬於該聚落系統的一個環節。所以說,在討論或者解釋人類行為的變異,以及社會文化的發展過程和變遷時,考古學者並不能,也無法只針對其中的一個遺址來做研究,而必需考慮到區域內聚落系統的每一個環節。也就是說,即使是研究區域內的某一個遺址,也應該整體考慮其所屬的聚落系統在自然環境下的空間分布,以及區域內各遺址之間相互關係的社會環境(SARG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