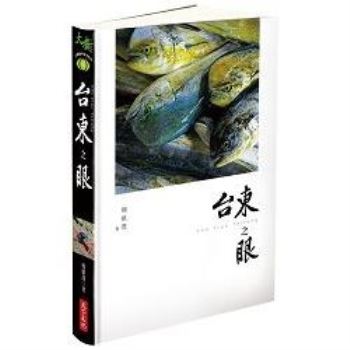迷霧之森
「每天都在看這座山,怎麼樣一生也要爬上一次啊!」已邁入中年尾聲的同行友人,來自台東利嘉部落的卑南族大哥,語重心長說出這番話。的確,位於台東市北方不遠處的都蘭山,硬是在山勢不高的海岸山脈中拔尖而起,無論從海岸或縱谷,甚或從台東市一直到太麻里,都看得到都蘭山金字塔般的山容。
高聳的地標往往成為神聖象徵,世居台東的阿美族與卑南族就視都蘭山為聖山,登臨都蘭山就對台東人有很大的意義,我這個新台東人不爬都蘭山說不過去,我也找不出理由拒絕卑南族友人們的登山邀約。出發前我們一行人談笑風生,並揶揄一位用賴床當理由放我們鴿子的友人,直到數個小時後我拖著疲憊雙腿下山,才發現最睿智的人原來是賴床的朋友。
累,我只能用這個字來形容這天陡上又陡下的折騰之路,更別說在氣候相對乾燥的台東,都蘭山步道竟以潮濕面容迎接我們,步道濕滑又多樹根阻礙,地面上還有不斷引頸期盼的吸血螞蝗大軍,多虧了牠們,讓我一路精神緊繃,驅趕早起之後久久不散的濃濃睡意,每個人一路上皆不忘當個低頭族,不時查看褲管或鞋內是否有不速之客「得來速(吸)」,若已被螞蝗吸上,還得想辦法拔掉牠。一定是惱人的螞蝗,我開始抱怨這趟旅程,抱怨路太陡太滑,抱怨一路上都是樹林遮擋而沒有風景可賞,抱怨沒幾隻動物現身讓我回去好誇耀一番。
途中經過一塊寫著「普悠瑪」的大石頭,這是處祭台,幾個卑南族部落每年還會有族人與拉罕(祭司)到此祭拜祖靈,當下我感受不到靈氣,因疲累想在此掉頭下山走人,可大夥沒有折返打算,膝蓋有些腫脹的我只好繼續硬著頭皮撐下去。
三個半小時後終於抵達長滿樹林而沒有展望的山頭,明明從山下望去高聳挺拔的都蘭山,怎麼身處其中反而心頭有點悶,或許是期望太高,期望登都蘭山而小天下,實際上,低海拔山林若能躲過人類伐木與開墾,以闊葉林為主的林相理當茂密繁盛,各類植物無不欣欣向榮,哪會有空隙讓你我目光輕易穿透。
想想釋懷不少,下山腳步轉為輕盈,我開始轉而欣賞稜線旁一棵棵姿態萬千的樹木,樹幹無一處不覆蓋滿苔蘚、地衣與蕨類,偶爾飄來一陣雲霧,眼前樹林轉為若隱若現,彷彿置身一個失去色彩,低飽和度的潑墨山水畫。這場籠罩山頂的雲霧似乎急著向我解釋,都蘭山終年潮濕的由來。我想起從台東市區遙望都蘭山,多數時間山頂總像是戴上一頂白色的帽子,已故台灣鄉土作家鍾理和在『笠山農場』一書中提到:「笠山每天牽起很厚很厚的雲霧,…我爹說笠山是有靈氣的。」老一輩從生活智慧中,體認一座山要有雲霧蓋頭才是座好山,雲霧就是山的靈氣。的確,未經開發破壞過的山,茂密森林與涓涓溪流涵養住水份,當熱對流上升,水氣將化為山嵐雲霧,經年覆蓋著保護著山頭。都蘭山就是一座有靈氣的山。
看來我爬了座好山、聖山,原住民入山前會灑米酒敬祖靈(卑南語稱達拉茂 Dalamau),沒帶米酒的我灑血好了,一路上驚嚇我吸我血的螞蝗,那一點點血就當做我對都蘭山的敬意。
國慶日下午的棒球賽
偶爾,下午興致來臨時我會換上短褲,到利嘉村唯一的利嘉國小紅土操場去慢跑,第一次踏上這座紅土跑道時,還納悶為何橢圓形跑道中央草皮,竟被整齊的剃去一塊方型,徒留裸露的紅土長出幾根稀疏且不整齊的雜草,當時百思不得其解。
國慶日這天我沒出遠門而待在部落中,往年此時我總會和三五好友從台北驅車直奔島之南的恆春半島,目的地是鄰近恆春鎮的滿州鄉一帶淺山地區,欣賞一場盛大的灰面鵟鷹過境秀,數萬隻灰面鵟鷹如同慶賀國慶,每年依約由北方向南遷徙過境台灣,牠們欲飛越國境之南,續往更南更溫暖的菲律賓方向遷徙。這年我未依約前往恆春,而是留在國境之東,像一隻應該遷徙而未遷徙的灰面鵟鷹,輾轉來到東部後,就決定擺脫遷徙的命定,選擇以留鳥身分展開新生活。
儘管腳踝不太舒服,我理當在一個涼風吹拂的下午出去伸展筋骨。
我找到跑道中央草皮消失的元兇了。原來光禿的角落並非荒蕪表象,而是個迷你棒球場,喜愛棒球的我怎麼沒看出來呢。國慶日不用上課,下午來場棒球賽是部落孩童治療手癢與心癢的好運動。他們身高參差不齊,看起來不像真正的棒球隊,人數不齊,連球衣也省去,身手仍有模有樣。我彷彿見著自己國中與高中時打球的身影,國中時,因朋友送的一隻右手手套(左撇子專用),讓我改練左投左打,高中時剛好中華職棒成立,全民燃起一股棒球瘋,三商虎、味全龍、鄭百勝、涂鴻欽、鷹俠…,不僅聽著、看著職棒轉播,我與國中、高中同學更拿起紅線球,拎起棒子學著球星搖晃球棒,一起度過幻想擊出全壘打的美好時光,那是升學考試中難得的慰藉(或逃避)。
孩童們擊出的軟式棒球暫時還威脅不到跑在紅土跑道上的我,我不用死盯著打擊區擊出的球,我仍可邊跑邊欣賞這個美麗校園,每一次經過校舍前方樹型高大優美的老苦楝樹,我就知道又跑了一圈,接近老苦楝時,我總是將目光游移在長滿伏石蕨的樹幹上,心中暗自稱奇。彼時幾個黑黑的身影掠過青山與雲朵的交界處,奪走我的目光,飛行姿態不像是此地常見的洋燕,體型上也大了不少。
我認出牠們了,在這國慶日的下午,約莫三十隻左右的灰面鵟鷹,像是國慶日閱兵中的飛行中隊,以劃破天際的驕傲高度飛過國小司令台,朝著北方振翅而去。沒到恆春賞鷹的我,竟然沒出遠門也見到遷徙中的鷹群,驚喜當下卻有點慚愧,當年勤跑野外的熱情到哪裡去了?我彷彿站在人生打擊區,連揮棒都懶得揮棒,即將被眼前過而不打的好球給三振。
回過神到現實,十月初灰面鵟鷹紛紛自韓國、日本或中國東北往南遷徙,過境台灣時因中央山脈阻隔,遷徙路線分為西部與東部兩條,從東部遷徙的鷹群大部分會在台東知本藥山一帶停歇過夜。我思考頭上這一小群灰面鵟鷹,不是應該在傍晚時向藥山飛去,怎麼反倒朝北飛向利嘉村,是遊興仍高不肯早早遁入森林歇息?還是風邀請了牠們來利嘉作客?我丟出了一顆問題球,但沒有人能接捕。
這場國慶日下午的棒球賽,觀眾除了跑道上的我,還有匆匆的過客灰面鵟鷹,最忠實的觀眾就是遠方高大的都蘭山,她千百年來見證這塊土地的每個脈動,以及棒球場或人生中的每個好壞球。
水圳與她所承載之生命
不知情的人還以為這是條大水溝。
身為台東新移民的我,此地沒有我的童年記憶,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的生活與體驗,要由我的嘴巴陳述一個台東故事,哪裡才是好的開頭呢?原來最好的故事就在身邊,故事起頭就來自於我家門前那條日夜奔流的水圳:卑南大圳。卑南大圳是條灌溉用水圳,從日治時期開鑿迄今,無數水稻田、菜園、釋迦園、荖葉園仰賴她的滋潤,雖然我不從事農業活動,水圳與我唯一的連結就是家庭生活廢水都往水圳裡排放(台東缺乏完善的污水下水道系統)。不知情的人還以為這不過是條大水溝罷了,混濁的水體也讓人以為水質不佳,真相是水圳源頭卑南大溪含石灰質高,水質終年混濁頗有土石流前兆。還好,那只是混濁。
某日,隔壁空屋的屋主從西部返回台東,這是我倆第一次見面,言談間不算熱絡,但我刻意詢問起卑南大圳,想為我們貧乏的交談注入些話題。我似乎找對話題,他彷彿將記憶倒轉回年少時光,話語開始滔滔不絕,他憶起孩提時每天得到水圳提水,再將水倒入屋旁的陶製大水缸,讓充滿石灰質的水靜置沈澱,家中才有清水可利用。彼時有多少人依賴這條水圳取水、洗衣、灌溉,多年後,通通化為鄉愁流向遠方。
這絕對不是條大水溝。
「颱風來時水會不會淹出來啊?」我最常被親友問到此問題,我告訴他們多心了,颱風來臨前,卑南大圳的取水口會採取預防性關閉,此時水圳遭到斷流,只剩下乾涸見底,整條光溜溜的水泥渠道,想淹水都很困難啊。在颱風季節中,我已歷經數次水圳無水的日子,水圳底部一層厚厚淤泥終於重見天日,讓整條水圳看起來就像是條氣若游絲的水蛇,毫無生氣可言。畢竟我是卑南大圳旁的新移民,對她了解仍不夠深,直到今年第一場颱風前夕,才對她蘊藏的生命力訝異不已。
彼時我沿著水圳邊慢跑,遠處水圳旁有些騷動,好奇心驅使我湊近觀望,已然乾涸的水圳內竟有人腳踏爛泥,手拿看似裝滿物體而顯得沉甸甸的水桶,還有兩個小孩拿了像是蚊帳的網具,撈啊撈的。我問了一位剛爬上來的男子,他伸手撈取水桶內獲物,「這還不夠大,我撈幾隻大隻的給你拍照,」他獻寶似的熱心回覆我,「以前還捉得到鱉,現在都沒看到了。」
剛跟我站在一旁觀望的三位孩童,也禁不住誘惑放下腳踏車,捲起褲管三兩下就爬到水圳內,用手中剛喝完飲料的空寶特瓶,克難地撈起蝦來,他們將回家後可能遭大人的責備拋在腦後,開懷地踏著爛泥,這般景象不曾發生在我的童年回憶中。我著實吃驚,平日流速不慢,水體還充斥大量泥沙的卑南大圳,竟會是部分溪流生物的家園。讀生物的朋友告訴我這些是「大和沼蝦」,儘管牠們終將成為桌上佳餚,我仍由衷感謝牠們讓我知道卑南大圳的生命力。卑南大圳自卑南大溪引入溪水,流經台東平原最後流入太平洋,屬於河海洄游生物的大和沼蝦反其道而行,依照生命本能自海洋逆河而上,與河海相通的卑南大圳意外成為重要的溯河通道。
當年日本人開鑿水圳時,或許還有成群的鰕虎魚苗與鰻苗,一起與大和沼蝦從太平洋「行軍」進入卑南大圳。我站水圳旁,揣想如此生態景象。
就說這不是條水溝了吧。
「每天都在看這座山,怎麼樣一生也要爬上一次啊!」已邁入中年尾聲的同行友人,來自台東利嘉部落的卑南族大哥,語重心長說出這番話。的確,位於台東市北方不遠處的都蘭山,硬是在山勢不高的海岸山脈中拔尖而起,無論從海岸或縱谷,甚或從台東市一直到太麻里,都看得到都蘭山金字塔般的山容。
高聳的地標往往成為神聖象徵,世居台東的阿美族與卑南族就視都蘭山為聖山,登臨都蘭山就對台東人有很大的意義,我這個新台東人不爬都蘭山說不過去,我也找不出理由拒絕卑南族友人們的登山邀約。出發前我們一行人談笑風生,並揶揄一位用賴床當理由放我們鴿子的友人,直到數個小時後我拖著疲憊雙腿下山,才發現最睿智的人原來是賴床的朋友。
累,我只能用這個字來形容這天陡上又陡下的折騰之路,更別說在氣候相對乾燥的台東,都蘭山步道竟以潮濕面容迎接我們,步道濕滑又多樹根阻礙,地面上還有不斷引頸期盼的吸血螞蝗大軍,多虧了牠們,讓我一路精神緊繃,驅趕早起之後久久不散的濃濃睡意,每個人一路上皆不忘當個低頭族,不時查看褲管或鞋內是否有不速之客「得來速(吸)」,若已被螞蝗吸上,還得想辦法拔掉牠。一定是惱人的螞蝗,我開始抱怨這趟旅程,抱怨路太陡太滑,抱怨一路上都是樹林遮擋而沒有風景可賞,抱怨沒幾隻動物現身讓我回去好誇耀一番。
途中經過一塊寫著「普悠瑪」的大石頭,這是處祭台,幾個卑南族部落每年還會有族人與拉罕(祭司)到此祭拜祖靈,當下我感受不到靈氣,因疲累想在此掉頭下山走人,可大夥沒有折返打算,膝蓋有些腫脹的我只好繼續硬著頭皮撐下去。
三個半小時後終於抵達長滿樹林而沒有展望的山頭,明明從山下望去高聳挺拔的都蘭山,怎麼身處其中反而心頭有點悶,或許是期望太高,期望登都蘭山而小天下,實際上,低海拔山林若能躲過人類伐木與開墾,以闊葉林為主的林相理當茂密繁盛,各類植物無不欣欣向榮,哪會有空隙讓你我目光輕易穿透。
想想釋懷不少,下山腳步轉為輕盈,我開始轉而欣賞稜線旁一棵棵姿態萬千的樹木,樹幹無一處不覆蓋滿苔蘚、地衣與蕨類,偶爾飄來一陣雲霧,眼前樹林轉為若隱若現,彷彿置身一個失去色彩,低飽和度的潑墨山水畫。這場籠罩山頂的雲霧似乎急著向我解釋,都蘭山終年潮濕的由來。我想起從台東市區遙望都蘭山,多數時間山頂總像是戴上一頂白色的帽子,已故台灣鄉土作家鍾理和在『笠山農場』一書中提到:「笠山每天牽起很厚很厚的雲霧,…我爹說笠山是有靈氣的。」老一輩從生活智慧中,體認一座山要有雲霧蓋頭才是座好山,雲霧就是山的靈氣。的確,未經開發破壞過的山,茂密森林與涓涓溪流涵養住水份,當熱對流上升,水氣將化為山嵐雲霧,經年覆蓋著保護著山頭。都蘭山就是一座有靈氣的山。
看來我爬了座好山、聖山,原住民入山前會灑米酒敬祖靈(卑南語稱達拉茂 Dalamau),沒帶米酒的我灑血好了,一路上驚嚇我吸我血的螞蝗,那一點點血就當做我對都蘭山的敬意。
國慶日下午的棒球賽
偶爾,下午興致來臨時我會換上短褲,到利嘉村唯一的利嘉國小紅土操場去慢跑,第一次踏上這座紅土跑道時,還納悶為何橢圓形跑道中央草皮,竟被整齊的剃去一塊方型,徒留裸露的紅土長出幾根稀疏且不整齊的雜草,當時百思不得其解。
國慶日這天我沒出遠門而待在部落中,往年此時我總會和三五好友從台北驅車直奔島之南的恆春半島,目的地是鄰近恆春鎮的滿州鄉一帶淺山地區,欣賞一場盛大的灰面鵟鷹過境秀,數萬隻灰面鵟鷹如同慶賀國慶,每年依約由北方向南遷徙過境台灣,牠們欲飛越國境之南,續往更南更溫暖的菲律賓方向遷徙。這年我未依約前往恆春,而是留在國境之東,像一隻應該遷徙而未遷徙的灰面鵟鷹,輾轉來到東部後,就決定擺脫遷徙的命定,選擇以留鳥身分展開新生活。
儘管腳踝不太舒服,我理當在一個涼風吹拂的下午出去伸展筋骨。
我找到跑道中央草皮消失的元兇了。原來光禿的角落並非荒蕪表象,而是個迷你棒球場,喜愛棒球的我怎麼沒看出來呢。國慶日不用上課,下午來場棒球賽是部落孩童治療手癢與心癢的好運動。他們身高參差不齊,看起來不像真正的棒球隊,人數不齊,連球衣也省去,身手仍有模有樣。我彷彿見著自己國中與高中時打球的身影,國中時,因朋友送的一隻右手手套(左撇子專用),讓我改練左投左打,高中時剛好中華職棒成立,全民燃起一股棒球瘋,三商虎、味全龍、鄭百勝、涂鴻欽、鷹俠…,不僅聽著、看著職棒轉播,我與國中、高中同學更拿起紅線球,拎起棒子學著球星搖晃球棒,一起度過幻想擊出全壘打的美好時光,那是升學考試中難得的慰藉(或逃避)。
孩童們擊出的軟式棒球暫時還威脅不到跑在紅土跑道上的我,我不用死盯著打擊區擊出的球,我仍可邊跑邊欣賞這個美麗校園,每一次經過校舍前方樹型高大優美的老苦楝樹,我就知道又跑了一圈,接近老苦楝時,我總是將目光游移在長滿伏石蕨的樹幹上,心中暗自稱奇。彼時幾個黑黑的身影掠過青山與雲朵的交界處,奪走我的目光,飛行姿態不像是此地常見的洋燕,體型上也大了不少。
我認出牠們了,在這國慶日的下午,約莫三十隻左右的灰面鵟鷹,像是國慶日閱兵中的飛行中隊,以劃破天際的驕傲高度飛過國小司令台,朝著北方振翅而去。沒到恆春賞鷹的我,竟然沒出遠門也見到遷徙中的鷹群,驚喜當下卻有點慚愧,當年勤跑野外的熱情到哪裡去了?我彷彿站在人生打擊區,連揮棒都懶得揮棒,即將被眼前過而不打的好球給三振。
回過神到現實,十月初灰面鵟鷹紛紛自韓國、日本或中國東北往南遷徙,過境台灣時因中央山脈阻隔,遷徙路線分為西部與東部兩條,從東部遷徙的鷹群大部分會在台東知本藥山一帶停歇過夜。我思考頭上這一小群灰面鵟鷹,不是應該在傍晚時向藥山飛去,怎麼反倒朝北飛向利嘉村,是遊興仍高不肯早早遁入森林歇息?還是風邀請了牠們來利嘉作客?我丟出了一顆問題球,但沒有人能接捕。
這場國慶日下午的棒球賽,觀眾除了跑道上的我,還有匆匆的過客灰面鵟鷹,最忠實的觀眾就是遠方高大的都蘭山,她千百年來見證這塊土地的每個脈動,以及棒球場或人生中的每個好壞球。
水圳與她所承載之生命
不知情的人還以為這是條大水溝。
身為台東新移民的我,此地沒有我的童年記憶,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的生活與體驗,要由我的嘴巴陳述一個台東故事,哪裡才是好的開頭呢?原來最好的故事就在身邊,故事起頭就來自於我家門前那條日夜奔流的水圳:卑南大圳。卑南大圳是條灌溉用水圳,從日治時期開鑿迄今,無數水稻田、菜園、釋迦園、荖葉園仰賴她的滋潤,雖然我不從事農業活動,水圳與我唯一的連結就是家庭生活廢水都往水圳裡排放(台東缺乏完善的污水下水道系統)。不知情的人還以為這不過是條大水溝罷了,混濁的水體也讓人以為水質不佳,真相是水圳源頭卑南大溪含石灰質高,水質終年混濁頗有土石流前兆。還好,那只是混濁。
某日,隔壁空屋的屋主從西部返回台東,這是我倆第一次見面,言談間不算熱絡,但我刻意詢問起卑南大圳,想為我們貧乏的交談注入些話題。我似乎找對話題,他彷彿將記憶倒轉回年少時光,話語開始滔滔不絕,他憶起孩提時每天得到水圳提水,再將水倒入屋旁的陶製大水缸,讓充滿石灰質的水靜置沈澱,家中才有清水可利用。彼時有多少人依賴這條水圳取水、洗衣、灌溉,多年後,通通化為鄉愁流向遠方。
這絕對不是條大水溝。
「颱風來時水會不會淹出來啊?」我最常被親友問到此問題,我告訴他們多心了,颱風來臨前,卑南大圳的取水口會採取預防性關閉,此時水圳遭到斷流,只剩下乾涸見底,整條光溜溜的水泥渠道,想淹水都很困難啊。在颱風季節中,我已歷經數次水圳無水的日子,水圳底部一層厚厚淤泥終於重見天日,讓整條水圳看起來就像是條氣若游絲的水蛇,毫無生氣可言。畢竟我是卑南大圳旁的新移民,對她了解仍不夠深,直到今年第一場颱風前夕,才對她蘊藏的生命力訝異不已。
彼時我沿著水圳邊慢跑,遠處水圳旁有些騷動,好奇心驅使我湊近觀望,已然乾涸的水圳內竟有人腳踏爛泥,手拿看似裝滿物體而顯得沉甸甸的水桶,還有兩個小孩拿了像是蚊帳的網具,撈啊撈的。我問了一位剛爬上來的男子,他伸手撈取水桶內獲物,「這還不夠大,我撈幾隻大隻的給你拍照,」他獻寶似的熱心回覆我,「以前還捉得到鱉,現在都沒看到了。」
剛跟我站在一旁觀望的三位孩童,也禁不住誘惑放下腳踏車,捲起褲管三兩下就爬到水圳內,用手中剛喝完飲料的空寶特瓶,克難地撈起蝦來,他們將回家後可能遭大人的責備拋在腦後,開懷地踏著爛泥,這般景象不曾發生在我的童年回憶中。我著實吃驚,平日流速不慢,水體還充斥大量泥沙的卑南大圳,竟會是部分溪流生物的家園。讀生物的朋友告訴我這些是「大和沼蝦」,儘管牠們終將成為桌上佳餚,我仍由衷感謝牠們讓我知道卑南大圳的生命力。卑南大圳自卑南大溪引入溪水,流經台東平原最後流入太平洋,屬於河海洄游生物的大和沼蝦反其道而行,依照生命本能自海洋逆河而上,與河海相通的卑南大圳意外成為重要的溯河通道。
當年日本人開鑿水圳時,或許還有成群的鰕虎魚苗與鰻苗,一起與大和沼蝦從太平洋「行軍」進入卑南大圳。我站水圳旁,揣想如此生態景象。
就說這不是條水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