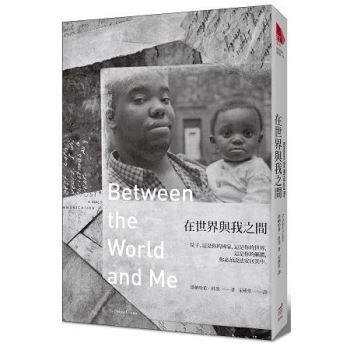某晨,我在林間草地
枝幹嶙峋的橡榆林立,
倏然撞見其景,
髒汙鉅細靡遺,
飄渺在世界與我之間。
—理查.萊特(譯注:Richard Wright,美國作家,1908-60)
第一篇
切勿對我提起壯烈成仁
切勿在教會活動日
談及後世緬懷之烈士。
我不信死的作用多大,
但我也終將一死。
紫羅蘭將如響板
響應我心聲。
—索妮亞.桑且斯(譯注:Sonia Sanchez,非裔美國詩人,1934-)
兒子:
上週日,當紅新聞節目的主持人訪問我,問我喪失軀體的感受如何。女主持人遠在華盛頓特區,而我坐在曼哈頓西緣的攝影棚,以衛星連線,但再先進的機器也無法拉近雙方代表的圈子。主持人問到我的軀體時,她的臉從畫面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我在同星期發表的文章片段。
句子浮現之際,主持人逐字朗讀給觀眾聽,讀完後,話題轉向我的軀體,只不過她並未直指「軀體」一詞。但到這階段,知識分子常不明究理關心我的軀體,我已經聽慣了。確切而言,主持人想知道的是,我為何認為美國白人圈的進化建築在掠奪和暴力之上。「白人」泛指向白人文化看齊的民眾。一聽她這麼問,一股存在已久的朦朧傷感湧上我心頭。這問題的答案在於信者恆信的紀錄上﹔答案在於美國歷史。
這句言論不算偏激。美國人把民主捧上天,崇尚到了隱隱意識到自己有時違逆上帝旨意的地步。幸好,民主是個寬容的上帝,而且美國的異端邪說——凌虐、盜竊、奴役——對許多人、許多國家而言是家常便飯,乃至於沒有人能自詡無罪。其實,從現實角度來看,美國未曾背叛上帝。一八六三年,林肯宣示,蓋茨堡(Gettysburg)戰役必須確保「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不得從地表消失,」其用意不僅在激發士氣。南北戰爭開打之初,美利堅合眾國的民眾參政率在全球名列前茅。問題不在於林肯是否誠心弘揚「民有」﹔問題在於,自古至今,美國認為「人民」這政治用語的真諦何在。在一八六三年,「人民」不包括你母親或外婆,也不包括你我。由此可見,美國的問題不在於悖離「民有政府」的理念﹔問題在於定義「人民」一詞的方式。
順勢探討另一項同等重要的理想,美國人默默接受卻從不明言的理想。美國人篤信的「種族」現實是一種自然界的特色,定位明確,無庸置疑。從這種無可撼動的定位,種族歧視必然隨之而起,先是為異族貼上根深蒂固的特質標籤,進而羞辱、貶損、摧毀異族。種族歧視因此被視為一種大自然的產物,天真無邪,可用來哀嘆大西洋盆地的販奴航線,用來悼念一八三○、四○年代印第安人被迫遷徙的慘劇,態度一如哀嘆地震、龍捲風等人力無法控制的現象。
然而,種族是種族歧視之子,不是種族歧視之父。界定「人民」一詞的過程向來側重於地位高低,與宗族和外觀的關係不大。膚色與頭髮的差異由來已久,但崇尚膚色與頭髮的優越性,認定這類因素能適切劃分社群、能彰顯難以磨滅的內在特質,這是新人民心中的一種新觀念。這群可憐新人民從小被矇騙、被強灌的想法是以白人自居。
這群新人民和你我一樣,同是現代產物。但與你我不同的是,若缺乏犯罪強權機制的加持,他們的新名稱毫無實質意義。在變成白人之前,這群新人民各有定位——天主教徒、法國科西嘉島人、英國威爾斯人、門諾派信徒、猶太裔。如果國人的願望全有實現的一天,這些人勢必會再變成另一種人。也許,這群人終將徹底蛻變為美國人,為他們的迷思奠定更高尚的依據。會不會有這一天?我無法判定。以現階段而言,非提不可的事實是,漂白各族裔的過程——崇白論獲抬舉的過程——並非透過品酒會、冰淇淋交誼會來達成,而是藉由掠奪生命、自由、勞動力、土地的方式,藉由剝除背皮凌遲的手段,藉由鏈鎖四肢、扼殺異議分子、抄家、強暴母親、販子賣女等各種惡行,最重要的是剝奪你我自保自主的權利。
在這方面,新人民的言行並無新意。在歷史上,或許有某強權不必對人體橫徵暴斂便能睥睨天下。就算史上發生過這種事,恕我無知,我沒聽過。但是,美國絕無法援引這種四海皆有的暴力模式,因為美國不屑與陳腐平庸為伍。美國相信自己超群絕倫,是古今全球最偉大、最高尚的國家,是單打獨鬥惡勢力的白人民主城邦,能隻身對抗恐怖分子、暴君、蠻族等等威脅文明世界的惡敵。無人能自稱聖賢卻在犯錯時以「孰能無過」為託詞。我提議認真看待國人的美國優越論,換言之,我提議以道德超高標檢視我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因為你我四週存在一套無形機制,而這機制頻頻勸人照單接受美國純真論,不必過度質疑。人之常情是睜一眼閉一眼,一面坐擁美國史賦予的果實,一面漠視打著美國人民旗號而造的大孽。但你我從未真正享受過這種福氣。我想你應該知道。
在你十五歲這一年,我寫這封信給你。我選這一年寫給你,是因為你見到艾瑞克.賈諾爾(Eric Garner)因兜售香菸而被勒死,是因為你如今明白了芮尼夏.麥克布萊德(Renisha McBride)求救時中彈,約翰.科洛富(John Crawford)逛百貨公司時遭擊斃。你也看過塔米爾.萊斯(Tamir Rice)在警車尚未停妥時就挨警槍,而他才十二歲大,是警察宣誓保護的兒童。你也見過男警在路旁痛毆祖母級的瑪琳.平諾克(Marlene Pinnock)。如果你以前不懂,現在應該明白了,你的國家授權給警察局,讓警察有權毀損你的軀體。毀損的行為是否源於反應過度,是否純屬不幸,並不重要﹔是否源於誤解,也不重要;是否衍生自昏庸的政策,也不重要。你賣私菸,你的軀體就能被毀損。有人設陷阱,想誘捕你的軀體,你憎恨他們,你的軀體就能被毀損。你走進黑黝黝的樓梯間,你的軀體就能被毀損。因此被追究責任的毀損者少之又少。毀損者多數領得到退休金。毀損僅僅是當權者施展特權到極致的行為,其他特權還包括搜身、拘留、毒打、羞辱。這些遭遇,黑人習以為常。對黑人來說,這一切全是老掉牙的事。沒有人被追究刑責。
其實,這些毀損者的惡性並不獨特,甚至目前的歪風也無特異之處。毀損者只是為國執法的代理人,正確詮釋國家的宿命與傳承。令人難以面對的是,種種用語,如種族互動、種族鴻溝、種族司法正義、種族貌相判定(profiling)、白人特權、甚至白人至上主義,用意全在模糊一件事﹕種族歧視是一種直鑽內心深處的經驗,能爆腦漿、阻塞呼吸道、撕裂肌肉、摘除器官、折骨斷牙。你萬萬不可不正視。你務必時時謹記,箇中的社會學、歷史、經濟學、圖表、退化曲線,全部排山倒海落在軀體上。
那星期天,接受新聞節目訪問時,我在時限內盡可能向主持人解釋這一點,但在訪問近尾聲時,主持人出示一張廣為流傳的畫面,相片裡的十一歲黑人男童淚眼擁抱白人警官。接著她要我針對「希望」發表看法。我當下明瞭,我失敗了。而我記得,我本來就料到會失敗。我再次想到湧上心頭的那股朦朧的傷感。我究竟因何悲哀呢﹖離開攝影棚,我散步一段路。十二月的那天一片祥和,自信是白人的大小家庭在街上走動。襁褓中的幼兒被當成白人來栽培,躺在嬰兒車上。我為這些人感到悲哀,和我為主持人感到悲哀一樣,為陶醉在華而不實美夢裡的所有觀眾感到悲哀。我總算悟出悲哀的原因了。主持人問到我的軀體時,好像在要求我喚醒她,不讓她繼續沉醉在最美好的大夢。那種美夢,我從小到大見慣了。草坪整潔的完美民宅。春末夏初國殤紀念日的戶外烤肉會。街區協進會。供自家車進出的車道。那種大夢是樹屋,是幼童軍。那種大夢的香氣近似薄荷,滋味卻像草莓小蛋糕。長久以來,我多想躲進那場大夢,把美國當成毛毯,蒙頭睡覺。無奈事與願違,因為大夢靠我們扛,寢具的原料來自我們的軀體。明瞭這一點後,明瞭到大夢能延續是靠著和現實對抗,我為主持人感到悲哀,為路上所有家庭悲哀,為我的國家悲哀,但在那一刻,我最悲哀的對象是你。
在那星期,你得知麥克.布朗(Michael Brown)的兇手不必坐牢。警察把他的屍體晾在街頭,當成一種了不起的宣言,以顯示自己擁有不可侵犯的大權。涉案警察始終沒有受到懲罰。我早料到,沒有人會被懲處。但你仍年輕,對體制仍有信心。那天晚上,你十一點還不就寢,看電視等候警察被起訴,卻聽到不處分的消息,你說,「我看不下去了,」然後回房間。我聽見你在哭。五分鐘後,我進你房間,不抱你,也不安慰你,因為我認為,安慰你是錯誤的舉動。我不勸你放心,因為我從不相信以後萬事OK。我對你傳達你祖父母曾試著灌輸給我的道理﹕這是你的國家,這是你的世界,這是你的軀體,你必須設法安居其中。我在此告訴你,生活在一個迷失在大夢裡的國家,如何安居於黑人軀殼裡,這是我畢生追尋解答的疑問,而我已經發現,尋答的過程到頭來能自我釋疑。
你一定覺得奇怪。我們活在一個「目標導向」的時代,媒體辭彙充滿著嚴選佳句、驚世創見,每件事的背後都有奧秘的理論。但是在幾年前,我已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魔法(譯注﹕不信宗教)。這種心態是你祖父母送給我的禮物。他們從不以來生安慰我,對美國固有的光輝抱持懷疑的態度。我坦然接受歷史中的紛擾,接受我在世上僅走這一回的事實,因而獲得解放,能徹底思考自己想要的生活—確切的思考方向是﹕以這副黑人軀體,我如何活得自由自在﹖這問題涵義深遠,因為美國自認是上帝親手打造的國家,但黑人軀體卻提供最明確的反證,證明美國是凡人的作品。同一道問題,我藉讀寫問過無數次,年少聽音樂時問過,也在我和你祖父、你母親、你姑媽、我大學好友班(Ben)和珍奈(Janai)辯論時問過。我找答案的地方包括教室、街頭、國族主義迷思,更踏上其他大陸尋答。這問題無解,卻也不是徒勞無功的清談。在反覆質問、在面對我國暴行的過程中,最豐厚的回報是,我不再受制於幽魂,能壯膽對抗魂體分離的椎心恐懼。
我內心有份恐懼。每當你不在我身邊時,這份恐懼感加劇。但早在你出生之前,我已有這份恐懼心,而且有同樣感受的人不獨我一個。在你這年紀,我認識的人全是黑皮膚,無一沒有巨大、頑強、險惡的恐懼心。我在童年見慣了這份恐懼,只是當時見了不一定知道是。
枝幹嶙峋的橡榆林立,
倏然撞見其景,
髒汙鉅細靡遺,
飄渺在世界與我之間。
—理查.萊特(譯注:Richard Wright,美國作家,1908-60)
第一篇
切勿對我提起壯烈成仁
切勿在教會活動日
談及後世緬懷之烈士。
我不信死的作用多大,
但我也終將一死。
紫羅蘭將如響板
響應我心聲。
—索妮亞.桑且斯(譯注:Sonia Sanchez,非裔美國詩人,1934-)
兒子:
上週日,當紅新聞節目的主持人訪問我,問我喪失軀體的感受如何。女主持人遠在華盛頓特區,而我坐在曼哈頓西緣的攝影棚,以衛星連線,但再先進的機器也無法拉近雙方代表的圈子。主持人問到我的軀體時,她的臉從畫面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我在同星期發表的文章片段。
句子浮現之際,主持人逐字朗讀給觀眾聽,讀完後,話題轉向我的軀體,只不過她並未直指「軀體」一詞。但到這階段,知識分子常不明究理關心我的軀體,我已經聽慣了。確切而言,主持人想知道的是,我為何認為美國白人圈的進化建築在掠奪和暴力之上。「白人」泛指向白人文化看齊的民眾。一聽她這麼問,一股存在已久的朦朧傷感湧上我心頭。這問題的答案在於信者恆信的紀錄上﹔答案在於美國歷史。
這句言論不算偏激。美國人把民主捧上天,崇尚到了隱隱意識到自己有時違逆上帝旨意的地步。幸好,民主是個寬容的上帝,而且美國的異端邪說——凌虐、盜竊、奴役——對許多人、許多國家而言是家常便飯,乃至於沒有人能自詡無罪。其實,從現實角度來看,美國未曾背叛上帝。一八六三年,林肯宣示,蓋茨堡(Gettysburg)戰役必須確保「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不得從地表消失,」其用意不僅在激發士氣。南北戰爭開打之初,美利堅合眾國的民眾參政率在全球名列前茅。問題不在於林肯是否誠心弘揚「民有」﹔問題在於,自古至今,美國認為「人民」這政治用語的真諦何在。在一八六三年,「人民」不包括你母親或外婆,也不包括你我。由此可見,美國的問題不在於悖離「民有政府」的理念﹔問題在於定義「人民」一詞的方式。
順勢探討另一項同等重要的理想,美國人默默接受卻從不明言的理想。美國人篤信的「種族」現實是一種自然界的特色,定位明確,無庸置疑。從這種無可撼動的定位,種族歧視必然隨之而起,先是為異族貼上根深蒂固的特質標籤,進而羞辱、貶損、摧毀異族。種族歧視因此被視為一種大自然的產物,天真無邪,可用來哀嘆大西洋盆地的販奴航線,用來悼念一八三○、四○年代印第安人被迫遷徙的慘劇,態度一如哀嘆地震、龍捲風等人力無法控制的現象。
然而,種族是種族歧視之子,不是種族歧視之父。界定「人民」一詞的過程向來側重於地位高低,與宗族和外觀的關係不大。膚色與頭髮的差異由來已久,但崇尚膚色與頭髮的優越性,認定這類因素能適切劃分社群、能彰顯難以磨滅的內在特質,這是新人民心中的一種新觀念。這群可憐新人民從小被矇騙、被強灌的想法是以白人自居。
這群新人民和你我一樣,同是現代產物。但與你我不同的是,若缺乏犯罪強權機制的加持,他們的新名稱毫無實質意義。在變成白人之前,這群新人民各有定位——天主教徒、法國科西嘉島人、英國威爾斯人、門諾派信徒、猶太裔。如果國人的願望全有實現的一天,這些人勢必會再變成另一種人。也許,這群人終將徹底蛻變為美國人,為他們的迷思奠定更高尚的依據。會不會有這一天?我無法判定。以現階段而言,非提不可的事實是,漂白各族裔的過程——崇白論獲抬舉的過程——並非透過品酒會、冰淇淋交誼會來達成,而是藉由掠奪生命、自由、勞動力、土地的方式,藉由剝除背皮凌遲的手段,藉由鏈鎖四肢、扼殺異議分子、抄家、強暴母親、販子賣女等各種惡行,最重要的是剝奪你我自保自主的權利。
在這方面,新人民的言行並無新意。在歷史上,或許有某強權不必對人體橫徵暴斂便能睥睨天下。就算史上發生過這種事,恕我無知,我沒聽過。但是,美國絕無法援引這種四海皆有的暴力模式,因為美國不屑與陳腐平庸為伍。美國相信自己超群絕倫,是古今全球最偉大、最高尚的國家,是單打獨鬥惡勢力的白人民主城邦,能隻身對抗恐怖分子、暴君、蠻族等等威脅文明世界的惡敵。無人能自稱聖賢卻在犯錯時以「孰能無過」為託詞。我提議認真看待國人的美國優越論,換言之,我提議以道德超高標檢視我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因為你我四週存在一套無形機制,而這機制頻頻勸人照單接受美國純真論,不必過度質疑。人之常情是睜一眼閉一眼,一面坐擁美國史賦予的果實,一面漠視打著美國人民旗號而造的大孽。但你我從未真正享受過這種福氣。我想你應該知道。
在你十五歲這一年,我寫這封信給你。我選這一年寫給你,是因為你見到艾瑞克.賈諾爾(Eric Garner)因兜售香菸而被勒死,是因為你如今明白了芮尼夏.麥克布萊德(Renisha McBride)求救時中彈,約翰.科洛富(John Crawford)逛百貨公司時遭擊斃。你也看過塔米爾.萊斯(Tamir Rice)在警車尚未停妥時就挨警槍,而他才十二歲大,是警察宣誓保護的兒童。你也見過男警在路旁痛毆祖母級的瑪琳.平諾克(Marlene Pinnock)。如果你以前不懂,現在應該明白了,你的國家授權給警察局,讓警察有權毀損你的軀體。毀損的行為是否源於反應過度,是否純屬不幸,並不重要﹔是否源於誤解,也不重要;是否衍生自昏庸的政策,也不重要。你賣私菸,你的軀體就能被毀損。有人設陷阱,想誘捕你的軀體,你憎恨他們,你的軀體就能被毀損。你走進黑黝黝的樓梯間,你的軀體就能被毀損。因此被追究責任的毀損者少之又少。毀損者多數領得到退休金。毀損僅僅是當權者施展特權到極致的行為,其他特權還包括搜身、拘留、毒打、羞辱。這些遭遇,黑人習以為常。對黑人來說,這一切全是老掉牙的事。沒有人被追究刑責。
其實,這些毀損者的惡性並不獨特,甚至目前的歪風也無特異之處。毀損者只是為國執法的代理人,正確詮釋國家的宿命與傳承。令人難以面對的是,種種用語,如種族互動、種族鴻溝、種族司法正義、種族貌相判定(profiling)、白人特權、甚至白人至上主義,用意全在模糊一件事﹕種族歧視是一種直鑽內心深處的經驗,能爆腦漿、阻塞呼吸道、撕裂肌肉、摘除器官、折骨斷牙。你萬萬不可不正視。你務必時時謹記,箇中的社會學、歷史、經濟學、圖表、退化曲線,全部排山倒海落在軀體上。
那星期天,接受新聞節目訪問時,我在時限內盡可能向主持人解釋這一點,但在訪問近尾聲時,主持人出示一張廣為流傳的畫面,相片裡的十一歲黑人男童淚眼擁抱白人警官。接著她要我針對「希望」發表看法。我當下明瞭,我失敗了。而我記得,我本來就料到會失敗。我再次想到湧上心頭的那股朦朧的傷感。我究竟因何悲哀呢﹖離開攝影棚,我散步一段路。十二月的那天一片祥和,自信是白人的大小家庭在街上走動。襁褓中的幼兒被當成白人來栽培,躺在嬰兒車上。我為這些人感到悲哀,和我為主持人感到悲哀一樣,為陶醉在華而不實美夢裡的所有觀眾感到悲哀。我總算悟出悲哀的原因了。主持人問到我的軀體時,好像在要求我喚醒她,不讓她繼續沉醉在最美好的大夢。那種美夢,我從小到大見慣了。草坪整潔的完美民宅。春末夏初國殤紀念日的戶外烤肉會。街區協進會。供自家車進出的車道。那種大夢是樹屋,是幼童軍。那種大夢的香氣近似薄荷,滋味卻像草莓小蛋糕。長久以來,我多想躲進那場大夢,把美國當成毛毯,蒙頭睡覺。無奈事與願違,因為大夢靠我們扛,寢具的原料來自我們的軀體。明瞭這一點後,明瞭到大夢能延續是靠著和現實對抗,我為主持人感到悲哀,為路上所有家庭悲哀,為我的國家悲哀,但在那一刻,我最悲哀的對象是你。
在那星期,你得知麥克.布朗(Michael Brown)的兇手不必坐牢。警察把他的屍體晾在街頭,當成一種了不起的宣言,以顯示自己擁有不可侵犯的大權。涉案警察始終沒有受到懲罰。我早料到,沒有人會被懲處。但你仍年輕,對體制仍有信心。那天晚上,你十一點還不就寢,看電視等候警察被起訴,卻聽到不處分的消息,你說,「我看不下去了,」然後回房間。我聽見你在哭。五分鐘後,我進你房間,不抱你,也不安慰你,因為我認為,安慰你是錯誤的舉動。我不勸你放心,因為我從不相信以後萬事OK。我對你傳達你祖父母曾試著灌輸給我的道理﹕這是你的國家,這是你的世界,這是你的軀體,你必須設法安居其中。我在此告訴你,生活在一個迷失在大夢裡的國家,如何安居於黑人軀殼裡,這是我畢生追尋解答的疑問,而我已經發現,尋答的過程到頭來能自我釋疑。
你一定覺得奇怪。我們活在一個「目標導向」的時代,媒體辭彙充滿著嚴選佳句、驚世創見,每件事的背後都有奧秘的理論。但是在幾年前,我已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魔法(譯注﹕不信宗教)。這種心態是你祖父母送給我的禮物。他們從不以來生安慰我,對美國固有的光輝抱持懷疑的態度。我坦然接受歷史中的紛擾,接受我在世上僅走這一回的事實,因而獲得解放,能徹底思考自己想要的生活—確切的思考方向是﹕以這副黑人軀體,我如何活得自由自在﹖這問題涵義深遠,因為美國自認是上帝親手打造的國家,但黑人軀體卻提供最明確的反證,證明美國是凡人的作品。同一道問題,我藉讀寫問過無數次,年少聽音樂時問過,也在我和你祖父、你母親、你姑媽、我大學好友班(Ben)和珍奈(Janai)辯論時問過。我找答案的地方包括教室、街頭、國族主義迷思,更踏上其他大陸尋答。這問題無解,卻也不是徒勞無功的清談。在反覆質問、在面對我國暴行的過程中,最豐厚的回報是,我不再受制於幽魂,能壯膽對抗魂體分離的椎心恐懼。
我內心有份恐懼。每當你不在我身邊時,這份恐懼感加劇。但早在你出生之前,我已有這份恐懼心,而且有同樣感受的人不獨我一個。在你這年紀,我認識的人全是黑皮膚,無一沒有巨大、頑強、險惡的恐懼心。我在童年見慣了這份恐懼,只是當時見了不一定知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