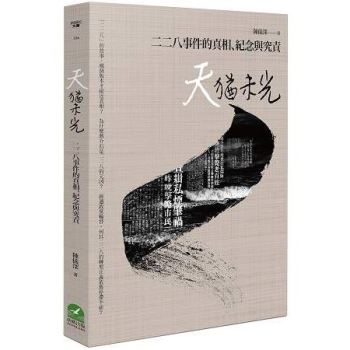從二二八檔案看到更多歷史事實
九○年代行政院的二二八研究小組,把官方交付的二二八檔案轉給中研院近史所,隨後整理出版成六冊「資料選輯」,這批資料與先前廈門大學出版、台灣稻鄉出版社翻印的資料集,以及人間出版社出版之南京二檔館收藏的相關史料,都是近年來二二八研究的必備工具。2000年政黨輪替以後,新成立的國家檔案局籌備處(今名檔案管理局),更動員許多歷史學者分組赴全台各地訪查檔案,這一番地毯式主動搜索的成果,如今大都數位化成為檔管局網站的服務項目,並且自2002年起由國史館陸續出版紙本,截至最近為止已達12冊之多,對學者而言堪稱便利。為了對扁政府這項「政績」鼓勵肯定,筆者雖未完全細讀新出土的史料,仍願將瀏覽到的重點,印證已知的史實作為今年二二八的紀念文字。
1947年3月10日,情治單位的葉秀、張鎮呈給蔣介石的一份報告,描述當時台灣的全部兵力,除原有空軍地勤人員及要塞守備部隊外,計有一營特務、五營憲兵以及21師全部(五個團,一個團約二千多人);然而這是兩次增援的結果,第一次包括由福州來台的兩營憲兵、由上海來台的21師師部以及21師第146團,第二次包括由福州來台的憲兵一營以及由連雲港來台的21師145團。值得注意的是,3月10日恰是蔣介石在南京「總理紀念週」首度公開發表有關二二八談話的日子,該篇講詞把派兵原因歸諸3月7日處理委員會提出32條越份要求所致,明顯不合事實,這兩批搭船艦來台增援的軍隊不是天兵天將,不可能在兩天之內說到就到,而是更早在柯遠芬一再保證中央不會派兵的時候,就已下令增兵。
其次,這篇報告描述處委會內部引起分化,計為蔣渭川等要求獨立自主之大台灣主義派,以及王添灯、王萬得等民盟奸偽派,蔣退出處委會之後另以自治青年同盟之力量與處委會對峙;像這樣濫用台獨、奸偽標籤的手法,與1979年12月13日美麗島人士被捕後,被分成「台獨」、「共匪」兩類進行偵訊的情況類似。於此,二二八事件遂與美麗島事件產生某種意義的連結。
3月9日再度戒嚴,一般注意的是軍隊掃蕩鎮壓、綏靖清鄉,但從「高雄中學檔案」可知,長官公署教育處要求各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須於特定時間內撰寫表白日記,內容包括2月28日至3月13日間與何人在一起?談些什麼、聽到什麼、看到什麼?曾參加何種集會、何種隊伍?會議中哪些人發表意見?所見所聞所行的感想最厲害的是:「學生作表白日記以後,發覺自己言行已被他人報告訐發而未曾載入表白日記中者,不得藉口遺忘而要求補記。」「學生如有故意規避,不作表白日記者,學校得撤銷其原有學籍。」高雄第一中學因教員、學生多人參與事件,事件後校長林景元遂被解職,改派第二中學校長林一鶴來接管處理校務,這位二中林校長在一份〈二二八事件私人損失調查表〉中,大剌剌詳列西裝三套、襯衣四件、襪五雙、短褲三條……合共台幣126,000千元。
在國家安全局檔案中,有許多台省各地的通訊員向「南京言普誠先生」提出的報告,例如一位高雄組義務通訊員劉鴻報稱:「3月3日暴動時前金區區長陳水印利用區公所為保安隊部,召集流氓充保安隊員,陳自任保安隊長肆意毆擊外省籍人民……」,另根據一位通訊員江心波抄送的「高雄市各區此次事變死傷調查表」,其中各機關人員受傷調查表率皆外省籍,時間是3月3日、4日,各區本省民眾死亡迄3月13日為止以鹽埕區34人為最多,死亡時間大多在3月6日,這份資料可以間接印證彭孟緝率兵攻入市區的時間就是3月6日,也就是傷亡最慘重的一天。另據高雄組謝愛吼的報告,彭孟緝使高雄市「恢復秩序」以後,3月8日即率部隊圍剿屏東,除繳獲武器並將屏市參議會議長葉秋木等三名首謀逮捕槍決,市府各機關於9日恢復辦公;台南方面則是3月11日晨由彭司令派上校參謀楊俊率領機動部隊前往,將各要點占據並控制交通後,「匪徒」旋即逃竄。確切時間與經過當需其他資料比對,惟以當時彭孟緝聽到陳儀的軟性廣播就判定長官必遭劫持,其積極表現且過度反應,是一致的印象。
實則,情治系統的報告也有冷靜客觀的部分,非皆誇大危情,例如一位金燮佳轉達義務通訊員蘇森的意見稱:「專賣局查緝私煙竟置走私商人於不顧,而捨本逐末專拘販賣私煙之小香煙攤,種下台人不滿之因。」至於28日請願民眾「動機與目的均尚屬單純」,不料復遭機槍掃射死傷甚重,於是釀成空前事變,前後描述已暗指陳儀一錯再錯,這份報告又說:「此次事變確非出諸共黨之煽動,惟事變擴大後共黨分子混雜其間進行部分的煽動則確有其事。」可惜蔣介石選擇性地認知情報,對陳儀一味袒護,當3月中下旬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曾以臨時動議方式檢討台省事變,通過懲辦陳儀的決議以後竟又被蔣翻案,蔣還稱讚陳儀負責盡職,那麼,誰是應該負責的二二八「元凶」還需爭論嗎?
二二八的族群衝突面向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出版、鄭鴻生先生所寫的一本新書,其中一篇文章〈誰的二二八?〉說到:「族群衝突」是二二八當時最末流、最不應該強調的因素,後來卻被誇大渲染成為最主要的矛盾;鄭先生說如果要談族群衝突,「我們能夠找到當時最鮮活、最具體的例證就只能是『打阿山仔』──就是在事變期間一些暴民不分青紅皂白,到處毆打、殺害一般外省人這件事。而這正是讓我年輕時候耿耿於懷的心頭之痛。」吾人推敲鄭先生所謂的「後來」,應該不包括戒嚴時代外來政權繼續扭曲二二八的一段吧,至於解嚴後,除了第一部探討二二八的著名電影《悲情城市》,對「打阿山仔」的情節有所交代以外,舉凡民間的公義和平運動、研討會論文或民進黨主要領導人的公開發言,有誰講過族群衝突是二二八最重要的因素或最主要的矛盾?有誰指責過「外省人」要負責任?
包括2006年2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重點亦在闡明蔣介石應負最大責任,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等軍政首長應負次要責任的理由,附論中同時認定這是政府犯罪,今日追究這些人的刑事責任,還具有還給其他「外省人」族群清白的積極效能。儘管如此,為什麼以鄭鴻生為代表的一群人還是會覺得「族群冒犯」呢?個人認為,解嚴以來的二二八真相追求與平反運動,是與塑造台灣認同的本土化運動乃至台獨運動分不開的,站在「反台獨」或親中、統一立場的人不免產生排斥,所以,是他們對號入座,不是別人做了什麼誇大扭曲。
進一步說,二二八事件爆發初期,尤其是長官公署衛兵開槍以後激起台灣人普遍的憤怒,很多地方確實發生「打阿山仔」的現象,但是台灣人仕紳組成的處理委員會立刻予以制止,而且不必等到3月8日援軍登陸,各地的巡邏士兵早已開槍反擊乃至報復;例如3月6日彭孟緝派出來的軍隊,在高雄市胡亂掃射、任意搶劫的現象,難道沒有族群因素作祟?高雄方面至少已經有許雪姬教授所做的三本口述訪問紀錄(1995年出版)可以作證。反台獨或親中的知識分子如果真正關心二二八悲劇,早就應該去完成(也只有他們能完成的)二二八當時外省人受害的口述歷史,可惜到今天一本也無。
就像電影《悲情城市》的情節所顯示的,一般台灣人對「祖國」的來臨多麼格格不入,台灣變成中華民國的初始必須經過暴力流血的轉化,可見國家認同的建(虛)構性。個人認為,惟有誠實面對二二八的「族群衝突」面向,才能深刻反省今日藍綠政黨宛若敵國,其背後的認同政治糾結。
為二二八控告國民黨的一段失敗經驗
1995年公布施行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只是由行政院設立的基金會進行補償作業,與轉型正義攸關的追求真相關連不大,遑論司法上的究責。所以,當2006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以後,一群二二八家屬以及台教會等社團就積極思考向法院控告國民黨的可能性。
2010年的2月26日,也就是二二八紀念日前夕,由張炎憲(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陳儀深(台灣教授協會會長)以及顧立雄、李勝雄等五位律師作為訴訟代理人,王不纏等108位受難家屬作為原告,終於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訴訟標的是要求國民黨將其黨史館收藏之二二八相關檔案,以及戒嚴時期之中常會紀錄、總裁批簽、海工會檔案悉數交由檔案管理局保存並公開;國民黨應以黨產捐出新台幣二十億元作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籌設及營運經費;國民黨必須在國內外重要報紙之頭版半版篇幅刊登起訴狀所附之道歉聲明。接下來,歷經同年4月14日開首次言詞辯論庭、8月6日判決原告敗訴、8月25日原告等再向高院提起上訴、11月25日高院開庭,隔年即2011年4月26日高院判決駁回上訴,同年5月20日我們向最高法院上訴,9月22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確定。
訴訟期間,中國國民黨的法定代理人是馬英九主席,訴訟代理人是賴素如、洪文浚兩位律師,從他們的辯論意旨狀和答辯狀看,只能說「毫無悔意」。例如,說蔣介石是「基於政府公務人員之職權所為公法上之行為,而非基於擔任政黨法定代理人之職務所為」,「該等公務員之作為應係本於其公務員之身分而於政府指揮下所為之,即屬政府之行為,亦與被上訴人(中國國民黨)無涉」;最厚顏的是,還敢引用「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即罹時效,如今距離二二八事件已經超過數十年,所以「不應准許」原告即這一百多位二二八家屬的請求。不幸的是,三級三審的法官們,只採信或抄襲國民黨的上述論點,對於我們書狀所說1947年事件發生當時尚屬「黨國一體、黨在國上」之訓政時期,台灣人之生命、財產、自由所遭受之鉅大損害,以及轉型正義之世界潮流云云皆視若無睹。
光是「罹於時效」的理由也敢拿出來當武器,即可見今日特別立法之必要。立法院還在處理中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即使通過,也不見得可以迫使國民黨接受上述家屬的三大訴求,但至少顯示台灣社會主流意見已然轉變,也許今後再來告它一次,會有不同的結果吧?
九○年代行政院的二二八研究小組,把官方交付的二二八檔案轉給中研院近史所,隨後整理出版成六冊「資料選輯」,這批資料與先前廈門大學出版、台灣稻鄉出版社翻印的資料集,以及人間出版社出版之南京二檔館收藏的相關史料,都是近年來二二八研究的必備工具。2000年政黨輪替以後,新成立的國家檔案局籌備處(今名檔案管理局),更動員許多歷史學者分組赴全台各地訪查檔案,這一番地毯式主動搜索的成果,如今大都數位化成為檔管局網站的服務項目,並且自2002年起由國史館陸續出版紙本,截至最近為止已達12冊之多,對學者而言堪稱便利。為了對扁政府這項「政績」鼓勵肯定,筆者雖未完全細讀新出土的史料,仍願將瀏覽到的重點,印證已知的史實作為今年二二八的紀念文字。
1947年3月10日,情治單位的葉秀、張鎮呈給蔣介石的一份報告,描述當時台灣的全部兵力,除原有空軍地勤人員及要塞守備部隊外,計有一營特務、五營憲兵以及21師全部(五個團,一個團約二千多人);然而這是兩次增援的結果,第一次包括由福州來台的兩營憲兵、由上海來台的21師師部以及21師第146團,第二次包括由福州來台的憲兵一營以及由連雲港來台的21師145團。值得注意的是,3月10日恰是蔣介石在南京「總理紀念週」首度公開發表有關二二八談話的日子,該篇講詞把派兵原因歸諸3月7日處理委員會提出32條越份要求所致,明顯不合事實,這兩批搭船艦來台增援的軍隊不是天兵天將,不可能在兩天之內說到就到,而是更早在柯遠芬一再保證中央不會派兵的時候,就已下令增兵。
其次,這篇報告描述處委會內部引起分化,計為蔣渭川等要求獨立自主之大台灣主義派,以及王添灯、王萬得等民盟奸偽派,蔣退出處委會之後另以自治青年同盟之力量與處委會對峙;像這樣濫用台獨、奸偽標籤的手法,與1979年12月13日美麗島人士被捕後,被分成「台獨」、「共匪」兩類進行偵訊的情況類似。於此,二二八事件遂與美麗島事件產生某種意義的連結。
3月9日再度戒嚴,一般注意的是軍隊掃蕩鎮壓、綏靖清鄉,但從「高雄中學檔案」可知,長官公署教育處要求各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須於特定時間內撰寫表白日記,內容包括2月28日至3月13日間與何人在一起?談些什麼、聽到什麼、看到什麼?曾參加何種集會、何種隊伍?會議中哪些人發表意見?所見所聞所行的感想最厲害的是:「學生作表白日記以後,發覺自己言行已被他人報告訐發而未曾載入表白日記中者,不得藉口遺忘而要求補記。」「學生如有故意規避,不作表白日記者,學校得撤銷其原有學籍。」高雄第一中學因教員、學生多人參與事件,事件後校長林景元遂被解職,改派第二中學校長林一鶴來接管處理校務,這位二中林校長在一份〈二二八事件私人損失調查表〉中,大剌剌詳列西裝三套、襯衣四件、襪五雙、短褲三條……合共台幣126,000千元。
在國家安全局檔案中,有許多台省各地的通訊員向「南京言普誠先生」提出的報告,例如一位高雄組義務通訊員劉鴻報稱:「3月3日暴動時前金區區長陳水印利用區公所為保安隊部,召集流氓充保安隊員,陳自任保安隊長肆意毆擊外省籍人民……」,另根據一位通訊員江心波抄送的「高雄市各區此次事變死傷調查表」,其中各機關人員受傷調查表率皆外省籍,時間是3月3日、4日,各區本省民眾死亡迄3月13日為止以鹽埕區34人為最多,死亡時間大多在3月6日,這份資料可以間接印證彭孟緝率兵攻入市區的時間就是3月6日,也就是傷亡最慘重的一天。另據高雄組謝愛吼的報告,彭孟緝使高雄市「恢復秩序」以後,3月8日即率部隊圍剿屏東,除繳獲武器並將屏市參議會議長葉秋木等三名首謀逮捕槍決,市府各機關於9日恢復辦公;台南方面則是3月11日晨由彭司令派上校參謀楊俊率領機動部隊前往,將各要點占據並控制交通後,「匪徒」旋即逃竄。確切時間與經過當需其他資料比對,惟以當時彭孟緝聽到陳儀的軟性廣播就判定長官必遭劫持,其積極表現且過度反應,是一致的印象。
實則,情治系統的報告也有冷靜客觀的部分,非皆誇大危情,例如一位金燮佳轉達義務通訊員蘇森的意見稱:「專賣局查緝私煙竟置走私商人於不顧,而捨本逐末專拘販賣私煙之小香煙攤,種下台人不滿之因。」至於28日請願民眾「動機與目的均尚屬單純」,不料復遭機槍掃射死傷甚重,於是釀成空前事變,前後描述已暗指陳儀一錯再錯,這份報告又說:「此次事變確非出諸共黨之煽動,惟事變擴大後共黨分子混雜其間進行部分的煽動則確有其事。」可惜蔣介石選擇性地認知情報,對陳儀一味袒護,當3月中下旬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曾以臨時動議方式檢討台省事變,通過懲辦陳儀的決議以後竟又被蔣翻案,蔣還稱讚陳儀負責盡職,那麼,誰是應該負責的二二八「元凶」還需爭論嗎?
二二八的族群衝突面向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出版、鄭鴻生先生所寫的一本新書,其中一篇文章〈誰的二二八?〉說到:「族群衝突」是二二八當時最末流、最不應該強調的因素,後來卻被誇大渲染成為最主要的矛盾;鄭先生說如果要談族群衝突,「我們能夠找到當時最鮮活、最具體的例證就只能是『打阿山仔』──就是在事變期間一些暴民不分青紅皂白,到處毆打、殺害一般外省人這件事。而這正是讓我年輕時候耿耿於懷的心頭之痛。」吾人推敲鄭先生所謂的「後來」,應該不包括戒嚴時代外來政權繼續扭曲二二八的一段吧,至於解嚴後,除了第一部探討二二八的著名電影《悲情城市》,對「打阿山仔」的情節有所交代以外,舉凡民間的公義和平運動、研討會論文或民進黨主要領導人的公開發言,有誰講過族群衝突是二二八最重要的因素或最主要的矛盾?有誰指責過「外省人」要負責任?
包括2006年2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重點亦在闡明蔣介石應負最大責任,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等軍政首長應負次要責任的理由,附論中同時認定這是政府犯罪,今日追究這些人的刑事責任,還具有還給其他「外省人」族群清白的積極效能。儘管如此,為什麼以鄭鴻生為代表的一群人還是會覺得「族群冒犯」呢?個人認為,解嚴以來的二二八真相追求與平反運動,是與塑造台灣認同的本土化運動乃至台獨運動分不開的,站在「反台獨」或親中、統一立場的人不免產生排斥,所以,是他們對號入座,不是別人做了什麼誇大扭曲。
進一步說,二二八事件爆發初期,尤其是長官公署衛兵開槍以後激起台灣人普遍的憤怒,很多地方確實發生「打阿山仔」的現象,但是台灣人仕紳組成的處理委員會立刻予以制止,而且不必等到3月8日援軍登陸,各地的巡邏士兵早已開槍反擊乃至報復;例如3月6日彭孟緝派出來的軍隊,在高雄市胡亂掃射、任意搶劫的現象,難道沒有族群因素作祟?高雄方面至少已經有許雪姬教授所做的三本口述訪問紀錄(1995年出版)可以作證。反台獨或親中的知識分子如果真正關心二二八悲劇,早就應該去完成(也只有他們能完成的)二二八當時外省人受害的口述歷史,可惜到今天一本也無。
就像電影《悲情城市》的情節所顯示的,一般台灣人對「祖國」的來臨多麼格格不入,台灣變成中華民國的初始必須經過暴力流血的轉化,可見國家認同的建(虛)構性。個人認為,惟有誠實面對二二八的「族群衝突」面向,才能深刻反省今日藍綠政黨宛若敵國,其背後的認同政治糾結。
為二二八控告國民黨的一段失敗經驗
1995年公布施行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只是由行政院設立的基金會進行補償作業,與轉型正義攸關的追求真相關連不大,遑論司法上的究責。所以,當2006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以後,一群二二八家屬以及台教會等社團就積極思考向法院控告國民黨的可能性。
2010年的2月26日,也就是二二八紀念日前夕,由張炎憲(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陳儀深(台灣教授協會會長)以及顧立雄、李勝雄等五位律師作為訴訟代理人,王不纏等108位受難家屬作為原告,終於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訴訟標的是要求國民黨將其黨史館收藏之二二八相關檔案,以及戒嚴時期之中常會紀錄、總裁批簽、海工會檔案悉數交由檔案管理局保存並公開;國民黨應以黨產捐出新台幣二十億元作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籌設及營運經費;國民黨必須在國內外重要報紙之頭版半版篇幅刊登起訴狀所附之道歉聲明。接下來,歷經同年4月14日開首次言詞辯論庭、8月6日判決原告敗訴、8月25日原告等再向高院提起上訴、11月25日高院開庭,隔年即2011年4月26日高院判決駁回上訴,同年5月20日我們向最高法院上訴,9月22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確定。
訴訟期間,中國國民黨的法定代理人是馬英九主席,訴訟代理人是賴素如、洪文浚兩位律師,從他們的辯論意旨狀和答辯狀看,只能說「毫無悔意」。例如,說蔣介石是「基於政府公務人員之職權所為公法上之行為,而非基於擔任政黨法定代理人之職務所為」,「該等公務員之作為應係本於其公務員之身分而於政府指揮下所為之,即屬政府之行為,亦與被上訴人(中國國民黨)無涉」;最厚顏的是,還敢引用「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即罹時效,如今距離二二八事件已經超過數十年,所以「不應准許」原告即這一百多位二二八家屬的請求。不幸的是,三級三審的法官們,只採信或抄襲國民黨的上述論點,對於我們書狀所說1947年事件發生當時尚屬「黨國一體、黨在國上」之訓政時期,台灣人之生命、財產、自由所遭受之鉅大損害,以及轉型正義之世界潮流云云皆視若無睹。
光是「罹於時效」的理由也敢拿出來當武器,即可見今日特別立法之必要。立法院還在處理中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即使通過,也不見得可以迫使國民黨接受上述家屬的三大訴求,但至少顯示台灣社會主流意見已然轉變,也許今後再來告它一次,會有不同的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