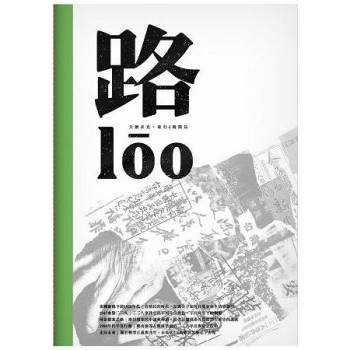〈二二八與詩作──跨越語言的人們,被語言所跨越的人生〉/徐祥弼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台灣後的隔年4月,隨即成立了「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大力推行「國語運動」,更於同年9月14日強制台灣人禁止說日語,因而被當時的知識分子大力抨擊:「此舉無異等於封死本省人之耳目⋯⋯連恣意施行鎮壓政策的日本當局,甚至也等到中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才禁止使用中國語」。就1942年日本當局的統計,那時台灣島內的日語普及率高達60%,更遑論經過幾年皇民化洗禮,「光復」後的台灣社會。
語言政策的影響是全面的,雖然對於學校外的常民生活影響有限,但至於知識分子與創作者則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因為他們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公眾的發聲,語言的傳遞對象不只是私下交談,更是要發布、傳達給廣大的社會大眾。此一政策的疾厲施行對他們而言是毀滅性的,特別是在原本的語言(日語)使用已經極為純熟的情況下。林亨泰就曾說:「要放棄一個熟悉的語言再來學習新的語言,這是非常痛苦的」、「語言是創作的根本,失去語言幾乎就等於被剝奪了表達的能力」──在此基礎上,他進而提出了「跨越語言的一代」這個詞,並形容那是「一場既抗拒又融合的過程」。就像杜潘芳格在〈聲音〉一詩所描述的:「從那時起,/語言失去出口。/現在,只能等待新的聲音,/一天又一天,/嚴肅地忍耐地等待。」他們恍如被禁聲。
在此同時,不學習「國語」還可能被質疑對國家不忠或對中國國民黨不滿,有如吳新榮的悲哀景況:「我們不得不遵守『沉默為金』『雄辯為銀』的西諺,除出於萬不得已外,蠻不說話……因此卻有人說我們驕傲,又有人真的誤解為我們不合作,於是現在不得不跟孩子學習國語。」林亨泰形容台灣人的難堪處境是「在日本人最黑暗的時候當了日本人,在中國人最絕望的時候當了中國人」。
在這個時代環境,以及1949年台大與師大發生的四六事件後長官公署對於作家的箝制與搜捕之下,造成了一批作家從此停筆,吳瀛濤也因此寫下〈在一個時期〉一詩:「啊,在那一個時期,我卻曾死過了一次」;然而,還是有其他一群人,在再日後重新再出發,書寫不懈。但這種語言的再學習,終究會使得他們的創作必須經過相當地轉譯後,才得以成為作品呈現在我們眼前。這種無法如過去使用母語時的順暢情景,成為了這代作家群共享的難堪,鍾肇政曾提到他的創作是「先把想法用日文寫下來,再一句一句翻譯成中文;再逐漸從文字的翻譯,到在腦子裡就可以翻譯」,陳千武也說他是在「學習了華語之後,才在河洛語和日語的根基上,疊上華語的外衣」。在這個基礎上,因而有學者翻轉了原先的概念,轉而認為這代作家群本身不只是「跨越語言的一代」,更是「被語言所跨越的一代」,將語言之中的個人角色由主動轉為被動,更加深刻的形容且強調這代作家群面對的困境,在大時代政權遞轉下的無奈,以及無力。
阮美慧將這「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群,以1920年代為界,劃分出了兩個世代。前期是1920年代前出生的作家,因受了嚴格的日語教育,因而深受語言的限制,如龍瑛宗、吳瀛濤、吳新榮、呂赫若等人;後期則是在日治晚期受的教育,語言使用上相對具有彈性,而文學成就也多在戰後,這「戰後第一代作家」有陳千武、葉石濤、鍾肇政、林亨泰、詹冰、錦連等人。在他們身上可以清楚地看見時代的演變,政治對於文學,甚至是對於個人的介入,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文學觀,使得他們更加重視鄉土與現實,後來《笠》詩刊的創設與成員也是與此息息相關。
在這些戰後第一代作家的帶領下,台灣文學逐漸成形。他們在中國的基礎上扎根台灣,再融合了西方所流行的文學風格,以及年少時的日本經驗,匯聚成為一套嶄新的台灣文學風貌,在困頓上重生,進而更使「台灣」得以從這之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大寫的主體。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台灣後的隔年4月,隨即成立了「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大力推行「國語運動」,更於同年9月14日強制台灣人禁止說日語,因而被當時的知識分子大力抨擊:「此舉無異等於封死本省人之耳目⋯⋯連恣意施行鎮壓政策的日本當局,甚至也等到中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才禁止使用中國語」。就1942年日本當局的統計,那時台灣島內的日語普及率高達60%,更遑論經過幾年皇民化洗禮,「光復」後的台灣社會。
語言政策的影響是全面的,雖然對於學校外的常民生活影響有限,但至於知識分子與創作者則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因為他們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公眾的發聲,語言的傳遞對象不只是私下交談,更是要發布、傳達給廣大的社會大眾。此一政策的疾厲施行對他們而言是毀滅性的,特別是在原本的語言(日語)使用已經極為純熟的情況下。林亨泰就曾說:「要放棄一個熟悉的語言再來學習新的語言,這是非常痛苦的」、「語言是創作的根本,失去語言幾乎就等於被剝奪了表達的能力」──在此基礎上,他進而提出了「跨越語言的一代」這個詞,並形容那是「一場既抗拒又融合的過程」。就像杜潘芳格在〈聲音〉一詩所描述的:「從那時起,/語言失去出口。/現在,只能等待新的聲音,/一天又一天,/嚴肅地忍耐地等待。」他們恍如被禁聲。
在此同時,不學習「國語」還可能被質疑對國家不忠或對中國國民黨不滿,有如吳新榮的悲哀景況:「我們不得不遵守『沉默為金』『雄辯為銀』的西諺,除出於萬不得已外,蠻不說話……因此卻有人說我們驕傲,又有人真的誤解為我們不合作,於是現在不得不跟孩子學習國語。」林亨泰形容台灣人的難堪處境是「在日本人最黑暗的時候當了日本人,在中國人最絕望的時候當了中國人」。
在這個時代環境,以及1949年台大與師大發生的四六事件後長官公署對於作家的箝制與搜捕之下,造成了一批作家從此停筆,吳瀛濤也因此寫下〈在一個時期〉一詩:「啊,在那一個時期,我卻曾死過了一次」;然而,還是有其他一群人,在再日後重新再出發,書寫不懈。但這種語言的再學習,終究會使得他們的創作必須經過相當地轉譯後,才得以成為作品呈現在我們眼前。這種無法如過去使用母語時的順暢情景,成為了這代作家群共享的難堪,鍾肇政曾提到他的創作是「先把想法用日文寫下來,再一句一句翻譯成中文;再逐漸從文字的翻譯,到在腦子裡就可以翻譯」,陳千武也說他是在「學習了華語之後,才在河洛語和日語的根基上,疊上華語的外衣」。在這個基礎上,因而有學者翻轉了原先的概念,轉而認為這代作家群本身不只是「跨越語言的一代」,更是「被語言所跨越的一代」,將語言之中的個人角色由主動轉為被動,更加深刻的形容且強調這代作家群面對的困境,在大時代政權遞轉下的無奈,以及無力。
阮美慧將這「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群,以1920年代為界,劃分出了兩個世代。前期是1920年代前出生的作家,因受了嚴格的日語教育,因而深受語言的限制,如龍瑛宗、吳瀛濤、吳新榮、呂赫若等人;後期則是在日治晚期受的教育,語言使用上相對具有彈性,而文學成就也多在戰後,這「戰後第一代作家」有陳千武、葉石濤、鍾肇政、林亨泰、詹冰、錦連等人。在他們身上可以清楚地看見時代的演變,政治對於文學,甚至是對於個人的介入,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文學觀,使得他們更加重視鄉土與現實,後來《笠》詩刊的創設與成員也是與此息息相關。
在這些戰後第一代作家的帶領下,台灣文學逐漸成形。他們在中國的基礎上扎根台灣,再融合了西方所流行的文學風格,以及年少時的日本經驗,匯聚成為一套嶄新的台灣文學風貌,在困頓上重生,進而更使「台灣」得以從這之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大寫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