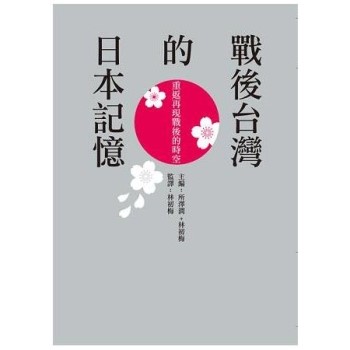序論導讀
那個年代的台灣
⊙所澤潤/著 周俊宇/譯
我想起了那個年代的台灣。雖然也許只是我的一種說法,這裡所謂的「那個年代」,指的是台灣從開始到完成民主化的過程,也就是一九七 ○年代末到一九九○年代中期為止的這段期間。只要是在那個年代和台灣有過接觸的日本人,無疑都會帶著某種眷戀之情來回憶當時的台灣。
本書雖以戰後台灣形成的「日本元素」為題但其實那個年代的文化現象如何形成?和現今之間又有何種關連?也是一個重點。現在造訪台灣的絕大多數日本人,或許會理所當然地覺得台灣是個民主又對日本抱持好感的已開發國家。然而,在那個年代首次造訪台灣的日本人所看到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一個充滿日本仿冒商品和拷貝歌曲的地方。本書各章所要處理的,就是這樣一個當時在台灣開花的文化現象。
作為閱讀本書的指引身為編者的我在〈序論〉裡期盼在某種程度上和讀者共享那個年代,以及戰爭結束以來的時代印象。因此,這篇〈序論〉亦可視作獨立的篇章,未必要放在其他章節前面來讀。
那麼,以下就先由我的片斷經驗,來為現在才開始接觸台灣的日本人,解讀他們所不瞭解的二、三十年前的台灣吧!
一、那個年代
既是醫師,也是大學教授的陳氏(名字暫且按下不表),在答應我對他做口述歷史訪談的請求後,就在我正要搭上計程車的道別之際,他這麼說:
「當沖繩回歸日本時,大家都很高興,以為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我第一次見到陳氏是一九九四年四月的事。
陳氏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戰後自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成為醫師。是一所知名醫學大學的教授當時的他理所當然地以為台灣人也會回歸日本。
在和陳氏見了幾次面以後,他還這麼對我說。
「現在在台灣講日語已經不太能通,而且事到如今已經不可能回歸日本,再來只能尋求台灣獨立了。」
對於陳氏他們來講,獨立不過是一個最大程度讓步的選項而已。台灣的日本教育世代(又稱作日語世代)裡頭,許多人抱持的就是這種想法。這樣的心境無法透過問卷調查來回答,而且只能對特定的日本人說,因此或許偏好統計數據的人會認為,這只是特定的一群人的問題而不值一顧,而我認為這是一種「無聲之聲」。
然而,在一九八 ○年代來到日本,比我還年輕的台灣本省籍留學生,所抱持的想法似乎完全不同。本省人指的是在日本統治時代,擁有日本國籍的台灣漢人及其後代。如今某位在台灣某國立大學擔任教授的友人,在選擇台灣獨立或是與中國大陸統一的兩岸議題,在各界認為於邁向統一方面稍有進展的那段時期,曾作了如下發言。
「只要想到那遼闊的中國都是自己的國家就覺得非常興奮自己的祖先同樣是來自中國源頭,中原的民族。」
長期以來,許多戰後教育世代的本省人自認為中國人,背後或許正有這樣的快感。這種感覺和大多數日本教育世代的感覺,宛如油與水一般,互不相容。
有關語言的想法,年輕一代和年長者間也多有相異之處。
現居台灣獨立派核心地位的一位友人,一九八 ○年在我提到想學台灣話時,曾對我說:「那不是語言,沒有用所以不用學」。那時我覺得莫名其妙,而感到莫大的衝擊。
每天和他們相處談話我漸漸地瞭解到幾件事他們在家幾乎都講台灣話在學校則用北京話來讀寫。「那麼寫日記時又是如何呢?」這麼一問,他們回答是依北京話來寫當我再進一步問「是用北京話來寫台灣話的口語內容嗎?」,他們甚至不理我,反而覺得我莫名其妙。
然而,在日本統治時代下畢業於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年齡層的雙親世代,則認為北京話是不同世界的話語。一九八 ○年我在留學生邀請下造訪台灣,某位友人尊翁所講的話則完全不同。當時我透過電視或電台開始學中國話,所以試著用幾句隻字片語的北京話交談。這時友人尊翁先是稱讚我:「你講的日語很漂亮,是東京那邊的話」,接著開始對我說教,他說:「日本人不可以學北京話。不需要那種語言。日本人只要講日本話就好了」。
在台灣許多家庭裡,日本教育世代和戰後教育世代一方面各懷不相容的價值觀,一方面又作為一家人共同生活台灣是家族聯繫很強的地方所以我常想他們這樣竟然還能一起生活,如果是在日本的話,大概就不成一家人了。
有關語言,還有下面這段回憶。
第一次和台灣留學生相識時,認識的留學生裡頭有幾位被雙親要求要用日文的父母還幫忙修改日文寫信。那時我是抱著原來如此的心情聽他們說這些事,並給我看寫有紅字被修改過的信,有一次一位留學生說自己。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事。其他留學生似乎也一樣。或許不少現年六十歲左右,有留日經驗的台灣人,都曾有過這樣的經驗。不過,說來很失禮,當時的我聽到留學生父母的日文好到還可以幫人修改,其實是半信半疑。因為自己清楚自己不管再怎麼努力學英文,也無法達到為人修改的程度。
一九八 ○年二月我第一次到台灣那時我接觸到了日語世代講的日本話,當然感覺到他們的日語能力是能夠為人修改的,也接觸到了各式各樣,例如能操雙語卻還是有台灣腔,或是完全沒有口音的人。我也記得,一位四十五歲左右的女性用半調子的日語很抱歉似地對我說,我的日語只學到小學校二年級。被友人帶著搭了好幾次的計程車,印象中頂多只有一位司機不會講日語。附帶一提,當時台北的計程車已經開始使用計程表,但那全部都是在大阪用過的中古貨,機器上還留有大阪公司的名稱。
第一次到台灣,關於日本話有不少地方令我感到困惑,而叫人驚訝的是也有外省人講日本話。那次我在台灣停留了兩個星期,透過友人家裡的關係,拜訪了台北市的古董店。那家古董店是一對外省夫婦經營的,對我用聽似並非平常用慣的日本話說自己原先住在北京。他們還說當時北京也有許多日本人,甚至有日本友人到台灣來找他們。還來不及多談一些,問個清楚,就在友人的催促下離開了,如今想來真是可惜。那對老夫婦給我的感覺是對日本人有很深的懷舊之情。
由於沒能好好聊上一段話而感到遺憾,回到友人府上後向友人父母提到這件事,他母親便警告我那些話全不可信那時我才開始意識到台灣的複雜也就是思考台灣是單憑曾受日本統治的這個認識,存在於台灣之中的「日本元素」並不單純,尚不足以充分理解的世界。
那個年代,日本文化非常深入台灣。對此,本篇〈序論〉接下來將進一步闡述,並說明本書各章概略,再以從戰後到現在為止的時代為背景,深入探討該以什麼框架來理解各章的內容。
我要對「戰爭結束後到那個年代為止的台灣」的種種日常樣態提出一個看法。那就是日本和台灣形成了一個同型性很高,可以稱得上是平行世界的關係;此外,其中既有連結兩個世界的裝置,也有在其間牽線的日本人。我強烈傾向主張這個相互關係,是在日本和台灣隔絕,即一九六五年左右以前約二十年的期間,也就是戰後初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對此,在〈序論〉將詳加說明。另外也要明確指出,本書各章或多或少都可以被定位在這樣一個平行世界的相互關係上。還要關注連結兩者的裝置和人物的有無上。〈序論〉最後則欲回顧民主化達成二十年後的現今,再次思考那個年代和稍早以前的這個時期的意義。
那個年代的台灣
⊙所澤潤/著 周俊宇/譯
我想起了那個年代的台灣。雖然也許只是我的一種說法,這裡所謂的「那個年代」,指的是台灣從開始到完成民主化的過程,也就是一九七 ○年代末到一九九○年代中期為止的這段期間。只要是在那個年代和台灣有過接觸的日本人,無疑都會帶著某種眷戀之情來回憶當時的台灣。
本書雖以戰後台灣形成的「日本元素」為題但其實那個年代的文化現象如何形成?和現今之間又有何種關連?也是一個重點。現在造訪台灣的絕大多數日本人,或許會理所當然地覺得台灣是個民主又對日本抱持好感的已開發國家。然而,在那個年代首次造訪台灣的日本人所看到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一個充滿日本仿冒商品和拷貝歌曲的地方。本書各章所要處理的,就是這樣一個當時在台灣開花的文化現象。
作為閱讀本書的指引身為編者的我在〈序論〉裡期盼在某種程度上和讀者共享那個年代,以及戰爭結束以來的時代印象。因此,這篇〈序論〉亦可視作獨立的篇章,未必要放在其他章節前面來讀。
那麼,以下就先由我的片斷經驗,來為現在才開始接觸台灣的日本人,解讀他們所不瞭解的二、三十年前的台灣吧!
一、那個年代
既是醫師,也是大學教授的陳氏(名字暫且按下不表),在答應我對他做口述歷史訪談的請求後,就在我正要搭上計程車的道別之際,他這麼說:
「當沖繩回歸日本時,大家都很高興,以為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我第一次見到陳氏是一九九四年四月的事。
陳氏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戰後自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成為醫師。是一所知名醫學大學的教授當時的他理所當然地以為台灣人也會回歸日本。
在和陳氏見了幾次面以後,他還這麼對我說。
「現在在台灣講日語已經不太能通,而且事到如今已經不可能回歸日本,再來只能尋求台灣獨立了。」
對於陳氏他們來講,獨立不過是一個最大程度讓步的選項而已。台灣的日本教育世代(又稱作日語世代)裡頭,許多人抱持的就是這種想法。這樣的心境無法透過問卷調查來回答,而且只能對特定的日本人說,因此或許偏好統計數據的人會認為,這只是特定的一群人的問題而不值一顧,而我認為這是一種「無聲之聲」。
然而,在一九八 ○年代來到日本,比我還年輕的台灣本省籍留學生,所抱持的想法似乎完全不同。本省人指的是在日本統治時代,擁有日本國籍的台灣漢人及其後代。如今某位在台灣某國立大學擔任教授的友人,在選擇台灣獨立或是與中國大陸統一的兩岸議題,在各界認為於邁向統一方面稍有進展的那段時期,曾作了如下發言。
「只要想到那遼闊的中國都是自己的國家就覺得非常興奮自己的祖先同樣是來自中國源頭,中原的民族。」
長期以來,許多戰後教育世代的本省人自認為中國人,背後或許正有這樣的快感。這種感覺和大多數日本教育世代的感覺,宛如油與水一般,互不相容。
有關語言的想法,年輕一代和年長者間也多有相異之處。
現居台灣獨立派核心地位的一位友人,一九八 ○年在我提到想學台灣話時,曾對我說:「那不是語言,沒有用所以不用學」。那時我覺得莫名其妙,而感到莫大的衝擊。
每天和他們相處談話我漸漸地瞭解到幾件事他們在家幾乎都講台灣話在學校則用北京話來讀寫。「那麼寫日記時又是如何呢?」這麼一問,他們回答是依北京話來寫當我再進一步問「是用北京話來寫台灣話的口語內容嗎?」,他們甚至不理我,反而覺得我莫名其妙。
然而,在日本統治時代下畢業於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年齡層的雙親世代,則認為北京話是不同世界的話語。一九八 ○年我在留學生邀請下造訪台灣,某位友人尊翁所講的話則完全不同。當時我透過電視或電台開始學中國話,所以試著用幾句隻字片語的北京話交談。這時友人尊翁先是稱讚我:「你講的日語很漂亮,是東京那邊的話」,接著開始對我說教,他說:「日本人不可以學北京話。不需要那種語言。日本人只要講日本話就好了」。
在台灣許多家庭裡,日本教育世代和戰後教育世代一方面各懷不相容的價值觀,一方面又作為一家人共同生活台灣是家族聯繫很強的地方所以我常想他們這樣竟然還能一起生活,如果是在日本的話,大概就不成一家人了。
有關語言,還有下面這段回憶。
第一次和台灣留學生相識時,認識的留學生裡頭有幾位被雙親要求要用日文的父母還幫忙修改日文寫信。那時我是抱著原來如此的心情聽他們說這些事,並給我看寫有紅字被修改過的信,有一次一位留學生說自己。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事。其他留學生似乎也一樣。或許不少現年六十歲左右,有留日經驗的台灣人,都曾有過這樣的經驗。不過,說來很失禮,當時的我聽到留學生父母的日文好到還可以幫人修改,其實是半信半疑。因為自己清楚自己不管再怎麼努力學英文,也無法達到為人修改的程度。
一九八 ○年二月我第一次到台灣那時我接觸到了日語世代講的日本話,當然感覺到他們的日語能力是能夠為人修改的,也接觸到了各式各樣,例如能操雙語卻還是有台灣腔,或是完全沒有口音的人。我也記得,一位四十五歲左右的女性用半調子的日語很抱歉似地對我說,我的日語只學到小學校二年級。被友人帶著搭了好幾次的計程車,印象中頂多只有一位司機不會講日語。附帶一提,當時台北的計程車已經開始使用計程表,但那全部都是在大阪用過的中古貨,機器上還留有大阪公司的名稱。
第一次到台灣,關於日本話有不少地方令我感到困惑,而叫人驚訝的是也有外省人講日本話。那次我在台灣停留了兩個星期,透過友人家裡的關係,拜訪了台北市的古董店。那家古董店是一對外省夫婦經營的,對我用聽似並非平常用慣的日本話說自己原先住在北京。他們還說當時北京也有許多日本人,甚至有日本友人到台灣來找他們。還來不及多談一些,問個清楚,就在友人的催促下離開了,如今想來真是可惜。那對老夫婦給我的感覺是對日本人有很深的懷舊之情。
由於沒能好好聊上一段話而感到遺憾,回到友人府上後向友人父母提到這件事,他母親便警告我那些話全不可信那時我才開始意識到台灣的複雜也就是思考台灣是單憑曾受日本統治的這個認識,存在於台灣之中的「日本元素」並不單純,尚不足以充分理解的世界。
那個年代,日本文化非常深入台灣。對此,本篇〈序論〉接下來將進一步闡述,並說明本書各章概略,再以從戰後到現在為止的時代為背景,深入探討該以什麼框架來理解各章的內容。
我要對「戰爭結束後到那個年代為止的台灣」的種種日常樣態提出一個看法。那就是日本和台灣形成了一個同型性很高,可以稱得上是平行世界的關係;此外,其中既有連結兩個世界的裝置,也有在其間牽線的日本人。我強烈傾向主張這個相互關係,是在日本和台灣隔絕,即一九六五年左右以前約二十年的期間,也就是戰後初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對此,在〈序論〉將詳加說明。另外也要明確指出,本書各章或多或少都可以被定位在這樣一個平行世界的相互關係上。還要關注連結兩者的裝置和人物的有無上。〈序論〉最後則欲回顧民主化達成二十年後的現今,再次思考那個年代和稍早以前的這個時期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