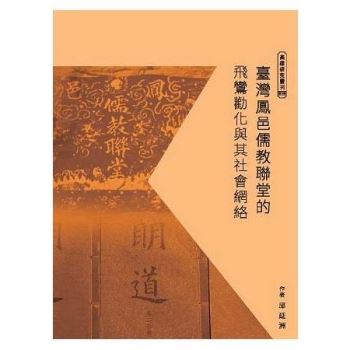導言
參與寺廟活動大概是多數臺灣人共同的生活經驗與記憶,其中以神明誕辰,也就是俗稱的「神明生」最多,從俗諺「三月痟媽祖」,即可反映此種現象,顯現臺灣民眾對寺廟活動的參與程度,然而在臺灣不僅僅只有農曆三月的「媽祖生」,每個月也都有各種神祇誕辰,可見寺廟活動的影響力是不容小覷。
與多數臺灣民眾相同,「看熱鬧(kuànn láu liat)」係從小養成的經驗和興趣,回憶幼時,因住家緊鄰寺廟,接觸宗教活動可謂頻繁,當時也與外界認為神秘之宗教儀式「扶鸞」有微妙的邂逅,小時候並不知這是多特殊的信仰儀式,如此的邂逅確實也影響筆者至今。其實接觸扶鸞並非偶然或者意外,祖父與父親皆是正鸞生,算是一種家族信仰,只是當時不知悉而已,這種兒時的經驗,也在成年之後化為實際的信仰行為,高三那年開始「行堂(kiânn tng)」,大學四年級(2010)奉恩師之命正式宣誓入堂。
基於這樣的生活經驗,又加上所學與民俗文化、民間信仰相關甚深,遂而提筆撰文,藉由大學以降的課程修習,啟發了對民間信仰與鸞堂議題的求知慾,閱讀相關的研究與書籍,深刻發覺書中呈現與筆者生長地「鳳山」的鸞堂信仰有甚多差異之處,這是本書得以成形的始端。經由大量的閱讀及田野觀察發現,許多研究者為避免探討主題失焦,都會免除討論周邊問題,鸞堂研究亦然,如王見川兩篇著作〈西來庵事件與道教、鸞堂之關係——兼論其周邊問題〉、〈略論陳中和家族的信仰與勸善活動〉提供對鸞堂研究之反思。
王見川兩篇文章,前者討論西來庵與鸞堂的關係,除全臺白龍庵開基五大家將團外,西來庵亦有五團的家將,其堂號以「吉」字為頭,是全臺灣「吉」字頭家將團之源,在整個家將信仰與文化的發展過程極為重要, 但王氏並未談及西來庵家將與鸞堂間的互動,令他人無法得知西來庵的信仰全貌及西來庵事件中,家將團是否參與或是扮演角色為何?後者亦是聚焦於陳中和及其家族在鸞堂的勸善事業,對陳中和家族是否為單純的鸞堂信仰者也未有討論。傳統上,地方神廟是公眾的議事場域,仕紳掌握了寺廟,亦是掌握了分配利益的權力,在此文中,只見身為仕紳階層的陳中和奔走於鸞堂的勸善活動,卻未見投身更廣泛之民間信仰相關事務,這顯然與一般大眾對大多數仕紳的地方參與情況印象有所不同。藉由上面兩篇論述,可有些許思考。首先,西來庵事件被定位為單純的鸞堂所發起之抗日事件;第二,陳中和等仕紳階層被導引為單純的鸞堂信仰者。而從先前閱讀與觀察經驗觀之,研究聚焦後造成鸞堂其他面向的問題不被看見,觀察到的也只是看到鸞堂外部現象,無法了解該鸞堂實際上的諸多問題。
鳳山地區約莫於戰後至1950年代初期出現了設立鸞堂的風潮,更在1961年聯合著造善書《眀道》,當時參與聯著共有十一座鸞堂,「聯著」不表示各鸞堂的組織就此合併,反而另設「鳳邑儒教聯堂」,作為聯著善書時處理相關事宜的組織,故鳳山地區的鸞堂之間仍是維持獨立的信仰領域。在剛開始的初步走訪,即發現這些鸞堂地理位置之分布極為有趣,似乎與庄頭聚落有所關聯;換言之,鸞堂與聚落民眾的生活,存在著某種從外部現象難以發現的互動關係。此外,戰後以來,鳳山地區鸞堂信仰與「地方公廟」亦有著微妙互動,然而現今鸞堂研究成果中鮮少關注鸞堂與地方信仰互動關係,職是,鳳山地區鸞堂與地方公廟的雙方互動似乎擁有與其他地區鸞堂不同且特殊之處。
經由田調過程與自身參與的經驗,發現幾個有趣的現象:1.鳳山地區各鸞堂皆具有強烈的獨立性,在此前提下,鸞堂之間以及鸞堂與地方公廟間仍存有頻繁互動情況;2.鸞堂的發展脈絡上,地方菁英似乎扮演著鸞堂之間,及地方公廟之信仰聯結的媒介角色;3 鳳山地區鸞堂網絡的若干互動關係中,似乎與聚落居民也存在著緊密聯結。在此,對初步田野觀察的現象,提出本書擬討論的問題面向:1.鳳山地區鸞堂在強烈的獨立性格驅使下,其社會網絡如何形成?2.鳳山地區鸞堂的社會網絡係透過怎樣模式進行互動?
扶鸞的形成,許地山認為文人扶乩始於宋代,7 基本上不論扶乩或是扶鸞等宗教儀式均不專屬任何民間教派,至少在臺灣所見如此。《臺灣慣習記事》與丸井圭治郎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都將鸞堂定義為迷信與巫覡,內容偏重信仰與活動介紹,形式上以調查報告為主。增田福太郎《臺灣本島人の宗教》對儒教神祇系統較有著墨,但討論面向侷限,且定義亦是朝迷信與巫覡進行解釋,與現行研究的討論相較,差異甚大。本書著重信仰與地方的討論,為了解鳳山地區鸞堂信仰與地方公廟、地方菁英、聚落民眾等多重的互動,主要仍以鸞堂信仰為研究主軸,從中延伸思考,論述鸞堂信仰及其社會網絡,然而目前在此項議題上,並無強烈之論述文章,為求深入知悉地方與信仰之間的關係,先從幾項有關地方與信仰互動的概念來說明。
目前信仰與地方研究多以「祭祀圈」作為論述的觀點,通常用在討論地方公廟與聚落居民之間的互動關係,最早使用此概念者為日治時期的岡田謙,以祭祀圈研究臺灣社會,其論點係同奉祀一個主神的民眾所居住的地域。到了1978 年許嘉明才重新為祭祀圈下了更明確的定義。林美容認為祭祀圈係為了所謂的「共神信仰」而共同舉行祭祀之居民所屬的地區單位,此後又於氏著〈由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進行對祭祀圈的反思,並提出「信仰圈」概念,其定義為:「所謂信仰圈,是以某一神明或其分身之信仰為中心,信徒所形成的志願性宗教組織,信徒的分布有一定的範圍,通常必須超越地方社區的範圍,才有信仰圈可言。」而祭祀圈抑或信仰圈,兩者之概念皆與信仰及地區有關。
雖然,祭祀圈係多數研究者用於探討民間信仰及地方社會組織的概念,但王志宇在其論著《寺廟與村落──臺灣漢人社會的歷史文化觀察》,不刻意地去討論祭祀圈,而是探討此空間中的人群如何與信仰進行互動, 從聚落的結構、聚落居民、村庄風水與道德實踐,進而論述「社會文化空間」的形成,引發省思鸞堂與聚落在信仰上與結構性的問題。鸞堂有別於一般的地方公廟,若以祭祀圈論述鸞堂與聚落民眾,似乎難以闡述完整, 針對此種在信仰與聚落的論述限制,社會文化空間之概念似乎較能解決本書在鸞堂與聚落互動的相關問題。陳建宏〈公廟與地方社會——以大溪鎮普濟堂為例〉,援引Prasenjit Duara(杜贊奇)的文化權力網絡(cultural nexus of power),以桃園大溪地區的鸞堂作為研究對象,從多項因素討論普濟堂如何從鸞堂變成地方民眾信仰的公廟,臺灣有相當多鸞堂在發展過程中成為地方公廟,其因眾多。就陳建宏認為,普濟堂轉變之因與地方菁英的介入有莫大關係,指出傳統地方菁英參與普濟堂活動,主要以地域及親屬作為關係結合的基礎,但在建廟之時加入了另一批地方菁英,削弱原先鸞生的勢力,導致普濟堂扶鸞活動衰微,鸞堂信仰本質減弱,並以象徵資本概念說明,後來加入的地方菁英其象徵資本多於之前的地方菁英。
此外,汪明怡之碩士論文〈臺南寺廟聯境組織變遷之研究〉也提出異於祭祀圈與社會文化空間的觀點。臺灣至日治以前,無論政治抑或經濟多以府城為中心,其發展過程中並無「村」或「庄」的觀念,則是以「境」來區分地域,汪氏的論文中即是闡述此種概念,清末因臺灣戰備能力不足,而由鄉紳以寺廟為中心團練鄉勇,發展出「聯境」的制度,隨著時代變遷,政權更迭,以致團練鄉勇的本質改變,轉而成為寺廟之間的「交陪」,其中除寺廟間的互動,亦牽涉寺廟與民眾的關係。汪氏在論著中援引Marcel Mauss 的「禮物交換」觀點討論之,以各寺廟間的神明誕辰的「插燭」、建醮系列活動、建醮後的送天師以及四安境的迎「聖爐、聖旗」等活動,論述聯境的變遷與寺廟的交陪。
交換理論主要為原始部落的「庫拉交易圈」及「誇富宴」後續之研究, 係一種屬於經濟人類學的研究觀點,主要論述者為Marcel Mauss,其認為原始社會的禮物交換是一種不含商業性質的相互贈予,且與宗教或巫術有直接關係,在其論著〈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一文中針對不同的交換模式提出「全面報稱體系」,此體系有三項義務,分別為給予、收取以及回報。Mauss 認為義務性的交換與餽贈係維持社會階級秩序與權力關係。無論Mauss 或汪明怡在討論交換理論時,均以禮物等屬物質情況作為論述之要點。汪氏試圖朝向傳統漢人關於「人情」部分進行論述,但最終仍回歸物質,Mauss 認為交換原則重要的係非商業性的互相贈與,且有巫術及宗教的意涵,提供思考在信仰的範疇中是如何進行交換,鳳山鸞堂社會網絡的形成,是否也存在交換的互動。鸞堂的現行研究成果,戰後至今投入研究者不少,有蔡懋棠、鄭喜夫、林永根、林漢章、王世慶、陳兆南、翁聖峰、許玉河等都曾撰文探討鸞堂或善書在臺灣的發展,其中宋光宇、鄭志明、王見川、王志宇、李世偉等人成果豐碩,探討的深度與廣度較為可觀。就戰後鸞堂研究型態的分期,1970至80年代,大致上是信仰內容與善書的介紹;1980至90年代, 則為大量使用日籍文獻資料與清末善書,呈現鸞堂歷史與善書中的內容及其反映之價值觀及與現代社會的互動回應;1990年代迄今研究之面向更為廣泛,舉凡鸞堂人物之生命史、族群性鸞堂均是研究議題,王見川提出未來鸞堂研究的六大面向:「一、鸞堂歷史,二、鸞堂的生態,三、鸞堂的宗教屬性,四、鸞書內容,五、鸞堂崇拜的主神,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互動」。此外,鄭志明更認為鸞堂研究除了著重歷史探析外,亦有其他議題可供未來研究者關注討論,如鸞堂文化的社會意義、社會心理、社會思想、倫理教化、社會控制等,顯示鸞堂宗教體系與社會的緊密結合,甚至鸞堂與當代政治的互動關係,都有被討論的空間。
鸞堂緣起與發展之研究,王世慶依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與鸞書《覺悟選新》所撰文之〈日據初期臺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整理出五種說法論述臺灣鸞堂的分布與系統,且認為扶鸞的傳入與鸞堂設立係順著臺人有吸食鴉片之勢,知識分子為改善當代社會之風氣,進而從扶鸞著手,此種論述難免限縮瞭解鸞堂設立之原因。王志宇的〈從鸞堂到儒宗神教——論鸞堂在臺之發展與傳布〉,從鸞堂設立之因素,歸納了三種類型:1.社區教化型鸞堂;2.戒煙型鸞堂;3.神威顯化型,據其歸納類型,有值得關注之處。鳳山地區鸞堂大多設立於戰後,對「戒煙(戒鴉片)」此項行為,應當式微,甚至已不存在。審視鳳山地區各鸞堂的設立,時間序上是緊密的, 各鸞堂成立肇因,似乎也不太合乎王志宇所提出的三大類型,基於時代及社會環境需求,戒煙成為鸞堂設立的肇因之一,但戰後不得見之,然而社會教化與神威顯化在現今的鸞堂信仰中仍可見得,這是否真為鸞堂設立契因,還是鸞堂發展的型態,值得深究。雖然王治宇論著所田調範圍為中部地區,但對本文欲論述之鳳山地區仍有諸多可以借鏡之處。鸞堂與一般地方公廟不同之處,在於擁有自成一格的信仰儀式,這些儀式皆與「鸞」有密切關聯,多從「扶鸞儀式」延伸。Jordan & Overmyer(焦大衛、歐大年)合著The Flying Phoenix: Aspect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Taiwan,以參與觀察,親身融入鸞堂信仰活動,詳盡記錄各項的儀式,並且對鸞堂信仰者作深度訪談,探討拜鸞活動及儀式在信仰中的意義。另外,鸞堂儀式研究,張家麟亦有論述,〈宗教儀式變遷認同與宗教發展—— 以鸞堂扶鸞活動為焦點〉及〈宗教儀式變遷與當代社會——論臺灣扶鸞儀式的型態及其形成原因〉,前文以問卷分析作為研究方法,透過問卷反映信眾對儀式變遷的接受程度,但過度以量化來論述,對信眾的信仰認同有何種強烈聯結並未有實質論證;後文屬質化研究,以獅頭山勸化堂、宜蘭新民堂與玄門真宗作為儀式變遷的討論對象,分別從鸞文形式、儀式進行及法器作為論述重點,也針對菁英、普羅階層及女性參鸞等議題進行變遷討論。然而這兩篇論著過度闡述儀式的變遷,宣稱儀式變遷有助吸引他人加入,同時在信眾認同度上是偏高的;對年事偏高的鸞堂參與者則堅守儀式之傳統性,張氏認為是習慣問題。因時代需求而儀式有所變遷實可理解, 但對儀式在「變」與「不變」的論述完整度仍有進一步討論之空間。
扶鸞儀式雖為跳脫世俗化的神聖性過程,實質上是為滿足教化功能, 因此鸞書亦成為研究鸞堂重要議題之一。蔡懋棠將臺灣善書之類型分為「新型」與「舊型」兩者,前者指明清以降在臺灣民間重新刊印,後者係指在臺灣各宗教扶鸞而成的鸞書;宋光宇指稱「古典善書」與「現代善書」, 兩人的基本概念是相同的。然善書的研究也僅止於區分其類型,於內容無太多的論述。陳兆南博士論文〈宣講及其唱本之研究〉,對清代的宣講做了詳盡的考察,有助本文從宣講的內容與形式,了解鸞堂的勸善行為。
有關高雄地區鸞堂研究,王見川首開先河,其文〈略論陳中和家族的信仰與勸善活動〉探討陳中和家族在鸞堂的勸善事業,但對陳中和及其家族人員是否為單純的鸞堂信仰者並有說明,文中引述《臺灣日日新報》之報導進行解釋:安瀾宮是苓雅寮地區的信仰中心,陳中和繪在大正七年捐資壹佰陸拾圓,幫助該廟重建。因同善社宣講臺尚未興建,只好先暫借此地宣講。
使人好奇的是陳中和家族,是否僅利用「捐資」的關係,進行商借安瀾宮之空間進行宣講?陳中和是否也積極投身地方公廟或是地方事務,才得以商借此宣講處所?全文中只見身為仕紳階層的陳中和投身於鸞堂勸善之活動,卻未見投入更廣泛的民間信仰相關事務。
目前有關高雄鸞堂發展的研究中,大致被分為福佬鸞堂與客家鸞堂兩大類型進行討論。張有志〈日治時期高雄地區鸞堂之研究〉有別於前人個案型研究的學位論文,雖斷代於日治時期,仍對各區域具代表性的鸞堂有相當討論,文中以福佬及客家作為區隔,並論述高雄地區各鸞堂的發展情況,但範圍甚大,僅能初步指出各鸞堂系譜概況,鳳山地區在日治時期僅有兩座鸞堂(舉善堂與協善堂),而其重要性,文中並無深刻論述,僅說明鳳山地區鸞堂發展佔有一定地位,雖然如此,卻也是該地區鸞堂信仰源起重要的討論資料。此外,對啟明堂、修善堂、意誠堂、善化堂與警化堂等五個福佬鸞堂之間的交流有所探討。李立涵在其碩論〈高雄無極明善天道院的起源與發展〉試圖說明鸞堂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之瓶頸,如何透過「聯造」善書解決困境,文中也從子母堂的關係,闡述意誠堂在早期明善天道院草創及其後發展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另外也點出鳳山地區的鸞堂與之互動關係。張有志與李立涵均指出鸞堂間微妙的互動,與本文欲論述的問題意識不謀而合,但過度將此現象簡單化,張氏強調鸞堂互動係透過人員的交流抑或流動,而李氏「聯造」善書作為鸞務交流的一種機制,上述兩項重點皆是表現鸞堂互動的機制,但都僅止於外在的表現形式,對此也提供思考鸞堂之間的交流是否有著更深層問題所在。對高雄地區扶鸞儀式有較完整研究為林原億之碩士論文〈高雄文化院的扶鸞儀式研究〉,文中詳細記錄了文化院的扶鸞儀式,但基督神學的教育背景,造成分析及論述扶鸞儀式的功能意義時,多以基督教對宗教儀式之觀點作為邏輯思考的前提,實難準確進行信仰的詮釋。鸞堂相關科儀儀式研究,有林金德的碩論〈鳳山鎮南宮仙公廟呂仙祖誕成儀式音樂之研究〉與賴薇如〈左營啟明堂神祇祭典儀式音樂及樂團之研究〉,兩篇論文皆是探討鸞堂在神祇誕辰的儀式與音樂,對高雄地區盛行的「聖樂團」亦有討論,雖然研究對象不同,但鸞堂信仰的本質並無太大之差異。從中檢視兩座鸞堂皆為「廟堂合一」的發展型態,但詳細觀察兩者實屬不同,兩篇研究之成果對科儀的闡述無太多差別,前者研究的鳳山仙公廟係由地方公廟發展中而設立鸞堂,後者則是由鸞堂逐步蛻變成為地方公廟,文中應該對此情況做一討論,可惜此部分的說明鮮少,顯然林氏與賴氏似乎並未發現此問題點,若是以此作為切入點,探討神祇誕辰儀式之架構,應可發現兩座鸞堂及其周邊社會網絡互動情形有無不同。
關於高雄地區福佬系善書及宣講方面之相關研究,目前僅有一篇學位論文。李淑芳碩論〈清代以來臺灣宣講活動發展研究——以高雄地區鸞堂為例〉,以楠梓天后宮、旗山天后宮及鳳邑雙慈亭的「宣講牌」作為動機,從高雄地區眾多鸞堂中,選出各代表三種性質之鸞堂進行討論,可惜較無強烈的論述,基本上其討論仍依循陳兆南對於清代宣講的想法,且用較多的篇幅去探討清代以來的宣講制度與內容,顯現高雄地區鸞堂宣講活動仍有探討的空間。
參與寺廟活動大概是多數臺灣人共同的生活經驗與記憶,其中以神明誕辰,也就是俗稱的「神明生」最多,從俗諺「三月痟媽祖」,即可反映此種現象,顯現臺灣民眾對寺廟活動的參與程度,然而在臺灣不僅僅只有農曆三月的「媽祖生」,每個月也都有各種神祇誕辰,可見寺廟活動的影響力是不容小覷。
與多數臺灣民眾相同,「看熱鬧(kuànn láu liat)」係從小養成的經驗和興趣,回憶幼時,因住家緊鄰寺廟,接觸宗教活動可謂頻繁,當時也與外界認為神秘之宗教儀式「扶鸞」有微妙的邂逅,小時候並不知這是多特殊的信仰儀式,如此的邂逅確實也影響筆者至今。其實接觸扶鸞並非偶然或者意外,祖父與父親皆是正鸞生,算是一種家族信仰,只是當時不知悉而已,這種兒時的經驗,也在成年之後化為實際的信仰行為,高三那年開始「行堂(kiânn tng)」,大學四年級(2010)奉恩師之命正式宣誓入堂。
基於這樣的生活經驗,又加上所學與民俗文化、民間信仰相關甚深,遂而提筆撰文,藉由大學以降的課程修習,啟發了對民間信仰與鸞堂議題的求知慾,閱讀相關的研究與書籍,深刻發覺書中呈現與筆者生長地「鳳山」的鸞堂信仰有甚多差異之處,這是本書得以成形的始端。經由大量的閱讀及田野觀察發現,許多研究者為避免探討主題失焦,都會免除討論周邊問題,鸞堂研究亦然,如王見川兩篇著作〈西來庵事件與道教、鸞堂之關係——兼論其周邊問題〉、〈略論陳中和家族的信仰與勸善活動〉提供對鸞堂研究之反思。
王見川兩篇文章,前者討論西來庵與鸞堂的關係,除全臺白龍庵開基五大家將團外,西來庵亦有五團的家將,其堂號以「吉」字為頭,是全臺灣「吉」字頭家將團之源,在整個家將信仰與文化的發展過程極為重要, 但王氏並未談及西來庵家將與鸞堂間的互動,令他人無法得知西來庵的信仰全貌及西來庵事件中,家將團是否參與或是扮演角色為何?後者亦是聚焦於陳中和及其家族在鸞堂的勸善事業,對陳中和家族是否為單純的鸞堂信仰者也未有討論。傳統上,地方神廟是公眾的議事場域,仕紳掌握了寺廟,亦是掌握了分配利益的權力,在此文中,只見身為仕紳階層的陳中和奔走於鸞堂的勸善活動,卻未見投身更廣泛之民間信仰相關事務,這顯然與一般大眾對大多數仕紳的地方參與情況印象有所不同。藉由上面兩篇論述,可有些許思考。首先,西來庵事件被定位為單純的鸞堂所發起之抗日事件;第二,陳中和等仕紳階層被導引為單純的鸞堂信仰者。而從先前閱讀與觀察經驗觀之,研究聚焦後造成鸞堂其他面向的問題不被看見,觀察到的也只是看到鸞堂外部現象,無法了解該鸞堂實際上的諸多問題。
鳳山地區約莫於戰後至1950年代初期出現了設立鸞堂的風潮,更在1961年聯合著造善書《眀道》,當時參與聯著共有十一座鸞堂,「聯著」不表示各鸞堂的組織就此合併,反而另設「鳳邑儒教聯堂」,作為聯著善書時處理相關事宜的組織,故鳳山地區的鸞堂之間仍是維持獨立的信仰領域。在剛開始的初步走訪,即發現這些鸞堂地理位置之分布極為有趣,似乎與庄頭聚落有所關聯;換言之,鸞堂與聚落民眾的生活,存在著某種從外部現象難以發現的互動關係。此外,戰後以來,鳳山地區鸞堂信仰與「地方公廟」亦有著微妙互動,然而現今鸞堂研究成果中鮮少關注鸞堂與地方信仰互動關係,職是,鳳山地區鸞堂與地方公廟的雙方互動似乎擁有與其他地區鸞堂不同且特殊之處。
經由田調過程與自身參與的經驗,發現幾個有趣的現象:1.鳳山地區各鸞堂皆具有強烈的獨立性,在此前提下,鸞堂之間以及鸞堂與地方公廟間仍存有頻繁互動情況;2.鸞堂的發展脈絡上,地方菁英似乎扮演著鸞堂之間,及地方公廟之信仰聯結的媒介角色;3 鳳山地區鸞堂網絡的若干互動關係中,似乎與聚落居民也存在著緊密聯結。在此,對初步田野觀察的現象,提出本書擬討論的問題面向:1.鳳山地區鸞堂在強烈的獨立性格驅使下,其社會網絡如何形成?2.鳳山地區鸞堂的社會網絡係透過怎樣模式進行互動?
扶鸞的形成,許地山認為文人扶乩始於宋代,7 基本上不論扶乩或是扶鸞等宗教儀式均不專屬任何民間教派,至少在臺灣所見如此。《臺灣慣習記事》與丸井圭治郎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都將鸞堂定義為迷信與巫覡,內容偏重信仰與活動介紹,形式上以調查報告為主。增田福太郎《臺灣本島人の宗教》對儒教神祇系統較有著墨,但討論面向侷限,且定義亦是朝迷信與巫覡進行解釋,與現行研究的討論相較,差異甚大。本書著重信仰與地方的討論,為了解鳳山地區鸞堂信仰與地方公廟、地方菁英、聚落民眾等多重的互動,主要仍以鸞堂信仰為研究主軸,從中延伸思考,論述鸞堂信仰及其社會網絡,然而目前在此項議題上,並無強烈之論述文章,為求深入知悉地方與信仰之間的關係,先從幾項有關地方與信仰互動的概念來說明。
目前信仰與地方研究多以「祭祀圈」作為論述的觀點,通常用在討論地方公廟與聚落居民之間的互動關係,最早使用此概念者為日治時期的岡田謙,以祭祀圈研究臺灣社會,其論點係同奉祀一個主神的民眾所居住的地域。到了1978 年許嘉明才重新為祭祀圈下了更明確的定義。林美容認為祭祀圈係為了所謂的「共神信仰」而共同舉行祭祀之居民所屬的地區單位,此後又於氏著〈由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進行對祭祀圈的反思,並提出「信仰圈」概念,其定義為:「所謂信仰圈,是以某一神明或其分身之信仰為中心,信徒所形成的志願性宗教組織,信徒的分布有一定的範圍,通常必須超越地方社區的範圍,才有信仰圈可言。」而祭祀圈抑或信仰圈,兩者之概念皆與信仰及地區有關。
雖然,祭祀圈係多數研究者用於探討民間信仰及地方社會組織的概念,但王志宇在其論著《寺廟與村落──臺灣漢人社會的歷史文化觀察》,不刻意地去討論祭祀圈,而是探討此空間中的人群如何與信仰進行互動, 從聚落的結構、聚落居民、村庄風水與道德實踐,進而論述「社會文化空間」的形成,引發省思鸞堂與聚落在信仰上與結構性的問題。鸞堂有別於一般的地方公廟,若以祭祀圈論述鸞堂與聚落民眾,似乎難以闡述完整, 針對此種在信仰與聚落的論述限制,社會文化空間之概念似乎較能解決本書在鸞堂與聚落互動的相關問題。陳建宏〈公廟與地方社會——以大溪鎮普濟堂為例〉,援引Prasenjit Duara(杜贊奇)的文化權力網絡(cultural nexus of power),以桃園大溪地區的鸞堂作為研究對象,從多項因素討論普濟堂如何從鸞堂變成地方民眾信仰的公廟,臺灣有相當多鸞堂在發展過程中成為地方公廟,其因眾多。就陳建宏認為,普濟堂轉變之因與地方菁英的介入有莫大關係,指出傳統地方菁英參與普濟堂活動,主要以地域及親屬作為關係結合的基礎,但在建廟之時加入了另一批地方菁英,削弱原先鸞生的勢力,導致普濟堂扶鸞活動衰微,鸞堂信仰本質減弱,並以象徵資本概念說明,後來加入的地方菁英其象徵資本多於之前的地方菁英。
此外,汪明怡之碩士論文〈臺南寺廟聯境組織變遷之研究〉也提出異於祭祀圈與社會文化空間的觀點。臺灣至日治以前,無論政治抑或經濟多以府城為中心,其發展過程中並無「村」或「庄」的觀念,則是以「境」來區分地域,汪氏的論文中即是闡述此種概念,清末因臺灣戰備能力不足,而由鄉紳以寺廟為中心團練鄉勇,發展出「聯境」的制度,隨著時代變遷,政權更迭,以致團練鄉勇的本質改變,轉而成為寺廟之間的「交陪」,其中除寺廟間的互動,亦牽涉寺廟與民眾的關係。汪氏在論著中援引Marcel Mauss 的「禮物交換」觀點討論之,以各寺廟間的神明誕辰的「插燭」、建醮系列活動、建醮後的送天師以及四安境的迎「聖爐、聖旗」等活動,論述聯境的變遷與寺廟的交陪。
交換理論主要為原始部落的「庫拉交易圈」及「誇富宴」後續之研究, 係一種屬於經濟人類學的研究觀點,主要論述者為Marcel Mauss,其認為原始社會的禮物交換是一種不含商業性質的相互贈予,且與宗教或巫術有直接關係,在其論著〈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一文中針對不同的交換模式提出「全面報稱體系」,此體系有三項義務,分別為給予、收取以及回報。Mauss 認為義務性的交換與餽贈係維持社會階級秩序與權力關係。無論Mauss 或汪明怡在討論交換理論時,均以禮物等屬物質情況作為論述之要點。汪氏試圖朝向傳統漢人關於「人情」部分進行論述,但最終仍回歸物質,Mauss 認為交換原則重要的係非商業性的互相贈與,且有巫術及宗教的意涵,提供思考在信仰的範疇中是如何進行交換,鳳山鸞堂社會網絡的形成,是否也存在交換的互動。鸞堂的現行研究成果,戰後至今投入研究者不少,有蔡懋棠、鄭喜夫、林永根、林漢章、王世慶、陳兆南、翁聖峰、許玉河等都曾撰文探討鸞堂或善書在臺灣的發展,其中宋光宇、鄭志明、王見川、王志宇、李世偉等人成果豐碩,探討的深度與廣度較為可觀。就戰後鸞堂研究型態的分期,1970至80年代,大致上是信仰內容與善書的介紹;1980至90年代, 則為大量使用日籍文獻資料與清末善書,呈現鸞堂歷史與善書中的內容及其反映之價值觀及與現代社會的互動回應;1990年代迄今研究之面向更為廣泛,舉凡鸞堂人物之生命史、族群性鸞堂均是研究議題,王見川提出未來鸞堂研究的六大面向:「一、鸞堂歷史,二、鸞堂的生態,三、鸞堂的宗教屬性,四、鸞書內容,五、鸞堂崇拜的主神,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互動」。此外,鄭志明更認為鸞堂研究除了著重歷史探析外,亦有其他議題可供未來研究者關注討論,如鸞堂文化的社會意義、社會心理、社會思想、倫理教化、社會控制等,顯示鸞堂宗教體系與社會的緊密結合,甚至鸞堂與當代政治的互動關係,都有被討論的空間。
鸞堂緣起與發展之研究,王世慶依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與鸞書《覺悟選新》所撰文之〈日據初期臺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整理出五種說法論述臺灣鸞堂的分布與系統,且認為扶鸞的傳入與鸞堂設立係順著臺人有吸食鴉片之勢,知識分子為改善當代社會之風氣,進而從扶鸞著手,此種論述難免限縮瞭解鸞堂設立之原因。王志宇的〈從鸞堂到儒宗神教——論鸞堂在臺之發展與傳布〉,從鸞堂設立之因素,歸納了三種類型:1.社區教化型鸞堂;2.戒煙型鸞堂;3.神威顯化型,據其歸納類型,有值得關注之處。鳳山地區鸞堂大多設立於戰後,對「戒煙(戒鴉片)」此項行為,應當式微,甚至已不存在。審視鳳山地區各鸞堂的設立,時間序上是緊密的, 各鸞堂成立肇因,似乎也不太合乎王志宇所提出的三大類型,基於時代及社會環境需求,戒煙成為鸞堂設立的肇因之一,但戰後不得見之,然而社會教化與神威顯化在現今的鸞堂信仰中仍可見得,這是否真為鸞堂設立契因,還是鸞堂發展的型態,值得深究。雖然王治宇論著所田調範圍為中部地區,但對本文欲論述之鳳山地區仍有諸多可以借鏡之處。鸞堂與一般地方公廟不同之處,在於擁有自成一格的信仰儀式,這些儀式皆與「鸞」有密切關聯,多從「扶鸞儀式」延伸。Jordan & Overmyer(焦大衛、歐大年)合著The Flying Phoenix: Aspect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Taiwan,以參與觀察,親身融入鸞堂信仰活動,詳盡記錄各項的儀式,並且對鸞堂信仰者作深度訪談,探討拜鸞活動及儀式在信仰中的意義。另外,鸞堂儀式研究,張家麟亦有論述,〈宗教儀式變遷認同與宗教發展—— 以鸞堂扶鸞活動為焦點〉及〈宗教儀式變遷與當代社會——論臺灣扶鸞儀式的型態及其形成原因〉,前文以問卷分析作為研究方法,透過問卷反映信眾對儀式變遷的接受程度,但過度以量化來論述,對信眾的信仰認同有何種強烈聯結並未有實質論證;後文屬質化研究,以獅頭山勸化堂、宜蘭新民堂與玄門真宗作為儀式變遷的討論對象,分別從鸞文形式、儀式進行及法器作為論述重點,也針對菁英、普羅階層及女性參鸞等議題進行變遷討論。然而這兩篇論著過度闡述儀式的變遷,宣稱儀式變遷有助吸引他人加入,同時在信眾認同度上是偏高的;對年事偏高的鸞堂參與者則堅守儀式之傳統性,張氏認為是習慣問題。因時代需求而儀式有所變遷實可理解, 但對儀式在「變」與「不變」的論述完整度仍有進一步討論之空間。
扶鸞儀式雖為跳脫世俗化的神聖性過程,實質上是為滿足教化功能, 因此鸞書亦成為研究鸞堂重要議題之一。蔡懋棠將臺灣善書之類型分為「新型」與「舊型」兩者,前者指明清以降在臺灣民間重新刊印,後者係指在臺灣各宗教扶鸞而成的鸞書;宋光宇指稱「古典善書」與「現代善書」, 兩人的基本概念是相同的。然善書的研究也僅止於區分其類型,於內容無太多的論述。陳兆南博士論文〈宣講及其唱本之研究〉,對清代的宣講做了詳盡的考察,有助本文從宣講的內容與形式,了解鸞堂的勸善行為。
有關高雄地區鸞堂研究,王見川首開先河,其文〈略論陳中和家族的信仰與勸善活動〉探討陳中和家族在鸞堂的勸善事業,但對陳中和及其家族人員是否為單純的鸞堂信仰者並有說明,文中引述《臺灣日日新報》之報導進行解釋:安瀾宮是苓雅寮地區的信仰中心,陳中和繪在大正七年捐資壹佰陸拾圓,幫助該廟重建。因同善社宣講臺尚未興建,只好先暫借此地宣講。
使人好奇的是陳中和家族,是否僅利用「捐資」的關係,進行商借安瀾宮之空間進行宣講?陳中和是否也積極投身地方公廟或是地方事務,才得以商借此宣講處所?全文中只見身為仕紳階層的陳中和投身於鸞堂勸善之活動,卻未見投入更廣泛的民間信仰相關事務。
目前有關高雄鸞堂發展的研究中,大致被分為福佬鸞堂與客家鸞堂兩大類型進行討論。張有志〈日治時期高雄地區鸞堂之研究〉有別於前人個案型研究的學位論文,雖斷代於日治時期,仍對各區域具代表性的鸞堂有相當討論,文中以福佬及客家作為區隔,並論述高雄地區各鸞堂的發展情況,但範圍甚大,僅能初步指出各鸞堂系譜概況,鳳山地區在日治時期僅有兩座鸞堂(舉善堂與協善堂),而其重要性,文中並無深刻論述,僅說明鳳山地區鸞堂發展佔有一定地位,雖然如此,卻也是該地區鸞堂信仰源起重要的討論資料。此外,對啟明堂、修善堂、意誠堂、善化堂與警化堂等五個福佬鸞堂之間的交流有所探討。李立涵在其碩論〈高雄無極明善天道院的起源與發展〉試圖說明鸞堂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之瓶頸,如何透過「聯造」善書解決困境,文中也從子母堂的關係,闡述意誠堂在早期明善天道院草創及其後發展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另外也點出鳳山地區的鸞堂與之互動關係。張有志與李立涵均指出鸞堂間微妙的互動,與本文欲論述的問題意識不謀而合,但過度將此現象簡單化,張氏強調鸞堂互動係透過人員的交流抑或流動,而李氏「聯造」善書作為鸞務交流的一種機制,上述兩項重點皆是表現鸞堂互動的機制,但都僅止於外在的表現形式,對此也提供思考鸞堂之間的交流是否有著更深層問題所在。對高雄地區扶鸞儀式有較完整研究為林原億之碩士論文〈高雄文化院的扶鸞儀式研究〉,文中詳細記錄了文化院的扶鸞儀式,但基督神學的教育背景,造成分析及論述扶鸞儀式的功能意義時,多以基督教對宗教儀式之觀點作為邏輯思考的前提,實難準確進行信仰的詮釋。鸞堂相關科儀儀式研究,有林金德的碩論〈鳳山鎮南宮仙公廟呂仙祖誕成儀式音樂之研究〉與賴薇如〈左營啟明堂神祇祭典儀式音樂及樂團之研究〉,兩篇論文皆是探討鸞堂在神祇誕辰的儀式與音樂,對高雄地區盛行的「聖樂團」亦有討論,雖然研究對象不同,但鸞堂信仰的本質並無太大之差異。從中檢視兩座鸞堂皆為「廟堂合一」的發展型態,但詳細觀察兩者實屬不同,兩篇研究之成果對科儀的闡述無太多差別,前者研究的鳳山仙公廟係由地方公廟發展中而設立鸞堂,後者則是由鸞堂逐步蛻變成為地方公廟,文中應該對此情況做一討論,可惜此部分的說明鮮少,顯然林氏與賴氏似乎並未發現此問題點,若是以此作為切入點,探討神祇誕辰儀式之架構,應可發現兩座鸞堂及其周邊社會網絡互動情形有無不同。
關於高雄地區福佬系善書及宣講方面之相關研究,目前僅有一篇學位論文。李淑芳碩論〈清代以來臺灣宣講活動發展研究——以高雄地區鸞堂為例〉,以楠梓天后宮、旗山天后宮及鳳邑雙慈亭的「宣講牌」作為動機,從高雄地區眾多鸞堂中,選出各代表三種性質之鸞堂進行討論,可惜較無強烈的論述,基本上其討論仍依循陳兆南對於清代宣講的想法,且用較多的篇幅去探討清代以來的宣講制度與內容,顯現高雄地區鸞堂宣講活動仍有探討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