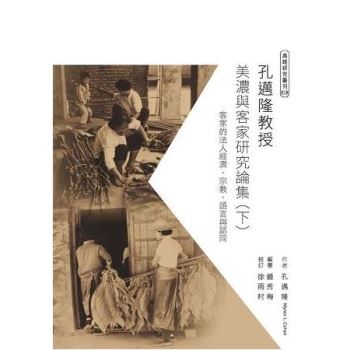清治臺灣瀰濃客家家庭的社經差異研究:從歷史人類學論南臺灣客家社會
Social and Economic Differences Among Minong Families During Qing: An Essay on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a Hakka Com- munity in Southern Taiwan
本論文是關於清治晚期南臺灣客家社會社經差異形式的初步調查成果。同時介紹來自這些資料分析及衍生的研究發現,所進行的更大型研究計畫,這項計畫更廣泛論及瀰濃地區在1895年之前的社會狀況(此地區即現今的臺灣高雄縣美濃鎮,日治之初估計約9,000名人口,而今日約有50,000名人口)。基於本文的論述目標,我援引了非常多樣的資料來呈現社會地位或資產的差異。就在日本佔領瀰濃僅僅數年之後的1902年所辦理的土地調查,使我們能將當時全部的地主依其持有地產大小與價值狀況作排序;1885年由鳳山知縣勒記於石碑的告示「端正風俗碑」,呈現當時從官府及瀰濃社群的角度所見的瀰濃仕紳階層的成員狀態,至少提及他們彼此往來的情形;一座在1890年的石碑載明了重建瀰濃土地公壇的捐題緣金者。姓名(及數額);一座在1894年樹立的捐獻功德碑刻有幾位瀰濃人士的名字,位於今日屏東縣內埔附近的西勢忠義亭,這裡是南臺灣客家社會的其中一個信仰及社群中心。其他補充資料來自多種不同文獻來源、1971至1972年筆者與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教授在美濃協同進行田野工作的紀錄、以及筆者在先前及此後多次造訪美濃的田野紀錄等。功名當然是清治時期社會地位的關鍵指標,也成為我這項研究急欲收集的目標,盡可能蒐集最多的清代瀰濃功名持有者資料。同樣重要的目標就是找出由清朝地方官府正式派任的人士──通常會事先徵詢功名持有者的意見──來綜理瀰濃地區地方日常事務的行政工作,一如在南臺灣其他各地,這些人士稱為「管事」或「經理」。在每個庄都有管事的情況下,在瀰濃各個不同區域的村莊結合起來,成為南臺灣客家地方團練組織「六堆」的其中一堆「右堆」,右堆就如同其他各堆及整個團結的六堆組織一般,具有多個領導職位,其中最重要者是總理及副總理。因此,可將晚清時期石碑所載明的捐獻實錄拿來跟土地資產持有資料相對照,最起碼可提供一項四個面向的分析,從土地產權、功名、正式官職(例如管事及總理),以及捐獻所呈現的地方公共事務參與等方面著手。這項分析的主要缺陷在於,土地調查資料未能完全呈現經濟生活各領域的資產所有權及參與程度,例如店鋪、糖廍及其他類似資產。同時,本分析也存在若干社會學層面的重大缺漏,例如在祖先法人或非祖先性質的擁有地產的宗教法人組織,或是有關灌溉、運輸或地方宗教等重要地方事業之中,具有影響力的正式或非正式職位。然而,我希望能在下文所呈現的可取得資料當中,能確實闡明一個看似悖論的東西,實際的社經階層化,以及依據社群成員最基本生存需求所產生的社群凝聚力,兩者是同時存在的。
晚清瀰濃社會地位排序與仕紳階層特質
在轉向對於前述的資料,特別是著重於經濟政治及社會性質的階層化與差異化進行分析之前(如前所述,依然是初步分析),我也想要描述這些資料來源土地調查
在1895年末,日本政府平定地方抵抗並實質佔領瀰濃地區後,就在1903年完成對現今美濃鎮所有土地的逐筆土地調查,這是全臺地籍大普查的其中一部分。以瀰濃地區而言,此次調查一共記錄並描述了7,243筆地籍。調查目的就是針對當時的土地所有權、相關權利與土地使用情形,無論是依法登記或依習慣法處置的現狀,提供完整詳實的細節。換言之,這項普查所提供的實錄絕大部分是清治時期土地權處置情形,在日本統治的頭七年僅發生極小改變,這項普查本身就是為了便於在日後執行更激烈的土地變革,諸如由日本政府廢止某些所有權與租約。
這些瀰濃土地調查資料已輸入數位資料庫之中。地籍登載事項均以中文輸入以便查認,並與下文提及的其他來源資料進行交互比對,例如日治初期戶籍登記與清治時期的碑文。我曾將這些土地調查資料運用在一篇正式出版論文(Cohen, 1993)以及另一篇論文,刊載在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同事所編輯的書籍當中(Cohen, 1999)。地籍資料是以土地利用方式來區分歸類(按照水田、旱田、住宅與其他建地等類別)。土地所有權屬與權利設定均有載列:有許多田地具有各自的「大租」(田底)與「小租」(田面)擁有者;此外,所有權也經常「典」給他人,以至於單單一筆土地就具有為數可觀的個人或法人共同持有者,他們可能擁有某一種或其他類型的權利或主張。值得一提的是,對於某一處特定土地擁有所有權的各方,都是依據人名與住所來鑑別。許多共同持分的所有者或權利持有者並非個人,而是各種不同形態的法人組織:包括宗教組織(神佛會)、祖先祭祀組織(嘗、祭祀公業)及其他更緊密聚焦於社會公益事業的組織,例如橋會。
Social and Economic Differences Among Minong Families During Qing: An Essay on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a Hakka Com- munity in Southern Taiwan
本論文是關於清治晚期南臺灣客家社會社經差異形式的初步調查成果。同時介紹來自這些資料分析及衍生的研究發現,所進行的更大型研究計畫,這項計畫更廣泛論及瀰濃地區在1895年之前的社會狀況(此地區即現今的臺灣高雄縣美濃鎮,日治之初估計約9,000名人口,而今日約有50,000名人口)。基於本文的論述目標,我援引了非常多樣的資料來呈現社會地位或資產的差異。就在日本佔領瀰濃僅僅數年之後的1902年所辦理的土地調查,使我們能將當時全部的地主依其持有地產大小與價值狀況作排序;1885年由鳳山知縣勒記於石碑的告示「端正風俗碑」,呈現當時從官府及瀰濃社群的角度所見的瀰濃仕紳階層的成員狀態,至少提及他們彼此往來的情形;一座在1890年的石碑載明了重建瀰濃土地公壇的捐題緣金者。姓名(及數額);一座在1894年樹立的捐獻功德碑刻有幾位瀰濃人士的名字,位於今日屏東縣內埔附近的西勢忠義亭,這裡是南臺灣客家社會的其中一個信仰及社群中心。其他補充資料來自多種不同文獻來源、1971至1972年筆者與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教授在美濃協同進行田野工作的紀錄、以及筆者在先前及此後多次造訪美濃的田野紀錄等。功名當然是清治時期社會地位的關鍵指標,也成為我這項研究急欲收集的目標,盡可能蒐集最多的清代瀰濃功名持有者資料。同樣重要的目標就是找出由清朝地方官府正式派任的人士──通常會事先徵詢功名持有者的意見──來綜理瀰濃地區地方日常事務的行政工作,一如在南臺灣其他各地,這些人士稱為「管事」或「經理」。在每個庄都有管事的情況下,在瀰濃各個不同區域的村莊結合起來,成為南臺灣客家地方團練組織「六堆」的其中一堆「右堆」,右堆就如同其他各堆及整個團結的六堆組織一般,具有多個領導職位,其中最重要者是總理及副總理。因此,可將晚清時期石碑所載明的捐獻實錄拿來跟土地資產持有資料相對照,最起碼可提供一項四個面向的分析,從土地產權、功名、正式官職(例如管事及總理),以及捐獻所呈現的地方公共事務參與等方面著手。這項分析的主要缺陷在於,土地調查資料未能完全呈現經濟生活各領域的資產所有權及參與程度,例如店鋪、糖廍及其他類似資產。同時,本分析也存在若干社會學層面的重大缺漏,例如在祖先法人或非祖先性質的擁有地產的宗教法人組織,或是有關灌溉、運輸或地方宗教等重要地方事業之中,具有影響力的正式或非正式職位。然而,我希望能在下文所呈現的可取得資料當中,能確實闡明一個看似悖論的東西,實際的社經階層化,以及依據社群成員最基本生存需求所產生的社群凝聚力,兩者是同時存在的。
晚清瀰濃社會地位排序與仕紳階層特質
在轉向對於前述的資料,特別是著重於經濟政治及社會性質的階層化與差異化進行分析之前(如前所述,依然是初步分析),我也想要描述這些資料來源土地調查
在1895年末,日本政府平定地方抵抗並實質佔領瀰濃地區後,就在1903年完成對現今美濃鎮所有土地的逐筆土地調查,這是全臺地籍大普查的其中一部分。以瀰濃地區而言,此次調查一共記錄並描述了7,243筆地籍。調查目的就是針對當時的土地所有權、相關權利與土地使用情形,無論是依法登記或依習慣法處置的現狀,提供完整詳實的細節。換言之,這項普查所提供的實錄絕大部分是清治時期土地權處置情形,在日本統治的頭七年僅發生極小改變,這項普查本身就是為了便於在日後執行更激烈的土地變革,諸如由日本政府廢止某些所有權與租約。
這些瀰濃土地調查資料已輸入數位資料庫之中。地籍登載事項均以中文輸入以便查認,並與下文提及的其他來源資料進行交互比對,例如日治初期戶籍登記與清治時期的碑文。我曾將這些土地調查資料運用在一篇正式出版論文(Cohen, 1993)以及另一篇論文,刊載在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同事所編輯的書籍當中(Cohen, 1999)。地籍資料是以土地利用方式來區分歸類(按照水田、旱田、住宅與其他建地等類別)。土地所有權屬與權利設定均有載列:有許多田地具有各自的「大租」(田底)與「小租」(田面)擁有者;此外,所有權也經常「典」給他人,以至於單單一筆土地就具有為數可觀的個人或法人共同持有者,他們可能擁有某一種或其他類型的權利或主張。值得一提的是,對於某一處特定土地擁有所有權的各方,都是依據人名與住所來鑑別。許多共同持分的所有者或權利持有者並非個人,而是各種不同形態的法人組織:包括宗教組織(神佛會)、祖先祭祀組織(嘗、祭祀公業)及其他更緊密聚焦於社會公益事業的組織,例如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