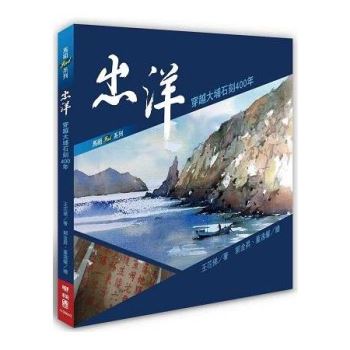「刺桐港為世界最大港之一。竟可謂是世界極大之海港,我在港中見大舶約有百艘,小舶不能數計。是為一大海灣,伸入陸地與大河連接。」這是元朝回教徒伊賓‧拔都達(Ibn Battuta)在中國遊記裡描述閩南泉州港的景象。
亞洲季風帶,自古以來就受季節風向轉換的影響,季風成為海上帆船的動力來源;因此,宋、元時期泉州地方官和市舶司,每年四月、十一月都要舉行祈風儀式,祝禱神明保佑來往的船隻順風平浪,今日泉州九日山還保留大批的祈風石刻,見證海上貿易的興盛。
北宋時期官府在泉州設市舶提舉司,採取鼓勵政策與合理稅收方式,招攬亞洲沿海國家與地區,前來朝貢或貿易。由於福建沿海一帶,谷灣式地形特別發達,島嶼灣澳綿延不絕,天然港灣眾多,泉州灣得天獨厚的優勢,逐漸形成東方的國際大港,海上絲路的輻輳地。自宋元以來,興起一批又一批的海商階層,他們具有冒險犯難的精神,順著亞洲季風帶既有的路徑,從東亞到東南亞,延伸至印度與阿拉伯半島,連結成世界最大的貿易圈與互市的網絡,沿線的港市紛紛崛起,隨處看到泉州與阿拉伯商人的蹤影。
「百貨隨潮船入市,萬家沽酒戶垂簾。蒼煙巷陌青榕老,白露園林紫蔗甜。」北宋‧龍昌期在〈三山即事〉詩裡描述福州的繁華景象。
福州位在江海的漕運樞紐,是福建另一座重要大港。北宋時期,福州太守蔡襄目睹港內「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三山志》記載「官造舟,率就河口彌勒院之旁」,宋朝在福州設有造船廠,打造出大「福船」,能夠破浪遠航於朝鮮半島與阿拉伯半島之間海域,得力於福州、泉州一帶造船工藝的蓬勃發展,能製造出來尖底多桅與水密隔艙的貿易帆船。而且羅盤導航技術與量天尺的定位技術,開始應用於航海,發展出一套全天候的「針路」,有了航海技術與造船工藝,穿梭洋面如履平地。
富饒的閩江流域,號稱福建的母親河,不僅孕育了福州港周邊的城市與腹地,千年以來更執掌福建省的政治與文化的中樞地位。相對於閩江口外的馬祖列島,戰略地位也跟著水漲船高,視為拱衛省城福州的前沿島嶼,總計36座島嶼和險礁星羅棋布於東海,自古以來即標示在針路上,成為東亞航線上的航標。
有人形容馬祖列島是「上天撒落在閩江口外的一串珍珠」,就地理位置來說確實如此,沿海岸線躍島北上,抵達浙江的舟山群島,向南逐島通過平潭列島、南日島到達泉州灣; 向東南隨著夏季季風,繞過北台灣頭基隆,順著風航向琉球群島。
這串珍珠最為明亮的一顆,就是東沙島(即今東莒島)。不同年代散發著不同的光芒,留下不同的歷史遺跡,可說是馬祖列島的「時間的膠囊,海洋的據點」。面積小到不足3平方公里的小島,由於地理位置的優越,位處於閩江口南側,是船隻出閩江口候風開洋的泊地,航海圖冊的座標,不僅有一席之地,更是遠古人類海洋活動的重要據點。
距今6000年的史前熾坪隴遺址,大量發現新石器時代的採集工具,以及夾砂繩紋陶,證實他們在這裡過著海洋生活; 另一處是福正村蔡園裡遺址,定位為「宋元時期歷史遺址」(距今1270年),透過出土的瓷器殘片,找到跟季風貿易有密切關聯的線索,比對窯系,遍及福建著名的德化窯、建窯、懷安窯、閩清窯、浦口窯、曾竹山窯、漳州窯……等窯藝,並擴及浙江的龍泉窯與越窯。這些出土的瓷片,不乏是外銷海外的壓艙貨,例如: 福州近郊的懷安窯,曾在唐末外銷到印尼、泰國、日本九州等地; 連江的浦口窯,主要生產青白瓷,曾在宋元時期外銷到日本和東南亞。
從東沙島的遺址,我們見識到東亞貿易圈的網絡,將中國的瓷器透過中西海上交通與貿易的交流,深深影響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同樣說明歷史上重要的海上事件,這座島未曾缺席過,包含400年前沈有容將軍征倭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