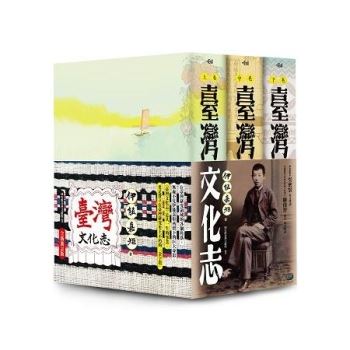導讀(一)
伊能嘉矩的臺灣研究及其當代意義
文╱吳密察(國史館館長)
伊能嘉矩來到臺灣之後,隨即於臺北附近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並將他的調查結果,幾乎是以每個月一回的頻率以「臺灣通信」的題目發表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這個「臺灣通信」專欄,目前可以確認的有二十八回,連載時間從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到一八九九年一月,長達三年又兩個月。「臺灣通信」的內容絕大部分是伊能嘉矩在臺北近郊及臺灣東北角基隆、宜蘭一帶的田野調查所得。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匯報了田代安定這類人類學同好的調查所得。
此時伊能嘉矩的田野調查特別集中於非漢人的「熟番」。「熟番」是清帝國管治之下的臺灣原住民,相對於「熟番」,清帝國將非管治區內的臺灣原住民稱為「生番」。
因此,「熟番」、「生番」未必是民族的區分,而是清帝國的「身分」區分。
一般來說,「熟番」居住於平原地區,也成為漢民族移入後首先邂逅的原住民,因此受到漢民族的壓迫、固有文化的流失也相對嚴重,到了十九世紀末已經大幅度地流失了他們的土地,也流失了包括語言、習俗等傳統文化。十九世紀八○年代來到臺灣的西洋傳教士,便經常感嘆這些Formosan(傳教士的紀錄裡這樣稱呼這些人;相對地,以Chinese稱呼漢人)的悲慘境遇。也就是說,伊能嘉矩在這些臺灣平原地區的原住民族之黃昏年代,來到了臺灣並為他們做出了珍貴的調查紀錄。
伊能嘉矩雖然有志於人類學調查,但他在臺的正式身分是總督府雇員,因此不可能長時間地赴田野做實地調查。目前可以確認的,伊能嘉矩有五次時間比較集中而長期的田野調查,大多是帶著總督府的任務而進行的。這五次田調查分別是:
(1)一八九六年七月至一八九七年四月間,斷續地在臺灣北部進行平埔調查。
(2)一八九六年十月起在宜蘭進行調查,總共二十四日。
(3)一八九七年五月至十一月,進行臺灣全島的原住民調查,總共一百九十二日。
(4)一九○○年七月至九月,在臺灣南部做原住民調查。
(5)一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一年一月,在澎湖島進行調查。
(1)、(2)的調查成果,伊能嘉矩將它們刊載於《東京人類學雜誌》,也就是前述的「臺灣通信」的大部分。(3)伊能嘉矩留下來了名為《巡臺日乘》的日記。(4)伊能嘉矩留下來了名為《南遊日乘》的調查日記。(5)伊能嘉矩留下來了名為《澎湖踏查》的調查日記。
伊能嘉矩於一八九七年五月至十一月應總督府學務部的指派,與粟野傳之丞進行了「蕃人教育設施準備ニ關スル調查」,日程總計一百九十二日,幾乎環繞臺灣島一周。
此次調查伊能嘉矩留下來了調查日記《巡臺日乘》,並在調查之後於一八九九年一月提出復命書。這個向總督府提出的復命書原本,目前並未能得見,但在大約一年之後的一九○○年三月,伊能嘉矩在此次調查復命書的基礎上參照傳統的漢文史料加以補充,出版了臺灣人類學史上的經典著作《臺灣蕃人事情》。
一八九七年這次長達半年的臺灣全島巡迴踏查,應該是伊能嘉矩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人類學田野調查,也奠定了他總體的臺灣原住民知識體系。一八九八年起,他陸續發表了幾篇可以算是他對於臺灣原住民知識的概括性重要文章,並且因為臺灣總督府行政改革的原因,他暫時解除了總督府的職位而於該年十二月回到了日本內地。回到日本內地的伊能嘉矩,接受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人類學教室委託擔任將在法國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臺灣の番人」展示的企劃人。同時他也利用此機會,在坪井教授主持的東京私立史學館進修人類學。在東京的期間,伊能嘉矩以他在此之前的臺灣田野調查配合他的人類學知識,構思了他龐大的研究體系。除此之外,他也在東京出版了《臺灣在世界中的位置》。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將一八九七年全島調查的復命書,參照傳統的漢文史料加以補充,而於一九○○年出版了上述的名著《臺灣蕃人事情》。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伊能嘉矩在回去日本一年之後,再度來到臺灣。這次伊能嘉矩是以總督府文書課兼殖產課雇員的身分,再度任職於總督府。此時總督府派給伊能嘉矩的幾項與調查有關的任務是調查基隆外海的無人小島彭佳嶼、赴臺南蒐集編纂地理、歷史教科書的資料、出差赴澎湖島。這些調查的目的,顯然與伊能嘉矩夙來的臺灣原住民人類學調查不同,其調查對象也轉向漢人社會和歷史。原本有志於成為人類學者的伊能嘉矩,就因為總督府給予的任務轉而向成為歷史學者的方向傾斜了。伊能嘉矩此時已經是公認的臺灣原住民與臺灣歷史的專家,因此一九○三年大阪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的臺灣館展示,就由他企劃。他在這個展覽中將臺灣原住民做了一個可視性的種族展示。
一九○四年伊能嘉矩出版了清帝國理番史的巨著《臺灣蕃政志》。這部著作可以說是伊能嘉矩在當時的平埔族人類學調查之基礎上,回溯梳理清帝國二百年來的熟蕃統治史,是關於臺灣理蕃史的開山之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一九○四年,伊能嘉矩改任總督府警察本署囑託。當時是總督府已經掌握了臺灣平原地區的治安,逐漸往山地,也就是「生蕃」的生息地域進出的時代。警察本署則是山地、蕃人統治的專責機關。伊能嘉矩此時的工作是被委託編纂《理番沿革誌》,其成果即為後來於一九一一年出版的《臺灣總督府理蕃誌稿 第一編》。
此書將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年的十五年間,總督府的理蕃施政做了編年體的記述。即使到了今日,此書都還是此一領域的入門必讀書。
其後,伊能嘉矩斷斷續續地擔任總督府文書課、蕃務課,或者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囑託,但其在臺灣之時間也相對地減少了。甚至一九○七年十月接受總督府警察本署之囑託職務時,已經註明「在鄉勤務」,也就是並不需居住臺灣工作,顯示伊能嘉矩已經將其生活場所,移轉回日本內地了。一九○八年二月,伊能回到了故鄉遠野。
以後只有幾次短期渡臺的機會。回到鄉里遠野的伊能嘉矩,於一九○八年五月獲得坪井教授的推薦,參與吉田東伍博士主持的《大日本地名辭書》臺灣篇的撰寫工作。伊能嘉矩透過這個機會,將他歷年來所蒐集的龐大史料根據地名加以分別彙編,於一九○九年二月完成了一部以地名為索引的臺灣各地的地方史。一九○九年二月,伊能嘉矩致書曾經擔任臺灣總督的乃木希典學習院院長,表示自己正在編寫《臺灣全志》。一九二二年,臺灣總督府設立史料編纂委員會,企圖以三年為期調查臺灣史料、編纂臺灣史,伊能嘉矩也被敦聘為委員。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伊能嘉矩結束了他的一生,留下了一部多達五十四冊的《臺灣全史》遺稿。這份遺稿應該就是他應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委託所執筆的成果之一。後來這份遺稿在其故舊、門生奔走之下,於一九二八年出版為《臺灣文化志》。日本學者福田德三在此書出版之際所寫的序文,推賞這部《臺灣文化志》在某意義上,就是一部關於清代臺灣史的文化性百科全書(cyclopedia)、年鑑(almanac),也是檔案(archive)。
導讀(二)
《臺灣文化志》的形成史與接受史
文╱陳偉智(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本書審訂者)
《臺灣文化志》的臺灣歷史敘述主軸,大致上延續著伊能從來臺之初在「臺灣雜俎」讀史筆記開始,經歷《臺灣在世界中的位置》,到一九○二年出版的《臺灣志》中逐漸形成的臺灣歷史發展知識。其主要的內容構成,在先前的人類學與歷史學研究的專著與期刊論文上的臺灣民族誌、歷史書寫、人物傳、民俗等研究成果,依據個別章節主題加以反覆加筆修改。整體來看,在《臺灣文化志》中如同柳田國男與楊雲萍等人都注意到伊能的人類學知識背景與方法影響了其歷史寫作的問題意識。而這樣的問題意識,也使伊能嘉矩從「臺灣人類學」到「臺灣全志」到《臺灣文化志》,以三十年的時間,完成整合了多重空間尺度、多元族群競爭互動、自然與人文地理、集團與個人、制度、習俗與風氣等具有整體性的臺灣歷史民族誌的知識建構。伊能的《臺灣文化志》當然也有其時代的限制乃致史料誤讀等問題。例如伊能特別強調歷史上臺灣由其他國家帶來的「有秩序的政治」,而即便臺灣在清朝政府統治下的兩百年間,也是處於非近代政治體制下的狀態。這些觀點都直接導向日本統治的必然性與必要性,除了是因為日本國家擴張所獲得新領土之外,更是內在於臺灣歷史的發展脈絡。換言之,缺乏近代政治主體(即近代國家)的臺灣,使日本的殖民統治具有了正當性。同時在個別的章節中,也有不少是因為史料解讀問題而產生的,在後來引發不少辯論的解釋,例如文獻紀錄中的「琉球」是否即為臺灣,或者對於清初渡臺禁令與臺灣閩粵族群地理分布的說法,甚至是將文獻中十八世紀末宜蘭開發的拓墾社會組織的「蘭人結首制」的「蘭人」,誤解為「荷蘭」時代的社會制度的時代錯置等問題。在後來的臺灣史研究中,也一一被批評修正。
一九四八年,歷史學者楊雲萍在《公論報》的「臺灣風土」副刊專欄中,發表了一篇〈臺灣的研究〉。楊雲萍在文章中指出:「『臺灣的研究』,曾有過許多的燦爛的歷史,黃叔璥、連雅堂、伊能嘉矩、Wm. Campbell、Ludwig Riess、J. W. Davidson,及其他諸氏的業績,確值得後學的我們的欽仰和感謝。」最後並說:「我們要前進!」同時,楊雲萍在同一報紙上也發表了〈《臺灣文化志》的著者〉,介紹伊能嘉矩的生平與業績,以及在「臺灣風土」發行第五十期時,將戰前發表的〈臺灣研究必讀十書〉再度發表。《公論報》的「臺灣風土」也陸續發表由人類學家陳奇祿與歷史學家劉枝萬翻譯的伊能嘉矩論文。楊雲萍提到的「我們要前進」,在戰後初期,就以翻譯伊能嘉矩的方式登場。戰後臺灣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更在一九五○年代成為中華民國的全部,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展開了「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文化與意識型態改造的工程。
「臺灣研究」成為臺灣一地的地方史的研究。而這樣的地方史研究,其機構上的制度形式,則是戰後成立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以及各縣市政府的文獻委員會。各地方文獻委員會基於修地方志的或是鄉土史的需要,將日治時期的臺灣研究成果翻譯成中文,作為修地方志的參考。在這樣的戰後臺灣的歷史知識生產狀況中,由各級文獻委員會,翻譯了部分伊能嘉矩的臺灣研究成果。其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在一九五○年代,出版了「臺灣叢書」,其中《臺灣番政志》則是以翻譯伊能嘉矩的《臺灣蕃政志》為主,並取材伊能的《臺灣文化志》、《理蕃誌稿》等文獻。到了一九七○年代,更進一步翻譯《臺灣文化志》一部分內容,登載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刊物《臺灣文獻》上。而後於一九八五年開始到一九九一年,將全本《臺灣文化志》三冊翻譯出版,同書於一九九七年再版,於二○一一年出版修訂版,並於二○一七年出版全新審訂版。
戰後伊能嘉矩在臺灣以「翻譯」的型態存在,也受到了當時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
社會上一方面有要求臺灣史知識的需求,另一方面有民族主義的歷史知識過濾器,使得伊能的臺灣研究在戰後臺灣透過翻譯的繼受,產生了一些影響。例如在一九八五年臺灣省文獻會出版《臺灣文化志》中譯本時,就曾在〈序言〉中提醒讀者:「近年來,國人對於臺灣歷史之研究與考證,興趣愈來愈濃,有關著述、期刊、等等發行愈來愈多,各大專院校開課討論者,亦所在多有,要求本會提供資料者紛至沓來,無時無之,確是可喜的現象。……本書之原著者為日人,由於民族觀點之不同,立論或有所異,但參考價值仍多,願國人於引用時,酌加考慮!」更在〈譯例〉中提到:「一、日人伊能嘉矩著《臺灣文化志》向為臺灣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料,著者以日人談臺事,間或立場偏頗及史實訛誤,亦不在少數,譯本萬非不得已,蓋照原文譯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或許是為了使中譯本能順利出版才蛇足地多了這些說明,不過從這裡也可以看到戰後作為官方意識型態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成果在重新出版時的政治干擾與影響。二○一一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前身即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修訂版《臺灣文化志》時,原序文仍保留,但已經將「譯例」撤除。
由於對臺灣歷史知識的社會需求一直存在,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伊能嘉矩就如同臺灣省文獻會所言的,以雖然「民族觀點之不同,立論或有所異,但參考價值仍多」的方式被閱讀,伊能嘉矩在戰後除了以被翻譯的方式繼續留在臺灣,其主要作品也陸續被複印出版。例如一九六五年,臺北古亭書屋翻印了伊能的《臺灣文化志》,一九七三年翻印了《臺灣蕃政志》與《臺灣志》。一九八五年成文出版社,也複印了伊能的《臺灣志》、《臺灣年表》以及《領臺十年史》。一九八九年,南天書局翻印出版了《臺灣舊地名辭典》(原為《大日本地名辭典 臺灣篇》),一九九四年翻印出版了《臺灣文化誌》(原《臺灣文化志》),以及一九九五年的《理蕃誌稿》等。
有不少學者曾批評,戰後臺灣的臺灣歷史研究過度使用日治時期日本學者的成果與素材。伊能嘉矩的作品也曾存在著一種被「過度引用」的現象。伊能以其著作的豐富與涵蓋的全面性,成為研究者們所必須參考的成果,但其中有不少不假思索即直接引用伊能陳說的狀況。這樣的現象,反過來也說明了戰後臺灣在很長的時間內,曾經有過的臺灣歷史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方式。透過翻譯與翻印的形式,伊能嘉矩繼續在戰後臺灣發揮影響力,存續於學院與地方文史社群中。一九八○年代臺灣解嚴,逐漸邁向民主化,社會上臺灣歷史知識的需求,使得臺灣史獲得了市民權,同時臺灣研究也成為新興中的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象徵資源。一九九○年代伊能嘉矩重新回到臺灣,其田野日記等新的材料出版,獲得廣大的讀者群。伊能嘉矩的收藏資料與手稿,在此時已由大學研究機構整理與數位化,重建其完整性,研究者也開始透過伊能嘉矩討論新的歷史議題。
此次《臺灣文化志》的全新審訂版,原則上恢復伊能原來的用語與觀點,也保留了伊能的史觀,乃至其史料誤讀的部分。民主化之後的臺灣,已經累積了不少的臺灣研究成果,各種史觀的論辯也有充分表達自由,專業的歷史學家與業餘的文史愛好者,應該已具備了批判性閱讀伊能嘉矩及其《臺灣文化志》的識讀能力。
《臺灣文化志》作為臺灣研究的經典作品,其存在的意義除了是史學史意義上的重要先行成果,更在於後來的讀者們對其不斷地批判性超越。
伊能嘉矩的臺灣研究及其當代意義
文╱吳密察(國史館館長)
伊能嘉矩來到臺灣之後,隨即於臺北附近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並將他的調查結果,幾乎是以每個月一回的頻率以「臺灣通信」的題目發表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這個「臺灣通信」專欄,目前可以確認的有二十八回,連載時間從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到一八九九年一月,長達三年又兩個月。「臺灣通信」的內容絕大部分是伊能嘉矩在臺北近郊及臺灣東北角基隆、宜蘭一帶的田野調查所得。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匯報了田代安定這類人類學同好的調查所得。
此時伊能嘉矩的田野調查特別集中於非漢人的「熟番」。「熟番」是清帝國管治之下的臺灣原住民,相對於「熟番」,清帝國將非管治區內的臺灣原住民稱為「生番」。
因此,「熟番」、「生番」未必是民族的區分,而是清帝國的「身分」區分。
一般來說,「熟番」居住於平原地區,也成為漢民族移入後首先邂逅的原住民,因此受到漢民族的壓迫、固有文化的流失也相對嚴重,到了十九世紀末已經大幅度地流失了他們的土地,也流失了包括語言、習俗等傳統文化。十九世紀八○年代來到臺灣的西洋傳教士,便經常感嘆這些Formosan(傳教士的紀錄裡這樣稱呼這些人;相對地,以Chinese稱呼漢人)的悲慘境遇。也就是說,伊能嘉矩在這些臺灣平原地區的原住民族之黃昏年代,來到了臺灣並為他們做出了珍貴的調查紀錄。
伊能嘉矩雖然有志於人類學調查,但他在臺的正式身分是總督府雇員,因此不可能長時間地赴田野做實地調查。目前可以確認的,伊能嘉矩有五次時間比較集中而長期的田野調查,大多是帶著總督府的任務而進行的。這五次田調查分別是:
(1)一八九六年七月至一八九七年四月間,斷續地在臺灣北部進行平埔調查。
(2)一八九六年十月起在宜蘭進行調查,總共二十四日。
(3)一八九七年五月至十一月,進行臺灣全島的原住民調查,總共一百九十二日。
(4)一九○○年七月至九月,在臺灣南部做原住民調查。
(5)一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一年一月,在澎湖島進行調查。
(1)、(2)的調查成果,伊能嘉矩將它們刊載於《東京人類學雜誌》,也就是前述的「臺灣通信」的大部分。(3)伊能嘉矩留下來了名為《巡臺日乘》的日記。(4)伊能嘉矩留下來了名為《南遊日乘》的調查日記。(5)伊能嘉矩留下來了名為《澎湖踏查》的調查日記。
伊能嘉矩於一八九七年五月至十一月應總督府學務部的指派,與粟野傳之丞進行了「蕃人教育設施準備ニ關スル調查」,日程總計一百九十二日,幾乎環繞臺灣島一周。
此次調查伊能嘉矩留下來了調查日記《巡臺日乘》,並在調查之後於一八九九年一月提出復命書。這個向總督府提出的復命書原本,目前並未能得見,但在大約一年之後的一九○○年三月,伊能嘉矩在此次調查復命書的基礎上參照傳統的漢文史料加以補充,出版了臺灣人類學史上的經典著作《臺灣蕃人事情》。
一八九七年這次長達半年的臺灣全島巡迴踏查,應該是伊能嘉矩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人類學田野調查,也奠定了他總體的臺灣原住民知識體系。一八九八年起,他陸續發表了幾篇可以算是他對於臺灣原住民知識的概括性重要文章,並且因為臺灣總督府行政改革的原因,他暫時解除了總督府的職位而於該年十二月回到了日本內地。回到日本內地的伊能嘉矩,接受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人類學教室委託擔任將在法國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臺灣の番人」展示的企劃人。同時他也利用此機會,在坪井教授主持的東京私立史學館進修人類學。在東京的期間,伊能嘉矩以他在此之前的臺灣田野調查配合他的人類學知識,構思了他龐大的研究體系。除此之外,他也在東京出版了《臺灣在世界中的位置》。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將一八九七年全島調查的復命書,參照傳統的漢文史料加以補充,而於一九○○年出版了上述的名著《臺灣蕃人事情》。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伊能嘉矩在回去日本一年之後,再度來到臺灣。這次伊能嘉矩是以總督府文書課兼殖產課雇員的身分,再度任職於總督府。此時總督府派給伊能嘉矩的幾項與調查有關的任務是調查基隆外海的無人小島彭佳嶼、赴臺南蒐集編纂地理、歷史教科書的資料、出差赴澎湖島。這些調查的目的,顯然與伊能嘉矩夙來的臺灣原住民人類學調查不同,其調查對象也轉向漢人社會和歷史。原本有志於成為人類學者的伊能嘉矩,就因為總督府給予的任務轉而向成為歷史學者的方向傾斜了。伊能嘉矩此時已經是公認的臺灣原住民與臺灣歷史的專家,因此一九○三年大阪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的臺灣館展示,就由他企劃。他在這個展覽中將臺灣原住民做了一個可視性的種族展示。
一九○四年伊能嘉矩出版了清帝國理番史的巨著《臺灣蕃政志》。這部著作可以說是伊能嘉矩在當時的平埔族人類學調查之基礎上,回溯梳理清帝國二百年來的熟蕃統治史,是關於臺灣理蕃史的開山之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一九○四年,伊能嘉矩改任總督府警察本署囑託。當時是總督府已經掌握了臺灣平原地區的治安,逐漸往山地,也就是「生蕃」的生息地域進出的時代。警察本署則是山地、蕃人統治的專責機關。伊能嘉矩此時的工作是被委託編纂《理番沿革誌》,其成果即為後來於一九一一年出版的《臺灣總督府理蕃誌稿 第一編》。
此書將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年的十五年間,總督府的理蕃施政做了編年體的記述。即使到了今日,此書都還是此一領域的入門必讀書。
其後,伊能嘉矩斷斷續續地擔任總督府文書課、蕃務課,或者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囑託,但其在臺灣之時間也相對地減少了。甚至一九○七年十月接受總督府警察本署之囑託職務時,已經註明「在鄉勤務」,也就是並不需居住臺灣工作,顯示伊能嘉矩已經將其生活場所,移轉回日本內地了。一九○八年二月,伊能回到了故鄉遠野。
以後只有幾次短期渡臺的機會。回到鄉里遠野的伊能嘉矩,於一九○八年五月獲得坪井教授的推薦,參與吉田東伍博士主持的《大日本地名辭書》臺灣篇的撰寫工作。伊能嘉矩透過這個機會,將他歷年來所蒐集的龐大史料根據地名加以分別彙編,於一九○九年二月完成了一部以地名為索引的臺灣各地的地方史。一九○九年二月,伊能嘉矩致書曾經擔任臺灣總督的乃木希典學習院院長,表示自己正在編寫《臺灣全志》。一九二二年,臺灣總督府設立史料編纂委員會,企圖以三年為期調查臺灣史料、編纂臺灣史,伊能嘉矩也被敦聘為委員。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伊能嘉矩結束了他的一生,留下了一部多達五十四冊的《臺灣全史》遺稿。這份遺稿應該就是他應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委託所執筆的成果之一。後來這份遺稿在其故舊、門生奔走之下,於一九二八年出版為《臺灣文化志》。日本學者福田德三在此書出版之際所寫的序文,推賞這部《臺灣文化志》在某意義上,就是一部關於清代臺灣史的文化性百科全書(cyclopedia)、年鑑(almanac),也是檔案(archive)。
導讀(二)
《臺灣文化志》的形成史與接受史
文╱陳偉智(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本書審訂者)
《臺灣文化志》的臺灣歷史敘述主軸,大致上延續著伊能從來臺之初在「臺灣雜俎」讀史筆記開始,經歷《臺灣在世界中的位置》,到一九○二年出版的《臺灣志》中逐漸形成的臺灣歷史發展知識。其主要的內容構成,在先前的人類學與歷史學研究的專著與期刊論文上的臺灣民族誌、歷史書寫、人物傳、民俗等研究成果,依據個別章節主題加以反覆加筆修改。整體來看,在《臺灣文化志》中如同柳田國男與楊雲萍等人都注意到伊能的人類學知識背景與方法影響了其歷史寫作的問題意識。而這樣的問題意識,也使伊能嘉矩從「臺灣人類學」到「臺灣全志」到《臺灣文化志》,以三十年的時間,完成整合了多重空間尺度、多元族群競爭互動、自然與人文地理、集團與個人、制度、習俗與風氣等具有整體性的臺灣歷史民族誌的知識建構。伊能的《臺灣文化志》當然也有其時代的限制乃致史料誤讀等問題。例如伊能特別強調歷史上臺灣由其他國家帶來的「有秩序的政治」,而即便臺灣在清朝政府統治下的兩百年間,也是處於非近代政治體制下的狀態。這些觀點都直接導向日本統治的必然性與必要性,除了是因為日本國家擴張所獲得新領土之外,更是內在於臺灣歷史的發展脈絡。換言之,缺乏近代政治主體(即近代國家)的臺灣,使日本的殖民統治具有了正當性。同時在個別的章節中,也有不少是因為史料解讀問題而產生的,在後來引發不少辯論的解釋,例如文獻紀錄中的「琉球」是否即為臺灣,或者對於清初渡臺禁令與臺灣閩粵族群地理分布的說法,甚至是將文獻中十八世紀末宜蘭開發的拓墾社會組織的「蘭人結首制」的「蘭人」,誤解為「荷蘭」時代的社會制度的時代錯置等問題。在後來的臺灣史研究中,也一一被批評修正。
一九四八年,歷史學者楊雲萍在《公論報》的「臺灣風土」副刊專欄中,發表了一篇〈臺灣的研究〉。楊雲萍在文章中指出:「『臺灣的研究』,曾有過許多的燦爛的歷史,黃叔璥、連雅堂、伊能嘉矩、Wm. Campbell、Ludwig Riess、J. W. Davidson,及其他諸氏的業績,確值得後學的我們的欽仰和感謝。」最後並說:「我們要前進!」同時,楊雲萍在同一報紙上也發表了〈《臺灣文化志》的著者〉,介紹伊能嘉矩的生平與業績,以及在「臺灣風土」發行第五十期時,將戰前發表的〈臺灣研究必讀十書〉再度發表。《公論報》的「臺灣風土」也陸續發表由人類學家陳奇祿與歷史學家劉枝萬翻譯的伊能嘉矩論文。楊雲萍提到的「我們要前進」,在戰後初期,就以翻譯伊能嘉矩的方式登場。戰後臺灣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更在一九五○年代成為中華民國的全部,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展開了「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文化與意識型態改造的工程。
「臺灣研究」成為臺灣一地的地方史的研究。而這樣的地方史研究,其機構上的制度形式,則是戰後成立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以及各縣市政府的文獻委員會。各地方文獻委員會基於修地方志的或是鄉土史的需要,將日治時期的臺灣研究成果翻譯成中文,作為修地方志的參考。在這樣的戰後臺灣的歷史知識生產狀況中,由各級文獻委員會,翻譯了部分伊能嘉矩的臺灣研究成果。其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在一九五○年代,出版了「臺灣叢書」,其中《臺灣番政志》則是以翻譯伊能嘉矩的《臺灣蕃政志》為主,並取材伊能的《臺灣文化志》、《理蕃誌稿》等文獻。到了一九七○年代,更進一步翻譯《臺灣文化志》一部分內容,登載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刊物《臺灣文獻》上。而後於一九八五年開始到一九九一年,將全本《臺灣文化志》三冊翻譯出版,同書於一九九七年再版,於二○一一年出版修訂版,並於二○一七年出版全新審訂版。
戰後伊能嘉矩在臺灣以「翻譯」的型態存在,也受到了當時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
社會上一方面有要求臺灣史知識的需求,另一方面有民族主義的歷史知識過濾器,使得伊能的臺灣研究在戰後臺灣透過翻譯的繼受,產生了一些影響。例如在一九八五年臺灣省文獻會出版《臺灣文化志》中譯本時,就曾在〈序言〉中提醒讀者:「近年來,國人對於臺灣歷史之研究與考證,興趣愈來愈濃,有關著述、期刊、等等發行愈來愈多,各大專院校開課討論者,亦所在多有,要求本會提供資料者紛至沓來,無時無之,確是可喜的現象。……本書之原著者為日人,由於民族觀點之不同,立論或有所異,但參考價值仍多,願國人於引用時,酌加考慮!」更在〈譯例〉中提到:「一、日人伊能嘉矩著《臺灣文化志》向為臺灣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料,著者以日人談臺事,間或立場偏頗及史實訛誤,亦不在少數,譯本萬非不得已,蓋照原文譯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或許是為了使中譯本能順利出版才蛇足地多了這些說明,不過從這裡也可以看到戰後作為官方意識型態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成果在重新出版時的政治干擾與影響。二○一一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前身即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修訂版《臺灣文化志》時,原序文仍保留,但已經將「譯例」撤除。
由於對臺灣歷史知識的社會需求一直存在,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伊能嘉矩就如同臺灣省文獻會所言的,以雖然「民族觀點之不同,立論或有所異,但參考價值仍多」的方式被閱讀,伊能嘉矩在戰後除了以被翻譯的方式繼續留在臺灣,其主要作品也陸續被複印出版。例如一九六五年,臺北古亭書屋翻印了伊能的《臺灣文化志》,一九七三年翻印了《臺灣蕃政志》與《臺灣志》。一九八五年成文出版社,也複印了伊能的《臺灣志》、《臺灣年表》以及《領臺十年史》。一九八九年,南天書局翻印出版了《臺灣舊地名辭典》(原為《大日本地名辭典 臺灣篇》),一九九四年翻印出版了《臺灣文化誌》(原《臺灣文化志》),以及一九九五年的《理蕃誌稿》等。
有不少學者曾批評,戰後臺灣的臺灣歷史研究過度使用日治時期日本學者的成果與素材。伊能嘉矩的作品也曾存在著一種被「過度引用」的現象。伊能以其著作的豐富與涵蓋的全面性,成為研究者們所必須參考的成果,但其中有不少不假思索即直接引用伊能陳說的狀況。這樣的現象,反過來也說明了戰後臺灣在很長的時間內,曾經有過的臺灣歷史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方式。透過翻譯與翻印的形式,伊能嘉矩繼續在戰後臺灣發揮影響力,存續於學院與地方文史社群中。一九八○年代臺灣解嚴,逐漸邁向民主化,社會上臺灣歷史知識的需求,使得臺灣史獲得了市民權,同時臺灣研究也成為新興中的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象徵資源。一九九○年代伊能嘉矩重新回到臺灣,其田野日記等新的材料出版,獲得廣大的讀者群。伊能嘉矩的收藏資料與手稿,在此時已由大學研究機構整理與數位化,重建其完整性,研究者也開始透過伊能嘉矩討論新的歷史議題。
此次《臺灣文化志》的全新審訂版,原則上恢復伊能原來的用語與觀點,也保留了伊能的史觀,乃至其史料誤讀的部分。民主化之後的臺灣,已經累積了不少的臺灣研究成果,各種史觀的論辯也有充分表達自由,專業的歷史學家與業餘的文史愛好者,應該已具備了批判性閱讀伊能嘉矩及其《臺灣文化志》的識讀能力。
《臺灣文化志》作為臺灣研究的經典作品,其存在的意義除了是史學史意義上的重要先行成果,更在於後來的讀者們對其不斷地批判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