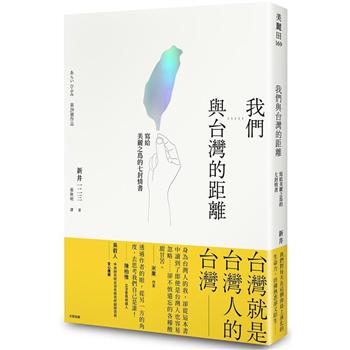前言
喜歡台灣的人。對台灣有興趣的人。有台灣朋友的人。打算去台灣旅行的人。
這是為你們而寫的書。
不論就地緣還是歷史方面,台灣和日本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但因為諸多因素,使得市面上日文寫的台灣書籍不是太多。
當寫出來的書少,不免令人擔心思考時必要的字彙恐怕相對不足。換言之,就像陷入單行道的死胡同一樣,總是鬼打牆似地回到同樣的結論。
就旅遊景點來說,台灣近來頗受到矚目。有關各地旅遊和美食的導覽資訊也跟著充實許多。因為治安良好又很方便,應該也能夠一個人拿著書本或手機遊走一下。
結果會不經意瞥見跟日本和其他國家不同,只有在台灣才會發生的情況。基於當各位心中冒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的疑問時,若是能提供解答、或是提供隻字片語觸發進一步調查的動機也好的想法,我動手寫下了這本書。
日文原文版的副標題「美麗島」的緣由可追溯至十六世紀航行到東亞的葡萄牙水手從海上眺望台灣時的一聲驚呼「Ilha formosa!」(福爾摩沙=美麗島),至今為全世界和當地人民對台灣共通的暱稱。
長年重複訪問台灣,我深深感受到每一個台灣人的背後都有著長篇小說般的故事。或許大家的人生多少有些共通之處,但那些長篇小說中充滿了許多外表看不出來,卻聽過一次後便永難忘懷的情節。
一旦和台灣人成為朋友,請試著傾聽他或她、以及他們的母親或是祖母的故事。
由衷祈願本書能成為解讀台灣此一物語的指引路標。
第一封 北與南的物語
(1)—台灣並不是「一個」
台北與「南部」
「妳知道嗎?台灣分為台北和『台北以外』,而且『台北以外』一概都被稱為『南部』。」
有一天聽到朋友跟我這麼說時,當下感覺有些心虛。因為自己已經來過台灣多次,卻從沒去過「台北以外」的地區。
畢竟來自日本的班機通常抵達的是台北機場;台北既是政治與經濟的中心,我的工作對象也都在台北。朋友自己十八歲上台北讀書,台灣大學畢業後也繼續留在台北擔任雜誌社編輯。不過她目前已考慮要回歸故鄉。
「流行歌曲不是也有唱嗎?『台北不是我的家』。剛好農曆春節要返鄉,妳要不要一起來?」
我自然是恭敬不如從命,決定跟著去叨擾。
台灣是個面積略小於九州的海島,南北狹長,當地居民暱稱般習慣用「番薯」一詞來形容其造型。朋友的故鄉是位於西海岸正中央的彰化。全縣人口一百二十萬,市區人口約二十萬餘人。距離靠近北端的台北將近兩百公里。當時號稱台灣新幹線的高鐵還沒開通,搭自強號火車得花兩個半小時才能到。
一抵達熱鬧的車站,「得先去吃彰化名產才行!」
朋友說完便帶我到周圍滿多的小吃攤之一嘗「肉圓」。我們坐進廚房在屋內、桌椅擺放在人行道上的小吃攤之一。手上接過來的碗裡面有著豬絞肉拌炒香菇的內餡、包裹在米粉和地瓜粉揉製而成的半透明餅皮中,上面還冒著熱氣。店員用剪刀把肉圓剪成兩半後,表面上澆了一層鹹鹹甜甜的濃稠醬汁。
「吃起來QQ的吧?」朋友笑著問我。
台灣人喜歡用「QQ」來形容柔軟有彈性的口感。以至於近年來珍珠奶茶的進化勢不可當。
朋友在南下的火車上告訴我:她家離市區有些偏遠,父親經營一家養豬場,有個弟弟幫忙一起打理。另外一個弟弟是修車工人,小弟還在當兵。三男一女的四姊弟中,只有她是不同母親生的。最後特別叮嚀「回到家的我和在台北時是完全不一樣的人,妳要有心理準備」。
作為充滿責任感的長女,她才一到家還沒來得及休息,便捲起衣袖一根又一根地削起粗大的蘿蔔。該說是母女的默契十足嗎,兩人幾乎未交一語地持續手上的工作。總之她看起來跟在台北的幹練編輯的確是判若兩人。將刨絲器夾在兩腿之間,只見削出來的蘿蔔絲逐漸堆滿類似嬰兒洗澡用的大水盆。原來年菜之一的蘿蔔糕是她負責的項目。
她家是兩層樓的透天厝,一樓地板鋪著磨砂磁磚,可以直接從外面穿鞋走進來。削蘿蔔絲的作業就是在這裡進行的。中間擺置接待客人的紅木桌椅,右後方走進去是廚房和餐廳。到此為止都是華南農村的風格。前面有通往二樓的樓梯,上樓前必須脫鞋。接下來就有點日本風。二樓是擦得光可鑑人的木頭地板,幾個房間並列在走廊兩側,每個房間裡都有一台大型電視。浴室裡有三溫暖蒸氣烤箱和按摩浴缸,喜愛洗澡的程度跟日本人不相上下。
聽朋友說整個彰化縣是以福建移民的後代子孫為主,不過她的祖先來自廣東省,附近住的都是當年一起飄洋過海的同鄉和親戚。從清朝時代集體移民至今已三百年。都市化的腳步方興未艾,原本以稻作為主的農村地帶仍零星散落著有別於中國北方四合院的傳統三合院建築。四方形的建地上,建築物環繞著中庭排列在北側和東西兩翼。只有南側開口,用來通風。確實要是不這麼做,住在位於亞熱帶和熱帶的台灣就太熱了。
由於祖母和外婆也都住在附近,台灣人的作風就是騎上速克達(Scooter)機車去露臉問聲好。不知道為何速克達在台灣特別受歡迎。我也借了頂安全帽,跨坐在機車後座,跟著一起去和大家打招呼。身為第一個考上最高學府國立台灣大學的她固然是家族之光,遇到的每個親戚卻都還是會問她「什麼時候要搬回故鄉呢」。
回到家後,我們到位於倉庫二樓的弟弟房間一起看電影。看的是侯孝賢導演的《戀戀風塵》。取代爆米花的是類似日清雞汁麵風味的統一麵,直接從袋子裡抓起來塞進嘴巴大口咀嚼。兩人都已經老大不小了,姊弟情深的景象讓人印象深刻。
農曆除夕午夜,將方桌搬至中庭,上面擺滿雞鴨魚肉和水果等供品。長長的香點燃後,由父親帶著全家人一起祭拜天上的神明。台灣人一般都很虔誠,供品也都準備得很豐盛。各地寺廟也總是香煙繚繞,擠滿膜拜祈福的善男信女。
壓歲錢則是一定要放進象徵吉祥喜氣的紅色紙袋中,稱之為紅包。大年初一早上,我也從朋友一向嚴肅沉默的父親手中領到紅包。朋友騎上速克達去給祖母和外婆送紅包。告別春節期間要留在故鄉的朋友和她家人,我一個人搭上開往台北的火車。
「台北不是我的家」
朋友提到的歌詞「台北不是我的家」是出自名聞整個大中華區的創作歌手羅大佑於一九八二年寫的暢銷歌曲〈鹿港小鎮〉。內容是到都會打拚失敗的寂寞男子思念起他留在故鄉的戀人,高唱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雖然經濟開始成長,但仍在很多方面都不自由的社會。鹿港是彰化縣的港口古鎮,地名中的鹿字意味著曾是出口鹿皮的港口,據說日本戰國時代織田信長等武將曾購買此地集散出口的鹿皮縫製成戰袍。或許因為如此,今日野生梅花鹿已完全滅絕。這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的歌詞似乎讓台灣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後也被許多歌曲引用。
〈鹿港小鎮〉經過八年後的一九九○年,和朋友同樣出生於彰化的林強用台語唱的〈向前走〉,歌聲中充滿了三年前終於解除戒嚴令,時代進入民主化的樂觀氛圍。
「再會啦故鄉,車站一站一站……台北車頭到了,我的理想和希望攏在這,卡早聽人唱『台北不是我的家』,但我一點攏無感覺。」
在過去提起台語歌,就想到古老悲情的演歌;而包含羅大佑暢銷歌曲的流行樂則非國語歌莫屬。林強以第一代搖滾音樂人的姿態現身,直接用台語表達自己的心聲。除了就像日本第一代以日語演唱搖滾樂的「Happy End樂團」(譯註:由細野晴臣、大瀧詠一、松本隆、鈴木茂於七○年代組成的民謠搖滾樂團。解散後也各自在日本的音樂界擁有一片天。)帶來新鮮感外;就使用學校禁止的語言唱歌這點來說,甚至還帶點革命的刺激感。
和林強幾乎是同一世代的編輯朋友,當時正在考慮,要麼身為台北第一代的職業婦女拚命下去,要麼聽親戚們的話回歸故鄉,抑或為了逃避家庭與事業的壓力,乾脆遠赴英倫學習建築。
「妳知道嗎?台灣分為台北和『台北以外』,而且『台北以外』一概都被稱為『南部』。」
之後我經常思索她說的這句話意味著什麼。感覺這是來自「台北以外」,又身處於媒體業的她才有的真知灼見。
台灣媒體業的總公司都設在台北,加上台北又位於台灣北端,使得台北以外的地方,不論在日常會話中還是白紙黑字上,長期以來都被統稱為「南部」。一如電影票房收入也是台北票房和全台票房分開計算,台北在台灣擁有特殊地位。然而因為外國媒體只在台北設置特派員,也就難以避免帶給全世界「台北=台灣」的印象了。台北市的人口約兩百七十萬,包含周邊地區也只有六百〜七百萬;而全台灣人口是兩千三百萬。儘管如此,除了媒體以外,包含公家機關和一般企業的運作都是以台北為中心。
就算是那樣,「台北以外」也並非只有南部,照理說也包含了中部和東部,卻一概稱為「南部」也太過籠統了吧。因為朋友是中部彰化出身,每次被歸類成「南部」不免心裡感覺怪怪的。尤其自己身為編輯,遇到非得用「南部」一詞時,感受更加強烈。
然而台北和「南部」除了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還有其他不同處:國語和方言、外省人和本省人、國民黨和民進黨。彰化的朋友在台北時跟外省人的上司和同事們用國語一起工作,可是一旦回到「南部」老家則是和本省人的家人親戚們用源自祖先故鄉的方言說話。政黨支持率的分布,台北是國民黨、「南部」是民進黨,當年也分得很清楚。
(2)—「台灣波士頓」
台南是美食天堂
「台南可說是台灣的波士頓。居民都很富裕,家家戶戶都會讓小孩學鋼琴或小提琴。」
聽到外省人A先生這麼介紹時,老實說我有些意外。
台南古都的歷史可追溯至十七世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時代,其實「台灣」這個地名本身乃是荷蘭人登陸台南時遇到原住民族所得知的地名。換言之台灣=台南。因此有人將台南拿來跟同樣是古都的京都比擬,相反地也有人主張「台南不是台灣的京都,而是台灣的台南」。
話又說回來,A先生雖非哈佛卻也是擁有留美博士學位的眷村子弟,說他至少有一隻腳踏在「天龍國」上應該不為過吧。這樣的他竟用羨慕般的語氣噘著嘴介紹這個人口約一百九十萬,六大直轄市中敬陪末座,在「南部」僅次於高雄的台南(相當於日本政令指定都市的六大直轄市依人口多寡排列為新北、台中、台北、桃園、高雄、台南。新北乃前台北縣,位於台北郊外)。
前往台南從台北搭高鐵並轉乘自強號需花費兩個小時。一九三六年完工的火車站,細緻堆疊得像白積木,顯得小巧美麗。二樓以前是附設西餐廳的鐵路飯店。米果說她小時候很期待週末跟父母外出時,能到車站二樓天花板挑高的西餐廳享用由穿著白襯衫、黑西裝褲的服務生送來的餐飲。該餐廳據說戰前是用進口的英國餐具盛裝西餐,戰後改成外省人做的中國菜,菜單上有著台灣當時還很少見的麻婆豆腐、宮保雞丁等川菜套餐(可惜西餐廳之後隨著飯店歇業也長期關閉了)。
清朝時代就盛行「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當時清朝官府所在的台南被稱為「府城」,至今台南人仍自認為是「府城人」。台南是具有歷史地位的都市。然而高鐵通車後,來自台北的觀光客增加,與其說是受到歷史魅力吸引,更多是為了其特有的美食文化而來。
鮮蝦高湯的麵條淋上肉燥,佐以滷蛋、香菜和蒜泥等調味的擔仔麵,現在台北也吃得到,但一八七二年創業的老店「再發號」知名的大肉粽則是不到台南就沒得品嘗。其他像是早餐吃的牛肉湯,一人份約有一整隻虱目魚的鹹粥、蝦仁裹上絞肉和魚漿炸成的蝦卷、炒飯上鋪滿小顆蝦仁的蝦仁飯、鱔魚炒麵等,奇妙的是台南就是有許多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美食。
滾燙的牛骨清湯中放入生牛肉片,稍微變色就能入口的早餐吃法(牛肉湯),完全是平常中國菜所沒有的概念。而大家習慣在大清早四、五點前來排隊享用,有一說是因為台南過去有牛墟可以買到新鮮牛肉,這道美食乃應運而生。也有一說太陽升起後氣溫會變熱,所以得趁著天色暗時食用。不管怎麼說,這都是一道極具特色的美食。
食物好吃的地方有一共通處,那就是點什麼菜都一樣好吃。在擔仔麵和肉粽店裡還可以點豬腳燉花生、蚵嗲、香腸、燙青菜等小菜和花枝丸、貢丸、魚丸、蛤蜊湯等湯品,風味就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至於台南特產的烏魚子更是好吃得沒話說。
這些台南美食一般都是由個人經營的小吃店提供,通常都是用日本人想像不到的小型餐具送上桌,所以不太容易吃飽,卻也多了邊散步邊嘗小吃的樂趣。想來應是生活富庶才有的情趣吧。相反地,豆花、紅豆冰、芒果冰等甜品類,不但分量十足,種類也繁多,可以兩三個人只點一份來吃。
誠品書店和奇美博物館
事實上外省人A先生「台南=波士頓」的說法是有一些根據的。
首先翻開世界史年表,為躲避宗教迫害離開英格蘭的清教徒們,搭乘五月花號抵達美國東海岸波士頓等現在被稱為新英格蘭州的土地是在一六二○年。東印度公司的荷蘭人登陸台南則是在僅四年後的一六二四年。荷蘭人還從對岸的中國招募移民,用船運送過來,台灣歷史因此有了重大轉變。換言之,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和台灣近代史幾乎是同一時期分別以波士頓和台南作為起始點。
台南也和波士頓一樣具有強烈的文化都市性格。
例如在全台灣有超過四十間店,也到香港和中國拓點,並決定於二○一九年進軍東京日本橋的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是台南出身的企業家。一九八九年第一家誠品於台北開店時,除了寬廣的空間,更讓愛書人驚豔的是架上的書以藝術和建築類為主,而且品項齊全,包含許多英日文的外文書。書店不僅歡迎顧客隨意拿起一本書站著或坐在地板上閱讀,創立當時便已附設咖啡廳,如今甚至還設置紅酒吧。也有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店鋪。始終堅持「尊重走進書店裡的每一個人」的經營文化,因此根據統計,平均每個台灣人一年會上五次誠品書店。
固然是理想書店,但若問如此經營方式能賺錢否,聽說是賠本的。然而工專畢業後因銷售餐廚設備事業有成的吳清友為貫徹「豐富台灣人的文化生活才有意義」的想法,據說仍不遺餘力援助誠品書店。因此當他六十七歲過世後,其故鄉台南市政府以其「體認到人文素養與藝術的重要性,打造出廣為華人社會知曉的書店模式」的成就審議認定為「歷史名人」。誠品書店創立於戒嚴令解除的兩年後,理想書店的出現可以說讓許多台灣人看到了言論自由的美好具象。
此外,台南還有奇美博物館,乃奇美實業創辦人也是李登輝前總統好友許文龍於一九九二年設立之台灣最大的私立博物館。矗立於九點五公頃的寬闊園區中,造型仿凡爾賽宮殿的奇美博物館,廣為人知的是收藏了上千把史特拉第瓦里(Stradivarius)等名家小提琴,可外借優秀音樂家使用。由於也收藏許多古樂器,該部門的收藏品絕對是世界頂級。另外,西洋美術、兵器、自然科學等部門的充實度比之國立博物館也毫不遜色。
聽說台南出身的許文龍,小時候最喜歡位於住家附近的台南博物館,那是一間不收費的小型博物館。可惜戰後因為國民黨政府的「北尊南卑」政策,使得「南部」文化狀況陷入停滯,於是他下定決心「有朝一日有錢了,要靠自己的力量開博物館」。許文龍高工畢業後,從事化工塑膠等實業,但因平日喜歡演奏小提琴而開始了樂器收藏之路。奇美集團基於許文龍要將古典音樂普及於台灣民間的想法,旗下也擁有交響樂團(奇美愛樂管弦樂團)。
企業家們的家鄉愛孕育出台南的文化土壤,在此潮流下據說台南人說的台語水準也很高。在台北,公家機關、學校、大企業的公用語言是國語,直到民主化後的今天仍持續未變。如此一來,有些人即便在家裡說的是台語,仍缺乏公開場所說正式台語的鍛鍊機會。相對地,台南的大企業連開公司會議都很理所當然地講台語。台北友人南下出差到該公司造訪後驚訝表示:「頭一次聽到水準那麼高的台語,嚇了一跳。」
「府城」的孩子—米果
雖說台南是擁有台灣最古老歷史的「府城」,飲食文化豐富,也的確備受許多有錢人愛戴,但我仍然以為外省人A先生口中「家家戶戶都會讓小孩學鋼琴或小提琴」的比喻太過誇張。搞不好是另一種版本的奇美傳說。
為了小心起見,我直接向台南出身的米果求證。她的說法如下:
「那是真的沒錯,我小時候也學過鋼琴。我家兄弟沒有學,不過同班有男生學拉小提琴。現在已經當醫生的男同學偶爾會在醫院裡開演奏會。」
好一個不可小覷的「府城」台南。
現在的台南大學是日治時代的前台南師範學校,音樂教育水平一向很高,據說畢業生任教小學後,利用課餘兼差教鋼琴的比比皆是。以米果的情況來說,一開始是跟姐姐的導師學彈鋼琴,後來是跟中學的音樂老師學。要想更上一層樓的話,也可找台南神學院(一八七六年由來自蘇格蘭的傳教士所設立)音樂科或大學講師接受個別指導。
米果的小學時代是一九七○年代。閱讀她回顧當時的文章發現居然和我所經驗過的昭和日本很類似。養樂多阿姨、玻璃瓶裝的配送鮮奶、到照相館拍攝的全家福照片。儘管日本人撤離台灣已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台灣本省人較多的南部仍瀰漫著濃厚的日本氣息。保留在台語中的日文就是見證遺物,像是榻榻米、枯立普(譯者註:Crepe,通常用來縫製內衣的皺紗棉。)、里亞卡(人力車)、美智子樣、遠足、注文。看似無脈絡可循,反而更顯得深入日常生活之中(事實上這股風潮至今仍持續著,例如已屆更年期的台灣友人都會在自己母親的推薦下飲用「命之母」(譯註:日本市售的婦女保健藥品。)
不過我這麼寫,恐怕會造成台南人的生活方式跟日本很類似的錯誤印象,實際上仍有許多地方跟同時代的日本有所差異。
從小的地方來看,雖然台灣的小孩也會帶便當上學,卻沒有吃冷飯的習慣,每個人都會將便當蒸過後吃熱的,學校也都備有大型的便當蒸籠。米果的母親認為重新熱過的飯菜不好吃,在她讀中學、高中的六年間,每天中午都送剛做好的便當到學校給她。
至於比較大的不同處,台灣到一九八○年代仍保有實質上的一夫多妻制。米果外祖母有個毫無血緣關係的妹妹(因為兩人從小就是養女),第一次出嫁就成了側室。後來丈夫過世後,又在葬禮上被小姑的丈夫看上,再度嫁作二房。當時小姑除了當媒人外,還將自己的兩個小孩過繼給膝下無子的她。米果在書中特別提到總是穿著正統旗袍、氣質優雅的姨嬤,實在無法跟出現在電視劇中陰險邪惡的「小妾」形象相提並論。
一九三○年代前出生的女性應該對類似的故事習以為常。主要前提在於女孩出生後,年幼期間就有被送出去當養女的習俗。傳統觀念認為女孩反正結婚後會離家,一開始就不屬於娘家所有。偏偏離開親生父母、尤其是離開母親身邊的孩子,在外面總是會遭遇許多傷心事。現在的台灣,女性走進社會已相當普及,甚至也選出了女總統。另一方面,僅僅上兩代之前男女在家庭和社會的地位仍存有顯著的差別,至今仍深刻烙印在記憶中,以至於形成出生率低於日本的陰影。
喜歡台灣的人。對台灣有興趣的人。有台灣朋友的人。打算去台灣旅行的人。
這是為你們而寫的書。
不論就地緣還是歷史方面,台灣和日本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但因為諸多因素,使得市面上日文寫的台灣書籍不是太多。
當寫出來的書少,不免令人擔心思考時必要的字彙恐怕相對不足。換言之,就像陷入單行道的死胡同一樣,總是鬼打牆似地回到同樣的結論。
就旅遊景點來說,台灣近來頗受到矚目。有關各地旅遊和美食的導覽資訊也跟著充實許多。因為治安良好又很方便,應該也能夠一個人拿著書本或手機遊走一下。
結果會不經意瞥見跟日本和其他國家不同,只有在台灣才會發生的情況。基於當各位心中冒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的疑問時,若是能提供解答、或是提供隻字片語觸發進一步調查的動機也好的想法,我動手寫下了這本書。
日文原文版的副標題「美麗島」的緣由可追溯至十六世紀航行到東亞的葡萄牙水手從海上眺望台灣時的一聲驚呼「Ilha formosa!」(福爾摩沙=美麗島),至今為全世界和當地人民對台灣共通的暱稱。
長年重複訪問台灣,我深深感受到每一個台灣人的背後都有著長篇小說般的故事。或許大家的人生多少有些共通之處,但那些長篇小說中充滿了許多外表看不出來,卻聽過一次後便永難忘懷的情節。
一旦和台灣人成為朋友,請試著傾聽他或她、以及他們的母親或是祖母的故事。
由衷祈願本書能成為解讀台灣此一物語的指引路標。
第一封 北與南的物語
(1)—台灣並不是「一個」
台北與「南部」
「妳知道嗎?台灣分為台北和『台北以外』,而且『台北以外』一概都被稱為『南部』。」
有一天聽到朋友跟我這麼說時,當下感覺有些心虛。因為自己已經來過台灣多次,卻從沒去過「台北以外」的地區。
畢竟來自日本的班機通常抵達的是台北機場;台北既是政治與經濟的中心,我的工作對象也都在台北。朋友自己十八歲上台北讀書,台灣大學畢業後也繼續留在台北擔任雜誌社編輯。不過她目前已考慮要回歸故鄉。
「流行歌曲不是也有唱嗎?『台北不是我的家』。剛好農曆春節要返鄉,妳要不要一起來?」
我自然是恭敬不如從命,決定跟著去叨擾。
台灣是個面積略小於九州的海島,南北狹長,當地居民暱稱般習慣用「番薯」一詞來形容其造型。朋友的故鄉是位於西海岸正中央的彰化。全縣人口一百二十萬,市區人口約二十萬餘人。距離靠近北端的台北將近兩百公里。當時號稱台灣新幹線的高鐵還沒開通,搭自強號火車得花兩個半小時才能到。
一抵達熱鬧的車站,「得先去吃彰化名產才行!」
朋友說完便帶我到周圍滿多的小吃攤之一嘗「肉圓」。我們坐進廚房在屋內、桌椅擺放在人行道上的小吃攤之一。手上接過來的碗裡面有著豬絞肉拌炒香菇的內餡、包裹在米粉和地瓜粉揉製而成的半透明餅皮中,上面還冒著熱氣。店員用剪刀把肉圓剪成兩半後,表面上澆了一層鹹鹹甜甜的濃稠醬汁。
「吃起來QQ的吧?」朋友笑著問我。
台灣人喜歡用「QQ」來形容柔軟有彈性的口感。以至於近年來珍珠奶茶的進化勢不可當。
朋友在南下的火車上告訴我:她家離市區有些偏遠,父親經營一家養豬場,有個弟弟幫忙一起打理。另外一個弟弟是修車工人,小弟還在當兵。三男一女的四姊弟中,只有她是不同母親生的。最後特別叮嚀「回到家的我和在台北時是完全不一樣的人,妳要有心理準備」。
作為充滿責任感的長女,她才一到家還沒來得及休息,便捲起衣袖一根又一根地削起粗大的蘿蔔。該說是母女的默契十足嗎,兩人幾乎未交一語地持續手上的工作。總之她看起來跟在台北的幹練編輯的確是判若兩人。將刨絲器夾在兩腿之間,只見削出來的蘿蔔絲逐漸堆滿類似嬰兒洗澡用的大水盆。原來年菜之一的蘿蔔糕是她負責的項目。
她家是兩層樓的透天厝,一樓地板鋪著磨砂磁磚,可以直接從外面穿鞋走進來。削蘿蔔絲的作業就是在這裡進行的。中間擺置接待客人的紅木桌椅,右後方走進去是廚房和餐廳。到此為止都是華南農村的風格。前面有通往二樓的樓梯,上樓前必須脫鞋。接下來就有點日本風。二樓是擦得光可鑑人的木頭地板,幾個房間並列在走廊兩側,每個房間裡都有一台大型電視。浴室裡有三溫暖蒸氣烤箱和按摩浴缸,喜愛洗澡的程度跟日本人不相上下。
聽朋友說整個彰化縣是以福建移民的後代子孫為主,不過她的祖先來自廣東省,附近住的都是當年一起飄洋過海的同鄉和親戚。從清朝時代集體移民至今已三百年。都市化的腳步方興未艾,原本以稻作為主的農村地帶仍零星散落著有別於中國北方四合院的傳統三合院建築。四方形的建地上,建築物環繞著中庭排列在北側和東西兩翼。只有南側開口,用來通風。確實要是不這麼做,住在位於亞熱帶和熱帶的台灣就太熱了。
由於祖母和外婆也都住在附近,台灣人的作風就是騎上速克達(Scooter)機車去露臉問聲好。不知道為何速克達在台灣特別受歡迎。我也借了頂安全帽,跨坐在機車後座,跟著一起去和大家打招呼。身為第一個考上最高學府國立台灣大學的她固然是家族之光,遇到的每個親戚卻都還是會問她「什麼時候要搬回故鄉呢」。
回到家後,我們到位於倉庫二樓的弟弟房間一起看電影。看的是侯孝賢導演的《戀戀風塵》。取代爆米花的是類似日清雞汁麵風味的統一麵,直接從袋子裡抓起來塞進嘴巴大口咀嚼。兩人都已經老大不小了,姊弟情深的景象讓人印象深刻。
農曆除夕午夜,將方桌搬至中庭,上面擺滿雞鴨魚肉和水果等供品。長長的香點燃後,由父親帶著全家人一起祭拜天上的神明。台灣人一般都很虔誠,供品也都準備得很豐盛。各地寺廟也總是香煙繚繞,擠滿膜拜祈福的善男信女。
壓歲錢則是一定要放進象徵吉祥喜氣的紅色紙袋中,稱之為紅包。大年初一早上,我也從朋友一向嚴肅沉默的父親手中領到紅包。朋友騎上速克達去給祖母和外婆送紅包。告別春節期間要留在故鄉的朋友和她家人,我一個人搭上開往台北的火車。
「台北不是我的家」
朋友提到的歌詞「台北不是我的家」是出自名聞整個大中華區的創作歌手羅大佑於一九八二年寫的暢銷歌曲〈鹿港小鎮〉。內容是到都會打拚失敗的寂寞男子思念起他留在故鄉的戀人,高唱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雖然經濟開始成長,但仍在很多方面都不自由的社會。鹿港是彰化縣的港口古鎮,地名中的鹿字意味著曾是出口鹿皮的港口,據說日本戰國時代織田信長等武將曾購買此地集散出口的鹿皮縫製成戰袍。或許因為如此,今日野生梅花鹿已完全滅絕。這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的歌詞似乎讓台灣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後也被許多歌曲引用。
〈鹿港小鎮〉經過八年後的一九九○年,和朋友同樣出生於彰化的林強用台語唱的〈向前走〉,歌聲中充滿了三年前終於解除戒嚴令,時代進入民主化的樂觀氛圍。
「再會啦故鄉,車站一站一站……台北車頭到了,我的理想和希望攏在這,卡早聽人唱『台北不是我的家』,但我一點攏無感覺。」
在過去提起台語歌,就想到古老悲情的演歌;而包含羅大佑暢銷歌曲的流行樂則非國語歌莫屬。林強以第一代搖滾音樂人的姿態現身,直接用台語表達自己的心聲。除了就像日本第一代以日語演唱搖滾樂的「Happy End樂團」(譯註:由細野晴臣、大瀧詠一、松本隆、鈴木茂於七○年代組成的民謠搖滾樂團。解散後也各自在日本的音樂界擁有一片天。)帶來新鮮感外;就使用學校禁止的語言唱歌這點來說,甚至還帶點革命的刺激感。
和林強幾乎是同一世代的編輯朋友,當時正在考慮,要麼身為台北第一代的職業婦女拚命下去,要麼聽親戚們的話回歸故鄉,抑或為了逃避家庭與事業的壓力,乾脆遠赴英倫學習建築。
「妳知道嗎?台灣分為台北和『台北以外』,而且『台北以外』一概都被稱為『南部』。」
之後我經常思索她說的這句話意味著什麼。感覺這是來自「台北以外」,又身處於媒體業的她才有的真知灼見。
台灣媒體業的總公司都設在台北,加上台北又位於台灣北端,使得台北以外的地方,不論在日常會話中還是白紙黑字上,長期以來都被統稱為「南部」。一如電影票房收入也是台北票房和全台票房分開計算,台北在台灣擁有特殊地位。然而因為外國媒體只在台北設置特派員,也就難以避免帶給全世界「台北=台灣」的印象了。台北市的人口約兩百七十萬,包含周邊地區也只有六百〜七百萬;而全台灣人口是兩千三百萬。儘管如此,除了媒體以外,包含公家機關和一般企業的運作都是以台北為中心。
就算是那樣,「台北以外」也並非只有南部,照理說也包含了中部和東部,卻一概稱為「南部」也太過籠統了吧。因為朋友是中部彰化出身,每次被歸類成「南部」不免心裡感覺怪怪的。尤其自己身為編輯,遇到非得用「南部」一詞時,感受更加強烈。
然而台北和「南部」除了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還有其他不同處:國語和方言、外省人和本省人、國民黨和民進黨。彰化的朋友在台北時跟外省人的上司和同事們用國語一起工作,可是一旦回到「南部」老家則是和本省人的家人親戚們用源自祖先故鄉的方言說話。政黨支持率的分布,台北是國民黨、「南部」是民進黨,當年也分得很清楚。
(2)—「台灣波士頓」
台南是美食天堂
「台南可說是台灣的波士頓。居民都很富裕,家家戶戶都會讓小孩學鋼琴或小提琴。」
聽到外省人A先生這麼介紹時,老實說我有些意外。
台南古都的歷史可追溯至十七世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時代,其實「台灣」這個地名本身乃是荷蘭人登陸台南時遇到原住民族所得知的地名。換言之台灣=台南。因此有人將台南拿來跟同樣是古都的京都比擬,相反地也有人主張「台南不是台灣的京都,而是台灣的台南」。
話又說回來,A先生雖非哈佛卻也是擁有留美博士學位的眷村子弟,說他至少有一隻腳踏在「天龍國」上應該不為過吧。這樣的他竟用羨慕般的語氣噘著嘴介紹這個人口約一百九十萬,六大直轄市中敬陪末座,在「南部」僅次於高雄的台南(相當於日本政令指定都市的六大直轄市依人口多寡排列為新北、台中、台北、桃園、高雄、台南。新北乃前台北縣,位於台北郊外)。
前往台南從台北搭高鐵並轉乘自強號需花費兩個小時。一九三六年完工的火車站,細緻堆疊得像白積木,顯得小巧美麗。二樓以前是附設西餐廳的鐵路飯店。米果說她小時候很期待週末跟父母外出時,能到車站二樓天花板挑高的西餐廳享用由穿著白襯衫、黑西裝褲的服務生送來的餐飲。該餐廳據說戰前是用進口的英國餐具盛裝西餐,戰後改成外省人做的中國菜,菜單上有著台灣當時還很少見的麻婆豆腐、宮保雞丁等川菜套餐(可惜西餐廳之後隨著飯店歇業也長期關閉了)。
清朝時代就盛行「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當時清朝官府所在的台南被稱為「府城」,至今台南人仍自認為是「府城人」。台南是具有歷史地位的都市。然而高鐵通車後,來自台北的觀光客增加,與其說是受到歷史魅力吸引,更多是為了其特有的美食文化而來。
鮮蝦高湯的麵條淋上肉燥,佐以滷蛋、香菜和蒜泥等調味的擔仔麵,現在台北也吃得到,但一八七二年創業的老店「再發號」知名的大肉粽則是不到台南就沒得品嘗。其他像是早餐吃的牛肉湯,一人份約有一整隻虱目魚的鹹粥、蝦仁裹上絞肉和魚漿炸成的蝦卷、炒飯上鋪滿小顆蝦仁的蝦仁飯、鱔魚炒麵等,奇妙的是台南就是有許多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美食。
滾燙的牛骨清湯中放入生牛肉片,稍微變色就能入口的早餐吃法(牛肉湯),完全是平常中國菜所沒有的概念。而大家習慣在大清早四、五點前來排隊享用,有一說是因為台南過去有牛墟可以買到新鮮牛肉,這道美食乃應運而生。也有一說太陽升起後氣溫會變熱,所以得趁著天色暗時食用。不管怎麼說,這都是一道極具特色的美食。
食物好吃的地方有一共通處,那就是點什麼菜都一樣好吃。在擔仔麵和肉粽店裡還可以點豬腳燉花生、蚵嗲、香腸、燙青菜等小菜和花枝丸、貢丸、魚丸、蛤蜊湯等湯品,風味就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至於台南特產的烏魚子更是好吃得沒話說。
這些台南美食一般都是由個人經營的小吃店提供,通常都是用日本人想像不到的小型餐具送上桌,所以不太容易吃飽,卻也多了邊散步邊嘗小吃的樂趣。想來應是生活富庶才有的情趣吧。相反地,豆花、紅豆冰、芒果冰等甜品類,不但分量十足,種類也繁多,可以兩三個人只點一份來吃。
誠品書店和奇美博物館
事實上外省人A先生「台南=波士頓」的說法是有一些根據的。
首先翻開世界史年表,為躲避宗教迫害離開英格蘭的清教徒們,搭乘五月花號抵達美國東海岸波士頓等現在被稱為新英格蘭州的土地是在一六二○年。東印度公司的荷蘭人登陸台南則是在僅四年後的一六二四年。荷蘭人還從對岸的中國招募移民,用船運送過來,台灣歷史因此有了重大轉變。換言之,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和台灣近代史幾乎是同一時期分別以波士頓和台南作為起始點。
台南也和波士頓一樣具有強烈的文化都市性格。
例如在全台灣有超過四十間店,也到香港和中國拓點,並決定於二○一九年進軍東京日本橋的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是台南出身的企業家。一九八九年第一家誠品於台北開店時,除了寬廣的空間,更讓愛書人驚豔的是架上的書以藝術和建築類為主,而且品項齊全,包含許多英日文的外文書。書店不僅歡迎顧客隨意拿起一本書站著或坐在地板上閱讀,創立當時便已附設咖啡廳,如今甚至還設置紅酒吧。也有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店鋪。始終堅持「尊重走進書店裡的每一個人」的經營文化,因此根據統計,平均每個台灣人一年會上五次誠品書店。
固然是理想書店,但若問如此經營方式能賺錢否,聽說是賠本的。然而工專畢業後因銷售餐廚設備事業有成的吳清友為貫徹「豐富台灣人的文化生活才有意義」的想法,據說仍不遺餘力援助誠品書店。因此當他六十七歲過世後,其故鄉台南市政府以其「體認到人文素養與藝術的重要性,打造出廣為華人社會知曉的書店模式」的成就審議認定為「歷史名人」。誠品書店創立於戒嚴令解除的兩年後,理想書店的出現可以說讓許多台灣人看到了言論自由的美好具象。
此外,台南還有奇美博物館,乃奇美實業創辦人也是李登輝前總統好友許文龍於一九九二年設立之台灣最大的私立博物館。矗立於九點五公頃的寬闊園區中,造型仿凡爾賽宮殿的奇美博物館,廣為人知的是收藏了上千把史特拉第瓦里(Stradivarius)等名家小提琴,可外借優秀音樂家使用。由於也收藏許多古樂器,該部門的收藏品絕對是世界頂級。另外,西洋美術、兵器、自然科學等部門的充實度比之國立博物館也毫不遜色。
聽說台南出身的許文龍,小時候最喜歡位於住家附近的台南博物館,那是一間不收費的小型博物館。可惜戰後因為國民黨政府的「北尊南卑」政策,使得「南部」文化狀況陷入停滯,於是他下定決心「有朝一日有錢了,要靠自己的力量開博物館」。許文龍高工畢業後,從事化工塑膠等實業,但因平日喜歡演奏小提琴而開始了樂器收藏之路。奇美集團基於許文龍要將古典音樂普及於台灣民間的想法,旗下也擁有交響樂團(奇美愛樂管弦樂團)。
企業家們的家鄉愛孕育出台南的文化土壤,在此潮流下據說台南人說的台語水準也很高。在台北,公家機關、學校、大企業的公用語言是國語,直到民主化後的今天仍持續未變。如此一來,有些人即便在家裡說的是台語,仍缺乏公開場所說正式台語的鍛鍊機會。相對地,台南的大企業連開公司會議都很理所當然地講台語。台北友人南下出差到該公司造訪後驚訝表示:「頭一次聽到水準那麼高的台語,嚇了一跳。」
「府城」的孩子—米果
雖說台南是擁有台灣最古老歷史的「府城」,飲食文化豐富,也的確備受許多有錢人愛戴,但我仍然以為外省人A先生口中「家家戶戶都會讓小孩學鋼琴或小提琴」的比喻太過誇張。搞不好是另一種版本的奇美傳說。
為了小心起見,我直接向台南出身的米果求證。她的說法如下:
「那是真的沒錯,我小時候也學過鋼琴。我家兄弟沒有學,不過同班有男生學拉小提琴。現在已經當醫生的男同學偶爾會在醫院裡開演奏會。」
好一個不可小覷的「府城」台南。
現在的台南大學是日治時代的前台南師範學校,音樂教育水平一向很高,據說畢業生任教小學後,利用課餘兼差教鋼琴的比比皆是。以米果的情況來說,一開始是跟姐姐的導師學彈鋼琴,後來是跟中學的音樂老師學。要想更上一層樓的話,也可找台南神學院(一八七六年由來自蘇格蘭的傳教士所設立)音樂科或大學講師接受個別指導。
米果的小學時代是一九七○年代。閱讀她回顧當時的文章發現居然和我所經驗過的昭和日本很類似。養樂多阿姨、玻璃瓶裝的配送鮮奶、到照相館拍攝的全家福照片。儘管日本人撤離台灣已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台灣本省人較多的南部仍瀰漫著濃厚的日本氣息。保留在台語中的日文就是見證遺物,像是榻榻米、枯立普(譯者註:Crepe,通常用來縫製內衣的皺紗棉。)、里亞卡(人力車)、美智子樣、遠足、注文。看似無脈絡可循,反而更顯得深入日常生活之中(事實上這股風潮至今仍持續著,例如已屆更年期的台灣友人都會在自己母親的推薦下飲用「命之母」(譯註:日本市售的婦女保健藥品。)
不過我這麼寫,恐怕會造成台南人的生活方式跟日本很類似的錯誤印象,實際上仍有許多地方跟同時代的日本有所差異。
從小的地方來看,雖然台灣的小孩也會帶便當上學,卻沒有吃冷飯的習慣,每個人都會將便當蒸過後吃熱的,學校也都備有大型的便當蒸籠。米果的母親認為重新熱過的飯菜不好吃,在她讀中學、高中的六年間,每天中午都送剛做好的便當到學校給她。
至於比較大的不同處,台灣到一九八○年代仍保有實質上的一夫多妻制。米果外祖母有個毫無血緣關係的妹妹(因為兩人從小就是養女),第一次出嫁就成了側室。後來丈夫過世後,又在葬禮上被小姑的丈夫看上,再度嫁作二房。當時小姑除了當媒人外,還將自己的兩個小孩過繼給膝下無子的她。米果在書中特別提到總是穿著正統旗袍、氣質優雅的姨嬤,實在無法跟出現在電視劇中陰險邪惡的「小妾」形象相提並論。
一九三○年代前出生的女性應該對類似的故事習以為常。主要前提在於女孩出生後,年幼期間就有被送出去當養女的習俗。傳統觀念認為女孩反正結婚後會離家,一開始就不屬於娘家所有。偏偏離開親生父母、尤其是離開母親身邊的孩子,在外面總是會遭遇許多傷心事。現在的台灣,女性走進社會已相當普及,甚至也選出了女總統。另一方面,僅僅上兩代之前男女在家庭和社會的地位仍存有顯著的差別,至今仍深刻烙印在記憶中,以至於形成出生率低於日本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