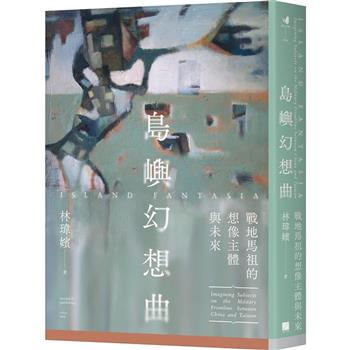第四章 與國家賭一賭(節錄)
【賭博成為戰地全民日常】
雖然政府大力禁止,賭博在軍事統治時期卻逐漸擴張,不但與各行各業人們的生活更為緊密連結,也發展出更豐富的意涵。《馬祖日報》從一九五七年創報以來到一九九二年解除戰地政務這段期間,報上屢屢刊載查緝賭博、燒賭具以及戒賭禁令等新聞,正呈現賭博在馬祖盛行的狀況。而且,賭博在這個時期已不再只是漁民之間的休閒娛樂了。
■公教人員
「抓得愈緊,賭得愈凶」,馬祖人說。以前只有漁民賭,現在不只是漁民了,戰地政務時期出現的公教人員也加入了戰局。《馬祖日報》上對公務人員的三令五申說明了公務單位與公務人員積極參與的情形。馬祖酒廠、物資處與馬祖日報社等公務單位都有人被抓,相繼上報。不過,即使官方一再嚇阻,並以嚴厲的撤職方式處罰,仍無法遏止他們的投入。一位任職馬祖電力公司的大哥描述那時的景象:
「當時我們辦公室的麻將桌從不收起來。中午十二點一休息,大家立刻衝過去搶位置,有的甚至飯都不吃。」
「為什麼他們如此瘋狂?」我追問。
「我也不知道……好像這樣日子才可以度過(他搔搔頭說)。」
大哥的支吾傳達了辦公室人們對於賭博某種無法言說的情感與渴望(inexpressible affect and desire);中午的麻將時光調解了公務機關例行性步調的單調與枯燥。
我們可以從物資處進一步來瞭解戰地政務時期公務員與賭博的關係。物資處是戰地政務時期特別單位,管控島內物資的流通。其處長、副處長與各科科長都由軍方派任,馬祖人擔任下屬辦事人員。因此,物資處有半軍方單位的性質:每天工作人員要先升旗、做完早操後才開始上班。物資處留下來的辦公室舊址至今還可以看到旗竿聳立在正中央(圖4.1)。
物資處負責調節島內重要物資。除了米由軍方直接管理之外,人民所需的民生用品,如麵粉、糖、各式酒類,以及建築材料如鋼筋、水泥等,都必須向物資處採買。整個物資處可說是一座大型倉庫(圖4.2)。
物資處的工作幾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歇。除了一般上班工作時間外,倉庫要有人看守。臺灣若有補給艦來,必須要有人馬上去港口支援,協助進貨。因此,工作人員要輪流值夜,睡在那裡。一個禮拜至少一次,事實上常常更多。物資處有自己的廚房,為工作人員準備三餐。員工直接睡在辦公室樓上(見圖4.2)。我們可以從物資處人員的作息時間表一窺他們的冗長辦公室生活(見表4.1)。
在物資處工作的人早上七點半前就要到,大家吃完早餐後,接著升旗、做早操,開始一天工作直到下午。下班吃完晚餐後,有的人可以回家,但不少人還要繼續留守。在這樣冗長的工作時間中,長官為了調劑員工的生活,特別設有下午三十分鐘左右的休息時間,要員工到廣場上去運動,打籃球(見圖4.2廣場中的兩個籃球框)。
不過,在這樣單調沉悶的生活節奏中,暗中也點綴著各式各樣的賭博方式。如中午休息時間有的時候會小賭一下撲克牌或象棋。下午三點半休息時間賭籃球。晚上時間多一點,大家就可以一起打麻將。物資處後方的防空洞是工作人員的天堂,他們牽了電線到那裡,安裝照明設施以度過漫漫長夜。通宵打牌後,隔日常常電線就被剪了─長官不高興在警告他們了!他們隔天可能就會乖一點早點回去睡。另外,相當有趣的是他們如何翻轉長官們眼中的正當娛樂「打籃球」成為「賭籃球」。
如圖4.3所示,罰球圈有九個位置。大家下場後,球拍一拍,使個眼色,就會開始賭了。通常是四個人一起玩,有時是每人一次投十個球,得分最多的人贏。更經常的方式是每個人輪流投球,球沒進就留在原位。若有進就可從位置一往二、三⋯⋯順序移位,先到位置九的人贏,其他視所在位置賠一百、兩百與三百。物資處單調的生活顏色就被這些各式各樣不同的賭博方式擦亮了。
■賭到墳墓去!
有時政府抓得很凶,辦公室或工作的地方也都沒辦法賭了,怎麼辦呢?人們就躲到荒廢的豬欄或往荒郊野外去賭。例如,牛角村落山上的墳地就是當時人們聚賭的地方。墓園有平坦的土地方便人們聚集,擺開陣勢。據說那裡只要公務人員中午休息時間十二點一到就很熱鬧。他們會來擲骰子,一直賭到一點半要上班了才結束。山上位置隱蔽,不容易被發現。賭徒也會安排人站哨,若有警察或憲兵聞風而來,可立即竄入林間,四散逃逸。
警察其實自己也會賭。為了要瞭解民眾賭博的情形,我訪問了戰地政務時期幾位曾擔任警察的人。其中一個在一九五○至一九六○年間擔任警察的長者回憶起他的同事,說他人很不錯,但被免職了,因為打麻將時被抓到。他也說他自己在山隴老街巡查時看人打牌時,被長官發現,記過一次;看來就連警察自身也很難抗拒打牌的誘惑。
好不容易我才終於在牛角遇到一位看起來很正派的阿伯說他從來不賭。但他接著說,他在一九七○年左右擔任警察期間,有一次有人通報牛角山丘上有人在賭博。他過去抓,沒想到竟然看到他媽媽也夾雜在人群中,是「賭徒」之一。母親看到兒子來抓,連忙逃跑,在驚慌中踉蹌跌倒。那時還年輕的阿伯趕快過去扶她起來,尷尬地說:「慢慢走就好。」
不過,事實上大部分賭徒都擅於逃跑,常讓年輕時當警察的阿伯抓不到。後來又有一次接獲檢舉說福澳有聚賭情形。他這次特別帶了不少人,兵分二路:一些從前門進去,他自己則繞行到後門,希望以全面包抄的方式一舉拿下所有賭徒。很幸運的,這次他成功了!但是一腳踹開門後,迎面而來竟是自己的兩個舅舅!阿伯說他覺得再這樣下去,親人都快被他抓光了,於是申請調離警察部門,轉到戶政去了。
■桌底下.坑道中
不只是公務人員,一般民眾有機會也賭。特別是在民防隊訓練期間,大家更是愛賭。他們神色自若地說:
軍官在講臺上口沫橫飛教導如何保養槍枝,防禦匪諜,我們坐在下面就在桌底下發牌,打「十三張」。
軍事演習更是賭博的好時機。特別是島上那些彎彎曲曲、綿延數里的坑道,簡直就是民防隊員賭博的天堂!因為長官看不見,也查不到。馬祖人說:
十分、二十分鐘都可以賭。時間短就發兩張牌比大小,時間多一點就發四張比對子。賭博本來就很有彈性(笑)。
教職人員也不例外。有的老師就躲在圖書館角落賭。大家事先約好,只要聽到有人腳步聲接近,就立即用布把麻將子蓋起來,趴在桌上假裝讀書讀累了在打盹兒。位於學校偏遠角落的貯藏室當然也是不錯的地點,人跡罕至、雜物障眼。
■女人與骰子
女人在戰地時期做阿兵哥生意有收入了,也會賭一把。特別是那些開店做阿兵哥生意的,以及到海邊採螺貝在市場賣的女人。她們有了收入後,即使在忙碌的工作中,仍會抽空賭一下。擲骰子通常是她們的最愛,因為擲骰子速度快,一把下去就立見輸贏,不會影響到她們的生活節奏。她們擲起骰子來,肢體語言非常多。特別是當莊家分數低,有機會可以贏的時刻。她們會先對著骰子喃喃自語,或是放在臉頰上,邊搓邊說:「猴子洗臉有錢賺。」(kau se mieng ou tsieng theing)然後吹氣、放在胸口上揉。等到要擲了,就會激動叫著:「四五六!四五六!」希望骰子能落在高點;莊家此時相對會喊:「一二三!一二三!」希望落在低點,來個不輸不贏,氣氛十分熱烈。她們知道萬一被抓,要罰掃街道、清水溝,甚至要挑糞,但仍暗中為之,樂此不疲。小賭一下後,她們就會趕快回去工作或回家煮飯,照顧老小。擲骰子與她們的步調配合得宜,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他們抓不到!」
「但是政府不是抓得很凶,一直燒賭具嗎?沒有賭具怎麼賭?」我問。前面提到那位年輕時做過警察的阿伯回答:
漁民有的把棋子藏在魚簍下面,有的與魚混在一起帶回來!漁民那麼多,我們怎麼查得完?
其他馬祖人也七嘴八舌地說:
拿到麻將的辦法很多。我們去臺灣參加活動,每個人分配幾個麻將子帶回來。到馬祖後就可湊成一副。
竹子裡面也可以藏啊!把竹節打通,就可以放很多運回來。
馬祖沒有瓦斯,要從臺灣進口。有人就把瓦斯桶鋸成兩半,把麻將、棋子、撲克牌都放進去,再焊接起來。油漆塗一塗,跟其他的桶子混在一起後就看不出來了。
「他們抓不到!」經常是這些敘述的結論。各式各樣與賭具有關的物質實踐成為馬祖人勇於冒險、挑戰國家的方式。他們以此想像自己能夠創造各種蔓延根莖狀的空間(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逃匿軍方嚴格的查緝。
【打黃魚與比牌九】
戰地時期,賭博有了另一種儀式性的發展,特別是東引的黃魚季期間。黃魚是中國沿海重要的魚種,漁場分布在南方外海。黃魚有結群洄游的習性,東引正位於黃魚洄游生殖的路徑上,因此是重要的漁場。每年春天四至六月黃魚從東南外海進入東引附近,是打黃魚主要的季節(陳治龍,2013: 102)。
東引很早就有捕黃魚傳統,當地耆老說以前春天漁汛來臨時大陸沿海的漁民都會前來捕魚,賣到大陸。兩岸隔絕後,東引人捕來新鮮的黃魚只能賣給軍人,軍人無法消耗時只能做魚乾,非常可惜。大概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有臺灣來的冷凍船在東引收購黃魚。馬祖漁會於是與臺灣魚商簽立保證收購合約,也就是不管捕獲的黃魚有多少,得標的船公司都必須以保證價格全數收購。因此,黃魚捕獲若豐,對漁民就是一筆不小的財富。更不用說那時魚商是以現金交易,能夠補到黃魚等於立即發了一筆橫財。因此從一九六八年起,每年馬祖各島的漁民都會結隊前往東引捕撈。出發前要先接受思想訓練三天,瞭解「共匪暴行」後,才可以準備啟航。漁船出港時,官員會到碼頭送行,燃放鞭炮預祝滿載而歸。
黃魚在大水時會上浮到接近海面處,比較容易捕捉。農曆初一和十五兩次大水,就是漁民滿心期待捉到黃魚的時候。黃魚在繁殖期間,鰾會震動,發出「咯咯」的聲音以吸引異性的注意,尤其在魚群密集時會發出如水沸聲或松濤般的叫聲(劉家國,2002)。以前沒有魚探器,漁民經常以聲音估測魚群的大小。地方有句俗諺:「東引黃瓜乞嘴害」(toeyng ing uong hua khoeyh tshui hai),就是形容黃魚因為自己發出聲音才會被漁民抓到,以此來調侃多話的人。
然而海中黃魚鳴叫聲四起,不代表每艘漁船都可以滿載而歸。東引一位非常有經驗的船長解釋說:
船開到有聲音的地方,熄火聽……
魚是在中間?外圍?還是還有一段距離?不是正中間就再找。
船長聽聲辨位的功力要好之外,還有天氣與潮水等其他無法預期的因素。所以即使是最有經驗的老船長,也不保證都能抓到。大家同時出發,甚至在鄰近的海面下網,結果也是有的漁船滿載而歸,有的漁船打到的魚,則還不夠一船人的生活開銷。為何如此?東引另一位非常有名的船長說,黃魚聚集叫聲很大的時候,很多船都會來。但是魚群究竟在哪一個位置,在漁業技術有限的時代,很不容易確認,能否抓到只能「靠運氣」(也見陳其敏,2009;嚴正,1977)。他大致畫了一幅圖說明(圖4.4):圖中的B最幸運,漁網剛好下在中間,可以滿載而歸。A稍偏左一點,但還是可以抓到一些。C太偏右,就不太有希望了。
因此,東引人說能夠抓到黃魚時,就是「發了」,「大家興奮得不得了,跟賭贏沒兩樣。」而且,打到黃魚時,「魚會浮到水面,就像大冰塊浮在水面一樣,人都可以站在上面。」(陳其敏,2009)。對於這樣的大豐收,南竿漁民也描述:
運氣好的時候,下網一次可以補到兩萬斤,連船都沒辦法載,只好把網砍斷,把魚放生!臺灣過來的包商一艘船最多只能載二百噸,多出來的沒辦法載,過磅以後,通通倒回海裡去!(陳治龍,2013: 104)
前面提到的東引資深船長還提到他有一次開雙拖漁船捕黃魚,結果一次抓到四十噸。他說:「我花了一天的時間才把魚全部吊上來,可見有多少!」看見魚那麼多,他決定直接把船開到基隆港賣,那一次就賺了四百萬!他笑笑地回憶說:
船長:船員那夜跑去「喝花酒」慶祝!那時坐檯小姐的價格是一人一百元(一九八○年前後)。你知道他們一出手給她多少錢嗎?
作者:多少?
船長:一萬!
知道漁民捕獲黃魚在臺灣的瘋狂慶祝方式,我們就不會訝異他們在東引下船後會大開賭局了。或許是再賭一次運氣,或者看看能不能再有同樣的奇蹟,抓到黃魚的漁民賭起來真是豪氣萬千!他們大手筆押注,無論勝負都面無表情,真正目的可能更在展示而非輸贏。
我好奇地問:「那些沒抓到的呢?他們賭嗎?」不少漁民回答:
沒抓到的也賭啊,看看能不能贏過來。
最壞就這樣了,借錢來拚,拚了就有希望。
今天輸兩萬,說不定明天就賺五、六萬回來。
在黃魚大豐收時,漁民喜歡打牌九(當地人稱為「比牌九」,pi pe ou)。比牌九原本多半在島上最大的節慶─元宵節─時分進行,由此可見黃魚季的儀式性特色。打牌九時,莊家發給每人發四張牌,賭客排列組合為兩組與莊家比大小。打牌九是單純比大小,發牌少,速度快,而且雖然限制四人玩,但其他旁觀的人也可押注,因此黃魚季時賭起牌九,桌邊人潮往往擠得水泄不通。聽東引人說至少會圍三圈:第一圈是實際上場打牌的人,第二圈是押注者,第三圈是圍觀的人,非常熱鬧。再加上賭注沒有上限,輸贏很大,氣氛更為熱烈。
我們可以說東引黃魚季打牌九是一種儀式性的活動。正由於儀式性,軍方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太取締。但是漁民一賭下來,有時把一整季的辛苦都輸光了。所以那個時候流行一句話:「黃魚發也哭,沒發也哭」(uong ua huah ya thi, mo huah ya thie),意指抓不到黃魚的人心裡難過,抓到黃魚的人也是在一夜之間把賺來的錢在賭桌上散盡。的確,漁季結束時,許多漁民把賺來的錢也差不多輸光了(陳其敏,2009)。牛角人曹順志就告訴我,小時候爸爸去東引打黃魚通常要兩個多月,但每次都是口袋空空回來。我問他既然沒有收入爸爸為什麼還要去打,他理直氣壯地回答說:
打魚人,怎能不去!
我猜他的意思應該是指整個打魚與賭博的過程才是漁人本色的展現吧。東引的黃魚在一九八五年之後,因魚源枯竭而走入歷史,然而至今長輩們對那段打黃魚與比牌九的記憶仍歷歷在目,念念不忘。
【賭博成為戰地全民日常】
雖然政府大力禁止,賭博在軍事統治時期卻逐漸擴張,不但與各行各業人們的生活更為緊密連結,也發展出更豐富的意涵。《馬祖日報》從一九五七年創報以來到一九九二年解除戰地政務這段期間,報上屢屢刊載查緝賭博、燒賭具以及戒賭禁令等新聞,正呈現賭博在馬祖盛行的狀況。而且,賭博在這個時期已不再只是漁民之間的休閒娛樂了。
■公教人員
「抓得愈緊,賭得愈凶」,馬祖人說。以前只有漁民賭,現在不只是漁民了,戰地政務時期出現的公教人員也加入了戰局。《馬祖日報》上對公務人員的三令五申說明了公務單位與公務人員積極參與的情形。馬祖酒廠、物資處與馬祖日報社等公務單位都有人被抓,相繼上報。不過,即使官方一再嚇阻,並以嚴厲的撤職方式處罰,仍無法遏止他們的投入。一位任職馬祖電力公司的大哥描述那時的景象:
「當時我們辦公室的麻將桌從不收起來。中午十二點一休息,大家立刻衝過去搶位置,有的甚至飯都不吃。」
「為什麼他們如此瘋狂?」我追問。
「我也不知道……好像這樣日子才可以度過(他搔搔頭說)。」
大哥的支吾傳達了辦公室人們對於賭博某種無法言說的情感與渴望(inexpressible affect and desire);中午的麻將時光調解了公務機關例行性步調的單調與枯燥。
我們可以從物資處進一步來瞭解戰地政務時期公務員與賭博的關係。物資處是戰地政務時期特別單位,管控島內物資的流通。其處長、副處長與各科科長都由軍方派任,馬祖人擔任下屬辦事人員。因此,物資處有半軍方單位的性質:每天工作人員要先升旗、做完早操後才開始上班。物資處留下來的辦公室舊址至今還可以看到旗竿聳立在正中央(圖4.1)。
物資處負責調節島內重要物資。除了米由軍方直接管理之外,人民所需的民生用品,如麵粉、糖、各式酒類,以及建築材料如鋼筋、水泥等,都必須向物資處採買。整個物資處可說是一座大型倉庫(圖4.2)。
物資處的工作幾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歇。除了一般上班工作時間外,倉庫要有人看守。臺灣若有補給艦來,必須要有人馬上去港口支援,協助進貨。因此,工作人員要輪流值夜,睡在那裡。一個禮拜至少一次,事實上常常更多。物資處有自己的廚房,為工作人員準備三餐。員工直接睡在辦公室樓上(見圖4.2)。我們可以從物資處人員的作息時間表一窺他們的冗長辦公室生活(見表4.1)。
在物資處工作的人早上七點半前就要到,大家吃完早餐後,接著升旗、做早操,開始一天工作直到下午。下班吃完晚餐後,有的人可以回家,但不少人還要繼續留守。在這樣冗長的工作時間中,長官為了調劑員工的生活,特別設有下午三十分鐘左右的休息時間,要員工到廣場上去運動,打籃球(見圖4.2廣場中的兩個籃球框)。
不過,在這樣單調沉悶的生活節奏中,暗中也點綴著各式各樣的賭博方式。如中午休息時間有的時候會小賭一下撲克牌或象棋。下午三點半休息時間賭籃球。晚上時間多一點,大家就可以一起打麻將。物資處後方的防空洞是工作人員的天堂,他們牽了電線到那裡,安裝照明設施以度過漫漫長夜。通宵打牌後,隔日常常電線就被剪了─長官不高興在警告他們了!他們隔天可能就會乖一點早點回去睡。另外,相當有趣的是他們如何翻轉長官們眼中的正當娛樂「打籃球」成為「賭籃球」。
如圖4.3所示,罰球圈有九個位置。大家下場後,球拍一拍,使個眼色,就會開始賭了。通常是四個人一起玩,有時是每人一次投十個球,得分最多的人贏。更經常的方式是每個人輪流投球,球沒進就留在原位。若有進就可從位置一往二、三⋯⋯順序移位,先到位置九的人贏,其他視所在位置賠一百、兩百與三百。物資處單調的生活顏色就被這些各式各樣不同的賭博方式擦亮了。
■賭到墳墓去!
有時政府抓得很凶,辦公室或工作的地方也都沒辦法賭了,怎麼辦呢?人們就躲到荒廢的豬欄或往荒郊野外去賭。例如,牛角村落山上的墳地就是當時人們聚賭的地方。墓園有平坦的土地方便人們聚集,擺開陣勢。據說那裡只要公務人員中午休息時間十二點一到就很熱鬧。他們會來擲骰子,一直賭到一點半要上班了才結束。山上位置隱蔽,不容易被發現。賭徒也會安排人站哨,若有警察或憲兵聞風而來,可立即竄入林間,四散逃逸。
警察其實自己也會賭。為了要瞭解民眾賭博的情形,我訪問了戰地政務時期幾位曾擔任警察的人。其中一個在一九五○至一九六○年間擔任警察的長者回憶起他的同事,說他人很不錯,但被免職了,因為打麻將時被抓到。他也說他自己在山隴老街巡查時看人打牌時,被長官發現,記過一次;看來就連警察自身也很難抗拒打牌的誘惑。
好不容易我才終於在牛角遇到一位看起來很正派的阿伯說他從來不賭。但他接著說,他在一九七○年左右擔任警察期間,有一次有人通報牛角山丘上有人在賭博。他過去抓,沒想到竟然看到他媽媽也夾雜在人群中,是「賭徒」之一。母親看到兒子來抓,連忙逃跑,在驚慌中踉蹌跌倒。那時還年輕的阿伯趕快過去扶她起來,尷尬地說:「慢慢走就好。」
不過,事實上大部分賭徒都擅於逃跑,常讓年輕時當警察的阿伯抓不到。後來又有一次接獲檢舉說福澳有聚賭情形。他這次特別帶了不少人,兵分二路:一些從前門進去,他自己則繞行到後門,希望以全面包抄的方式一舉拿下所有賭徒。很幸運的,這次他成功了!但是一腳踹開門後,迎面而來竟是自己的兩個舅舅!阿伯說他覺得再這樣下去,親人都快被他抓光了,於是申請調離警察部門,轉到戶政去了。
■桌底下.坑道中
不只是公務人員,一般民眾有機會也賭。特別是在民防隊訓練期間,大家更是愛賭。他們神色自若地說:
軍官在講臺上口沫橫飛教導如何保養槍枝,防禦匪諜,我們坐在下面就在桌底下發牌,打「十三張」。
軍事演習更是賭博的好時機。特別是島上那些彎彎曲曲、綿延數里的坑道,簡直就是民防隊員賭博的天堂!因為長官看不見,也查不到。馬祖人說:
十分、二十分鐘都可以賭。時間短就發兩張牌比大小,時間多一點就發四張比對子。賭博本來就很有彈性(笑)。
教職人員也不例外。有的老師就躲在圖書館角落賭。大家事先約好,只要聽到有人腳步聲接近,就立即用布把麻將子蓋起來,趴在桌上假裝讀書讀累了在打盹兒。位於學校偏遠角落的貯藏室當然也是不錯的地點,人跡罕至、雜物障眼。
■女人與骰子
女人在戰地時期做阿兵哥生意有收入了,也會賭一把。特別是那些開店做阿兵哥生意的,以及到海邊採螺貝在市場賣的女人。她們有了收入後,即使在忙碌的工作中,仍會抽空賭一下。擲骰子通常是她們的最愛,因為擲骰子速度快,一把下去就立見輸贏,不會影響到她們的生活節奏。她們擲起骰子來,肢體語言非常多。特別是當莊家分數低,有機會可以贏的時刻。她們會先對著骰子喃喃自語,或是放在臉頰上,邊搓邊說:「猴子洗臉有錢賺。」(kau se mieng ou tsieng theing)然後吹氣、放在胸口上揉。等到要擲了,就會激動叫著:「四五六!四五六!」希望骰子能落在高點;莊家此時相對會喊:「一二三!一二三!」希望落在低點,來個不輸不贏,氣氛十分熱烈。她們知道萬一被抓,要罰掃街道、清水溝,甚至要挑糞,但仍暗中為之,樂此不疲。小賭一下後,她們就會趕快回去工作或回家煮飯,照顧老小。擲骰子與她們的步調配合得宜,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他們抓不到!」
「但是政府不是抓得很凶,一直燒賭具嗎?沒有賭具怎麼賭?」我問。前面提到那位年輕時做過警察的阿伯回答:
漁民有的把棋子藏在魚簍下面,有的與魚混在一起帶回來!漁民那麼多,我們怎麼查得完?
其他馬祖人也七嘴八舌地說:
拿到麻將的辦法很多。我們去臺灣參加活動,每個人分配幾個麻將子帶回來。到馬祖後就可湊成一副。
竹子裡面也可以藏啊!把竹節打通,就可以放很多運回來。
馬祖沒有瓦斯,要從臺灣進口。有人就把瓦斯桶鋸成兩半,把麻將、棋子、撲克牌都放進去,再焊接起來。油漆塗一塗,跟其他的桶子混在一起後就看不出來了。
「他們抓不到!」經常是這些敘述的結論。各式各樣與賭具有關的物質實踐成為馬祖人勇於冒險、挑戰國家的方式。他們以此想像自己能夠創造各種蔓延根莖狀的空間(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逃匿軍方嚴格的查緝。
【打黃魚與比牌九】
戰地時期,賭博有了另一種儀式性的發展,特別是東引的黃魚季期間。黃魚是中國沿海重要的魚種,漁場分布在南方外海。黃魚有結群洄游的習性,東引正位於黃魚洄游生殖的路徑上,因此是重要的漁場。每年春天四至六月黃魚從東南外海進入東引附近,是打黃魚主要的季節(陳治龍,2013: 102)。
東引很早就有捕黃魚傳統,當地耆老說以前春天漁汛來臨時大陸沿海的漁民都會前來捕魚,賣到大陸。兩岸隔絕後,東引人捕來新鮮的黃魚只能賣給軍人,軍人無法消耗時只能做魚乾,非常可惜。大概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有臺灣來的冷凍船在東引收購黃魚。馬祖漁會於是與臺灣魚商簽立保證收購合約,也就是不管捕獲的黃魚有多少,得標的船公司都必須以保證價格全數收購。因此,黃魚捕獲若豐,對漁民就是一筆不小的財富。更不用說那時魚商是以現金交易,能夠補到黃魚等於立即發了一筆橫財。因此從一九六八年起,每年馬祖各島的漁民都會結隊前往東引捕撈。出發前要先接受思想訓練三天,瞭解「共匪暴行」後,才可以準備啟航。漁船出港時,官員會到碼頭送行,燃放鞭炮預祝滿載而歸。
黃魚在大水時會上浮到接近海面處,比較容易捕捉。農曆初一和十五兩次大水,就是漁民滿心期待捉到黃魚的時候。黃魚在繁殖期間,鰾會震動,發出「咯咯」的聲音以吸引異性的注意,尤其在魚群密集時會發出如水沸聲或松濤般的叫聲(劉家國,2002)。以前沒有魚探器,漁民經常以聲音估測魚群的大小。地方有句俗諺:「東引黃瓜乞嘴害」(toeyng ing uong hua khoeyh tshui hai),就是形容黃魚因為自己發出聲音才會被漁民抓到,以此來調侃多話的人。
然而海中黃魚鳴叫聲四起,不代表每艘漁船都可以滿載而歸。東引一位非常有經驗的船長解釋說:
船開到有聲音的地方,熄火聽……
魚是在中間?外圍?還是還有一段距離?不是正中間就再找。
船長聽聲辨位的功力要好之外,還有天氣與潮水等其他無法預期的因素。所以即使是最有經驗的老船長,也不保證都能抓到。大家同時出發,甚至在鄰近的海面下網,結果也是有的漁船滿載而歸,有的漁船打到的魚,則還不夠一船人的生活開銷。為何如此?東引另一位非常有名的船長說,黃魚聚集叫聲很大的時候,很多船都會來。但是魚群究竟在哪一個位置,在漁業技術有限的時代,很不容易確認,能否抓到只能「靠運氣」(也見陳其敏,2009;嚴正,1977)。他大致畫了一幅圖說明(圖4.4):圖中的B最幸運,漁網剛好下在中間,可以滿載而歸。A稍偏左一點,但還是可以抓到一些。C太偏右,就不太有希望了。
因此,東引人說能夠抓到黃魚時,就是「發了」,「大家興奮得不得了,跟賭贏沒兩樣。」而且,打到黃魚時,「魚會浮到水面,就像大冰塊浮在水面一樣,人都可以站在上面。」(陳其敏,2009)。對於這樣的大豐收,南竿漁民也描述:
運氣好的時候,下網一次可以補到兩萬斤,連船都沒辦法載,只好把網砍斷,把魚放生!臺灣過來的包商一艘船最多只能載二百噸,多出來的沒辦法載,過磅以後,通通倒回海裡去!(陳治龍,2013: 104)
前面提到的東引資深船長還提到他有一次開雙拖漁船捕黃魚,結果一次抓到四十噸。他說:「我花了一天的時間才把魚全部吊上來,可見有多少!」看見魚那麼多,他決定直接把船開到基隆港賣,那一次就賺了四百萬!他笑笑地回憶說:
船長:船員那夜跑去「喝花酒」慶祝!那時坐檯小姐的價格是一人一百元(一九八○年前後)。你知道他們一出手給她多少錢嗎?
作者:多少?
船長:一萬!
知道漁民捕獲黃魚在臺灣的瘋狂慶祝方式,我們就不會訝異他們在東引下船後會大開賭局了。或許是再賭一次運氣,或者看看能不能再有同樣的奇蹟,抓到黃魚的漁民賭起來真是豪氣萬千!他們大手筆押注,無論勝負都面無表情,真正目的可能更在展示而非輸贏。
我好奇地問:「那些沒抓到的呢?他們賭嗎?」不少漁民回答:
沒抓到的也賭啊,看看能不能贏過來。
最壞就這樣了,借錢來拚,拚了就有希望。
今天輸兩萬,說不定明天就賺五、六萬回來。
在黃魚大豐收時,漁民喜歡打牌九(當地人稱為「比牌九」,pi pe ou)。比牌九原本多半在島上最大的節慶─元宵節─時分進行,由此可見黃魚季的儀式性特色。打牌九時,莊家發給每人發四張牌,賭客排列組合為兩組與莊家比大小。打牌九是單純比大小,發牌少,速度快,而且雖然限制四人玩,但其他旁觀的人也可押注,因此黃魚季時賭起牌九,桌邊人潮往往擠得水泄不通。聽東引人說至少會圍三圈:第一圈是實際上場打牌的人,第二圈是押注者,第三圈是圍觀的人,非常熱鬧。再加上賭注沒有上限,輸贏很大,氣氛更為熱烈。
我們可以說東引黃魚季打牌九是一種儀式性的活動。正由於儀式性,軍方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太取締。但是漁民一賭下來,有時把一整季的辛苦都輸光了。所以那個時候流行一句話:「黃魚發也哭,沒發也哭」(uong ua huah ya thi, mo huah ya thie),意指抓不到黃魚的人心裡難過,抓到黃魚的人也是在一夜之間把賺來的錢在賭桌上散盡。的確,漁季結束時,許多漁民把賺來的錢也差不多輸光了(陳其敏,2009)。牛角人曹順志就告訴我,小時候爸爸去東引打黃魚通常要兩個多月,但每次都是口袋空空回來。我問他既然沒有收入爸爸為什麼還要去打,他理直氣壯地回答說:
打魚人,怎能不去!
我猜他的意思應該是指整個打魚與賭博的過程才是漁人本色的展現吧。東引的黃魚在一九八五年之後,因魚源枯竭而走入歷史,然而至今長輩們對那段打黃魚與比牌九的記憶仍歷歷在目,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