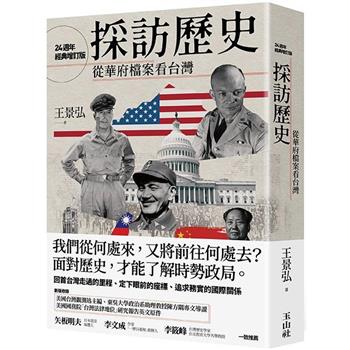前言 讓歷史還原
從事新聞工作者,都希望能寫點「內幕」,因為人都有好奇心,「內幕」不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且,可以滿足更多讀者的好奇心。
但是真正可信的「內幕」不多,在自由、開放的社會如此,在缺乏自由的社會更是如此。在自由社會,雖然言論、寫作不受政治干預,但是,因為新聞工作者所要寫的「內幕」,並不是自己直接參與,而是「他說」「她說」的組合。
這並不是說經過轉述的「內幕」都不可靠,但毫無疑問的,當事人在轉述時,即使再求公正,也會因為認知、記憶、立場、利益、保護自己、衛護友人等各種不同因素而發生偏差。更糟的是有的人會存心誤導,扭曲真相。
在沒有新聞自由的集權、威權統治下,新聞工作者和媒體都是統治者的宣傳工具,那更談不上能寫什麼「內幕」。
我在威權時代開始新聞工作,到美國進修之前,採訪外交新聞。那時尼克森已宣布一九七二年要訪問北京,而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眼看難保。雖然外交界知道局面不利,應有務實做法,但這種話,誰也不敢對媒體說。如果引用一點外國媒體,或外國政府的觀察,那已經很「內幕」了。
威權時代的政治、外交新聞,大部分屬「宣傳」,目的在粉飾太平,不讓民眾知道事實真相,和它所代表的意義。
到美國鄉下密蘇里大學進修時,選了兩門美國外交史,開始了解和接觸美國外交關係檔案。舒勒教授一有假日便前往華府查閱新解密之檔案的精神,更使我印象深刻。
美國外交關係文件,在解密後均由該國國務院歷史室編選成書出版,尚未及出版或未被編選的文件,開放供研究者查閱。在一九八○年代美國預算還寬裕時,採訪國務院的外交記者可以優先免費取得新出版的外交關係文件,後來這種待遇取消,需要者可以到歷史室查閱,或自己購取。
在戒嚴體制下,每天看官樣文章、表面聲明的新聞工作者,能接觸到真正「機密」的文件,內心的興奮與激動,實難以形容,即使那些「機密」已是二、三十年前舊事。翻閱舊檔,看美國外交官如何思考問題、蔣介石時代的外交官如何與美國交涉、得到何種回應,成了自己的一種嗜好。那也滿足了自己在威權時代無法滿足的好奇心。
新聞工作者的任務是要採訪「現在」,但我業餘卻在採訪「歷史」。「現在」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不容易得到「真相大白」;「歷史」屬「俱往矣」的大事,有真正檔案可查,重建真相還較可為。
我把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三年間,美國與台灣的十件大事,寫成這本書,目的在使歷史真相能還原。一九七三年的截期並不是我的選擇,那只是美國外交檔案經解密可供研究的資料,目前(初版成書為二○○○年)只到一九七三年。但那也是一個很有意義、很重要的階段,因為自一九七○年代開始,台灣處境日艱,美國對華政策轉向,蔣介石健康惡化,「革新保台」之聲高張,而蔣經國走到前台,繼承他父親主導台灣政局。
這不是一本學術性的歷史書,因為我使用的資料主要是美國已出版或當時公開,但尚未出版的檔案。我並沒有機會接觸到台灣的檔案文件,也沒有引述像已故駐美大使顧維鈞回憶錄中,對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談判,及因應台海危機的第一手描述。正如書名所言,我只是「採訪歷史」。
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七三年那個時空背景及不同的政治體制及官場文化,我相信美國政府檔案的記載,應該比台灣的文件可信。台灣官場丟不開對上級玩模糊文字遊戲以邀功或自保的毛病,在報告中刻意省略或淡化逆耳之詞的情況必多。美國官僚使用枯燥、精確的文字記錄,而他們也沒有蓄意留下不實文字的動機。
運用美國的檔案,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優點:可以看到美國政府內部考慮問題的角度,包括不同部門及個人的立場。這些內部的思考,無法正確反映在台灣的文件檔案,因為美國提出交涉的立場是已經定案的政策,他們不會把它真正的考慮全部告知對方。
我選這十個題目,完全是從台灣的角度來衡量。我要寫與台灣最直接有關的重要問題,而不是在美國對「華」政策上去費的功夫。不錯,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最直接衝擊到台灣,但是,參與美國對「華」政策改變的當事人,在機密檔案未公開前,都已經寫下他們的回憶錄,從尼克森、季辛吉、何志立,到卡特、范錫、布瑞辛斯基都有詳細的描述。在沒有新資料的情況下,這些角度已經被過分重複。
對台灣而言,不論是冷戰時代、後冷戰時代、威權時代或民主時代,與美關係還是保持安全與和平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儘管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前讀小學的人,都唱過「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的歌,也聽過、看過多少「今年是反攻大陸年」「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與標語,實際上,美國外交官認為蔣介石克服中共在大陸上當權的機會,在馬歇爾調停失敗後便告消失。
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對台灣安全是重要的一件事。雖然在條約簽訂後,「反攻大陸」的口號仍在喊,但那已是假象:葉公超與杜勒斯的換文,向美國重申保證「未經美國同意,不對大陸發動攻擊性行動」。杜勒斯是反共大將,但他苦口婆心,要蔣介石「忍耐」,他「反攻大陸」的希望只有在大陸發生革命、中共政權分裂或共黨對外擴張引發大戰時,才有可能。
美國要蔣介石聽清楚的是:「我可以保護你」;條約是純防衛性質,但「你不能先動手去打人」。如果要發生戰爭,最重要的是要讓對方先動手,而不要因為自由世界先挑起。
現在看起來似乎很矛盾可笑,但在美國支持中華民國政府最力的時候,其承認在台北的政府代表中國,警告中共不能侵犯台灣。它明知台灣沒有它的支持不可能「反攻大陸」,但它也要不斷提醒蔣介石,不能對大陸用武,台海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華府擔心的是被蔣介石拖入與中共的戰爭。
現在情勢轉變,美國承認的是北京政府,但得要警告中共不能對台灣使用武力。美國片面保證台灣安全,同時也要求台灣不能做出可能引發台海衝突的行動。不論是「反攻大陸」「解放台灣」,都與美國所主張「和平解決」分歧的政策利益相抵觸,都會受到美國的阻力。美國可以防衛台灣抗拒武力侵犯,但它不能容許台灣先動手犯人,把美國拉入不是自己選擇的戰爭。
在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後,美國在一九五○年代應付了兩次台海衝突,它使用嚇阻、勸蔣介石撤離外島、恢復與中共會談、外島問題提交聯合國、請第三國對中共說明美國立場等措施,最重要的目的在緩和緊張,避免被捲入台海衝突。
國民黨沒有能力「反攻大陸」,美國人看得很清楚,即便台灣內部文臣如葉公超、武將如王叔銘,也看得很清楚。甘迺迪雖然怕蔣介石在「反攻無望」的刺激下妄動,把美國拖下水,而避免斷然否定他的行動準備;但還是警告他的行動必須建立在可靠之情報上,而不是一廂情願的「希望」。甘迺迪派駐台北的大使柯克,與蔣介石連吵三場,強調蔣介石須受共同防禦條約換文的約束,打破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夢。
一九六四年,中共試爆核子武器,一九六五年,蔣經國第三次訪美,提出蔣介石「反攻大西南」的計畫當然被華府壓下,以後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便被逼到自身難保的處境。美國外交官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台灣人」未獲公平政治參與的問題,但也看出中華民國不可避免的「台灣化」走向。本書〈台灣、台灣政治與台灣人〉及〈台灣化與蔣經國的台灣人〉兩章,便是從美國外交官的密檔中,看這種歷史演變。
蔣經國最後一次訪美遇刺及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對台灣造成極大衝擊,也加速「台灣化」的腳步。聯合國代表權保衛戰、台北官方的公開聲明及實際的運作,顯出台北並不是像它表面那麼嘴硬。美國外交密檔透露的是:台北以對內交代的理由,要表示反對雙重代表權案,但希望友邦聽了就算,不必當真;台北還是希望他們支持雙重代表權案,即使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讓給中共都可以。
那二十幾年的交涉往來,參與的人物不少,他們的言詞、思考、行動也在密檔中顯現。我並不想去評論他們的是非功過,我只是讓他們思考、動作的歷史真相還原,以幫助我們了解那個時代,也可能幫助我們更了解這個時代。
經過幾十年戰亂流離,有千千萬萬人的命運受到不可抗拒的轉折,他們的夢、他們的希望都被犧牲。經過那階段的人,有權利知道那段事實真相。
沒有經過那個階段的人,也有權利知道那個時代的真相,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更了解台灣的歷史演變,更清楚的看出台灣的處境,及「那個時代也有明智之士,為台灣的生存及免於落入中共之手」有長遠性的思考。
這本書滿足了個人寫「內幕」的職業性願望,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在台灣的人民,透過對戒嚴時代這段歷史真相的認識,會更珍惜、熱愛和奉獻台灣這塊土地
從事新聞工作者,都希望能寫點「內幕」,因為人都有好奇心,「內幕」不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且,可以滿足更多讀者的好奇心。
但是真正可信的「內幕」不多,在自由、開放的社會如此,在缺乏自由的社會更是如此。在自由社會,雖然言論、寫作不受政治干預,但是,因為新聞工作者所要寫的「內幕」,並不是自己直接參與,而是「他說」「她說」的組合。
這並不是說經過轉述的「內幕」都不可靠,但毫無疑問的,當事人在轉述時,即使再求公正,也會因為認知、記憶、立場、利益、保護自己、衛護友人等各種不同因素而發生偏差。更糟的是有的人會存心誤導,扭曲真相。
在沒有新聞自由的集權、威權統治下,新聞工作者和媒體都是統治者的宣傳工具,那更談不上能寫什麼「內幕」。
我在威權時代開始新聞工作,到美國進修之前,採訪外交新聞。那時尼克森已宣布一九七二年要訪問北京,而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眼看難保。雖然外交界知道局面不利,應有務實做法,但這種話,誰也不敢對媒體說。如果引用一點外國媒體,或外國政府的觀察,那已經很「內幕」了。
威權時代的政治、外交新聞,大部分屬「宣傳」,目的在粉飾太平,不讓民眾知道事實真相,和它所代表的意義。
到美國鄉下密蘇里大學進修時,選了兩門美國外交史,開始了解和接觸美國外交關係檔案。舒勒教授一有假日便前往華府查閱新解密之檔案的精神,更使我印象深刻。
美國外交關係文件,在解密後均由該國國務院歷史室編選成書出版,尚未及出版或未被編選的文件,開放供研究者查閱。在一九八○年代美國預算還寬裕時,採訪國務院的外交記者可以優先免費取得新出版的外交關係文件,後來這種待遇取消,需要者可以到歷史室查閱,或自己購取。
在戒嚴體制下,每天看官樣文章、表面聲明的新聞工作者,能接觸到真正「機密」的文件,內心的興奮與激動,實難以形容,即使那些「機密」已是二、三十年前舊事。翻閱舊檔,看美國外交官如何思考問題、蔣介石時代的外交官如何與美國交涉、得到何種回應,成了自己的一種嗜好。那也滿足了自己在威權時代無法滿足的好奇心。
新聞工作者的任務是要採訪「現在」,但我業餘卻在採訪「歷史」。「現在」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不容易得到「真相大白」;「歷史」屬「俱往矣」的大事,有真正檔案可查,重建真相還較可為。
我把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三年間,美國與台灣的十件大事,寫成這本書,目的在使歷史真相能還原。一九七三年的截期並不是我的選擇,那只是美國外交檔案經解密可供研究的資料,目前(初版成書為二○○○年)只到一九七三年。但那也是一個很有意義、很重要的階段,因為自一九七○年代開始,台灣處境日艱,美國對華政策轉向,蔣介石健康惡化,「革新保台」之聲高張,而蔣經國走到前台,繼承他父親主導台灣政局。
這不是一本學術性的歷史書,因為我使用的資料主要是美國已出版或當時公開,但尚未出版的檔案。我並沒有機會接觸到台灣的檔案文件,也沒有引述像已故駐美大使顧維鈞回憶錄中,對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談判,及因應台海危機的第一手描述。正如書名所言,我只是「採訪歷史」。
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七三年那個時空背景及不同的政治體制及官場文化,我相信美國政府檔案的記載,應該比台灣的文件可信。台灣官場丟不開對上級玩模糊文字遊戲以邀功或自保的毛病,在報告中刻意省略或淡化逆耳之詞的情況必多。美國官僚使用枯燥、精確的文字記錄,而他們也沒有蓄意留下不實文字的動機。
運用美國的檔案,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優點:可以看到美國政府內部考慮問題的角度,包括不同部門及個人的立場。這些內部的思考,無法正確反映在台灣的文件檔案,因為美國提出交涉的立場是已經定案的政策,他們不會把它真正的考慮全部告知對方。
我選這十個題目,完全是從台灣的角度來衡量。我要寫與台灣最直接有關的重要問題,而不是在美國對「華」政策上去費的功夫。不錯,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最直接衝擊到台灣,但是,參與美國對「華」政策改變的當事人,在機密檔案未公開前,都已經寫下他們的回憶錄,從尼克森、季辛吉、何志立,到卡特、范錫、布瑞辛斯基都有詳細的描述。在沒有新資料的情況下,這些角度已經被過分重複。
對台灣而言,不論是冷戰時代、後冷戰時代、威權時代或民主時代,與美關係還是保持安全與和平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儘管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前讀小學的人,都唱過「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的歌,也聽過、看過多少「今年是反攻大陸年」「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與標語,實際上,美國外交官認為蔣介石克服中共在大陸上當權的機會,在馬歇爾調停失敗後便告消失。
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對台灣安全是重要的一件事。雖然在條約簽訂後,「反攻大陸」的口號仍在喊,但那已是假象:葉公超與杜勒斯的換文,向美國重申保證「未經美國同意,不對大陸發動攻擊性行動」。杜勒斯是反共大將,但他苦口婆心,要蔣介石「忍耐」,他「反攻大陸」的希望只有在大陸發生革命、中共政權分裂或共黨對外擴張引發大戰時,才有可能。
美國要蔣介石聽清楚的是:「我可以保護你」;條約是純防衛性質,但「你不能先動手去打人」。如果要發生戰爭,最重要的是要讓對方先動手,而不要因為自由世界先挑起。
現在看起來似乎很矛盾可笑,但在美國支持中華民國政府最力的時候,其承認在台北的政府代表中國,警告中共不能侵犯台灣。它明知台灣沒有它的支持不可能「反攻大陸」,但它也要不斷提醒蔣介石,不能對大陸用武,台海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華府擔心的是被蔣介石拖入與中共的戰爭。
現在情勢轉變,美國承認的是北京政府,但得要警告中共不能對台灣使用武力。美國片面保證台灣安全,同時也要求台灣不能做出可能引發台海衝突的行動。不論是「反攻大陸」「解放台灣」,都與美國所主張「和平解決」分歧的政策利益相抵觸,都會受到美國的阻力。美國可以防衛台灣抗拒武力侵犯,但它不能容許台灣先動手犯人,把美國拉入不是自己選擇的戰爭。
在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後,美國在一九五○年代應付了兩次台海衝突,它使用嚇阻、勸蔣介石撤離外島、恢復與中共會談、外島問題提交聯合國、請第三國對中共說明美國立場等措施,最重要的目的在緩和緊張,避免被捲入台海衝突。
國民黨沒有能力「反攻大陸」,美國人看得很清楚,即便台灣內部文臣如葉公超、武將如王叔銘,也看得很清楚。甘迺迪雖然怕蔣介石在「反攻無望」的刺激下妄動,把美國拖下水,而避免斷然否定他的行動準備;但還是警告他的行動必須建立在可靠之情報上,而不是一廂情願的「希望」。甘迺迪派駐台北的大使柯克,與蔣介石連吵三場,強調蔣介石須受共同防禦條約換文的約束,打破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夢。
一九六四年,中共試爆核子武器,一九六五年,蔣經國第三次訪美,提出蔣介石「反攻大西南」的計畫當然被華府壓下,以後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便被逼到自身難保的處境。美國外交官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台灣人」未獲公平政治參與的問題,但也看出中華民國不可避免的「台灣化」走向。本書〈台灣、台灣政治與台灣人〉及〈台灣化與蔣經國的台灣人〉兩章,便是從美國外交官的密檔中,看這種歷史演變。
蔣經國最後一次訪美遇刺及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對台灣造成極大衝擊,也加速「台灣化」的腳步。聯合國代表權保衛戰、台北官方的公開聲明及實際的運作,顯出台北並不是像它表面那麼嘴硬。美國外交密檔透露的是:台北以對內交代的理由,要表示反對雙重代表權案,但希望友邦聽了就算,不必當真;台北還是希望他們支持雙重代表權案,即使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讓給中共都可以。
那二十幾年的交涉往來,參與的人物不少,他們的言詞、思考、行動也在密檔中顯現。我並不想去評論他們的是非功過,我只是讓他們思考、動作的歷史真相還原,以幫助我們了解那個時代,也可能幫助我們更了解這個時代。
經過幾十年戰亂流離,有千千萬萬人的命運受到不可抗拒的轉折,他們的夢、他們的希望都被犧牲。經過那階段的人,有權利知道那段事實真相。
沒有經過那個階段的人,也有權利知道那個時代的真相,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更了解台灣的歷史演變,更清楚的看出台灣的處境,及「那個時代也有明智之士,為台灣的生存及免於落入中共之手」有長遠性的思考。
這本書滿足了個人寫「內幕」的職業性願望,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在台灣的人民,透過對戒嚴時代這段歷史真相的認識,會更珍惜、熱愛和奉獻台灣這塊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