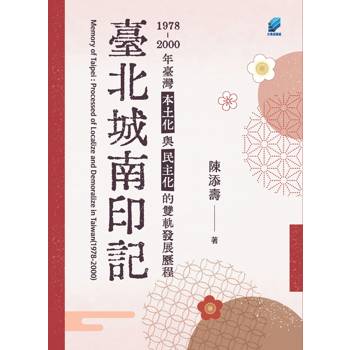第一部分 溫州街「名人居」印記(節錄)
〈從臺南鄉下到臺北名巷〉
1978年秋,我還在臺南市後壁區下茄苳老家附近的一所學校教書,比較有機會可以參與地方活動,也因為縣長楊寶發先生的厚愛,當時讓我接觸省主席謝東閔先生、前臺南縣議長戴再生先生、現任議長陳三元先生、中國國民黨縣黨部主委李讚成先生等地方重要人士。
到現在,我一直都妥善保存一張當時臺南縣長公家宿舍拍的照片,時間是1978年,蔣經國先生挑選當時的臺灣省主席謝東閔先生搭配總統大選前後。從這時間之前,經國先生推動「吹臺青」本土化政策,應屬第一階段;之後,楊寶發先生、李讚成先生等人應屬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也是最後階段應該已經是來到1978年年底之後的發展了。
我是在這一時間離開臺南教書,在親友滿滿寄望和祝福下,北上投入新的工作環境,落腳在臺北溫州街的小巷,展開我人生的另一段生活。是年5月,蔣經國、謝東閔就任總統、副總統;12月,美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致使預定進行的立法委員選舉不得不暫停。我何其有幸在國家政經面臨重大轉變的關鍵時刻躬逢其盛。
在臺南教書的這段時間,我與楊寶發縣長有了比較長時間的相處,我從他的為人處事學習了很多,也多多少少因此了解當時國家發展面臨的艱難與複雜環境。他鼓勵我再進修,我也表達我亦正有此意,只是當時南部再進修的機會較少。
年輕的我,記得大學時期讀到美國文學家梭羅在《湖濱散記》的一段話:「一個人如不能追隨同伴的腳步,或許是因為他聽到不同的鼓聲,就讓他跟隨自己所聽到的音樂繼續前進吧,不管有多遠。」這句話深深地印烙在我腦海裡。
正如有些人步伐與人不同,那是因為他聽到了遠方的鼓聲。有次,楊縣長從臺北開會回來,說他有位「革命實踐研究院」國建班3期的同學,其服務單位有個缺額,希望找位年輕朋友來幫忙。楊縣長說他已推薦我去應徵,要我把履歷和發表過的作品一起寄過去。
等先審核資料通過,再作筆試,並且由該單位負責人馬星野主任委員面試通過後,我才束裝北上,於是那年的12月1日正式到職上班。之後,我也真正深入了解到當年蔣經國先生,為什麼要辦理「國家建設研究班」的目的,和他為培養未來國家政經人才的苦心,以及他經常下鄉親近地方人士的初心與深意。
當年經國先生在「革命實踐研究院」開辦國建班,主要是承襲他父親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之前所辦理「黨政軍聯合作戰班」的成功經驗而來。在蔣經國主導和充分信任下,負責當年執行「革命實踐研究院」重要幹部訓練任務的承辦人,正是之後曾受拔擢擔任行政院長的李煥先生。
李煥先生當時可用「紅遍半邊天」的炙手可熱來形容,他不但是國民黨的「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同時身兼「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一組」(後來改組為組織工作會)主任,可說是集這三個重要單位的職權於一身。
當年「革命實踐研究院」是負責訓練黨政軍警重要領導幹部的單位,在戒嚴黨國體制一體的時期,黨政軍警等重要職務的調升,幾乎都要具備有受過該單位訓練資格的人士來擔任。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則是負責全國大專院校、高中學校的團務活動,在各學校、縣市也都分別設立青年救國團組織和青年活動中心,青年學生最想參加的是救國團舉辦的寒暑假的冬夏令營活動。1960年代前後,當我們念高中的時候,同學大部分就都已有過參與了該團舉辦青年活動的體驗。
「中央黨部一組」,或是後來改稱的「組織工作會」,更是負責黨組織的選舉提名,和輔選的動員工作。在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的資深監察委員、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尚未改選之前,所有各縣市長、省縣市議員等民意機構,和各農漁水利會等社會團體幹部,都要經由「中央黨部一組」,即是國民黨大陸時期的「中央組織部」,也就是後來所稱「組織工作會」來負責執行這項任務。
「革命實踐研究院」、「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中央黨部一組」,這三個單位是蔣經國鞏固權力,重視政治菁英,推動本土化的重要單位。李煥先生的擔任這三個單位的主任,一直要到1977年的縣市長選舉,因為爆發了「中壢事件」之後,李煥先生才被調離這三個職務。
我們檢視蔣經國自從1971年擔任行政院長以來,乃至於國民黨主席、中華民國總統的階段,他所重用的謝東閔、連震東、林洋港、邱創煥、李登輝,而後的張豐緒、連戰、陳奇祿、楊寶發等,乃至於「本土化」政策最後階段的全面提升地方基層黨務工作人員的素質,再再證實蔣經國「吹臺青」的「本土化」政策,是有助於中華民國與臺灣重大發展的連結。(2021-02-25)
〈張道藩蔣碧微與「中國文藝協會」〉
我會落腳在溫州街,主要是辦公室同仁的介紹,當時我對於當地的環境並不熟,但聽說它就位近公館的臺灣大學,即引發我的興趣,並前往了解屋況和居家附近的環境。
對溫州街鄰近臺灣大學的好感,始於我對於臺灣大學自由學風和學習環境的嚮往,可是臺灣大學對於我而言,真如俗話所稱的「校門太窄」,感嘆自己無緣能進入就讀。但我自青少年時期即閱讀胡適、傅斯年、殷海光、李敖等多位學人的作品,對於學術文化仍難忘情,想到可以選擇住在溫州街,也算是一種虛榮心的滿足吧!
記得自己高中、大學時期的閱讀胡適、傅斯年、殷海光、李敖等人的作品,也買了許多有關於他們和自由主義方面的著作,尤其對於《自由中國》和《文星》等雜誌的印象特別深刻。
諸如文星書店出版的《胡適選集》、《傅斯年選集》、《傳統下的獨白》、《胡適評傳》等等。尤其喜歡《傅斯年選集》收錄傅斯年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的談論〈自由與平等〉,與《大公報》〈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等多篇的評論性文章。
傅斯年先生承襲胡適先生的自由主義思想,其與曾任國防部長俞大維之間的親戚關係,以及俞大維先生在「八二三炮戰」中的表現,他們倆人都曾住過的臺灣大學校長宿舍,都讓我對溫州街當時的名聲產生了一些連結。
最後決定買房住居溫州街的另外重要原因,是它位置在羅斯福路、新生南路和辛亥路的交叉點附近,交通便利。當時內人上班的地點就在溫州街對面的羅斯福路上,而我要到金華街「月涵堂」辦公室上班也只要一趟公車即可抵達。
1980年代前後的溫州街,沒有如現在已經興蓋完成的臺電大樓、臺北信友堂,和溫州國宅等比較具代表性的明顯建物。尤其溫州國宅當時還是臺大教職員的宿舍,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日式建築居多。
印象中當時比較顯目的大樓,只有在羅斯福路三段281號附近的羅斯福路大廈。當初我對這棟大廈沒有特殊的印象,可是在我住溫州街後不久,有天我路過這棟大廈,我心想這裡面到底是住了哪些人家或公司行號,於是我特別走近仔細看了一樓層所掛住戶的牌板,赫然發現「中國文藝協會」字樣的名牌。
「中國文藝協會」突然讓我回憶起1970年代初期,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因為喜歡閱讀和買書。記得有一年的書展,我已經記不起來舉辦的地點是在耕莘文教院,或是在羅斯福大廈的「中國文藝協會」,但是那場文藝性質的書展,還吸引我特地從新莊的輔仁大學宿舍,輾轉乘車趕到溫州街這附近的地方來。
後來也因為張道藩曾任「中國文藝協會」理事長的這層關係,我腦子裡有了張道藩這位政治與文藝人物的印象。巧的是在一個偶然機會,聽到與我住同棟公寓,曾任蔣彥士秘書長的錢仲鳴秘書,他告訴我當時有關張道藩擔任立法院長時,與蔣碧微女士就住這裡,更讓溫州街這裡令人有更多的好奇。我在《近代名人文化記述》,和《筆記與對話:臺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都還特別詳細敘及。
張道藩與蔣碧微剛到臺灣來的時候,有一段時間,他們是一起住在張道藩擔任立法院院長住的日式房子,這正是溫州街96巷10號。他們更妙的是一個大門,右邊門牌掛「張道藩寓」,左邊掛「蔣碧微寓」,很容易就被人聯想,形容他們是過「神仙生活」。
張道藩蔣碧微與徐悲鴻之間的複雜愛情故事,早已在政治文化圈傳聞已久。尤其《蔣碧微回憶錄》上篇寫的是《我與徐悲鴻》,下篇寫的是《我與張道藩》的愛情描述。
特別是在這篇〈卻道海棠依舊〉的晚年回憶文字,真讓人會「問世間情何物」?也更人對照聯想張道藩與蔣碧微他們兩人來臺之後,一起住在溫州街生活的這段「悲滄歲月」來。(2021-03-04)
〈郎靜山與林絲緞舞蹈社〉
現在羅斯福路三段283巷,在30多年前的景點,除了溫州公園,和臺電宿舍內的加羅林魚木等這兩個地點最為有名氣,特別引起大家的注意與興趣。
這棵醒目又美麗的加羅林魚木,當年是種植在臺電公司宿舍的圍牆內,隨著知名度的打開,吸引許多賞花者和攝影師來此地。現在已不再專屬於臺電公司的獨享,而改為公共空間的提供大家可以自由觀賞活動,和備有座椅成為可以休閒的景點。
溫州公園近年來的加以整理和美化,更是讓溫州街成為臺北市區重要方位的指標之一。猶記得當年內人坐月子期間,家父從臺南後壁下茄苳老家上臺北來探望他三媳婦和孫女。
當下車轉搭計程車時,家父向計程車司機說「溫州公園」,或許是因為家父受日本教育,講的是臺灣國語,司機竟然將家父直接就載到「恩主公」(臺語行天宮的稱呼),我們得費一番工夫向司機解釋清楚後,家父和他特地攜帶上來,而且已經過處理乾淨好的七隻雞,才得以順利抵達溫州街的家。
我住283巷的期間,有天在附近的一棟公寓樓上掛著「林絲緞舞蹈社」的招牌,讓我想起1960年代中期我念高中時候買林絲緞小姐寫的《我的模特兒生涯》。這書1965年由「文星書店」出版,而當年我對於這位勇於挑戰社會,開國內專業人體模特兒風氣之先,後又習舞蹈的傑出女性,印象極為深刻。
2009年6月7日《中國時報》刊出,林絲緞小姐接受專訪的記述,林絲緞說20幾年前,她在溫州街開設舞蹈教室,以啟發式舞蹈為特色。這時候我也才更深入了解,她在夫婿李哲洋於1990年過世之後,她將李哲洋遺留下來的音樂史料七十大箱捐給藝術學院(今臺北藝術大學),來嘉惠有志於臺灣音樂歷史研究的後繼者。
以此推算,「林絲緞舞蹈社」這時間正是1980-90年代,我家住溫州街的時期,只是我家小孩沒有從林絲緞老師的學習舞蹈,而是在住家附近武功國小的老師家學書法、鋼琴等其他方面的才藝課程。
林絲緞《我的模特兒生涯》中有段文字:
攝影界要想徵求一個模特兒都還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當時,我在雕塑家楊英風先生那?兼職,他誠意的要求我為一位很有聲譽的攝影家服務,我總算答應了,這就是我進入攝影界的開始。我第一次替他服務的這位攝影家,就是那位以奇特技法聞名於世的郎靜山先生。
上述這段文字敘述的時間,當是1960年代前後發生的事。1970年代後期,乃至於1980年代我從住家走出來,繞過溫州街加羅林魚木往臺灣大學校園的路上,特別是在86巷附近,我經常可以遇一位總是一襲青衫,或是長袍馬褂,他的這身穿著和獨特相貌,加上蓄鬍,從遠而近的擦身而過,很容易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來是攝影大師郎靜山先生。
我想我可以確定這時期的郎先生曾住過溫州街,但我不能確定他是住溫州街86巷的公寓,或是臺灣大學教職員宿舍所改建的國宅大樓裡。記憶中我家小孩學繪畫的麥老師(其家人開設老麥攝影社)授課地點,就在臺大教授宿舍改建的溫州國宅大樓裡,偶爾會看見郎先生在附近進出。
郎靜山先生是以中國山水式的集錦攝影著稱,1949年來到臺灣之後,也拍了許多當時黨政軍、商、社會文化各層面的名流名士,如張大千與蔣經國、溥心畬與京劇名伶焦鴻英的合影,特別是拍攝一幀著名電影明星李麗華的嫵媚照等等。
相較於郎先生的拍攝林絲緞照片,許多人因為從來沒有見過郎先生有半裸女的作品,就對林絲緞上述的話懷疑起來,林絲緞自己想這也許是當時因為限於經驗,未能使郎先生完成一幀理想的作品的緣故。(2021-03-08)
〈從臺南鄉下到臺北名巷〉
1978年秋,我還在臺南市後壁區下茄苳老家附近的一所學校教書,比較有機會可以參與地方活動,也因為縣長楊寶發先生的厚愛,當時讓我接觸省主席謝東閔先生、前臺南縣議長戴再生先生、現任議長陳三元先生、中國國民黨縣黨部主委李讚成先生等地方重要人士。
到現在,我一直都妥善保存一張當時臺南縣長公家宿舍拍的照片,時間是1978年,蔣經國先生挑選當時的臺灣省主席謝東閔先生搭配總統大選前後。從這時間之前,經國先生推動「吹臺青」本土化政策,應屬第一階段;之後,楊寶發先生、李讚成先生等人應屬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也是最後階段應該已經是來到1978年年底之後的發展了。
我是在這一時間離開臺南教書,在親友滿滿寄望和祝福下,北上投入新的工作環境,落腳在臺北溫州街的小巷,展開我人生的另一段生活。是年5月,蔣經國、謝東閔就任總統、副總統;12月,美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致使預定進行的立法委員選舉不得不暫停。我何其有幸在國家政經面臨重大轉變的關鍵時刻躬逢其盛。
在臺南教書的這段時間,我與楊寶發縣長有了比較長時間的相處,我從他的為人處事學習了很多,也多多少少因此了解當時國家發展面臨的艱難與複雜環境。他鼓勵我再進修,我也表達我亦正有此意,只是當時南部再進修的機會較少。
年輕的我,記得大學時期讀到美國文學家梭羅在《湖濱散記》的一段話:「一個人如不能追隨同伴的腳步,或許是因為他聽到不同的鼓聲,就讓他跟隨自己所聽到的音樂繼續前進吧,不管有多遠。」這句話深深地印烙在我腦海裡。
正如有些人步伐與人不同,那是因為他聽到了遠方的鼓聲。有次,楊縣長從臺北開會回來,說他有位「革命實踐研究院」國建班3期的同學,其服務單位有個缺額,希望找位年輕朋友來幫忙。楊縣長說他已推薦我去應徵,要我把履歷和發表過的作品一起寄過去。
等先審核資料通過,再作筆試,並且由該單位負責人馬星野主任委員面試通過後,我才束裝北上,於是那年的12月1日正式到職上班。之後,我也真正深入了解到當年蔣經國先生,為什麼要辦理「國家建設研究班」的目的,和他為培養未來國家政經人才的苦心,以及他經常下鄉親近地方人士的初心與深意。
當年經國先生在「革命實踐研究院」開辦國建班,主要是承襲他父親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之前所辦理「黨政軍聯合作戰班」的成功經驗而來。在蔣經國主導和充分信任下,負責當年執行「革命實踐研究院」重要幹部訓練任務的承辦人,正是之後曾受拔擢擔任行政院長的李煥先生。
李煥先生當時可用「紅遍半邊天」的炙手可熱來形容,他不但是國民黨的「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同時身兼「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一組」(後來改組為組織工作會)主任,可說是集這三個重要單位的職權於一身。
當年「革命實踐研究院」是負責訓練黨政軍警重要領導幹部的單位,在戒嚴黨國體制一體的時期,黨政軍警等重要職務的調升,幾乎都要具備有受過該單位訓練資格的人士來擔任。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則是負責全國大專院校、高中學校的團務活動,在各學校、縣市也都分別設立青年救國團組織和青年活動中心,青年學生最想參加的是救國團舉辦的寒暑假的冬夏令營活動。1960年代前後,當我們念高中的時候,同學大部分就都已有過參與了該團舉辦青年活動的體驗。
「中央黨部一組」,或是後來改稱的「組織工作會」,更是負責黨組織的選舉提名,和輔選的動員工作。在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的資深監察委員、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尚未改選之前,所有各縣市長、省縣市議員等民意機構,和各農漁水利會等社會團體幹部,都要經由「中央黨部一組」,即是國民黨大陸時期的「中央組織部」,也就是後來所稱「組織工作會」來負責執行這項任務。
「革命實踐研究院」、「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中央黨部一組」,這三個單位是蔣經國鞏固權力,重視政治菁英,推動本土化的重要單位。李煥先生的擔任這三個單位的主任,一直要到1977年的縣市長選舉,因為爆發了「中壢事件」之後,李煥先生才被調離這三個職務。
我們檢視蔣經國自從1971年擔任行政院長以來,乃至於國民黨主席、中華民國總統的階段,他所重用的謝東閔、連震東、林洋港、邱創煥、李登輝,而後的張豐緒、連戰、陳奇祿、楊寶發等,乃至於「本土化」政策最後階段的全面提升地方基層黨務工作人員的素質,再再證實蔣經國「吹臺青」的「本土化」政策,是有助於中華民國與臺灣重大發展的連結。(2021-02-25)
〈張道藩蔣碧微與「中國文藝協會」〉
我會落腳在溫州街,主要是辦公室同仁的介紹,當時我對於當地的環境並不熟,但聽說它就位近公館的臺灣大學,即引發我的興趣,並前往了解屋況和居家附近的環境。
對溫州街鄰近臺灣大學的好感,始於我對於臺灣大學自由學風和學習環境的嚮往,可是臺灣大學對於我而言,真如俗話所稱的「校門太窄」,感嘆自己無緣能進入就讀。但我自青少年時期即閱讀胡適、傅斯年、殷海光、李敖等多位學人的作品,對於學術文化仍難忘情,想到可以選擇住在溫州街,也算是一種虛榮心的滿足吧!
記得自己高中、大學時期的閱讀胡適、傅斯年、殷海光、李敖等人的作品,也買了許多有關於他們和自由主義方面的著作,尤其對於《自由中國》和《文星》等雜誌的印象特別深刻。
諸如文星書店出版的《胡適選集》、《傅斯年選集》、《傳統下的獨白》、《胡適評傳》等等。尤其喜歡《傅斯年選集》收錄傅斯年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的談論〈自由與平等〉,與《大公報》〈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等多篇的評論性文章。
傅斯年先生承襲胡適先生的自由主義思想,其與曾任國防部長俞大維之間的親戚關係,以及俞大維先生在「八二三炮戰」中的表現,他們倆人都曾住過的臺灣大學校長宿舍,都讓我對溫州街當時的名聲產生了一些連結。
最後決定買房住居溫州街的另外重要原因,是它位置在羅斯福路、新生南路和辛亥路的交叉點附近,交通便利。當時內人上班的地點就在溫州街對面的羅斯福路上,而我要到金華街「月涵堂」辦公室上班也只要一趟公車即可抵達。
1980年代前後的溫州街,沒有如現在已經興蓋完成的臺電大樓、臺北信友堂,和溫州國宅等比較具代表性的明顯建物。尤其溫州國宅當時還是臺大教職員的宿舍,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日式建築居多。
印象中當時比較顯目的大樓,只有在羅斯福路三段281號附近的羅斯福路大廈。當初我對這棟大廈沒有特殊的印象,可是在我住溫州街後不久,有天我路過這棟大廈,我心想這裡面到底是住了哪些人家或公司行號,於是我特別走近仔細看了一樓層所掛住戶的牌板,赫然發現「中國文藝協會」字樣的名牌。
「中國文藝協會」突然讓我回憶起1970年代初期,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因為喜歡閱讀和買書。記得有一年的書展,我已經記不起來舉辦的地點是在耕莘文教院,或是在羅斯福大廈的「中國文藝協會」,但是那場文藝性質的書展,還吸引我特地從新莊的輔仁大學宿舍,輾轉乘車趕到溫州街這附近的地方來。
後來也因為張道藩曾任「中國文藝協會」理事長的這層關係,我腦子裡有了張道藩這位政治與文藝人物的印象。巧的是在一個偶然機會,聽到與我住同棟公寓,曾任蔣彥士秘書長的錢仲鳴秘書,他告訴我當時有關張道藩擔任立法院長時,與蔣碧微女士就住這裡,更讓溫州街這裡令人有更多的好奇。我在《近代名人文化記述》,和《筆記與對話:臺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都還特別詳細敘及。
張道藩與蔣碧微剛到臺灣來的時候,有一段時間,他們是一起住在張道藩擔任立法院院長住的日式房子,這正是溫州街96巷10號。他們更妙的是一個大門,右邊門牌掛「張道藩寓」,左邊掛「蔣碧微寓」,很容易就被人聯想,形容他們是過「神仙生活」。
張道藩蔣碧微與徐悲鴻之間的複雜愛情故事,早已在政治文化圈傳聞已久。尤其《蔣碧微回憶錄》上篇寫的是《我與徐悲鴻》,下篇寫的是《我與張道藩》的愛情描述。
特別是在這篇〈卻道海棠依舊〉的晚年回憶文字,真讓人會「問世間情何物」?也更人對照聯想張道藩與蔣碧微他們兩人來臺之後,一起住在溫州街生活的這段「悲滄歲月」來。(2021-03-04)
〈郎靜山與林絲緞舞蹈社〉
現在羅斯福路三段283巷,在30多年前的景點,除了溫州公園,和臺電宿舍內的加羅林魚木等這兩個地點最為有名氣,特別引起大家的注意與興趣。
這棵醒目又美麗的加羅林魚木,當年是種植在臺電公司宿舍的圍牆內,隨著知名度的打開,吸引許多賞花者和攝影師來此地。現在已不再專屬於臺電公司的獨享,而改為公共空間的提供大家可以自由觀賞活動,和備有座椅成為可以休閒的景點。
溫州公園近年來的加以整理和美化,更是讓溫州街成為臺北市區重要方位的指標之一。猶記得當年內人坐月子期間,家父從臺南後壁下茄苳老家上臺北來探望他三媳婦和孫女。
當下車轉搭計程車時,家父向計程車司機說「溫州公園」,或許是因為家父受日本教育,講的是臺灣國語,司機竟然將家父直接就載到「恩主公」(臺語行天宮的稱呼),我們得費一番工夫向司機解釋清楚後,家父和他特地攜帶上來,而且已經過處理乾淨好的七隻雞,才得以順利抵達溫州街的家。
我住283巷的期間,有天在附近的一棟公寓樓上掛著「林絲緞舞蹈社」的招牌,讓我想起1960年代中期我念高中時候買林絲緞小姐寫的《我的模特兒生涯》。這書1965年由「文星書店」出版,而當年我對於這位勇於挑戰社會,開國內專業人體模特兒風氣之先,後又習舞蹈的傑出女性,印象極為深刻。
2009年6月7日《中國時報》刊出,林絲緞小姐接受專訪的記述,林絲緞說20幾年前,她在溫州街開設舞蹈教室,以啟發式舞蹈為特色。這時候我也才更深入了解,她在夫婿李哲洋於1990年過世之後,她將李哲洋遺留下來的音樂史料七十大箱捐給藝術學院(今臺北藝術大學),來嘉惠有志於臺灣音樂歷史研究的後繼者。
以此推算,「林絲緞舞蹈社」這時間正是1980-90年代,我家住溫州街的時期,只是我家小孩沒有從林絲緞老師的學習舞蹈,而是在住家附近武功國小的老師家學書法、鋼琴等其他方面的才藝課程。
林絲緞《我的模特兒生涯》中有段文字:
攝影界要想徵求一個模特兒都還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當時,我在雕塑家楊英風先生那?兼職,他誠意的要求我為一位很有聲譽的攝影家服務,我總算答應了,這就是我進入攝影界的開始。我第一次替他服務的這位攝影家,就是那位以奇特技法聞名於世的郎靜山先生。
上述這段文字敘述的時間,當是1960年代前後發生的事。1970年代後期,乃至於1980年代我從住家走出來,繞過溫州街加羅林魚木往臺灣大學校園的路上,特別是在86巷附近,我經常可以遇一位總是一襲青衫,或是長袍馬褂,他的這身穿著和獨特相貌,加上蓄鬍,從遠而近的擦身而過,很容易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來是攝影大師郎靜山先生。
我想我可以確定這時期的郎先生曾住過溫州街,但我不能確定他是住溫州街86巷的公寓,或是臺灣大學教職員宿舍所改建的國宅大樓裡。記憶中我家小孩學繪畫的麥老師(其家人開設老麥攝影社)授課地點,就在臺大教授宿舍改建的溫州國宅大樓裡,偶爾會看見郎先生在附近進出。
郎靜山先生是以中國山水式的集錦攝影著稱,1949年來到臺灣之後,也拍了許多當時黨政軍、商、社會文化各層面的名流名士,如張大千與蔣經國、溥心畬與京劇名伶焦鴻英的合影,特別是拍攝一幀著名電影明星李麗華的嫵媚照等等。
相較於郎先生的拍攝林絲緞照片,許多人因為從來沒有見過郎先生有半裸女的作品,就對林絲緞上述的話懷疑起來,林絲緞自己想這也許是當時因為限於經驗,未能使郎先生完成一幀理想的作品的緣故。(2021-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