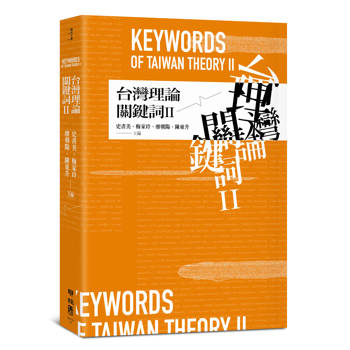縫(Seam)
蘇 榕
台灣位於太平洋邊緣西北側,以台灣海峽與中國大陸相隔;島嶼的地緣性使中國歷代治理的長鞭莫及於傳說中葡萄牙水手讚嘆的「伊拉.福爾摩沙!」此偏踞中國一隅,林木蓊鬱的蒼翠之島,自17世紀原住民建立「大肚王國」以來,歷經荷蘭、西班牙分據殖民城;明鄭驅逐荷蘭人;滿清管轄、日本殖民、國民政府統治等「連續殖民」,以至二戰後美國之為保護勢力,在摹仿(imitation)、刮除覆寫(palimpsest)、與翻譯中邁入21世紀。台灣文化的發展進程在地理、歷史、文化與現代化層面上,分受不同主流文化衝擊而產生「縫」。本文以「縫」(seam)作為隱喻,據以析論台灣文化現象,開發文化策略。由隔而縫具現了台灣位於邊緣的處境:「隔」是物質的阻隔(insulation),也是心理的隔絕(isolation);「縫」(seam)是缺口、裂縫;「縫」(seam)也是縫合的行動。隔/縫互為演化。
以漢字的象形和音義而言,「縫」的篆文寫作: 絲線(糸)+相遇(逢)。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糸部釋義:「縫」乃「以鍼紩衣也。从糸逢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注解:「鍼下曰所縫也。《召南》羔羊之縫。《傳》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宜。引申之意也。從糸。逢聲。符身切。九部」。故「縫」指用針線將兩塊布縫合,是動詞,讀作「逢」(féng),指縫補、縫合、縫綴,有往返穿梭的運動性。《康熙字典》收錄了「縫」的另一讀法:「《廣韻》扶用切《集韻》房用切,𠀤音俸。衣縫也。」。據此「縫」亦可讀作「俸」(fèng),指衣縫、需連合彌補的開口、縫隙等,是名詞。由上可知,「縫」若讀作「逢」,可指縫合、縫補。「縫」若讀作「奉」,可指「裂縫、隙縫、衣縫」。因此「縫」既是行動也是存在,具有物質性(如織品的縫紉、傷口縫合等),也有情感性(如創傷的彌補等)。
「縫」具現了台灣在後殖民/後現代情境下形成的混生特質。「縫」是距離,也是實存。台灣文化除了國民政府黨國體系保存的傳統中華文化外;也在20世紀後半大量吸收了西方現代性以及批判理論思想,西方思潮透過物質與意識形態的滲透,不斷以翻譯形式和力量滲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建制和日常生活。形成(後)殖民國家無可避免的殖民銘刻與再銘刻。台灣文化在斷裂中生成,也在裂縫下接縫。在以圖象為主的中文書寫系統中,隱藏於文字下的「雜腔異調」(史書美以「華語語系」統稱之)僅能閃爍於語言的接縫以求掙脫文字束縛;其多音歧義的異質性或地域性,若非輔以口語讀出,很難呈現眾聲喧嘩的本質。當代中文吸納諸多外國語、非漢族語彙、新創辭彙、混生語等,即興縫入日常生活語言的表達形式,使文化產品,例如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展現了「皇袍上的縐褶」般的接縫,不僅翻譯,更來回穿梭地縫合了主流語言和弱勢語言,以「接縫」方式表現不同語言形式的衝突。下文析論的黃春明小說,即是一個顯例。本文以「縫」作為視覺隱喻,在於具現台灣文化歷經撕裂、分隔、縫合、癒合、再生的韌性、生命力,和創造力。
以上現況,受到西方理論,特別是弱勢族裔論述的推波助瀾,使台灣文化的「縫」現象日益明顯,不斷演化。近代西方文化論述中,班雅明(Walt er Benjamin)、巴巴(Homi K. Bhabha)、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譯作的語言互補性、純粹語言、文化翻譯、縐折等概念促成了文化越界、互補、解疆域、重劃疆域等概念的普及。「縫」也可視為吸納這些概念後的演化。首先,「縫」是類似但不等同於翻譯的行動。因為「縫」具象化了台灣文化在地理、歷史、文化、政治上的特殊性,更標示了台灣的位置性和行動力。
當代台灣文化揉合了原住民文化、中華傳統漢文化、日本殖民文化、美式文化、西方現代性,和東南亞移民文化等多重文化元素,表意模式不斷衝撞縫合。有翻譯、演繹、延異/沿易,也有演化;有撕裂、折衝、協商,也有縫合;有傷痛、癒合、結痂,也有新生,不斷變化。「縫」的隱喻即以此展現台灣文化特有的創造力與韌性,以居間穿梭的運動性跳脫「翻譯←顛覆→霸權」的二元對立,並補充班雅明翻譯理論較少著墨於語言形式和內容的情感成分之空缺。「縫」具有破壞力、裂解性、衝突性,和傷痛感;「縫」也具有中介性、運動性、癒合力,和創造力。「縫」(讀為「奉」)是撕裂、衝撞、分離、演化;「縫」(讀為「逢」)可縫紉、黏合、編織、鋦釘、重組文化的碎瓷殘片為新器皿,縫隙即存在。「縫」從空無至往復運動「拆/合」,蓄積能量,在運動中完成社會實踐。
黃春明、王禎和等台灣小說家的作品,就大量運用了現代主義形式和鄉土經驗,語言裂縫和縫合現象十分明顯。限於篇幅,此處以黃春明的短篇小說〈蘋果的滋味〉為例,說明小說中多元語言的衝突如何戲劇化1970年代的美台權力關係。語言的裂縫與縫合在此小說中可被視為諷刺美國政經優勢和霸權主義的文化策略。黃春明採用當時的主流語言(「國語」/白話文)書寫這個故事;但在他的筆下,小說的敘述語言產生了裂縫、縐折、接縫——台語、英語不時浮現於「國語」的罅隙,成為閃爍於主流語言縫隙的弱勢語言,經過折疊縫合,構成國台英語交織的流暢對話,諷喻了美台強/弱、主/從地位,精準捕捉了「純正國語」難以傳達的庶民情感和後殖民文化情境,反映出70年代美國新殖民主義下台灣底層階級日常生活的現實。「縫」使這篇小說成為語言衝撞抗爭的文化場域。
〈蘋果的滋味〉寫於1972 年,黃春明以工人江阿發騎腳踏車被美國上校的賓士車撞斷腿住院為起點,用喜劇的諷刺口吻,縫合江阿發一家(台灣底層階級)、美國上校格雷和他的二等祕書(美國官方)、外事警察(台灣統治階級)三方的觀點,以台灣工人初嚐(美國)「蘋果」的滋味,對照1960、70年代台灣接受美國物資援助和軍事協防,由農業社會過渡至工商社會的後現代/後殖民情境。就題目而言,〈蘋果的滋味〉不像〈莎喲拉娜.再見〉那般明顯縫合中/日語,卻從感官角度(吃蘋果的滋味)戲劇化美台文化的相遇、衝撞、斷裂、協商,和縫合:台灣底層階級(工人阿發)被美國文化(格雷上校)衝撞(腳踏車被賓士車撞翻)→產生斷裂(阿發的雙腿被撞斷—接合)→協商(透過格雷的二等祕書、外事警察、外國修女的翻譯,格雷表達歉意並賠償阿發一家)→縫合(送阿發的啞巴女兒到美國讀書,和江家作朋友)。這個衝撞→斷裂→協商(翻譯)→縫合的過程,在故事結尾被黃春明用「初嚐蘋果的滋味」(味覺/觸覺/聽覺)和定價方式表達:「總覺得沒有想像那麼甜美,酸酸澀澀,嚼起來泡泡的有點假假的感覺」、「一只蘋果可以買四斤米」、「噗喳噗喳的聲音」,精準地諷喻了小說家欲批判的「美國經濟文化對台灣的支配與控制」。在黃春明精心的安排下,讀者體會到格雷上校的歉意和友善(「他說非常非常的對不起,請你原諒。他說他願意負一切責任,並且希望和你的家庭作朋友」)就像天上掉下來的蘋果,吃起來「有點假假的」,因為小說家一開頭就讓二等祕書說出美方的立場:「是工人!所以說嘛,我們惹不起⋯⋯美國不想雙腳都陷入泥淖裡!」
這些人物使用的英、國、台語之間的翻譯和縫合是〈蘋果的滋味〉精確捕捉現實的功臣,因為這些對話以從屬階級觀點鮮活地反映了當時的台灣情境。黃春明所使用的語言策略,可以被視為一種縫合「國語白話文」、台、英語轉譯成的「國語」,和受外國文學影響的翻譯語言的藝術創作行動。這必須從他早年的文學教育說起。黃春明曾多次提到他最初的文學「爺爺」來自沈從文和契可夫(Anton Chekhov)。此外還有約翰.克里斯多夫(John Christopher)、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馬克.吐溫(Mark Twain)、福克納,和電影的影響。這使他的書寫採用了結合白話文與外國文學翻譯語言的中文寫作,但是產生了裂縫,就是中文與他的母語間的裂隙。
黃春明的書寫縫合了白話文、外國文學翻譯語言、翻譯成白話文的台、日、英語等,依據角色身分和口吻交織運用。以這種方式,他將「鄉土語言,翻譯成主流的書面語」,「讓這些文本可以進入主流場域中,被閱讀及理解」。他考慮用主流語言寫作,以進入主流文化市場。因此他採取折衷辦法,把母語和其他語言翻譯成「國語」,依據說話角色的身分和發話情境,把對話技巧地縫在一起。這種翻譯策略在〈蘋果的滋味〉的人物對話中運用得相當成功。語言的障礙和溝通成為衝突和協商的主要場域,不同語言則透過翻譯縫成有聲有色的畫面,有時刻意露出縫綴褶縫,藉以營造詼諧諷刺的效果。
年輕外事警察帶洋人到江家住的違章建築。敘述事件時,作者使用簡潔流暢的白話文:「密密的雨點打在鐵皮上,造成屋裡很大的噪音,警察不得不叫嚷似的翻譯洋人的話」,之後作者用翻譯和語言縫合來表現阿桂和警察無法以語言溝通的情境:
〔阿桂〕驚慌地問:「阿珠,什麼事?」
「媽——」緊緊抿閉的嘴,一開口禁不住就哭起來。
「什麼事?快說!」
「爸、爸爸,被汽車壓了——」
「啊!爸爸——?在哪裡?在哪裡?……」阿桂的臉一下被扭曲得變形,「在哪裡?……」接著就喃喃唸個不停。
警察用很彆腳的本地話安慰著說:「莫緊啦,免驚啦。」〔斜體字為筆者所加〕他又改用國語向小女孩說:「叫你媽媽不要難過,你也不要哭,他們已經把你爸爸送到醫院急救去了。」洋人在旁很歉疚地說了些話,並且要求警察替他轉告她們。
「這位美國人說他們會負責的,叫你媽媽不要哭。」當他說的時候,洋人走過去把手放在阿珠的頭上,自己頻頻點頭示意,希望她能明白。這時候,那個揹著嬰兒的啞巴女孩,淋了一身雨從外面闖進來。她不知道裡面發生了什麼事,一進門看到剛才遇見的警察和洋人,驚奇地睜大眼睛大聲地連著手勢,咿咿啞啞地叫嚷起來。
…
「噢!上帝。」洋人又一次輕輕地呼叫起來。
這段對話巧妙呈現出美國官方/台灣官方/台灣底層的三角權力關係,以「國語」/閩南語/英語/啞巴的咿啞/肢體語言縫接出彼此無法溝通的困境。在絕大部分的對話都翻譯成「國語」的情況下,黃春明刻意露出主流語言的裂縫(或語言的接縫)——「莫緊啦,免驚啦」——凸顯警察努力說出有限閩南語安慰阿桂,以強化語言不通的臨場感和戲劇效果。警察和阿珠在此扮演了譯者的角色,因為洋人、阿桂、啞巴都聽不懂對方的語言,需要靠這兩枚敘述之針穿針引線,細細密縫。語言的穿梭織縫在此扮演了關鍵角色。若拿掉語言的穿梭縫紉,用「純正」「國語」書寫,「蘋果的滋味」就少了辛辣而平淡無味。這就是「縫」的文化策略成功之處。
黃春明小說的例子說明了以下:「縫」可視為缺裂、罅隙、缺陷,「縫」也可做為運動、行動、實踐。「縫」是在場、佔有、存在。「縫」也是縫合、修補、創造。「縫」是虛實變換/幻的在地文化策略。
蘇 榕
台灣位於太平洋邊緣西北側,以台灣海峽與中國大陸相隔;島嶼的地緣性使中國歷代治理的長鞭莫及於傳說中葡萄牙水手讚嘆的「伊拉.福爾摩沙!」此偏踞中國一隅,林木蓊鬱的蒼翠之島,自17世紀原住民建立「大肚王國」以來,歷經荷蘭、西班牙分據殖民城;明鄭驅逐荷蘭人;滿清管轄、日本殖民、國民政府統治等「連續殖民」,以至二戰後美國之為保護勢力,在摹仿(imitation)、刮除覆寫(palimpsest)、與翻譯中邁入21世紀。台灣文化的發展進程在地理、歷史、文化與現代化層面上,分受不同主流文化衝擊而產生「縫」。本文以「縫」(seam)作為隱喻,據以析論台灣文化現象,開發文化策略。由隔而縫具現了台灣位於邊緣的處境:「隔」是物質的阻隔(insulation),也是心理的隔絕(isolation);「縫」(seam)是缺口、裂縫;「縫」(seam)也是縫合的行動。隔/縫互為演化。
以漢字的象形和音義而言,「縫」的篆文寫作: 絲線(糸)+相遇(逢)。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糸部釋義:「縫」乃「以鍼紩衣也。从糸逢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注解:「鍼下曰所縫也。《召南》羔羊之縫。《傳》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宜。引申之意也。從糸。逢聲。符身切。九部」。故「縫」指用針線將兩塊布縫合,是動詞,讀作「逢」(féng),指縫補、縫合、縫綴,有往返穿梭的運動性。《康熙字典》收錄了「縫」的另一讀法:「《廣韻》扶用切《集韻》房用切,𠀤音俸。衣縫也。」。據此「縫」亦可讀作「俸」(fèng),指衣縫、需連合彌補的開口、縫隙等,是名詞。由上可知,「縫」若讀作「逢」,可指縫合、縫補。「縫」若讀作「奉」,可指「裂縫、隙縫、衣縫」。因此「縫」既是行動也是存在,具有物質性(如織品的縫紉、傷口縫合等),也有情感性(如創傷的彌補等)。
「縫」具現了台灣在後殖民/後現代情境下形成的混生特質。「縫」是距離,也是實存。台灣文化除了國民政府黨國體系保存的傳統中華文化外;也在20世紀後半大量吸收了西方現代性以及批判理論思想,西方思潮透過物質與意識形態的滲透,不斷以翻譯形式和力量滲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建制和日常生活。形成(後)殖民國家無可避免的殖民銘刻與再銘刻。台灣文化在斷裂中生成,也在裂縫下接縫。在以圖象為主的中文書寫系統中,隱藏於文字下的「雜腔異調」(史書美以「華語語系」統稱之)僅能閃爍於語言的接縫以求掙脫文字束縛;其多音歧義的異質性或地域性,若非輔以口語讀出,很難呈現眾聲喧嘩的本質。當代中文吸納諸多外國語、非漢族語彙、新創辭彙、混生語等,即興縫入日常生活語言的表達形式,使文化產品,例如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展現了「皇袍上的縐褶」般的接縫,不僅翻譯,更來回穿梭地縫合了主流語言和弱勢語言,以「接縫」方式表現不同語言形式的衝突。下文析論的黃春明小說,即是一個顯例。本文以「縫」作為視覺隱喻,在於具現台灣文化歷經撕裂、分隔、縫合、癒合、再生的韌性、生命力,和創造力。
以上現況,受到西方理論,特別是弱勢族裔論述的推波助瀾,使台灣文化的「縫」現象日益明顯,不斷演化。近代西方文化論述中,班雅明(Walt er Benjamin)、巴巴(Homi K. Bhabha)、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譯作的語言互補性、純粹語言、文化翻譯、縐折等概念促成了文化越界、互補、解疆域、重劃疆域等概念的普及。「縫」也可視為吸納這些概念後的演化。首先,「縫」是類似但不等同於翻譯的行動。因為「縫」具象化了台灣文化在地理、歷史、文化、政治上的特殊性,更標示了台灣的位置性和行動力。
當代台灣文化揉合了原住民文化、中華傳統漢文化、日本殖民文化、美式文化、西方現代性,和東南亞移民文化等多重文化元素,表意模式不斷衝撞縫合。有翻譯、演繹、延異/沿易,也有演化;有撕裂、折衝、協商,也有縫合;有傷痛、癒合、結痂,也有新生,不斷變化。「縫」的隱喻即以此展現台灣文化特有的創造力與韌性,以居間穿梭的運動性跳脫「翻譯←顛覆→霸權」的二元對立,並補充班雅明翻譯理論較少著墨於語言形式和內容的情感成分之空缺。「縫」具有破壞力、裂解性、衝突性,和傷痛感;「縫」也具有中介性、運動性、癒合力,和創造力。「縫」(讀為「奉」)是撕裂、衝撞、分離、演化;「縫」(讀為「逢」)可縫紉、黏合、編織、鋦釘、重組文化的碎瓷殘片為新器皿,縫隙即存在。「縫」從空無至往復運動「拆/合」,蓄積能量,在運動中完成社會實踐。
黃春明、王禎和等台灣小說家的作品,就大量運用了現代主義形式和鄉土經驗,語言裂縫和縫合現象十分明顯。限於篇幅,此處以黃春明的短篇小說〈蘋果的滋味〉為例,說明小說中多元語言的衝突如何戲劇化1970年代的美台權力關係。語言的裂縫與縫合在此小說中可被視為諷刺美國政經優勢和霸權主義的文化策略。黃春明採用當時的主流語言(「國語」/白話文)書寫這個故事;但在他的筆下,小說的敘述語言產生了裂縫、縐折、接縫——台語、英語不時浮現於「國語」的罅隙,成為閃爍於主流語言縫隙的弱勢語言,經過折疊縫合,構成國台英語交織的流暢對話,諷喻了美台強/弱、主/從地位,精準捕捉了「純正國語」難以傳達的庶民情感和後殖民文化情境,反映出70年代美國新殖民主義下台灣底層階級日常生活的現實。「縫」使這篇小說成為語言衝撞抗爭的文化場域。
〈蘋果的滋味〉寫於1972 年,黃春明以工人江阿發騎腳踏車被美國上校的賓士車撞斷腿住院為起點,用喜劇的諷刺口吻,縫合江阿發一家(台灣底層階級)、美國上校格雷和他的二等祕書(美國官方)、外事警察(台灣統治階級)三方的觀點,以台灣工人初嚐(美國)「蘋果」的滋味,對照1960、70年代台灣接受美國物資援助和軍事協防,由農業社會過渡至工商社會的後現代/後殖民情境。就題目而言,〈蘋果的滋味〉不像〈莎喲拉娜.再見〉那般明顯縫合中/日語,卻從感官角度(吃蘋果的滋味)戲劇化美台文化的相遇、衝撞、斷裂、協商,和縫合:台灣底層階級(工人阿發)被美國文化(格雷上校)衝撞(腳踏車被賓士車撞翻)→產生斷裂(阿發的雙腿被撞斷—接合)→協商(透過格雷的二等祕書、外事警察、外國修女的翻譯,格雷表達歉意並賠償阿發一家)→縫合(送阿發的啞巴女兒到美國讀書,和江家作朋友)。這個衝撞→斷裂→協商(翻譯)→縫合的過程,在故事結尾被黃春明用「初嚐蘋果的滋味」(味覺/觸覺/聽覺)和定價方式表達:「總覺得沒有想像那麼甜美,酸酸澀澀,嚼起來泡泡的有點假假的感覺」、「一只蘋果可以買四斤米」、「噗喳噗喳的聲音」,精準地諷喻了小說家欲批判的「美國經濟文化對台灣的支配與控制」。在黃春明精心的安排下,讀者體會到格雷上校的歉意和友善(「他說非常非常的對不起,請你原諒。他說他願意負一切責任,並且希望和你的家庭作朋友」)就像天上掉下來的蘋果,吃起來「有點假假的」,因為小說家一開頭就讓二等祕書說出美方的立場:「是工人!所以說嘛,我們惹不起⋯⋯美國不想雙腳都陷入泥淖裡!」
這些人物使用的英、國、台語之間的翻譯和縫合是〈蘋果的滋味〉精確捕捉現實的功臣,因為這些對話以從屬階級觀點鮮活地反映了當時的台灣情境。黃春明所使用的語言策略,可以被視為一種縫合「國語白話文」、台、英語轉譯成的「國語」,和受外國文學影響的翻譯語言的藝術創作行動。這必須從他早年的文學教育說起。黃春明曾多次提到他最初的文學「爺爺」來自沈從文和契可夫(Anton Chekhov)。此外還有約翰.克里斯多夫(John Christopher)、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馬克.吐溫(Mark Twain)、福克納,和電影的影響。這使他的書寫採用了結合白話文與外國文學翻譯語言的中文寫作,但是產生了裂縫,就是中文與他的母語間的裂隙。
黃春明的書寫縫合了白話文、外國文學翻譯語言、翻譯成白話文的台、日、英語等,依據角色身分和口吻交織運用。以這種方式,他將「鄉土語言,翻譯成主流的書面語」,「讓這些文本可以進入主流場域中,被閱讀及理解」。他考慮用主流語言寫作,以進入主流文化市場。因此他採取折衷辦法,把母語和其他語言翻譯成「國語」,依據說話角色的身分和發話情境,把對話技巧地縫在一起。這種翻譯策略在〈蘋果的滋味〉的人物對話中運用得相當成功。語言的障礙和溝通成為衝突和協商的主要場域,不同語言則透過翻譯縫成有聲有色的畫面,有時刻意露出縫綴褶縫,藉以營造詼諧諷刺的效果。
年輕外事警察帶洋人到江家住的違章建築。敘述事件時,作者使用簡潔流暢的白話文:「密密的雨點打在鐵皮上,造成屋裡很大的噪音,警察不得不叫嚷似的翻譯洋人的話」,之後作者用翻譯和語言縫合來表現阿桂和警察無法以語言溝通的情境:
〔阿桂〕驚慌地問:「阿珠,什麼事?」
「媽——」緊緊抿閉的嘴,一開口禁不住就哭起來。
「什麼事?快說!」
「爸、爸爸,被汽車壓了——」
「啊!爸爸——?在哪裡?在哪裡?……」阿桂的臉一下被扭曲得變形,「在哪裡?……」接著就喃喃唸個不停。
警察用很彆腳的本地話安慰著說:「莫緊啦,免驚啦。」〔斜體字為筆者所加〕他又改用國語向小女孩說:「叫你媽媽不要難過,你也不要哭,他們已經把你爸爸送到醫院急救去了。」洋人在旁很歉疚地說了些話,並且要求警察替他轉告她們。
「這位美國人說他們會負責的,叫你媽媽不要哭。」當他說的時候,洋人走過去把手放在阿珠的頭上,自己頻頻點頭示意,希望她能明白。這時候,那個揹著嬰兒的啞巴女孩,淋了一身雨從外面闖進來。她不知道裡面發生了什麼事,一進門看到剛才遇見的警察和洋人,驚奇地睜大眼睛大聲地連著手勢,咿咿啞啞地叫嚷起來。
…
「噢!上帝。」洋人又一次輕輕地呼叫起來。
這段對話巧妙呈現出美國官方/台灣官方/台灣底層的三角權力關係,以「國語」/閩南語/英語/啞巴的咿啞/肢體語言縫接出彼此無法溝通的困境。在絕大部分的對話都翻譯成「國語」的情況下,黃春明刻意露出主流語言的裂縫(或語言的接縫)——「莫緊啦,免驚啦」——凸顯警察努力說出有限閩南語安慰阿桂,以強化語言不通的臨場感和戲劇效果。警察和阿珠在此扮演了譯者的角色,因為洋人、阿桂、啞巴都聽不懂對方的語言,需要靠這兩枚敘述之針穿針引線,細細密縫。語言的穿梭織縫在此扮演了關鍵角色。若拿掉語言的穿梭縫紉,用「純正」「國語」書寫,「蘋果的滋味」就少了辛辣而平淡無味。這就是「縫」的文化策略成功之處。
黃春明小說的例子說明了以下:「縫」可視為缺裂、罅隙、缺陷,「縫」也可做為運動、行動、實踐。「縫」是在場、佔有、存在。「縫」也是縫合、修補、創造。「縫」是虛實變換/幻的在地文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