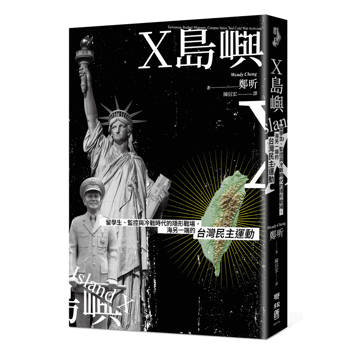研究「亞洲問題」的台灣學生
一九六七年三月,威斯康辛大學校長弗瑞.哈林頓(Fred Harrington)向美國國務卿迪恩.魯斯克(Dean Rusk)拍發緊急電報:
緊急請求您介入威斯康辛大學中華民國研究生黃啟明的案件,他目前遭到台灣的中國政府監禁。……台灣問題研究社(Formosan Affairs Study Group)是正式登記的威大學生團體,也依據規定指派指導教授。這類團體經常自由辯論各種議題。教職員對這類會議的參與,確保這類會議絕不會遭到煽動叛亂的指控。……沒有一所自由的大學能夠容忍正當研究遭到這種政治干預。
哈林頓以電報式的簡明文字接著指出:「來自中華民國的學生如果不能自由參加這個國家的討論課程,那麼我們將無法繼續接收這些學生,也會如此建議其他研究所。」身為教育領域博士生的黃啟明,為論文返台從事研究卻遭逮捕,以煽動叛亂的罪名獲判刑五年,理由是他參加台灣問題研究社、出席台獨團體在芝加哥舉行的會議,以及在返台途中於東京會見一名台獨領袖。美國國務卿與美國駐台北大使館雖宣稱與黃案無關,但哈林頓的電報以及《紐約時報》對黃案的報導,可能是黃啟明在幾個月後得以受重審的原因;一九六七年七月,他以緩刑獲釋,但從此遭禁止離台。
黃啟明的案件,可能是首例因國民黨監控而被捕的留美學生;這起案件也頗為典型,他是因為涉入支持獨立的台灣學生團體,引起國民黨當局注意。如同第一章與第二章討論過的若干故事,黃案也發生於威斯康辛大學,進一步凸顯了麥迪遜以及整個中西部地區對台美人歷史的多面向重要性。
黃啟明出生於一九三一年,是分布於美國中西部與東岸那群構成早期在美台灣僑民社運行動的台灣學生當中的一員。不過,他的案例又和其他較常見的狀況不同。大部分台灣人來美國攻讀的都是醫學、科學與工程學這類學科,所以政治運動通常與學業追求無關。然而,在一九六三年秋季抵達麥迪遜的黃啟明,該年六月才剛取得哈佛大學遠東語言與文學碩士學位—這是當時全美規模最大的亞洲研究學程。
舉例而言,目前能取得的一九六○年代資料顯示,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六五年間,來自台灣的學生當中,有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攻讀工程學以及自然與物理科學。攻讀人文學科者占百分之十三,另外有百分之十.七的人攻讀社會科學。這些攻讀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學生,很可能有不少人也修習了某種型態的區域研究。新成立的區域研究學系與中心獲公家與私人的豐厚資助,使外國學生能夠申請全額獎學金、教學助理獎學金,以及研究助理獎學金。許多在一九六○年代初赴美的台灣學生出生於日本殖民時期,接受一段時間的日本學校教育,由說日語的父母撫養長大,因此擁有精通日語和中文、相對獨特的優勢。此條件使他們相當適合參與區域研究在戰後教育機構當中的成長,也同時於成長中獲益。黃啟明就是個頗為典型的例子;他精通日語,研究的是日本文學及台灣的日本殖民時期。
和攻讀科學領域的同胞一起,做亞洲研究的台灣學生,也參與建立強大的社會組織及區域性和全國性網絡。不過,和科學領域學子不同的是,做亞洲研究的學生的學術研究與關注中,高居要位的是台灣與東亞的歷史與政治。此外,這些學生也有比較豐富的政府與知識精英方面的人脈,因為他們那些通常是白人美國男性的教授,在進入學術界任職之前大多曾是派駐亞洲的外交官或政府、軍事官員,在成為學界人士之後,他們仍保有原本的人脈—且積極加以維繫,儘管也許僅限於非正式層面。如同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一九六四年所言:
學術史上有個奇特的事實,就是區域研究的第一個重大中心……(乃是)戰略情報局。……設有區域學程的大學與政府的資訊蒐集機構之間,至今仍然高度相互滲透,而且我希望以後仍然如此。
實際上,黃啟明後來的雇主暨恩師道格拉斯.孟岱爾,在成為學術人之前就曾在二戰期間、戰後任派駐日本的海軍情報官。至於與台灣有關的例子,則以葛超智最為著名。他在一九六五年出版《被出賣的台灣》,因此在美國啟發了一個世代的台灣學生社運人士,而他曾是美國海軍軍官以及駐台外交官。此外,他還在戰後美國占領日本期間,開設了日本的第一個美國研究學程。
孟岱爾似乎完全認同亞洲研究當中那種明確親美反共的精神,把對於「那個區域」的知識視為一種手段,用來控制該區域各民族的行動與渴望,藉以支持由美國支配的全球霸權。一九五○年代,任洛杉磯加州大學政治學教授期間,他為《洛杉磯時報》寫了一系列文章,不但醜化日本國內新興的左派,也針對遏阻反美情緒的最佳方法提出建議。他把菲律賓描述為曾受美國監護的一個病態、不道德而又腐敗的國家,只因為在嚇阻共產勢力時扮演了支持性的角色,才得以稍微補救名聲。另外,他也主張夏威夷立州是「在我們的種族政策當中贏得亞洲人信心」的一個重要步驟,因為「自由國家對抗共產主義侵襲的全球鬥爭,其結果很可能會由亞洲的心意決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七日,他在一篇題為〈珍珠港有帶給我們多少教訓嗎?〉(Did Pearl Harbor Teach Us Much?)的觀點文章裡寫道:
美國大眾以及官員對亞洲的無知,在珍珠港事件後已有所改善,但我們有多少人預見了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的發展(韓戰爆發)?即便到了今天,有多少人學習亞洲的語言,或是對東南亞火藥庫有任何了解?珍珠港不論為我們帶來了其他哪些教訓,最重要的是讓我們意識到自己在公共與私人領域都必須更關注亞洲,以免問題倏然爆發面前,就像過去十三年來兩度出現的那種狀況。
必須了解亞洲,才能夠控制「亞洲問題」,以及為可能爆發的「東南亞火藥庫」做好準備—也就是預防美國的權力與全球霸權在未來可能遭受的威脅。孟岱爾採取的這些立場,在戰後亞洲研究的既定常態當中相當典型,也就是把自由主義的親美反共意識形態構成的道德與意識形態世界,視為理所當然的思考與行動基準。
看起來,黃啟明和其同學大體上並未意識到,他們的研究領域和美國政府的利益帶有這些糾纏不清的關係,不然就是他們對此關係並未抱持批判態度。也許不難理解的是,他們比較關注的是學業及在美國生活的地點,對他們自己與台灣有關的人生、命運以及渴望,會帶來什麼影響。與黃啟明交好且同為威斯康辛大學博士生的田弘茂,一九六四年寫信向孟岱爾指出:「我不能在這個國家待太久。我們必須設法推翻蔣政府。這裡的每個台灣青年都應該盡快拿到學位,這樣我們才能更全心投入做好組織工作。」
就這方面而言,他們一赴美求學,很快便發現了一個充滿豐富資訊和無窮可能性的龐大世界。黃啟明一抵達麥迪遜,立刻就成了威大台灣同鄉會的祕書。那是美國最早的一個台灣學生組織,當時甫成立不久。創辦人之一吳得民回憶道,當時既有的中國同學會由來自台灣的親國民黨學生領導,因而強烈反對該組織的成立。對於美國校園裡抱持台灣人認同的學生而言,此情形雖在後來成了頗為尋常的經驗,但吳得民對當時的異議懷有鮮明的回憶,顯示麥迪遜早已有國民黨的監控人員存在。實際上,到了一九六三年,威斯康辛大學教職員周烒明與他身為研究員的妻子吳秀惠,就已因為涉入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而被列入黑名單,兩人的中華民國護照也遭吊銷。劉兆民是在該年初抵麥迪遜的台灣學生,他記得,當時有個熱心的外省人學生親近他,一再告誡他不要參與台灣同鄉會的活動,也不要和周氏夫妻往來;後來有一天,他向這位朋友借車,卻在車上發現國民黨的文件和台灣報紙,才發現「這個友善的傢伙是個特務」。一九六四年來到麥迪遜的農藝學博士生林慶宏則回憶:「這是環境優美的湖畔校園,在那美麗的校區,台灣留學生圈中卻蔓延著莫名不安的氣氛。……不可想像的事情是發生在校園裡。」
一九六七年三月,威斯康辛大學校長弗瑞.哈林頓(Fred Harrington)向美國國務卿迪恩.魯斯克(Dean Rusk)拍發緊急電報:
緊急請求您介入威斯康辛大學中華民國研究生黃啟明的案件,他目前遭到台灣的中國政府監禁。……台灣問題研究社(Formosan Affairs Study Group)是正式登記的威大學生團體,也依據規定指派指導教授。這類團體經常自由辯論各種議題。教職員對這類會議的參與,確保這類會議絕不會遭到煽動叛亂的指控。……沒有一所自由的大學能夠容忍正當研究遭到這種政治干預。
哈林頓以電報式的簡明文字接著指出:「來自中華民國的學生如果不能自由參加這個國家的討論課程,那麼我們將無法繼續接收這些學生,也會如此建議其他研究所。」身為教育領域博士生的黃啟明,為論文返台從事研究卻遭逮捕,以煽動叛亂的罪名獲判刑五年,理由是他參加台灣問題研究社、出席台獨團體在芝加哥舉行的會議,以及在返台途中於東京會見一名台獨領袖。美國國務卿與美國駐台北大使館雖宣稱與黃案無關,但哈林頓的電報以及《紐約時報》對黃案的報導,可能是黃啟明在幾個月後得以受重審的原因;一九六七年七月,他以緩刑獲釋,但從此遭禁止離台。
黃啟明的案件,可能是首例因國民黨監控而被捕的留美學生;這起案件也頗為典型,他是因為涉入支持獨立的台灣學生團體,引起國民黨當局注意。如同第一章與第二章討論過的若干故事,黃案也發生於威斯康辛大學,進一步凸顯了麥迪遜以及整個中西部地區對台美人歷史的多面向重要性。
黃啟明出生於一九三一年,是分布於美國中西部與東岸那群構成早期在美台灣僑民社運行動的台灣學生當中的一員。不過,他的案例又和其他較常見的狀況不同。大部分台灣人來美國攻讀的都是醫學、科學與工程學這類學科,所以政治運動通常與學業追求無關。然而,在一九六三年秋季抵達麥迪遜的黃啟明,該年六月才剛取得哈佛大學遠東語言與文學碩士學位—這是當時全美規模最大的亞洲研究學程。
舉例而言,目前能取得的一九六○年代資料顯示,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六五年間,來自台灣的學生當中,有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攻讀工程學以及自然與物理科學。攻讀人文學科者占百分之十三,另外有百分之十.七的人攻讀社會科學。這些攻讀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學生,很可能有不少人也修習了某種型態的區域研究。新成立的區域研究學系與中心獲公家與私人的豐厚資助,使外國學生能夠申請全額獎學金、教學助理獎學金,以及研究助理獎學金。許多在一九六○年代初赴美的台灣學生出生於日本殖民時期,接受一段時間的日本學校教育,由說日語的父母撫養長大,因此擁有精通日語和中文、相對獨特的優勢。此條件使他們相當適合參與區域研究在戰後教育機構當中的成長,也同時於成長中獲益。黃啟明就是個頗為典型的例子;他精通日語,研究的是日本文學及台灣的日本殖民時期。
和攻讀科學領域的同胞一起,做亞洲研究的台灣學生,也參與建立強大的社會組織及區域性和全國性網絡。不過,和科學領域學子不同的是,做亞洲研究的學生的學術研究與關注中,高居要位的是台灣與東亞的歷史與政治。此外,這些學生也有比較豐富的政府與知識精英方面的人脈,因為他們那些通常是白人美國男性的教授,在進入學術界任職之前大多曾是派駐亞洲的外交官或政府、軍事官員,在成為學界人士之後,他們仍保有原本的人脈—且積極加以維繫,儘管也許僅限於非正式層面。如同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一九六四年所言:
學術史上有個奇特的事實,就是區域研究的第一個重大中心……(乃是)戰略情報局。……設有區域學程的大學與政府的資訊蒐集機構之間,至今仍然高度相互滲透,而且我希望以後仍然如此。
實際上,黃啟明後來的雇主暨恩師道格拉斯.孟岱爾,在成為學術人之前就曾在二戰期間、戰後任派駐日本的海軍情報官。至於與台灣有關的例子,則以葛超智最為著名。他在一九六五年出版《被出賣的台灣》,因此在美國啟發了一個世代的台灣學生社運人士,而他曾是美國海軍軍官以及駐台外交官。此外,他還在戰後美國占領日本期間,開設了日本的第一個美國研究學程。
孟岱爾似乎完全認同亞洲研究當中那種明確親美反共的精神,把對於「那個區域」的知識視為一種手段,用來控制該區域各民族的行動與渴望,藉以支持由美國支配的全球霸權。一九五○年代,任洛杉磯加州大學政治學教授期間,他為《洛杉磯時報》寫了一系列文章,不但醜化日本國內新興的左派,也針對遏阻反美情緒的最佳方法提出建議。他把菲律賓描述為曾受美國監護的一個病態、不道德而又腐敗的國家,只因為在嚇阻共產勢力時扮演了支持性的角色,才得以稍微補救名聲。另外,他也主張夏威夷立州是「在我們的種族政策當中贏得亞洲人信心」的一個重要步驟,因為「自由國家對抗共產主義侵襲的全球鬥爭,其結果很可能會由亞洲的心意決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七日,他在一篇題為〈珍珠港有帶給我們多少教訓嗎?〉(Did Pearl Harbor Teach Us Much?)的觀點文章裡寫道:
美國大眾以及官員對亞洲的無知,在珍珠港事件後已有所改善,但我們有多少人預見了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的發展(韓戰爆發)?即便到了今天,有多少人學習亞洲的語言,或是對東南亞火藥庫有任何了解?珍珠港不論為我們帶來了其他哪些教訓,最重要的是讓我們意識到自己在公共與私人領域都必須更關注亞洲,以免問題倏然爆發面前,就像過去十三年來兩度出現的那種狀況。
必須了解亞洲,才能夠控制「亞洲問題」,以及為可能爆發的「東南亞火藥庫」做好準備—也就是預防美國的權力與全球霸權在未來可能遭受的威脅。孟岱爾採取的這些立場,在戰後亞洲研究的既定常態當中相當典型,也就是把自由主義的親美反共意識形態構成的道德與意識形態世界,視為理所當然的思考與行動基準。
看起來,黃啟明和其同學大體上並未意識到,他們的研究領域和美國政府的利益帶有這些糾纏不清的關係,不然就是他們對此關係並未抱持批判態度。也許不難理解的是,他們比較關注的是學業及在美國生活的地點,對他們自己與台灣有關的人生、命運以及渴望,會帶來什麼影響。與黃啟明交好且同為威斯康辛大學博士生的田弘茂,一九六四年寫信向孟岱爾指出:「我不能在這個國家待太久。我們必須設法推翻蔣政府。這裡的每個台灣青年都應該盡快拿到學位,這樣我們才能更全心投入做好組織工作。」
就這方面而言,他們一赴美求學,很快便發現了一個充滿豐富資訊和無窮可能性的龐大世界。黃啟明一抵達麥迪遜,立刻就成了威大台灣同鄉會的祕書。那是美國最早的一個台灣學生組織,當時甫成立不久。創辦人之一吳得民回憶道,當時既有的中國同學會由來自台灣的親國民黨學生領導,因而強烈反對該組織的成立。對於美國校園裡抱持台灣人認同的學生而言,此情形雖在後來成了頗為尋常的經驗,但吳得民對當時的異議懷有鮮明的回憶,顯示麥迪遜早已有國民黨的監控人員存在。實際上,到了一九六三年,威斯康辛大學教職員周烒明與他身為研究員的妻子吳秀惠,就已因為涉入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而被列入黑名單,兩人的中華民國護照也遭吊銷。劉兆民是在該年初抵麥迪遜的台灣學生,他記得,當時有個熱心的外省人學生親近他,一再告誡他不要參與台灣同鄉會的活動,也不要和周氏夫妻往來;後來有一天,他向這位朋友借車,卻在車上發現國民黨的文件和台灣報紙,才發現「這個友善的傢伙是個特務」。一九六四年來到麥迪遜的農藝學博士生林慶宏則回憶:「這是環境優美的湖畔校園,在那美麗的校區,台灣留學生圈中卻蔓延著莫名不安的氣氛。……不可想像的事情是發生在校園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