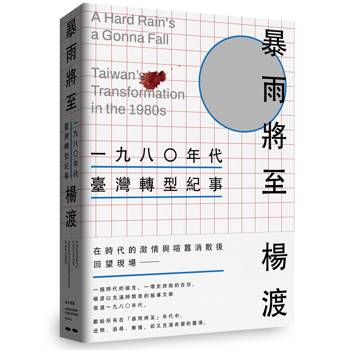三 礦坑裡的黑靈魂
前言:
本文發表於一九八二年一月《大地生活》雜誌,是我寫作報導文學的開端。當時因一部電影《礦工的女兒》(由女星西西.史派克Sissy Spacek主演)在臺灣頗為轟動,《時報周刊》希望我去做報導。因傳說臺灣煤礦工人生活艱難,女兒往往被賣到瑞芳八角亭(當時是一處酒家與茶室混居,龍蛇雜處的地方),成為茶室酒女。
為了了解礦工生活,報館安排了地方記者帶我去看一間頗具規模的煤礦。他們在寬大的礦坑入口(約有一層樓高),安排了一場剪報。讓我了解礦坑如何採礦的結構圖。但既未採訪礦工,也未談及礦工家屬。雖然我提出請求進礦坑實地採訪,但場礦以安全為由,拒絕讓我進入。
沒有現場,沒有真相。為真正進入礦坑實地體驗,我請基隆朋友私下介紹,終得以進入一間小型礦場,在礦工一步步帶領下,深入地底,進行了一整天的採訪工作。這是首度披露的煤礦底層的工作樣態,艱辛、殘酷、堅忍、卑微、幽黯、苦鬥等諸種人性面貌,是我想傳達的。
此文發表兩年多以後,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海山煤礦發生煤塵爆炸。一如文中所述,由於臺車第七車和第八車的插銷沒有插好,造成臺車滑落,又因為撞擊到高壓電,引發的火花迅即點燃彌漫在空氣中的煤粉,引發爆炸。撞擊過程中,多人喪命,另有許多礦工,因為空氣中布滿一氧化碳而喪命。此次災變,造成七十二人死亡,其中大多數是阿美族礦工。
災變二十日後,七月十日,臺北縣瑞芳鎮再度發生煤山煤礦災變。礦災是由於壓風機房突然發生火災,機房的坑木支架與機械潤滑油等迅速燃燒,煙霧隨氣流進入斜坑,使第一班休工欲出坑及第二班已入坑的共一百二十三名礦工深陷充滿薰煙與一氧化碳的坑內。於搶救後二十二人送醫救活,其餘一百零一人罹難,但救活的人中有半數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成為植物人。
又過了五個多月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中午十二時五十九分,位於新北市三峽區的海山一坑本斜坑坑道,在中午礦工上下班交接之際,突然發生煤塵爆炸,導致坑道岩石崩落,原本在本斜坑內工作的九十五名員工因逃生不及被困在坑道內,其中一名礦工先在十二月五日晚上十時被救援隊救出,另有一名礦工周宗魯在九十三小時後獲救。他後來坦承是靠著割取同伴的肉吃,才勉強維生。此次災變,九十三名礦工罹難。
一九八四年間接連發生礦災,造成至少兩百七十七人死亡,敲響臺灣煤礦業喪鐘。之後因本地煤的價格競爭力不如進口煤,臺灣僅有的幾處煤礦陸續停採關閉。兩千年臺灣全面停止採礦。
----------------------------------------------------------------
傾頹了的黃金大山
轉過一個又一個的山頭,盤旋過環山繞行的公路,我隨著「礦工的女兒」阿淑,終於抵達了伊的父親向某大公司承包的山谷小礦場。
與瑞三、建基等大礦區相較之下,這兒的的確確是個小礦場罷了。明朗活潑且有著一雙鳳眼的阿淑便是在其中負責會計、薪資,有時並兼任管理等工作。然而,當我隨著阿淑健捷的步伐走下陡斜的山坡石梯後,聽著阿淑與洗煤搬運的女工一一打招呼時,便油然地生起一種家族小公司所特有的感受。
阿淑在前頭介紹環繞著礦場的雞籠山、金瓜石山脈、茶壺山等等地形,然後,她突然指著遠方在山路上盤旋而下的、載滿了黃土沙石的卡車說:「看見沒有?那一輛卡車,就是載黃金的車子。」伊說。
「那不是一輛黃土嗎?」我驚問道。
「對啊!都是從金瓜石山上挖下來的。本來九份、金瓜石盛產黃金,但是已採得差不多了。現在金瓜石的藏量相當少了,所以,乾脆!」伊回頭笑著說:「把山通通挖下來提煉算了!」
「那能提煉多少黃金呢?」
「據說一卡車大約可以提煉一兩吧!」伊說。
我於是無聲地笑了。
一座山的死滅,一座充滿傳奇、夢幻與閃閃黃金的大山,終於即將傾頹了。那尋金者曾經蜂擁沉迷的國度,那貧窮者以「吞金」來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捉迷藏的對抗,終將在大卡車的來回搬運中,傾頹且幻滅了。充滿了夢幻與傳奇的這山頭,終將只剩得一片荒涼而破碎的面貌,化為一兩一兩的黃金流入市場,化為一灘一灘的黃土沙石,向太平洋永遠沉沒了。
礦場上,礦坑口的臺車軌道在陽光中閃亮著褐色的光芒。自礦坑入口蜿蜒而出後,軌道分叉,一條筆直伸入山谷口,用來傾倒廢棄的沙石;一條向右延伸約二十公尺後爬斜坡而上,運上坡地後,傾倒入洗煤場。幾個婦女工作者頭戴斗笠上包著一條大方巾,以便遮陽;身穿碎花粗布衣裳,下身著長褲及塑膠雨鞋。然而衣褲上,卻因煤沙的沾染,大多呈現煤黑色澤。她們在礦坑外從事搬運及洗煤的工作。一個婦女推著裝滿煤礦的臺車到斜坡下,然後又跑上斜坡拉下鐵索,勾好煤車,在陽光中,隨著煤車拉曳而止,她勤奮地上下跑動著,流汗著。
走進了簡陋的辦公室裡,兩個頭戴安全燈的工作者正蹲在地上修理東西。他們抬起頭訝異地望著我。阿淑說:「這是楊先生,他想報導礦工,你們多照顧哦!」他們和善地站起來,說:「手很髒呢!歹勢!歹勢!」我說:「沒關係啦!怕髒就不來了!」「沒要緊啦!握不握都一樣!」他們爽朗地說。
由於他們今天的工作相當繁忙,無法帶我進入礦坑,便相約次日再來。於是我與這位做了幾十年礦工而今因著承租礦場而成為資方的礦場負責人聊天,並詢問了礦工的工作、薪資及身體健康等問題。
薪資與危險性齊頭並進
基本上,礦工的工作時數並不算長,早晨八點入礦坑,中午吃過便當後,將工作告一段落,下午兩點左右便陸續出坑了。每天約工作五小時。工作時間雖不長,但是因全然的體力勞動,因而相當勞累。為了避免身體過疲而疏忽心神,多數礦工在能夠維持生活的原則上,大多不願工作太久。其薪資則係論件計酬的方式,以每天採掘幾車煤來決定。因此與煤層的良否具有莫大關連。好的礦脈可以日進千元以上,壞的礦脈沙土特多時,便只有幾百元而已,所以,礦工們當然指望挖到好礦脈,然而,由於礦工在老成凋謝退休而又後繼乏人的情況下漸漸少了,在「稀為貴」的情況下,礦工的薪資也漸有保障,亦即如果挖到不良礦脈而出煤甚少時,可向資方提出要求,而獲得某一程度的補償。這是指「採掘工」而言。至於「進度工」則是開闢新的坑道,架設支木,好讓採掘工進入工作,因此其薪資是依所開闢坑道的長短而定,越長薪資越多。
礦坑外的「運煤工」與「洗煤工」的薪資,則可分為論件計酬及工作時數兩種方式。平均起來,進度工與採掘工日薪約在七百至一千元左右。不過因著工作疲累,工人們鮮少天天上工,因此,一般月薪約在一萬至兩萬左右。坑外工則因危險性較低,工作較輕鬆,相對的薪資也低很多。
然而,高薪資卻難以吸引年輕人進入礦坑工作了。一來危險性很高,稍一不慎,動輒落盤、入水、瓦斯爆炸,常常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其次則是嚴重的職業病。
目前礦工平均年齡約在四十五至五十之間,他們大多因長期的工作,吸入空氣中的沙塵,沉積肺部而造成了「沙肺」。沙肺本身雖然不至於致命,但會使身體衰弱。更怕因感冒、疲勞過度、煙酒過量等等引起併發症,而將沙肺轉成肺癆,便能置人於死地了。礦場負責人雖然一再強調做礦工是如何的輕鬆好賺錢,但是,當他談起沙肺時,也不禁變色悚然地表示自己也儘量避免進礦坑。因他也在礦坑工作數十年,也患有沙肺。沙肺雖然不傳染、不致命,卻是無法治療的病症。患者只能儘量維持健康,使它不至於轉為肺癆罷了!
但是,普遍罹患沙肺的礦工們卻也只能繼續進入黝暗的礦坑裡,繼續吸取沙塵,一鋤一鏟地謀取生存,一鋤一鏟地為臺灣能源貢獻全部的血汗與生命。
這就是我們面目黧黑,手足胼胝的弟兄的一生。
一切都是這般危殆而艱險
次日早晨,抵達晨光閃耀的山谷小礦場後,我隨同安全人員蘇仔在工寮裡換下全身衣褲,穿上工作服及雨靴,戴上膠盔並佩好安全燈,隨同另外兩人,一齊坐上駛向礦坑的空煤車,緩緩向礦坑入口前進。
煤車由礦坑裡的捲揚機拉曳著,緩緩駛進了礦坑。洞口的光線迅即消失而全然地進入了黑暗。只剩下安全燈照著前面積水的軌道,牆壁上粗大黑溼的支架相思木,和煤車輪子與軌道哐哐噹噹的撞擊聲在四壁有力的迴響著。
我們沿「平水巷」前行。
牆壁上有泉水不時地滲滴下來。不只淋溼了支撐的相思木,更使之發霉而長了一層白色的黴菌,在光線與水珠的襯映下,閃著冰冷森白的光芒。
我在心裡暗暗憂懼起來了:如果相思木因年久失修而斷裂了;如果岩壁因泉水侵蝕而鬆垮了;如果地底冒出一陣狂烈的瓦斯;如果泉水驟而增大向地底淹去……那麼我們平常在報刊上所看到的「災變」,就將成為我們生離死別的葬禮了。是的,在這樣低矮潮溼的坑洞裡,在延伸向地底數百公尺的黑洞中,這個唯一的出口,卻長滿森白的黴菌,泉水淹沒了軌道,一切都是這般危殆而艱險……
然而,這只是我這般庸懦軟弱者的憂懼罷了。蘇仔和他的弟兄們了無懼意地注視著前方,平凡且堅定地開始他們一天的工作,駛向地脈深處。
通過一百多公尺的「平水巷」後,到達「斜坑」的交叉口。我們傴僂著身軀下了煤車,又傴僂著身軀順斜坑向下行走。
所謂平水巷,係指由礦坑入口向山中水平掘進的坑道,其作用只是引入進入山的中心,發現煤礦。然後再順著煤層分布的狀況挖掘。例如煤層以二十五度角向下延伸,坑道便以二十五度角向下挖掘,此謂之「斜坑」。斜坑為向下沿伸的主展線,其兩側又可平行採掘如枝幹,是謂「平巷」。因著左右次序之不同而各有名稱,如左邊第一平巷叫「左一片」,左邊第二平巷叫「左二片」,依此類推。而平巷與平巷間,亦多藏有煤礦,故平巷之間亦可順煤層分布角度而挖掘。其角度大多與斜坑相同,稱之為「工作面」。
一種模糊而親切的感覺
最初,我們沿斜坑軌道向下走。斜坑裡的泉水並不小,嘩嘩地向地底流去,使得路面根本看不清楚,也使得軌道中間的橫木與石頭滑溜難行,再加上低矮的坑道,必須彎腰縮頸才能前進。不多時,我便因時而滑倒、時而頭頂直撞支架而狼狽暈眩不已了。幸而蘇仔不時回顧我是否跟得上,而走在最前端的兩人卻早已失卻蹤跡了。這時,蘇仔頭上的那盞安全燈光以及他的背影遂成為我唯一追尋的前導了。
他在前方以慣於顛躓的步伐,不失穩定地前進著。我在後面狼狽尾隨。且因彎腰過久而腰酸背痛脖硬了。但是望著他的形姿如此,我暗自咬牙提神,勉力緊隨顛躓前行。
蘇仔在左二片的叉口停住,轉過頭來,太強烈的燈光射刺而來,使我無法看清他的面容。他的煤黑色衣服與面容與岩壁融成了整體,只有那一盞強炙的光圈,證實著人與光明之存在。然而當我以光線直射他的面容,看見了他瞇成一條縫的眼睛時,我終而了解,我們在黝暗的地底,都同樣地努力辨認彼此的面容。雖然在黑深的情境裡,無法辨識清晰,但是一種模糊而親切的感覺,卻使我心裡感到一陣溫熱。
闇無一人的左二片裡,靜寂無聲。相思木上厚厚的一層白黴菌閃著森白光芒。水滴不時滲漏下來。而且因著此地是循環系統的末端,空氣較不好,是以一股令人難以呼吸的又溼又辣的味道使我緊張了起來。「會有瓦斯嗎?」我不禁問他。卻又先被自己的焦急乾燥的話聲嚇了一跳。
蘇仔先是驚愕了一下,抬頭以燈光照著我惶惶的面容,才笑了起來,說:「不會啦!放心啦!這裡的礦場屬於金礦山脈的地質結構,很少有瓦斯的。專門產煤的礦區才容易有煤氣、瓦斯的出現。這裡──」他拍拍我的肩膀說:「很安全啦!這只是相思木長黴的味道而已。」
「但是泉水這樣的侵蝕,長期下來,造成岩壁的鬆動,相思木又長黴,會不會危險呢?」我憂心忡忡問道。
「岩壁上的壓力是會變化沒有錯,但是沒有那麼嚴重,而且泉水也有一定的流動層面,即使腐蝕了,也會在支架的相思木上顯出痕跡來。相思木的好處是韌性很強,會變彎曲,但不易斷裂。如果它變彎了,我們就得注意,或者更換支架,或者重新修理,如果不行,就得放棄而封閉它。像這些泉水剛好在山裡而流過,被我們挖到了,便讓它順著斜坑往下流,流到底下,再用抽水機抽出坑外。」他平靜地敘述著。「危險,當然有啦!所以礦工每天進出都得隨時注意啊!不能開玩笑的,自己的生命咧!」
我們面目黧黑、手足胼胝的弟兄
我們繼續傴僂彎腰前進。推開至巷坑口竹門時,一陣強烈新鮮的風颯然灌進來。出了平巷後,我們順著狹窄低矮的斜坑軌道向下走。
這時,一列裝滿了煤沙的車子,自地底黑暗處正哐噹哐噹的拉曳而上。我們趕緊走向稍寬處,緊貼著冷溼的相思木與白黴,煤車剎時恰好在膝蓋前轟然駛過。
我們依舊顛躓前行。最初我尚且能夠注意兩壁的相思木、聯絡線及長度標示牌,但是深入百公尺多以後,在滑跌及撞頂之下,我完完全全地成為狼狽而無意識的尾隨者了。這時我只希望能夠挺直腰身,抬起頭來走路而已。
斜坑裡的泉水嘩嘩向下流,溼淋淋的岩壁閃著黑冷的懾人的壓迫。時高時低的橫樑支架依然撞得我頭暈目眩。然而,站在能源之最源頭的工作者,我們面目黧黑,手足胼胝的弟兄,便是日日在這樣的環境下,彎著腰,縮著脖子,傴僂身軀,勤奮地掘進、採挖、修補,為自己的生存而搏鬥著,在危險幽深的地底,一無憤懣怨氣的奠下工業的磐石。
我們向地底緩緩地深入。
這時,背後的上方傳來煤車駛下來的聲音。我回頭看去,只見兩盞燈光,迅速滑落逼近。蘇仔在他們接近之時,敏捷地拉了一下壁上聯絡的黑繩,車子便停下來,我們搭上便車,順斜坑向下滑落。
斜坑的底部,兩個赤裸上身的進度工正頂著安全燈挖掘著。一個拿著丁字鎬奮力敲擊堅硬的岩壁;一個正彎腰搬運廢石進入煤車裡。安全燈的暖黃光圈照著岩壁,使其凹凸不平的表面的光影之間,現出浮雕般的形狀來。然而安全燈一移開,岩壁便又全然地陷入黑暗了。他們回頭注視蘇仔站在一旁測試空氣。望著他們汗溼的軀體,我說:「很累哦?」
「不會啦?粗工做久,習慣就好了。」他們笑著說。
血汗締造的地下國度
蘇仔於是指著岩壁上一層狹長的黑色質土說:「你看,這一層就是煤礦。」說完撥下一塊拿給我看。我拿在手藉著安全燈加以審視,發現它質地疏鬆,結構相當易碎。他又從其較下方拿下一塊說:「這個就不是煤了。」燈光的照射下,它除了較硬質外,兩者同樣是黑色粗糙,頗難分辨。
事實上,據說這黑色煤質的露頭雖然是狹小條物,卻表示著其中可能蘊藏較大的礦脈,惟不能保證藏量的多寡。所以,很可能在掘進一段坑洞後,卻又發覺藏量稀少而放棄。因此,進度工的工作便不僅是掘進而已,更需要豐富的經驗與敏銳的觀察力,才能使工程更準確、更有效地進行。據說,早期一名熟練的礦工的培養,至少需要費時兩年的長期訓練。
蘇仔與我一邊談著,他們一面繼續工作。方才那位對我笑得真率猶如孩童的掘進者這時舉起丁字鎬,奮力向壁上擊打。壁上咯然一聲悶響,一片岩石便掉了下來,細細的塵土也揚離岩壁,緩緩飄浮然後降落地面。他再度舉鎬揮擊。這一回撞上較硬的岩石,鏗鏘一聲,岩壁悶響,冒出一點火花,岩石並未落下。
他繼續奮力揮鎬,彷彿面對頑強巨大的敵人一般,全身浮凸出一塊塊堅實的肌肉,肌肉上輝閃著一顆顆微小晶瑩的汗珠,以及黏附其上的細細的塵土,幾下擊打後,一大塊岩石鏗然掉落下來,滾過他的腳下,向前翻滾,落在蘇仔的跟前。
我默默地注視著這段過程。不由得在心中暗暗想著:這麼長的坑道,這麼深的地底,便是在他們這般肌肉糾結的擊打中,一鎬一鎬地,一塊一塊地,一寸一寸地試探前進;將岩壁鑿動,尋覓煤礦的蹤跡;將相思木一根一根紮實地架設好;將臺車軌道一段段鋪排;然後,才有著今日深入山的中心,深入地底數百公尺的礦場。
這是如何的血汗,如何的手足所締造的地下國度啊!
前言:
本文發表於一九八二年一月《大地生活》雜誌,是我寫作報導文學的開端。當時因一部電影《礦工的女兒》(由女星西西.史派克Sissy Spacek主演)在臺灣頗為轟動,《時報周刊》希望我去做報導。因傳說臺灣煤礦工人生活艱難,女兒往往被賣到瑞芳八角亭(當時是一處酒家與茶室混居,龍蛇雜處的地方),成為茶室酒女。
為了了解礦工生活,報館安排了地方記者帶我去看一間頗具規模的煤礦。他們在寬大的礦坑入口(約有一層樓高),安排了一場剪報。讓我了解礦坑如何採礦的結構圖。但既未採訪礦工,也未談及礦工家屬。雖然我提出請求進礦坑實地採訪,但場礦以安全為由,拒絕讓我進入。
沒有現場,沒有真相。為真正進入礦坑實地體驗,我請基隆朋友私下介紹,終得以進入一間小型礦場,在礦工一步步帶領下,深入地底,進行了一整天的採訪工作。這是首度披露的煤礦底層的工作樣態,艱辛、殘酷、堅忍、卑微、幽黯、苦鬥等諸種人性面貌,是我想傳達的。
此文發表兩年多以後,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海山煤礦發生煤塵爆炸。一如文中所述,由於臺車第七車和第八車的插銷沒有插好,造成臺車滑落,又因為撞擊到高壓電,引發的火花迅即點燃彌漫在空氣中的煤粉,引發爆炸。撞擊過程中,多人喪命,另有許多礦工,因為空氣中布滿一氧化碳而喪命。此次災變,造成七十二人死亡,其中大多數是阿美族礦工。
災變二十日後,七月十日,臺北縣瑞芳鎮再度發生煤山煤礦災變。礦災是由於壓風機房突然發生火災,機房的坑木支架與機械潤滑油等迅速燃燒,煙霧隨氣流進入斜坑,使第一班休工欲出坑及第二班已入坑的共一百二十三名礦工深陷充滿薰煙與一氧化碳的坑內。於搶救後二十二人送醫救活,其餘一百零一人罹難,但救活的人中有半數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成為植物人。
又過了五個多月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中午十二時五十九分,位於新北市三峽區的海山一坑本斜坑坑道,在中午礦工上下班交接之際,突然發生煤塵爆炸,導致坑道岩石崩落,原本在本斜坑內工作的九十五名員工因逃生不及被困在坑道內,其中一名礦工先在十二月五日晚上十時被救援隊救出,另有一名礦工周宗魯在九十三小時後獲救。他後來坦承是靠著割取同伴的肉吃,才勉強維生。此次災變,九十三名礦工罹難。
一九八四年間接連發生礦災,造成至少兩百七十七人死亡,敲響臺灣煤礦業喪鐘。之後因本地煤的價格競爭力不如進口煤,臺灣僅有的幾處煤礦陸續停採關閉。兩千年臺灣全面停止採礦。
----------------------------------------------------------------
傾頹了的黃金大山
轉過一個又一個的山頭,盤旋過環山繞行的公路,我隨著「礦工的女兒」阿淑,終於抵達了伊的父親向某大公司承包的山谷小礦場。
與瑞三、建基等大礦區相較之下,這兒的的確確是個小礦場罷了。明朗活潑且有著一雙鳳眼的阿淑便是在其中負責會計、薪資,有時並兼任管理等工作。然而,當我隨著阿淑健捷的步伐走下陡斜的山坡石梯後,聽著阿淑與洗煤搬運的女工一一打招呼時,便油然地生起一種家族小公司所特有的感受。
阿淑在前頭介紹環繞著礦場的雞籠山、金瓜石山脈、茶壺山等等地形,然後,她突然指著遠方在山路上盤旋而下的、載滿了黃土沙石的卡車說:「看見沒有?那一輛卡車,就是載黃金的車子。」伊說。
「那不是一輛黃土嗎?」我驚問道。
「對啊!都是從金瓜石山上挖下來的。本來九份、金瓜石盛產黃金,但是已採得差不多了。現在金瓜石的藏量相當少了,所以,乾脆!」伊回頭笑著說:「把山通通挖下來提煉算了!」
「那能提煉多少黃金呢?」
「據說一卡車大約可以提煉一兩吧!」伊說。
我於是無聲地笑了。
一座山的死滅,一座充滿傳奇、夢幻與閃閃黃金的大山,終於即將傾頹了。那尋金者曾經蜂擁沉迷的國度,那貧窮者以「吞金」來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捉迷藏的對抗,終將在大卡車的來回搬運中,傾頹且幻滅了。充滿了夢幻與傳奇的這山頭,終將只剩得一片荒涼而破碎的面貌,化為一兩一兩的黃金流入市場,化為一灘一灘的黃土沙石,向太平洋永遠沉沒了。
礦場上,礦坑口的臺車軌道在陽光中閃亮著褐色的光芒。自礦坑入口蜿蜒而出後,軌道分叉,一條筆直伸入山谷口,用來傾倒廢棄的沙石;一條向右延伸約二十公尺後爬斜坡而上,運上坡地後,傾倒入洗煤場。幾個婦女工作者頭戴斗笠上包著一條大方巾,以便遮陽;身穿碎花粗布衣裳,下身著長褲及塑膠雨鞋。然而衣褲上,卻因煤沙的沾染,大多呈現煤黑色澤。她們在礦坑外從事搬運及洗煤的工作。一個婦女推著裝滿煤礦的臺車到斜坡下,然後又跑上斜坡拉下鐵索,勾好煤車,在陽光中,隨著煤車拉曳而止,她勤奮地上下跑動著,流汗著。
走進了簡陋的辦公室裡,兩個頭戴安全燈的工作者正蹲在地上修理東西。他們抬起頭訝異地望著我。阿淑說:「這是楊先生,他想報導礦工,你們多照顧哦!」他們和善地站起來,說:「手很髒呢!歹勢!歹勢!」我說:「沒關係啦!怕髒就不來了!」「沒要緊啦!握不握都一樣!」他們爽朗地說。
由於他們今天的工作相當繁忙,無法帶我進入礦坑,便相約次日再來。於是我與這位做了幾十年礦工而今因著承租礦場而成為資方的礦場負責人聊天,並詢問了礦工的工作、薪資及身體健康等問題。
薪資與危險性齊頭並進
基本上,礦工的工作時數並不算長,早晨八點入礦坑,中午吃過便當後,將工作告一段落,下午兩點左右便陸續出坑了。每天約工作五小時。工作時間雖不長,但是因全然的體力勞動,因而相當勞累。為了避免身體過疲而疏忽心神,多數礦工在能夠維持生活的原則上,大多不願工作太久。其薪資則係論件計酬的方式,以每天採掘幾車煤來決定。因此與煤層的良否具有莫大關連。好的礦脈可以日進千元以上,壞的礦脈沙土特多時,便只有幾百元而已,所以,礦工們當然指望挖到好礦脈,然而,由於礦工在老成凋謝退休而又後繼乏人的情況下漸漸少了,在「稀為貴」的情況下,礦工的薪資也漸有保障,亦即如果挖到不良礦脈而出煤甚少時,可向資方提出要求,而獲得某一程度的補償。這是指「採掘工」而言。至於「進度工」則是開闢新的坑道,架設支木,好讓採掘工進入工作,因此其薪資是依所開闢坑道的長短而定,越長薪資越多。
礦坑外的「運煤工」與「洗煤工」的薪資,則可分為論件計酬及工作時數兩種方式。平均起來,進度工與採掘工日薪約在七百至一千元左右。不過因著工作疲累,工人們鮮少天天上工,因此,一般月薪約在一萬至兩萬左右。坑外工則因危險性較低,工作較輕鬆,相對的薪資也低很多。
然而,高薪資卻難以吸引年輕人進入礦坑工作了。一來危險性很高,稍一不慎,動輒落盤、入水、瓦斯爆炸,常常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其次則是嚴重的職業病。
目前礦工平均年齡約在四十五至五十之間,他們大多因長期的工作,吸入空氣中的沙塵,沉積肺部而造成了「沙肺」。沙肺本身雖然不至於致命,但會使身體衰弱。更怕因感冒、疲勞過度、煙酒過量等等引起併發症,而將沙肺轉成肺癆,便能置人於死地了。礦場負責人雖然一再強調做礦工是如何的輕鬆好賺錢,但是,當他談起沙肺時,也不禁變色悚然地表示自己也儘量避免進礦坑。因他也在礦坑工作數十年,也患有沙肺。沙肺雖然不傳染、不致命,卻是無法治療的病症。患者只能儘量維持健康,使它不至於轉為肺癆罷了!
但是,普遍罹患沙肺的礦工們卻也只能繼續進入黝暗的礦坑裡,繼續吸取沙塵,一鋤一鏟地謀取生存,一鋤一鏟地為臺灣能源貢獻全部的血汗與生命。
這就是我們面目黧黑,手足胼胝的弟兄的一生。
一切都是這般危殆而艱險
次日早晨,抵達晨光閃耀的山谷小礦場後,我隨同安全人員蘇仔在工寮裡換下全身衣褲,穿上工作服及雨靴,戴上膠盔並佩好安全燈,隨同另外兩人,一齊坐上駛向礦坑的空煤車,緩緩向礦坑入口前進。
煤車由礦坑裡的捲揚機拉曳著,緩緩駛進了礦坑。洞口的光線迅即消失而全然地進入了黑暗。只剩下安全燈照著前面積水的軌道,牆壁上粗大黑溼的支架相思木,和煤車輪子與軌道哐哐噹噹的撞擊聲在四壁有力的迴響著。
我們沿「平水巷」前行。
牆壁上有泉水不時地滲滴下來。不只淋溼了支撐的相思木,更使之發霉而長了一層白色的黴菌,在光線與水珠的襯映下,閃著冰冷森白的光芒。
我在心裡暗暗憂懼起來了:如果相思木因年久失修而斷裂了;如果岩壁因泉水侵蝕而鬆垮了;如果地底冒出一陣狂烈的瓦斯;如果泉水驟而增大向地底淹去……那麼我們平常在報刊上所看到的「災變」,就將成為我們生離死別的葬禮了。是的,在這樣低矮潮溼的坑洞裡,在延伸向地底數百公尺的黑洞中,這個唯一的出口,卻長滿森白的黴菌,泉水淹沒了軌道,一切都是這般危殆而艱險……
然而,這只是我這般庸懦軟弱者的憂懼罷了。蘇仔和他的弟兄們了無懼意地注視著前方,平凡且堅定地開始他們一天的工作,駛向地脈深處。
通過一百多公尺的「平水巷」後,到達「斜坑」的交叉口。我們傴僂著身軀下了煤車,又傴僂著身軀順斜坑向下行走。
所謂平水巷,係指由礦坑入口向山中水平掘進的坑道,其作用只是引入進入山的中心,發現煤礦。然後再順著煤層分布的狀況挖掘。例如煤層以二十五度角向下延伸,坑道便以二十五度角向下挖掘,此謂之「斜坑」。斜坑為向下沿伸的主展線,其兩側又可平行採掘如枝幹,是謂「平巷」。因著左右次序之不同而各有名稱,如左邊第一平巷叫「左一片」,左邊第二平巷叫「左二片」,依此類推。而平巷與平巷間,亦多藏有煤礦,故平巷之間亦可順煤層分布角度而挖掘。其角度大多與斜坑相同,稱之為「工作面」。
一種模糊而親切的感覺
最初,我們沿斜坑軌道向下走。斜坑裡的泉水並不小,嘩嘩地向地底流去,使得路面根本看不清楚,也使得軌道中間的橫木與石頭滑溜難行,再加上低矮的坑道,必須彎腰縮頸才能前進。不多時,我便因時而滑倒、時而頭頂直撞支架而狼狽暈眩不已了。幸而蘇仔不時回顧我是否跟得上,而走在最前端的兩人卻早已失卻蹤跡了。這時,蘇仔頭上的那盞安全燈光以及他的背影遂成為我唯一追尋的前導了。
他在前方以慣於顛躓的步伐,不失穩定地前進著。我在後面狼狽尾隨。且因彎腰過久而腰酸背痛脖硬了。但是望著他的形姿如此,我暗自咬牙提神,勉力緊隨顛躓前行。
蘇仔在左二片的叉口停住,轉過頭來,太強烈的燈光射刺而來,使我無法看清他的面容。他的煤黑色衣服與面容與岩壁融成了整體,只有那一盞強炙的光圈,證實著人與光明之存在。然而當我以光線直射他的面容,看見了他瞇成一條縫的眼睛時,我終而了解,我們在黝暗的地底,都同樣地努力辨認彼此的面容。雖然在黑深的情境裡,無法辨識清晰,但是一種模糊而親切的感覺,卻使我心裡感到一陣溫熱。
闇無一人的左二片裡,靜寂無聲。相思木上厚厚的一層白黴菌閃著森白光芒。水滴不時滲漏下來。而且因著此地是循環系統的末端,空氣較不好,是以一股令人難以呼吸的又溼又辣的味道使我緊張了起來。「會有瓦斯嗎?」我不禁問他。卻又先被自己的焦急乾燥的話聲嚇了一跳。
蘇仔先是驚愕了一下,抬頭以燈光照著我惶惶的面容,才笑了起來,說:「不會啦!放心啦!這裡的礦場屬於金礦山脈的地質結構,很少有瓦斯的。專門產煤的礦區才容易有煤氣、瓦斯的出現。這裡──」他拍拍我的肩膀說:「很安全啦!這只是相思木長黴的味道而已。」
「但是泉水這樣的侵蝕,長期下來,造成岩壁的鬆動,相思木又長黴,會不會危險呢?」我憂心忡忡問道。
「岩壁上的壓力是會變化沒有錯,但是沒有那麼嚴重,而且泉水也有一定的流動層面,即使腐蝕了,也會在支架的相思木上顯出痕跡來。相思木的好處是韌性很強,會變彎曲,但不易斷裂。如果它變彎了,我們就得注意,或者更換支架,或者重新修理,如果不行,就得放棄而封閉它。像這些泉水剛好在山裡而流過,被我們挖到了,便讓它順著斜坑往下流,流到底下,再用抽水機抽出坑外。」他平靜地敘述著。「危險,當然有啦!所以礦工每天進出都得隨時注意啊!不能開玩笑的,自己的生命咧!」
我們面目黧黑、手足胼胝的弟兄
我們繼續傴僂彎腰前進。推開至巷坑口竹門時,一陣強烈新鮮的風颯然灌進來。出了平巷後,我們順著狹窄低矮的斜坑軌道向下走。
這時,一列裝滿了煤沙的車子,自地底黑暗處正哐噹哐噹的拉曳而上。我們趕緊走向稍寬處,緊貼著冷溼的相思木與白黴,煤車剎時恰好在膝蓋前轟然駛過。
我們依舊顛躓前行。最初我尚且能夠注意兩壁的相思木、聯絡線及長度標示牌,但是深入百公尺多以後,在滑跌及撞頂之下,我完完全全地成為狼狽而無意識的尾隨者了。這時我只希望能夠挺直腰身,抬起頭來走路而已。
斜坑裡的泉水嘩嘩向下流,溼淋淋的岩壁閃著黑冷的懾人的壓迫。時高時低的橫樑支架依然撞得我頭暈目眩。然而,站在能源之最源頭的工作者,我們面目黧黑,手足胼胝的弟兄,便是日日在這樣的環境下,彎著腰,縮著脖子,傴僂身軀,勤奮地掘進、採挖、修補,為自己的生存而搏鬥著,在危險幽深的地底,一無憤懣怨氣的奠下工業的磐石。
我們向地底緩緩地深入。
這時,背後的上方傳來煤車駛下來的聲音。我回頭看去,只見兩盞燈光,迅速滑落逼近。蘇仔在他們接近之時,敏捷地拉了一下壁上聯絡的黑繩,車子便停下來,我們搭上便車,順斜坑向下滑落。
斜坑的底部,兩個赤裸上身的進度工正頂著安全燈挖掘著。一個拿著丁字鎬奮力敲擊堅硬的岩壁;一個正彎腰搬運廢石進入煤車裡。安全燈的暖黃光圈照著岩壁,使其凹凸不平的表面的光影之間,現出浮雕般的形狀來。然而安全燈一移開,岩壁便又全然地陷入黑暗了。他們回頭注視蘇仔站在一旁測試空氣。望著他們汗溼的軀體,我說:「很累哦?」
「不會啦?粗工做久,習慣就好了。」他們笑著說。
血汗締造的地下國度
蘇仔於是指著岩壁上一層狹長的黑色質土說:「你看,這一層就是煤礦。」說完撥下一塊拿給我看。我拿在手藉著安全燈加以審視,發現它質地疏鬆,結構相當易碎。他又從其較下方拿下一塊說:「這個就不是煤了。」燈光的照射下,它除了較硬質外,兩者同樣是黑色粗糙,頗難分辨。
事實上,據說這黑色煤質的露頭雖然是狹小條物,卻表示著其中可能蘊藏較大的礦脈,惟不能保證藏量的多寡。所以,很可能在掘進一段坑洞後,卻又發覺藏量稀少而放棄。因此,進度工的工作便不僅是掘進而已,更需要豐富的經驗與敏銳的觀察力,才能使工程更準確、更有效地進行。據說,早期一名熟練的礦工的培養,至少需要費時兩年的長期訓練。
蘇仔與我一邊談著,他們一面繼續工作。方才那位對我笑得真率猶如孩童的掘進者這時舉起丁字鎬,奮力向壁上擊打。壁上咯然一聲悶響,一片岩石便掉了下來,細細的塵土也揚離岩壁,緩緩飄浮然後降落地面。他再度舉鎬揮擊。這一回撞上較硬的岩石,鏗鏘一聲,岩壁悶響,冒出一點火花,岩石並未落下。
他繼續奮力揮鎬,彷彿面對頑強巨大的敵人一般,全身浮凸出一塊塊堅實的肌肉,肌肉上輝閃著一顆顆微小晶瑩的汗珠,以及黏附其上的細細的塵土,幾下擊打後,一大塊岩石鏗然掉落下來,滾過他的腳下,向前翻滾,落在蘇仔的跟前。
我默默地注視著這段過程。不由得在心中暗暗想著:這麼長的坑道,這麼深的地底,便是在他們這般肌肉糾結的擊打中,一鎬一鎬地,一塊一塊地,一寸一寸地試探前進;將岩壁鑿動,尋覓煤礦的蹤跡;將相思木一根一根紮實地架設好;將臺車軌道一段段鋪排;然後,才有著今日深入山的中心,深入地底數百公尺的礦場。
這是如何的血汗,如何的手足所締造的地下國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