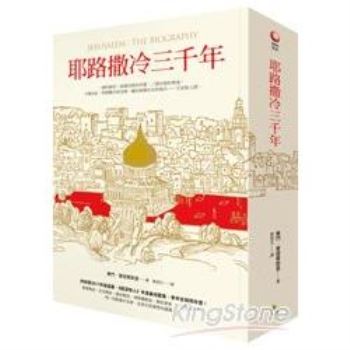再一次置身國際風暴的中心。
不管是雅典還是羅馬,都無法引發如此強烈的熱情。
當猶太人第一次造訪耶路撒冷時,
我們不說那是初來乍到,我們說那是落葉歸根。
──埃利‧維瑟爾
給巴拉克‧歐巴馬的公開信,二○一○年
耶路撒冷的明天
耶路撒冷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渴望求得寬容、分享與慷慨的妙方,以解開偏見、排外與占有的毒素。但這些妙方不容易尋得。兩千年來,耶路撒冷從未像今日一樣如此繁榮、熱鬧且絕大多數由猶太人構成。此外,耶路撒冷也是巴勒斯坦人口最多的城市。有時候,耶路撒冷的猶太性格以一種融合的風格呈現,而與耶路撒冷固有的特質格格不入,因而扭曲了這座城市的過去與現在。
耶路撒冷的歷史是一部移民、殖民者與朝聖者的歷史,這些人包括了阿拉伯人、猶太人與其他民族,而這座城市在歷史上也興衰了數回。經過一千多年的伊斯蘭統治,耶路撒冷不斷受到伊斯蘭移民、學者、蘇菲派與朝聖者的殖民,這些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蘇丹人、伊朗人、庫德族人、伊拉克人與馬格里布人,其他還包括信仰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喬治亞人與俄羅斯人──他們移居耶路撒冷的理由與後來的塞法迪猶太人與俄羅斯猶太人沒什麼不同。正因這樣的特質使阿拉伯的勞倫斯相信,與其說耶路撒冷是阿拉伯城市,不如說它是黎凡特城市,而這正是耶路撒冷固有的特質。
人們經常忽略一件事,城牆外的耶路撒冷郊區是一八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間,由阿拉伯人、猶太人與歐洲人共同建立的新居住區。阿拉伯區域,例如謝克雅拉,並不比猶太區域來得悠久,也不比它來得具正當性。
穆斯林與猶太人提出的歷史主張都無可置疑。猶太人居住與尊崇耶路撒冷已有三千年的歷史,他們與阿拉伯人一樣有權居住在耶路撒冷。然而有時就連恢復最無害的猶太建築物也會被認為不正當:二○一○年,以色列人終於為猶太區重建的胡瓦會堂進行祝聖,這座會堂在一九四八年被約旦人摧毀,但以色列人祝聖的舉動卻引發歐洲媒體的批評,東耶路撒冷也出現小規模的暴動。
然而,還存在著另一種與恢復胡瓦會堂截然不同的做法:既有的阿拉伯居民遭到強行搬遷,他們的財產在可疑的法律判決下遭到剝奪,並且移轉給猶太移民。這些行為在國家與市政府的權力背書下進行,身負神聖使命的宗教狂熱分子也熱心地推動這項行動。充滿侵略性的屯墾建設,目的是為了殖民阿拉伯社區與破壞城市共治的和平協定,此外也有系統地忽視阿拉伯區域的公共與住房建設,凡此種種都讓最不帶特殊色彩的猶太建設蒙上惡名。
以色列面對兩條路線—─耶路撒冷式的宗教民族主義國家,或自由主義的、西化的特拉維夫,後者又有「泡泡」之稱。這裡存在著一種危險,在耶路撒冷推動民族主義計畫,以及在西岸大舉屯墾,很可能弄巧成拙,對猶太人耶路撒冷雖然帶來利益,但對以色列造成的傷害可能更大。然而,無論輿論的看法如何,以色列與其他國家一樣,有權追求自身的安全與繁榮──雖然耶路撒冷的意義不僅只是一國的首都。屯墾有可能破壞以色列做為耶路撒冷一切信仰的保護者的名聲,如果回顧整個歷史來看更是如此。二○一○年,埃利.維瑟爾寫了一封公開信給美國總統歐巴馬,他表示,在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下,「猶太教徒、基督徒與穆斯林在歷史上首度能自由地在自己的神龕進行崇拜」。這句話其實並沒有說錯。
這顯然是西元七○年以來第一次猶太人能夠在耶路撒冷自由崇拜。在基督徒統治期間,猶太人甚至不准進入耶路撒冷。在伊斯蘭統治的數世紀裡,基督徒與猶太人被當成受保護者而獲得寬容,但也經常遭受打壓。猶太人不像基督徒一樣有歐洲大國加以保護,因此經常遭受苛待—─不過不會比在基督教歐洲遭受的最糟待遇更糟。猶太人會因為接近伊斯蘭或基督教聖地而被殺—─但任何人都可以乘驢經過西牆旁的通道,不過就技術上來說,他們必須拿到通行證才行。即使到了二十世紀,猶太人要到西牆仍受到英國人的嚴厲限制,而且遭到約旦人的完全禁止。然而,在以色列人所謂「情勢」下,維瑟爾宣稱的信仰自由對於非猶太人來說是可望不可即,他們必須忍受官僚的騷擾,而隔離牆也使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更難抵達耶路撒冷的圓頂清真寺或阿克薩清真寺祈禱。(待續)當猶太人、穆斯林與基督徒未發生衝突時,他們會回歸古代的耶路撒冷傳統,自欺欺人──把頭埋在沙裡,假裝其他人不存在。二○○八年九月,猶太神聖節日與齋戒月重疊,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前來清真寺與西牆祈禱,造成街頭巷尾的「一神教交通堵塞」,但「若因此稱為『緊繃的遭遇』則並不正確,因為實際上雙方根本碰不到面」,《紐約時報》的伊森.布隆納(Ethan Bronner)表示,「雙方並不交談;眼神也無交流。每個地方與每個時刻都存在著兩個名字不同的平行宇宙,雙方各自宣稱這是他們的聖地與慶典,就這樣持續到深夜」。
從耶路撒冷過去的歷史來看,這種視而不見的做法反而是常態──自從耶路撒冷在全球地位日趨重要後更是如此。今日的耶路撒冷是中東的鬥雞場,是西方世俗主義對上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戰場,更甭說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鬥爭的中心。紐約人、倫敦人與巴黎人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無神的世俗世界裡,有組織的宗教及其信徒頂多只是受到輕微地嘲弄,但基本教義派千禧年亞伯拉罕宗教的信徒數量──基督徒、猶太教徒與穆斯林──卻不斷在增加當中。
耶路撒冷的天啟與政治角色變得越來越令人憂慮。美國充滿活力的民主,總是充斥著多元而世俗的聲音,但它同時也是最後、或許也是最強大的基督教大國──美國的福音派依然在耶路撒冷尋求末日,正如美國政府認為平靜的耶路撒冷是中東和平的關鍵,同時對美國與其他阿拉伯盟友的關係來說也具有戰略核心地位。在此同時,以色列對耶路撒冷的統治也強化了這座城市在穆斯林心中的重要性。在伊朗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日中—─由何梅尼在一九七九年訂定—─耶路撒冷的意義不僅僅是伊斯蘭聖地與巴勒斯坦首都而已。在伊朗以核武追求地區霸權以及與美國冷戰的過程中,耶路撒冷是德黑蘭當局用來團結伊斯蘭什葉派與遜尼派阿拉伯人(遜尼派一直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野心感到懷疑)的工具。不管是黎巴嫩的什葉派真主黨,還是加薩的遜尼派哈馬斯,對他們來說,耶路撒冷現在已成為集合反錫安主義、反美勢力與伊朗領導階層的圖騰。伊朗總統阿哈瑪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表示:「耶路撒冷的占領政權應該從歷史上消失。」他主張千禧年信仰,認為「真主揀選的正直、完美之人馬哈迪(Al-Madhi)」即將再臨,這位「充滿奧秘」的第十二位伊瑪目將解放耶路撒冷,為《古蘭經》「審判日」的到來預做準備。
這種末世論的政治觀點,把二十一世紀的耶路撒冷—─三大宗教共同揀選的城市—─置於一切衝突與願景的交叉點上。耶路撒冷的末日地位也許受到誇大,但隨著變遷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權力、信仰與流行也獨特地結合在耶路撒冷上,這一切全以二十四小時新聞報導的方式呈現,使這座普世之城的脆弱石塊承受極大的壓力,耶路撒冷也因此再度成為世界的中心。
二○一○年,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二世(倉促者阿布杜拉的曾孫)警告:「耶路撒冷這個火絨盒,隨時可能點燃。」「我們這個地區一切的行動,一切的衝突,都會牽扯上耶路撒冷。」因此美國歷任總統總是要在最險惡的時刻趕緊召集各方進行會談。以色列民主內部的鴿派勢力正不斷衰微,脆弱的政府受到強大宗教民族主義黨派的左右,反觀分崩離析的巴勒斯坦派系則在阿拉伯之春的激勵下,企圖協調各方計畫—─例如法塔赫的協商與世俗路線,與哈馬斯的好戰與伊斯蘭主義路線—─以形成統一的巴勒斯坦政府。法塔赫治下的西岸越來越繁榮,但最具活力的巴勒斯坦組織卻是基本教義派的哈馬斯,該組織統治加薩並仍堅持消滅以色列。哈馬斯以自殺炸彈做為首要武器,並且週期性地朝以色列南部發射飛彈,以挑起以色列人入侵。歐洲人與美國人將哈馬斯視為恐怖主義組織,而到目前為止,雙方回歸一九六七年疆界方案的意願似乎仍曖昧不明。在某個時刻,曾一度出現選舉出巴勒斯坦民主政府的曙光,但目前仍無法看出這兩個派系能否彼此合作,組成可靠的政府與以色列對話;此外,我們也無法確定哈馬斯能否成為以色列可信任的夥伴,願意放棄暴力並承認猶太國的存在。與過去的歷史一樣,耶路撒冷總是深受埃及與敘利亞多舛的命運影響—─這兩個國家的革命將重塑整個阿拉伯世界。(待續)一九九三年後的協商歷史,以及高尚言詞與不可信的暴力行為之間的差異,顯示雙方並無意願做出必要讓步以永久分享耶路撒冷。即使在情勢大好之時,要針對耶路撒冷的宗教、民族與情感問題協調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方案,也如同大海撈針般困難—─在整個二十世紀,有超過四十件耶路撒冷計畫失敗,而時至今日,也有十三件方案要求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共同擁有聖殿山。
二○一○年,美國總統歐巴馬要求與巴拉克合組政府的內塔尼雅胡暫時凍結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屯墾計畫。在美以關係陷入空前低潮的情況下,歐巴馬至少能讓雙方重啟談判,不過進展極為緩慢,而且不久即胎死腹中。二○一二年,內塔尼雅胡組織了中間派聯合政府,賦予以色列總理罕有的權力,使其能進行協商—─如果巴勒斯坦地區能暫時維持穩定,而巴勒斯坦各派系可以達成共識,那麼這樣的冒險便是恰當的。
以色列的外交立場相當強硬,不惜犧牲自己的安全與聲譽也要建立屯墾區,但後者是可協商的。巴勒斯坦方面似乎也是一樣。在拉賓、巴拉克與歐爾梅爾特時期,以色列提出耶路撒冷共治方案,包括舊城。一九九三年後將近二十年間,協商仍持續進行,但巴勒斯坦人從未正式同意共治城市,不過當中仍存有一線希望:二○○七年到二○○八年,雙方仍秘密、非正式地進行協商。然而當雙方提出最具彈性的方案,且彼此立場已相當接近時,卻因為協商提早曝光而破局。巴勒斯坦提出的方案遭到洩露,因而引發阿拉伯世界憤怒的指控,紛紛指責巴勒斯坦政府背叛。
耶路撒冷目前的狀態可能持續數十年,然而一旦和約簽訂,必然出現兩個國家,以色列將以國家與民主的形式繼續存在,而巴勒斯坦人將獲得公平的對待與尊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都知道巴勒斯坦國將建於何處,而耶路撒冷勢將由兩國共享。「耶路撒冷將是兩國的首都,阿拉伯郊區將屬巴勒斯坦所有,猶太郊區將屬以色列所有」,以色列總統佩雷斯說道。佩雷斯是奧斯陸協定的推動者,他跟其他人一樣了解這個方案最終會是什麼樣子。以色列人將根據柯林頓定下的條件獲得東耶路撒冷十二個左右的屯墾區,但巴勒斯坦人將從其他以色列土地獲得補償,而西岸絕大多數的以色列屯墾區將予以撤除。以上都算簡單易解的問題,「但真正的挑戰,」佩雷斯解釋說:「是舊城。我們必須在主權與宗教之間做出區別。雙方可以控制自己的神龕,但舊城的主權不可能切割成碎片。」
舊城將成為非軍事化的梵蒂岡,由國際委員會管理,治安由阿拉伯—以色列共同維護或由國際託管國維持,甚至可能出現耶路撒冷版的梵蒂岡瑞士衛兵。阿拉伯人不願接受美國,而以色列不信任聯合國與歐盟,因此這份工作可能交由北約與俄國共同執行,後者再次希望在耶路撒冷發揮一定的影響力。要將聖殿山交由國際管理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沒有任何以色列政治人物可以完全將聖殿礎石的權利讓渡給別人而能存活,同樣地,沒有任何伊斯蘭重要人物可以承認以色列對聖地有完全的主權而能活命。此外,從但澤到的里雅斯德,凡是交由國際管理的城市或自由市,下場都不太好。
聖殿山很難區隔。圓頂清真寺、阿克薩清真寺與西牆都屬於相同結構的一部分。佩雷斯說:「沒有人可以獨占神聖。耶路撒冷與其說是一座城市,不如說是火焰,沒有人可以分割火焰。」無論是不是火焰,主權總要有所歸屬,因此出現了各種計畫主張將地表交給穆斯林,將地道與地下水槽(以及聖殿礎石)交給以色列。地下洞穴、管線與水道形成的昏暗世界,其中的細微與複雜令人驚奇,在耶路撒冷尤其如此:誰擁有地下,誰擁有地表,誰擁有天上?(待續)協議的達成與持續需要其他條件配合。政治主權可以在地圖上釐定,以法律協議表達,並且以M16步槍強制執行,但少了歷史、神秘與情感,那麼這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勞且毫無意義。「阿拉伯與以色列的衝突有三分之二來自心理」,沙達特說。和平的真正條件不只是希律水槽屬於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人所有這些細節,而是互信與尊重這些內心感受的無形之物。雙方都有人否認對方的歷史。如果說這本書有什麼任務,那就是我誠懇地希望它能鼓勵雙方認識與尊重對方的古代遺產:阿拉法特否認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歷史,連巴勒斯坦史家(他們私底下樂於承認猶太人的歷史)都認為荒謬,但沒有人敢冒著掉腦袋的風險向他提出異議。最晚到了二○一○年,只有哲學家薩里.努賽巴有勇氣承認崇高的聖所就是猶太聖殿的遺址。以色列不斷設立屯墾區,不僅削弱阿拉伯人的信心,也使巴勒斯坦建國更加困難。哈馬斯朝以色列發射飛彈等同於戰爭行為,以及巴勒斯坦否認猶太古代歷史也對和平進程帶來重大傷害。然而還有更大的挑戰:雙方必須承認對方的現代神聖敘事,包括各種悲劇與英雄主義。這等於要承認自己原本認為的大惡棍是英雄—─不過即使這一點也有可能做到。
這是耶路撒冷,人們可以輕易想像不可想像之事:耶路撒冷還能存在五年乃至於四十年嗎?我們不排除極端主義分子隨時有摧毀聖殿山的可能,他們會破壞世界的核心,讓基本教義派相信審判日已近,基督與敵基督之戰即將開始。
阿摩斯.奧茲—耶路撒冷作家,現居內蓋夫—曾提出一項離奇的方案:「我們應該把聖地所有的石頭全拆下來,運到斯堪地那維亞存放一百年,直到耶路撒冷人學會和平共處時再運回來。」遺憾的是,這似乎不太可行。
有一千年的時間,耶路撒冷完全掌握在猶太人之手;約四百年的時間,轉而由基督徒掌管;之後的一千三百年,則受到伊斯蘭世界的統治;這三大信仰為了取得耶路撒冷,往往必須動用刀劍、投石機與榴彈砲。他們的民族主義歷史講述的故事,總是經歷一連串的英雄式勝利與突發的災難,但我試圖顯示歷史並非出於必然,當中仍存在各種機會。耶路撒冷人的命運與認同無法截然劃分。希律時代、十字軍時代或英屬耶路撒冷時代的生活就跟今日一樣複雜且充滿細微差異。
這當中有寧靜的發展,也有猛烈的革命。有時候,改變耶路撒冷的是炸藥、鋼鐵與鮮血,但更重要的卻是緩慢的世代傳承,傳唱的歌曲、故事與詩文、雕刻的塑像,家族數百年綿延,從日常生活中養成的潛意識,就像緩步走下迴旋的階梯,而後倏地躍過隔鄰的門檻,或者是不斷打磨粗石,直到其平滑光亮為止。
耶路撒冷是如此可愛,又如此可恨,它層層覆蓋著聖物與殘骸,布滿極其庸俗與極其華美之物,耶路撒冷的生活遠比其他地方來得急切而充滿張力;一切看似靜止,卻又充滿變動。每日破曉,三大信仰的三大聖地各以自己的方式甦醒。(待續)耶路撒冷的今晨
清晨四點三十分,西牆與聖地拉比施穆爾.拉比諾維茨(Shmuel Rabinowitz)從睡夢中醒來,開始一天的早課,閱讀摩西五經。他走過猶太區來到西牆,這裡全天候開放,一層層巨大的希律方石在黑暗中閃爍微光。無論晝夜寒暑,總會有猶太人在這裡祈禱。
這名拉比年約四十歲,是俄羅斯移民的後裔,他的家族來自格爾與魯巴維奇教團,定居耶路撒冷已有七代之久。育有七名子女的他,眼鏡後頭透著藍色眼睛,滿臉鬍子,身穿黑色西裝,頭戴無邊便帽,無論寒暑雨雪,他每日都從這條路行經猶太區,直到巍峨的大希律王城牆出現在他面前。每當他走近「這座世界最大的猶太會堂時,心跳都會禁不住加速。世間的語言不足以形容這種個人與石頭的連結,它完全是精神性的」。
在希律的石牆之上,是圓頂清真寺與阿克薩清真寺,它們坐落在猶太人口中的聖殿山上。拉比諾維茨說:「這裡的空間對我們而言已經足夠,」他堅決反對侵入聖殿山。「總有一天,上帝會重建聖殿—─但此事非人力所能干預。一切應聽任上帝安排。」
身為拉比,他必須保持西牆的整潔:石塊的間隙塞滿了信眾的紙條。一年有兩次清除這些紙條,一次在逾越節前,另一次在猶太新年前。這些紙條被視為神聖之物,他把這些紙條埋在橄欖山上。
當拉比諾維茨抵達西牆時,太陽已經升起,大約七百名猶太人在現場祈禱,但他們總是同一批人,而且總是站在同一個位置:「儀式很重要,它可以讓人集中精神祈禱。」拉比諾維茨不跟這些人打招呼,他也許會向他們點頭示意,但絕不開口說話,因為「第一句話要獻給上帝」。此時他的手臂夾著特菲林(tefillin)。他背誦晨禱文,末尾一句是:「上帝保佑國泰民安。」直到此時,他才適切地與朋友寒暄。西牆的一天於焉開始。
清晨四點前不久,在猶太區的拉比諾維茨起床時,有人拿小卵石敲了幾下瓦基.努賽巴(Wajeeh al-Nusseibeh)位於謝克雅拉的家的窗戶。當努賽巴走出家門時,八十歲的阿迪德.猶貝(Aded al-Judeh)交給他一把沉甸甸的中世紀十二英寸鑰匙。六十歲的努賽巴是耶路撒冷最顯赫的大家族子孫,他穿好西裝,打好領帶,快步通過大馬士革門,前往聖墓教堂。
努賽巴擔任聖墓教堂守護人已超過二十五年,他於清晨四點抵達教堂,準時敲打嵌在梅莉桑德羅曼式正面的高聳古門。努賽巴每晚八點鎖門,在教堂裡擔任司事的希臘人、拉丁人與亞美尼亞人已經分配好哪一天由誰開門。管理聖墓教堂的三個教會僧侶整晚相處愉快,並且進行各項禮拜儀式。凌晨兩點,居於支配地位的正教會率先進行彌撒,八名僧侶繞著聖墓以希臘語詠唱聖歌;之後接棒的是亞美尼亞人,他們以亞美尼亞語進行巴達拉克(badarak)儀式,儀式開始的時間正好是開門的時間;天主教徒的儀式從早晨六點開始。就在此時,所有的教團一起進行晨禱。只有一名科普特僧侶獲准整夜祈禱,不過他用的語言是古科普特埃及語。
教堂大門開啟時,衣索比亞人—─他們待在屋頂的修院與聖米迦勒禮拜堂裡,禮拜堂的入口就在正門旁邊—─開始以阿姆哈拉語(Amharic)詠唱聖歌,他們的儀式非常漫長,因此他們經常會斜倚在牧者的曲柄杖上,這些堆放在教堂裡的木杖原是為疲倦的崇拜者準備的。到了晚間,各種語言的誦念聲與聖歌在教堂內迴盪著,宛如各種鳥類在石林中鳴唱悅耳的樂曲。這裡是耶路撒冷,努賽巴無法預料下一刻將發生什麼事:「我知道有數千人仰賴我打開大門,我擔心如果有一天開不了大門或出了什麼差錯該怎麼辦。我第一次開門是在十五歲時,當時的我覺得新奇有趣,但現在我知道這是件嚴肅的事。」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他都必須準時開門,他說他的父親為了以防萬一,經常睡在教堂的門廊。(待續)努賽巴知道一年之中教堂內的僧侶總會有幾次爭吵。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僧侶只是偶爾表現出謙恭有禮的樣子(也許只是基於禮貌,或藉此打發聖墓教堂漫長守夜的無聊),實際上歷史累積的憎恨很可能在任何時刻爆發,特別是在復活節。希臘人控制了大部分的聖墓教堂,他們的人數最多,也經常在與天主教徒及亞美尼亞人的衝突中獲勝。科普特人與衣索比亞人雖然都主張單性說,兩者之間的仇恨卻特深:六日戰爭後,以色列人罕見地將科普特聖米迦勒禮拜堂交給衣索比亞人使用,以懲罰納瑟的埃及與支持海爾.塞拉西的衣索比亞。在進行和平協商時,埃及不斷提出支持科普特人的方案。以色列高等法院判決聖米迦勒禮拜堂屬科普特人所有,但實際占有者仍是衣索比亞人,相當典型的耶路撒冷解決模式。二○○二年七月,當科普特僧侶在衣索比亞搖搖欲墜的屋頂建築物旁曬太陽時,遭衣索比亞人以鐵棒攻擊,以報復科普特人苛待他們的非洲同胞。科普特人立刻趕去幫忙被揍的僧侶,結果四名科普特人與七名衣索比亞人(後者似乎每次衝突都會輸)被送往醫院。
二○○四年九月的聖十字架節,希臘宗主教伊瑞奈歐斯(Ireneos)要求方濟會關閉顯靈禮拜堂。當對方拒絕時,伊瑞奈歐斯便率領衛兵與僧侶對抗拉丁人。以色列警方進行干預,卻遭到攻擊,當這些僧侶成為敵人時,凶悍程度不下於巴勒斯坦的投石者。二○○五年的聖火儀式,亞美尼亞人與希臘人發生集體鬥毆,結果亞美尼亞人獲勝,取代希臘人成為儀式的主持者。好鬥的伊瑞奈歐斯宗主教,最後因將雅法門附近的帝國飯店賣給以色列移民而遭到免職。努賽巴無奈地聳肩:「當他們有煩惱時,我還是要為他們定紛止爭,因為大家都是同胞兄弟。我們就像聯合國一樣保持中立,我們的任務是讓聖地保持和平。」努賽巴與猶貝每次遇到基督教節慶,往往必須負擔各種複雜的角色。在狂熱而擁擠的聖火儀式中,努賽巴擔任的是官方的見證人。
現在,教堂內的司事打開嵌在右手邊大門上的小門,從裡面遞出一道梯子。努賽巴接過梯子,然後將梯子斜靠在左手邊大門上。努賽巴先把右手邊大門下方的鎖打開,然後爬上梯子把上面的鎖打開。努賽巴爬下梯子之後,教堂內的僧侶將大門搖晃了幾下,然後將大門左扇門板推開。努賽巴走進教堂,向僧侶們問好:「祝平安!」
「祝平安!」他們愉快地回道。努賽巴家族與猶貝家族至少從一一九二年起就持續開啟著聖墓教堂的大門,薩拉丁任命猶貝家族為「鑰匙的保管者」,而努賽巴家族為「聖墓教堂的守護人與守門人」(瓦基的名片上印著這個頭銜)。努賽巴家族—他們也曾被任命為圓頂清真寺裡的薩克拉(礎石)世襲清掃人—─表示薩拉丁曾讓他們恢復六三八年歐瑪爾哈里發授予他們的地位。直到一八三○年代阿爾巴尼亞人征服為止,努賽巴家族一直非常富裕,但之後則淪為擔任導遊為生。(待續)努賽巴家族與猶貝家族彼此處於警戒對立的關係。「努賽巴家族與我們沒有關係,」八十歲的猶貝說道,他已保管了二十二年的鑰匙,「他們只是守門人。」而努賽巴則堅稱「猶貝家族不許觸摸大門或門鎖」,顯示伊斯蘭本身的對立與基督徒自身的對立一樣鮮明。瓦基的兒子歐巴達(Obadah)是他的繼承人。
跟過去八百年來的祖先一樣,努賽巴與猶貝每天會待在大廳一段時間—─但這裡並非他們的信仰所在。「我了解這裡的每一塊石頭,這裡就像我家一樣」,努賽巴若有所思地說。他尊崇聖墓教堂:「我們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耶穌與摩西是先知,而馬利亞非常神聖,所以這座教堂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如果他想祈禱的話,可以從側門出去,前往隔壁的清真寺(當初建造這座清真寺是為了震懾基督徒),或走個五分鐘到阿克薩清真寺。
就在西牆拉比醒來與努賽巴守護人聽見有人敲窗準備遞給他聖墓教堂鑰匙的同時,四十二歲、育有五名子女的阿德布.安薩里(Adeb al-Ansari),身穿黑色皮革外套走出他位於穆斯林區的馬木魯克房子(這是他的家族共有的房子),沿著街道走了五分鐘,來到東北角的哈旺梅門。他通過身穿藍衣的以色列警察檢查哨,諷刺的是,這些警察通常由德魯茲派或加利利阿拉伯人出任,他們負責禁止猶太人進入。然後,安薩里來到崇高的聖所。
神聖的廣場已經設了電燈,在過去,他的父親要耗費兩個小時才能將所有的燈點上。安薩里與聖地安全人員打過招呼之後,開始開啟圓頂清真寺的四扇大門,與阿克薩清真寺的十扇門。這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安薩里家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與穆罕默德一起前往麥地那的安薩里家族,他們宣稱自己曾被歐瑪爾任命為聖地守護人,日後他們的職位又進一步受到薩拉丁的確認。(安薩里家族曾有管理聖地的謝克收受蒙提.帕克的賄賂,這成了家族的恥辱。)
清真寺必須在晨禱前一個小時開啟。安薩里不需要每天前來,他現在有一個團隊,但在他繼承世襲的守護人職位之前,他每天早上都必須過來開門,而他也感到自豪:「首先這是一份工作,然後是家族的財產與重大的責任,然而最重要的是,這是一項高尚而神聖的任務。但薪水不高,所以我必須在橄欖山的飯店櫃臺工作。」
聖地的世襲職位逐漸消失。席哈比家族(Shihabis)是另一個大家族,他們是黎巴嫩王公的後裔,住在靠近小牆的家族共有住宅,並且曾經是先知鬍子的守護人。鬍子與守護人的職位已經不存在,但聖地對他們仍具有吸引力—─席哈比家族仍在聖地工作。
如同拉比走向西牆,努賽巴在聖墓教堂敲門,安薩里打開清真寺大門,那吉.卡札茲(Naji Qazaz)離開位於勝利鐵門街家族已擁有兩百二十五年的屋子,沿著老馬木魯克街道步行幾碼,然後走上臺階,經過鐵門,來到聖地。卡札茲直接前往阿克薩清真寺,進到一個小房間裡,裡面擺著麥克風與幾瓶礦泉水。一九六○年前,卡札茲家族仍使用清真寺尖塔叫拜,現在他們則利用這個房間來預做準備,彷彿運動選手一樣。古札茲有二十分鐘的時間做伸展運動,他深呼吸,然後漱口。確認麥克風已經開啟,再看看牆上的時鐘,時間一到,他便面向麥加克爾白,開始叫拜,他的聲音在整座舊城裡迴盪著。
自從馬木魯克蘇丹卡伊特拜伊統治以來,卡札茲家族在阿克薩清真寺擔任宣禮員已有五百年的歷史。那吉擔任宣禮員已有三十年,他和兒子菲拉茲(Firaz)與兩個親戚共同分攤這份工作。
現在,距離日出還有一個小時。圓頂清真寺已經開放:穆斯林正在禱告。西牆一直是開放的:猶太人正在禱告。聖墓教堂開放了:基督徒以各種語言禱告。太陽升起,照耀著耶路撒冷,它的光芒使希律西牆的石塊亮如白雪—─如同兩千年前約瑟夫斯所描述的—─清真寺的黃金圓頂也熠熠生輝。神聖的廣場是天與地、上帝與人類交會之處,它依然是人類難以描繪之地。唯有太陽的光芒能遍照整座廣場,最後,所有的光線將照耀在耶路撒冷最優美而神秘的建築物上。沐浴於日光之中,散發出奪目的光采,它也因此博得黃金的美名。但金門依然深鎖,直到末日來臨,它才有重新開啟的機會。
不管是雅典還是羅馬,都無法引發如此強烈的熱情。
當猶太人第一次造訪耶路撒冷時,
我們不說那是初來乍到,我們說那是落葉歸根。
──埃利‧維瑟爾
給巴拉克‧歐巴馬的公開信,二○一○年
耶路撒冷的明天
耶路撒冷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渴望求得寬容、分享與慷慨的妙方,以解開偏見、排外與占有的毒素。但這些妙方不容易尋得。兩千年來,耶路撒冷從未像今日一樣如此繁榮、熱鬧且絕大多數由猶太人構成。此外,耶路撒冷也是巴勒斯坦人口最多的城市。有時候,耶路撒冷的猶太性格以一種融合的風格呈現,而與耶路撒冷固有的特質格格不入,因而扭曲了這座城市的過去與現在。
耶路撒冷的歷史是一部移民、殖民者與朝聖者的歷史,這些人包括了阿拉伯人、猶太人與其他民族,而這座城市在歷史上也興衰了數回。經過一千多年的伊斯蘭統治,耶路撒冷不斷受到伊斯蘭移民、學者、蘇菲派與朝聖者的殖民,這些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蘇丹人、伊朗人、庫德族人、伊拉克人與馬格里布人,其他還包括信仰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喬治亞人與俄羅斯人──他們移居耶路撒冷的理由與後來的塞法迪猶太人與俄羅斯猶太人沒什麼不同。正因這樣的特質使阿拉伯的勞倫斯相信,與其說耶路撒冷是阿拉伯城市,不如說它是黎凡特城市,而這正是耶路撒冷固有的特質。
人們經常忽略一件事,城牆外的耶路撒冷郊區是一八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間,由阿拉伯人、猶太人與歐洲人共同建立的新居住區。阿拉伯區域,例如謝克雅拉,並不比猶太區域來得悠久,也不比它來得具正當性。
穆斯林與猶太人提出的歷史主張都無可置疑。猶太人居住與尊崇耶路撒冷已有三千年的歷史,他們與阿拉伯人一樣有權居住在耶路撒冷。然而有時就連恢復最無害的猶太建築物也會被認為不正當:二○一○年,以色列人終於為猶太區重建的胡瓦會堂進行祝聖,這座會堂在一九四八年被約旦人摧毀,但以色列人祝聖的舉動卻引發歐洲媒體的批評,東耶路撒冷也出現小規模的暴動。
然而,還存在著另一種與恢復胡瓦會堂截然不同的做法:既有的阿拉伯居民遭到強行搬遷,他們的財產在可疑的法律判決下遭到剝奪,並且移轉給猶太移民。這些行為在國家與市政府的權力背書下進行,身負神聖使命的宗教狂熱分子也熱心地推動這項行動。充滿侵略性的屯墾建設,目的是為了殖民阿拉伯社區與破壞城市共治的和平協定,此外也有系統地忽視阿拉伯區域的公共與住房建設,凡此種種都讓最不帶特殊色彩的猶太建設蒙上惡名。
以色列面對兩條路線—─耶路撒冷式的宗教民族主義國家,或自由主義的、西化的特拉維夫,後者又有「泡泡」之稱。這裡存在著一種危險,在耶路撒冷推動民族主義計畫,以及在西岸大舉屯墾,很可能弄巧成拙,對猶太人耶路撒冷雖然帶來利益,但對以色列造成的傷害可能更大。然而,無論輿論的看法如何,以色列與其他國家一樣,有權追求自身的安全與繁榮──雖然耶路撒冷的意義不僅只是一國的首都。屯墾有可能破壞以色列做為耶路撒冷一切信仰的保護者的名聲,如果回顧整個歷史來看更是如此。二○一○年,埃利.維瑟爾寫了一封公開信給美國總統歐巴馬,他表示,在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下,「猶太教徒、基督徒與穆斯林在歷史上首度能自由地在自己的神龕進行崇拜」。這句話其實並沒有說錯。
這顯然是西元七○年以來第一次猶太人能夠在耶路撒冷自由崇拜。在基督徒統治期間,猶太人甚至不准進入耶路撒冷。在伊斯蘭統治的數世紀裡,基督徒與猶太人被當成受保護者而獲得寬容,但也經常遭受打壓。猶太人不像基督徒一樣有歐洲大國加以保護,因此經常遭受苛待—─不過不會比在基督教歐洲遭受的最糟待遇更糟。猶太人會因為接近伊斯蘭或基督教聖地而被殺—─但任何人都可以乘驢經過西牆旁的通道,不過就技術上來說,他們必須拿到通行證才行。即使到了二十世紀,猶太人要到西牆仍受到英國人的嚴厲限制,而且遭到約旦人的完全禁止。然而,在以色列人所謂「情勢」下,維瑟爾宣稱的信仰自由對於非猶太人來說是可望不可即,他們必須忍受官僚的騷擾,而隔離牆也使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更難抵達耶路撒冷的圓頂清真寺或阿克薩清真寺祈禱。(待續)當猶太人、穆斯林與基督徒未發生衝突時,他們會回歸古代的耶路撒冷傳統,自欺欺人──把頭埋在沙裡,假裝其他人不存在。二○○八年九月,猶太神聖節日與齋戒月重疊,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前來清真寺與西牆祈禱,造成街頭巷尾的「一神教交通堵塞」,但「若因此稱為『緊繃的遭遇』則並不正確,因為實際上雙方根本碰不到面」,《紐約時報》的伊森.布隆納(Ethan Bronner)表示,「雙方並不交談;眼神也無交流。每個地方與每個時刻都存在著兩個名字不同的平行宇宙,雙方各自宣稱這是他們的聖地與慶典,就這樣持續到深夜」。
從耶路撒冷過去的歷史來看,這種視而不見的做法反而是常態──自從耶路撒冷在全球地位日趨重要後更是如此。今日的耶路撒冷是中東的鬥雞場,是西方世俗主義對上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戰場,更甭說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鬥爭的中心。紐約人、倫敦人與巴黎人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無神的世俗世界裡,有組織的宗教及其信徒頂多只是受到輕微地嘲弄,但基本教義派千禧年亞伯拉罕宗教的信徒數量──基督徒、猶太教徒與穆斯林──卻不斷在增加當中。
耶路撒冷的天啟與政治角色變得越來越令人憂慮。美國充滿活力的民主,總是充斥著多元而世俗的聲音,但它同時也是最後、或許也是最強大的基督教大國──美國的福音派依然在耶路撒冷尋求末日,正如美國政府認為平靜的耶路撒冷是中東和平的關鍵,同時對美國與其他阿拉伯盟友的關係來說也具有戰略核心地位。在此同時,以色列對耶路撒冷的統治也強化了這座城市在穆斯林心中的重要性。在伊朗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日中—─由何梅尼在一九七九年訂定—─耶路撒冷的意義不僅僅是伊斯蘭聖地與巴勒斯坦首都而已。在伊朗以核武追求地區霸權以及與美國冷戰的過程中,耶路撒冷是德黑蘭當局用來團結伊斯蘭什葉派與遜尼派阿拉伯人(遜尼派一直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野心感到懷疑)的工具。不管是黎巴嫩的什葉派真主黨,還是加薩的遜尼派哈馬斯,對他們來說,耶路撒冷現在已成為集合反錫安主義、反美勢力與伊朗領導階層的圖騰。伊朗總統阿哈瑪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表示:「耶路撒冷的占領政權應該從歷史上消失。」他主張千禧年信仰,認為「真主揀選的正直、完美之人馬哈迪(Al-Madhi)」即將再臨,這位「充滿奧秘」的第十二位伊瑪目將解放耶路撒冷,為《古蘭經》「審判日」的到來預做準備。
這種末世論的政治觀點,把二十一世紀的耶路撒冷—─三大宗教共同揀選的城市—─置於一切衝突與願景的交叉點上。耶路撒冷的末日地位也許受到誇大,但隨著變遷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權力、信仰與流行也獨特地結合在耶路撒冷上,這一切全以二十四小時新聞報導的方式呈現,使這座普世之城的脆弱石塊承受極大的壓力,耶路撒冷也因此再度成為世界的中心。
二○一○年,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二世(倉促者阿布杜拉的曾孫)警告:「耶路撒冷這個火絨盒,隨時可能點燃。」「我們這個地區一切的行動,一切的衝突,都會牽扯上耶路撒冷。」因此美國歷任總統總是要在最險惡的時刻趕緊召集各方進行會談。以色列民主內部的鴿派勢力正不斷衰微,脆弱的政府受到強大宗教民族主義黨派的左右,反觀分崩離析的巴勒斯坦派系則在阿拉伯之春的激勵下,企圖協調各方計畫—─例如法塔赫的協商與世俗路線,與哈馬斯的好戰與伊斯蘭主義路線—─以形成統一的巴勒斯坦政府。法塔赫治下的西岸越來越繁榮,但最具活力的巴勒斯坦組織卻是基本教義派的哈馬斯,該組織統治加薩並仍堅持消滅以色列。哈馬斯以自殺炸彈做為首要武器,並且週期性地朝以色列南部發射飛彈,以挑起以色列人入侵。歐洲人與美國人將哈馬斯視為恐怖主義組織,而到目前為止,雙方回歸一九六七年疆界方案的意願似乎仍曖昧不明。在某個時刻,曾一度出現選舉出巴勒斯坦民主政府的曙光,但目前仍無法看出這兩個派系能否彼此合作,組成可靠的政府與以色列對話;此外,我們也無法確定哈馬斯能否成為以色列可信任的夥伴,願意放棄暴力並承認猶太國的存在。與過去的歷史一樣,耶路撒冷總是深受埃及與敘利亞多舛的命運影響—─這兩個國家的革命將重塑整個阿拉伯世界。(待續)一九九三年後的協商歷史,以及高尚言詞與不可信的暴力行為之間的差異,顯示雙方並無意願做出必要讓步以永久分享耶路撒冷。即使在情勢大好之時,要針對耶路撒冷的宗教、民族與情感問題協調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方案,也如同大海撈針般困難—─在整個二十世紀,有超過四十件耶路撒冷計畫失敗,而時至今日,也有十三件方案要求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共同擁有聖殿山。
二○一○年,美國總統歐巴馬要求與巴拉克合組政府的內塔尼雅胡暫時凍結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屯墾計畫。在美以關係陷入空前低潮的情況下,歐巴馬至少能讓雙方重啟談判,不過進展極為緩慢,而且不久即胎死腹中。二○一二年,內塔尼雅胡組織了中間派聯合政府,賦予以色列總理罕有的權力,使其能進行協商—─如果巴勒斯坦地區能暫時維持穩定,而巴勒斯坦各派系可以達成共識,那麼這樣的冒險便是恰當的。
以色列的外交立場相當強硬,不惜犧牲自己的安全與聲譽也要建立屯墾區,但後者是可協商的。巴勒斯坦方面似乎也是一樣。在拉賓、巴拉克與歐爾梅爾特時期,以色列提出耶路撒冷共治方案,包括舊城。一九九三年後將近二十年間,協商仍持續進行,但巴勒斯坦人從未正式同意共治城市,不過當中仍存有一線希望:二○○七年到二○○八年,雙方仍秘密、非正式地進行協商。然而當雙方提出最具彈性的方案,且彼此立場已相當接近時,卻因為協商提早曝光而破局。巴勒斯坦提出的方案遭到洩露,因而引發阿拉伯世界憤怒的指控,紛紛指責巴勒斯坦政府背叛。
耶路撒冷目前的狀態可能持續數十年,然而一旦和約簽訂,必然出現兩個國家,以色列將以國家與民主的形式繼續存在,而巴勒斯坦人將獲得公平的對待與尊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都知道巴勒斯坦國將建於何處,而耶路撒冷勢將由兩國共享。「耶路撒冷將是兩國的首都,阿拉伯郊區將屬巴勒斯坦所有,猶太郊區將屬以色列所有」,以色列總統佩雷斯說道。佩雷斯是奧斯陸協定的推動者,他跟其他人一樣了解這個方案最終會是什麼樣子。以色列人將根據柯林頓定下的條件獲得東耶路撒冷十二個左右的屯墾區,但巴勒斯坦人將從其他以色列土地獲得補償,而西岸絕大多數的以色列屯墾區將予以撤除。以上都算簡單易解的問題,「但真正的挑戰,」佩雷斯解釋說:「是舊城。我們必須在主權與宗教之間做出區別。雙方可以控制自己的神龕,但舊城的主權不可能切割成碎片。」
舊城將成為非軍事化的梵蒂岡,由國際委員會管理,治安由阿拉伯—以色列共同維護或由國際託管國維持,甚至可能出現耶路撒冷版的梵蒂岡瑞士衛兵。阿拉伯人不願接受美國,而以色列不信任聯合國與歐盟,因此這份工作可能交由北約與俄國共同執行,後者再次希望在耶路撒冷發揮一定的影響力。要將聖殿山交由國際管理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沒有任何以色列政治人物可以完全將聖殿礎石的權利讓渡給別人而能存活,同樣地,沒有任何伊斯蘭重要人物可以承認以色列對聖地有完全的主權而能活命。此外,從但澤到的里雅斯德,凡是交由國際管理的城市或自由市,下場都不太好。
聖殿山很難區隔。圓頂清真寺、阿克薩清真寺與西牆都屬於相同結構的一部分。佩雷斯說:「沒有人可以獨占神聖。耶路撒冷與其說是一座城市,不如說是火焰,沒有人可以分割火焰。」無論是不是火焰,主權總要有所歸屬,因此出現了各種計畫主張將地表交給穆斯林,將地道與地下水槽(以及聖殿礎石)交給以色列。地下洞穴、管線與水道形成的昏暗世界,其中的細微與複雜令人驚奇,在耶路撒冷尤其如此:誰擁有地下,誰擁有地表,誰擁有天上?(待續)協議的達成與持續需要其他條件配合。政治主權可以在地圖上釐定,以法律協議表達,並且以M16步槍強制執行,但少了歷史、神秘與情感,那麼這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勞且毫無意義。「阿拉伯與以色列的衝突有三分之二來自心理」,沙達特說。和平的真正條件不只是希律水槽屬於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人所有這些細節,而是互信與尊重這些內心感受的無形之物。雙方都有人否認對方的歷史。如果說這本書有什麼任務,那就是我誠懇地希望它能鼓勵雙方認識與尊重對方的古代遺產:阿拉法特否認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歷史,連巴勒斯坦史家(他們私底下樂於承認猶太人的歷史)都認為荒謬,但沒有人敢冒著掉腦袋的風險向他提出異議。最晚到了二○一○年,只有哲學家薩里.努賽巴有勇氣承認崇高的聖所就是猶太聖殿的遺址。以色列不斷設立屯墾區,不僅削弱阿拉伯人的信心,也使巴勒斯坦建國更加困難。哈馬斯朝以色列發射飛彈等同於戰爭行為,以及巴勒斯坦否認猶太古代歷史也對和平進程帶來重大傷害。然而還有更大的挑戰:雙方必須承認對方的現代神聖敘事,包括各種悲劇與英雄主義。這等於要承認自己原本認為的大惡棍是英雄—─不過即使這一點也有可能做到。
這是耶路撒冷,人們可以輕易想像不可想像之事:耶路撒冷還能存在五年乃至於四十年嗎?我們不排除極端主義分子隨時有摧毀聖殿山的可能,他們會破壞世界的核心,讓基本教義派相信審判日已近,基督與敵基督之戰即將開始。
阿摩斯.奧茲—耶路撒冷作家,現居內蓋夫—曾提出一項離奇的方案:「我們應該把聖地所有的石頭全拆下來,運到斯堪地那維亞存放一百年,直到耶路撒冷人學會和平共處時再運回來。」遺憾的是,這似乎不太可行。
有一千年的時間,耶路撒冷完全掌握在猶太人之手;約四百年的時間,轉而由基督徒掌管;之後的一千三百年,則受到伊斯蘭世界的統治;這三大信仰為了取得耶路撒冷,往往必須動用刀劍、投石機與榴彈砲。他們的民族主義歷史講述的故事,總是經歷一連串的英雄式勝利與突發的災難,但我試圖顯示歷史並非出於必然,當中仍存在各種機會。耶路撒冷人的命運與認同無法截然劃分。希律時代、十字軍時代或英屬耶路撒冷時代的生活就跟今日一樣複雜且充滿細微差異。
這當中有寧靜的發展,也有猛烈的革命。有時候,改變耶路撒冷的是炸藥、鋼鐵與鮮血,但更重要的卻是緩慢的世代傳承,傳唱的歌曲、故事與詩文、雕刻的塑像,家族數百年綿延,從日常生活中養成的潛意識,就像緩步走下迴旋的階梯,而後倏地躍過隔鄰的門檻,或者是不斷打磨粗石,直到其平滑光亮為止。
耶路撒冷是如此可愛,又如此可恨,它層層覆蓋著聖物與殘骸,布滿極其庸俗與極其華美之物,耶路撒冷的生活遠比其他地方來得急切而充滿張力;一切看似靜止,卻又充滿變動。每日破曉,三大信仰的三大聖地各以自己的方式甦醒。(待續)耶路撒冷的今晨
清晨四點三十分,西牆與聖地拉比施穆爾.拉比諾維茨(Shmuel Rabinowitz)從睡夢中醒來,開始一天的早課,閱讀摩西五經。他走過猶太區來到西牆,這裡全天候開放,一層層巨大的希律方石在黑暗中閃爍微光。無論晝夜寒暑,總會有猶太人在這裡祈禱。
這名拉比年約四十歲,是俄羅斯移民的後裔,他的家族來自格爾與魯巴維奇教團,定居耶路撒冷已有七代之久。育有七名子女的他,眼鏡後頭透著藍色眼睛,滿臉鬍子,身穿黑色西裝,頭戴無邊便帽,無論寒暑雨雪,他每日都從這條路行經猶太區,直到巍峨的大希律王城牆出現在他面前。每當他走近「這座世界最大的猶太會堂時,心跳都會禁不住加速。世間的語言不足以形容這種個人與石頭的連結,它完全是精神性的」。
在希律的石牆之上,是圓頂清真寺與阿克薩清真寺,它們坐落在猶太人口中的聖殿山上。拉比諾維茨說:「這裡的空間對我們而言已經足夠,」他堅決反對侵入聖殿山。「總有一天,上帝會重建聖殿—─但此事非人力所能干預。一切應聽任上帝安排。」
身為拉比,他必須保持西牆的整潔:石塊的間隙塞滿了信眾的紙條。一年有兩次清除這些紙條,一次在逾越節前,另一次在猶太新年前。這些紙條被視為神聖之物,他把這些紙條埋在橄欖山上。
當拉比諾維茨抵達西牆時,太陽已經升起,大約七百名猶太人在現場祈禱,但他們總是同一批人,而且總是站在同一個位置:「儀式很重要,它可以讓人集中精神祈禱。」拉比諾維茨不跟這些人打招呼,他也許會向他們點頭示意,但絕不開口說話,因為「第一句話要獻給上帝」。此時他的手臂夾著特菲林(tefillin)。他背誦晨禱文,末尾一句是:「上帝保佑國泰民安。」直到此時,他才適切地與朋友寒暄。西牆的一天於焉開始。
清晨四點前不久,在猶太區的拉比諾維茨起床時,有人拿小卵石敲了幾下瓦基.努賽巴(Wajeeh al-Nusseibeh)位於謝克雅拉的家的窗戶。當努賽巴走出家門時,八十歲的阿迪德.猶貝(Aded al-Judeh)交給他一把沉甸甸的中世紀十二英寸鑰匙。六十歲的努賽巴是耶路撒冷最顯赫的大家族子孫,他穿好西裝,打好領帶,快步通過大馬士革門,前往聖墓教堂。
努賽巴擔任聖墓教堂守護人已超過二十五年,他於清晨四點抵達教堂,準時敲打嵌在梅莉桑德羅曼式正面的高聳古門。努賽巴每晚八點鎖門,在教堂裡擔任司事的希臘人、拉丁人與亞美尼亞人已經分配好哪一天由誰開門。管理聖墓教堂的三個教會僧侶整晚相處愉快,並且進行各項禮拜儀式。凌晨兩點,居於支配地位的正教會率先進行彌撒,八名僧侶繞著聖墓以希臘語詠唱聖歌;之後接棒的是亞美尼亞人,他們以亞美尼亞語進行巴達拉克(badarak)儀式,儀式開始的時間正好是開門的時間;天主教徒的儀式從早晨六點開始。就在此時,所有的教團一起進行晨禱。只有一名科普特僧侶獲准整夜祈禱,不過他用的語言是古科普特埃及語。
教堂大門開啟時,衣索比亞人—─他們待在屋頂的修院與聖米迦勒禮拜堂裡,禮拜堂的入口就在正門旁邊—─開始以阿姆哈拉語(Amharic)詠唱聖歌,他們的儀式非常漫長,因此他們經常會斜倚在牧者的曲柄杖上,這些堆放在教堂裡的木杖原是為疲倦的崇拜者準備的。到了晚間,各種語言的誦念聲與聖歌在教堂內迴盪著,宛如各種鳥類在石林中鳴唱悅耳的樂曲。這裡是耶路撒冷,努賽巴無法預料下一刻將發生什麼事:「我知道有數千人仰賴我打開大門,我擔心如果有一天開不了大門或出了什麼差錯該怎麼辦。我第一次開門是在十五歲時,當時的我覺得新奇有趣,但現在我知道這是件嚴肅的事。」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他都必須準時開門,他說他的父親為了以防萬一,經常睡在教堂的門廊。(待續)努賽巴知道一年之中教堂內的僧侶總會有幾次爭吵。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僧侶只是偶爾表現出謙恭有禮的樣子(也許只是基於禮貌,或藉此打發聖墓教堂漫長守夜的無聊),實際上歷史累積的憎恨很可能在任何時刻爆發,特別是在復活節。希臘人控制了大部分的聖墓教堂,他們的人數最多,也經常在與天主教徒及亞美尼亞人的衝突中獲勝。科普特人與衣索比亞人雖然都主張單性說,兩者之間的仇恨卻特深:六日戰爭後,以色列人罕見地將科普特聖米迦勒禮拜堂交給衣索比亞人使用,以懲罰納瑟的埃及與支持海爾.塞拉西的衣索比亞。在進行和平協商時,埃及不斷提出支持科普特人的方案。以色列高等法院判決聖米迦勒禮拜堂屬科普特人所有,但實際占有者仍是衣索比亞人,相當典型的耶路撒冷解決模式。二○○二年七月,當科普特僧侶在衣索比亞搖搖欲墜的屋頂建築物旁曬太陽時,遭衣索比亞人以鐵棒攻擊,以報復科普特人苛待他們的非洲同胞。科普特人立刻趕去幫忙被揍的僧侶,結果四名科普特人與七名衣索比亞人(後者似乎每次衝突都會輸)被送往醫院。
二○○四年九月的聖十字架節,希臘宗主教伊瑞奈歐斯(Ireneos)要求方濟會關閉顯靈禮拜堂。當對方拒絕時,伊瑞奈歐斯便率領衛兵與僧侶對抗拉丁人。以色列警方進行干預,卻遭到攻擊,當這些僧侶成為敵人時,凶悍程度不下於巴勒斯坦的投石者。二○○五年的聖火儀式,亞美尼亞人與希臘人發生集體鬥毆,結果亞美尼亞人獲勝,取代希臘人成為儀式的主持者。好鬥的伊瑞奈歐斯宗主教,最後因將雅法門附近的帝國飯店賣給以色列移民而遭到免職。努賽巴無奈地聳肩:「當他們有煩惱時,我還是要為他們定紛止爭,因為大家都是同胞兄弟。我們就像聯合國一樣保持中立,我們的任務是讓聖地保持和平。」努賽巴與猶貝每次遇到基督教節慶,往往必須負擔各種複雜的角色。在狂熱而擁擠的聖火儀式中,努賽巴擔任的是官方的見證人。
現在,教堂內的司事打開嵌在右手邊大門上的小門,從裡面遞出一道梯子。努賽巴接過梯子,然後將梯子斜靠在左手邊大門上。努賽巴先把右手邊大門下方的鎖打開,然後爬上梯子把上面的鎖打開。努賽巴爬下梯子之後,教堂內的僧侶將大門搖晃了幾下,然後將大門左扇門板推開。努賽巴走進教堂,向僧侶們問好:「祝平安!」
「祝平安!」他們愉快地回道。努賽巴家族與猶貝家族至少從一一九二年起就持續開啟著聖墓教堂的大門,薩拉丁任命猶貝家族為「鑰匙的保管者」,而努賽巴家族為「聖墓教堂的守護人與守門人」(瓦基的名片上印著這個頭銜)。努賽巴家族—他們也曾被任命為圓頂清真寺裡的薩克拉(礎石)世襲清掃人—─表示薩拉丁曾讓他們恢復六三八年歐瑪爾哈里發授予他們的地位。直到一八三○年代阿爾巴尼亞人征服為止,努賽巴家族一直非常富裕,但之後則淪為擔任導遊為生。(待續)努賽巴家族與猶貝家族彼此處於警戒對立的關係。「努賽巴家族與我們沒有關係,」八十歲的猶貝說道,他已保管了二十二年的鑰匙,「他們只是守門人。」而努賽巴則堅稱「猶貝家族不許觸摸大門或門鎖」,顯示伊斯蘭本身的對立與基督徒自身的對立一樣鮮明。瓦基的兒子歐巴達(Obadah)是他的繼承人。
跟過去八百年來的祖先一樣,努賽巴與猶貝每天會待在大廳一段時間—─但這裡並非他們的信仰所在。「我了解這裡的每一塊石頭,這裡就像我家一樣」,努賽巴若有所思地說。他尊崇聖墓教堂:「我們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耶穌與摩西是先知,而馬利亞非常神聖,所以這座教堂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如果他想祈禱的話,可以從側門出去,前往隔壁的清真寺(當初建造這座清真寺是為了震懾基督徒),或走個五分鐘到阿克薩清真寺。
就在西牆拉比醒來與努賽巴守護人聽見有人敲窗準備遞給他聖墓教堂鑰匙的同時,四十二歲、育有五名子女的阿德布.安薩里(Adeb al-Ansari),身穿黑色皮革外套走出他位於穆斯林區的馬木魯克房子(這是他的家族共有的房子),沿著街道走了五分鐘,來到東北角的哈旺梅門。他通過身穿藍衣的以色列警察檢查哨,諷刺的是,這些警察通常由德魯茲派或加利利阿拉伯人出任,他們負責禁止猶太人進入。然後,安薩里來到崇高的聖所。
神聖的廣場已經設了電燈,在過去,他的父親要耗費兩個小時才能將所有的燈點上。安薩里與聖地安全人員打過招呼之後,開始開啟圓頂清真寺的四扇大門,與阿克薩清真寺的十扇門。這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安薩里家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與穆罕默德一起前往麥地那的安薩里家族,他們宣稱自己曾被歐瑪爾任命為聖地守護人,日後他們的職位又進一步受到薩拉丁的確認。(安薩里家族曾有管理聖地的謝克收受蒙提.帕克的賄賂,這成了家族的恥辱。)
清真寺必須在晨禱前一個小時開啟。安薩里不需要每天前來,他現在有一個團隊,但在他繼承世襲的守護人職位之前,他每天早上都必須過來開門,而他也感到自豪:「首先這是一份工作,然後是家族的財產與重大的責任,然而最重要的是,這是一項高尚而神聖的任務。但薪水不高,所以我必須在橄欖山的飯店櫃臺工作。」
聖地的世襲職位逐漸消失。席哈比家族(Shihabis)是另一個大家族,他們是黎巴嫩王公的後裔,住在靠近小牆的家族共有住宅,並且曾經是先知鬍子的守護人。鬍子與守護人的職位已經不存在,但聖地對他們仍具有吸引力—─席哈比家族仍在聖地工作。
如同拉比走向西牆,努賽巴在聖墓教堂敲門,安薩里打開清真寺大門,那吉.卡札茲(Naji Qazaz)離開位於勝利鐵門街家族已擁有兩百二十五年的屋子,沿著老馬木魯克街道步行幾碼,然後走上臺階,經過鐵門,來到聖地。卡札茲直接前往阿克薩清真寺,進到一個小房間裡,裡面擺著麥克風與幾瓶礦泉水。一九六○年前,卡札茲家族仍使用清真寺尖塔叫拜,現在他們則利用這個房間來預做準備,彷彿運動選手一樣。古札茲有二十分鐘的時間做伸展運動,他深呼吸,然後漱口。確認麥克風已經開啟,再看看牆上的時鐘,時間一到,他便面向麥加克爾白,開始叫拜,他的聲音在整座舊城裡迴盪著。
自從馬木魯克蘇丹卡伊特拜伊統治以來,卡札茲家族在阿克薩清真寺擔任宣禮員已有五百年的歷史。那吉擔任宣禮員已有三十年,他和兒子菲拉茲(Firaz)與兩個親戚共同分攤這份工作。
現在,距離日出還有一個小時。圓頂清真寺已經開放:穆斯林正在禱告。西牆一直是開放的:猶太人正在禱告。聖墓教堂開放了:基督徒以各種語言禱告。太陽升起,照耀著耶路撒冷,它的光芒使希律西牆的石塊亮如白雪—─如同兩千年前約瑟夫斯所描述的—─清真寺的黃金圓頂也熠熠生輝。神聖的廣場是天與地、上帝與人類交會之處,它依然是人類難以描繪之地。唯有太陽的光芒能遍照整座廣場,最後,所有的光線將照耀在耶路撒冷最優美而神秘的建築物上。沐浴於日光之中,散發出奪目的光采,它也因此博得黃金的美名。但金門依然深鎖,直到末日來臨,它才有重新開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