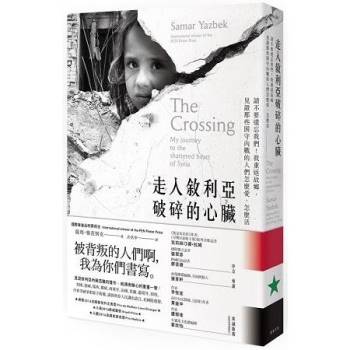我的背擦過鐵絲網,忍不住顫抖起來。先前為了躲避土耳其士兵視線,我苦候數小時,直到抬頭仰望,遠方蒼穹終於連成一片黑。鐵絲網下,被挖出剛好容得下一個人的小空隙。我趴下往後踹開沙土,匍匐爬過國界,尖刺劃過身體。
我深呼吸,拱起背,跑,用生命跑,照別人教的做。一穿過國界,就頭也不回往前跑,全力衝刺半小時,就會安全在望。我跑,不停奔跑,直到離開危險地帶。地上坑坑窪窪,礫石遍地,但愈來愈感受不到雙腳的存在,心臟怦怦怦跳個不停,整個身體被熱血帶著往前衝,氣喘吁吁之中,心底不斷吶喊:我回來了!這不是電影場景,這是真的。我喃喃自語跑著:我回來了……我在這。
後頭傳來槍聲,軍事車輛在土耳其那一頭集結,但我們已經成功穿越國界,一直往前跑,一切感覺像是命運早已安排好。為了這一天,我特地戴上頭巾,換穿長外套和寬鬆長褲,跳上接應的車子之前,先得爬上一道陡坡。此次返鄉,天地之中,只有嚮導和我,身旁沒有其他逃難人群,甚至不曉得稍後能否活著寫下這段經歷;我原本以為自己回歸故土時,將如同無數前人,死於半路。黑夜降臨,四周看似一片祥和,但難保下一秒危機將至。
接下來的十八個月,我將多次穿越邊界,這其中情勢千變萬化:敘利亞邊境安塔基亞(Antakya)機場的混亂狀況,說明許多事。我將自己的見聞,以及所有能見證國家急遽變動的事物,深深刻印在腦中。不過,我第一次衝下邊境山丘時,渾然不知等在前方的是什麼,只曉得雙腿抽痛不已。
我跑至丘底時,至少蹲下休息了十分鐘,不停大力地抽氣,試圖讓心跳恢復正常。一旁陪著的年輕嚮導,一定還以為我全身顫抖,為的是再度見到家鄉過於激動,不過實情是,那一刻我顧不上傷感。剛才逃命太久,肺和身體好像分家了,腿直不起來。
上車後,我終於又能正常呼吸。我坐在後座,一旁是未來將替我帶路的梅薩拉(Maysara)與穆罕默德(Mohammed)。這兩位性格迥異的戰士,來自同一個家族,我將借住他們的祖宅。梅薩拉是起義鬥士,原本以和平方式對抗阿薩德(Assad)政權,後來才拿起武器。二十多歲的穆罕默德原是商科生,跟梅薩拉一樣,最初也是參與和平抗議運動,之後才加入武裝反抗。接下來數星期,我將與穆罕默德在合作過程中成為至交,前座是司機與另一名年輕人。
我們一路開過敘利亞西北的伊德利卜省(Idlib),那一區僅部分脫離阿薩德的武裝控制。我們在敘利亞自由軍(Free Army)豎起的無數路障中,駛過一旁植滿橄欖樹的道路,放眼望去都是武裝民兵的身影與勝利旗幟。我把頭伸出車窗,試著以冷靜超然的態度,將路旁景象印在腦海中。前方道路似乎怎麼樣也走不完,遠方依舊傳來轟炸聲,然而我看著眼前這片幾乎已經脫離阿薩德軍隊的區域時,全身每一個細胞依舊激動不已。
不過,地面或許自由了,空襲還不允許我們放鬆,烽火依舊連天,太多影像爭先映入眼簾,我需要後腦杓也有眼睛,耳朵也有眼睛──甚至指尖也得有。我凝視前方,試圖解讀周遭環境,滿目瘡痍的地面與猩紅天空之中,一輛孤零零的車載著一女四男,一路駛過敘利亞西北薩拉奎布市(Saraqeb)的橄欖樹。
我記憶中的敘利亞是世上最美的地方。我的童年時期在又名「革命市」(al-Thawra)的塔布哈(al-Tabqa)度過,那裡離幼發拉底河的拉卡(Raqqa)不遠。青少年時期,我漫步於地中海旁的文明古城賈柏萊(Jableh),附近是敘利亞最主要的港口城拉塔基亞(Latakia)。成年後,我帶著女兒在首都大馬士革(Damascus)住了幾年,遠離家人以及鄉親宗派的根,獨自生活,自由做選擇。不過,這種生活方式也讓我付出很大的代價,我被親族棄絕於外,飽受批評,名譽受損。一個女性要在保守社會中生存十分不容易,這樣的地方不允許女性違反戒律,恆久的秩序對抗著變化。我完全沒料到,自己會是在荒煙百里之中,首度造訪敘利亞北部的農村地帶。
接下來的敘事全是真的,唯一的虛幻人物是敘事者,也就是我:我感覺自己像是一個不真實的人,在戰火之中穿越邊界,就好像人生是一部離奇小說。我試著理解周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選擇九死一生的虛構角色。我放下自己在真實生活的女性身分,成為想像中的人物,試著替自己所追求的理想挺身而出。這個女人在這裡做什麼?試圖生存?挑戰天生的身分?抗拒流放?為正義挺身而出?對抗荒謬的流血?
二〇一一年七月,我被迫流亡法國,一路上並不平靜,在敘利亞穆卡巴拉情報局(mukhabarat)的追殺下,帶著女兒逃跑,原因是我在革命初期,參加了一場和平抗議活動,還寫了幾篇文章說真話,講出情報局是如何暗殺與刑求抗議阿薩德的人士。然而我抵達法國後,感到有必要返回北敘利亞,追求讓家鄉民主自由的夢想。我心心念念惦記著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這是身為知識分子與作家的責任,我要和自己的同胞站在一起,一同追求理想,執行小規模的女性計劃,成立女性賦權組織,同時也讓孩子有機會受教育。萬一情況無法在我們這一代就改變,只能寄望下一代。此外,我也希望能在已經脫離阿薩德掌控的區域,設法成立民主公民組織。
漆黑的夜晚之中,我們駛過一條又一條道路,奔向即將接待我的家庭,那家人將成為我新生活的重心。車子進入薩拉奎布的狹窄巷弄,眾人提高警覺,這座城鎮尚未全面獲得自由,守在無線電塔上的狙擊手,依舊每日奪走無數性命。
接待我的主人住在一座大合院,外觀看得出有繁榮、好客的過往。院裡一個女人告訴我,她們這些日子以來僅「慘淡度日」。建物最古老的原始部分,有一個美麗圓頂,多年前由先前的世代建造,而我將在大家稱為「地窖」的房間,待上一段時間。大合院的左側,住著這家的長子夫婦阿布•伊布拉亨(Abu Ibrahim)與諾拉(Noura),由他們兩位負責接待我。院子的右側住著小兒子一家,也就是我的嚮導梅薩拉和他的妻子瑪納(Manal),以及兩人的孩子露哈(Ruha)、愛拉(Aala)、瑪默德(Mahmoud)、塔拉(Tala)。露哈是早熟冷靜的十一歲孩子,愛拉七歲,瑪默德四歲,塔拉兩歲半。此外,大合院那一側還住著梅薩拉的老母親與阿姨,兩人皆行動不便,由長子阿布•伊布拉亨未婚的妹妹、五十歲出頭的艾育歇(Ayouche)負責照顧。
當時我並不知道,接待我的主人和我對國家抱持著相同的願景,不過我們雙方種下非常深的緣分。敘利亞人極度好客,我們一抵達,所有人動起來為我們準備晚餐。我們盤腿坐在塑膠墊和泡棉墊上吃吃喝喝,小女孩露哈和愛拉在我身旁寸步不離。我看著眾人和善的面孔,想起自己的親族還生活在受政府掌控的區域,無法拜訪他們。
晚上,我告訴家族女人幾則故事,講出自己是如何在十六歲首次離家,我希望靠著分享小祕密,贏得她們的信任,順道傳遞自由的真諦──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我想讓她們明白,女性要獲得自由,就得為自己的人生負起責任,這與敘利亞輿論認為女性解放背離傳統、導致社會混亂的看法背道而馳。我告訴大家自己和丈夫離婚後,是如何辛苦生活與工作,以求經濟獨立,撫養女兒。我為了餵飽自己和女兒,不得不從事各種工作。親朋好友與我斷絕關係,但為了成為作家與記者,什麼苦我都願意吃。我說出自己是如何來到薩拉奎布,在場的女性拋出一個又一個問題。
我首度造訪薩拉奎布、開始熟悉環境時,有過躲避射傷戴安娜的狙擊手的第一手經驗。招待我的主人教我來往於各棟房子的方法,避開狙擊手監視的那條街。我們悄悄穿梭於建築物之間,躲避狙擊步槍,每家每戶都對我們敞開大門。鎮上許多人拆下房子與房子間的牆壁,大家的屋子連成一片。我們通過陌生人的家,跳出窗戶,爬下梯子,跑到一樓,提鞋溜過院子。
有一次,我、穆罕默德和兩名年輕人外出,鑽過一位老太太家的客廳。我們打招呼,老太太也打招呼,但老太太完全沒離開躺著的地方,動也不動,顯然很習慣地方居民就這樣在自己家進進出出。我跳出窗戶之前,回頭望了一眼,看看是否嚇了老人家一跳,但她只是凝視著天花板,就好像從未見過我們四人。我們以這樣的方式通過好幾家的房子,安全抵達目的地,這是不被射殺的唯一辦法。
後來地方上一名女子告訴我,在我待在當地的最後一天,狙擊手射傷某個女人的陰部,還殺害一名十二歲女孩。這個消息令我無法動彈,六神無主,膝蓋支撐不住。「妳在幹什麼?」男人們吼我,「堅強點!不能那麼脆弱!」這件事教會我保持心理距離,晚一點再哀痛。
儘管如此,敘利亞唯一的贏家是死神,每個人三句不離死。每一件事都很難說,唯一能確定的只有死亡終將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