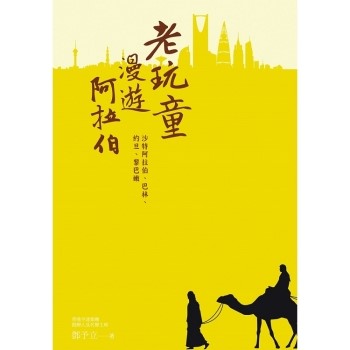黃沙路迢迢的沙特之旅
二○一七年二到三月,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臺灣譯為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薩勒曼展開一場高調的亞洲之行,陸續到訪馬來西亞、印尼、文萊(臺灣譯為汶萊)、日本,三月十五日則到中國進行為期三日的訪華行程。
此行的陣仗十分龐大,非常引人注目,代表團近一千五百人,行李逾五百噸,其中還包括兩部讓國王走出機艙便可以搭乘下到地面的鍍金自動電扶梯。據稱在東京訪問期間,代表團預訂了一千兩百間高級客房,並以數百輛豪車代步,著實令人大開眼界。
在中國的訪問也深受矚目。中國是沙特最大的出口國及進口國,雙方經貿往來頻仍。沙特目前致力於經濟轉型,不希望將全國的經濟押在石油產業上,雙方此次簽署了多項協議和諒解備忘錄,在石油與非石油領域上,更進一步推動兩國之間的相互合作,加深雙邊關係。
典型的沙漠之國,可耕面積占全國1%
很湊巧的,二○一六年十一月秋末冬初,我也才剛經歷一段「沙漠之國」沙特阿拉伯的旅程。
沙特阿拉伯位於世界最大的半島――阿拉伯半島(Arabic Peninsula)上,半島在亞洲和非洲之間,總面積約三百多萬平方公里。我從二○一二年開始,就頻繁往返半島,甚至在阿聯酋的迪拜(Dubai,臺灣譯為迪拜)建立了公司據點。除此之外,我分別到過阿曼、卡塔爾、科威特。二○一七年的炎夏七月,更前往約旦首都安曼,獨闖紅岩峽谷的玫瑰古城佩特拉,還漂浮在美麗又神奇的死海上。
此次半島行,唯一的目的地就是沙特阿拉伯這個伊斯蘭教的發源地了。
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半島上最大的國家,國土約占整個半島的80%,相等於新疆和青海兩省區的面積總和。沙特剛好在半島中央,東瀕波斯灣,西臨紅海,是半島上唯一一個同時擁有兩條海岸線的國家,不過她大部分土地都是貧瘠的荒野,差不多有一半是荒茫的沙漠,適合耕種的土地不到全國的1%。
天無絕人之路,大抵是上天給予的補償,土地貧瘠的沙特卻擁有極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尤其沙特的名字幾乎可以與石油劃上等號,被稱為「石油王國」――她是世界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和出口國,石油儲藏量也僅次於委內瑞拉,為世界第二多,隨著持續的探勘開發,石油的儲量仍不斷增加。石油的發現,改變了沙特的命運,使她從傳統的農耕游牧蛻變為石油化工業的國家,也一躍成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其實對於沙特,我認識的並不多,大部分都是聽來的傳聞:該國仍然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君主專制國家,全國人民必須是穆斯林,外國人要移民到此並不是件易事。目前全國人口約三千多萬,其中20至30%是外來人口。在信奉伊斯蘭教的人之中,約85%屬於遜尼派,僅有15%是什葉派。
沙特擁有兩個聖城,一是麥加(Mecca),一是麥地那(Medina)。麥加是所有穆斯林心中共同的聖城,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誕生地和伊斯蘭教的發源地,信徒每天都要朝麥加城的方向行禮跪拜五次,唸誦《可蘭經》;麥地那是穆斯林的第二聖地,是先知穆罕默德復興伊斯蘭教初期的政治、宗教活動中心,亦是其安葬之地。兩者皆為全球穆斯林必來朝覲的聖地。
女性的統一服裝:黑袍、黑面紗、黑手套、黑鞋襪
沙特的治安相當良好,皆因對國民的管治十分嚴厲,執法嚴峻,仍然保存鞭刑、剁手刑罰和斬首等。再者,人民的信仰非常虔誠,宗教本身對於人們也十分具有約束力。沙特除了維持社會治安的警察外,特別的是還有一批宗教警察(Religious Police),他們由一群「志願者」或「執法者」組成,根據《可蘭經》經文規定,維護宗教風紀。這些宗教警察身穿白袍,攜帶木棍或皮鞭,每天在市內巡邏執勤。一旦遇見違背宗教風紀行為的人,無論國民或外籍人士,都會揮起木棍、皮鞭抽向他們,毫不手軟,往往被西方社會認為是「不文明」的行為。不過近一兩年來,宗教警察已經日趨少見了。
沙特對女性服飾的要求,相較於半島上其他六個國家,是更為嚴格的。當地的婦女全身都必須罩上黑袍、黑面紗、黑手套,甚至連鞋襪都是黑的,外人唯一能見到的只有一雙明亮的眼睛。就連前來旅遊的女性,也一視同仁。一踏進入境大堂,女性就必須與男性分開,若服裝未遵守規定,就會立即被要求披上一襲特別為女性旅客準備的黑色長袍和頭巾,然後才准許過關。然而對女性裝扮如此嚴格的規範之下,黑袍的樣式其實也非一成不變的,除了最普通單調的,另外也有帶了花紋圖案的,或者在邊緣或袖口裝飾不同顏色的滾邊,據說有些昂貴的黑袍上甚至還鑲了鑽呢!
來沙特,禁忌不可不知
出發到沙特前夕,我被一再提醒,許多重要的宗教聖地、古跡都只對穆斯林開放,像我這樣的外地旅客是不能隨便進入的。臺灣旅行社的陳總知道我喜歡拍照,又愛隨處抓拍,更是絮絮不休地叮嚀我,千萬不要把在其他國家的習慣帶到沙特,在公眾場所不可把黑衣婦女攝入鏡頭,更不要在聖跡一類的地點隨意拍照,否則會招致不必要的麻煩。林林總總一堆規條,真讓我感到有點惶恐。
值得一提的是,要到沙特,必須先申請當地的入境簽證,可是申請過程和手續並不容易,而且耗時較長。我打聽過申請入境簽證分為朝覲、訪問和工作簽證,並沒有一般國家的旅遊觀光簽證。感謝中國駐沙特使館朋友的關照和幫助,使我只花一個小時就在北京的沙特使館獲得「特事特辦」的入境簽證,也讓我這趟黃沙萬里行得以實現。
經過十多個小時的航程,我搭乘的飛機終於徐徐降落在有「帳篷城」之稱,以開國君主名字命名的吉達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國際機場(King Abdulaziz International Airport)。
吉達(Jeddah)是沙特第二大城市,距離麥加聖城不過七十多公里,因而每年的朝覲期間,機場總是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覲者,根據統計,每年單是正式朝覲期間接待的旅客就逾兩百多萬人,若再加上副朝(正式朝覲以外時間進行的朝覲)和觀光遊客等,人數就更多了,可說是世界上最為繁忙的機場之一。
白色帳篷設計的吉達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國際機場,融合傳統阿拉伯和現代風格設
計,且有折射陽光、通風等環保功能機場共有四個航站樓,分別是王室專用、朝覲專用、沙特航空公司專用和其他航空公司使用。
其中的朝覲航廈(Hajj Terminal)非介紹不可,它占地面積達一百零五平方公里,可同時容納八萬多名旅客。特別之處在於它屬於室外航站樓的型態,採用法國人的設計,融合傳統阿拉伯和現代風格,新穎創意。整個航廈用帳篷覆蓋,採用鋼柱支撐,帳篷是以一種反光的玻璃纖維製成,有效地把75%的陽光折射出去,降低了機場的酷熱程度,加上室外航廈四周並沒有用牆壁圍起,更多了一重通風的作用。
我搭乘擺渡車(Shuttle bus,接駁車)經過航廈時,遠遠望見一片白色的大帳篷,非常壯觀。這令我回想起幾年前曾經去過澳洲北領地沙漠中的艾爾斯岩渡假村,該處也是採用白色帳篷設計,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論及規模,當然無法與吉達機場這兩百一十頂高四十五米的傘形帳篷相匹比了,今天它已成為吉達的地標性建築。可惜我乘坐的航機停泊在北航站樓,只能遠觀,無緣近距離欣賞它的特別設計。
羅馬之外的羅馬
位於約旦北部的杰拉什古城遺址(Jerash)距安曼約五十公里,是我在約旦的下一個旅遊目的地。這座有三千五百多年歷史的古羅馬城,是義大利境外保存得最完整、最大的,被譽為「中東龐貝」。
公元前一千六百年,杰拉什就有人類居住並繁衍生息。古希臘時期,此處展開城鎮的建設。公元前六十三年,羅馬軍隊占據敘利亞及杰拉什周邊地區,這兒開始興建起羅馬風格的建築,城市的規模逐漸形成,杰拉什就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隨著羅馬帝國的起伏動盪,以及拜占庭、阿拉伯倭馬亞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的興起與衰落,這塊地方也經歷多次的戰亂和爭奪。最為興盛繁華的時候,人口達兩萬多人,是中東的貿易中心,一度名列中東地區四大名城之一。爾後杰拉什受到多次地震摧殘,尤其公元七四九年一場毀滅性的強烈地震,建築物禁受不起嚴重破壞,城市幾乎毀於一旦。直至九世紀,杰拉什已埋沒在荒煙蔓草之下,就此銷聲匿跡。直到一八○六年,德國探險家奧里赫(Urich Jasper Seetzen)途經此處,發現了部分遺跡。二○年代開始,在考古隊不斷發掘和修復下,終於讓深埋在黃土之下、失落千年的文明古跡重見天日。
我跟隨導遊的腳步,以遺城的凱旋門為起點。凱旋門又叫做哈德良凱旋門,公元一二九年,為了歡迎當時的羅馬皇帝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 Augustus)蒞臨此地而建,不僅以他來命名此門,更舉行了大型的進譽為「中東龐貝」的杰拉什古城遺址城慶祝儀式。根據歷史記載,這位羅馬皇帝博學多才,又喜愛旅遊,在他身為統治者期間,羅馬帝國治下有不少行省都留下他的足跡。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所著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裡就有這樣的一段話:「哈德良的生活幾乎是始終處在永無止境的旅途之中。」在公務之餘不忘旅遊的我不禁心有戚戚焉,倘若我能穿越時空跟他見上一面,一定會擦出火花,聊起許多關於旅遊的共同話題。
歲月的摧殘並沒有減損這座凱旋門的宏偉大氣、威武不凡,巨大的石塊疊築起中央與左右三道拱門,近前一看,門上的石柱雕刻著精緻的圖案和花紋,粗獷中帶有細緻。穿越拱門後,左手邊是一座羅馬賽馬場,約長兩百六十米,寬五十米,一側是石階看臺,可容納一萬五千多名觀眾,過去用來進行賽馬、戰車和體育比賽等,是整個杰拉什城內占地面積最大的場地。我坐上看臺,環視整個賽馬場,彷彿置身在電影《賓虛》(Ben Hur,臺灣譯為賓漢)馬車競技的場景中,非常具有臨場感。此時傳來陣陣鼓角聲,原來場內正在拍攝古羅馬賽馬和戰士格鬥的場面,當年馬車馳騁的緊張氣氛立即撲面而來。
過了賽馬場,斑駁而厚實的石牆向城內延伸。導遊介紹說,城牆共有四座城門,同時每隔一定距離就建有一座塔樓或高臺,總共有一百多座。我們繼續往前行,主要入口是一座殘破不堪的南大門,然而想要一探昔日繁華的古城,卻正是從門後的南大街揭開序幕。
橢圓形的羅馬廣場規模長九十米、寬八十米,十分寬闊,周圍環繞有邊廊,清一色的愛奧尼亞式石柱(Ionic Order),保存得相當完整。這款石柱屬於古希臘建築的特色之一,柱頭有一對向下的渦卷裝飾,特點是比較纖細,所以又有女性柱的美稱。舊時廣場中央設有兩個祭壇和一座噴泉,現在已不復存在了。連接羅馬廣場是一條長達八百米的廊柱大街,高聳的石柱是另一種古希臘的柱式――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比愛奧尼亞柱式更為纖細精緻,柱頭形狀似盛滿花草的花籃。據導遊的介紹,這條石柱街建於公元一世紀,原來也是愛奧尼亞式石柱,後來到公元二世紀時進行改建,才將石柱換成科林斯式。
從橢圓形廣場往上走,山丘高處分別有宙斯和月神阿爾忒彌斯兩座神廟,以及南北兩座劇場,包括提供一千六百多名觀眾觀看唱歌、朗誦演出的北劇場,和南邊做為每年杰拉什藝術季表演場地,可容納三千名觀眾的古羅馬劇場。我們在南劇場巧遇街頭藝人的表演,坐在石階看臺上,樂音及鼓聲皆十分清晰。
神廟建築坍塌毀損得較為嚴重,但仍保有數根高聳入雲的巨大石柱。站在神廟的石柱旁,更感覺石柱的氣勢恢宏與自己的渺小。從高處環視整座古城,眾多巍然挺拔的石柱千百年來屹立不倒,這些建築承載著「千柱之城」的美譽,讓人悠然懷想此處曾是如何盛極一時、偉大輝煌,足可與羅馬境內的古城匹敵,難怪這個被掩埋千餘年的古城也被譽為「羅馬之外的羅馬(A Rome away from Rome)」。然而漫步於古城散落的遺跡間,四處遍布凌亂倒塌的殘垣斷壁,又忍不住感嘆世事滄桑。
城內除了希臘羅馬建築之外,也曾經建有十五座基督教堂,如今仍有部分殘存。教堂多建於五、六世紀間,地板嵌有色彩斑斕的馬賽克圖案,非常漂亮。可惜我受限時間,未能進入內部仔細欣賞。
杰拉什整體的面積不算小,所以若時間充裕的話,建議能夠安排一整天,身臨其境了解
它的發展史,收穫與感受將遠不是文字和圖片所能給予的。
以上內容節錄自《老玩童漫遊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巴林、約旦、黎巴嫩》鄧予立◎著.白象文化出版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http://www.pressstore.com.tw/freereading/9789863587880.pdf
二○一七年二到三月,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臺灣譯為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薩勒曼展開一場高調的亞洲之行,陸續到訪馬來西亞、印尼、文萊(臺灣譯為汶萊)、日本,三月十五日則到中國進行為期三日的訪華行程。
此行的陣仗十分龐大,非常引人注目,代表團近一千五百人,行李逾五百噸,其中還包括兩部讓國王走出機艙便可以搭乘下到地面的鍍金自動電扶梯。據稱在東京訪問期間,代表團預訂了一千兩百間高級客房,並以數百輛豪車代步,著實令人大開眼界。
在中國的訪問也深受矚目。中國是沙特最大的出口國及進口國,雙方經貿往來頻仍。沙特目前致力於經濟轉型,不希望將全國的經濟押在石油產業上,雙方此次簽署了多項協議和諒解備忘錄,在石油與非石油領域上,更進一步推動兩國之間的相互合作,加深雙邊關係。
典型的沙漠之國,可耕面積占全國1%
很湊巧的,二○一六年十一月秋末冬初,我也才剛經歷一段「沙漠之國」沙特阿拉伯的旅程。
沙特阿拉伯位於世界最大的半島――阿拉伯半島(Arabic Peninsula)上,半島在亞洲和非洲之間,總面積約三百多萬平方公里。我從二○一二年開始,就頻繁往返半島,甚至在阿聯酋的迪拜(Dubai,臺灣譯為迪拜)建立了公司據點。除此之外,我分別到過阿曼、卡塔爾、科威特。二○一七年的炎夏七月,更前往約旦首都安曼,獨闖紅岩峽谷的玫瑰古城佩特拉,還漂浮在美麗又神奇的死海上。
此次半島行,唯一的目的地就是沙特阿拉伯這個伊斯蘭教的發源地了。
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半島上最大的國家,國土約占整個半島的80%,相等於新疆和青海兩省區的面積總和。沙特剛好在半島中央,東瀕波斯灣,西臨紅海,是半島上唯一一個同時擁有兩條海岸線的國家,不過她大部分土地都是貧瘠的荒野,差不多有一半是荒茫的沙漠,適合耕種的土地不到全國的1%。
天無絕人之路,大抵是上天給予的補償,土地貧瘠的沙特卻擁有極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尤其沙特的名字幾乎可以與石油劃上等號,被稱為「石油王國」――她是世界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和出口國,石油儲藏量也僅次於委內瑞拉,為世界第二多,隨著持續的探勘開發,石油的儲量仍不斷增加。石油的發現,改變了沙特的命運,使她從傳統的農耕游牧蛻變為石油化工業的國家,也一躍成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其實對於沙特,我認識的並不多,大部分都是聽來的傳聞:該國仍然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君主專制國家,全國人民必須是穆斯林,外國人要移民到此並不是件易事。目前全國人口約三千多萬,其中20至30%是外來人口。在信奉伊斯蘭教的人之中,約85%屬於遜尼派,僅有15%是什葉派。
沙特擁有兩個聖城,一是麥加(Mecca),一是麥地那(Medina)。麥加是所有穆斯林心中共同的聖城,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誕生地和伊斯蘭教的發源地,信徒每天都要朝麥加城的方向行禮跪拜五次,唸誦《可蘭經》;麥地那是穆斯林的第二聖地,是先知穆罕默德復興伊斯蘭教初期的政治、宗教活動中心,亦是其安葬之地。兩者皆為全球穆斯林必來朝覲的聖地。
女性的統一服裝:黑袍、黑面紗、黑手套、黑鞋襪
沙特的治安相當良好,皆因對國民的管治十分嚴厲,執法嚴峻,仍然保存鞭刑、剁手刑罰和斬首等。再者,人民的信仰非常虔誠,宗教本身對於人們也十分具有約束力。沙特除了維持社會治安的警察外,特別的是還有一批宗教警察(Religious Police),他們由一群「志願者」或「執法者」組成,根據《可蘭經》經文規定,維護宗教風紀。這些宗教警察身穿白袍,攜帶木棍或皮鞭,每天在市內巡邏執勤。一旦遇見違背宗教風紀行為的人,無論國民或外籍人士,都會揮起木棍、皮鞭抽向他們,毫不手軟,往往被西方社會認為是「不文明」的行為。不過近一兩年來,宗教警察已經日趨少見了。
沙特對女性服飾的要求,相較於半島上其他六個國家,是更為嚴格的。當地的婦女全身都必須罩上黑袍、黑面紗、黑手套,甚至連鞋襪都是黑的,外人唯一能見到的只有一雙明亮的眼睛。就連前來旅遊的女性,也一視同仁。一踏進入境大堂,女性就必須與男性分開,若服裝未遵守規定,就會立即被要求披上一襲特別為女性旅客準備的黑色長袍和頭巾,然後才准許過關。然而對女性裝扮如此嚴格的規範之下,黑袍的樣式其實也非一成不變的,除了最普通單調的,另外也有帶了花紋圖案的,或者在邊緣或袖口裝飾不同顏色的滾邊,據說有些昂貴的黑袍上甚至還鑲了鑽呢!
來沙特,禁忌不可不知
出發到沙特前夕,我被一再提醒,許多重要的宗教聖地、古跡都只對穆斯林開放,像我這樣的外地旅客是不能隨便進入的。臺灣旅行社的陳總知道我喜歡拍照,又愛隨處抓拍,更是絮絮不休地叮嚀我,千萬不要把在其他國家的習慣帶到沙特,在公眾場所不可把黑衣婦女攝入鏡頭,更不要在聖跡一類的地點隨意拍照,否則會招致不必要的麻煩。林林總總一堆規條,真讓我感到有點惶恐。
值得一提的是,要到沙特,必須先申請當地的入境簽證,可是申請過程和手續並不容易,而且耗時較長。我打聽過申請入境簽證分為朝覲、訪問和工作簽證,並沒有一般國家的旅遊觀光簽證。感謝中國駐沙特使館朋友的關照和幫助,使我只花一個小時就在北京的沙特使館獲得「特事特辦」的入境簽證,也讓我這趟黃沙萬里行得以實現。
經過十多個小時的航程,我搭乘的飛機終於徐徐降落在有「帳篷城」之稱,以開國君主名字命名的吉達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國際機場(King Abdulaziz International Airport)。
吉達(Jeddah)是沙特第二大城市,距離麥加聖城不過七十多公里,因而每年的朝覲期間,機場總是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覲者,根據統計,每年單是正式朝覲期間接待的旅客就逾兩百多萬人,若再加上副朝(正式朝覲以外時間進行的朝覲)和觀光遊客等,人數就更多了,可說是世界上最為繁忙的機場之一。
白色帳篷設計的吉達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國際機場,融合傳統阿拉伯和現代風格設
計,且有折射陽光、通風等環保功能機場共有四個航站樓,分別是王室專用、朝覲專用、沙特航空公司專用和其他航空公司使用。
其中的朝覲航廈(Hajj Terminal)非介紹不可,它占地面積達一百零五平方公里,可同時容納八萬多名旅客。特別之處在於它屬於室外航站樓的型態,採用法國人的設計,融合傳統阿拉伯和現代風格,新穎創意。整個航廈用帳篷覆蓋,採用鋼柱支撐,帳篷是以一種反光的玻璃纖維製成,有效地把75%的陽光折射出去,降低了機場的酷熱程度,加上室外航廈四周並沒有用牆壁圍起,更多了一重通風的作用。
我搭乘擺渡車(Shuttle bus,接駁車)經過航廈時,遠遠望見一片白色的大帳篷,非常壯觀。這令我回想起幾年前曾經去過澳洲北領地沙漠中的艾爾斯岩渡假村,該處也是採用白色帳篷設計,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論及規模,當然無法與吉達機場這兩百一十頂高四十五米的傘形帳篷相匹比了,今天它已成為吉達的地標性建築。可惜我乘坐的航機停泊在北航站樓,只能遠觀,無緣近距離欣賞它的特別設計。
羅馬之外的羅馬
位於約旦北部的杰拉什古城遺址(Jerash)距安曼約五十公里,是我在約旦的下一個旅遊目的地。這座有三千五百多年歷史的古羅馬城,是義大利境外保存得最完整、最大的,被譽為「中東龐貝」。
公元前一千六百年,杰拉什就有人類居住並繁衍生息。古希臘時期,此處展開城鎮的建設。公元前六十三年,羅馬軍隊占據敘利亞及杰拉什周邊地區,這兒開始興建起羅馬風格的建築,城市的規模逐漸形成,杰拉什就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隨著羅馬帝國的起伏動盪,以及拜占庭、阿拉伯倭馬亞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的興起與衰落,這塊地方也經歷多次的戰亂和爭奪。最為興盛繁華的時候,人口達兩萬多人,是中東的貿易中心,一度名列中東地區四大名城之一。爾後杰拉什受到多次地震摧殘,尤其公元七四九年一場毀滅性的強烈地震,建築物禁受不起嚴重破壞,城市幾乎毀於一旦。直至九世紀,杰拉什已埋沒在荒煙蔓草之下,就此銷聲匿跡。直到一八○六年,德國探險家奧里赫(Urich Jasper Seetzen)途經此處,發現了部分遺跡。二○年代開始,在考古隊不斷發掘和修復下,終於讓深埋在黃土之下、失落千年的文明古跡重見天日。
我跟隨導遊的腳步,以遺城的凱旋門為起點。凱旋門又叫做哈德良凱旋門,公元一二九年,為了歡迎當時的羅馬皇帝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 Augustus)蒞臨此地而建,不僅以他來命名此門,更舉行了大型的進譽為「中東龐貝」的杰拉什古城遺址城慶祝儀式。根據歷史記載,這位羅馬皇帝博學多才,又喜愛旅遊,在他身為統治者期間,羅馬帝國治下有不少行省都留下他的足跡。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所著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裡就有這樣的一段話:「哈德良的生活幾乎是始終處在永無止境的旅途之中。」在公務之餘不忘旅遊的我不禁心有戚戚焉,倘若我能穿越時空跟他見上一面,一定會擦出火花,聊起許多關於旅遊的共同話題。
歲月的摧殘並沒有減損這座凱旋門的宏偉大氣、威武不凡,巨大的石塊疊築起中央與左右三道拱門,近前一看,門上的石柱雕刻著精緻的圖案和花紋,粗獷中帶有細緻。穿越拱門後,左手邊是一座羅馬賽馬場,約長兩百六十米,寬五十米,一側是石階看臺,可容納一萬五千多名觀眾,過去用來進行賽馬、戰車和體育比賽等,是整個杰拉什城內占地面積最大的場地。我坐上看臺,環視整個賽馬場,彷彿置身在電影《賓虛》(Ben Hur,臺灣譯為賓漢)馬車競技的場景中,非常具有臨場感。此時傳來陣陣鼓角聲,原來場內正在拍攝古羅馬賽馬和戰士格鬥的場面,當年馬車馳騁的緊張氣氛立即撲面而來。
過了賽馬場,斑駁而厚實的石牆向城內延伸。導遊介紹說,城牆共有四座城門,同時每隔一定距離就建有一座塔樓或高臺,總共有一百多座。我們繼續往前行,主要入口是一座殘破不堪的南大門,然而想要一探昔日繁華的古城,卻正是從門後的南大街揭開序幕。
橢圓形的羅馬廣場規模長九十米、寬八十米,十分寬闊,周圍環繞有邊廊,清一色的愛奧尼亞式石柱(Ionic Order),保存得相當完整。這款石柱屬於古希臘建築的特色之一,柱頭有一對向下的渦卷裝飾,特點是比較纖細,所以又有女性柱的美稱。舊時廣場中央設有兩個祭壇和一座噴泉,現在已不復存在了。連接羅馬廣場是一條長達八百米的廊柱大街,高聳的石柱是另一種古希臘的柱式――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比愛奧尼亞柱式更為纖細精緻,柱頭形狀似盛滿花草的花籃。據導遊的介紹,這條石柱街建於公元一世紀,原來也是愛奧尼亞式石柱,後來到公元二世紀時進行改建,才將石柱換成科林斯式。
從橢圓形廣場往上走,山丘高處分別有宙斯和月神阿爾忒彌斯兩座神廟,以及南北兩座劇場,包括提供一千六百多名觀眾觀看唱歌、朗誦演出的北劇場,和南邊做為每年杰拉什藝術季表演場地,可容納三千名觀眾的古羅馬劇場。我們在南劇場巧遇街頭藝人的表演,坐在石階看臺上,樂音及鼓聲皆十分清晰。
神廟建築坍塌毀損得較為嚴重,但仍保有數根高聳入雲的巨大石柱。站在神廟的石柱旁,更感覺石柱的氣勢恢宏與自己的渺小。從高處環視整座古城,眾多巍然挺拔的石柱千百年來屹立不倒,這些建築承載著「千柱之城」的美譽,讓人悠然懷想此處曾是如何盛極一時、偉大輝煌,足可與羅馬境內的古城匹敵,難怪這個被掩埋千餘年的古城也被譽為「羅馬之外的羅馬(A Rome away from Rome)」。然而漫步於古城散落的遺跡間,四處遍布凌亂倒塌的殘垣斷壁,又忍不住感嘆世事滄桑。
城內除了希臘羅馬建築之外,也曾經建有十五座基督教堂,如今仍有部分殘存。教堂多建於五、六世紀間,地板嵌有色彩斑斕的馬賽克圖案,非常漂亮。可惜我受限時間,未能進入內部仔細欣賞。
杰拉什整體的面積不算小,所以若時間充裕的話,建議能夠安排一整天,身臨其境了解
它的發展史,收穫與感受將遠不是文字和圖片所能給予的。
以上內容節錄自《老玩童漫遊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巴林、約旦、黎巴嫩》鄧予立◎著.白象文化出版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http://www.pressstore.com.tw/freereading/978986358788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