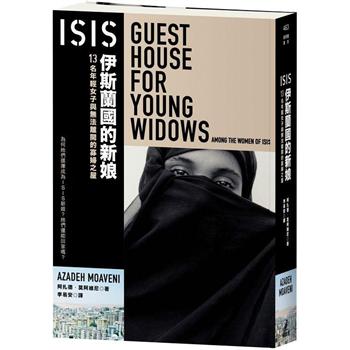二○○七年春天,突尼斯,克蘭姆
努兒並不覺得自己是顆少了保護殼的珍珠,也不覺得自己是支褪去包裝紙的棒棒糖。她覺得自己就是個十三歲的女孩,想要努力實踐自己的宗教信仰。她曾在 YouTube 上聽過一位謝赫論證,為何穆斯林女性有義務戴面紗。聽了四遍之後,謝赫的話便像電報字條一般,開始在她的腦海裡不斷播放。古蘭經的〈光明章〉要求女性不得展現自己的美麗和打扮,「只有那些明顯可見的部分除外。」照這樣說來,臉算是明顯可見的部分嗎?那位謝赫如此問道。有比臉部還要更不明顯可見的部位嗎?作為一名想順從真主聖意,希望蒙受真主祝福、並受祂認可的女性,將自己的臉部遮蔽起來,就是最能表達你真心誠意的方式。謝赫的話對努兒來說既直觀、又合理:只要衣著得當,女性就能被包覆在伊斯蘭的核心價值之中,包覆在和平、平靜與平等之中。那讓所有女人可見的差異都模糊了起來,不論貧富、不論美醜,也不論膚色深淺,大家都是一樣。這種做法可以提醒我們:真主對於所有祂創造出來的事物,都抱持著同等的愛。
二○○七年春天的某個下午,當努兒和幾個女性朋友坐在公園裡時,她將這個新的觀點告訴她們。那個公園雖然名義上是克蘭姆的社區綠地,但裡頭其實只有乾枯的棕櫚樹、幾堆垃圾,以及一個布滿鏽斑、搖搖欲墜的盪鞦韆。其他女孩都同意,這是個很具說服力的說法,其中一個女孩還問:「那要先從誰開始呢?」她們大部分都在過去幾年身體變得豐腴之後,就開始戴頭巾了(雖然只是一條薄薄的絲巾而已),並且像家裡、左鄰右舍的許多人那樣開始做禮拜。戴頭巾的行為並不罕見;即使法律禁止女性在學校戴頭巾,違者也可能會被趕回家去,但戴頭巾依然是個頗為常見的違規行為。至於戴面紗呢?這個行為所傳達出的訊息就更有力、更堅定了。YouTube 上的那位謝赫曾說,雖然在很多地方,要戴頭巾並不容易,但我們不應為自己的伊斯蘭信仰感到退卻,「如果我們的人數愈多,傳達出的訊息就會愈強烈。」
突尼斯有個郊區叫做瑪爾莎,那裡住著許多自由派的突尼西亞人,他們和來自西方的跨國工作者比鄰而居,街上還有供應義式生豬肉火腿和琴酒的餐廳;如果努兒也出生在瑪爾莎某個中上階級家庭的話,那麼她可能就會用穿舌環的方式來表達叛逆。但她終究是個出生在克蘭姆的女孩,那是個勞工階級社區,而這個國家的政府還會監控人民,避免他們變得太過虔誠。因此很自然地,對於一個青少女來說,戴頭巾就是一種抵抗行為。那天她們在公園裡,當陽光把果汁盒的鋁箔面晒得閃閃發亮之際,她心裡卻因為使命感而感到有點緊張、有點興奮,胃裡不禁一陣翻攪。「從我開始吧。我從明天起就會戴面紗。」她如此跟朋友們說道。
她已經有一條面紗了,那是她從披薩店旁邊的頭巾鋪買來的。上週看完謝赫的影片之後,她就去那裡買了一條。她把自己鎖在家中的廁所裡,試戴了一下那條頭巾,還轉了轉身子,想從不同角度確認自己的眼睛在戴上面紗後好不好看。
隔天早上,她把頭巾塞進書包裡,接著像往常那樣和母親道別。靠近學校時,她鑽進一個門廊,然後將面紗固定在自己的頭巾上──其實也沒什麼,面紗不過就是一小塊遮住口鼻的布罷了。呼吸時,她能感覺到那塊布把自己的嘴脣磨得癢癢的。
校長早上通常都會站在校門口,迎接趕著上學的學生們。努兒緊跟在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女生後面,希望經過時不會被注意到,但校長還是攔住了她。
「你是誰?」校長一邊如此問道,一邊盯著她隱在黑布後面的纖細身軀。或許是幻想吧,但努兒似乎在女校長的聲音中聽到了一絲絲讚許。「我會讓你進校門,但你必須自己過你們老師那關。」校長如此說道。
努兒那天的第一堂課是法文課,她在自己平日的座位上坐了下來,然後把筆記本和原子筆都放到了木桌上。老師在教室的另一端看著她。起初老師並沒有說什麼,只是瞇起了自己的眼睛、帶點敵意地看著努兒,然後才走了過來,最後在離她兩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了下來,靠在一張沒有人使用的桌子上。
「你戴的那個是什麼可笑的東西啊?你以為真主希望你把一扇窗簾掛在自己的臉上嗎?我恨真主。祂才不是什麼和藹、仁慈的力量,祂非常殘酷。」老師將雙臂交叉在自己的胸前,鼻孔還在抽動著。對努兒來說,法文老師這幾句話是在褻瀆真主。努兒直直盯著黑板,全神貫注地看著老師在上面寫出的奇怪線條。「真主殺死了我的父母。」法文老師繼續說道。「如果可以對真主報仇的話,我一定會這麼做的。」全班學生都在看老師如何嚴厲地斥責她,他們從來沒有如此安靜過。法文老師最後終於起身,開始進行當天的課程。
努兒的下一堂課是阿拉伯文學。在突尼西亞,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學)吸引到的一般都是一些說法語的世俗主義者,他們通常都非常討厭信教的人,認為那些人既落後、又愚昧。當文學老師看到努兒時,她驚訝地從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來,接著走了過來,卡在努兒和桌子之間。
「你如果要戴這個,就別想在我的班上上課。馬上給我摘掉。」她說。
努兒的臉熱得發燙。她拒絕了老師的命令。
「我說了,給我摘掉。」老師又重複了一次,每個音節都鏗鏘有力。
努兒心想,不知道老師知不知道眼前的人是她。文學老師明明很喜歡她的。她是誰重要嗎?「不,我沒辦法摘掉,拜託。是我,我是努兒。」她的聲音在顫抖著。
老師聽了向前踏了一步,將自己的手壓在努兒的胸口上。「你沒聽到我說什麼嗎?我叫你把它摘掉。」她現在是用吼的了,臉部因為憤怒而扭曲變形。
努兒的耳裡充滿了自己的心跳聲。她向後退了一步,想擺脫老師用手施加的壓力。其他學生則圍了過來,試圖讓老師冷靜下來。她接著一把推開了學生,將自己的雙手都壓到了努兒的胸口上,用力地推著,彷彿想要把她推倒似的。
努兒倒抽了一口氣,向後踉蹌了幾步。老師再次把手臂舉了起來,像是要出手打她,又像是要將她的面紗摘下來似的。此時,努兒在班上的一個朋友──一個偶爾會被大家稱作「長頸鹿」的女生抓住了老師的手。「拜託,老師,拜託,冷靜一下。」
努兒哭了。她慶幸沒有人看得到她藏在面紗後方、因為屈辱而落下的淚水。整個班此時都陷入了混亂。有人去把校長找了過來,後來校長衝進了教室裡,命令所有學生到操場上集合。當天接下來的課程,全都被取消。
努兒並不覺得自己是顆少了保護殼的珍珠,也不覺得自己是支褪去包裝紙的棒棒糖。她覺得自己就是個十三歲的女孩,想要努力實踐自己的宗教信仰。她曾在 YouTube 上聽過一位謝赫論證,為何穆斯林女性有義務戴面紗。聽了四遍之後,謝赫的話便像電報字條一般,開始在她的腦海裡不斷播放。古蘭經的〈光明章〉要求女性不得展現自己的美麗和打扮,「只有那些明顯可見的部分除外。」照這樣說來,臉算是明顯可見的部分嗎?那位謝赫如此問道。有比臉部還要更不明顯可見的部位嗎?作為一名想順從真主聖意,希望蒙受真主祝福、並受祂認可的女性,將自己的臉部遮蔽起來,就是最能表達你真心誠意的方式。謝赫的話對努兒來說既直觀、又合理:只要衣著得當,女性就能被包覆在伊斯蘭的核心價值之中,包覆在和平、平靜與平等之中。那讓所有女人可見的差異都模糊了起來,不論貧富、不論美醜,也不論膚色深淺,大家都是一樣。這種做法可以提醒我們:真主對於所有祂創造出來的事物,都抱持著同等的愛。
二○○七年春天的某個下午,當努兒和幾個女性朋友坐在公園裡時,她將這個新的觀點告訴她們。那個公園雖然名義上是克蘭姆的社區綠地,但裡頭其實只有乾枯的棕櫚樹、幾堆垃圾,以及一個布滿鏽斑、搖搖欲墜的盪鞦韆。其他女孩都同意,這是個很具說服力的說法,其中一個女孩還問:「那要先從誰開始呢?」她們大部分都在過去幾年身體變得豐腴之後,就開始戴頭巾了(雖然只是一條薄薄的絲巾而已),並且像家裡、左鄰右舍的許多人那樣開始做禮拜。戴頭巾的行為並不罕見;即使法律禁止女性在學校戴頭巾,違者也可能會被趕回家去,但戴頭巾依然是個頗為常見的違規行為。至於戴面紗呢?這個行為所傳達出的訊息就更有力、更堅定了。YouTube 上的那位謝赫曾說,雖然在很多地方,要戴頭巾並不容易,但我們不應為自己的伊斯蘭信仰感到退卻,「如果我們的人數愈多,傳達出的訊息就會愈強烈。」
突尼斯有個郊區叫做瑪爾莎,那裡住著許多自由派的突尼西亞人,他們和來自西方的跨國工作者比鄰而居,街上還有供應義式生豬肉火腿和琴酒的餐廳;如果努兒也出生在瑪爾莎某個中上階級家庭的話,那麼她可能就會用穿舌環的方式來表達叛逆。但她終究是個出生在克蘭姆的女孩,那是個勞工階級社區,而這個國家的政府還會監控人民,避免他們變得太過虔誠。因此很自然地,對於一個青少女來說,戴頭巾就是一種抵抗行為。那天她們在公園裡,當陽光把果汁盒的鋁箔面晒得閃閃發亮之際,她心裡卻因為使命感而感到有點緊張、有點興奮,胃裡不禁一陣翻攪。「從我開始吧。我從明天起就會戴面紗。」她如此跟朋友們說道。
她已經有一條面紗了,那是她從披薩店旁邊的頭巾鋪買來的。上週看完謝赫的影片之後,她就去那裡買了一條。她把自己鎖在家中的廁所裡,試戴了一下那條頭巾,還轉了轉身子,想從不同角度確認自己的眼睛在戴上面紗後好不好看。
隔天早上,她把頭巾塞進書包裡,接著像往常那樣和母親道別。靠近學校時,她鑽進一個門廊,然後將面紗固定在自己的頭巾上──其實也沒什麼,面紗不過就是一小塊遮住口鼻的布罷了。呼吸時,她能感覺到那塊布把自己的嘴脣磨得癢癢的。
校長早上通常都會站在校門口,迎接趕著上學的學生們。努兒緊跟在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女生後面,希望經過時不會被注意到,但校長還是攔住了她。
「你是誰?」校長一邊如此問道,一邊盯著她隱在黑布後面的纖細身軀。或許是幻想吧,但努兒似乎在女校長的聲音中聽到了一絲絲讚許。「我會讓你進校門,但你必須自己過你們老師那關。」校長如此說道。
努兒那天的第一堂課是法文課,她在自己平日的座位上坐了下來,然後把筆記本和原子筆都放到了木桌上。老師在教室的另一端看著她。起初老師並沒有說什麼,只是瞇起了自己的眼睛、帶點敵意地看著努兒,然後才走了過來,最後在離她兩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了下來,靠在一張沒有人使用的桌子上。
「你戴的那個是什麼可笑的東西啊?你以為真主希望你把一扇窗簾掛在自己的臉上嗎?我恨真主。祂才不是什麼和藹、仁慈的力量,祂非常殘酷。」老師將雙臂交叉在自己的胸前,鼻孔還在抽動著。對努兒來說,法文老師這幾句話是在褻瀆真主。努兒直直盯著黑板,全神貫注地看著老師在上面寫出的奇怪線條。「真主殺死了我的父母。」法文老師繼續說道。「如果可以對真主報仇的話,我一定會這麼做的。」全班學生都在看老師如何嚴厲地斥責她,他們從來沒有如此安靜過。法文老師最後終於起身,開始進行當天的課程。
努兒的下一堂課是阿拉伯文學。在突尼西亞,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學)吸引到的一般都是一些說法語的世俗主義者,他們通常都非常討厭信教的人,認為那些人既落後、又愚昧。當文學老師看到努兒時,她驚訝地從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來,接著走了過來,卡在努兒和桌子之間。
「你如果要戴這個,就別想在我的班上上課。馬上給我摘掉。」她說。
努兒的臉熱得發燙。她拒絕了老師的命令。
「我說了,給我摘掉。」老師又重複了一次,每個音節都鏗鏘有力。
努兒心想,不知道老師知不知道眼前的人是她。文學老師明明很喜歡她的。她是誰重要嗎?「不,我沒辦法摘掉,拜託。是我,我是努兒。」她的聲音在顫抖著。
老師聽了向前踏了一步,將自己的手壓在努兒的胸口上。「你沒聽到我說什麼嗎?我叫你把它摘掉。」她現在是用吼的了,臉部因為憤怒而扭曲變形。
努兒的耳裡充滿了自己的心跳聲。她向後退了一步,想擺脫老師用手施加的壓力。其他學生則圍了過來,試圖讓老師冷靜下來。她接著一把推開了學生,將自己的雙手都壓到了努兒的胸口上,用力地推著,彷彿想要把她推倒似的。
努兒倒抽了一口氣,向後踉蹌了幾步。老師再次把手臂舉了起來,像是要出手打她,又像是要將她的面紗摘下來似的。此時,努兒在班上的一個朋友──一個偶爾會被大家稱作「長頸鹿」的女生抓住了老師的手。「拜託,老師,拜託,冷靜一下。」
努兒哭了。她慶幸沒有人看得到她藏在面紗後方、因為屈辱而落下的淚水。整個班此時都陷入了混亂。有人去把校長找了過來,後來校長衝進了教室裡,命令所有學生到操場上集合。當天接下來的課程,全都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