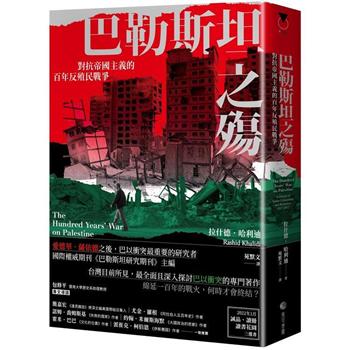引言
在一九九○年代初的幾年裡,我每次回到耶路撒冷就會長住幾個月,在城裡一些最古老的私人家族圖書館裡做研究,這裡面也包括我的家族的私立圖書館。我和妻子、孩子們住在一個屬於哈利迪家族義產基金會(waqf,宗教捐贈)的公寓裡,該公寓位於擁擠、嘈雜的耶路撒冷老城中心。站在這棟樓的屋頂上,可以看到早期伊斯蘭建築中最偉大的兩件傑作:一是就矗立在三百多英尺外的尊貴聖地(Haram al-Sharif,聖殿山)上金光閃閃的聖石圓頂寺(Dome of the Rock),以及在它的後方,小一些的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遠寺)的銀灰色圓頂,它們的背後是橄欖山(Mount of Olives)。向其他方向望去,可以看到老城裡的教堂和猶太教堂。
只要沿著西希拉門大街(Bab al-Silsila Street)往下走,就會看到哈利迪圖書館(Khalidi Library)的主體建築了,它是由我的祖父,哈吉.拉吉布.哈利迪(Hajj Raghib al-Khalidi)用他的媽媽海迪嘉.哈利迪(Khadija al-Khalidi)的遺產於一八九九年建立的。圖書館裡收藏了一千二百多份手稿,主要是阿拉伯文(一些是波斯文和奧斯曼土耳其文),其中最古老的手稿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紀初。藏書裡包括大約兩千本十九世紀的阿拉伯文書籍和品項繁雜的各種家庭文件,這些藏品是整個巴勒斯坦最廣的收藏品之一,它們至今仍然掌握在原家族主人的手中。
在我的逗留期間,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紀的圖書館主體結構正在進行維修,因此,那些藏書被放在紙箱中,暫存在一棟馬穆魯克王朝時期的建築中,這棟建築可以透過一個狹窄的樓梯與我們的公寓相通。我花了超過一年時間翻閱這些大箱子中被塵封已久、蟲蛀過的書籍、文件和屬於幾代哈利迪家族成員們的信件,它們中也有我的曾曾叔父優素福.迪亞.丁.帕夏.哈利迪(Yusuf Diya al-Din Pasha al-Khalidi)的信件。透過他的各種文件,我發現他是一個沉穩老練的人,他在耶路撒冷、馬爾他、伊斯坦堡和維也納接受了內容豐富、領域廣泛的教育,他對比較宗教,特別是猶太教,持有濃厚的興趣,他擁有許多用歐洲語言撰寫的關於這方面和其他主題的書。
優素福.迪亞是一代又一代的耶路撒冷伊斯蘭學者和法學家們的後代;他的父親塞伊德.穆罕默德.阿里.哈利迪(al-Sayyid Muhammad ‘Ali al-Khalidi)曾擔任過耶路撒冷伊斯蘭教法法庭祕書處的副主任和主任長達五十年左右。但在年輕時,優素福.迪亞為自己尋找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在吸收了傳統伊斯蘭教育的基本知識後,他在十八歲時離開了巴勒斯坦,據說他沒有經過他父親的同意,就在馬爾他的一所英國人開辦的教會傳教士學校裡學習了兩年。從馬爾他啟程,他又去了伊斯坦堡的帝國醫學院裡學習,之後他進入這裡的羅伯特學院(Robert College)學習,該學院是當時才剛剛由美國的新教傳教士創辦的。在一八六○年代的五年時間裡,優素福.迪亞在該地區最早的一些提供現代西式教育的機構中學習,他學會了英語、法語、德語和其他的許多知識。這對於十九世紀中期一個來自穆斯林宗教學者家庭的年輕人來說,是一條非常不尋常的發展軌跡。
在獲得這種內容廣泛的教育訓練後,優素福.迪亞擔任了奧斯曼帝國政府中的各種官員,包括外交部的翻譯;駐俄羅斯黑海波提港(port of Poti)的領事;庫德斯坦、黎巴嫩、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等地區的區長;並擔任了耶路撒冷市長將近十年時間,還曾任教於維也納皇家帝國大學。一八七六年時,在根據奧斯曼帝國新憲法而成立的奧斯曼帝國短暫的議會中,他當選為耶路撒冷代表,但因為他支持議會有權行使行政權力而惹來了蘇丹阿布杜哈米德(‘Abd al-Hamid)的敵意。
根據家族傳統和他所接受的伊斯蘭的和西方的教育,哈利迪成為了一名出色的學者。哈利迪圖書館裡收藏了他的許多法語、德語和英語書籍,以及他和歐洲及中東地區學識淵博的人物的通信。此外,圖書館中收藏的奧地利、法國和英國舊報紙傳達出,優素福.迪亞經常閱讀海外報刊。有證據表明,他是透過位於伊斯坦堡的奧地利郵局收到這些材料的,因為該郵局不受奧斯曼帝國嚴厲的審查法的限制。
透過廣泛的閱讀、在維也納和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歷以及與基督教傳教士的接觸,優素福.迪亞充分地認識到了反猶主義(anti-Semitism)在西方的普遍。他還對錫安主義(Zionism,猶太復國主義)的思想淵源有了深刻的了解,他尤其深刻地理解到,猶太復國主義的本質是在回應基督教歐洲強烈的反猶主義。
毫無疑問的,他也十分熟悉維也納記者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於一八九六年出版的《猶太國家》(Der Judenstaat)這本書,並知道一八九七年和九八年在瑞士巴塞爾召開的最初兩次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事實似乎很明顯,他在維也納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赫茨爾了)。他知道不同的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和猶太復國主義傾向的辯論和觀點,其中也包括赫茨爾明確呼籲為猶太人建立一個擁有控制移民之「主權權利」的國家。此外,身為耶路撒冷市長,他目睹了在原型錫安主義者(proto-Zionist)活動的最初幾年裡,這些人和當地居民所產生的摩擦,這些人是在一八七○年代末至一八八○年代初時來自歐洲的最早的猶太定居者。
赫茨爾是這個他創立的日益壯大的運動的公認領袖,他在一八九八年完成了自己對耶路撒冷的唯一一次造訪,他到來的時間與德皇威廉二世訪問的時間相重合。在這時候,他已經開始思考對巴勒斯坦進行殖民所涉及的一些問題了,他在一八九五年的日記中寫道:
我們必須在劃給我們的土地上,和緩地沒收巴勒斯坦的私有財產。我們得在他們(巴勒斯坦人)過境的各國提供他們工作機會,並同時讓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找不到工作,以此來鼓動那些身無分文的人口勇於跨出國界。有產者會站到我們這邊來。徵用和驅趕窮人的過程都必須謹慎小心地進行。
優素福.迪亞比他的大多數巴勒斯坦同胞更清楚新生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野心及其力量、資源和吸引力。他很清楚,猶太復國主義對巴勒斯坦的主張及在那裡建立猶太國家和主權的明確目標,這跟該國本地居民的權利和福祉是無法調和的。大概正是出於這些原因,在一八九九年三月一日,優素福.迪亞給法國的首席猶太教拉比札多克.卡恩(Zadoc Kahn)寄去了一封長達七頁的極具先見之明的信,並要求將這封信轉交給現代猶太復國主義的創始人赫茨爾。
信中首先表達了優素福.迪亞對於赫茨爾的欽佩,他認為赫茨爾「作為個人,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是一位真正熱愛猶太民族的人。」優素福.迪亞還表達了他對猶太教和猶太人的尊重,他說猶太人是「我們的堂兄弟」,他的意思是說亞伯拉罕(易卜拉欣)是同時受猶太人和穆斯林尊敬的先輩。
他是理解猶太復國主義的動機的,正如他對猶太人在歐洲受到的迫害表示遺憾一樣。有鑑於此,他寫道,猶太復國主義在原則上是「自然而然的、美麗的和理所應當的」,而且,「誰能對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權利提出異議?我的主啊,它是你歷史上的國家!」
這句話有時候會被從上下文語境地單獨剝離出來,以此代表優素福.迪亞熱情接受巴勒斯坦的整個猶太復國主義計畫。然而,這位前耶路撒冷市長和副市長馬上就提出了他的警告,他預見到在巴勒斯坦實施猶太復國主義主權國家計畫的後果是危險的。猶太復國主義的想法會挑起在那裡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之間的爭端。它將危及猶太人在奧斯曼帝國領土上一直享有的地位和安全。談到他的主要目的,優素福.迪亞清醒地表示,無論猶太復國主義有什麼優點,「都必須要考慮到形勢的殘酷」。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巴勒斯坦是奧斯曼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嚴重的是,它上面有其他人居住。」巴勒斯坦已經有了本地居民,他們絕不會接受被別人取而代之。優素福.迪亞「在充分了解事實的情況下」做出了論斷,斷言猶太復國主義接管巴勒斯坦的計畫是「純粹的荒唐」。沒有什麼比讓「不幸的猶太民族」在其他地方找到避難所更為公允和公平了。但是,他最後衷心地請求:「以神的名義,別碰巴勒斯坦。」
赫茨爾很快就回信給優素福.迪亞。他在三月十九日寄達的信可能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創始人,首次回應巴勒斯坦人對萌芽中的巴勒斯坦計畫的合理拒絕。在信中,赫茨爾確立了一種把本地居民的利益,有時甚至是把他們的存在視為無足輕重的公式。這位猶太復國主義領袖根本無視信中的基本論點,即巴勒斯坦已經存在一個不會同意被取而代之的居民的事實。雖然赫茨爾曾經訪問過這個國家,但他和大多數早期的歐洲猶太復國主義者一樣,對當地居民沒有多少了解或接觸。他也沒有回應哈利迪所指出,猶太復國主義計畫將會給整個中東地區大量的已發展成熟的猶太人社區造成危險。
在給猶太復國主義(最終意味著猶太人控制巴勒斯坦的事實)擦脂抹粉時,赫茨爾拿出了一個在任何其他時候、任何其他地點的殖民主義者,也會拿出來當作萬用法寶的說辭,這個說辭也將會成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主要論點:猶太移民將會讓巴勒斯坦的本地居民獲益。「我們帶人進去,這會增加他們的好處,增加他們的個人財富。」呼應著他在《猶太國家》中使用的語言,他補充道:「如果能允許有一些猶太移民的話,他們的智慧、他們的經濟頭腦和他們的企業手段都會被帶到這個國家去,沒有人會懷疑,這對整個國家的福祉都是一個好結果。」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信中提到了優素福.迪亞甚至沒有提起的一個擔憂。「閣下,你看到了另一個困難,即巴勒斯坦有非猶太人的民族存在。但誰會想到要把他們送走呢?」赫茨爾在回答哈利迪未曾問過的問題時,用他的保證暗示了他在日記中所記錄下來,希望將該國的貧困人口「和緩地」送出國界的願望。從這段令人不寒而慄的引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赫茨爾完全知道,「消失」巴勒斯坦本地人口對於猶太復國主義成功的重要性。此外,他為猶太-奧斯曼土地公司(Jewish-Ottoman Land Company)共同起草的一九○一年章程中,也包含了同樣的原則,即把巴勒斯坦居民遷往「奧斯曼帝國的其他省份和領土上去」。儘管赫茨爾在其著作中強調,他的計畫是建立在「最高的容忍度」的基礎上的,所有人都享有充分的權利,但這句話的意思只不過是在其餘的人被遷往其他地方去了以後,容忍可能殘餘的少數群體。
赫茨爾低估了這位和他通信的人。從哈利迪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哈利迪完全明白問題的關鍵不是把數目有限的「一些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而是將整塊土地轉化成一個猶太國家。鑑於赫茨爾給他的答覆,優素福.迪亞只能得出以下兩種結論中的一個。要麼是猶太復國主義領袖有意透過隱瞞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真正目的來欺騙他,要麼就是赫茨爾根本不認為優素福.迪亞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值得被認真對待。
相反的,赫茨爾本著十九世紀歐洲人常見的自鳴得意和自信,提出了一個荒謬的誘因,即讓一群陌生人殖民本地居民的土地,並最終篡奪這片土地,這種行為將有利於該國的人民。赫茨爾的想法和他對優素福.迪亞的答覆,似乎是基於一種假定的基礎,認為阿拉伯人最終可以被收買或愚弄,然後忽視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對巴勒斯坦懷有的實際意圖。這種面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智慧的傲慢態度(更遑論權利),在隨後的幾十年裡一直不斷地在猶太復國主義、英國、歐洲和美國的領導人身上重複出現。至於赫茨爾創立的運動所最終建立起來的猶太國家,正如優素福.迪亞所預見到的那樣,那裡只容得下一個民族,也就是猶太民族。至於其他的民族,他們將確實地被「趕走」,或者頂多是被容忍留下。
在一九九○年代初的幾年裡,我每次回到耶路撒冷就會長住幾個月,在城裡一些最古老的私人家族圖書館裡做研究,這裡面也包括我的家族的私立圖書館。我和妻子、孩子們住在一個屬於哈利迪家族義產基金會(waqf,宗教捐贈)的公寓裡,該公寓位於擁擠、嘈雜的耶路撒冷老城中心。站在這棟樓的屋頂上,可以看到早期伊斯蘭建築中最偉大的兩件傑作:一是就矗立在三百多英尺外的尊貴聖地(Haram al-Sharif,聖殿山)上金光閃閃的聖石圓頂寺(Dome of the Rock),以及在它的後方,小一些的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遠寺)的銀灰色圓頂,它們的背後是橄欖山(Mount of Olives)。向其他方向望去,可以看到老城裡的教堂和猶太教堂。
只要沿著西希拉門大街(Bab al-Silsila Street)往下走,就會看到哈利迪圖書館(Khalidi Library)的主體建築了,它是由我的祖父,哈吉.拉吉布.哈利迪(Hajj Raghib al-Khalidi)用他的媽媽海迪嘉.哈利迪(Khadija al-Khalidi)的遺產於一八九九年建立的。圖書館裡收藏了一千二百多份手稿,主要是阿拉伯文(一些是波斯文和奧斯曼土耳其文),其中最古老的手稿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紀初。藏書裡包括大約兩千本十九世紀的阿拉伯文書籍和品項繁雜的各種家庭文件,這些藏品是整個巴勒斯坦最廣的收藏品之一,它們至今仍然掌握在原家族主人的手中。
在我的逗留期間,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紀的圖書館主體結構正在進行維修,因此,那些藏書被放在紙箱中,暫存在一棟馬穆魯克王朝時期的建築中,這棟建築可以透過一個狹窄的樓梯與我們的公寓相通。我花了超過一年時間翻閱這些大箱子中被塵封已久、蟲蛀過的書籍、文件和屬於幾代哈利迪家族成員們的信件,它們中也有我的曾曾叔父優素福.迪亞.丁.帕夏.哈利迪(Yusuf Diya al-Din Pasha al-Khalidi)的信件。透過他的各種文件,我發現他是一個沉穩老練的人,他在耶路撒冷、馬爾他、伊斯坦堡和維也納接受了內容豐富、領域廣泛的教育,他對比較宗教,特別是猶太教,持有濃厚的興趣,他擁有許多用歐洲語言撰寫的關於這方面和其他主題的書。
優素福.迪亞是一代又一代的耶路撒冷伊斯蘭學者和法學家們的後代;他的父親塞伊德.穆罕默德.阿里.哈利迪(al-Sayyid Muhammad ‘Ali al-Khalidi)曾擔任過耶路撒冷伊斯蘭教法法庭祕書處的副主任和主任長達五十年左右。但在年輕時,優素福.迪亞為自己尋找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在吸收了傳統伊斯蘭教育的基本知識後,他在十八歲時離開了巴勒斯坦,據說他沒有經過他父親的同意,就在馬爾他的一所英國人開辦的教會傳教士學校裡學習了兩年。從馬爾他啟程,他又去了伊斯坦堡的帝國醫學院裡學習,之後他進入這裡的羅伯特學院(Robert College)學習,該學院是當時才剛剛由美國的新教傳教士創辦的。在一八六○年代的五年時間裡,優素福.迪亞在該地區最早的一些提供現代西式教育的機構中學習,他學會了英語、法語、德語和其他的許多知識。這對於十九世紀中期一個來自穆斯林宗教學者家庭的年輕人來說,是一條非常不尋常的發展軌跡。
在獲得這種內容廣泛的教育訓練後,優素福.迪亞擔任了奧斯曼帝國政府中的各種官員,包括外交部的翻譯;駐俄羅斯黑海波提港(port of Poti)的領事;庫德斯坦、黎巴嫩、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等地區的區長;並擔任了耶路撒冷市長將近十年時間,還曾任教於維也納皇家帝國大學。一八七六年時,在根據奧斯曼帝國新憲法而成立的奧斯曼帝國短暫的議會中,他當選為耶路撒冷代表,但因為他支持議會有權行使行政權力而惹來了蘇丹阿布杜哈米德(‘Abd al-Hamid)的敵意。
根據家族傳統和他所接受的伊斯蘭的和西方的教育,哈利迪成為了一名出色的學者。哈利迪圖書館裡收藏了他的許多法語、德語和英語書籍,以及他和歐洲及中東地區學識淵博的人物的通信。此外,圖書館中收藏的奧地利、法國和英國舊報紙傳達出,優素福.迪亞經常閱讀海外報刊。有證據表明,他是透過位於伊斯坦堡的奧地利郵局收到這些材料的,因為該郵局不受奧斯曼帝國嚴厲的審查法的限制。
透過廣泛的閱讀、在維也納和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歷以及與基督教傳教士的接觸,優素福.迪亞充分地認識到了反猶主義(anti-Semitism)在西方的普遍。他還對錫安主義(Zionism,猶太復國主義)的思想淵源有了深刻的了解,他尤其深刻地理解到,猶太復國主義的本質是在回應基督教歐洲強烈的反猶主義。
毫無疑問的,他也十分熟悉維也納記者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於一八九六年出版的《猶太國家》(Der Judenstaat)這本書,並知道一八九七年和九八年在瑞士巴塞爾召開的最初兩次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事實似乎很明顯,他在維也納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赫茨爾了)。他知道不同的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和猶太復國主義傾向的辯論和觀點,其中也包括赫茨爾明確呼籲為猶太人建立一個擁有控制移民之「主權權利」的國家。此外,身為耶路撒冷市長,他目睹了在原型錫安主義者(proto-Zionist)活動的最初幾年裡,這些人和當地居民所產生的摩擦,這些人是在一八七○年代末至一八八○年代初時來自歐洲的最早的猶太定居者。
赫茨爾是這個他創立的日益壯大的運動的公認領袖,他在一八九八年完成了自己對耶路撒冷的唯一一次造訪,他到來的時間與德皇威廉二世訪問的時間相重合。在這時候,他已經開始思考對巴勒斯坦進行殖民所涉及的一些問題了,他在一八九五年的日記中寫道:
我們必須在劃給我們的土地上,和緩地沒收巴勒斯坦的私有財產。我們得在他們(巴勒斯坦人)過境的各國提供他們工作機會,並同時讓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找不到工作,以此來鼓動那些身無分文的人口勇於跨出國界。有產者會站到我們這邊來。徵用和驅趕窮人的過程都必須謹慎小心地進行。
優素福.迪亞比他的大多數巴勒斯坦同胞更清楚新生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野心及其力量、資源和吸引力。他很清楚,猶太復國主義對巴勒斯坦的主張及在那裡建立猶太國家和主權的明確目標,這跟該國本地居民的權利和福祉是無法調和的。大概正是出於這些原因,在一八九九年三月一日,優素福.迪亞給法國的首席猶太教拉比札多克.卡恩(Zadoc Kahn)寄去了一封長達七頁的極具先見之明的信,並要求將這封信轉交給現代猶太復國主義的創始人赫茨爾。
信中首先表達了優素福.迪亞對於赫茨爾的欽佩,他認為赫茨爾「作為個人,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是一位真正熱愛猶太民族的人。」優素福.迪亞還表達了他對猶太教和猶太人的尊重,他說猶太人是「我們的堂兄弟」,他的意思是說亞伯拉罕(易卜拉欣)是同時受猶太人和穆斯林尊敬的先輩。
他是理解猶太復國主義的動機的,正如他對猶太人在歐洲受到的迫害表示遺憾一樣。有鑑於此,他寫道,猶太復國主義在原則上是「自然而然的、美麗的和理所應當的」,而且,「誰能對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權利提出異議?我的主啊,它是你歷史上的國家!」
這句話有時候會被從上下文語境地單獨剝離出來,以此代表優素福.迪亞熱情接受巴勒斯坦的整個猶太復國主義計畫。然而,這位前耶路撒冷市長和副市長馬上就提出了他的警告,他預見到在巴勒斯坦實施猶太復國主義主權國家計畫的後果是危險的。猶太復國主義的想法會挑起在那裡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之間的爭端。它將危及猶太人在奧斯曼帝國領土上一直享有的地位和安全。談到他的主要目的,優素福.迪亞清醒地表示,無論猶太復國主義有什麼優點,「都必須要考慮到形勢的殘酷」。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巴勒斯坦是奧斯曼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嚴重的是,它上面有其他人居住。」巴勒斯坦已經有了本地居民,他們絕不會接受被別人取而代之。優素福.迪亞「在充分了解事實的情況下」做出了論斷,斷言猶太復國主義接管巴勒斯坦的計畫是「純粹的荒唐」。沒有什麼比讓「不幸的猶太民族」在其他地方找到避難所更為公允和公平了。但是,他最後衷心地請求:「以神的名義,別碰巴勒斯坦。」
赫茨爾很快就回信給優素福.迪亞。他在三月十九日寄達的信可能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創始人,首次回應巴勒斯坦人對萌芽中的巴勒斯坦計畫的合理拒絕。在信中,赫茨爾確立了一種把本地居民的利益,有時甚至是把他們的存在視為無足輕重的公式。這位猶太復國主義領袖根本無視信中的基本論點,即巴勒斯坦已經存在一個不會同意被取而代之的居民的事實。雖然赫茨爾曾經訪問過這個國家,但他和大多數早期的歐洲猶太復國主義者一樣,對當地居民沒有多少了解或接觸。他也沒有回應哈利迪所指出,猶太復國主義計畫將會給整個中東地區大量的已發展成熟的猶太人社區造成危險。
在給猶太復國主義(最終意味著猶太人控制巴勒斯坦的事實)擦脂抹粉時,赫茨爾拿出了一個在任何其他時候、任何其他地點的殖民主義者,也會拿出來當作萬用法寶的說辭,這個說辭也將會成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主要論點:猶太移民將會讓巴勒斯坦的本地居民獲益。「我們帶人進去,這會增加他們的好處,增加他們的個人財富。」呼應著他在《猶太國家》中使用的語言,他補充道:「如果能允許有一些猶太移民的話,他們的智慧、他們的經濟頭腦和他們的企業手段都會被帶到這個國家去,沒有人會懷疑,這對整個國家的福祉都是一個好結果。」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信中提到了優素福.迪亞甚至沒有提起的一個擔憂。「閣下,你看到了另一個困難,即巴勒斯坦有非猶太人的民族存在。但誰會想到要把他們送走呢?」赫茨爾在回答哈利迪未曾問過的問題時,用他的保證暗示了他在日記中所記錄下來,希望將該國的貧困人口「和緩地」送出國界的願望。從這段令人不寒而慄的引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赫茨爾完全知道,「消失」巴勒斯坦本地人口對於猶太復國主義成功的重要性。此外,他為猶太-奧斯曼土地公司(Jewish-Ottoman Land Company)共同起草的一九○一年章程中,也包含了同樣的原則,即把巴勒斯坦居民遷往「奧斯曼帝國的其他省份和領土上去」。儘管赫茨爾在其著作中強調,他的計畫是建立在「最高的容忍度」的基礎上的,所有人都享有充分的權利,但這句話的意思只不過是在其餘的人被遷往其他地方去了以後,容忍可能殘餘的少數群體。
赫茨爾低估了這位和他通信的人。從哈利迪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哈利迪完全明白問題的關鍵不是把數目有限的「一些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而是將整塊土地轉化成一個猶太國家。鑑於赫茨爾給他的答覆,優素福.迪亞只能得出以下兩種結論中的一個。要麼是猶太復國主義領袖有意透過隱瞞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真正目的來欺騙他,要麼就是赫茨爾根本不認為優素福.迪亞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值得被認真對待。
相反的,赫茨爾本著十九世紀歐洲人常見的自鳴得意和自信,提出了一個荒謬的誘因,即讓一群陌生人殖民本地居民的土地,並最終篡奪這片土地,這種行為將有利於該國的人民。赫茨爾的想法和他對優素福.迪亞的答覆,似乎是基於一種假定的基礎,認為阿拉伯人最終可以被收買或愚弄,然後忽視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對巴勒斯坦懷有的實際意圖。這種面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智慧的傲慢態度(更遑論權利),在隨後的幾十年裡一直不斷地在猶太復國主義、英國、歐洲和美國的領導人身上重複出現。至於赫茨爾創立的運動所最終建立起來的猶太國家,正如優素福.迪亞所預見到的那樣,那裡只容得下一個民族,也就是猶太民族。至於其他的民族,他們將確實地被「趕走」,或者頂多是被容忍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