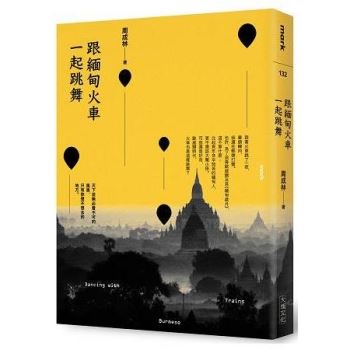這個緬甸
開場白
緬甸在變。在仰光三十七街小小的蒲甘書店(Bagan Book House),你幾乎找得到所有關於緬甸的英文書,從撣邦歷史孟邦(Mon State)歷史到英國人廢黜的熱寶王朝,從蒲甘的興衰到極其怪異的新首都內比都,從翁山蘇姬到不受歡迎的丹瑞將軍,從西方人寫的緬甸遊記到緬甸女作家用英文寫的緬甸遊記……「沒錯,影印本占多數,但誰在乎。」我告訴店內偶遇的一位六十開外的美國攝影師;我們聊起書架上幾本讀過的傳記、遊記和地緣政治論著,如逢知己。
蒲甘書店的老闆是位矮胖的中年人,和善,卻又不乏生意人的精明。五天前初次光顧,我買了兩本影印的英文書,議價時,他一臉苦相:「Don’t make my cry.」這一次,我指著幾本從前的禁書對老闆說:「三年前,這些都不可能。」「兩年前。」他糾正我。「從前只能藏起來。」最後一次光顧,我買了英國人喬治.史考特(George Scott)寫的The Burman: His Life and Notions(《緬甸人的生活與觀念》);作者是十九世紀典型的帝國主義者,化名Shway Yoe(緬甸人名),撰成這本至今流傳的小範圍經典。見我選了這本書,美國攝影師恍然大悟:他讀過我正在讀的那本關於史考特的書:「哈,Shway Yoe 原來就是Scott。」一下賣出兩冊,書店老闆給了我們折扣:每本便宜一千緬幣。「謝謝。」老闆接過錢,像幾乎所有緬甸平民一樣客氣。
在仰光郊外髒亂昏暗的昂敏加拉爾(Aung Mingalar)汽車站,我坐在露天茶室,喝著一罐越南產的可口可樂,等著開往曼德勒的夜車。鄰桌坐了幾個緬甸年輕人和一個嬉皮裝扮的美國黑人。其中一位緬甸後生英語講得流利。他說美國黑人是他姻親。我說外國人從陸路進入緬甸依舊困難而且昂貴。「會變的。我們現在有了民主。會變的。」緬甸後生信心滿滿,我忍著沒說這個民主還不是真正民主,路還很長,哪怕現有改變是個良好開端,就像今年一月最後一期英文版《緬甸時報》(The Myanmar Times)的頭條新聞,講到新聞審查取消後自由記者面臨的挑戰:報導政府軍和少數族裔的武裝衝突不再犯禁,記者也不再因此受到當局恐嚇,但是難在從各類傳聞之中找出真相。同一期報紙的文化版還有一篇報導,導演U Anthony 要拍一部電影,主人公是一名十六歲的高中女生Ma Win MawOo,一九八八年的民主運動之中死在軍政府的槍下。
二十多年來,當局不斷恐嚇死者父母,甚至在死者祭日阻止僧人到家中接受布施。而今,父母終於可以公開紀念女兒,這部四月開拍、九月十九日(死者忌日)上映的電影,也將以家人的紀念作為最後一幕。
不是所有人都信心滿滿。在撣邦南部的格勞,一位退休的印裔老者告訴我,他做過政府部門打字員,每月退休金只有四千緬幣(不足五美元)。「夠什麼?」老頭歎道。他現在幫NGO(非政府組織)做項目掙外快,兒子則在香港做事。我說我喜歡格勞遍山松林、清新安寧。他撇撇嘴,有些不屑:「從前更好。現在滿街中國摩托車。很吵。一輛只要三、四百美金。材料廉價。」在曼德勒山腳的露天茶室,一位印裔計程車司機,黑瘦,五十來歲,坐著在喝可樂。「緬甸人現在很懶。他們不想做事,只想享樂。」計程車司機有些忿然。在蒲甘,一座荒蕪小廟近旁的洋槐樹下,十三歲的莫莫(Momo),領我去看小廟後面她的家:祖孫三代八人同居的竹棚。莫莫告訴我,她十七歲的姐姐不時要去鄰村幫人洗衣,一天只賺五百緬幣(權作對比:一瓶純淨水在緬甸通常要賣三百緬幣)。
等我第三次回到仰光,載我到仰光機場的司機也開了一輛廉價的中國車。仰光郊外綠蔭宜人。車過大學路,我脫口而出:「翁山蘇姬就住這條路。」「對。就往左。你去看過?」「沒。又進不去。現在也沒集會。」沉默片刻,年輕計程車司機說:「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一夜之間,全世界,尤其富裕國家的遊客和旅行者,似乎都湧來緬甸。不只一次,我告訴這趟旅行遇到的諸多西方旅伴:前幾年來緬甸或許太早,過幾年又怕太遲,現在來,或許正是時候。
一
飛機晚點了。我到仰光已是薄暮。機窗下,不再是一片雲南的紅褐,綠色叢林點綴著金色佛塔和瓦楞鐵屋頂的平房,大小不等的水塘與河湖,泛著雲影的稻田,豬腸一樣細窄的公路,火柴盒一樣的零星車輛。「這個國家看上去很多農田嘛!怎麼會窮呢?」坐在後排的中國鄉下人用西南口音告訴同伴,滿腦袋當代中國式的不解。
仰光機場就像昆明機場一樣現代,男廁的小便池放著防臭的綠色衛生丸,足以讓你產生幻覺,以為自己來到一個中等發達的國家。帶著不容置疑的堅決,一美元也不退讓,我告訴中年印裔計程車司機要去市中心獨立紀念碑附近某家旅店。仰光沒我想像的熱,或許我在靠近熱帶的澳門住過多年,回到南國反而令我興奮。「你從哪來?」計程車司機問。這個問題就像日常問候,我隨後天天都會遇到,也很快因為自己的國籍和提問者的沉默而尷尬,不得不隨機改變自己的身分。但是初來乍到,報上國籍,我還察覺不出計程車司機的不置可否。
我要投宿的旅店只剩二十四美元一晚的雙人房。無暇細看仰光鬧市滿街小販遍地吃喝,我在獨立紀念碑和蘇萊塔附近找到棲所:三美元一夜的地鋪,最後一個空位。客棧位於衰敗的殖民時代磚樓第三層,地鋪則在閣樓,四人同居,鄰鋪都是白人男女,兩台電扇一高一低吹著熱風,窗外則是車水馬龍的摩訶班都拉大街(Mahabandoola Road),殘破的仰光巴士,日本淘汰的舊車,車尾的發動機蓋掀起,賽車一般呼嘯而過。一名豐滿的金髮妹跟我一樣剛到,也跟我一樣,總算找到廉價住處。「三美元。還想怎樣?況且我帶了耳塞。」「我也帶了。」她笑道。下到逼仄前台,客棧兩名小廝,來自仰光附近的勃固(Pegu),纏著紗籠,臉上塗著清涼的特納卡(Thanakha),正跟一名上身赤裸圍著浴巾的印度住客講笑。「這是什麼?」中年印度人板起臉,指著小廝臉上的特納卡,自問自答。「你就像非洲人!」
「你是日本人?」一名小廝問我。我笑著搖頭,但他認定我是日本人。兩個小廝跟我講起歪歪扭扭的日語:空巴哇。阿裡嘎多歌紮依馬西達。哦哈喲……
客棧隔壁就是一家啤酒屋,臨著小街,斜對蘇萊塔。這類啤酒屋,通常只有男人光顧,__緬式英語叫作Beer Station,聽來堂皇,實則酒吧的替代物(你在緬甸很少見到真正的酒吧),除了酒,還賣佐酒小食和簡單飯菜。我坐在啤酒屋,喝著一杯緬甸生啤,鄰桌的中年男子在喝一小瓶緬甸威士忌,不時對我微笑,露出檳榔汁染紅的牙齒。身後,一台液晶電視懸在半空,播著一場官式慶典:體育場內,軍樂隊走著隊列奏著軍樂,看台上的男女衣冠楚楚。鏡頭單調,只在軍樂隊和觀眾之間緩慢切換。
「內比都?」我問鄰桌(內比都是緬甸的新首都)。
「內比都。」他點點頭,幾乎講不了英語。他長得不好看,甚至有點「樣衰」,讓你想到書中讀到的官方密探,幾年前遍布該國茶室與啤酒屋,偷聽食客閒談,舉報「不軌」言論。對當局的任何公開不滿都會引來麻煩,哪怕幾句調侃。上個世紀九○年代,一位著名的緬甸喜劇演員講了一個笑話,說自己買了一台彩色電視,搬回家發現彩色電視只有兩種顏色:綠色和橙色(綠色是軍人,橙色是僧人)。他諷刺電視裡將軍向僧人捐贈財物積累功德的「善舉」沒完沒了。表演結束,這名演員被捕,在仰光北郊的永盛監獄待了五年。
「嗯!」「密探」一臉通紅,啞巴一樣發聲,把一小碟炒蠶豆遞到我面前,要我嘗嘗。斜對一桌來了幾個印裔緬甸人,說著,笑著,其中一人,厚厚一疊緬幣用橡皮筋捆紮,通貨膨脹一般,別在圍著紗籠的腰間。見你張望,對方也會回望,微笑,點頭,哈囉,沒有我來的國度那些國民的目光躲閃表情僵硬。等我吃完一碗湯麵,灌完三杯生啤,「密探」也搖搖晃晃,徑直買單走人,沒有道別,彷彿真的是個趕著回去交差的密探。
不到九點,仰光已經打著呵欠。蘇萊塔旁的摩訶班都拉大街路燈昏暗,商店十門九閉,街邊發電機轟鳴。殘破的大小巴士猛然煞到路旁,車上負責收錢的男子,長臂猿一般,半身懸出門外,高聲兜著最後的生意。然而人未散盡,每條窄巷的巷口,都是印度人的露天食檔、檳榔攤和菸攤(我的住處靠近印度人社區)。廢墟一樣的街道,凹凸不平,危機四伏。
我在街邊一處還算明亮的冷飲攤坐下,喝著雪糕、草莓和小粒果凍混合的泡露達,研究電子版的旅行指南。冷飲攤的主人,一位將近六十的瘦小男子,突然湊近,友好、怯生,指著Kindle 用英語問我:「這是什麼?」
「這是電子書。」
「這是什麼?」他指向我放在桌上包裝精巧的小包紙巾,來自另一世界。
「這是紙巾。」內心惻然,我翻出電子書中翁山蘇姬最新傳記的封面照片給他看。他咧著嘴笑,像個憨厚的老農。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