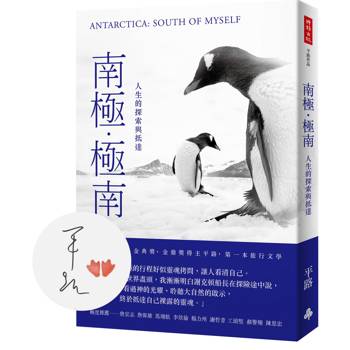前言
為什麼去南極?
為什麼是南極,我第一本旅行做主題的成書?
之前,我沒有寫過遊記。對於我,旅行純粹為了樂趣,總帶著漫無目標的情調。
心中甚至有一種疑惑,不寫,為了不要毀掉純屬於個人的趣味。同樣的恐懼,一直是種恐懼,彷彿某種悖論。我寫什麼,什麼就消失不見。我寫童年,愈去追想,我真正的童年會不會消失不見?我寫父親,父親的形影在我眼前愈來愈淡薄,會不會看不見他了?
一旦選定主題,按下快門,就此遺失了不在相片內的一切。
不寫遊記,曾是同樣的理由吧。這一回,卻是一本不像遊記的遊記。
人在南極,詭奇的景色中,串起我大半生剪影。
那是鏡子的魔法,鏡面裡還有鏡面。自從接近南極洲,許多時刻,像一隻飛鳥,我分明是在記憶裡滑翔。往昔時光,在鏡中清楚又模糊,「南極」反過來成了「極南」。一幀幀攝影負片,照出我的顛倒夢想。
冰山如鏡,純白的稜線更像是內心通道,多重折射中,映現出我的嚮往、我的探索、我的迷惘、我的漂泊、我的挫敗,直達自己赤裸的靈魂。偶爾冰山滾落一角,掉進南冰洋裡,咚咚沉下去,我逐漸明白,這些年為什麼自己聽到的⋯⋯總是不一樣的鼓聲?
卡繆的話:「要了解這個世界,有時必須離開它。」旅程是解鎖,為了明瞭此生所為何來。
1 出發前
出發在即,冬至前一天,台北大寒。
早幾個小時,我忙著整理此行要帶的書。
在南極,哪裡能夠沒有書?我出神的想著,譬如第一個抵達南極點的阿蒙森,除了巧克力與肉餅,還帶著三千本書。
書架上一本本瀏覽,打開一本再放回去,原本屬於我的快樂時光。哪些適合船艙,哪些適合山屋,哪些適合在機場席地等待,哪些又適合連續的紅眼飛行。這次去南極,將有好些日子在船上。哪些適合坐在陽台上看,哪些又適合床邊一盞燈的搖晃時光⋯⋯
翻找架上的書,打開我隨身的閱讀器,清點其中原先存下的書,什麼時候我就開始閱讀有關南極的札記?
只要與南極有關,對於我,始終是沉浸式的閱讀。滿布筆跡的航海圖,寫下心情的航海日誌:食物吃完,燈油燒盡,多年前我就常在擬想,極地的漫漫永夜怎麼過?
當年,南極的先行者,他們追尋什麼、相信什麼,又如何對抗不時湧上來的自我懷疑? 沒有無線電沒有通訊設備,當年的極地險境,如今恰當的比喻是搭上瞬間失去動力的太空船,「寂靜的宇宙裡,你的尖叫,無人知曉」。
雪原?冰架?生還機會渺茫,為什麼有人要去南極?莫非接近危險,才讓一件事在心裡無比崇高?
對這些人,靈魂或有一個部分,嚮往著行險的趣味吧。至於我,年輕時心態叛逆,寧可撞得粉碎,也不要落入無趣的人生套路。許多時候,讀探險家事蹟,像是獲得替代式的滿足,包括當年以失敗收場的事蹟,讓我自覺僥倖,正好像在家中聽聞遠方的災難,重重吁出口氣,心裡是荷馬的句子:「正因為我們在劫難逃,萬物才顯得更加美好。」
閱讀更讓我隨意聯想,讀過的科幻小說裡,南極有條地心通道,消失的東西都進入那扇任意門。接著,就永遠留在地心?如同波赫士的想像,他說,月球像保管箱,貯存了所有地球找不到的,包括情侶的眼淚、虛擲的時間等。至於南極,有人說,千萬年堅冰裡埋藏著失去的「亞特蘭提斯」,在我想像中,南極說不定⋯⋯正是失物招領的進口。
如果有個失物招領的櫃檯,我問自己,最想找到的是什麼?
啟程前夕,腦袋裡浮出問題,也閃現冰山變幻出的光影。
牽連到記憶裡的色彩,我曾在冰島的鑽石海灘看過、曾在阿拉斯加水岸看過。冰山從淺綠到褚紅,到難以形容的寶藍。冰山有一種清澈,一種深邃,瞇著眼,想像冰上的成群企鵝,還有信天翁展翅飛翔的姿勢⋯⋯
視力變得更差之前,如冬眠前的土撥鼠一樣,想要為自己埋藏下足夠的記憶。虛幻中的絕美,絕美中的虛幻,不是視覺暫留,而是視覺永存。我以為,那是與永恆接壤的可能。
去之前,我是這樣想的。
第三章 企鵝
航行整日。到耶誕前夕,在福克蘭群島的史坦利港(Port Stanley)下船。酣睡一夜,暈船症狀沒有惡化。我迫不及待要腳踏實地。
福克蘭群島上有兩處登陸點,第一日,停泊福克蘭東部的史坦利港,第二天,再停泊福克蘭西端的新港。兩處都是動物棲息地,我們將看到企鵝,最期待的包括福克蘭群島上的麥哲倫企鵝。
由船停泊的碼頭,巴士載我們去到吉普賽灣(Gypsy Cove)。途中,駕駛提到對台灣非常熟悉,因為台灣的遠洋漁業,漁船來這裡捕捉魷魚。
聽了很親切,當然也心生敬佩,我們的漁民遠涉重洋,漁場竟然延伸到南半球的福克蘭群島。
吉普賽灣有一段步道,彎曲如新月的白色沙灘上,見到成群的麥哲倫企鵝。
在南極期間,登陸的重點常是看企鵝。麥哲倫企鵝體型不大,眼圈黑白相間,身上有黑白環紋,取這個「麥哲倫」名字,因為是由航海家麥哲倫第一次發現。麥哲倫企鵝在草叢築巢,適合近距離觀察。
躲在芒草後面,我低下身子悄悄看,巢穴中躲藏著雛鳥,一團毛茸茸,其實我看不太清楚,努力想像雛鳥嬌弱的樣子。
麥哲倫企鵝曾是電影主角,與尚雷諾搭檔《我的企鵝朋友》。牠的黑眼珠特別吸睛,眼眸旁的環紋似乎蘊含著感情。片中描寫老漁夫跟企鵝的友誼,賺過許多人眼淚。
傍晚再啟航,航行兩百多海哩。第二天,到達福克蘭群島另一端的新島。
新島是跳岩企鵝的棲地。跳岩企鵝長得很威風,耳朵旁邊生著翎毛,看上去橫眉豎眼,一副挑釁的模樣。這種企鵝腳力強,在岩石間躍上躍下,會攀岩,又會跳水,牠們像企鵝中的暴走族,常由峭壁一頭扎進海裡。在新島,跳岩企鵝搖著翎毛四處跳動,讓我毫無來由的想起叔本華,那位不修邊幅的哲學家。
之後在不同的登陸地點,陸續看到另幾種企鵝,包括身材挺拔的國王企鵝,頸際、眼側、嘴邊,點綴著鵝黃或艷橘,非常亮麗。還有特徵分明的帽帶企鵝(又叫南極企鵝、紋頰企鵝),臉頰上有條細紋,像綁著頭盔,一眼可以辨識,牠們喜歡在岩礁間孵蛋與育幼。巴布亞企鵝(又叫紳士企鵝、白眉企鵝、金圖企鵝)則是速度高手,海裡的游泳冠軍,水中時速高達三十六公里。
在陸地,巴布亞企鵝也比其他種類的企鵝靈活。後來在白雪覆蓋的登陸地點,山坡上似乎有泥巴路,遠遠看像是奇觀。用望遠鏡對著望,原來牠們在疾走。
身體左搖右擺,走出一條企鵝公路。
船再航行數天,十二月三十號下午,到達南喬治亞島。地處偏遠的大島上,企鵝數量更令人震撼。山谷中黑白相間,這個島是幾十萬隻企鵝的聚居地。
近處一條水流,站著一堆堆未成年企鵝。國王企鵝體型大,未成年企鵝全身亂亂的棕色毛,活像竪直在河邊的奇異果。牠們尚未換上防水的黑色毛皮,還不可以下海覓食。有的奇異果距離成鳥近了,看起來急於轉大人,尷尬在於,大部分身體穿好了黑色皮衣,但稚氣藏不住,背後還留著一小撮未褪盡的
棕色雜毛。
等著防水毛皮覆滿身體,青少年企鵝排隊站在河畔,是在準備上游泳課?
幾隻成年企鵝在旁邊踱步,大概是負責守護牠們,順便告訴牠們海浪兇猛、未來覓食艱難。
成年企鵝則有胖有瘦,有的搖著一個大肚皮,明顯需要減肥。其實身材怎樣,都不怪企鵝貪吃,要看牠們前一日的覓食成果。天氣陰晴不定,海裡禍福難料,下一餐不知在哪裡,靠肚腹存下的磷蝦「度小月」。
自從來到南極的登陸點,我眼界大開,無論眼前出現哪一種企鵝,都讓我舉起手機。為什麼牠們如此吸睛?因為一身黑緞似的燕尾服?因為企鵝可以站起來走路?因為牠們煞有介事的模樣?企鵝確實像是一個個造型公仔,牠腿短,動作滑稽,踩不穩步子,搖搖擺擺在碎石路上,只要有坡度,冷不防牠就往前仆跌;地上有凹凸的石頭,更注定打滑。看到企鵝跌倒,我忍不住笑出聲。盯著看企鵝滑跤,我簡直幸災樂禍,原來造物主又有失手時刻,眼前出現比我更笨拙的生物,著實令人欣慰。
動畫片裡企鵝常是舒壓主角,到了南極開始明白原因。一個理由是,難得有一種動物,讓我們人類如此放鬆。企鵝走自己的路,根本無視人的存在,映在人類眸子裡,牠對我們全然視若無睹。企鵝對人類不存防備心,原因也是帶給企鵝威脅的天敵絕大多數生存在海中。
儘管《南極條約》寫明,訪客要與企鵝保持五公尺距離,總有躲閃不及的時刻。企鵝走路無聲無息,一沒留神,牠朝著人站立的地方過來了,接著,不免近距離接觸!人類擅會過度解讀,這隻企鵝是不是對自己有興趣?牠是不是特別富含好奇心?牠應該是故意靠過來,或者牠想研究一下,旁邊這腿長臂長的變形金剛是怎麼回事。
恰恰企鵝許多習性與人類似乎有共同點。其中,包括我們解釋為「美德」的行為。譬如企鵝堅守一夫一妻,看在人類眼睛裡簡直伉儷情深;又譬如,企鵝似乎認同性別平權,牠們輪流出外捕食,承擔孵化、育幼的工作,無分雌雄,皆甘願做負責任的親鳥。令人出現粉紅泡泡的是,年復一年,企鵝可以忍受寂寞、拒絕誘惑,經過海裡的冬天,牠矢志不移,回來岸上尋找之前的伴侶。又譬如,企鵝前戲很長而交配很短,看在人類眼中,顯然這樣的戀愛非常形而上,牠們寧可花時間在調情。其中阿德利企鵝,更堪稱動物界的情聖。為贏得芳心,拍翅跳舞、拉長喉嚨發出嗓音都是既定儀式,除此之外,阿德利企鵝以小石頭作為求愛信物,銜來本身嚴選的一粒小石頭,熱切的等待對方接受。一旦脫單成功,兩隻企鵝從此相伴到老。
企鵝對人類多所啟發,如果我任職廣告公司,一定推薦企鵝做鑽石大使。廣告詞也渾然天成:「每段姻緣都是從一顆美麗石頭開始。」連企鵝都知道送石頭示愛,那麼,人類以鑽石做定情禮絕對天經地義。
來到南極,是讓自己有機會打開心胸,之前,自己的知識體系過於狹窄,因而略過了太多重要資訊。經過一趟南極之旅,我搜尋頻道上的新知,關注企鵝的消息。過去許多年,我不只對企鵝無知,對整個動物界都了解有限,更以自己眼睛裡的好惡去界定牠們。
譬如,在南極這裡我偶爾忘形,還會插手干預。「啊,你走開!」「遠一點,不准過去!」怒目瞪視不夠,加上命令語氣,再加上揮手的驅趕姿勢。當時我看到草叢躲著一隻賊鷗,隨時可能撲過來,突襲小企鵝。比起超級萌的小企鵝,賊鷗灰灰醜醜,一看就是壞胚子。然而,此刻應該停下來問自己:我是誰?我在扮演上帝?扮演審判者?
記住這是大自然,大自然不濫情、不施恩!
看過的南極紀錄片中,有一幕我印象特別深刻,岬角岩石上,一隻企鵝昂然立著,牠肚子打開,望見血紅的內臟。才經歷海豹襲擊?勉強爬上岬角?牠站得那麼直,好似天地不仁的一幀剪影。牠挺立的當下,是在啟示人們生命的尊嚴?
顯然我想得太多,然而這份感性卻是有益的,對我這樣閉鎖的人,因為跟動物產生近身的感情,便有機會從感性出發,由關注南極生態,明白自己雖然渺小,亦是生態圈中一個環節。
船上安排許多課程,只要走進教室,就快速累積關於生態的知識。「銀海號」沒什麼娛樂項目。這一艘航向南極的交通工具,若符合對郵輪的刻板印象,提供歌星/歡唱/舞會/賭場等配備,這概念本身就令人不安。
生態課教室裡,我愈來愈清楚冰川正逐年退縮,冰量減少,企鵝失去育幼場所;氣候暖化的趨勢若無法翻轉,二一○○年,依賴海冰的皇帝企鵝將面臨「準滅絕」。
我繼續想著,海水溫度攀高,海冰下的冰藻急遽縮小面積,而冰藻是食物鏈中最基礎的一環。冰藻屬於磷蝦的食物,磷蝦則屬於企鵝與海豹、鯨魚的食物,海裡少了磷蝦,我想著小企鵝瘦伶伶的身體,可憐牠要餓扁了。我們人類的貪婪又雪上加霜,給海洋生物帶來另一個災難,為商業利益,人類正大量捕撈磷蝦,做成各種加工品,包括摻入寵物飼料,這分明是跟企鵝、海豹、鯨魚等爭食,搶奪牠們生存所繫的口糧。前瞻未來,企鵝不只失去食物,也失去棲地。海冰愈縮愈小,企鵝被迫過早泅泳海中,防水的毛皮沒有長成,就會導致群體死亡。
企鵝面對的威脅不只一端,南極高溫更帶來許多傳染病,動物群聚的地方最容易交叉感染。譬如說,南極本來也是黃眼企鵝的活動範圍,因為環境變遷,黃眼企鵝從南極消失。
船靠近南喬治島的一處登陸點,我更親身感受到禽流感帶來的死亡。前哨小船上岸探測後,立刻改變計畫,決定啟航,避免乘客目睹太多動物屍體。下一處登陸點,據說災情稍輕,乘客被允許上岸。列隊跳下橡皮艇後,探險隊員催大家戴起口罩,儘可能快步走。我低著頭,遮住臉也照樣瞥見,橫屍在海灘上的是一堆堆海豹與企鵝。
站在冰原上,雨靴愈來愈重,頭上開始滲出汗珠。繼續向前走,探險隊員指著遠近幾處冰川,告訴我們冰川舌原來到這裡,現在縮至那裡。我想著十年後,說不定穿單衣就可以來到南極。到那時候,山谷內沒長大的娃娃企鵝,怎麼活下去?
氣溫攀升,冰架將陸續解體,海面淹上來,城市下沉到水裡。浩劫近了,人類豈能獨存?此刻往未來看,不只企鵝,地球所有生物都在「準滅絕」前夕。
為什麼去南極?
為什麼是南極,我第一本旅行做主題的成書?
之前,我沒有寫過遊記。對於我,旅行純粹為了樂趣,總帶著漫無目標的情調。
心中甚至有一種疑惑,不寫,為了不要毀掉純屬於個人的趣味。同樣的恐懼,一直是種恐懼,彷彿某種悖論。我寫什麼,什麼就消失不見。我寫童年,愈去追想,我真正的童年會不會消失不見?我寫父親,父親的形影在我眼前愈來愈淡薄,會不會看不見他了?
一旦選定主題,按下快門,就此遺失了不在相片內的一切。
不寫遊記,曾是同樣的理由吧。這一回,卻是一本不像遊記的遊記。
人在南極,詭奇的景色中,串起我大半生剪影。
那是鏡子的魔法,鏡面裡還有鏡面。自從接近南極洲,許多時刻,像一隻飛鳥,我分明是在記憶裡滑翔。往昔時光,在鏡中清楚又模糊,「南極」反過來成了「極南」。一幀幀攝影負片,照出我的顛倒夢想。
冰山如鏡,純白的稜線更像是內心通道,多重折射中,映現出我的嚮往、我的探索、我的迷惘、我的漂泊、我的挫敗,直達自己赤裸的靈魂。偶爾冰山滾落一角,掉進南冰洋裡,咚咚沉下去,我逐漸明白,這些年為什麼自己聽到的⋯⋯總是不一樣的鼓聲?
卡繆的話:「要了解這個世界,有時必須離開它。」旅程是解鎖,為了明瞭此生所為何來。
1 出發前
出發在即,冬至前一天,台北大寒。
早幾個小時,我忙著整理此行要帶的書。
在南極,哪裡能夠沒有書?我出神的想著,譬如第一個抵達南極點的阿蒙森,除了巧克力與肉餅,還帶著三千本書。
書架上一本本瀏覽,打開一本再放回去,原本屬於我的快樂時光。哪些適合船艙,哪些適合山屋,哪些適合在機場席地等待,哪些又適合連續的紅眼飛行。這次去南極,將有好些日子在船上。哪些適合坐在陽台上看,哪些又適合床邊一盞燈的搖晃時光⋯⋯
翻找架上的書,打開我隨身的閱讀器,清點其中原先存下的書,什麼時候我就開始閱讀有關南極的札記?
只要與南極有關,對於我,始終是沉浸式的閱讀。滿布筆跡的航海圖,寫下心情的航海日誌:食物吃完,燈油燒盡,多年前我就常在擬想,極地的漫漫永夜怎麼過?
當年,南極的先行者,他們追尋什麼、相信什麼,又如何對抗不時湧上來的自我懷疑? 沒有無線電沒有通訊設備,當年的極地險境,如今恰當的比喻是搭上瞬間失去動力的太空船,「寂靜的宇宙裡,你的尖叫,無人知曉」。
雪原?冰架?生還機會渺茫,為什麼有人要去南極?莫非接近危險,才讓一件事在心裡無比崇高?
對這些人,靈魂或有一個部分,嚮往著行險的趣味吧。至於我,年輕時心態叛逆,寧可撞得粉碎,也不要落入無趣的人生套路。許多時候,讀探險家事蹟,像是獲得替代式的滿足,包括當年以失敗收場的事蹟,讓我自覺僥倖,正好像在家中聽聞遠方的災難,重重吁出口氣,心裡是荷馬的句子:「正因為我們在劫難逃,萬物才顯得更加美好。」
閱讀更讓我隨意聯想,讀過的科幻小說裡,南極有條地心通道,消失的東西都進入那扇任意門。接著,就永遠留在地心?如同波赫士的想像,他說,月球像保管箱,貯存了所有地球找不到的,包括情侶的眼淚、虛擲的時間等。至於南極,有人說,千萬年堅冰裡埋藏著失去的「亞特蘭提斯」,在我想像中,南極說不定⋯⋯正是失物招領的進口。
如果有個失物招領的櫃檯,我問自己,最想找到的是什麼?
啟程前夕,腦袋裡浮出問題,也閃現冰山變幻出的光影。
牽連到記憶裡的色彩,我曾在冰島的鑽石海灘看過、曾在阿拉斯加水岸看過。冰山從淺綠到褚紅,到難以形容的寶藍。冰山有一種清澈,一種深邃,瞇著眼,想像冰上的成群企鵝,還有信天翁展翅飛翔的姿勢⋯⋯
視力變得更差之前,如冬眠前的土撥鼠一樣,想要為自己埋藏下足夠的記憶。虛幻中的絕美,絕美中的虛幻,不是視覺暫留,而是視覺永存。我以為,那是與永恆接壤的可能。
去之前,我是這樣想的。
第三章 企鵝
航行整日。到耶誕前夕,在福克蘭群島的史坦利港(Port Stanley)下船。酣睡一夜,暈船症狀沒有惡化。我迫不及待要腳踏實地。
福克蘭群島上有兩處登陸點,第一日,停泊福克蘭東部的史坦利港,第二天,再停泊福克蘭西端的新港。兩處都是動物棲息地,我們將看到企鵝,最期待的包括福克蘭群島上的麥哲倫企鵝。
由船停泊的碼頭,巴士載我們去到吉普賽灣(Gypsy Cove)。途中,駕駛提到對台灣非常熟悉,因為台灣的遠洋漁業,漁船來這裡捕捉魷魚。
聽了很親切,當然也心生敬佩,我們的漁民遠涉重洋,漁場竟然延伸到南半球的福克蘭群島。
吉普賽灣有一段步道,彎曲如新月的白色沙灘上,見到成群的麥哲倫企鵝。
在南極期間,登陸的重點常是看企鵝。麥哲倫企鵝體型不大,眼圈黑白相間,身上有黑白環紋,取這個「麥哲倫」名字,因為是由航海家麥哲倫第一次發現。麥哲倫企鵝在草叢築巢,適合近距離觀察。
躲在芒草後面,我低下身子悄悄看,巢穴中躲藏著雛鳥,一團毛茸茸,其實我看不太清楚,努力想像雛鳥嬌弱的樣子。
麥哲倫企鵝曾是電影主角,與尚雷諾搭檔《我的企鵝朋友》。牠的黑眼珠特別吸睛,眼眸旁的環紋似乎蘊含著感情。片中描寫老漁夫跟企鵝的友誼,賺過許多人眼淚。
傍晚再啟航,航行兩百多海哩。第二天,到達福克蘭群島另一端的新島。
新島是跳岩企鵝的棲地。跳岩企鵝長得很威風,耳朵旁邊生著翎毛,看上去橫眉豎眼,一副挑釁的模樣。這種企鵝腳力強,在岩石間躍上躍下,會攀岩,又會跳水,牠們像企鵝中的暴走族,常由峭壁一頭扎進海裡。在新島,跳岩企鵝搖著翎毛四處跳動,讓我毫無來由的想起叔本華,那位不修邊幅的哲學家。
之後在不同的登陸地點,陸續看到另幾種企鵝,包括身材挺拔的國王企鵝,頸際、眼側、嘴邊,點綴著鵝黃或艷橘,非常亮麗。還有特徵分明的帽帶企鵝(又叫南極企鵝、紋頰企鵝),臉頰上有條細紋,像綁著頭盔,一眼可以辨識,牠們喜歡在岩礁間孵蛋與育幼。巴布亞企鵝(又叫紳士企鵝、白眉企鵝、金圖企鵝)則是速度高手,海裡的游泳冠軍,水中時速高達三十六公里。
在陸地,巴布亞企鵝也比其他種類的企鵝靈活。後來在白雪覆蓋的登陸地點,山坡上似乎有泥巴路,遠遠看像是奇觀。用望遠鏡對著望,原來牠們在疾走。
身體左搖右擺,走出一條企鵝公路。
船再航行數天,十二月三十號下午,到達南喬治亞島。地處偏遠的大島上,企鵝數量更令人震撼。山谷中黑白相間,這個島是幾十萬隻企鵝的聚居地。
近處一條水流,站著一堆堆未成年企鵝。國王企鵝體型大,未成年企鵝全身亂亂的棕色毛,活像竪直在河邊的奇異果。牠們尚未換上防水的黑色毛皮,還不可以下海覓食。有的奇異果距離成鳥近了,看起來急於轉大人,尷尬在於,大部分身體穿好了黑色皮衣,但稚氣藏不住,背後還留著一小撮未褪盡的
棕色雜毛。
等著防水毛皮覆滿身體,青少年企鵝排隊站在河畔,是在準備上游泳課?
幾隻成年企鵝在旁邊踱步,大概是負責守護牠們,順便告訴牠們海浪兇猛、未來覓食艱難。
成年企鵝則有胖有瘦,有的搖著一個大肚皮,明顯需要減肥。其實身材怎樣,都不怪企鵝貪吃,要看牠們前一日的覓食成果。天氣陰晴不定,海裡禍福難料,下一餐不知在哪裡,靠肚腹存下的磷蝦「度小月」。
自從來到南極的登陸點,我眼界大開,無論眼前出現哪一種企鵝,都讓我舉起手機。為什麼牠們如此吸睛?因為一身黑緞似的燕尾服?因為企鵝可以站起來走路?因為牠們煞有介事的模樣?企鵝確實像是一個個造型公仔,牠腿短,動作滑稽,踩不穩步子,搖搖擺擺在碎石路上,只要有坡度,冷不防牠就往前仆跌;地上有凹凸的石頭,更注定打滑。看到企鵝跌倒,我忍不住笑出聲。盯著看企鵝滑跤,我簡直幸災樂禍,原來造物主又有失手時刻,眼前出現比我更笨拙的生物,著實令人欣慰。
動畫片裡企鵝常是舒壓主角,到了南極開始明白原因。一個理由是,難得有一種動物,讓我們人類如此放鬆。企鵝走自己的路,根本無視人的存在,映在人類眸子裡,牠對我們全然視若無睹。企鵝對人類不存防備心,原因也是帶給企鵝威脅的天敵絕大多數生存在海中。
儘管《南極條約》寫明,訪客要與企鵝保持五公尺距離,總有躲閃不及的時刻。企鵝走路無聲無息,一沒留神,牠朝著人站立的地方過來了,接著,不免近距離接觸!人類擅會過度解讀,這隻企鵝是不是對自己有興趣?牠是不是特別富含好奇心?牠應該是故意靠過來,或者牠想研究一下,旁邊這腿長臂長的變形金剛是怎麼回事。
恰恰企鵝許多習性與人類似乎有共同點。其中,包括我們解釋為「美德」的行為。譬如企鵝堅守一夫一妻,看在人類眼睛裡簡直伉儷情深;又譬如,企鵝似乎認同性別平權,牠們輪流出外捕食,承擔孵化、育幼的工作,無分雌雄,皆甘願做負責任的親鳥。令人出現粉紅泡泡的是,年復一年,企鵝可以忍受寂寞、拒絕誘惑,經過海裡的冬天,牠矢志不移,回來岸上尋找之前的伴侶。又譬如,企鵝前戲很長而交配很短,看在人類眼中,顯然這樣的戀愛非常形而上,牠們寧可花時間在調情。其中阿德利企鵝,更堪稱動物界的情聖。為贏得芳心,拍翅跳舞、拉長喉嚨發出嗓音都是既定儀式,除此之外,阿德利企鵝以小石頭作為求愛信物,銜來本身嚴選的一粒小石頭,熱切的等待對方接受。一旦脫單成功,兩隻企鵝從此相伴到老。
企鵝對人類多所啟發,如果我任職廣告公司,一定推薦企鵝做鑽石大使。廣告詞也渾然天成:「每段姻緣都是從一顆美麗石頭開始。」連企鵝都知道送石頭示愛,那麼,人類以鑽石做定情禮絕對天經地義。
來到南極,是讓自己有機會打開心胸,之前,自己的知識體系過於狹窄,因而略過了太多重要資訊。經過一趟南極之旅,我搜尋頻道上的新知,關注企鵝的消息。過去許多年,我不只對企鵝無知,對整個動物界都了解有限,更以自己眼睛裡的好惡去界定牠們。
譬如,在南極這裡我偶爾忘形,還會插手干預。「啊,你走開!」「遠一點,不准過去!」怒目瞪視不夠,加上命令語氣,再加上揮手的驅趕姿勢。當時我看到草叢躲著一隻賊鷗,隨時可能撲過來,突襲小企鵝。比起超級萌的小企鵝,賊鷗灰灰醜醜,一看就是壞胚子。然而,此刻應該停下來問自己:我是誰?我在扮演上帝?扮演審判者?
記住這是大自然,大自然不濫情、不施恩!
看過的南極紀錄片中,有一幕我印象特別深刻,岬角岩石上,一隻企鵝昂然立著,牠肚子打開,望見血紅的內臟。才經歷海豹襲擊?勉強爬上岬角?牠站得那麼直,好似天地不仁的一幀剪影。牠挺立的當下,是在啟示人們生命的尊嚴?
顯然我想得太多,然而這份感性卻是有益的,對我這樣閉鎖的人,因為跟動物產生近身的感情,便有機會從感性出發,由關注南極生態,明白自己雖然渺小,亦是生態圈中一個環節。
船上安排許多課程,只要走進教室,就快速累積關於生態的知識。「銀海號」沒什麼娛樂項目。這一艘航向南極的交通工具,若符合對郵輪的刻板印象,提供歌星/歡唱/舞會/賭場等配備,這概念本身就令人不安。
生態課教室裡,我愈來愈清楚冰川正逐年退縮,冰量減少,企鵝失去育幼場所;氣候暖化的趨勢若無法翻轉,二一○○年,依賴海冰的皇帝企鵝將面臨「準滅絕」。
我繼續想著,海水溫度攀高,海冰下的冰藻急遽縮小面積,而冰藻是食物鏈中最基礎的一環。冰藻屬於磷蝦的食物,磷蝦則屬於企鵝與海豹、鯨魚的食物,海裡少了磷蝦,我想著小企鵝瘦伶伶的身體,可憐牠要餓扁了。我們人類的貪婪又雪上加霜,給海洋生物帶來另一個災難,為商業利益,人類正大量捕撈磷蝦,做成各種加工品,包括摻入寵物飼料,這分明是跟企鵝、海豹、鯨魚等爭食,搶奪牠們生存所繫的口糧。前瞻未來,企鵝不只失去食物,也失去棲地。海冰愈縮愈小,企鵝被迫過早泅泳海中,防水的毛皮沒有長成,就會導致群體死亡。
企鵝面對的威脅不只一端,南極高溫更帶來許多傳染病,動物群聚的地方最容易交叉感染。譬如說,南極本來也是黃眼企鵝的活動範圍,因為環境變遷,黃眼企鵝從南極消失。
船靠近南喬治島的一處登陸點,我更親身感受到禽流感帶來的死亡。前哨小船上岸探測後,立刻改變計畫,決定啟航,避免乘客目睹太多動物屍體。下一處登陸點,據說災情稍輕,乘客被允許上岸。列隊跳下橡皮艇後,探險隊員催大家戴起口罩,儘可能快步走。我低著頭,遮住臉也照樣瞥見,橫屍在海灘上的是一堆堆海豹與企鵝。
站在冰原上,雨靴愈來愈重,頭上開始滲出汗珠。繼續向前走,探險隊員指著遠近幾處冰川,告訴我們冰川舌原來到這裡,現在縮至那裡。我想著十年後,說不定穿單衣就可以來到南極。到那時候,山谷內沒長大的娃娃企鵝,怎麼活下去?
氣溫攀升,冰架將陸續解體,海面淹上來,城市下沉到水裡。浩劫近了,人類豈能獨存?此刻往未來看,不只企鵝,地球所有生物都在「準滅絕」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