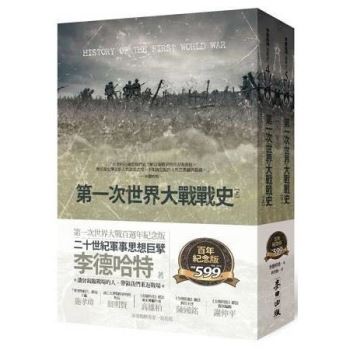第一篇 戰爭緣起
讓歐洲步向爆炸,過程花費了五十年。引爆它,卻僅需五天時間。我們所要研究的這套爆炸材料的製造,也即形成衝突的基本原因,其實在這段短暫的一次大戰史範圍中是找不到的。事實上,一方面,我們應當回顧普魯士對於開創德意志帝國(Reich)的影響,俾斯麥的政治構想,德國思想深刻的個性傾向,以及當時的經濟狀況——德國曾企圖以商業出口為主,不過目的並未達成。此外,加上一些其他理由,使德國自原本的商業大國理念,改變為世界強權觀。我們並應分析蘊含各色各樣中世紀遺風的奧匈帝國,認識其複雜的種族問題,做作的統治機制,暗藏在膚淺野心底下,令其煩擾不堪的內部崩解的恐懼,以及其狂亂尋求苟延殘喘的行徑。
另一方面,我們應檢視那令人稱奇的,支配俄羅斯政策的野心與理想主義混合物。它致使靠近俄羅斯邊界的,特別在日耳曼鄰邦間,瀰漫一片恐怖感。這也可能是最終引爆戰爭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種。我們並應了解自一八七○年以來,法國因遭受侵略而對新侵略所發出的持續警號;我們更應研究法國重建的自信心。它強化了法國抵禦進一步外侮的力量。還有,我們應牢記德國攫奪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對法國所造成的傷害。最後,我們應回顧英國從孤立政策轉變為參與歐洲,成為歐洲系統成員的作法,以及當它面對德國的敏感現實時,所展現的緩慢覺醒。
在對半世紀歐洲歷史做出上述的研究之後,我們所獲得的整體認知,應比絕大部分記載鉅細靡遺的歷史更詳實。這場戰爭發生的基本原因可歸納為三點:恐懼、飢餓與傲慢。除此之外,發生在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的國際事件,也是徵候。
總之,要找出點燃這次戰火蛛絲馬跡當中最重要的轉捩點,是有可能,而且容易看到的。這些蛛絲馬跡事實上穿越了一八七一年之後,俾斯麥所建立的同盟結構中。諷刺的是,俾斯麥原本並非將這同盟結構當作火藥庫,而是將它視為保護傘,以使他所開創的德意志帝國能和平成長。雖然俾斯麥的想法,早濃縮在他一八六八年的一句話——「弱國終被強國吞噬」之中,他自己的胃口,卻在一八七○至七一年戰爭(譯註:即普法戰爭)的三頓飽餐之後,感到滿足。所以,我們不能譴責他,認為他的野心比胃口大;就像他所說,他感覺德國現今是一個「心滿意足」的國家。他的統治理念自此之後並非擴張,而是團結。為了爭取足夠的時間與和平,使新德國保持穩定,他企圖抑制法國國力的發展,使法國維持在無法進行復仇之戰的局面。但是結果證明這些作法對德意志帝國並無好處。
俾斯麥並未對法國實施經常不斷的直接脅迫。他只準備切斷法國與友邦或支持者之間的關係,以便間接打擊令人困擾的法國快速復甦。俾斯麥首先拉攏奧地利與俄羅斯,使他們和德國結為普通的結盟關係;同時努力促成巴爾幹半島的和平,以防後者對結盟關係造成任何危機。有好幾年時間,他的政策是,在歐洲外交利益交換上,不對任何一方做出承諾,僅做一名「忠實的經紀人」。然而,他與俄羅斯首相戈恰可夫(Gortchakov)之間的不和,以及由於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Russo-Turkish War)的紛擾,使他不顧年老的德皇威廉一世的反對,與奧地利在一八七九年訂定了防衛聯盟。德皇原本將這種作法視為「出賣」俄羅斯,甚至曾威脅說自己要退位。不過這紙明確的承諾,後來並無明確的結果。儘管如此,俾斯麥在一八八一年以巧妙的外交手段,經由俄、奧、德三國所簽訂的「三帝同盟」(Three Emperors Alliance),暫時取回主導地位。這著名的「三帝同盟」,原先目的在於干預所有巴爾幹半島事務。雖然該同盟稍後在一八八七年廢止,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則另以祕密訂定的二雙重保障條約」(Reinsurance Treaty)作為補償,並獲加強。經由該約,兩強同意除非德國攻擊法國,或俄國攻擊奧地利的情形發生,雙方各自與第三國交戰時,彼此將維持善意的中立。在這兩次巧妙的,具有驚人欺瞞效果的外交手法下,俾斯麥避免了當時迫在眉睫的俄法聯盟。
同時,德奧之間的結盟,由於一八八二年義大利的參與而擴大。其結盟目的是,如果德國與俄國作戰,提防俄國從背後暗算奧地利;義大利如遭法國攻擊,德奧將出兵相助。不過義大利為保護與英國老友的關係,及其本身海岸線的安全,卻在條約上附加一段特別協議,闡明絕不直接與英國衝突。一八八三年,羅馬尼亞(Rumania)經由該國國王個人與一些祕密運作過程,也加入了這新的「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後來甚至連塞爾維亞(Serbia)與西班牙也分別短暫與奧地利及義大利,以另締條約的方式結盟。
對於英國,俾斯麥的目標似乎企圖使英國僅與德國保持友好,而與法國保持不友好的關係。他對英國的感覺,在友好與輕蔑之間搖晃不定。其態度轉變的關鍵點,在於英國不同政黨的輪替執政。對於「老猶太」狄斯累利(Disraeli),他由衷敬重;但他無法了解格萊斯東自由黨(Gladstonian Liberals)的觀點,同時他也瞧不起自由黨政策搖擺不定的行徑。當狄斯累利當權時,俾斯麥大談拉攏英國為其同盟的想法;雖然維多利亞女王曾低調表示,「確信德國在任何一方面都將是最安全的盟友」,她卻不敢肯定俾斯麥是否能託以信任,狄斯累利的看法亦同。因此俾斯麥繼續玩弄藉由英俄、英法之間不和,使自己漁翁得利的政策。幾經精心的評估,他贊成英國占領埃及,因為英國占領埃及會使英法不和。在另一方面,由於德國的極端殖民主義,在未來具有與英國發生衝突之虞,所以他反對國內漸起的殖民擴張聲浪。他曾說:「我們極端殖民主義者的貪婪,大過我們所需要的,或能滿足的。」他以支持英國占領埃及,企圖逐漸換取英國在海外的小讓步。經由這些小讓步,他緩和了德國利益團體強大的,連他都無法忽視的殖民要求。然而英國保守黨的重新執政,以及英法之間與日俱增的摩擦,使英德建立起新的緊密關係。俾斯麥提出的正式結盟,受到沙里斯布雷爵士內閣(Lord Salisbury’s Cabinet)的熱烈歡迎;不過後者似乎因擔心國會反對與外國牽扯而退縮。然而,俾斯麥從這非正式的協議中,以微不足道的代價取得了英國對海利哥蘭島(Heligoland)的割讓。海利哥蘭島在後一世代,對德國海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於是到了一八八○年代末,俾斯麥偉大的政治架構似乎已沛然成形。德國受到「三國同盟」的支撐;而英俄若即若離的態勢,對它只有利而無弊。在這樣穩定的基礎上,德國為商業擴張做好了準備。而且俾斯麥已將法國驅入一個孤獨而侷限的政治隔離圈內。
但自一八九○年代初開始,俾斯麥規畫的政治架構出現了一道裂痕;後繼者幾乎到要趕走這架構起造者的地步。年輕的德皇威廉二世於一八八八年即位。他與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素不友好;後者既不喜歡德皇的「侵略性友善」,也懷疑他的意圖。然而對俾斯麥的政治架構來說,問題並非來自沙皇,而是威廉二世。俾斯麥的掌權方式,向為德國參謀本部與軍隊所詬病,如今也令威廉二世厭惡不已。由於威廉二世幾乎在參謀本部與軍隊中成長,所以他很自然發現這些人與他站在一邊。但他未覺察,這種關係也束縛了自己。
第一個效應是,趕走「親俄」的首相之後,繼任者拒絕與俄續訂「雙重保障條約」。第二效應則是第一效應的必然結果。沙皇忍下對共和主義的嫌憎,於一八九一年與法國訂定了協議。這協議並於一年之後發展成軍事協定。雙方希望在遭敵攻擊時,彼此相助。這協定中的重大要點是,倘若「三國同盟」中任何一方進行動員,法俄將立即動員。由於法方談判人波斯德福將軍(General Boisdeffre)曾費心向沙皇解釋,「動員意味宣戰」,所以沙皇至少無法說他不懂這其中的意涵。
沙皇在害怕英德即將結盟之餘,喝下了這劑俄法結盟湯藥,後來卻一直苦惱著沙皇。因此在簽約後,長期未對法國產生任何外交價值。
儘管如此,法國跳出了政治「隔離圈」。從現在起,歐洲並非僅止於一個政治集團,而是兩個政治集團。雖然其中一個關係較寬鬆,另一個卻較緊密。這兩個集團形成了均勢,即使各方勢力尚未全然均衡。
對於德國廢止德俄祕密條約,尚有要點值得一提。柏林的議會在早先覆審這項條約內容時,曾反對訂約。理由是該條約不但對奧國不忠,而且對英國不誠。其實,不論德皇的缺點如何,他的性格比俾斯麥更真誠;他在矛盾發言中所顯現的偽善外表,似乎是因為過度坦率與經常快速轉變心意。他們兩人基本相異之處在於,一個是以始終如一的欺騙,來尋求國家安全;另一個則是在突發式的真誠態度下行事,得到的僅是不安穩的保障。英國方面對此的看法與德皇一致。雖然德皇對待俄羅斯的態度與俾斯麥迥異,他卻維持俾斯麥對英的友好態度,這也許是因為他的性格中多了一份真誠,較少政治動機之故。但英德兩國間卻有一件緣起於私人因素的不睦。原來德皇與他的舅父威爾斯親王(譯註:威廉二世的母親是英女王維多利亞的長女),也就是後來的英王愛德華七世彼此相惡。妙的是,這私人裂痕是被俾斯麥家族弄得愈來愈糟的。
不過這私人之間的不和,如果沒有更大的問題介入其中,是不會釀成國際友誼的裂痕。事實上,英德不睦來自於一個主因,以及附加的許多小因素。這一切都需自德國的政策從重視內部轉變為向外擴展說起。當德國的商業與影響力,擴增到世界級的規模時,其利益無可避免與英國在多方面發生接觸。但經俾斯麥式老奸巨猾手段處理之後,這類接觸不會造成一觸即發的摩擦,因為英國的政治手腕原本就相當不敏銳。而這時期英國最關心帝國疆土的政黨,碰巧就是最同情德意志帝國的政黨。然而,現在俾斯麥已走,卻無圓通練達者取代其位。有一種情形時常發生在像俾斯麥這類偉人身上:他的門徒忘記主子的行事原則,卻只記得他的方法——武嚇。不過,德皇此時自己已可運用魅力達到目的了。儘管他屢犯眾怒,他不僅成功地維持了在英國的名望,而且在俄羅斯新即位的,軟弱而友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曾經有一度,他還無條件擁有對沙皇的影響力。
德英之間第一次較大的摩擦是為了土耳其。此事件的陰影影響了未來。一八九二年,當時英國自由黨重新執政;就像格雷(Sir Edward Grey,譯註: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任英國外交大臣)所說,「突然間,從柏林送來一封像最後通牒的文件,要求我們為土耳其的鐵路,終止與德國人競爭。」並且在此後數年,德皇從未忘記強調,在德國所擴展的商業網中,「坐鎮著一隻牙齒鋒利的蜘蛛」。一八九五年,由於他的干預,使俄國自日本手中奪得了與中國作戰所攫取的戰利品。一八九六年,他再次與英國發生衝突。這回就比較嚴重了。諷刺的是,起因是由於某英國人士對俾斯麥式霸業的狂熱欽佩。這位名叫羅德茲(Cecil John Rhodes)的英國人,不但對俾斯麥式的霸業推崇不已,而且對威廉二世也曾做出相等的讚譽。但德皇卻不領情,並對羅德茲所擬訂的英國南非擴張計畫深感忿怒,甚至像是自己受挫似的。經過幾回酸溜溜對英國的批評,以及南非外伐爾的波爾人(Transvaal Boers)的甜蜜慫恿,對於詹姆森(Sir Leander Starr Jameson,譯註:英裔南非政治家)率兵入侵外伐爾共和國之舉,發現了一個誘人的藉口。一八九六年一月三日,德皇在議會中提出構想,他認為德國應聲明為外伐爾共和國的保護國,然後派兵前往該地。首相何亨羅(Hohenlohe)聞言,則以「這等於與英國宣戰」為由,反對此種作法。德皇卻直率答道:「是的,但這只是在陸地上作戰。」不過,有人提出稍微緩和的辦法。建議他不如拍發賀電給南非外伐爾共和國總統克魯格(Kruger)。但電文言詞間不但高度冒犯英國,而且否認英國對外伐爾共和國的宗主權(譯註:此賀電事件史稱「克魯格電報事件」,指德國電賀克魯格擊退英國殖民者詹姆森來犯的軍隊。惟英國否認參與該事件)。
這下,由於一方有著壓抑不住的妒嫉,一方則驚見傳統老友驟變為新敵,於是兩國人心都鼎沸了起來。德國人自認惱恨有理。他們認為,已占據許多殖民地的英國,如今又要開疆闢土。但這塊新殖民地,正是另一位遲來者想要的。然而英國人拓展殖民地已習慣成性,他們竟平靜地以為這樣做才符合英國約翰牛形象。他們無法理解,除了傳統的對手俄國與法國外,居然還有人對此事感到如此掛念。所以在一般的交往上,不論德國做出如何的不自覺挑釁,英國始終保持冷靜的自信。這種態度也成為這次危機的一帖鎮靜劑,而且幾乎是成功的。原來德國曾下令採取戰爭手段,建議法俄聯合攻擊英國。但後來,一者由於法俄缺乏興趣,一者英國沙里斯布雷政府的冷靜,使德國自覺海軍不夠強大而自我克制,一觸即發的危機因而消失。
然而,危機因欠缺實力而避開,並不表示危機已解除。德國海軍的野心,即在此時開始萌發。這股野心明顯浮現在一八九七年威廉二世的一段話上,「三叉戟應握在我們手中」,以及他對鐵必制將軍(Admiral Tirpitz)所下達的命令。他要求建造這支三叉戟。翌年,德國海軍的擴建計畫開始進行。並且,據說在德皇訪問大馬士革期間,曾宣布他是全世界伊斯蘭教徒的保護者。這簡直是對英法的直接挑釁。不僅如此,由於他明白聲稱要擔任土耳其的守護神,也造成與俄國的嚴重不和,因為他阻礙了俄國覬覦君士坦丁堡的美夢。就像被拿破崙嘲弄的對手一樣,德皇因「眼中有太多事務」而將其外交章法打亂。致使這些曾被俾斯麥耍弄過而相互攻擊的列強,現在在任何地方只見到一件事——德國的拳頭,而未見其他。儘管如此,一八九八年,英國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譯註:一八九五年任英國殖民大臣。是二次大戰前夕英國首相尼微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之父)為英國介入南非紛爭之事,向德國提出俾斯麥曾尋求過的結盟建議,卻遭德國的侮慢。原來張伯倫的提議,現在輪到德國存疑了。事實上英國做出這樣提議,是因為英國有了新的顧慮。英國正考量本身所受的孤立與弱點,儘管在觀點上基於一種舊意識——與德國有其天生的密切關係。但這提議現在看來,卻像是自己在招認弱點。至少部分是如此。而以弱點為由的提議,對於新德國並非上策。俾斯麥遺留給繼任者的幾種遺風之一,就是低估英國實力,高估俄國的實力。
德國自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年之間,幾度拒絕張伯倫的建議,主要竟與個人因素有關,也就是與隱身在後的霍斯坦(Friedrich von Holstein)有關。霍斯坦是一位性格晦澀,狐疑,貪婪的外交部官員;喜深藏不露,作沒沒無聞狀。因為他以為唯有如此,方能增強其在追求「真正政策」方面的實權。霍斯坦雖然堂而皇之利用官方知識,祕密進行相當冒風險的事情,卻也不願替自己縫製一套掩遮外表的新衣。雖然他表態說是俾斯麥的門徒,卻曾密謀讓他師父下台。現在則以俾斯麥精神繼承者的姿態,令人肅然起敬,雖然他所傳承的,只是師父的一些旁門左道。最重要的是,他欠缺俾斯麥的膽識。
結果,儘管他願意接受英國的建議,卻害怕變成英國的爪牙,成為英俄衝突的避震器。在另一方面他認為,若現在將英國置於若即若離的範圍,英國的弱點正好可加利用,並可逼迫其讓步;而在此同時,仍需讓英國心存與德國保有較密切關係的期望。這樣的觀點,他至少獲得首相比羅(Bernhard von Bülow)的支持。德皇更將他的觀點,籠統敘述在給比羅的信上。他寫道:「儘管他們想扭身掙脫,我現在已經抓住了英國。」然後,德國在一九○○年再次擴建海軍,成為扭緊英國的工具。
此後數年,特別在南非危機與戰爭期間,英國政府為德國的態度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段時期,英國並不期待德國為南非戰爭伸出援手,只求德國不將威脅與侮蔑付諸行動。於是,無論在葡屬殖民地,在薩摩亞,在中國,英國沙里斯布雷政府所表現的軟弱,幾乎印證了德皇所說的,「十足的笨蛋」。這幾年間的外交檔案所揭露的,也都是讀來令人可鄙的文件。從外交檔案,可追出沙里斯布雷政府對於後來的衝突,應負間接責任。因為很自然的,德皇與他顧問的思維,必然可從他們的武嚇法(mailed-fist method)想法證實。不過,德皇可以不負將武嚇推及真正戰爭之責。這不只是因為他曾有不喜歡武嚇的證據、而是他有從膚淺外表斷事的傾向。他推斷,對英國有限的威脅,很明顯在未經風險下,即可為德國帶來戰爭利益。這種過於淺顯的推論,是與他個性契合的。
讓歐洲步向爆炸,過程花費了五十年。引爆它,卻僅需五天時間。我們所要研究的這套爆炸材料的製造,也即形成衝突的基本原因,其實在這段短暫的一次大戰史範圍中是找不到的。事實上,一方面,我們應當回顧普魯士對於開創德意志帝國(Reich)的影響,俾斯麥的政治構想,德國思想深刻的個性傾向,以及當時的經濟狀況——德國曾企圖以商業出口為主,不過目的並未達成。此外,加上一些其他理由,使德國自原本的商業大國理念,改變為世界強權觀。我們並應分析蘊含各色各樣中世紀遺風的奧匈帝國,認識其複雜的種族問題,做作的統治機制,暗藏在膚淺野心底下,令其煩擾不堪的內部崩解的恐懼,以及其狂亂尋求苟延殘喘的行徑。
另一方面,我們應檢視那令人稱奇的,支配俄羅斯政策的野心與理想主義混合物。它致使靠近俄羅斯邊界的,特別在日耳曼鄰邦間,瀰漫一片恐怖感。這也可能是最終引爆戰爭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種。我們並應了解自一八七○年以來,法國因遭受侵略而對新侵略所發出的持續警號;我們更應研究法國重建的自信心。它強化了法國抵禦進一步外侮的力量。還有,我們應牢記德國攫奪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對法國所造成的傷害。最後,我們應回顧英國從孤立政策轉變為參與歐洲,成為歐洲系統成員的作法,以及當它面對德國的敏感現實時,所展現的緩慢覺醒。
在對半世紀歐洲歷史做出上述的研究之後,我們所獲得的整體認知,應比絕大部分記載鉅細靡遺的歷史更詳實。這場戰爭發生的基本原因可歸納為三點:恐懼、飢餓與傲慢。除此之外,發生在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的國際事件,也是徵候。
總之,要找出點燃這次戰火蛛絲馬跡當中最重要的轉捩點,是有可能,而且容易看到的。這些蛛絲馬跡事實上穿越了一八七一年之後,俾斯麥所建立的同盟結構中。諷刺的是,俾斯麥原本並非將這同盟結構當作火藥庫,而是將它視為保護傘,以使他所開創的德意志帝國能和平成長。雖然俾斯麥的想法,早濃縮在他一八六八年的一句話——「弱國終被強國吞噬」之中,他自己的胃口,卻在一八七○至七一年戰爭(譯註:即普法戰爭)的三頓飽餐之後,感到滿足。所以,我們不能譴責他,認為他的野心比胃口大;就像他所說,他感覺德國現今是一個「心滿意足」的國家。他的統治理念自此之後並非擴張,而是團結。為了爭取足夠的時間與和平,使新德國保持穩定,他企圖抑制法國國力的發展,使法國維持在無法進行復仇之戰的局面。但是結果證明這些作法對德意志帝國並無好處。
俾斯麥並未對法國實施經常不斷的直接脅迫。他只準備切斷法國與友邦或支持者之間的關係,以便間接打擊令人困擾的法國快速復甦。俾斯麥首先拉攏奧地利與俄羅斯,使他們和德國結為普通的結盟關係;同時努力促成巴爾幹半島的和平,以防後者對結盟關係造成任何危機。有好幾年時間,他的政策是,在歐洲外交利益交換上,不對任何一方做出承諾,僅做一名「忠實的經紀人」。然而,他與俄羅斯首相戈恰可夫(Gortchakov)之間的不和,以及由於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Russo-Turkish War)的紛擾,使他不顧年老的德皇威廉一世的反對,與奧地利在一八七九年訂定了防衛聯盟。德皇原本將這種作法視為「出賣」俄羅斯,甚至曾威脅說自己要退位。不過這紙明確的承諾,後來並無明確的結果。儘管如此,俾斯麥在一八八一年以巧妙的外交手段,經由俄、奧、德三國所簽訂的「三帝同盟」(Three Emperors Alliance),暫時取回主導地位。這著名的「三帝同盟」,原先目的在於干預所有巴爾幹半島事務。雖然該同盟稍後在一八八七年廢止,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則另以祕密訂定的二雙重保障條約」(Reinsurance Treaty)作為補償,並獲加強。經由該約,兩強同意除非德國攻擊法國,或俄國攻擊奧地利的情形發生,雙方各自與第三國交戰時,彼此將維持善意的中立。在這兩次巧妙的,具有驚人欺瞞效果的外交手法下,俾斯麥避免了當時迫在眉睫的俄法聯盟。
同時,德奧之間的結盟,由於一八八二年義大利的參與而擴大。其結盟目的是,如果德國與俄國作戰,提防俄國從背後暗算奧地利;義大利如遭法國攻擊,德奧將出兵相助。不過義大利為保護與英國老友的關係,及其本身海岸線的安全,卻在條約上附加一段特別協議,闡明絕不直接與英國衝突。一八八三年,羅馬尼亞(Rumania)經由該國國王個人與一些祕密運作過程,也加入了這新的「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後來甚至連塞爾維亞(Serbia)與西班牙也分別短暫與奧地利及義大利,以另締條約的方式結盟。
對於英國,俾斯麥的目標似乎企圖使英國僅與德國保持友好,而與法國保持不友好的關係。他對英國的感覺,在友好與輕蔑之間搖晃不定。其態度轉變的關鍵點,在於英國不同政黨的輪替執政。對於「老猶太」狄斯累利(Disraeli),他由衷敬重;但他無法了解格萊斯東自由黨(Gladstonian Liberals)的觀點,同時他也瞧不起自由黨政策搖擺不定的行徑。當狄斯累利當權時,俾斯麥大談拉攏英國為其同盟的想法;雖然維多利亞女王曾低調表示,「確信德國在任何一方面都將是最安全的盟友」,她卻不敢肯定俾斯麥是否能託以信任,狄斯累利的看法亦同。因此俾斯麥繼續玩弄藉由英俄、英法之間不和,使自己漁翁得利的政策。幾經精心的評估,他贊成英國占領埃及,因為英國占領埃及會使英法不和。在另一方面,由於德國的極端殖民主義,在未來具有與英國發生衝突之虞,所以他反對國內漸起的殖民擴張聲浪。他曾說:「我們極端殖民主義者的貪婪,大過我們所需要的,或能滿足的。」他以支持英國占領埃及,企圖逐漸換取英國在海外的小讓步。經由這些小讓步,他緩和了德國利益團體強大的,連他都無法忽視的殖民要求。然而英國保守黨的重新執政,以及英法之間與日俱增的摩擦,使英德建立起新的緊密關係。俾斯麥提出的正式結盟,受到沙里斯布雷爵士內閣(Lord Salisbury’s Cabinet)的熱烈歡迎;不過後者似乎因擔心國會反對與外國牽扯而退縮。然而,俾斯麥從這非正式的協議中,以微不足道的代價取得了英國對海利哥蘭島(Heligoland)的割讓。海利哥蘭島在後一世代,對德國海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於是到了一八八○年代末,俾斯麥偉大的政治架構似乎已沛然成形。德國受到「三國同盟」的支撐;而英俄若即若離的態勢,對它只有利而無弊。在這樣穩定的基礎上,德國為商業擴張做好了準備。而且俾斯麥已將法國驅入一個孤獨而侷限的政治隔離圈內。
但自一八九○年代初開始,俾斯麥規畫的政治架構出現了一道裂痕;後繼者幾乎到要趕走這架構起造者的地步。年輕的德皇威廉二世於一八八八年即位。他與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素不友好;後者既不喜歡德皇的「侵略性友善」,也懷疑他的意圖。然而對俾斯麥的政治架構來說,問題並非來自沙皇,而是威廉二世。俾斯麥的掌權方式,向為德國參謀本部與軍隊所詬病,如今也令威廉二世厭惡不已。由於威廉二世幾乎在參謀本部與軍隊中成長,所以他很自然發現這些人與他站在一邊。但他未覺察,這種關係也束縛了自己。
第一個效應是,趕走「親俄」的首相之後,繼任者拒絕與俄續訂「雙重保障條約」。第二效應則是第一效應的必然結果。沙皇忍下對共和主義的嫌憎,於一八九一年與法國訂定了協議。這協議並於一年之後發展成軍事協定。雙方希望在遭敵攻擊時,彼此相助。這協定中的重大要點是,倘若「三國同盟」中任何一方進行動員,法俄將立即動員。由於法方談判人波斯德福將軍(General Boisdeffre)曾費心向沙皇解釋,「動員意味宣戰」,所以沙皇至少無法說他不懂這其中的意涵。
沙皇在害怕英德即將結盟之餘,喝下了這劑俄法結盟湯藥,後來卻一直苦惱著沙皇。因此在簽約後,長期未對法國產生任何外交價值。
儘管如此,法國跳出了政治「隔離圈」。從現在起,歐洲並非僅止於一個政治集團,而是兩個政治集團。雖然其中一個關係較寬鬆,另一個卻較緊密。這兩個集團形成了均勢,即使各方勢力尚未全然均衡。
對於德國廢止德俄祕密條約,尚有要點值得一提。柏林的議會在早先覆審這項條約內容時,曾反對訂約。理由是該條約不但對奧國不忠,而且對英國不誠。其實,不論德皇的缺點如何,他的性格比俾斯麥更真誠;他在矛盾發言中所顯現的偽善外表,似乎是因為過度坦率與經常快速轉變心意。他們兩人基本相異之處在於,一個是以始終如一的欺騙,來尋求國家安全;另一個則是在突發式的真誠態度下行事,得到的僅是不安穩的保障。英國方面對此的看法與德皇一致。雖然德皇對待俄羅斯的態度與俾斯麥迥異,他卻維持俾斯麥對英的友好態度,這也許是因為他的性格中多了一份真誠,較少政治動機之故。但英德兩國間卻有一件緣起於私人因素的不睦。原來德皇與他的舅父威爾斯親王(譯註:威廉二世的母親是英女王維多利亞的長女),也就是後來的英王愛德華七世彼此相惡。妙的是,這私人裂痕是被俾斯麥家族弄得愈來愈糟的。
不過這私人之間的不和,如果沒有更大的問題介入其中,是不會釀成國際友誼的裂痕。事實上,英德不睦來自於一個主因,以及附加的許多小因素。這一切都需自德國的政策從重視內部轉變為向外擴展說起。當德國的商業與影響力,擴增到世界級的規模時,其利益無可避免與英國在多方面發生接觸。但經俾斯麥式老奸巨猾手段處理之後,這類接觸不會造成一觸即發的摩擦,因為英國的政治手腕原本就相當不敏銳。而這時期英國最關心帝國疆土的政黨,碰巧就是最同情德意志帝國的政黨。然而,現在俾斯麥已走,卻無圓通練達者取代其位。有一種情形時常發生在像俾斯麥這類偉人身上:他的門徒忘記主子的行事原則,卻只記得他的方法——武嚇。不過,德皇此時自己已可運用魅力達到目的了。儘管他屢犯眾怒,他不僅成功地維持了在英國的名望,而且在俄羅斯新即位的,軟弱而友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曾經有一度,他還無條件擁有對沙皇的影響力。
德英之間第一次較大的摩擦是為了土耳其。此事件的陰影影響了未來。一八九二年,當時英國自由黨重新執政;就像格雷(Sir Edward Grey,譯註: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任英國外交大臣)所說,「突然間,從柏林送來一封像最後通牒的文件,要求我們為土耳其的鐵路,終止與德國人競爭。」並且在此後數年,德皇從未忘記強調,在德國所擴展的商業網中,「坐鎮著一隻牙齒鋒利的蜘蛛」。一八九五年,由於他的干預,使俄國自日本手中奪得了與中國作戰所攫取的戰利品。一八九六年,他再次與英國發生衝突。這回就比較嚴重了。諷刺的是,起因是由於某英國人士對俾斯麥式霸業的狂熱欽佩。這位名叫羅德茲(Cecil John Rhodes)的英國人,不但對俾斯麥式的霸業推崇不已,而且對威廉二世也曾做出相等的讚譽。但德皇卻不領情,並對羅德茲所擬訂的英國南非擴張計畫深感忿怒,甚至像是自己受挫似的。經過幾回酸溜溜對英國的批評,以及南非外伐爾的波爾人(Transvaal Boers)的甜蜜慫恿,對於詹姆森(Sir Leander Starr Jameson,譯註:英裔南非政治家)率兵入侵外伐爾共和國之舉,發現了一個誘人的藉口。一八九六年一月三日,德皇在議會中提出構想,他認為德國應聲明為外伐爾共和國的保護國,然後派兵前往該地。首相何亨羅(Hohenlohe)聞言,則以「這等於與英國宣戰」為由,反對此種作法。德皇卻直率答道:「是的,但這只是在陸地上作戰。」不過,有人提出稍微緩和的辦法。建議他不如拍發賀電給南非外伐爾共和國總統克魯格(Kruger)。但電文言詞間不但高度冒犯英國,而且否認英國對外伐爾共和國的宗主權(譯註:此賀電事件史稱「克魯格電報事件」,指德國電賀克魯格擊退英國殖民者詹姆森來犯的軍隊。惟英國否認參與該事件)。
這下,由於一方有著壓抑不住的妒嫉,一方則驚見傳統老友驟變為新敵,於是兩國人心都鼎沸了起來。德國人自認惱恨有理。他們認為,已占據許多殖民地的英國,如今又要開疆闢土。但這塊新殖民地,正是另一位遲來者想要的。然而英國人拓展殖民地已習慣成性,他們竟平靜地以為這樣做才符合英國約翰牛形象。他們無法理解,除了傳統的對手俄國與法國外,居然還有人對此事感到如此掛念。所以在一般的交往上,不論德國做出如何的不自覺挑釁,英國始終保持冷靜的自信。這種態度也成為這次危機的一帖鎮靜劑,而且幾乎是成功的。原來德國曾下令採取戰爭手段,建議法俄聯合攻擊英國。但後來,一者由於法俄缺乏興趣,一者英國沙里斯布雷政府的冷靜,使德國自覺海軍不夠強大而自我克制,一觸即發的危機因而消失。
然而,危機因欠缺實力而避開,並不表示危機已解除。德國海軍的野心,即在此時開始萌發。這股野心明顯浮現在一八九七年威廉二世的一段話上,「三叉戟應握在我們手中」,以及他對鐵必制將軍(Admiral Tirpitz)所下達的命令。他要求建造這支三叉戟。翌年,德國海軍的擴建計畫開始進行。並且,據說在德皇訪問大馬士革期間,曾宣布他是全世界伊斯蘭教徒的保護者。這簡直是對英法的直接挑釁。不僅如此,由於他明白聲稱要擔任土耳其的守護神,也造成與俄國的嚴重不和,因為他阻礙了俄國覬覦君士坦丁堡的美夢。就像被拿破崙嘲弄的對手一樣,德皇因「眼中有太多事務」而將其外交章法打亂。致使這些曾被俾斯麥耍弄過而相互攻擊的列強,現在在任何地方只見到一件事——德國的拳頭,而未見其他。儘管如此,一八九八年,英國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譯註:一八九五年任英國殖民大臣。是二次大戰前夕英國首相尼微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之父)為英國介入南非紛爭之事,向德國提出俾斯麥曾尋求過的結盟建議,卻遭德國的侮慢。原來張伯倫的提議,現在輪到德國存疑了。事實上英國做出這樣提議,是因為英國有了新的顧慮。英國正考量本身所受的孤立與弱點,儘管在觀點上基於一種舊意識——與德國有其天生的密切關係。但這提議現在看來,卻像是自己在招認弱點。至少部分是如此。而以弱點為由的提議,對於新德國並非上策。俾斯麥遺留給繼任者的幾種遺風之一,就是低估英國實力,高估俄國的實力。
德國自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年之間,幾度拒絕張伯倫的建議,主要竟與個人因素有關,也就是與隱身在後的霍斯坦(Friedrich von Holstein)有關。霍斯坦是一位性格晦澀,狐疑,貪婪的外交部官員;喜深藏不露,作沒沒無聞狀。因為他以為唯有如此,方能增強其在追求「真正政策」方面的實權。霍斯坦雖然堂而皇之利用官方知識,祕密進行相當冒風險的事情,卻也不願替自己縫製一套掩遮外表的新衣。雖然他表態說是俾斯麥的門徒,卻曾密謀讓他師父下台。現在則以俾斯麥精神繼承者的姿態,令人肅然起敬,雖然他所傳承的,只是師父的一些旁門左道。最重要的是,他欠缺俾斯麥的膽識。
結果,儘管他願意接受英國的建議,卻害怕變成英國的爪牙,成為英俄衝突的避震器。在另一方面他認為,若現在將英國置於若即若離的範圍,英國的弱點正好可加利用,並可逼迫其讓步;而在此同時,仍需讓英國心存與德國保有較密切關係的期望。這樣的觀點,他至少獲得首相比羅(Bernhard von Bülow)的支持。德皇更將他的觀點,籠統敘述在給比羅的信上。他寫道:「儘管他們想扭身掙脫,我現在已經抓住了英國。」然後,德國在一九○○年再次擴建海軍,成為扭緊英國的工具。
此後數年,特別在南非危機與戰爭期間,英國政府為德國的態度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段時期,英國並不期待德國為南非戰爭伸出援手,只求德國不將威脅與侮蔑付諸行動。於是,無論在葡屬殖民地,在薩摩亞,在中國,英國沙里斯布雷政府所表現的軟弱,幾乎印證了德皇所說的,「十足的笨蛋」。這幾年間的外交檔案所揭露的,也都是讀來令人可鄙的文件。從外交檔案,可追出沙里斯布雷政府對於後來的衝突,應負間接責任。因為很自然的,德皇與他顧問的思維,必然可從他們的武嚇法(mailed-fist method)想法證實。不過,德皇可以不負將武嚇推及真正戰爭之責。這不只是因為他曾有不喜歡武嚇的證據、而是他有從膚淺外表斷事的傾向。他推斷,對英國有限的威脅,很明顯在未經風險下,即可為德國帶來戰爭利益。這種過於淺顯的推論,是與他個性契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