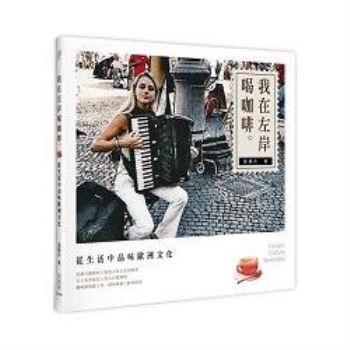巴黎與處女
新年夜的朋友聚會上,尼古拉說了一個法國式的謎語,他問我們知道巴黎和處女的區別嗎?我們正想著答案時,他說巴黎永遠是巴黎啊。
的確。
然後我又補充說,你說的是不同,其實巴黎和處女也有相同之處—迷人,總有驚喜。
古今中外有那麼多名人寫過巴黎的迷人—雨果、左拉、徐志摩⋯⋯等等。與其說寫的是他們筆下的巴黎,不如說是在寫巴黎生活中的他們。
在這個城市裡,你常年在藝術的氛圍中被薰陶,用自己的感官接收,再以不同的途徑釋放—所以畫家可以用文字述說,作家可能會拿畫筆勾勒,音樂家可以作詩表達,雕塑家可以用流動的音樂來建築。藝術是相通的,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裡的藝術家多才多藝。這是在這個城市生活的結果,總有驚喜,總有新鮮感,總有被激發的創作靈感,總想以不同方式表達。巴黎似乎是一種象徵,一個符號,一種永恆。
巴黎還是清晨麵包店門口排著的長長隊伍,只為那根剛出爐長棍麵包的滿口脆香;巴黎是在咖啡店門口的面街一坐,只為那午後時分的陽光享受;巴黎是傍晚不知名小巷散步的片刻悠閒,是偶然在小巷發現間店面不大卻道地美味的驚喜;巴黎是腳踩狗屎的尷尬;是熬過漫長的預約等待;是看過搖曳燭光與塞納河面的交相輝映的經歷;是不小心被偷被搶的鬱悶心情;是每晚戲劇歌舞豐富多彩的夜生活—這些都是巴黎的不同面孔與表情。她的魅力源於豐富,她的豐富又體現在經典與流行、時尚與浪漫。
法國的朋友總對我說,逛巴黎有空一定要去看那些老街區,那才是真正有味道的。最好是拋開地圖,逛「丟」了自己,而不是待在旅遊者多的景點。他是個老巴黎,經常自己帶著相機穿梭在巴黎的城區。某個周日陽光很好的下午,他曾帶著我走過了許多很有故事的街區,看有家族歷史的小店,還有最古老的出版社,然後回到旺多姆廣場。途中他向我講述著他們古老的歷史,他是個稱職的導遊,讓我感受到了另一種巴黎的味道,以後的日子裡,我也會經常作這樣的探索之旅,像第一次來到法國一樣打量著周圍,並隨意在巴黎的小巷走,即使是生活的街區,我也有不少驚喜的發現,挖掘出一些很有意思的小徑小店。我想,他是對的,要品嘗這座城真正的味道,就要不著痕跡融在其中,變成巴黎人,而不是過路客。然後再看那鐵塔間閃爍著的暮色之城—抬頭是奧斯曼建築風格,優雅的雕花設計,每片磚瓦似乎都在講述光陰的故事;到街道盡頭的小館喝一杯咖啡,說不定就坐在海明威寫作的凳子,遞過的菜單會不經意發現沙特留下的筆跡;轉往下個街口,飄來剛出爐可頌的誘人氣息,傳遞百年老店不變的味道;即使是陳舊的地鐵隧道,老人一曲薩克斯風輕而易舉撩撥我心底柔軟情愫,走了一段路才發現眼角已濕。漫步在黃昏時分巴黎窄窄的街道上,有輛小轎車正用「巴黎式停車法」前頂頂又後拱拱地終於費勁擠進車位,左邊那夕陽斜照的哥德式聖母院前,一對情侶點了蠟燭斟了杯紅酒在河邊野餐;再走兩步,又看見一個少年肆無忌憚地在牆角撒了一泡尿,頓時把浪漫澆滅⋯⋯
慵懶、優雅、細緻、不拘小節甚至那滲入骨髓的自以為是,使這座城與別的城市相比下顯得獨特。
所謂巴黎人,並不是生在巴黎,而是在巴黎生活過的人,沾染了這座城的習性,重生而成。
每天都有新的故事發生,而巴黎永遠是巴黎。
新年夜的朋友聚會上,尼古拉說了一個法國式的謎語,他問我們知道巴黎和處女的區別嗎?我們正想著答案時,他說巴黎永遠是巴黎啊。
的確。
然後我又補充說,你說的是不同,其實巴黎和處女也有相同之處—迷人,總有驚喜。
古今中外有那麼多名人寫過巴黎的迷人—雨果、左拉、徐志摩⋯⋯等等。與其說寫的是他們筆下的巴黎,不如說是在寫巴黎生活中的他們。
在這個城市裡,你常年在藝術的氛圍中被薰陶,用自己的感官接收,再以不同的途徑釋放—所以畫家可以用文字述說,作家可能會拿畫筆勾勒,音樂家可以作詩表達,雕塑家可以用流動的音樂來建築。藝術是相通的,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裡的藝術家多才多藝。這是在這個城市生活的結果,總有驚喜,總有新鮮感,總有被激發的創作靈感,總想以不同方式表達。巴黎似乎是一種象徵,一個符號,一種永恆。
巴黎還是清晨麵包店門口排著的長長隊伍,只為那根剛出爐長棍麵包的滿口脆香;巴黎是在咖啡店門口的面街一坐,只為那午後時分的陽光享受;巴黎是傍晚不知名小巷散步的片刻悠閒,是偶然在小巷發現間店面不大卻道地美味的驚喜;巴黎是腳踩狗屎的尷尬;是熬過漫長的預約等待;是看過搖曳燭光與塞納河面的交相輝映的經歷;是不小心被偷被搶的鬱悶心情;是每晚戲劇歌舞豐富多彩的夜生活—這些都是巴黎的不同面孔與表情。她的魅力源於豐富,她的豐富又體現在經典與流行、時尚與浪漫。
法國的朋友總對我說,逛巴黎有空一定要去看那些老街區,那才是真正有味道的。最好是拋開地圖,逛「丟」了自己,而不是待在旅遊者多的景點。他是個老巴黎,經常自己帶著相機穿梭在巴黎的城區。某個周日陽光很好的下午,他曾帶著我走過了許多很有故事的街區,看有家族歷史的小店,還有最古老的出版社,然後回到旺多姆廣場。途中他向我講述著他們古老的歷史,他是個稱職的導遊,讓我感受到了另一種巴黎的味道,以後的日子裡,我也會經常作這樣的探索之旅,像第一次來到法國一樣打量著周圍,並隨意在巴黎的小巷走,即使是生活的街區,我也有不少驚喜的發現,挖掘出一些很有意思的小徑小店。我想,他是對的,要品嘗這座城真正的味道,就要不著痕跡融在其中,變成巴黎人,而不是過路客。然後再看那鐵塔間閃爍著的暮色之城—抬頭是奧斯曼建築風格,優雅的雕花設計,每片磚瓦似乎都在講述光陰的故事;到街道盡頭的小館喝一杯咖啡,說不定就坐在海明威寫作的凳子,遞過的菜單會不經意發現沙特留下的筆跡;轉往下個街口,飄來剛出爐可頌的誘人氣息,傳遞百年老店不變的味道;即使是陳舊的地鐵隧道,老人一曲薩克斯風輕而易舉撩撥我心底柔軟情愫,走了一段路才發現眼角已濕。漫步在黃昏時分巴黎窄窄的街道上,有輛小轎車正用「巴黎式停車法」前頂頂又後拱拱地終於費勁擠進車位,左邊那夕陽斜照的哥德式聖母院前,一對情侶點了蠟燭斟了杯紅酒在河邊野餐;再走兩步,又看見一個少年肆無忌憚地在牆角撒了一泡尿,頓時把浪漫澆滅⋯⋯
慵懶、優雅、細緻、不拘小節甚至那滲入骨髓的自以為是,使這座城與別的城市相比下顯得獨特。
所謂巴黎人,並不是生在巴黎,而是在巴黎生活過的人,沾染了這座城的習性,重生而成。
每天都有新的故事發生,而巴黎永遠是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