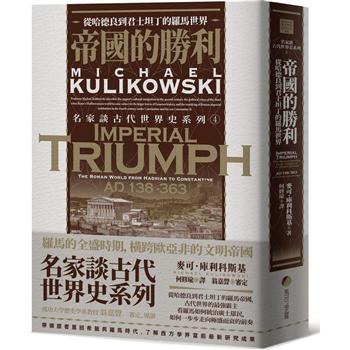照亮歷史的黑暗山洞:
《帝國的勝利:從哈德良到君士坦丁的羅馬世界》導讀
翁嘉聲
「晚期古代」的誕生
吉朋參觀羅馬廢墟時多所感慨,開始構想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他說若有機會在人類歷史中選擇一個自己要生活的時代,那會是從西元九六到一八○年羅馬五賢帝的「黃金時代」。但他也相信自己正處於衰落的時代,而羅馬帝國的命運似乎可以提供借鏡。《羅馬帝國衰亡史》的羅馬於是從黃金時代結束後開始衰亡,一直要等到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為止。他說衰亡是因為羅馬再也無法負荷她那「毫無節制的偉大」(immoderate greatness),再加上羅馬人皈依基督教以及野蠻外族同步入侵等的內憂外患。但有個疑問會立即浮現心中:羅馬的衰亡何以會長達千年之久?這是如何的衰亡呢?
吉朋認為羅馬帝國黃金時代結束後步入衰亡,淪落到中古基督教黑暗世界。如此「衰亡」概念其實是文藝復興學者最先提出來的。他們將歷史分為古代、中古及現代,並認為自己所處的現代初期是從中古黑暗世界中「復甦」、「復興」,是古典世界的「再生」。這種架構長期影響我們,而大學相關科系的課程結構也接受如此前提,推波助瀾,因為在五十年前歐美大學有關古典文化(classics)教學,反映出這樣的偏見。例如相關科系所教授的希臘文及拉丁文作品幾乎沒有二○○年之後的作家,而儘管(例如)拉丁文作品最多產的作家是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三五四至四三○年)。
另外,希臘羅馬古典歷史的教學強調政治、軍事及外交,而五賢帝時代結束後,羅馬帝國在這些方面每況愈下,因此五賢帝時期幾乎變成羅馬史教學的最後一章。此外,《劍橋古代史》第一版在一九二○年代起開始編輯,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最後一冊(第十二冊)最後一篇作者貝恩斯(Norman Baynes)說,當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亞宣布大公會議開始時,正式宣告歐洲中古時代的來臨。無論哪種說法,古代世界結束,直接進入中古世界,而且中古黑暗時期都來得相當早。
但牛津學者彼得.布朗(Peter Brown)在一九七一年出版《晚期古代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完全改變整個希臘羅馬古典歷史研究的格局。「晚期古代」這概念最先出現在十九世紀末藝術史研究裡,但現在被布朗用來劃分出一段古代世界逐漸轉變成中古時期的過渡時期,是段希臘羅馬古典異教文化及基督教文化融合、創造出屬於自己特色的時代。晚期古代的文化融合最後分別轉化為羅馬帝國西方的日耳曼後繼國家、羅馬帝國東方的拜占庭帝國,以及占有相當大羅馬幅員、沿用羅馬典章制度,但融合更多其他文化元素的伊斯蘭文明王朝。
布朗認為,晚期古代約從二五○至七五○年,是從羅馬「三世紀危機」或「黑暗時期」起(二三五至二八四年),到伊斯蘭阿巴斯(Abbasid)王朝在七五○年以巴格達為首都的五百年。哈佛學者格倫.博爾索克(Glen Bowersock)甚至將這段時間延長到八八八年卡洛琳王朝滅亡為止。因為晚期古代在知識領域上的出現,所以在一九七○年代重新編寫《劍橋古代史》第二版時,便將古代史結束時間延到皇帝莫里斯(Maurice,五八二至六○二年在位)被殺為止。如今「晚期古代」或(根據不同語境)「晚期羅馬帝國」或「早期拜占廷帝國」,已經是古典文化及古代史研究的顯學之一。
麥可.庫利科斯基(Michael Kulikowski)是專研這段晚期古代歷史的高手。他將這段複雜、但精采的晚期古代歷史分成兩部分來寫。本書《帝國的勝利:從哈德良到君士坦丁的羅馬世界》涵蓋哈德良於一一七年即位,到君士坦丁王朝(或稱為新弗拉維王朝)最後一位皇帝「叛教者」尤利安(於波斯遠征陣亡為止。這主要是討論晚期帝國的「主宰政治」(Dominate)型態如何出現以及有何特色。接下來的故事則出現在《帝國的悲劇:從君士坦丁到羅馬義大利的毀滅》(暫譯),交代其餘到約六○○年的故事。
台灣歷史教學及文化出版在介紹羅馬歷史時,常集中在共和時期及早期帝國,但晚期古代或晚期羅馬帝國史在內容上其實更加精采,除了羅馬帝國歷史本身外,還包括(例如)早期教會史、人才輩出的教父文學(patristics)、日耳曼民族歷史以及薩珊波斯歷史等等。這段歷史中出現的議題也常更具現代關連性,例如國家治理、宗教流變、教會與帝國、族群衝突及遷徙,和文明轉化及系統崩潰等等。庫利科斯基巨細靡遺的兩冊著作在馬可孛羅出版的翻譯及引介下,適時且適當地填補這段重要歷史該有的知識。
二三五至二八四年是羅馬史的暗黑山洞?
《帝國的勝利》詳細交代羅馬政治及體制如何歷經「元首政治」(Principate)時期的安東尼時代、塞維魯王朝、三世紀危機,到「主宰政治」(Dominate)時期的戴克里先改革,最後在君士坦丁王朝確立晚期帝國格式及規模的敘事史。 我們在學習及教授這段歷史時,時常面臨在塞維魯王朝結束,進入二三五至二八四年危機時代的羅馬黑暗時期時,立即陷入史料真空的黑暗狀態,以及面對不忍卒睹的帝國徹底混亂及失序的另種黑暗,因此常匆匆交代這羅馬黑暗時期的大致輪廓後,便急忙進入格局及氛圍截然不同的戴克里先改革及體制。或用個比喻說,我們從早期帝國的元首政治,通過二三五至二八四年這段時間的「暗黑的歷史山洞」,然後不知何故地在山洞另個開口,浮現出與之前不同的主宰政治,悄然開始晚期羅馬帝國的歷史。這種歷史斷裂感在一般羅馬史的敘述中常被強調,彷彿三世紀危機的時代是座隔屏,隔出一邊是好的帝國、鼎盛帝國、黃金時代,但另邊則是壞的、極權專制、高壓統治的中古黑暗時期。除了上述文藝復興及吉朋的影響外、這危機時代的文獻史料十分不足,而特別是羅馬帝國在這段時間面臨空前的艱巨挑戰,加起來形同「黑暗時期」。
但《帝國的勝利》這本書強調的不是絕望,因為羅馬帝國畢竟挺過去,進而開啟晚期古代的歷史。庫利科斯基藉助錢幣、碑銘、考古以及對文字史料的重新詮釋,加上他對羅馬人勇敢和創意的信心,使得這段之前大部分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時代,經過他的敘述後,變得相對清晰、正面。他指證出:羅馬領導人在二三五至二八四年危機時代中,勇敢面對多種併發的內外挑戰,開始或持續改造、轉化之前的元首政治,創造出新體制來應付變局。戴克里先從二八四年起復興帝國及完成的「主宰政治」,必須以這段黑暗時期的成果為基礎。庫利科斯基的目的是要填補這歷史斷裂,照亮這黑暗的歷史山洞,所以這段被吉朋認為是「衰亡史」初步階段的歷史,原本是黯淡、沮喪、甚至失敗的歷史,最後卻在庫利科斯基的寫作下,成為帝國的「勝利」。「勝利」若有所指,那或許應該指在二三五至二八四年充滿危機的時代中,羅馬克服種種挑戰,成功建立晚期羅馬帝國新政治體制的「勝利」。
與之前相關羅馬史研究相比,這樣的「勝利」是本書最大的貢獻。我最先百思不得其解,何以此書命名為《帝國的勝利》。若換成像是《羅馬帝國三世紀危機》、《羅馬黑暗時代》或《漫長的羅馬危機時代》,或許更能更符合部分主旨,但這些都無法傳遞作者認為那時代羅馬領導人顯示出的堅持、勇氣、創造力以及成就。
所以「元首政治」經過二三五至二八四年黑暗時期的危機,最後在戴克里先統整,再加上君士坦丁鞏固、確定「主宰政治」的體制。但那是如何的變化?我們首先要理解一下在這所謂危機時代「隔屏」兩側之一的「元首政治」(西元前二七至西元二三五年)是如何一回事,然後再論述羅馬黑暗時代如何面對危機提出對策,最後如何整合到戴克里先所啟動的「主宰政治」(二八四至六一○年)系統;如何從以結構簡單的城邦體制來統治幅員遼闊、族群複雜的世界,在經過黑暗時期的轉化後,變成以皇帝為中心,建立複雜的中央官僚機制來統治帝國。首先我們先說「元首政治」。
元首政治:政治威權≠行政治理
羅馬共和是寡頭政權,權力由人數有限的元老貴族把持。「共和」(Res Publica)是指這群少數人的共和,而「自由」(libertas)是這少數人爭權奪利的自由。其他平民則享有法律保障以及分享戰利品。羅馬在對外擴張過程中經常透過結盟方式,開放公民權給其他社區,因為這公民權擴大分享不會動搖寡頭統治的基礎,反而為羅馬帶來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提供更進一步擴張的基礎。這些盟邦菁英在自己社區裡經常複製羅馬的寡頭政體及制度,並主動效忠羅馬,為羅馬執行徵兵、徵稅等政府基本功能,同時治理地方。羅馬則以保障這些菁英的地位及福址來回饋。統治者與受統治者因此有相同的利益來一起經營羅馬這帝國共同體。即使奧古斯都在西元前二七年結束共和,開始元首政治,這種羅馬與盟友合作治理帝國的型態仍然持續,並在五賢帝時期到達顛峰。 羅馬以三十左右個專業兵團上提供「羅馬和平」(Pax Roman)的繁榮環境,保證忠誠的地方議員階級能夠創業積財,享有在地的政治地位及榮華富貴;在地菁英則投桃報李,深信效忠服務帝國是對自己的最好選擇,成為一群「願意的子民」(willing subjects)。所謂「羅馬化」(Romanization)常是帝國子民主動模仿羅馬、調整自己的結果。
因此二世紀小亞細亞希臘作家阿里斯提德斯(Aelius Aristides,一一七至一八一年)在獻給皇帝安東尼烏斯.庇烏斯的《論統治權力》(On Ruling Power)演說詞中,將羅馬比喻為城邦聯盟之首,正如奧古斯都是「同儕之首」。這種將羅馬帝國視為城邦聯盟的說法經常被嘲笑,但我認為卻是洞見,因為這隱含對羅馬帝國運作的一個理想化想像圖像,更是禮讚這套簡潔的政府治理藝術。這策略使得羅馬成為有史以來在帝國治理成本最為經濟的巨型政體。根據加恩西和沙勒(Garnsey & Saller)研究,在二世紀五賢帝(九六至一八○年)時期,帝國以不到兩百位官僚來經營五千萬人口和五百萬平方公里,而其所依賴的便是地方社區菁英階級主動願意與羅馬中央合作。
無論不到兩百這數字是否正確,重要的是羅馬的治理方式十分特殊,完全不同於我們常見頭重腳輕或由上而下的帝國治理方式,如晚期羅馬帝國主宰政治的中央集權便是典型例子:甚至當一位皇帝及集權官僚無法控制帝國時,則繼續將帝國一分為二、為四,但每個帝國所統轄的地區仍比現在法國或土耳其大上許多倍,因此需要複雜的官僚組織架構來治理。晚期羅馬皇帝權力透過這各層級的治理機構,滲透到帝國每個角落、落到帝國每位子民身上。但奧古斯都「元首政治」建立的早期帝國,卻充分利用地方社區的高度自治及菁英階級認同羅馬的心願,一起經營帝國。以比喻來說,元首政治的羅馬帝國像是現在流行的「雲計算」方式,數以千計組織簡單的地方城邦,在帝國網路裡擔任功能簡單的運算節點,配合絕佳軟體串連,同步進行運算,解決複雜問題。所以當元首政治時期的羅馬向帝國境內各地城邦發送如徵兵、徵稅指令,各地高度自治的議員階級菁英主動為羅馬效勞,自行吸收行政成本,執行普查、徵稅及徵兵的任務。相形之下,我們所熟悉的帝國,包括晚期羅馬帝國或像一些現代集權國家,則像部有強大處理器及大量隨取記憶體的超級電腦,藉著無所不在的大量官僚科層,以極大治理成本,到處派出官員執行法令。晚期羅馬帝國皇帝的政治威權透過行政治理而無所不在。
元首政治時期的羅馬帝國容許因地制宜及不同在地傳統的治理方式同時並存,極具彈性。因此我們見到在元首政治下,例如,皇帝和元老院分別管轄不同類型的行省,外加特殊地位的義大利及羅馬,還有由皇帝親派騎士出任總督的埃及。中央、行省及在地城邦也沒有明顯階層化情形,而治理方式及規範(特別是稅收)常因地制宜,尊重在地傳統,十分多樣。從受統治者的心理狀態來看,大部分羅馬帝國子民想必除了承認、心領神會遙遠羅馬皇帝那無比威嚴的政治威權外,其實甚少感受到「被羅馬統治」的實際治理,而是繼續生活在羅馬統治之前熟悉的環境中。簡單說:在「元首政治」的早期羅馬帝國中,皇帝或元首的「政治威權」,並未透過「行政治理」傳達下去。相對之下,在晚期羅馬帝國的每個帝國子民都透過官僚系統的行政治理,清楚感受到皇帝威權,深刻感覺自己是「被羅馬統治」。
這種被學者稱為元首政治時期的「雙重法律系統」(double legal systems)或甚至更多重的彈性,使得羅馬皇帝在面對新問題,需創造出新行政位置(nova officia)來面對時,變得更為方便,但這些主動權多落入皇帝手中。那些原來由元老院或地方所執行的功能,卻因為與元老院政治地位的滑落,以及羅馬從一九二年起(或更早)的動亂,社區開始萎縮,而逐漸處於被動,無法參與。所以我們會見到像是哈德良設法派任四位總督級官員治理義大利,降低其特殊地位到與其他行省地位相當;這種平等化(levelling)讓傳統心態的羅馬元老院極為不安不滿。另外,從圖拉真開始起,羅馬皇帝逐漸不再出身義大利,而是從伊比利、高盧、北非及帝國各地入主羅馬,更加重皇帝從帝國各地延引人才的趨勢。羅馬帝國變得愈來愈「帝國」,而愈來愈不「羅馬」。皇帝也不斷擴大在正規外的民事及刑事司法權。整個二世紀及三世紀初帝國治理的總體趨勢可以看出皇帝逐漸擴張權力,犧牲其他如元老院、人民及地方自治的權力。
這過程在塞維魯王朝更是加速,特別是皇帝權力在財政上大幅擴權。這一方面是塞維魯在皇位爭奪的內戰及之後的政治整肅中,沒收對手資產,數量大到必須設立專職單位處理。另方面,這時軍需不斷增加(如軍隊員額增加、屢次加薪及為籠絡軍心而頻繁出現的賞金),皇產及皇帝私產在國家財政上的比重愈來愈大,皇帝指派到各地的各類財務官員(procurators)愈形重要,甚至取代正式官員,在國家財政以及其他領域上的角色凌駕在傳統機構之上。但特別是二一二年卡拉卡拉的安東尼烏斯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的公布,使帝國內所有自由人均成為羅馬公民,更是將之前那複雜多樣、量身訂作、因地制宜的各種法律給均一化:在法律上,帝國內的每個人從此都直接是皇帝子民,適用相同的法律。塞維魯王朝中出現多位法學大家,常位居行政系統頂峰的禁衛軍統領;他們詮釋、編整法律以及管理帝國,都可理解為企圖理性化、合理化及體制化皇帝那愈來愈乾綱獨斷的絕對權力。之前元首政治中的種種特例、特權,現在逐漸被取消,而被整合到一個為皇帝服務的官僚系統中。法律文獻中逐漸浮現初以官員職權的概念來整合皇帝具體及詳細的法律權力,取代之前元首政治那種籠統代表元首特殊地位的「較高延任執政官權力」(imperium pronconsulare maius)及「護民官權力」(tribunicia potestas)的憲政地位。
庫利科斯基用「騎士化」(equestrianization)這名詞來形容這趨勢以及官僚系統的建立過程。這名詞當然主要是指帝國治理的人事。我們一向認為傳統元老會被摒除在外,主要是因為外省出身的皇帝不喜歡或蓄意打壓傳統羅馬菁英。但庫利科斯基認為,雖然元老菁英有時還是有無法接受是皇帝「僕人」這種有些「共和」的想法,但根本上還是因為他們無法在變局中勝任這些新變化。另方面,這些「騎士」來源廣泛,皇帝可以從全國選才,適才適用。因此除了傳統騎士階層(如經歷過「三種軍職」[tres militiae]的軍事基層歷練)出身者外,還包括那些軍隊行伍出身、脫穎而出者。這些人會受命去統治行省及率領軍隊,以致於所有兵團軍團長(legate)最後都是騎士階級或行伍出身,而沒有元老。另外,還有那些不屬於上述,但受過教育、有能力的各地人士,則擔任各地皇家財務官員,或在朝廷各部門及祕書處服務。皇帝在元首政治初期會使用家奴或解放奴(這所謂的familia Caesaris)擔任皇帝機要及部門負責人,這從塞維魯王朝起完全不見:所有為皇帝服務的人都是出身自由(ingenui)、常與皇家沒太多直接關連的人,而升遷多憑能力。帝國官僚系統正朝著理性化、體制化的目標前進。
晚期羅馬帝國如何從黑暗時期的挑戰與回應中學習
所以當二三五年塞維魯.亞歷山大被殺害,結束元首政治,馬克西米努斯拒絕到帝國中心的羅馬即位,象徵元老院與控制軍隊的皇帝的許多矛盾,之前雖曾藉著元首政治的偽裝來緩和,但現在正式終結。但這也立即導致三世紀危機中常見的「合法化危機」,約五十年的黑暗時期出現了二十六位皇帝、三位合法副皇帝以及四十一位僭位者;皇帝更迭不斷,政治十分動盪。黑暗時期的皇帝們究竟要如何確定合法或僭位?他們嘗試過王朝世襲或舉才收養,但更發展出將皇權與神明緊密連結(如奧勒良的「所向所向無敵太陽神」[Sol Invictus])。這在將在世皇帝視為神明,在元首時期原本只發生在那些被人認為瘋狂的壞皇帝,例如卡利古拉、尼祿、圖密善或康茂德身上,其中一些人還遭受死後「記憶抹煞」(damnatio memriae),但現在皇帝是神或神的在世代表,則是義正嚴詞、理所當然。
另外,皇帝認清遼闊帝國已經無法由一人從羅馬中央來指揮控制。所以加里恩努斯在父親瓦勒良兵敗波斯被俘後,接受帝國被割據成三塊(波斯杜姆斯的高盧、帕邁拉人奧登納圖斯的東方,及自己控制帝國其餘部分)來治理,並未企圖重新統一,坦然接受帝國分而治之是面對當代危機的方法。因此戴克里先「四帝共治」(tetrarchy)將帝國一切為二、為四,或君士坦丁最後由三位兒子分治帝國的政治體制,便是將黑暗時期這些君權合法化、穩定繼承,以及有效治理帝國的成果給統整起來而成為新的系統。在將皇權神聖化中,無論是戴克里先為四帝共治設計的朱比特(Jupiter)王朝及海克力斯(Hercules)王朝,或君士坦丁決定皈依基督教(無論他是否真正相信),都是奧勒良「所向無敵太陽神」的不同呈現;君士坦丁甚至在錢幣上使用「所向無敵太陽神」的圖像及頭銜。從這裡也開始發展出凡跟皇帝有關的都變成「神聖」,臣民只可遠觀、不可近褻;臣民無法再以元首政治時期的「致意」(salutatio)、而是必須以「崇拜」(adoratio)來接近被種種繁複威儀包圍的皇帝本尊。他們宛若神明。
但羅馬黑暗時期更承受同時且連續發生日耳曼民族、波斯及柏柏人從各方面入侵,所以軍事也是皇帝的重要關切。元首時期的三十個上下的兵團及人數相當的輔助兵團(auxiliaries)兵力規劃及部署設計,都是將軍力沿邊界安排,並假設這些外族入侵不會同時發生,因此軍力可以彼此調動支援,運用沿邊界修築的道路快速移動換防,堵住缺口,甚至越界出擊。但黑暗時期外族的同時入侵讓羅馬人措手不及,無力有效回應,因此發展出類似「縱深防禦」(defense in depth)的機動部署:羅馬皇帝一方面繼續沿用邊界駐紮邊防軍,擔任預警功能、初步阻擋及延緩入侵的功能;但同時在戰略地點集中部署機動打擊部隊,隨時反應打擊成功入侵的敵軍。機動性極高的輕、重裝騎兵因此變得極為重要,特別是在加里恩努斯任內;他廣泛雇用善騎的外族及裝配及更具彈性的任務編組來保護帝國。也因此,指揮騎兵的司令常權傾一時(如奧瑞魯斯),甚至問鼎皇位(如克勞狄烏斯二世和奧勒良)。戴克里先繼續沿用這規劃,但到君士坦丁則正式化為守邊的邊防軍(limitanesis)以及兩位分控騎兵及步兵的首長(magister equitum及magister peditum)所指揮的機動中央軍(Comitatensis),而都使用可能更高比例的外族。君士坦丁將黑暗時期發展出來的戰略及戰術給體制化。另方面,當君士坦丁在三一二年擊敗馬克森提烏斯,入主羅馬時,因為禁衛軍部隊曾支持他,因此被解散,而統領則被正式文職化,形同帝國行政及司法首長或是宰相(viceroy),但這禁衛軍統領文職化的趨勢早已在塞維魯王朝出現過。晚期帝國軍職及文職的兩種仕途確立,但晚期帝國高度的軍事化,使得文官也有軍階
黑暗時期也是羅馬經濟陷入極大困難的時代。農業及其他產業因為政治不穩、內戰頻仍及外族入侵,而受到很大破壞。元首政治時期經營地方的議員階級也因為經濟凋敝,再也無力、無意願負擔治理及建設地方,或配合中央徵稅徵兵。在黑暗時期除了防禦工事外(如奧勒良擴大羅馬城牆),甚少出現新公共建物;既有社區普遍萎縮到以自保為主的規模,或乾脆棄城。元首政治時期星羅棋布的城邦世界面貌,開始改變。財政現在完全專注在續命的軍隊維持上。但整個問題更被如脫韁野馬的通膨,弄得更難以對付。有學者認為二○○年時花費零點五第納里烏斯銀幣(denarius)能買到約五十公升(一個medimnos)穀物,到三○○年則必須花費三百第納里烏斯銀幣。換言之,主食在這一世紀的通膨率是六百倍。法定通貨的銀幣最後其實只是個位數百分比銀含量的洗銀銅幣。黑暗時期的皇帝一直想克服這通膨的問題,但解決通膨一向都是財政學的難題,至今仍是,所以在黑暗時期進展有限。
戴克里先繼承這樣的問題,但他多管道面對。他首先要了解帝國有多少資源,所以以土地及人頭做為稽徵單位來進行普查,計算出帝國有多少單位。他計算出全國所需預算(主要是軍需),然後除以這些人頭及土地單位後,按單位徵稅,部分以現物(包括當兵的「人」)來支付軍隊,部分以貴金屬。帝國每隔五年、之後每隔十五年,重新普查一次。如果說之前元首政治時期的國家財政常是「混過去」(muddle through),以臨時徵稅、沒收充公或如哲學家皇帝拍賣皇產來應急,那主宰政治則是首次以類似預算的理性方式來處理國家財政。而這能如此是因為自塞維魯王朝以來皇家財政官員大幅擴張,建立需要的機制來運作,這繼續在黑暗時期被保留運作,現在被戴克里先的改革正式體制化。這些工作在元首政治時期常由地方議會來進行,但現在則是由皇帝手下專職的財務官員來執行。普查、徵稅、徵兵等財政措施對一般帝國子民而言,想必是他們最有感的「政府治理」,直接充分具現何謂「羅馬威權」。雖然共和及元首政治時期的包稅法人團體(publicani)並未完全消失,但在晚期帝國皇帝的各類財務官員,形同我們的國稅局官員,來直接向我們要錢要人。
就統治者來看,為了方便控制資源,必須立法限制職業、身分及遷徙的變動。所以原來地方議員階級現在被迫繼續承擔他們愈來愈無能為力的任務,而其他不同行業也開始管制,甚至世襲。上述預算措施以及這些管制,使得我們有時稱呼晚期羅馬帝國採行所謂的「指令經濟」或「管制經濟」(command economy, dirigisme),以指令及管制方式來運作政府治理,特別是經濟。這也造成晚期羅馬是個高壓專制統治的形象。最能代表這種由上而下來運作「指令經濟」,莫若三○一年公布的「最高物價指令」(Edict of Maximum Prices)。這是戴克里先因為自己幣制改革無法解決通膨問題,所做出的新嘗試。在這道對多達一千四百件物品及服務項目設定最高價格的巨細靡遺指令中,貴金屬被定價相對地低,似乎暗示對貴金屬持有者(多是富人)較為不利,但這反而造成貴金屬變得稀缺,加劇通膨。最後君士坦丁(據說)沒收異教徒神廟數百年的廟產為儲備金,發行以一羅馬鎊七十二枚金幣為單位的通貨:solidus,解決這通貨不穩及通膨的問題。solidus直到十一世紀一直是地中海國家、拜占廷帝國,甚至伊斯蘭世界最受歡迎、最具公信力的通貨。今天在一英鎊金屬幣的邊緣,仍可看到solidus的字樣。
這時期在文化、道德及精神上雖也被認為是個危機時代,但大巨變下的精神生活是既豐富又躁動。多茲(E. R. Dodds)說這是「焦慮的時代」(Age of Anxiety);神廟籤文常看到對自己未來命運的忐忑不安:「我會變得如何?」或「我會被賣掉嗎?」這時期沒有與維吉爾(Virgil)或尤維納(Juvenal)齊名的古典作品留存。但學者注意到這時代出現所謂「禁欲衝動」(ascetic impulse),一種決定「跳脫離」(opt out)世界的決心;另外,認為宇宙最終只有一神,並在各民族各有化身的「單一神論」(henotheism)普遍流行,如已經提及的「所向無敵太陽神」。這些傾向在古典哲學上最終體現於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那摒棄物質世界,追求無限超越,如這思想的開山祖師普羅提諾(Plotinus)的巨作《九章集》(Enneads)。新柏拉圖主義除了促成晚期希臘哲學(Late Greek Philosophy)的發展外,更是將古典哲學導入到基督教神學,形成所謂的「柏拉圖基督教化」或「基督教柏拉圖化」的必要人物,啟發如拉丁西方聖安博若修(St. Ambrose of Milan)及聖奧古斯丁,但特別是希臘東方幾位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教父。這些人都是基督教文明吸收、轉化古典文明精華的代表關鍵人物。
另方面,黑暗時期也是基督教發展極為迅速的時候,出現古代希臘基督教最偉大的聖經學者及神學家俄利根(Origen)。黑暗時期的亞歷山卓及安提阿教會也分別對三位一體及基督論發展出各自的獨特觀點、傳統,甚至流派;羅馬和迦太基教會也對教會紀律問題(如再洗禮)表達不同觀點。最後,基督教會在度過德西烏斯皇帝二五一年及瓦勒良皇帝二五八年兩次全國大迫害後,在接下來的四十年的發展更加迅速、扎根更深,所以當三○三年戴克里先「大迫害」來臨時,基督教已經準備好面對這最後的全面性考驗。這些發展都指出:當君士坦丁決定支持基督教、面對北非多納圖斯教派紀律爭議以及處理東方的亞流教義爭執時,這些多是在黑暗時期已經出現的發展現象。
「主宰政治」:政治威權=行政治理
所以晚期羅馬帝國許多體制及思潮已經在元首政治及黑暗時期開始萌芽發展,而戴克里先及君士坦丁則加以統整及系統化,變成晚期羅馬帝國的主宰政治,與黑暗時期前的元首政治有截然不同的風貌。整個成效可以從晚期羅馬帝國基本上解決了黑暗時期所面對的各種考驗:皇位繼承穩定、內戰歇止或偶爾發生、有效壓制通膨以及治理帝國等等。這些若沒有黑暗時期的基礎,勢必未定在天。
但這些要付出代價。「主宰政治」是個由上而下,將政治威權透過官僚化的治理,來延伸、擴散到帝國每位子民身上;每個人「理論上」都生活在皇帝監視下來「被治理」,生活在相對高度管制的社會中,與元首政治時期許多百姓可能會有「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感覺,或許很不一樣。現在皇帝不是「眾人之首」,而是遙遠、但十分強大,且無所不在、無不干預的「主人」(dominus),甚至是神明(deus)本尊或神的在世代理,有龐大有效的官僚體系協助他治理帝國,讓子民直接感受到皇帝那無比的威嚴。
如果帝國太大,那切割為二、為四,然後再將行省細切為更多省,派更多官員治理。這些不只是為了防止官員坐大,威脅皇權,因而蓄意將權力碎裂化;更是為了將皇帝的威權觸角延伸更廣、更有效治理、統治。正如庫利科斯基所言「興起的新騎士階級比之前的羅馬政府形式更深入行省生活」(頁一八四)。所以五世紀狄奧多西二世的法典編定前的最重要兩部法典,分別是戴克里先任內的荷默金尼斯(Hermogenes)及格雷戈里亞斯(Gregorius)所完成,這象徵將戴克里先的治理給合法化、合理化、系統化,甚至理性化。但這些改革並非從戴克里先一人憑空擘畫,而是由他從黑暗時代裡的前輩在政府治理、軍事部署、財政規劃、社會政策,甚至更抽象的宗教思想等各方面,來進行統整。他一方面確保帝國各項指令在根本上的一致,另方面更強調皇帝權威出現在帝國各地,皇帝指令被有效執行。這系統性的努力以及權力透過治理來散布,才是戴克里先四帝共治的新穎之處。君士坦丁及後繼者除了提倡基督教的宗教政策外,根本上是繼續這趨勢。我想沒有一件事會比君士坦丁決定放棄「舊羅馬」以及其所象徵的舊傳統,在三三○年建立並遷都君士坦丁堡的「新羅馬」和新傳統,來得更具象徵性:象徵晚期羅馬帝國的正式上場。
對《帝國的勝利》的一些意見
庫利科斯基的《帝國的勝利》成功陳述元首政治時期、黑暗時期及主宰政治時期的歷史延續性。他的敘事清晰條理,內容扎實詳細,令人在閱讀完後,能清楚掌握這段複雜的歷史,特別是充滿危機的黑暗時期其實並非那麼「黑暗」。黑暗時期是之前羅馬史連貫敘述的missing link;一些教科書喜歡強調黑暗時期的「軍營皇帝」出身巴爾幹偏遠行省、粗魯不文、不夠「羅馬」等等,因此一事無成,不值得「懷念」(missed)。但黑暗時期皇帝的成就經過庫利科斯基的敘述,融入到晚期羅馬帝國的主宰政治體制。無論如何,他的歷史絕非羅馬帝國「衰亡史」,而是清楚指認出三世紀那黑暗時期的問題解決努力「催生了全新的羅馬帝國」(頁三五二)。這是「帝國的勝利」。
我個人受益最多的是這段對我十分「黑暗」的二三五至二八四年危機時代。在閱讀後我欣賞在危機時代裡如加里恩努斯或奧勒良那種大破大立的「創造性毀滅」,有勇氣去想去問那傳統格局的人不敢碰的可能性,如羅馬為何需只由一人統治?為何如此強大的皇帝在世時何以不是神或神的在世代表?另外,庫利科斯基雖然焦點在羅馬,但第八章「歐亞歷史與羅馬帝國」將羅馬邊疆問題放在全球視野裡(雖然當代人或許不清楚這些複雜民族遷徙的更大圖像),使得羅馬史透過這些入侵外族,而成為世界史的一部分。羅馬滅亡後出現的三大文明:西歐日耳曼後繼國家、拜占庭帝國及伊斯蘭文明帝國,則又再次將晚期古代的羅馬帝國連接到更廣大的世界史。
翻譯者克服晚期羅馬那些十分繁複的官職名稱,但仍維持行文流暢,實在功不可沒。最後,本書選擇的圖片十分精美,說明也相當清楚,讓閱讀的經驗更加圓滿充分。但地圖集中在一處(原文即以如此),讓人必須時常回去翻閱查詢,有些不便。有些時候行文中提及的地名(如埃及尼羅河畔的托勒密城[Ptolemais])沒出現,反而出現它處的同名、但正文似乎沒提及的城市(如在利比亞的托勒密港)。不知是否製圖人將這兩地混淆?另外,我想本書若能有幾個皇帝系譜,那將更加完美,因為系譜能顯示出王朝結構,特別是君士坦提烏斯一世及君士坦丁一世各有兩次婚姻(他們的第二次婚姻使父子兩人有相同的岳父馬克西米安),對王朝後來的發展有極大影響。這本書中若能有以下王朝的系譜,一定更能促進理解:安東尼王朝、塞維魯王朝,以及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王朝。所幸這些都可以方便地在網路上找到。
我想大家都會如我一樣,衷心期待庫利科斯基《帝國的悲劇》能儘早出版,聽完這整段晚期古代歷史。
最後我說一些個人與庫利科斯基不同的看法,謹供大家指教。雖然彼得.布朗用文化史的角度開創「晚期古代」這領域,但庫利科斯基的《帝國的勝利》對黑暗時期裡的文化及宗教著墨較少,但這方面的成就相較之下其實是相對可觀,特別是教會史及哲學史方面。因此當進入到《帝國的勝利》君士坦丁王朝的教會爭議時,不熟悉早期教會史的讀者可能會覺得有些唐突,缺乏脈絡感。庫利科斯基在這方面著墨有限,或許可以辯稱說許多宗教及文化上的發展並非黑暗時期皇帝所直接導致的。這有道理。但若缺乏這些方面的陳述,總是會讓黑暗時期和晚期羅馬之間的聯繫少了些關鍵線索。這特別是因為君士坦丁在宗教政策上的一些決定,是與三世紀的教會有關。例如北非多納圖斯教派繼承二、三世紀之交特土良(Tertullian of Carthage)以降的強悍、不與世俗(這最後包括君士坦丁的羅馬帝國)妥協的北非聖靈教會傳統,堅持潔淨、小教派的想法,十分不利於君士坦丁統一帝國的普世教會理念。他因此在面對北非基督教時,沒選擇在北非人數更多的多納圖斯教派,而寧可偏袒在北非彷彿孤島的少數城邦菁英所接受的正統教會。
君士坦丁普世帝國及普世教會的理念也影響到他處理亞流教義。關於這點我個人覺得他雖可能受到歐西烏斯(Ossius of Cordoba)影響,但他自己對教義可能不是很堅持:他只想要帝國所有基督教徒都願意接受一個相同的教義,無論這是聖父聖子「本質相同」(homoousia)或多一個i 的聖父聖子「本質相似」(homoiousia),可能都一樣好,都能完成他一個上帝、一個教會、一個皇帝、一個帝國的理念。所以他才會在書信中要求主教們要能像哲學家一樣,對教義那種小問題能「彼此同意彼此不同意」(agree to disagree)!所以他可以在通過尼西亞信經不久後,輕易接受亞流回到教會(雖然後者在和解前突然暴斃);他也接受被定罪的亞流教義大將優西比烏(Eusebius of Nicomedia)違反尼西亞大公會議通過的教會法,像蝴蝶一樣從貝魯特斯(Berytus)轉調到尼科米底亞(Nicomedia),然後在君士坦丁堡完成後,再轉調到這「新羅馬」擔任主教,甚至為君士坦丁臨終洗禮。結果是:君士坦丁在晚期帝國正統教會史家筆下變成有些像是佛地魔那「不可說的名字」,因為他最後終究接受了異端的洗禮,使得他在教會史的歷史性貢獻被壓低或忽略。他身為皇帝不拘小節、求大格局的做法,我會覺得是更合理的說法。附帶一點,我對庫利科斯基對尼西亞信條最堅強的護衛者亞歷山卓主教亞他那修(Athanasius)的低評,一樣訝異和不解。
另外,我無法同意庫利科斯基對戴克里事先將馬克西米安及君士坦提烏斯一世都有親生兒子的事實,列入四帝共治的接班考量。如果君士坦丁在約克獲得他父親軍隊擁戴稱帝,那是因為血緣世襲原則以及他本人在現場,提供軍隊的誘惑實在難以抗拒,這應該不是原定接班計畫,而是「篡位」。相反地,我們何不認為君士坦丁之前被扣留在尼科米底亞當人質,正是戴克里先希望四帝共治的接班原則,不受血緣世襲的干擾?否則君士坦提烏斯何以在馬克西米安退位時,會直接選擇老戰友塞維魯當凱撒?
連帶地,我對君士坦丁何以會支持基督教的真正理由一向比較抱持著「不可知論」的立場,無法接受庫利科斯基將啟動「大迫害」的動機,關連到東方皇帝(特別是伽列里烏斯)為防止基督徒君士坦丁將繼承其父的皇位,因此啟動「大迫害」,宣布基督徒是非法,讓君士坦丁無法如願。我覺得史料似乎無法以持這樣的論點。
但這些個人意見絕不會降低我對《帝國的勝利》的adoratio(崇拜)。
《帝國的勝利:從哈德良到君士坦丁的羅馬世界》導讀
翁嘉聲
「晚期古代」的誕生
吉朋參觀羅馬廢墟時多所感慨,開始構想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他說若有機會在人類歷史中選擇一個自己要生活的時代,那會是從西元九六到一八○年羅馬五賢帝的「黃金時代」。但他也相信自己正處於衰落的時代,而羅馬帝國的命運似乎可以提供借鏡。《羅馬帝國衰亡史》的羅馬於是從黃金時代結束後開始衰亡,一直要等到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為止。他說衰亡是因為羅馬再也無法負荷她那「毫無節制的偉大」(immoderate greatness),再加上羅馬人皈依基督教以及野蠻外族同步入侵等的內憂外患。但有個疑問會立即浮現心中:羅馬的衰亡何以會長達千年之久?這是如何的衰亡呢?
吉朋認為羅馬帝國黃金時代結束後步入衰亡,淪落到中古基督教黑暗世界。如此「衰亡」概念其實是文藝復興學者最先提出來的。他們將歷史分為古代、中古及現代,並認為自己所處的現代初期是從中古黑暗世界中「復甦」、「復興」,是古典世界的「再生」。這種架構長期影響我們,而大學相關科系的課程結構也接受如此前提,推波助瀾,因為在五十年前歐美大學有關古典文化(classics)教學,反映出這樣的偏見。例如相關科系所教授的希臘文及拉丁文作品幾乎沒有二○○年之後的作家,而儘管(例如)拉丁文作品最多產的作家是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三五四至四三○年)。
另外,希臘羅馬古典歷史的教學強調政治、軍事及外交,而五賢帝時代結束後,羅馬帝國在這些方面每況愈下,因此五賢帝時期幾乎變成羅馬史教學的最後一章。此外,《劍橋古代史》第一版在一九二○年代起開始編輯,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最後一冊(第十二冊)最後一篇作者貝恩斯(Norman Baynes)說,當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亞宣布大公會議開始時,正式宣告歐洲中古時代的來臨。無論哪種說法,古代世界結束,直接進入中古世界,而且中古黑暗時期都來得相當早。
但牛津學者彼得.布朗(Peter Brown)在一九七一年出版《晚期古代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完全改變整個希臘羅馬古典歷史研究的格局。「晚期古代」這概念最先出現在十九世紀末藝術史研究裡,但現在被布朗用來劃分出一段古代世界逐漸轉變成中古時期的過渡時期,是段希臘羅馬古典異教文化及基督教文化融合、創造出屬於自己特色的時代。晚期古代的文化融合最後分別轉化為羅馬帝國西方的日耳曼後繼國家、羅馬帝國東方的拜占庭帝國,以及占有相當大羅馬幅員、沿用羅馬典章制度,但融合更多其他文化元素的伊斯蘭文明王朝。
布朗認為,晚期古代約從二五○至七五○年,是從羅馬「三世紀危機」或「黑暗時期」起(二三五至二八四年),到伊斯蘭阿巴斯(Abbasid)王朝在七五○年以巴格達為首都的五百年。哈佛學者格倫.博爾索克(Glen Bowersock)甚至將這段時間延長到八八八年卡洛琳王朝滅亡為止。因為晚期古代在知識領域上的出現,所以在一九七○年代重新編寫《劍橋古代史》第二版時,便將古代史結束時間延到皇帝莫里斯(Maurice,五八二至六○二年在位)被殺為止。如今「晚期古代」或(根據不同語境)「晚期羅馬帝國」或「早期拜占廷帝國」,已經是古典文化及古代史研究的顯學之一。
麥可.庫利科斯基(Michael Kulikowski)是專研這段晚期古代歷史的高手。他將這段複雜、但精采的晚期古代歷史分成兩部分來寫。本書《帝國的勝利:從哈德良到君士坦丁的羅馬世界》涵蓋哈德良於一一七年即位,到君士坦丁王朝(或稱為新弗拉維王朝)最後一位皇帝「叛教者」尤利安(於波斯遠征陣亡為止。這主要是討論晚期帝國的「主宰政治」(Dominate)型態如何出現以及有何特色。接下來的故事則出現在《帝國的悲劇:從君士坦丁到羅馬義大利的毀滅》(暫譯),交代其餘到約六○○年的故事。
台灣歷史教學及文化出版在介紹羅馬歷史時,常集中在共和時期及早期帝國,但晚期古代或晚期羅馬帝國史在內容上其實更加精采,除了羅馬帝國歷史本身外,還包括(例如)早期教會史、人才輩出的教父文學(patristics)、日耳曼民族歷史以及薩珊波斯歷史等等。這段歷史中出現的議題也常更具現代關連性,例如國家治理、宗教流變、教會與帝國、族群衝突及遷徙,和文明轉化及系統崩潰等等。庫利科斯基巨細靡遺的兩冊著作在馬可孛羅出版的翻譯及引介下,適時且適當地填補這段重要歷史該有的知識。
二三五至二八四年是羅馬史的暗黑山洞?
《帝國的勝利》詳細交代羅馬政治及體制如何歷經「元首政治」(Principate)時期的安東尼時代、塞維魯王朝、三世紀危機,到「主宰政治」(Dominate)時期的戴克里先改革,最後在君士坦丁王朝確立晚期帝國格式及規模的敘事史。 我們在學習及教授這段歷史時,時常面臨在塞維魯王朝結束,進入二三五至二八四年危機時代的羅馬黑暗時期時,立即陷入史料真空的黑暗狀態,以及面對不忍卒睹的帝國徹底混亂及失序的另種黑暗,因此常匆匆交代這羅馬黑暗時期的大致輪廓後,便急忙進入格局及氛圍截然不同的戴克里先改革及體制。或用個比喻說,我們從早期帝國的元首政治,通過二三五至二八四年這段時間的「暗黑的歷史山洞」,然後不知何故地在山洞另個開口,浮現出與之前不同的主宰政治,悄然開始晚期羅馬帝國的歷史。這種歷史斷裂感在一般羅馬史的敘述中常被強調,彷彿三世紀危機的時代是座隔屏,隔出一邊是好的帝國、鼎盛帝國、黃金時代,但另邊則是壞的、極權專制、高壓統治的中古黑暗時期。除了上述文藝復興及吉朋的影響外、這危機時代的文獻史料十分不足,而特別是羅馬帝國在這段時間面臨空前的艱巨挑戰,加起來形同「黑暗時期」。
但《帝國的勝利》這本書強調的不是絕望,因為羅馬帝國畢竟挺過去,進而開啟晚期古代的歷史。庫利科斯基藉助錢幣、碑銘、考古以及對文字史料的重新詮釋,加上他對羅馬人勇敢和創意的信心,使得這段之前大部分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時代,經過他的敘述後,變得相對清晰、正面。他指證出:羅馬領導人在二三五至二八四年危機時代中,勇敢面對多種併發的內外挑戰,開始或持續改造、轉化之前的元首政治,創造出新體制來應付變局。戴克里先從二八四年起復興帝國及完成的「主宰政治」,必須以這段黑暗時期的成果為基礎。庫利科斯基的目的是要填補這歷史斷裂,照亮這黑暗的歷史山洞,所以這段被吉朋認為是「衰亡史」初步階段的歷史,原本是黯淡、沮喪、甚至失敗的歷史,最後卻在庫利科斯基的寫作下,成為帝國的「勝利」。「勝利」若有所指,那或許應該指在二三五至二八四年充滿危機的時代中,羅馬克服種種挑戰,成功建立晚期羅馬帝國新政治體制的「勝利」。
與之前相關羅馬史研究相比,這樣的「勝利」是本書最大的貢獻。我最先百思不得其解,何以此書命名為《帝國的勝利》。若換成像是《羅馬帝國三世紀危機》、《羅馬黑暗時代》或《漫長的羅馬危機時代》,或許更能更符合部分主旨,但這些都無法傳遞作者認為那時代羅馬領導人顯示出的堅持、勇氣、創造力以及成就。
所以「元首政治」經過二三五至二八四年黑暗時期的危機,最後在戴克里先統整,再加上君士坦丁鞏固、確定「主宰政治」的體制。但那是如何的變化?我們首先要理解一下在這所謂危機時代「隔屏」兩側之一的「元首政治」(西元前二七至西元二三五年)是如何一回事,然後再論述羅馬黑暗時代如何面對危機提出對策,最後如何整合到戴克里先所啟動的「主宰政治」(二八四至六一○年)系統;如何從以結構簡單的城邦體制來統治幅員遼闊、族群複雜的世界,在經過黑暗時期的轉化後,變成以皇帝為中心,建立複雜的中央官僚機制來統治帝國。首先我們先說「元首政治」。
元首政治:政治威權≠行政治理
羅馬共和是寡頭政權,權力由人數有限的元老貴族把持。「共和」(Res Publica)是指這群少數人的共和,而「自由」(libertas)是這少數人爭權奪利的自由。其他平民則享有法律保障以及分享戰利品。羅馬在對外擴張過程中經常透過結盟方式,開放公民權給其他社區,因為這公民權擴大分享不會動搖寡頭統治的基礎,反而為羅馬帶來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提供更進一步擴張的基礎。這些盟邦菁英在自己社區裡經常複製羅馬的寡頭政體及制度,並主動效忠羅馬,為羅馬執行徵兵、徵稅等政府基本功能,同時治理地方。羅馬則以保障這些菁英的地位及福址來回饋。統治者與受統治者因此有相同的利益來一起經營羅馬這帝國共同體。即使奧古斯都在西元前二七年結束共和,開始元首政治,這種羅馬與盟友合作治理帝國的型態仍然持續,並在五賢帝時期到達顛峰。 羅馬以三十左右個專業兵團上提供「羅馬和平」(Pax Roman)的繁榮環境,保證忠誠的地方議員階級能夠創業積財,享有在地的政治地位及榮華富貴;在地菁英則投桃報李,深信效忠服務帝國是對自己的最好選擇,成為一群「願意的子民」(willing subjects)。所謂「羅馬化」(Romanization)常是帝國子民主動模仿羅馬、調整自己的結果。
因此二世紀小亞細亞希臘作家阿里斯提德斯(Aelius Aristides,一一七至一八一年)在獻給皇帝安東尼烏斯.庇烏斯的《論統治權力》(On Ruling Power)演說詞中,將羅馬比喻為城邦聯盟之首,正如奧古斯都是「同儕之首」。這種將羅馬帝國視為城邦聯盟的說法經常被嘲笑,但我認為卻是洞見,因為這隱含對羅馬帝國運作的一個理想化想像圖像,更是禮讚這套簡潔的政府治理藝術。這策略使得羅馬成為有史以來在帝國治理成本最為經濟的巨型政體。根據加恩西和沙勒(Garnsey & Saller)研究,在二世紀五賢帝(九六至一八○年)時期,帝國以不到兩百位官僚來經營五千萬人口和五百萬平方公里,而其所依賴的便是地方社區菁英階級主動願意與羅馬中央合作。
無論不到兩百這數字是否正確,重要的是羅馬的治理方式十分特殊,完全不同於我們常見頭重腳輕或由上而下的帝國治理方式,如晚期羅馬帝國主宰政治的中央集權便是典型例子:甚至當一位皇帝及集權官僚無法控制帝國時,則繼續將帝國一分為二、為四,但每個帝國所統轄的地區仍比現在法國或土耳其大上許多倍,因此需要複雜的官僚組織架構來治理。晚期羅馬皇帝權力透過這各層級的治理機構,滲透到帝國每個角落、落到帝國每位子民身上。但奧古斯都「元首政治」建立的早期帝國,卻充分利用地方社區的高度自治及菁英階級認同羅馬的心願,一起經營帝國。以比喻來說,元首政治的羅馬帝國像是現在流行的「雲計算」方式,數以千計組織簡單的地方城邦,在帝國網路裡擔任功能簡單的運算節點,配合絕佳軟體串連,同步進行運算,解決複雜問題。所以當元首政治時期的羅馬向帝國境內各地城邦發送如徵兵、徵稅指令,各地高度自治的議員階級菁英主動為羅馬效勞,自行吸收行政成本,執行普查、徵稅及徵兵的任務。相形之下,我們所熟悉的帝國,包括晚期羅馬帝國或像一些現代集權國家,則像部有強大處理器及大量隨取記憶體的超級電腦,藉著無所不在的大量官僚科層,以極大治理成本,到處派出官員執行法令。晚期羅馬帝國皇帝的政治威權透過行政治理而無所不在。
元首政治時期的羅馬帝國容許因地制宜及不同在地傳統的治理方式同時並存,極具彈性。因此我們見到在元首政治下,例如,皇帝和元老院分別管轄不同類型的行省,外加特殊地位的義大利及羅馬,還有由皇帝親派騎士出任總督的埃及。中央、行省及在地城邦也沒有明顯階層化情形,而治理方式及規範(特別是稅收)常因地制宜,尊重在地傳統,十分多樣。從受統治者的心理狀態來看,大部分羅馬帝國子民想必除了承認、心領神會遙遠羅馬皇帝那無比威嚴的政治威權外,其實甚少感受到「被羅馬統治」的實際治理,而是繼續生活在羅馬統治之前熟悉的環境中。簡單說:在「元首政治」的早期羅馬帝國中,皇帝或元首的「政治威權」,並未透過「行政治理」傳達下去。相對之下,在晚期羅馬帝國的每個帝國子民都透過官僚系統的行政治理,清楚感受到皇帝威權,深刻感覺自己是「被羅馬統治」。
這種被學者稱為元首政治時期的「雙重法律系統」(double legal systems)或甚至更多重的彈性,使得羅馬皇帝在面對新問題,需創造出新行政位置(nova officia)來面對時,變得更為方便,但這些主動權多落入皇帝手中。那些原來由元老院或地方所執行的功能,卻因為與元老院政治地位的滑落,以及羅馬從一九二年起(或更早)的動亂,社區開始萎縮,而逐漸處於被動,無法參與。所以我們會見到像是哈德良設法派任四位總督級官員治理義大利,降低其特殊地位到與其他行省地位相當;這種平等化(levelling)讓傳統心態的羅馬元老院極為不安不滿。另外,從圖拉真開始起,羅馬皇帝逐漸不再出身義大利,而是從伊比利、高盧、北非及帝國各地入主羅馬,更加重皇帝從帝國各地延引人才的趨勢。羅馬帝國變得愈來愈「帝國」,而愈來愈不「羅馬」。皇帝也不斷擴大在正規外的民事及刑事司法權。整個二世紀及三世紀初帝國治理的總體趨勢可以看出皇帝逐漸擴張權力,犧牲其他如元老院、人民及地方自治的權力。
這過程在塞維魯王朝更是加速,特別是皇帝權力在財政上大幅擴權。這一方面是塞維魯在皇位爭奪的內戰及之後的政治整肅中,沒收對手資產,數量大到必須設立專職單位處理。另方面,這時軍需不斷增加(如軍隊員額增加、屢次加薪及為籠絡軍心而頻繁出現的賞金),皇產及皇帝私產在國家財政上的比重愈來愈大,皇帝指派到各地的各類財務官員(procurators)愈形重要,甚至取代正式官員,在國家財政以及其他領域上的角色凌駕在傳統機構之上。但特別是二一二年卡拉卡拉的安東尼烏斯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的公布,使帝國內所有自由人均成為羅馬公民,更是將之前那複雜多樣、量身訂作、因地制宜的各種法律給均一化:在法律上,帝國內的每個人從此都直接是皇帝子民,適用相同的法律。塞維魯王朝中出現多位法學大家,常位居行政系統頂峰的禁衛軍統領;他們詮釋、編整法律以及管理帝國,都可理解為企圖理性化、合理化及體制化皇帝那愈來愈乾綱獨斷的絕對權力。之前元首政治中的種種特例、特權,現在逐漸被取消,而被整合到一個為皇帝服務的官僚系統中。法律文獻中逐漸浮現初以官員職權的概念來整合皇帝具體及詳細的法律權力,取代之前元首政治那種籠統代表元首特殊地位的「較高延任執政官權力」(imperium pronconsulare maius)及「護民官權力」(tribunicia potestas)的憲政地位。
庫利科斯基用「騎士化」(equestrianization)這名詞來形容這趨勢以及官僚系統的建立過程。這名詞當然主要是指帝國治理的人事。我們一向認為傳統元老會被摒除在外,主要是因為外省出身的皇帝不喜歡或蓄意打壓傳統羅馬菁英。但庫利科斯基認為,雖然元老菁英有時還是有無法接受是皇帝「僕人」這種有些「共和」的想法,但根本上還是因為他們無法在變局中勝任這些新變化。另方面,這些「騎士」來源廣泛,皇帝可以從全國選才,適才適用。因此除了傳統騎士階層(如經歷過「三種軍職」[tres militiae]的軍事基層歷練)出身者外,還包括那些軍隊行伍出身、脫穎而出者。這些人會受命去統治行省及率領軍隊,以致於所有兵團軍團長(legate)最後都是騎士階級或行伍出身,而沒有元老。另外,還有那些不屬於上述,但受過教育、有能力的各地人士,則擔任各地皇家財務官員,或在朝廷各部門及祕書處服務。皇帝在元首政治初期會使用家奴或解放奴(這所謂的familia Caesaris)擔任皇帝機要及部門負責人,這從塞維魯王朝起完全不見:所有為皇帝服務的人都是出身自由(ingenui)、常與皇家沒太多直接關連的人,而升遷多憑能力。帝國官僚系統正朝著理性化、體制化的目標前進。
晚期羅馬帝國如何從黑暗時期的挑戰與回應中學習
所以當二三五年塞維魯.亞歷山大被殺害,結束元首政治,馬克西米努斯拒絕到帝國中心的羅馬即位,象徵元老院與控制軍隊的皇帝的許多矛盾,之前雖曾藉著元首政治的偽裝來緩和,但現在正式終結。但這也立即導致三世紀危機中常見的「合法化危機」,約五十年的黑暗時期出現了二十六位皇帝、三位合法副皇帝以及四十一位僭位者;皇帝更迭不斷,政治十分動盪。黑暗時期的皇帝們究竟要如何確定合法或僭位?他們嘗試過王朝世襲或舉才收養,但更發展出將皇權與神明緊密連結(如奧勒良的「所向所向無敵太陽神」[Sol Invictus])。這在將在世皇帝視為神明,在元首時期原本只發生在那些被人認為瘋狂的壞皇帝,例如卡利古拉、尼祿、圖密善或康茂德身上,其中一些人還遭受死後「記憶抹煞」(damnatio memriae),但現在皇帝是神或神的在世代表,則是義正嚴詞、理所當然。
另外,皇帝認清遼闊帝國已經無法由一人從羅馬中央來指揮控制。所以加里恩努斯在父親瓦勒良兵敗波斯被俘後,接受帝國被割據成三塊(波斯杜姆斯的高盧、帕邁拉人奧登納圖斯的東方,及自己控制帝國其餘部分)來治理,並未企圖重新統一,坦然接受帝國分而治之是面對當代危機的方法。因此戴克里先「四帝共治」(tetrarchy)將帝國一切為二、為四,或君士坦丁最後由三位兒子分治帝國的政治體制,便是將黑暗時期這些君權合法化、穩定繼承,以及有效治理帝國的成果給統整起來而成為新的系統。在將皇權神聖化中,無論是戴克里先為四帝共治設計的朱比特(Jupiter)王朝及海克力斯(Hercules)王朝,或君士坦丁決定皈依基督教(無論他是否真正相信),都是奧勒良「所向無敵太陽神」的不同呈現;君士坦丁甚至在錢幣上使用「所向無敵太陽神」的圖像及頭銜。從這裡也開始發展出凡跟皇帝有關的都變成「神聖」,臣民只可遠觀、不可近褻;臣民無法再以元首政治時期的「致意」(salutatio)、而是必須以「崇拜」(adoratio)來接近被種種繁複威儀包圍的皇帝本尊。他們宛若神明。
但羅馬黑暗時期更承受同時且連續發生日耳曼民族、波斯及柏柏人從各方面入侵,所以軍事也是皇帝的重要關切。元首時期的三十個上下的兵團及人數相當的輔助兵團(auxiliaries)兵力規劃及部署設計,都是將軍力沿邊界安排,並假設這些外族入侵不會同時發生,因此軍力可以彼此調動支援,運用沿邊界修築的道路快速移動換防,堵住缺口,甚至越界出擊。但黑暗時期外族的同時入侵讓羅馬人措手不及,無力有效回應,因此發展出類似「縱深防禦」(defense in depth)的機動部署:羅馬皇帝一方面繼續沿用邊界駐紮邊防軍,擔任預警功能、初步阻擋及延緩入侵的功能;但同時在戰略地點集中部署機動打擊部隊,隨時反應打擊成功入侵的敵軍。機動性極高的輕、重裝騎兵因此變得極為重要,特別是在加里恩努斯任內;他廣泛雇用善騎的外族及裝配及更具彈性的任務編組來保護帝國。也因此,指揮騎兵的司令常權傾一時(如奧瑞魯斯),甚至問鼎皇位(如克勞狄烏斯二世和奧勒良)。戴克里先繼續沿用這規劃,但到君士坦丁則正式化為守邊的邊防軍(limitanesis)以及兩位分控騎兵及步兵的首長(magister equitum及magister peditum)所指揮的機動中央軍(Comitatensis),而都使用可能更高比例的外族。君士坦丁將黑暗時期發展出來的戰略及戰術給體制化。另方面,當君士坦丁在三一二年擊敗馬克森提烏斯,入主羅馬時,因為禁衛軍部隊曾支持他,因此被解散,而統領則被正式文職化,形同帝國行政及司法首長或是宰相(viceroy),但這禁衛軍統領文職化的趨勢早已在塞維魯王朝出現過。晚期帝國軍職及文職的兩種仕途確立,但晚期帝國高度的軍事化,使得文官也有軍階
黑暗時期也是羅馬經濟陷入極大困難的時代。農業及其他產業因為政治不穩、內戰頻仍及外族入侵,而受到很大破壞。元首政治時期經營地方的議員階級也因為經濟凋敝,再也無力、無意願負擔治理及建設地方,或配合中央徵稅徵兵。在黑暗時期除了防禦工事外(如奧勒良擴大羅馬城牆),甚少出現新公共建物;既有社區普遍萎縮到以自保為主的規模,或乾脆棄城。元首政治時期星羅棋布的城邦世界面貌,開始改變。財政現在完全專注在續命的軍隊維持上。但整個問題更被如脫韁野馬的通膨,弄得更難以對付。有學者認為二○○年時花費零點五第納里烏斯銀幣(denarius)能買到約五十公升(一個medimnos)穀物,到三○○年則必須花費三百第納里烏斯銀幣。換言之,主食在這一世紀的通膨率是六百倍。法定通貨的銀幣最後其實只是個位數百分比銀含量的洗銀銅幣。黑暗時期的皇帝一直想克服這通膨的問題,但解決通膨一向都是財政學的難題,至今仍是,所以在黑暗時期進展有限。
戴克里先繼承這樣的問題,但他多管道面對。他首先要了解帝國有多少資源,所以以土地及人頭做為稽徵單位來進行普查,計算出帝國有多少單位。他計算出全國所需預算(主要是軍需),然後除以這些人頭及土地單位後,按單位徵稅,部分以現物(包括當兵的「人」)來支付軍隊,部分以貴金屬。帝國每隔五年、之後每隔十五年,重新普查一次。如果說之前元首政治時期的國家財政常是「混過去」(muddle through),以臨時徵稅、沒收充公或如哲學家皇帝拍賣皇產來應急,那主宰政治則是首次以類似預算的理性方式來處理國家財政。而這能如此是因為自塞維魯王朝以來皇家財政官員大幅擴張,建立需要的機制來運作,這繼續在黑暗時期被保留運作,現在被戴克里先的改革正式體制化。這些工作在元首政治時期常由地方議會來進行,但現在則是由皇帝手下專職的財務官員來執行。普查、徵稅、徵兵等財政措施對一般帝國子民而言,想必是他們最有感的「政府治理」,直接充分具現何謂「羅馬威權」。雖然共和及元首政治時期的包稅法人團體(publicani)並未完全消失,但在晚期帝國皇帝的各類財務官員,形同我們的國稅局官員,來直接向我們要錢要人。
就統治者來看,為了方便控制資源,必須立法限制職業、身分及遷徙的變動。所以原來地方議員階級現在被迫繼續承擔他們愈來愈無能為力的任務,而其他不同行業也開始管制,甚至世襲。上述預算措施以及這些管制,使得我們有時稱呼晚期羅馬帝國採行所謂的「指令經濟」或「管制經濟」(command economy, dirigisme),以指令及管制方式來運作政府治理,特別是經濟。這也造成晚期羅馬是個高壓專制統治的形象。最能代表這種由上而下來運作「指令經濟」,莫若三○一年公布的「最高物價指令」(Edict of Maximum Prices)。這是戴克里先因為自己幣制改革無法解決通膨問題,所做出的新嘗試。在這道對多達一千四百件物品及服務項目設定最高價格的巨細靡遺指令中,貴金屬被定價相對地低,似乎暗示對貴金屬持有者(多是富人)較為不利,但這反而造成貴金屬變得稀缺,加劇通膨。最後君士坦丁(據說)沒收異教徒神廟數百年的廟產為儲備金,發行以一羅馬鎊七十二枚金幣為單位的通貨:solidus,解決這通貨不穩及通膨的問題。solidus直到十一世紀一直是地中海國家、拜占廷帝國,甚至伊斯蘭世界最受歡迎、最具公信力的通貨。今天在一英鎊金屬幣的邊緣,仍可看到solidus的字樣。
這時期在文化、道德及精神上雖也被認為是個危機時代,但大巨變下的精神生活是既豐富又躁動。多茲(E. R. Dodds)說這是「焦慮的時代」(Age of Anxiety);神廟籤文常看到對自己未來命運的忐忑不安:「我會變得如何?」或「我會被賣掉嗎?」這時期沒有與維吉爾(Virgil)或尤維納(Juvenal)齊名的古典作品留存。但學者注意到這時代出現所謂「禁欲衝動」(ascetic impulse),一種決定「跳脫離」(opt out)世界的決心;另外,認為宇宙最終只有一神,並在各民族各有化身的「單一神論」(henotheism)普遍流行,如已經提及的「所向無敵太陽神」。這些傾向在古典哲學上最終體現於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那摒棄物質世界,追求無限超越,如這思想的開山祖師普羅提諾(Plotinus)的巨作《九章集》(Enneads)。新柏拉圖主義除了促成晚期希臘哲學(Late Greek Philosophy)的發展外,更是將古典哲學導入到基督教神學,形成所謂的「柏拉圖基督教化」或「基督教柏拉圖化」的必要人物,啟發如拉丁西方聖安博若修(St. Ambrose of Milan)及聖奧古斯丁,但特別是希臘東方幾位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教父。這些人都是基督教文明吸收、轉化古典文明精華的代表關鍵人物。
另方面,黑暗時期也是基督教發展極為迅速的時候,出現古代希臘基督教最偉大的聖經學者及神學家俄利根(Origen)。黑暗時期的亞歷山卓及安提阿教會也分別對三位一體及基督論發展出各自的獨特觀點、傳統,甚至流派;羅馬和迦太基教會也對教會紀律問題(如再洗禮)表達不同觀點。最後,基督教會在度過德西烏斯皇帝二五一年及瓦勒良皇帝二五八年兩次全國大迫害後,在接下來的四十年的發展更加迅速、扎根更深,所以當三○三年戴克里先「大迫害」來臨時,基督教已經準備好面對這最後的全面性考驗。這些發展都指出:當君士坦丁決定支持基督教、面對北非多納圖斯教派紀律爭議以及處理東方的亞流教義爭執時,這些多是在黑暗時期已經出現的發展現象。
「主宰政治」:政治威權=行政治理
所以晚期羅馬帝國許多體制及思潮已經在元首政治及黑暗時期開始萌芽發展,而戴克里先及君士坦丁則加以統整及系統化,變成晚期羅馬帝國的主宰政治,與黑暗時期前的元首政治有截然不同的風貌。整個成效可以從晚期羅馬帝國基本上解決了黑暗時期所面對的各種考驗:皇位繼承穩定、內戰歇止或偶爾發生、有效壓制通膨以及治理帝國等等。這些若沒有黑暗時期的基礎,勢必未定在天。
但這些要付出代價。「主宰政治」是個由上而下,將政治威權透過官僚化的治理,來延伸、擴散到帝國每位子民身上;每個人「理論上」都生活在皇帝監視下來「被治理」,生活在相對高度管制的社會中,與元首政治時期許多百姓可能會有「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感覺,或許很不一樣。現在皇帝不是「眾人之首」,而是遙遠、但十分強大,且無所不在、無不干預的「主人」(dominus),甚至是神明(deus)本尊或神的在世代理,有龐大有效的官僚體系協助他治理帝國,讓子民直接感受到皇帝那無比的威嚴。
如果帝國太大,那切割為二、為四,然後再將行省細切為更多省,派更多官員治理。這些不只是為了防止官員坐大,威脅皇權,因而蓄意將權力碎裂化;更是為了將皇帝的威權觸角延伸更廣、更有效治理、統治。正如庫利科斯基所言「興起的新騎士階級比之前的羅馬政府形式更深入行省生活」(頁一八四)。所以五世紀狄奧多西二世的法典編定前的最重要兩部法典,分別是戴克里先任內的荷默金尼斯(Hermogenes)及格雷戈里亞斯(Gregorius)所完成,這象徵將戴克里先的治理給合法化、合理化、系統化,甚至理性化。但這些改革並非從戴克里先一人憑空擘畫,而是由他從黑暗時代裡的前輩在政府治理、軍事部署、財政規劃、社會政策,甚至更抽象的宗教思想等各方面,來進行統整。他一方面確保帝國各項指令在根本上的一致,另方面更強調皇帝權威出現在帝國各地,皇帝指令被有效執行。這系統性的努力以及權力透過治理來散布,才是戴克里先四帝共治的新穎之處。君士坦丁及後繼者除了提倡基督教的宗教政策外,根本上是繼續這趨勢。我想沒有一件事會比君士坦丁決定放棄「舊羅馬」以及其所象徵的舊傳統,在三三○年建立並遷都君士坦丁堡的「新羅馬」和新傳統,來得更具象徵性:象徵晚期羅馬帝國的正式上場。
對《帝國的勝利》的一些意見
庫利科斯基的《帝國的勝利》成功陳述元首政治時期、黑暗時期及主宰政治時期的歷史延續性。他的敘事清晰條理,內容扎實詳細,令人在閱讀完後,能清楚掌握這段複雜的歷史,特別是充滿危機的黑暗時期其實並非那麼「黑暗」。黑暗時期是之前羅馬史連貫敘述的missing link;一些教科書喜歡強調黑暗時期的「軍營皇帝」出身巴爾幹偏遠行省、粗魯不文、不夠「羅馬」等等,因此一事無成,不值得「懷念」(missed)。但黑暗時期皇帝的成就經過庫利科斯基的敘述,融入到晚期羅馬帝國的主宰政治體制。無論如何,他的歷史絕非羅馬帝國「衰亡史」,而是清楚指認出三世紀那黑暗時期的問題解決努力「催生了全新的羅馬帝國」(頁三五二)。這是「帝國的勝利」。
我個人受益最多的是這段對我十分「黑暗」的二三五至二八四年危機時代。在閱讀後我欣賞在危機時代裡如加里恩努斯或奧勒良那種大破大立的「創造性毀滅」,有勇氣去想去問那傳統格局的人不敢碰的可能性,如羅馬為何需只由一人統治?為何如此強大的皇帝在世時何以不是神或神的在世代表?另外,庫利科斯基雖然焦點在羅馬,但第八章「歐亞歷史與羅馬帝國」將羅馬邊疆問題放在全球視野裡(雖然當代人或許不清楚這些複雜民族遷徙的更大圖像),使得羅馬史透過這些入侵外族,而成為世界史的一部分。羅馬滅亡後出現的三大文明:西歐日耳曼後繼國家、拜占庭帝國及伊斯蘭文明帝國,則又再次將晚期古代的羅馬帝國連接到更廣大的世界史。
翻譯者克服晚期羅馬那些十分繁複的官職名稱,但仍維持行文流暢,實在功不可沒。最後,本書選擇的圖片十分精美,說明也相當清楚,讓閱讀的經驗更加圓滿充分。但地圖集中在一處(原文即以如此),讓人必須時常回去翻閱查詢,有些不便。有些時候行文中提及的地名(如埃及尼羅河畔的托勒密城[Ptolemais])沒出現,反而出現它處的同名、但正文似乎沒提及的城市(如在利比亞的托勒密港)。不知是否製圖人將這兩地混淆?另外,我想本書若能有幾個皇帝系譜,那將更加完美,因為系譜能顯示出王朝結構,特別是君士坦提烏斯一世及君士坦丁一世各有兩次婚姻(他們的第二次婚姻使父子兩人有相同的岳父馬克西米安),對王朝後來的發展有極大影響。這本書中若能有以下王朝的系譜,一定更能促進理解:安東尼王朝、塞維魯王朝,以及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王朝。所幸這些都可以方便地在網路上找到。
我想大家都會如我一樣,衷心期待庫利科斯基《帝國的悲劇》能儘早出版,聽完這整段晚期古代歷史。
最後我說一些個人與庫利科斯基不同的看法,謹供大家指教。雖然彼得.布朗用文化史的角度開創「晚期古代」這領域,但庫利科斯基的《帝國的勝利》對黑暗時期裡的文化及宗教著墨較少,但這方面的成就相較之下其實是相對可觀,特別是教會史及哲學史方面。因此當進入到《帝國的勝利》君士坦丁王朝的教會爭議時,不熟悉早期教會史的讀者可能會覺得有些唐突,缺乏脈絡感。庫利科斯基在這方面著墨有限,或許可以辯稱說許多宗教及文化上的發展並非黑暗時期皇帝所直接導致的。這有道理。但若缺乏這些方面的陳述,總是會讓黑暗時期和晚期羅馬之間的聯繫少了些關鍵線索。這特別是因為君士坦丁在宗教政策上的一些決定,是與三世紀的教會有關。例如北非多納圖斯教派繼承二、三世紀之交特土良(Tertullian of Carthage)以降的強悍、不與世俗(這最後包括君士坦丁的羅馬帝國)妥協的北非聖靈教會傳統,堅持潔淨、小教派的想法,十分不利於君士坦丁統一帝國的普世教會理念。他因此在面對北非基督教時,沒選擇在北非人數更多的多納圖斯教派,而寧可偏袒在北非彷彿孤島的少數城邦菁英所接受的正統教會。
君士坦丁普世帝國及普世教會的理念也影響到他處理亞流教義。關於這點我個人覺得他雖可能受到歐西烏斯(Ossius of Cordoba)影響,但他自己對教義可能不是很堅持:他只想要帝國所有基督教徒都願意接受一個相同的教義,無論這是聖父聖子「本質相同」(homoousia)或多一個i 的聖父聖子「本質相似」(homoiousia),可能都一樣好,都能完成他一個上帝、一個教會、一個皇帝、一個帝國的理念。所以他才會在書信中要求主教們要能像哲學家一樣,對教義那種小問題能「彼此同意彼此不同意」(agree to disagree)!所以他可以在通過尼西亞信經不久後,輕易接受亞流回到教會(雖然後者在和解前突然暴斃);他也接受被定罪的亞流教義大將優西比烏(Eusebius of Nicomedia)違反尼西亞大公會議通過的教會法,像蝴蝶一樣從貝魯特斯(Berytus)轉調到尼科米底亞(Nicomedia),然後在君士坦丁堡完成後,再轉調到這「新羅馬」擔任主教,甚至為君士坦丁臨終洗禮。結果是:君士坦丁在晚期帝國正統教會史家筆下變成有些像是佛地魔那「不可說的名字」,因為他最後終究接受了異端的洗禮,使得他在教會史的歷史性貢獻被壓低或忽略。他身為皇帝不拘小節、求大格局的做法,我會覺得是更合理的說法。附帶一點,我對庫利科斯基對尼西亞信條最堅強的護衛者亞歷山卓主教亞他那修(Athanasius)的低評,一樣訝異和不解。
另外,我無法同意庫利科斯基對戴克里事先將馬克西米安及君士坦提烏斯一世都有親生兒子的事實,列入四帝共治的接班考量。如果君士坦丁在約克獲得他父親軍隊擁戴稱帝,那是因為血緣世襲原則以及他本人在現場,提供軍隊的誘惑實在難以抗拒,這應該不是原定接班計畫,而是「篡位」。相反地,我們何不認為君士坦丁之前被扣留在尼科米底亞當人質,正是戴克里先希望四帝共治的接班原則,不受血緣世襲的干擾?否則君士坦提烏斯何以在馬克西米安退位時,會直接選擇老戰友塞維魯當凱撒?
連帶地,我對君士坦丁何以會支持基督教的真正理由一向比較抱持著「不可知論」的立場,無法接受庫利科斯基將啟動「大迫害」的動機,關連到東方皇帝(特別是伽列里烏斯)為防止基督徒君士坦丁將繼承其父的皇位,因此啟動「大迫害」,宣布基督徒是非法,讓君士坦丁無法如願。我覺得史料似乎無法以持這樣的論點。
但這些個人意見絕不會降低我對《帝國的勝利》的adoratio(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