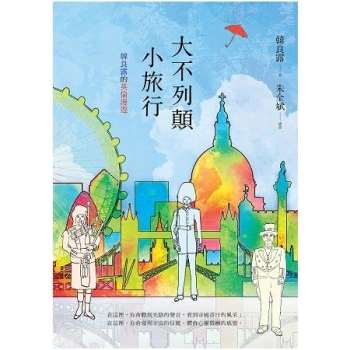艾芳河上的莎士比亞鎮—史特拉福
《羅蜜歐與茱麗葉》、《馬可白》、《仲夏夜之夢》是誰寫的? 這個問題對一般英國人而言,簡直是太侮辱心智了,稍微受過教育的人,誰會不知道莎士比亞?
然而,在英國,卻也有一小撮的人,他們認為大部分公眾相信的事情未必一定是真相,這些人組成了一個「培根協會」,他們認為所謂莎翁的戲劇,其實並非莎士比亞所寫,而是法蘭西斯.培根(Francais Bacon)匿名莎士比亞創作的。
當我人在艾芳河上的史特拉福鎮(Straford-upon-Avon)的莎士比亞博物館前,有位穿著得體、談吐不俗的老先生遞了張印刷文件給我,我拿過來一看,是「培根協會」出版的,上面登了一篇文章,大意是在探討,為什麼十七世紀初期英國大韻文家培根為文的風格與莎翁的名著那麼接近? 而培根本是當代飽學多聞的名士,對歷史、皇室典故、文學、戲劇都學有專長,但在劇場任演員、導演的莎士比亞卻只是一介平民,沒受過太多的教育,也沒發表過作品。而最啟人疑竇的是,為什麼當培根停止以培根之名發表作品的同時(因培根得罪了當朝權貴,上了黑名單),卻開始出現大量以莎士比亞為名的劇作? 培根協會認為是培根寫成了劇本,但交給莎士比亞去演出。
這件歷史公案迄今仍無解,雖然英國人喜歡說「真理是時間的女兒」,也許對培根或莎士比亞而言,時間還沒長到可以讓這件謎團的真相誕生。而也許,這件謎案要派英國當代的推理小說家而非歷史學家來解謎才成。
我看完了文件,我身後一對像我一樣在排隊進入莎翁博物館的美國夫婦,也剛看完「培根協會」的宣傳品,我問他們對此事的想法,那個太太的回答很有趣。她說,人們都喜歡傳奇,莎翁劇作如果是有名的上層階級的仕紳培根所寫就一點也不特別,但因為是沒沒無名的莎士比亞所寫,才更讓人覺得莎士比亞是天才。莎翁博物館位於史特拉福市區中心的翰利街(Henley St.)上,是一棟兩層樓加一層閣樓木造的都鐸式建築。據歷史記載,莎士比亞是在一五六四年的四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六日誕生於此地。目前這棟房子分成兩區,一區展示了莎翁生平的遺物及相關資訊(如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演出),另一區則重現了十六世紀末的家庭生活情景。這棟房子的天花板很矮,顯示了當年一般人的普遍身高,我身後的美國男人得一直縮著脖子,狀極辛苦。在標明為莎士比亞誕生的那個房裡(誰知道是不是真的?),木窗玻璃上有一些英國歷代文人的簽名,上面有卡萊爾(Thomas Carlyle)、史考特爵士(Walter Scott)……他們在這留下到此一遊的題字,恐怕是希望自己的聲名能如莎士比亞般巨大和永恆吧!
史特拉福留下了不少都鐸式的建築,散步在市中心的主街(High St.)、教堂街(Church St.)石板路上,看著身邊一棟一棟古老的白牆黑木條裝飾的房子,心情就會飛揚起來。都鐸王朝因為血腥瑪麗都鐸(Bloody Mary Tudor)的關係,並不是個讓人愉快的時代,但奇怪的是,都鐸王朝時的建築都呈現出某種童話的氣氛,每棟房子的外牆上橫直排列的黑木,都好像塗上墨汁的牙齒一般有趣。
有些英國人譏笑史特拉福如今已成了「莎士比亞企業鎮」(Shakespear IndustryCountry)。的確,鎮上主街有不少商家在賣莎翁的紀念品,但只要離開亨利街遠一點,史特拉福立即顯出了自己的韻味。對於肯多走兩步路的旅客而言,走上艾芳河的堤岸,就立即會進入仍有中世紀牧歌般的田園情調之中,艾芳河岸上的細小黃花在風中吹拂著,河上有人在撐平底船(Punt),有空閒的人不妨坐一趟艾芳河之旅。
在離史特拉福二公里遠的鄉村中,有一棟伊麗莎白王朝村舍,屋頂仍用茅草覆頂,屋前有一個百花齊放的花園,這裡就是莎士比亞的妻子安.海瑟威(Anne Hathaway)的家,這棟村舍保存得非常好,室內仍照十六世紀末期的陳設布置在這裡。和莎士比亞已結婚的安獨居了十六年,一直到莎士比亞從倫敦返鄉後,兩個人才一起另找了一棟房子度晚年。從安的房子,可以坐巴士,也可以沿著路標走回市中心。有時間的旅人不妨沿著鄉村小路走回去,一路上的田野風景十分秀麗,別忘了這裡是英國人最喜歡退休的柯茲窩丘陵區(Cotswolds)。回程的路上會遇到幾家鄉村酒館,走累了可以歇腳喝一杯英式啤酒,聽聽當地老人說的一種特殊的柯茲窩口音的英語,也許莎士比亞當年也說這樣口音的老式英語吧!
一般觀光客到史特拉福是不過夜的,但史特拉福的夜晚卻十分美麗,因為大部分旅客走了,小鎮變得較安靜,走在鎮上古老的都鐸老街,會有一種步入時光隧道之感。再加上晚上可以在莎翁出生地,看一場由皇家莎士比亞劇場演出的莎翁戲,尤其有味道。
皇家莎士比亞劇場在史特拉福有三所劇院,在每年四月至十一月之間演出,分成下午場及晚場演出,大部分的票在演出前都售光,因此最好事先預約,以免撲空。
釣河鱒的幽靜小鎮—馬羅
馬羅(Marlow)離溫莎(Windsor)不遠,從派丁頓(Paddington)坐火車約一小時即可抵達,中間要換一種小火車,還是老式木頭坐椅,很有古老風味。這班小火車最後會開過一條兩邊是鄉村原野的火車道,景觀十分美麗,每次都令我心動不已。這一小段綠色景觀,是我在倫敦看過最美的風光,其中綠色風景的變幻萬千,彷彿有上百種不同的綠在眼簾上跳動。
馬羅是很富裕的村莊,但一點都不招搖,當地居民知識水平很高,光從主街上的小小商店就可看出,有不少古董店、珍本書店、精美家飾店等等。還有當地特色商店─漁具店。
馬羅是倫敦釣河鱒的著名之地,當地有個旅館,就叫「道地釣客旅棧」(Macdonald Compleat Angler),還提供釣河鱒的課程。河鱒只能生長在水流清澈之處,也因此可見當地對生態保育工作一定很注重,否則河鱒早就絕種了(就像新店溪的香魚的命運)。
在英國釣魚是要有執照的,但旅館會幫客人準備一種一天的執照,也會囑咐客人要遵守政府制定的規定,例如魚在產卵的季節不能釣,以及長不到足夠尺寸的魚釣了上來後要放生等等。
釣河鱒的人,喜歡用「假蚊甩竿」(Fly Fishing)的方法,這也是目前英國上層階級瘋狂著迷的閒暇嗜好。很多企業鉅子認為從假蚊甩竿學到的人生哲學,遠甚於高爾夫。我的英國朋友尼克就是個假蚊甩竿迷,他老家在英格蘭北方的諾丁翰(Nottingham),那裡有不少釣河鱒的荒僻溪流,搬來倫敦住的他,平日難得回老家過釣魚癮,因此常常在泰晤士河支流做週末釣客。
我一直央求他帶我去做一日釣客,後來他答應了,但他說要選擇較安全之處,因為釣河鱒者,常常必須站在溪流中,而溪水的石塊十分滑溜,因此要慎選較平緩的溪流。
離馬羅鎮上不遠,就是泰晤士河的支流,路段平緩,溪水不急,兩岸老樹遍布,垂柳依依,身入其中,十分幽靜。
尼克選了一處下風段,他告訴我釣河鱒的人一定要懂得判斷風向,永遠不要在上風下竿。
去過一次馬羅後,我就愛上了這個地方。但我後來再去馬羅,都不是去釣魚,畢竟我不是道地釣客,可是我喜歡沿著幾乎無人跡的溪流旁的小徑散步。春日的荒草中會長著黃色的水仙花,細嫩的花莖在風中飄搖,空氣中滿是溪水的綠藻清香,徜徉在這樣的鄉村風光中,馬上讓人有置身桃花源之感。
這樣的環境,離馬羅的主街不過二十分鐘散步之遠,意味著住在這裡的人,只要願意,誰都可以隨時享有恬靜的田園時間。但走上了主街,又有各家精緻的商店,提供文明的愉悅。
主街上自然有茶館,可以悠閒地享有一頓英式下午茶,如果想過過豐盛的下午茶宴,多花點錢就可以去「道地釣客旅棧」。那裡的下午茶很出名,有些倫敦客會專門在週末前來,只為坐在草坪上,一邊看著河岸風光,一邊享用由精緻英國瓷器盛放的黃瓜三明治、鬆餅和蛋糕。
馬羅一日遊,是我在倫敦客居生活中偶爾會寫的綠色日記,那些流水、草徑、樹林、沼澤,每次都讓我的心靈變得清新了。
英國海上的美食家樂園—澤西島
英國的冬天日短夜長,常常下午四點鐘天就黑了,因此有些日照不足的人就容易患上冬日憂鬱症,而要對抗憂鬱最好的辦法就是曬太陽。所以,冬天一到,許多英國人見面時最喜歡聊的話題就是去哪曬太陽,這些英國人常被比喻為候鳥,一到冬天就往南飛,飛去西班牙、突尼西亞、賽普勒斯。我剛到倫敦的前兩年,一點都不覺得冬天有什麼好憂鬱的,在台灣時見慣亞熱帶的冬天,倫敦的冬天剛好成了我的新歡。我喜歡走在海德公園的落葉步道上,一路踩著乾脆的黃葉發出刷刷響聲,呼吸著冷冽的空氣,張嘴還可以吐出一口白霧,這種樂趣,只有念小學台灣比較冷時才能玩的花樣,如今又可以在倫敦重溫了。
可是好景不常,到了第三年,就像花粉熱會突然上身,冬日憂鬱症也逮捕了我!過了一星期垂頭喪氣的日子後,我終於向全斌說我想曬太陽了,但全斌當時剛好在趕學校論文,不宜大動作地跑去西班牙或突尼西亞,他希望我們的陽光假期可以三天兩夜打發,而且不要跑得太遠。
我看著家中的英國地圖,突然想到何不就去聞名已久的澤西島(Jersey Island)?
位於英吉利海峽群島中的最大島澤西,因為地理位置偏南,冬季日照較足,因此吸引了不少退休人士。
但在澤西島退休並不容易。這個島是免稅天堂,有錢人定居或退休於此可以避稅,但澤西島是大不列顛王國的皇家屬地並非本土,有自己獨立的經濟系統,其他不列顛子民是不能說要來此地定居就定居,必須得到當地政府的允可。然而當地政府只收有錢人,因此申請移民的人,身家沒有幾百萬英鎊以上的人是很難獲准的。
澤西島有不少美麗的別墅住家,都是占地數畝的豪宅,但因其依據地形蓋得很隱密,所以不顯招搖。這些豪宅都是數百萬至千萬英鎊的價格,大部分豪宅都有自己的農園、山丘和私人海濱,讓有錢人既可避稅,又可避世。
但要欣賞澤西島的海島風景,並不需要花很多錢,因為在一九二○、三○年代,當時還不流行有錢人移居澤西島,為了因應英國大眾旅遊的市場,澤西島蓋了非常多的海濱渡假旅館,有的旅館十分豪華,有的只是小規模的民宿,但這些旅棧後來都沒落了,因為英國大眾後來流行出國曬太陽。澤西島溫和的陽光和海風以及不能游泳的崎嶇礁石海岸,只能吸引五、六十歲以上的退休老人了。我和全斌住進了一間攝政時期風格的白色木造大旅館,旅館的天花板很高,有許多木製的大窗,陽光會穿過木格及白紗簾灑在長條的老式地板上。旅館有個中庭花園,養著一些英國不易見到的厥類植物,花園旁有個木頭架起的露台,可以坐在那望著波光粼粼的大海。
這麼美好的旅館,如今卻沒落了,因此旅館的細部充滿了年久失修的痕跡,有一種昔日美人如今滄桑的味道。但對我而言,這種年華不再的旅館卻有種特別的感覺,走在如今客人稀少,空盪蕭瑟的旅館大廳及走廊上,我都覺得可以嗅聞得到昔日時光殘留的味道。
來到了澤西,我的心情馬上轉好,其實不只是這裡的陽光較倫敦明麗,我敏感的鼻子馬上聞出澤西的食物一定好吃。
澤西島四面環海,靠近的又是法國的不列塔尼海岸,而法國的不列塔尼,一向以出產優質的龍蝦、生蠔、螃蟹、貽貝出名,澤西島當然也以這些海產出名。但比起不列塔尼,澤西島還有另一個優勢,因為澤西島自古以來就有優良的畜牧業及農業的傳統。有種澤西牛,一向採自然放牧,肉質甜美,不輸蘇格蘭有名的安格斯牛。在九○年代初的那些年,英國大受狂牛症的威脅,因此許多人不敢吃英格蘭北部過度擁擠的人工圈養牛,但澤西牛產量少,幾乎不外銷外地,不像蘇格蘭安格斯牛到處吃得到,更顯出澤西牛的尊貴。
澤西牛的肉質佳,牛奶也好,因此澤西鮮奶油也很出名,比起有名的德文郡及康瓦爾的鮮泡奶油,也因量少而更稀奇。再加上澤西島種植的有機小馬鈴薯、小番茄,都是倫敦美食超市中的昂貴嬌客。
除了自然因素外,澤西島之所以有「英國的海上美食家樂園」這樣的封號,還有幾項特殊的人文因素,造成她擁有獨特的美食傳統。首先,它的地理位置及歷史因緣一直與法國密切相關,澤西島上有些人迄今還能追溯到他們的法國貴族遠親。這些人的祖先有不少是躲避法國大革命而流亡的貴族,像雨果當年遭流放,就是被囚禁在澤西島旁的另一小島(根西島)。
由於法國的淵源,使得法國烹飪藝術一直是澤西料理的靈魂。除了法國之外,從二十世紀中葉起,不少義大利北部的餐飲世家也到澤西島落地生根,並帶來了優良的義大利烹飪傳統。不過,真正使澤西料理享有國際知名度的,倒不是以上的自然及人文因素,而是市場因素。澤西島是國際聞名的避稅金融天堂,小小的市區內有上百家國際知名的銀行在此設立岸外免稅銀行,因此,每年富商巨賈、高級行政人員拜訪澤西的人數眾多,再加上移居澤西島的有錢島民,這些人都是懂吃,又花得起錢的美食家,自然帶動了澤西島的美食文化。
澤西島美食出名,但最讓人高興的,是這裡的美食價格一向以合理出名,尤其和高物價的倫敦相比,澤西島的美食就顯得格外物美價廉。
當我在旅館住定後,傍晚沿著礁岩海邊散步,好讓肚子餓一點後再大啖美食,當天晚上我已經預定好一家我在倫敦的友人向我大力推薦的,以賣炭烤澤西牛排出名的餐廳。
在這家叫Rosalino Rocque 的餐館,我吃到了一生中吃過最好吃的炭烤菲力牛排,五分熟的牛排,表面有一層微焦的煙醺硬皮,又香又有嚼勁,內層是酒紅色又甜又嫩的牛肉,吃這道牛排是連鹽及黑胡椒都不用加的,完完全全的原味。吃完這樣的牛排,我都想為了人類美食而犧牲的澤西牛致敬了。
吃完了澤西牛排,我又吃了由澤西奶油做成的手工冰淇淋,也是好吃得沒話說。最後我滿足地坐在椅子上,幾乎陷入冥想狀態,這頓美食經驗,讓我彷彿瞥見了天堂樂園的形狀。
旅館第二天提供的早餐也值得一書。我曾在毛姆(W. Somerset Maugham)及克莉絲蒂的小說中,看過英國上流社會古典早餐,是和今日的英式早餐不太相同的。因為上流階級的人很早就有健康意識,因此,他們是不吃被喻為吃了會得心臟病的英式早餐(想想看,油淋淋的雙蛋及鹹肉培根,卡路里多高啊!)。那麼,上流階級吃的早餐是什麼呢? 這家沒落的豪華旅館提供的早餐,正好解決了我的疑問。
當天早上,我和外子全斌坐在整間白牆、白桌、白椅、白桌布,吊著白色水晶燈,侍者著白衣黑褲,在我們桌上的白色鑲銀邊的骨瓷盤中放下蒸過的一片鹹鮭魚、一粒完全沒油的水泡蛋、水煮的澤西島小番茄、小馬鈴薯及嫩蘆筍,再配上一碗澤西牛奶煮成的燕麥粥(Porridge)及一碗水煮甜桃。這樣的早餐,真讓人喜歡早起。第二天中午,我去了有名的Jersey Pottery Restaurant 吃到了冬天盛產的生蠔當前菜,而主菜叫了各式炭烤海鮮,從炭烤烏賊到帶子、旗魚、海鱸、和尚魚等等,都是新鮮得有如海邊剛釣上來的海產(至少是當天上午才捕獲的)。之後,吃澤西島溫室產的小粒鮮草莓加澤西鮮奶油。第二天的晚餐,我們去了當地剛得到米其林一星的朗格維利莊園酒店(Longueville Manor Hotel)的餐廳。這家飯店以前是一棟十三世紀的領主莊園,充滿了中世紀古老風情,餐廳的裝潢十分華麗正式,有如中世紀貴族的晚宴廳。這家餐館以澤西海鮮出名,我們叫了美味極了的海鮮濃湯,又吃起司烤生蠔當前菜,主菜是清蒸澤西鰈魚,因為加了白酒一起蒸,味道比港式青衣還細膩。
在澤西島待了三天兩夜,我完全沉沒在美食的歡愉中,到了不得不離開的時候,我問全斌想不想來這裡退休,全斌的答案是「不」。因為這幾天,他帶來要完成的工作都沒做,日子太好過了,而人最好不要活在太享樂的地方。這句話也有道理,因此,才會讓如今在台北的我,深深懷念著澤西島。
《羅蜜歐與茱麗葉》、《馬可白》、《仲夏夜之夢》是誰寫的? 這個問題對一般英國人而言,簡直是太侮辱心智了,稍微受過教育的人,誰會不知道莎士比亞?
然而,在英國,卻也有一小撮的人,他們認為大部分公眾相信的事情未必一定是真相,這些人組成了一個「培根協會」,他們認為所謂莎翁的戲劇,其實並非莎士比亞所寫,而是法蘭西斯.培根(Francais Bacon)匿名莎士比亞創作的。
當我人在艾芳河上的史特拉福鎮(Straford-upon-Avon)的莎士比亞博物館前,有位穿著得體、談吐不俗的老先生遞了張印刷文件給我,我拿過來一看,是「培根協會」出版的,上面登了一篇文章,大意是在探討,為什麼十七世紀初期英國大韻文家培根為文的風格與莎翁的名著那麼接近? 而培根本是當代飽學多聞的名士,對歷史、皇室典故、文學、戲劇都學有專長,但在劇場任演員、導演的莎士比亞卻只是一介平民,沒受過太多的教育,也沒發表過作品。而最啟人疑竇的是,為什麼當培根停止以培根之名發表作品的同時(因培根得罪了當朝權貴,上了黑名單),卻開始出現大量以莎士比亞為名的劇作? 培根協會認為是培根寫成了劇本,但交給莎士比亞去演出。
這件歷史公案迄今仍無解,雖然英國人喜歡說「真理是時間的女兒」,也許對培根或莎士比亞而言,時間還沒長到可以讓這件謎團的真相誕生。而也許,這件謎案要派英國當代的推理小說家而非歷史學家來解謎才成。
我看完了文件,我身後一對像我一樣在排隊進入莎翁博物館的美國夫婦,也剛看完「培根協會」的宣傳品,我問他們對此事的想法,那個太太的回答很有趣。她說,人們都喜歡傳奇,莎翁劇作如果是有名的上層階級的仕紳培根所寫就一點也不特別,但因為是沒沒無名的莎士比亞所寫,才更讓人覺得莎士比亞是天才。莎翁博物館位於史特拉福市區中心的翰利街(Henley St.)上,是一棟兩層樓加一層閣樓木造的都鐸式建築。據歷史記載,莎士比亞是在一五六四年的四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六日誕生於此地。目前這棟房子分成兩區,一區展示了莎翁生平的遺物及相關資訊(如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演出),另一區則重現了十六世紀末的家庭生活情景。這棟房子的天花板很矮,顯示了當年一般人的普遍身高,我身後的美國男人得一直縮著脖子,狀極辛苦。在標明為莎士比亞誕生的那個房裡(誰知道是不是真的?),木窗玻璃上有一些英國歷代文人的簽名,上面有卡萊爾(Thomas Carlyle)、史考特爵士(Walter Scott)……他們在這留下到此一遊的題字,恐怕是希望自己的聲名能如莎士比亞般巨大和永恆吧!
史特拉福留下了不少都鐸式的建築,散步在市中心的主街(High St.)、教堂街(Church St.)石板路上,看著身邊一棟一棟古老的白牆黑木條裝飾的房子,心情就會飛揚起來。都鐸王朝因為血腥瑪麗都鐸(Bloody Mary Tudor)的關係,並不是個讓人愉快的時代,但奇怪的是,都鐸王朝時的建築都呈現出某種童話的氣氛,每棟房子的外牆上橫直排列的黑木,都好像塗上墨汁的牙齒一般有趣。
有些英國人譏笑史特拉福如今已成了「莎士比亞企業鎮」(Shakespear IndustryCountry)。的確,鎮上主街有不少商家在賣莎翁的紀念品,但只要離開亨利街遠一點,史特拉福立即顯出了自己的韻味。對於肯多走兩步路的旅客而言,走上艾芳河的堤岸,就立即會進入仍有中世紀牧歌般的田園情調之中,艾芳河岸上的細小黃花在風中吹拂著,河上有人在撐平底船(Punt),有空閒的人不妨坐一趟艾芳河之旅。
在離史特拉福二公里遠的鄉村中,有一棟伊麗莎白王朝村舍,屋頂仍用茅草覆頂,屋前有一個百花齊放的花園,這裡就是莎士比亞的妻子安.海瑟威(Anne Hathaway)的家,這棟村舍保存得非常好,室內仍照十六世紀末期的陳設布置在這裡。和莎士比亞已結婚的安獨居了十六年,一直到莎士比亞從倫敦返鄉後,兩個人才一起另找了一棟房子度晚年。從安的房子,可以坐巴士,也可以沿著路標走回市中心。有時間的旅人不妨沿著鄉村小路走回去,一路上的田野風景十分秀麗,別忘了這裡是英國人最喜歡退休的柯茲窩丘陵區(Cotswolds)。回程的路上會遇到幾家鄉村酒館,走累了可以歇腳喝一杯英式啤酒,聽聽當地老人說的一種特殊的柯茲窩口音的英語,也許莎士比亞當年也說這樣口音的老式英語吧!
一般觀光客到史特拉福是不過夜的,但史特拉福的夜晚卻十分美麗,因為大部分旅客走了,小鎮變得較安靜,走在鎮上古老的都鐸老街,會有一種步入時光隧道之感。再加上晚上可以在莎翁出生地,看一場由皇家莎士比亞劇場演出的莎翁戲,尤其有味道。
皇家莎士比亞劇場在史特拉福有三所劇院,在每年四月至十一月之間演出,分成下午場及晚場演出,大部分的票在演出前都售光,因此最好事先預約,以免撲空。
釣河鱒的幽靜小鎮—馬羅
馬羅(Marlow)離溫莎(Windsor)不遠,從派丁頓(Paddington)坐火車約一小時即可抵達,中間要換一種小火車,還是老式木頭坐椅,很有古老風味。這班小火車最後會開過一條兩邊是鄉村原野的火車道,景觀十分美麗,每次都令我心動不已。這一小段綠色景觀,是我在倫敦看過最美的風光,其中綠色風景的變幻萬千,彷彿有上百種不同的綠在眼簾上跳動。
馬羅是很富裕的村莊,但一點都不招搖,當地居民知識水平很高,光從主街上的小小商店就可看出,有不少古董店、珍本書店、精美家飾店等等。還有當地特色商店─漁具店。
馬羅是倫敦釣河鱒的著名之地,當地有個旅館,就叫「道地釣客旅棧」(Macdonald Compleat Angler),還提供釣河鱒的課程。河鱒只能生長在水流清澈之處,也因此可見當地對生態保育工作一定很注重,否則河鱒早就絕種了(就像新店溪的香魚的命運)。
在英國釣魚是要有執照的,但旅館會幫客人準備一種一天的執照,也會囑咐客人要遵守政府制定的規定,例如魚在產卵的季節不能釣,以及長不到足夠尺寸的魚釣了上來後要放生等等。
釣河鱒的人,喜歡用「假蚊甩竿」(Fly Fishing)的方法,這也是目前英國上層階級瘋狂著迷的閒暇嗜好。很多企業鉅子認為從假蚊甩竿學到的人生哲學,遠甚於高爾夫。我的英國朋友尼克就是個假蚊甩竿迷,他老家在英格蘭北方的諾丁翰(Nottingham),那裡有不少釣河鱒的荒僻溪流,搬來倫敦住的他,平日難得回老家過釣魚癮,因此常常在泰晤士河支流做週末釣客。
我一直央求他帶我去做一日釣客,後來他答應了,但他說要選擇較安全之處,因為釣河鱒者,常常必須站在溪流中,而溪水的石塊十分滑溜,因此要慎選較平緩的溪流。
離馬羅鎮上不遠,就是泰晤士河的支流,路段平緩,溪水不急,兩岸老樹遍布,垂柳依依,身入其中,十分幽靜。
尼克選了一處下風段,他告訴我釣河鱒的人一定要懂得判斷風向,永遠不要在上風下竿。
去過一次馬羅後,我就愛上了這個地方。但我後來再去馬羅,都不是去釣魚,畢竟我不是道地釣客,可是我喜歡沿著幾乎無人跡的溪流旁的小徑散步。春日的荒草中會長著黃色的水仙花,細嫩的花莖在風中飄搖,空氣中滿是溪水的綠藻清香,徜徉在這樣的鄉村風光中,馬上讓人有置身桃花源之感。
這樣的環境,離馬羅的主街不過二十分鐘散步之遠,意味著住在這裡的人,只要願意,誰都可以隨時享有恬靜的田園時間。但走上了主街,又有各家精緻的商店,提供文明的愉悅。
主街上自然有茶館,可以悠閒地享有一頓英式下午茶,如果想過過豐盛的下午茶宴,多花點錢就可以去「道地釣客旅棧」。那裡的下午茶很出名,有些倫敦客會專門在週末前來,只為坐在草坪上,一邊看著河岸風光,一邊享用由精緻英國瓷器盛放的黃瓜三明治、鬆餅和蛋糕。
馬羅一日遊,是我在倫敦客居生活中偶爾會寫的綠色日記,那些流水、草徑、樹林、沼澤,每次都讓我的心靈變得清新了。
英國海上的美食家樂園—澤西島
英國的冬天日短夜長,常常下午四點鐘天就黑了,因此有些日照不足的人就容易患上冬日憂鬱症,而要對抗憂鬱最好的辦法就是曬太陽。所以,冬天一到,許多英國人見面時最喜歡聊的話題就是去哪曬太陽,這些英國人常被比喻為候鳥,一到冬天就往南飛,飛去西班牙、突尼西亞、賽普勒斯。我剛到倫敦的前兩年,一點都不覺得冬天有什麼好憂鬱的,在台灣時見慣亞熱帶的冬天,倫敦的冬天剛好成了我的新歡。我喜歡走在海德公園的落葉步道上,一路踩著乾脆的黃葉發出刷刷響聲,呼吸著冷冽的空氣,張嘴還可以吐出一口白霧,這種樂趣,只有念小學台灣比較冷時才能玩的花樣,如今又可以在倫敦重溫了。
可是好景不常,到了第三年,就像花粉熱會突然上身,冬日憂鬱症也逮捕了我!過了一星期垂頭喪氣的日子後,我終於向全斌說我想曬太陽了,但全斌當時剛好在趕學校論文,不宜大動作地跑去西班牙或突尼西亞,他希望我們的陽光假期可以三天兩夜打發,而且不要跑得太遠。
我看著家中的英國地圖,突然想到何不就去聞名已久的澤西島(Jersey Island)?
位於英吉利海峽群島中的最大島澤西,因為地理位置偏南,冬季日照較足,因此吸引了不少退休人士。
但在澤西島退休並不容易。這個島是免稅天堂,有錢人定居或退休於此可以避稅,但澤西島是大不列顛王國的皇家屬地並非本土,有自己獨立的經濟系統,其他不列顛子民是不能說要來此地定居就定居,必須得到當地政府的允可。然而當地政府只收有錢人,因此申請移民的人,身家沒有幾百萬英鎊以上的人是很難獲准的。
澤西島有不少美麗的別墅住家,都是占地數畝的豪宅,但因其依據地形蓋得很隱密,所以不顯招搖。這些豪宅都是數百萬至千萬英鎊的價格,大部分豪宅都有自己的農園、山丘和私人海濱,讓有錢人既可避稅,又可避世。
但要欣賞澤西島的海島風景,並不需要花很多錢,因為在一九二○、三○年代,當時還不流行有錢人移居澤西島,為了因應英國大眾旅遊的市場,澤西島蓋了非常多的海濱渡假旅館,有的旅館十分豪華,有的只是小規模的民宿,但這些旅棧後來都沒落了,因為英國大眾後來流行出國曬太陽。澤西島溫和的陽光和海風以及不能游泳的崎嶇礁石海岸,只能吸引五、六十歲以上的退休老人了。我和全斌住進了一間攝政時期風格的白色木造大旅館,旅館的天花板很高,有許多木製的大窗,陽光會穿過木格及白紗簾灑在長條的老式地板上。旅館有個中庭花園,養著一些英國不易見到的厥類植物,花園旁有個木頭架起的露台,可以坐在那望著波光粼粼的大海。
這麼美好的旅館,如今卻沒落了,因此旅館的細部充滿了年久失修的痕跡,有一種昔日美人如今滄桑的味道。但對我而言,這種年華不再的旅館卻有種特別的感覺,走在如今客人稀少,空盪蕭瑟的旅館大廳及走廊上,我都覺得可以嗅聞得到昔日時光殘留的味道。
來到了澤西,我的心情馬上轉好,其實不只是這裡的陽光較倫敦明麗,我敏感的鼻子馬上聞出澤西的食物一定好吃。
澤西島四面環海,靠近的又是法國的不列塔尼海岸,而法國的不列塔尼,一向以出產優質的龍蝦、生蠔、螃蟹、貽貝出名,澤西島當然也以這些海產出名。但比起不列塔尼,澤西島還有另一個優勢,因為澤西島自古以來就有優良的畜牧業及農業的傳統。有種澤西牛,一向採自然放牧,肉質甜美,不輸蘇格蘭有名的安格斯牛。在九○年代初的那些年,英國大受狂牛症的威脅,因此許多人不敢吃英格蘭北部過度擁擠的人工圈養牛,但澤西牛產量少,幾乎不外銷外地,不像蘇格蘭安格斯牛到處吃得到,更顯出澤西牛的尊貴。
澤西牛的肉質佳,牛奶也好,因此澤西鮮奶油也很出名,比起有名的德文郡及康瓦爾的鮮泡奶油,也因量少而更稀奇。再加上澤西島種植的有機小馬鈴薯、小番茄,都是倫敦美食超市中的昂貴嬌客。
除了自然因素外,澤西島之所以有「英國的海上美食家樂園」這樣的封號,還有幾項特殊的人文因素,造成她擁有獨特的美食傳統。首先,它的地理位置及歷史因緣一直與法國密切相關,澤西島上有些人迄今還能追溯到他們的法國貴族遠親。這些人的祖先有不少是躲避法國大革命而流亡的貴族,像雨果當年遭流放,就是被囚禁在澤西島旁的另一小島(根西島)。
由於法國的淵源,使得法國烹飪藝術一直是澤西料理的靈魂。除了法國之外,從二十世紀中葉起,不少義大利北部的餐飲世家也到澤西島落地生根,並帶來了優良的義大利烹飪傳統。不過,真正使澤西料理享有國際知名度的,倒不是以上的自然及人文因素,而是市場因素。澤西島是國際聞名的避稅金融天堂,小小的市區內有上百家國際知名的銀行在此設立岸外免稅銀行,因此,每年富商巨賈、高級行政人員拜訪澤西的人數眾多,再加上移居澤西島的有錢島民,這些人都是懂吃,又花得起錢的美食家,自然帶動了澤西島的美食文化。
澤西島美食出名,但最讓人高興的,是這裡的美食價格一向以合理出名,尤其和高物價的倫敦相比,澤西島的美食就顯得格外物美價廉。
當我在旅館住定後,傍晚沿著礁岩海邊散步,好讓肚子餓一點後再大啖美食,當天晚上我已經預定好一家我在倫敦的友人向我大力推薦的,以賣炭烤澤西牛排出名的餐廳。
在這家叫Rosalino Rocque 的餐館,我吃到了一生中吃過最好吃的炭烤菲力牛排,五分熟的牛排,表面有一層微焦的煙醺硬皮,又香又有嚼勁,內層是酒紅色又甜又嫩的牛肉,吃這道牛排是連鹽及黑胡椒都不用加的,完完全全的原味。吃完這樣的牛排,我都想為了人類美食而犧牲的澤西牛致敬了。
吃完了澤西牛排,我又吃了由澤西奶油做成的手工冰淇淋,也是好吃得沒話說。最後我滿足地坐在椅子上,幾乎陷入冥想狀態,這頓美食經驗,讓我彷彿瞥見了天堂樂園的形狀。
旅館第二天提供的早餐也值得一書。我曾在毛姆(W. Somerset Maugham)及克莉絲蒂的小說中,看過英國上流社會古典早餐,是和今日的英式早餐不太相同的。因為上流階級的人很早就有健康意識,因此,他們是不吃被喻為吃了會得心臟病的英式早餐(想想看,油淋淋的雙蛋及鹹肉培根,卡路里多高啊!)。那麼,上流階級吃的早餐是什麼呢? 這家沒落的豪華旅館提供的早餐,正好解決了我的疑問。
當天早上,我和外子全斌坐在整間白牆、白桌、白椅、白桌布,吊著白色水晶燈,侍者著白衣黑褲,在我們桌上的白色鑲銀邊的骨瓷盤中放下蒸過的一片鹹鮭魚、一粒完全沒油的水泡蛋、水煮的澤西島小番茄、小馬鈴薯及嫩蘆筍,再配上一碗澤西牛奶煮成的燕麥粥(Porridge)及一碗水煮甜桃。這樣的早餐,真讓人喜歡早起。第二天中午,我去了有名的Jersey Pottery Restaurant 吃到了冬天盛產的生蠔當前菜,而主菜叫了各式炭烤海鮮,從炭烤烏賊到帶子、旗魚、海鱸、和尚魚等等,都是新鮮得有如海邊剛釣上來的海產(至少是當天上午才捕獲的)。之後,吃澤西島溫室產的小粒鮮草莓加澤西鮮奶油。第二天的晚餐,我們去了當地剛得到米其林一星的朗格維利莊園酒店(Longueville Manor Hotel)的餐廳。這家飯店以前是一棟十三世紀的領主莊園,充滿了中世紀古老風情,餐廳的裝潢十分華麗正式,有如中世紀貴族的晚宴廳。這家餐館以澤西海鮮出名,我們叫了美味極了的海鮮濃湯,又吃起司烤生蠔當前菜,主菜是清蒸澤西鰈魚,因為加了白酒一起蒸,味道比港式青衣還細膩。
在澤西島待了三天兩夜,我完全沉沒在美食的歡愉中,到了不得不離開的時候,我問全斌想不想來這裡退休,全斌的答案是「不」。因為這幾天,他帶來要完成的工作都沒做,日子太好過了,而人最好不要活在太享樂的地方。這句話也有道理,因此,才會讓如今在台北的我,深深懷念著澤西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