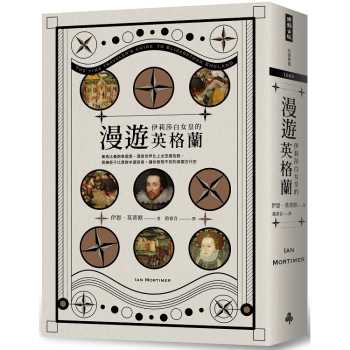第一章 景觀
不同社會看到的景觀不同,你可能會認為伊麗莎白時代主要是一片綠地,特點在於大片開闊的田野和林地,不過要伊麗莎白時代的自耕農描述的話,他會說自己的家鄉有城鎮、有港口、有大房子,還有橋樑和道路。在你眼中那也許是人煙稀少之地──一五六一年時,每平方英哩的平均人口密度不到六十個人(相較於今日遠超過一千人)──但是同時代的說明卻會提到過度擁擠和人口擴張的問題。因此描述景觀是觀點的問題:你所重視之處會影響你看到什麼。請德文郡人(Devonian)講講自己的家鄉,大多數人都會提到大城市埃克塞特(Exeter)、港口達特茅資(Dartmouth)、普利茅斯(Plymouth)和班斯塔普(Barnstaple),還有好幾十個能舉辦市集的城鎮(market town),他們通常會略過不提的是,該地區有個大沼澤、達特穆爾(Dartmoor),某些地方高達兩千英呎,佔地超過兩百平方英哩。這片荒地上沒有道路,只有踩踏出來的古道,伊麗莎白時代的人認為此地一無是處,只能當作牧地、開採錫礦,還有靠著上升地形通過的河流穩定供水。許多人都怕像這樣的沼澤和森林,「無情、廣闊而幽暗的樹林......是大自然替謀殺犯和強暴犯所預備的」,莎士比亞在《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中如此寫道,當然不會有人認為達特穆爾美麗。十六世紀的藝術家畫的是富人、繁榮的城市和食物,他們不畫風景。
造成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不難發現,在一個仍然有人死於飢餓的社會裡,果園本身並無美麗之處:美的是果園能夠生產蘋果和蘋果酒這件事情,一片寬廣平坦的田地「勝過」崎嶇的地形,因為前者可供不費力的耕種,能夠生產小麥,因此代表著有好的白麵包可吃。一間茅草小屋在現代人眼中看來可能很美,但是對伊麗莎白時代的旅人卻不具吸引力,因為住這種小屋的村民通常很窮,沒有多少東西能招待客人。連綿的丘陵和山脈對伊麗莎白時代的旅人而言是阻礙,絕不像你眼中所見風景如畫,丘陵也許會出現在伊麗莎白時代作家筆下的描述中,因為可以用來放牧羊群,不過整體而言,作家更關心的是詳細列出士紳名下的住宅、領地和莊園。
值得一開始就留意這些差異,那些伊麗莎白時代的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正是你最矚目的地方:大片的開闊敞田、泥濘的道路,還有許多勞工的小型屋舍,事實上,一直要到伊麗莎白時代晚期、一五九〇年代末的時候,大家才開始使用「景觀」(landscape)來描述風景,在此之前,他們不需要這樣的詞彙,因為大家並非如此看待「景觀」──對他們而言,只有那些構成的要素才有意義:樹林、田野、河流、果園、花園、橋樑、道路,還有最重要的城鎮。莎士比亞完全不使用「景觀」一詞,他用的是「鄉間」(country)這個詞彙──在這個概念中,人與物質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因此在描述自己眼中所見的伊麗莎白時代景觀時,你所講的並不一定是伊麗莎白時代民眾眼中看見的「鄉間」。每一次觀看的行為都是獨特的──對於伊麗莎白時代的農民來說,看著自己種植的玉米生長是如此,對於現在即將回到十六世紀你來說,也是如此。
城鎮
亞芬河畔的史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位於英格蘭的中心地帶,大約在倫敦西北方九十四英哩處,中世紀的教區教堂座落在這個城鎮南端,距離亞芬河(River Avon)只有幾碼之遙,河流緩緩地蜿蜒在東邊,教堂塔樓頂上有著寬矮的木製尖頂。往北瞧,你會看到一座好看的十四拱門石橋,由休.克洛普頓爵士(Sir Hugh Clopton)在一四九〇年代建造,牛群在遠方河岸邊的寬闊草地上吃草,下游有座小木橋,就在磨坊俯瞰河面變窄之處。
一五五八年十一月時站在史特拉福這一帶,就在伊麗莎白統治伊始之際,你很可能會認為這座城鎮自中世紀以來幾乎沒有改變,如果你往市中心走,看到的建築物大部分都是中世紀的,教堂墓地正對面就是學院的石頭四方院建築,由史特拉福最著名的男性成員約翰.史特拉福(John Stratford)在一三三〇年所創辦,他也是坎特伯里大主教。經過一座果園和幾間低矮的兩層樓茅草小屋,你會來到一個泥濘的角落:右轉進入教堂街往前看,你會看到標準隔間的廉價住宅,是結實牢固的木結構房子,有許多間的總寬度達六十英呎,那是十二世紀規劃城鎮時所制定的。往前幾百碼,右邊是中世紀聖十字公會(Guild of the Holy Cross)的濟貧院,這些房屋排成一列木結構的兩層樓建築物,沒有玻璃的窗戶、鋪設瓦片的屋頂和上方的突起,聳立在街道上方六英呎高的地方。再往前有文法學校和公會大廳,是類似的長型低矮建築,用了粉刷過的木材和木支柱窗戶,相鄰處是公會教堂,有座堂皇的石塔,上面的時鐘會在整點響起,伴隨著你在潮濕的秋日空氣中走過泥濘的街道。
繼續走下去,在你右手邊教堂小巷正對面是鎮上最具盛名的房屋:新居(New Place),由休.克洛普頓爵士建造,也就是蓋了拱門橋的那位,這是一棟三層樓高的木結構房屋,木材之間用的是磚塊,而非柳木或抹上灰泥,有五個框架寬,中央門廊兩側各有一扇大窗戶,上面一層樓有五扇窗,再往上一層樓也有五個窗戶,頂樓每扇窗子都開在山牆上,俯瞰整座城鎮,整棟建築昂然宏偉,很適合向一名成功的商人致敬。一五五八年時,休爵士是史特拉福第二有名的人物(僅次於大主教),深受鎮上民眾愛戴,文法學校裡的男孩放學後,從學校走回市中心的路上,都把這棟建築視為一種成功的表現,將來會有個學生名叫威廉.莎士比亞,他最終會追隨休爵士的步伐,在倫敦致富,然後回到這棟房屋渡過他的餘生。
沿著街道繼續前進,你會看到一些比較狹窄的建築物,舊時的廉價住宅隔成三十英呎的寬度(半塊地皮,half a plot),也有二十英呎寬(三分之一)或僅僅十五英呎寬的。比較狹窄的房屋往往比較高:共三層樓,每一層都有木製突出,向外延伸約一英呎左右,不過與某些城鎮不同的是,史特拉福這兒的房屋不會被突出的高樓層遮住光線,中世紀的市集城鎮經過精心規劃,寬敞的大街能讓大量光線進入前廳和工坊裡。在大街上,你能找到手套製造商、裁縫、屠夫,也有幾名富裕的綢布商和一位羊毛商人。每週六天,他們會在大街上擺設商品陳列台,讓路過的人能看到他們的商品,大多有木製招牌──上面畫著龍、獅子、獨角獸、大釜、圓木桶──以金屬鉤子掛在突出的木桿上,注意招牌上所繪製的符號,並不一定與實際營業項目有關:金器匠的鋪子很可能叫做「綠飛龍」(The Green Dragon),手套製造商的營業招牌可能叫做「白公鹿」(The White Hart)。在你右邊通往河岸牧地的道路叫綿羊街(Sheep Street),有更多羊毛商人住在這裡,羊毛和動物交易也在此地進行;在你左邊的伊利街(Ely Street)是豬隻易手的地方。繼續沿著大街再往前走一百碼左右,你會來到市場十字形建築(market cross):這個有頂蓋的區域是縫衣針製造商、襪商和其他類似手藝工匠販售商品的地方,更遠處是主要的市集地、橋街(Bridge Street),這條街道比較像是一個拉長的矩形開放空間──或者至少本來是如此:如今在中央臨街處全是攤位和店鋪,上方的樓層則是住家。
在這裡如果向右轉就能看到休.克洛普頓爵士那座壯觀的橋樑,橫越在寬闊清淺的一彎河流上,向左轉,你會看見有兩條街上全是木結構的房屋,其中一條是木頭街(Wood Street),通往牲口市集,另一條朝向西北方的是亨利街(Henley Street),沿著這條街走,右手邊你會看到手套製造商約翰.莎士比亞的房子,他與妻子瑪麗和他們的頭生女兒瓊安住在這裡,就像這個自治市鎮裡大部分的房屋一樣,這棟房屋使用編築枝條,抹上灰泥後填充在橫梁之間,低矮的屋頂覆蓋在三個框架之上,就在這間屋子裡,他們才華洋溢的兒子在一五六四年四月誕生了。
到了亨利街這一端,你也幾乎抵達這座城鎮的邊緣了,如果繼續往前再走一百碼遠,你會來到通往亞頓區亨利鎮(Henley-in-Arden)的路上,正如所有城鎮的郊區一樣,你會聞到有害的惡臭,氣味來自附近居民使用的垃圾堆或糞堆,大家知道約翰.莎士比亞會把垃圾堆放在自己的廉價住宅裡,但是他家後院也有個鞣革場,他就在那裡準備製作手套所需要的皮革──沒有什麼比鞣革場更臭的了。在亨利街上這排房屋的後面走一遭,你會發現不只莎士比亞先生懂得善用自家的廉價住宅來處理廢棄物,許多鄰居也一樣,把魚類和動物的內臟、糞便、腐爛的蔬菜和地面上腐舊的燈心草,全都扔在自宅後方大片田地邊上的垃圾堆裡,如果從這些粉刷木結構房屋一團亂的後院向內窺看,你也會看到菜園、糞堆,種植蘋果、西洋梨和櫻桃樹的果園、雞舍、馬車車庫和穀倉──有處理腐爛食物的地方,也有能種植新作物的地方。你可以說,史特拉福似乎既是農民的城鎮,也是工匠的城鎮,這些外圍建築有許多是茅草屋頂:與臨街那些房屋的光鮮瓦片形成明顯的對比,注意某些比較古老的房子會有獨立出來的廚房,另外蓋在花園裡,也可以留意一下,好些花園裡有養豬,利用廚房裡的殘渣來餵食。
至此你可能會再度對此地的中世紀外觀感到詫異,史特拉福的糞堆所散發出來的惡臭就跟兩百年前一樣,這裡的房屋主要仍然由木結構建造而成,許多都已經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自治市鎮的邊界和規劃配置,從一一九六年之後幾乎沒有變動,市集地一直不曾遷移,是什麼改變了呢?
最重大的變化在實際上並不明顯,並非有形的具體事物,比如說,史特拉福在一五五三年收到來自愛德華六世(Edward VI)的自治特許狀,如今在五年之後,這兒由郡副司法長官(bailiff)、高級市政官(aldermen)和最重要的自治市公民(burgesses)一起治理。一五四七年以前,城鎮歸公會管理,如今公會已經解散,財產轉移到新的城鎮委員會名下,儘管一五五八年時的城鎮看起來跟一五〇〇年時差不多,治理方式卻有了徹底的變化,而且不是有什麼已經改變了的問題 ,而是還有哪些正在改變,一五五八年時還存在的中古世紀房屋,大多都是堂屋(hall-house):一樓有一到兩個房間(大廳和私室),鋪設土夯地板、開放式屋頂,大廳中央還有一座壁爐,沒有煙囪,不過想想有了煙囪會多麽不一樣:能在一間加溫的房間上方興建另一個房間,這樣一來,就可以在一棟舊日堂屋所佔的地坪上,興建大量的房間。毫無疑問地,約翰.莎士比亞家那方土地上曾經有過一棟堂屋,後來取而代之的房屋有背對背的壁爐,聳立的煙囪貫穿整棟房屋,替樓下兩個房間以及樓上兩個房間提供溫暖,另一個煙囪在盡頭處,為工坊和上方的房間帶來暖意。約翰家許多鄰居仍然住在單一樓層的房屋裡,不過一五五八年十一月的時候,史特拉福就像其他英格蘭的小城鎮一樣,已經開始擴展了──但與其說是向外,倒不如說是往上。
如果四十年後重返史特拉福,你就能清楚看見史特拉福的變化有多快,那是一五九八年、伊麗莎白統治時期即將結束之際,教堂還在那裡,道路也沒有改變,公會建築和學校基本上沒有變化──但是整座城鎮有一半以上都改建過了,部分原因是一五九四年和一五九五年兩場毀滅性的火災,造成一百二十棟房屋毀損,使得大約四分之一的民眾無家可歸。如今有更多的磚砌煙囪,因此也有了更多的高樓層房屋,事實上,磚塊是改變的關鍵之一,能生產出實惠又耐用的防火煙囪建材,意味著可以建造出兩層樓或三層樓的房屋,即使在石材稀少、石作昂貴的地方也沒問題。沿著亨利街往回走,穿過市集地回到大街上,你會看到整個天際線都已經改變,幾乎所有在你右邊的房屋,如今全有三層樓高,木結構顯得更加優雅對稱,臨街那面的橫梁上有比較多的雕刻木作,有些房屋在窗戶的柵格上用了油紙或布料,能引進些許光線又能擋風,不過其他房屋現在開始在臨街的房間使用玻璃窗,玻璃在一五五八年的城市住宅很少見,但是到了一五七〇年代,手頭稍微寬裕些的人都負擔得起了。並非所有臨街興建的新建築都打算安裝玻璃窗,因為一五九八年之時,玻璃仍然不易取得,不過大多數收入有餘裕的人,都會想辦法取得──如果在英格蘭弄不到,就從勃根第(Burgundy)、諾曼地(Normandy)或是法蘭德斯(Flanders),進口預先製作好的框架。屋主也未必會把整棟房屋一下子全裝上玻璃窗:他可能會在廳堂和起居室安裝玻璃窗,至於其他次要的房間就算了。一五五八年時,煙囪是用來向鄰居炫耀的主要地位象徵,到了一五九八年則是玻璃窗。
史特拉福這波變化中,比較不可取的是窮人的住宿,你可能認為穀倉大變身是現代世界的特色,不過只要看一眼某些房屋的後院,你就知道並非如此,有不少老舊的穀倉出租給無處可去的貧民。史特拉福在一五五八年的人口數大約是一千五百人,到了一六〇三年已經膨脹到兩千五百人了。後者這個數字大概還不包括城裡外全部的窮人和流浪漢──一六〇一年時有份報告提到,市政當局正努力應付七百個貧民。現在你知道為什麼有錢人都講究排場,住在堂皇的玻璃窗房屋裡了:這麼做可以讓他們跟那些家無恆產者有所區隔,你可以了解為何手套製造商之子、威廉.莎士比亞,在一五九七年買下新居時會感到如此驕傲,這棟房子以磚塊砌成,還有玻璃窗和煙囪──與他童年時住的那棟散發臭氣的房屋相比,有天壤之別(他年邁的父親仍然住在那裡),你也可以了解為何威廉的妻子安(Anne),很樂意住新居這兒,而不是她從小長大的霄特里(Shottery)兩房農舍,那裡的大廳可以看到屋頂椽條,仍是泥土地面,她與七名手足共用的房間也是泥土地面。確實住在新居時,她必須應付丈夫長期離家待在倫敦的情形,但是自從一五八二年結婚以來,在這十六年內,她看到自己的生活水準經歷了非比尋常的轉變,部分原因是錢比較多了,部分則是因為錢能買到的東西有了變化。
史特拉福這個城鎮及其居民的經歷,也適用於其他城市住宅區,一六〇〇年時,英格蘭和威爾斯有二十五個座堂城市(cathedral cities)和六百四十一個市集城鎮, 全部都在重建中,因此無法比較規模,各地的人口都正在迅速變化中,例如倫敦一五五八年時總人口大約是七萬,到了一六〇三年則大約有二十萬,原本是歐洲第六大城(排在那不勒斯、威尼斯、巴黎、安特普衛和里斯本之後),後來成為歐洲第三大城(僅次於那不勒斯的二十八萬一千人、巴黎的二十二萬人)。
某些其他的英格蘭城鎮,也以類似的戲劇化方式增長中,例如普利茅斯的人口,在統治伊始之際有三千到四千人,到最後則有八千人,新堡(Newcastle)的人口在一五三〇年到一六〇〇年之間也呈現倍數成長。另一方面,某些地方的數字則是停滯不變: 埃克塞特在整個十六世紀期間,人口總數都在八千左右,有幾個城鎮的人口甚至減少了,比如索爾斯伯里(Salisbury)和科徹斯特(Colchester),這兩個地方在一六〇〇年的總人口,都比一五二〇年代中期時減少了兩千人。不過整體而言,增長顯而易見,因為在一五二〇年代中期時只有十座城鎮的人口總數超過五千人,到了一六〇〇年時,已經增加到二十座城鎮了。
不同社會看到的景觀不同,你可能會認為伊麗莎白時代主要是一片綠地,特點在於大片開闊的田野和林地,不過要伊麗莎白時代的自耕農描述的話,他會說自己的家鄉有城鎮、有港口、有大房子,還有橋樑和道路。在你眼中那也許是人煙稀少之地──一五六一年時,每平方英哩的平均人口密度不到六十個人(相較於今日遠超過一千人)──但是同時代的說明卻會提到過度擁擠和人口擴張的問題。因此描述景觀是觀點的問題:你所重視之處會影響你看到什麼。請德文郡人(Devonian)講講自己的家鄉,大多數人都會提到大城市埃克塞特(Exeter)、港口達特茅資(Dartmouth)、普利茅斯(Plymouth)和班斯塔普(Barnstaple),還有好幾十個能舉辦市集的城鎮(market town),他們通常會略過不提的是,該地區有個大沼澤、達特穆爾(Dartmoor),某些地方高達兩千英呎,佔地超過兩百平方英哩。這片荒地上沒有道路,只有踩踏出來的古道,伊麗莎白時代的人認為此地一無是處,只能當作牧地、開採錫礦,還有靠著上升地形通過的河流穩定供水。許多人都怕像這樣的沼澤和森林,「無情、廣闊而幽暗的樹林......是大自然替謀殺犯和強暴犯所預備的」,莎士比亞在《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中如此寫道,當然不會有人認為達特穆爾美麗。十六世紀的藝術家畫的是富人、繁榮的城市和食物,他們不畫風景。
造成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不難發現,在一個仍然有人死於飢餓的社會裡,果園本身並無美麗之處:美的是果園能夠生產蘋果和蘋果酒這件事情,一片寬廣平坦的田地「勝過」崎嶇的地形,因為前者可供不費力的耕種,能夠生產小麥,因此代表著有好的白麵包可吃。一間茅草小屋在現代人眼中看來可能很美,但是對伊麗莎白時代的旅人卻不具吸引力,因為住這種小屋的村民通常很窮,沒有多少東西能招待客人。連綿的丘陵和山脈對伊麗莎白時代的旅人而言是阻礙,絕不像你眼中所見風景如畫,丘陵也許會出現在伊麗莎白時代作家筆下的描述中,因為可以用來放牧羊群,不過整體而言,作家更關心的是詳細列出士紳名下的住宅、領地和莊園。
值得一開始就留意這些差異,那些伊麗莎白時代的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正是你最矚目的地方:大片的開闊敞田、泥濘的道路,還有許多勞工的小型屋舍,事實上,一直要到伊麗莎白時代晚期、一五九〇年代末的時候,大家才開始使用「景觀」(landscape)來描述風景,在此之前,他們不需要這樣的詞彙,因為大家並非如此看待「景觀」──對他們而言,只有那些構成的要素才有意義:樹林、田野、河流、果園、花園、橋樑、道路,還有最重要的城鎮。莎士比亞完全不使用「景觀」一詞,他用的是「鄉間」(country)這個詞彙──在這個概念中,人與物質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因此在描述自己眼中所見的伊麗莎白時代景觀時,你所講的並不一定是伊麗莎白時代民眾眼中看見的「鄉間」。每一次觀看的行為都是獨特的──對於伊麗莎白時代的農民來說,看著自己種植的玉米生長是如此,對於現在即將回到十六世紀你來說,也是如此。
城鎮
亞芬河畔的史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位於英格蘭的中心地帶,大約在倫敦西北方九十四英哩處,中世紀的教區教堂座落在這個城鎮南端,距離亞芬河(River Avon)只有幾碼之遙,河流緩緩地蜿蜒在東邊,教堂塔樓頂上有著寬矮的木製尖頂。往北瞧,你會看到一座好看的十四拱門石橋,由休.克洛普頓爵士(Sir Hugh Clopton)在一四九〇年代建造,牛群在遠方河岸邊的寬闊草地上吃草,下游有座小木橋,就在磨坊俯瞰河面變窄之處。
一五五八年十一月時站在史特拉福這一帶,就在伊麗莎白統治伊始之際,你很可能會認為這座城鎮自中世紀以來幾乎沒有改變,如果你往市中心走,看到的建築物大部分都是中世紀的,教堂墓地正對面就是學院的石頭四方院建築,由史特拉福最著名的男性成員約翰.史特拉福(John Stratford)在一三三〇年所創辦,他也是坎特伯里大主教。經過一座果園和幾間低矮的兩層樓茅草小屋,你會來到一個泥濘的角落:右轉進入教堂街往前看,你會看到標準隔間的廉價住宅,是結實牢固的木結構房子,有許多間的總寬度達六十英呎,那是十二世紀規劃城鎮時所制定的。往前幾百碼,右邊是中世紀聖十字公會(Guild of the Holy Cross)的濟貧院,這些房屋排成一列木結構的兩層樓建築物,沒有玻璃的窗戶、鋪設瓦片的屋頂和上方的突起,聳立在街道上方六英呎高的地方。再往前有文法學校和公會大廳,是類似的長型低矮建築,用了粉刷過的木材和木支柱窗戶,相鄰處是公會教堂,有座堂皇的石塔,上面的時鐘會在整點響起,伴隨著你在潮濕的秋日空氣中走過泥濘的街道。
繼續走下去,在你右手邊教堂小巷正對面是鎮上最具盛名的房屋:新居(New Place),由休.克洛普頓爵士建造,也就是蓋了拱門橋的那位,這是一棟三層樓高的木結構房屋,木材之間用的是磚塊,而非柳木或抹上灰泥,有五個框架寬,中央門廊兩側各有一扇大窗戶,上面一層樓有五扇窗,再往上一層樓也有五個窗戶,頂樓每扇窗子都開在山牆上,俯瞰整座城鎮,整棟建築昂然宏偉,很適合向一名成功的商人致敬。一五五八年時,休爵士是史特拉福第二有名的人物(僅次於大主教),深受鎮上民眾愛戴,文法學校裡的男孩放學後,從學校走回市中心的路上,都把這棟建築視為一種成功的表現,將來會有個學生名叫威廉.莎士比亞,他最終會追隨休爵士的步伐,在倫敦致富,然後回到這棟房屋渡過他的餘生。
沿著街道繼續前進,你會看到一些比較狹窄的建築物,舊時的廉價住宅隔成三十英呎的寬度(半塊地皮,half a plot),也有二十英呎寬(三分之一)或僅僅十五英呎寬的。比較狹窄的房屋往往比較高:共三層樓,每一層都有木製突出,向外延伸約一英呎左右,不過與某些城鎮不同的是,史特拉福這兒的房屋不會被突出的高樓層遮住光線,中世紀的市集城鎮經過精心規劃,寬敞的大街能讓大量光線進入前廳和工坊裡。在大街上,你能找到手套製造商、裁縫、屠夫,也有幾名富裕的綢布商和一位羊毛商人。每週六天,他們會在大街上擺設商品陳列台,讓路過的人能看到他們的商品,大多有木製招牌──上面畫著龍、獅子、獨角獸、大釜、圓木桶──以金屬鉤子掛在突出的木桿上,注意招牌上所繪製的符號,並不一定與實際營業項目有關:金器匠的鋪子很可能叫做「綠飛龍」(The Green Dragon),手套製造商的營業招牌可能叫做「白公鹿」(The White Hart)。在你右邊通往河岸牧地的道路叫綿羊街(Sheep Street),有更多羊毛商人住在這裡,羊毛和動物交易也在此地進行;在你左邊的伊利街(Ely Street)是豬隻易手的地方。繼續沿著大街再往前走一百碼左右,你會來到市場十字形建築(market cross):這個有頂蓋的區域是縫衣針製造商、襪商和其他類似手藝工匠販售商品的地方,更遠處是主要的市集地、橋街(Bridge Street),這條街道比較像是一個拉長的矩形開放空間──或者至少本來是如此:如今在中央臨街處全是攤位和店鋪,上方的樓層則是住家。
在這裡如果向右轉就能看到休.克洛普頓爵士那座壯觀的橋樑,橫越在寬闊清淺的一彎河流上,向左轉,你會看見有兩條街上全是木結構的房屋,其中一條是木頭街(Wood Street),通往牲口市集,另一條朝向西北方的是亨利街(Henley Street),沿著這條街走,右手邊你會看到手套製造商約翰.莎士比亞的房子,他與妻子瑪麗和他們的頭生女兒瓊安住在這裡,就像這個自治市鎮裡大部分的房屋一樣,這棟房屋使用編築枝條,抹上灰泥後填充在橫梁之間,低矮的屋頂覆蓋在三個框架之上,就在這間屋子裡,他們才華洋溢的兒子在一五六四年四月誕生了。
到了亨利街這一端,你也幾乎抵達這座城鎮的邊緣了,如果繼續往前再走一百碼遠,你會來到通往亞頓區亨利鎮(Henley-in-Arden)的路上,正如所有城鎮的郊區一樣,你會聞到有害的惡臭,氣味來自附近居民使用的垃圾堆或糞堆,大家知道約翰.莎士比亞會把垃圾堆放在自己的廉價住宅裡,但是他家後院也有個鞣革場,他就在那裡準備製作手套所需要的皮革──沒有什麼比鞣革場更臭的了。在亨利街上這排房屋的後面走一遭,你會發現不只莎士比亞先生懂得善用自家的廉價住宅來處理廢棄物,許多鄰居也一樣,把魚類和動物的內臟、糞便、腐爛的蔬菜和地面上腐舊的燈心草,全都扔在自宅後方大片田地邊上的垃圾堆裡,如果從這些粉刷木結構房屋一團亂的後院向內窺看,你也會看到菜園、糞堆,種植蘋果、西洋梨和櫻桃樹的果園、雞舍、馬車車庫和穀倉──有處理腐爛食物的地方,也有能種植新作物的地方。你可以說,史特拉福似乎既是農民的城鎮,也是工匠的城鎮,這些外圍建築有許多是茅草屋頂:與臨街那些房屋的光鮮瓦片形成明顯的對比,注意某些比較古老的房子會有獨立出來的廚房,另外蓋在花園裡,也可以留意一下,好些花園裡有養豬,利用廚房裡的殘渣來餵食。
至此你可能會再度對此地的中世紀外觀感到詫異,史特拉福的糞堆所散發出來的惡臭就跟兩百年前一樣,這裡的房屋主要仍然由木結構建造而成,許多都已經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自治市鎮的邊界和規劃配置,從一一九六年之後幾乎沒有變動,市集地一直不曾遷移,是什麼改變了呢?
最重大的變化在實際上並不明顯,並非有形的具體事物,比如說,史特拉福在一五五三年收到來自愛德華六世(Edward VI)的自治特許狀,如今在五年之後,這兒由郡副司法長官(bailiff)、高級市政官(aldermen)和最重要的自治市公民(burgesses)一起治理。一五四七年以前,城鎮歸公會管理,如今公會已經解散,財產轉移到新的城鎮委員會名下,儘管一五五八年時的城鎮看起來跟一五〇〇年時差不多,治理方式卻有了徹底的變化,而且不是有什麼已經改變了的問題 ,而是還有哪些正在改變,一五五八年時還存在的中古世紀房屋,大多都是堂屋(hall-house):一樓有一到兩個房間(大廳和私室),鋪設土夯地板、開放式屋頂,大廳中央還有一座壁爐,沒有煙囪,不過想想有了煙囪會多麽不一樣:能在一間加溫的房間上方興建另一個房間,這樣一來,就可以在一棟舊日堂屋所佔的地坪上,興建大量的房間。毫無疑問地,約翰.莎士比亞家那方土地上曾經有過一棟堂屋,後來取而代之的房屋有背對背的壁爐,聳立的煙囪貫穿整棟房屋,替樓下兩個房間以及樓上兩個房間提供溫暖,另一個煙囪在盡頭處,為工坊和上方的房間帶來暖意。約翰家許多鄰居仍然住在單一樓層的房屋裡,不過一五五八年十一月的時候,史特拉福就像其他英格蘭的小城鎮一樣,已經開始擴展了──但與其說是向外,倒不如說是往上。
如果四十年後重返史特拉福,你就能清楚看見史特拉福的變化有多快,那是一五九八年、伊麗莎白統治時期即將結束之際,教堂還在那裡,道路也沒有改變,公會建築和學校基本上沒有變化──但是整座城鎮有一半以上都改建過了,部分原因是一五九四年和一五九五年兩場毀滅性的火災,造成一百二十棟房屋毀損,使得大約四分之一的民眾無家可歸。如今有更多的磚砌煙囪,因此也有了更多的高樓層房屋,事實上,磚塊是改變的關鍵之一,能生產出實惠又耐用的防火煙囪建材,意味著可以建造出兩層樓或三層樓的房屋,即使在石材稀少、石作昂貴的地方也沒問題。沿著亨利街往回走,穿過市集地回到大街上,你會看到整個天際線都已經改變,幾乎所有在你右邊的房屋,如今全有三層樓高,木結構顯得更加優雅對稱,臨街那面的橫梁上有比較多的雕刻木作,有些房屋在窗戶的柵格上用了油紙或布料,能引進些許光線又能擋風,不過其他房屋現在開始在臨街的房間使用玻璃窗,玻璃在一五五八年的城市住宅很少見,但是到了一五七〇年代,手頭稍微寬裕些的人都負擔得起了。並非所有臨街興建的新建築都打算安裝玻璃窗,因為一五九八年之時,玻璃仍然不易取得,不過大多數收入有餘裕的人,都會想辦法取得──如果在英格蘭弄不到,就從勃根第(Burgundy)、諾曼地(Normandy)或是法蘭德斯(Flanders),進口預先製作好的框架。屋主也未必會把整棟房屋一下子全裝上玻璃窗:他可能會在廳堂和起居室安裝玻璃窗,至於其他次要的房間就算了。一五五八年時,煙囪是用來向鄰居炫耀的主要地位象徵,到了一五九八年則是玻璃窗。
史特拉福這波變化中,比較不可取的是窮人的住宿,你可能認為穀倉大變身是現代世界的特色,不過只要看一眼某些房屋的後院,你就知道並非如此,有不少老舊的穀倉出租給無處可去的貧民。史特拉福在一五五八年的人口數大約是一千五百人,到了一六〇三年已經膨脹到兩千五百人了。後者這個數字大概還不包括城裡外全部的窮人和流浪漢──一六〇一年時有份報告提到,市政當局正努力應付七百個貧民。現在你知道為什麼有錢人都講究排場,住在堂皇的玻璃窗房屋裡了:這麼做可以讓他們跟那些家無恆產者有所區隔,你可以了解為何手套製造商之子、威廉.莎士比亞,在一五九七年買下新居時會感到如此驕傲,這棟房子以磚塊砌成,還有玻璃窗和煙囪──與他童年時住的那棟散發臭氣的房屋相比,有天壤之別(他年邁的父親仍然住在那裡),你也可以了解為何威廉的妻子安(Anne),很樂意住新居這兒,而不是她從小長大的霄特里(Shottery)兩房農舍,那裡的大廳可以看到屋頂椽條,仍是泥土地面,她與七名手足共用的房間也是泥土地面。確實住在新居時,她必須應付丈夫長期離家待在倫敦的情形,但是自從一五八二年結婚以來,在這十六年內,她看到自己的生活水準經歷了非比尋常的轉變,部分原因是錢比較多了,部分則是因為錢能買到的東西有了變化。
史特拉福這個城鎮及其居民的經歷,也適用於其他城市住宅區,一六〇〇年時,英格蘭和威爾斯有二十五個座堂城市(cathedral cities)和六百四十一個市集城鎮, 全部都在重建中,因此無法比較規模,各地的人口都正在迅速變化中,例如倫敦一五五八年時總人口大約是七萬,到了一六〇三年則大約有二十萬,原本是歐洲第六大城(排在那不勒斯、威尼斯、巴黎、安特普衛和里斯本之後),後來成為歐洲第三大城(僅次於那不勒斯的二十八萬一千人、巴黎的二十二萬人)。
某些其他的英格蘭城鎮,也以類似的戲劇化方式增長中,例如普利茅斯的人口,在統治伊始之際有三千到四千人,到最後則有八千人,新堡(Newcastle)的人口在一五三〇年到一六〇〇年之間也呈現倍數成長。另一方面,某些地方的數字則是停滯不變: 埃克塞特在整個十六世紀期間,人口總數都在八千左右,有幾個城鎮的人口甚至減少了,比如索爾斯伯里(Salisbury)和科徹斯特(Colchester),這兩個地方在一六〇〇年的總人口,都比一五二〇年代中期時減少了兩千人。不過整體而言,增長顯而易見,因為在一五二〇年代中期時只有十座城鎮的人口總數超過五千人,到了一六〇〇年時,已經增加到二十座城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