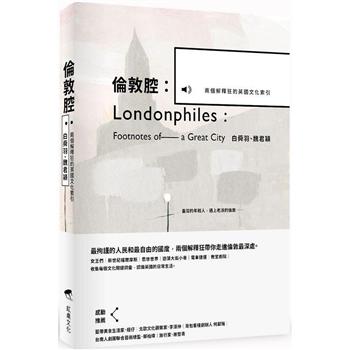荒島唱片Desert Island Discs
如果有一天你被流放到荒島上,身上只能帶八張唱片,你會帶哪八張?
這個問題造就了英國廣播史上最長壽的節目「荒島唱片」(Desert Island Discs),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九日開播以來,荒島唱片在二○一二年歡慶七十週年,歷經四代主持人,目前接手的是來自蘇格蘭的克絲緹楊(Kristy Young)。節目進行方式是主持人每週找來一位名人,用八段音樂串起他/她的人生片段,讓聽眾得以享受一個完整精采的故事。
我喜歡這個節目的親密與坦誠,克絲緹是一位非常有技巧的主持人,除了事先會把所有能找到的資料都詳加研讀外,她也用一種溫暖同理的態度面對受訪者,讓受訪者能講出平常不輕易出口的人生片段與情感。比方說親人離去、職涯起伏,甚或個人病痛,都以平實而真切方式呈現出來。有次訪問到前任副首相克雷格(Nick Clegg),克絲緹直接問他:「你對於最近被釘得滿頭包有什麼感想?」或在被問到如果去荒島能帶一樣奢侈品的話想要帶點什麼,他的回答是一包香煙。我不禁想,如果在台灣,我猜很可能會有衛道人士抗議吧,這種不過於修飾的真實正是節目吸引人之處。另外,聽什麼音樂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個性跟氣質,男高音阿爾菲.鮑(Alfie Boe)雖然演唱歌劇,但他選的唱片裡沒有半張歌劇,他跟克絲緹說叫他唱可以,可是歌劇實在不是他的菜。在音樂中了解一個人,他的情感與際遇,對我來說真的是一件很純粹的事。
二○一一年六月十一日,克絲緹說老是聽名人講古也太無趣,因此特別企劃請觀眾票選屬於自己的荒島唱片,介紹前八名,現場也請來幾位專家來評論這個榜單,同時也把一些觀眾比較特別的故事與音樂選擇放到節目中穿插播放。有個在中東作戰的軍人說,聽到同袍拿著吉他唱迪倫伯(Bob Dylan)的〈Shelter from the Storm〉,奇妙地在危急的砲火下平靜下來。或有位去過南非的聽眾,聽到小朋友唱當時還未成為南非國歌的南非國歌〈Nkosi Sikelel’ iAfrika〉,由於當時還是種族隔離曼德拉坐牢的時代,這首歌是有名的禁歌,當地人跟他說可能此生再沒可能聽到這首歌。當他多年後開車在路上聽到廣播上的這首歌,無法抑制地停到路邊流淚,這些故事都深刻至極,音樂能喚起的回憶是如此強大,節目播放的同時也開放推特回應,主持人收到聽眾的推特說:「可不可以不要再播些會讓我流淚的歌,謝謝。」主持人還一本正經地說:「很遺憾,不行。」
二○○九年起,解決版權爭議的節目全部都放在網路上,供聽眾任意下載。你可以用自己喜歡的歌曲搜尋訪談,或從自己的偶像開始聽起。克絲緹說:「我的前任主持人說過,荒島唱片是廣播界裡最棒的工作,我想我很難反駁她。」身為聽眾,也很幸運有這些充滿熱情的主持人讓我們聽到那麼多名人的人生風景,也可以開始想像那些讓自己陷入音樂回憶的人生片段:如果有一天你被流放到荒島上,身上只能帶八張唱片,你會帶哪八張?
司康Scone
我曾經很討厭吃「司康餅」(scone),總想著又乾又沒味道怎麼會好吃。來到倫敦後,每次室友想烤東西,我都改點一些我的心頭好,比方說巧克力可頌布丁之類的。直到最近,室友在讀了強者我朋友妞仔的食譜後,決定不顧我的碎唸烤下去,一出爐我才發現自己大錯特錯。剛出爐的司康餅香氣四溢,配上表面光澤與中間自然產生的裂痕,本身就夠誘人了,掰開後抹上凝脂奶油與果醬,完全就是人間美味啊。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通常覺得東西難吃,可能只是剛好吃到做得差的,不要放棄治療,要再給自己一次機會啊。言歸正傳,我顯然沒資格講要如何做出好吃的司康餅,或哪裡可以買到好吃的司康餅,但我或許可以解開關於司康餅的幾大爭議(最好是)。
首先是發音,英國多數地方對此物的發音與gone相同;但美式發音則多偏向tone,兩者的區別大抵是scone跟scone的差別。
對英國人來說,發音這件事首先是地域上的差別,有時也免不了跟階級扯上關係,BBC的建議播報發音偏向gone,但妙的是兩種發音都覺得對方的發音比較天龍,這事恐怕還有得吵,如果再加上蘇格蘭腔(scoon,史庫恩)或是英格蘭東北腔(scown,史靠恩)就更熱鬧了。其次,關於司康餅的起源也是眾說紛紜,幾種說法分別是蘇格蘭地名(Scone,在司康鎮吃司康應該別有風味)、蘇格蘭蓋爾語(sgonn,一沱)荷蘭文(schoonbrood,好白麵包)或德文(Schönbrot,好麵包)演變而來。無論起源為何,英國最早的文字記載是一五一三年,諸多考據都跟燕麥烤餅(bannock)系出同源,在還沒有泡打粉的年代,司康是種中型的扁圓餅。一直要到泡打粉普及後,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模樣。
接下來談吃法,有些餐廳為求平整,直接用刀把司康餅切成兩半,後來看了各方資料才發現這是不恰當的,司康餅如果烤得好,中間會出現一個自然的裂縫,用手掰開才能讓凝脂奶油跟果醬塗得夠厚;而究竟先加果醬還是先加奶油?康沃爾郡吃法是先果醬再奶油,德文郡吃法是先奶油再果醬,後面會提到兩個郡的世紀之爭;奶油一定得加凝脂奶油,這是靠間接加熱與緩慢冷卻得到的乳製品,據敝宅的乳品供應商表示,他們都直接開一間房間低溫慢烤!萬不得已找不到凝脂奶油,才會用鮮奶油或是奶油。為此,某數學系教授還寫了一篇好笑的廢文,「證明」凝脂奶油比鮮奶油好。最後則是世紀之爭:Cream Tea(司康餅配茶的輕食下午茶)到底是來自德文郡還是康沃爾郡?康沃爾郡已經先下一城,拿到凝脂奶油的原產地名稱保護(PDO)。德文郡則不甘示弱,想要取得整套Cream Tea的原產地保護,目前戰爭還在持續中,有待後續觀察。
說實在,我本來沒有要寫得那麼宅,結果越看覺得越有趣,英國人怎麼都在這麼好笑的事情上面認真啊。可是換個角度看,不就是因為很重視這件事,才會想要在這些雞毛蒜皮的細節上面琢磨嗎?仔細想想,如果真的愛吃,是不是也應該用一樣認真到好笑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食物?而如果這樣的話,吃進莫名其妙化學物的機會,會不會也因此少一點?
夏令時間Summer Time
「時間有兩種,一種是人們的時間,往前走;一個是自己的時間,停留在最值得紀念的瞬間。」這是很久以前的戲劇演出《在那遙遠的星球,一粒沙》裏頭的句子,想一想,對某些人,某些事而言,時間止在那時那刻,再多的流淌也微不足道。
英國的時間也有兩種,一種叫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reenwich Mean Time, GMT),一種叫不列顛夏季時間(British Summer Time, BST)。前者指的便是「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當地時間。天文台離我們家不遠,在天文台外的地上有條「經度零度」的線,可以讓人兩腳分別踏在東西半球上。博物館裡頭展示了各種計時器的演進,還有「時間」這個概念的發展歷史,相當有趣。
而夏季時間,指的則是每年三月最後一個週日開始,到十月最後一個週日止的日光節約時間。夏季時間比格林威治時間早一個小時,所以BST即是GMT+1。台灣也曾經實施過日光節約時間,但是每年調時鐘的時間跟英國不一樣。
第一次經歷冬令調時鐘的時候非常困惑,不知道是怎麼調?什麼時候調?宿舍室友有一台收音機,恰好我們都晚睡,湊耳在喇叭旁聽廣播報時,原來該是週日凌晨一點的報時,就報成了凌晨兩點,眨著困惑但也睏倦的眼睛睡去,覺得次日的白天異常短暫。到了三月底那次就更奇妙了,日光一下子變得很長,得提醒自己調手錶,以免出門時遲到一個小時。不過手機、筆電這些電子產品都會自動調整,非常方便。某次三月調夏令時間時,我們正好去了比利時,比倫敦早一小時,也在同一天進入夏令時間,旅程中調了好幾次手錶。
不管時間怎麼調,每年三月底固定的碎碎念就是:「對啦對啦夏令時間,這氣溫哪叫夏日。」三、四月在倫敦偶爾還會下雪,羽絨衣也還沒得收,暖氣也不能停,這樣說是「夏天」,根本就是要亞熱帶的子民們,眼球運動預備起。差不多得要到了復活節前後,才覺得有些春意,當然也得吃吃巧克力蛋。然後五月有接骨木花(Elderflower)盛開,可以跟檸檬做成糖漿兌水,或是買明明是蔬菜卻常拿來做甜點的大黃(Rhubarb)做飲料;六月看溫布頓吃草莓配鮮奶油,或是買五鎊票去聽逍遙音樂會,我也老想著要在夏天去環形劇場看「仲夏夜之夢」,最好是晚場,這樣才能和劇名相互輝映。
夏天一到,酒吧裡的生意總是特別好,而地鐵上的醉漢也會多一些。海德公園裏也擺上躺椅,讓遊客可以躺著曬太陽。在春天整理花園的努力,也在夏天得到回報。只要是天氣晴朗的週末,家附近總可以聞到烤肉的味道。說實在,夏天到,感覺連路上陌生人都會友善一些。只是,倫敦的夏天常叫人失望地短,也難以捉摸。若以為晴天要延續數日,興奮地買好皮姆斯(Pimm’s)調酒來喝,過沒兩天就又雨又冷,足可提供人們對於天氣的談資。
小學放起暑假,大學則只剩下研究生還在埋頭苦幹(嚴格來說,英國的研究生是沒有暑假的),我倒是挺喜歡七、八月的校園,適合沉思,反而不愛在此時踏上牛津街人擠人。一直要到九月的第二個週末,BBC逍遙音樂會結束、倫敦市政府辦完泰晤士河嘉年華(Thames Festival),閒散慵懶歡樂的夏日才告結束。接下來,秋季野味上市,然後就又得做些安慰食物囤積脂肪,好迎接冬天了。
零工時契約Zero-Hour Contract
在英國,持學生簽證入境的非歐盟學生可以打工,但限制也不少。以攻讀學位的學生來說,現行規定是學期間(term time)可以工作的時數是每週不超過二十小時。聽過身邊的朋友有兼職的,較多是在學校裡工作,其中又以在圖書館居多。
零工時契約的形式,是指雇主跟員工簽約,以時數計薪,但是雇主並不保證固定給予各個員工多少工作時數。在此情況下,雇主得以視不同時機的需求彈性調整人力安排、節省人事費用;同時,受僱者也沒有答應、接受雇主指派工作的義務。聽起來,這樣的工作模式很有彈性,想工作的時候做,不想,或是不需要的時候就休息。對於假期有空的學生,或是找第二份外快的上班族而言,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在英國,無論公私部門,或是非營利組織,都使用這樣的契約方式,甚至白金漢宮每年固定夏季開放時所需要的多餘人力,也用這種合約找人。
問題就在於,往往制度在設計時都是用意良善,而落實上常會有意想不到的狀況。正如《衛報》的文章中所說,並非零工時契約有問題,問題出在濫用這個合約形式的雇主。正因為雇主不保證給予員工多少時數,使員工可能面臨本週工作爆量,但下週完全沒得做的狀況,對於需要養家活口,或是有貸款要繳的員工來說,十分不利。同時,也有公司發出班表的預告期太短,造成員工無法預期收入狀況,也無法安排其他份工作來補足收入。更有甚者,即便僱主不保證給予工作時數,卻禁止員工去找其他兼職。凡此種種,都是對受僱者極不合理的要求。二○一三年底,當時的商務大臣文斯.凱博(Vince Cable)宣布要對零工時契約做全面檢視,相關的新聞討論,一直到隔年六月都還可以見到。諮詢之後,零工時契約並不會被禁用,而必須杜絕其他不合理的附帶條件。
在倫敦生活這幾年也經歷過幾次大大小小的罷工,無論是地鐵,博物館、或是學校教師工會發起的罷工,生活上的不便當然有,但同時它也是促進大眾討論勞工議題的契機。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勞資關係也隨之進化(雖然看起來不像是往比較好的方向去)如果不是報紙、媒體窮追不捨的分析跟整理,我恐怕也不會曉得,原來零工時契約這樣的雇傭模式,會有如此多潛在的問題。勞工問題並非事不關己就不存在,其實種種議題都需要長期的關注,才有改變的可能。這也是在倫敦生活的幾年中,感受最深的事情之一。
如果有一天你被流放到荒島上,身上只能帶八張唱片,你會帶哪八張?
這個問題造就了英國廣播史上最長壽的節目「荒島唱片」(Desert Island Discs),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九日開播以來,荒島唱片在二○一二年歡慶七十週年,歷經四代主持人,目前接手的是來自蘇格蘭的克絲緹楊(Kristy Young)。節目進行方式是主持人每週找來一位名人,用八段音樂串起他/她的人生片段,讓聽眾得以享受一個完整精采的故事。
我喜歡這個節目的親密與坦誠,克絲緹是一位非常有技巧的主持人,除了事先會把所有能找到的資料都詳加研讀外,她也用一種溫暖同理的態度面對受訪者,讓受訪者能講出平常不輕易出口的人生片段與情感。比方說親人離去、職涯起伏,甚或個人病痛,都以平實而真切方式呈現出來。有次訪問到前任副首相克雷格(Nick Clegg),克絲緹直接問他:「你對於最近被釘得滿頭包有什麼感想?」或在被問到如果去荒島能帶一樣奢侈品的話想要帶點什麼,他的回答是一包香煙。我不禁想,如果在台灣,我猜很可能會有衛道人士抗議吧,這種不過於修飾的真實正是節目吸引人之處。另外,聽什麼音樂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個性跟氣質,男高音阿爾菲.鮑(Alfie Boe)雖然演唱歌劇,但他選的唱片裡沒有半張歌劇,他跟克絲緹說叫他唱可以,可是歌劇實在不是他的菜。在音樂中了解一個人,他的情感與際遇,對我來說真的是一件很純粹的事。
二○一一年六月十一日,克絲緹說老是聽名人講古也太無趣,因此特別企劃請觀眾票選屬於自己的荒島唱片,介紹前八名,現場也請來幾位專家來評論這個榜單,同時也把一些觀眾比較特別的故事與音樂選擇放到節目中穿插播放。有個在中東作戰的軍人說,聽到同袍拿著吉他唱迪倫伯(Bob Dylan)的〈Shelter from the Storm〉,奇妙地在危急的砲火下平靜下來。或有位去過南非的聽眾,聽到小朋友唱當時還未成為南非國歌的南非國歌〈Nkosi Sikelel’ iAfrika〉,由於當時還是種族隔離曼德拉坐牢的時代,這首歌是有名的禁歌,當地人跟他說可能此生再沒可能聽到這首歌。當他多年後開車在路上聽到廣播上的這首歌,無法抑制地停到路邊流淚,這些故事都深刻至極,音樂能喚起的回憶是如此強大,節目播放的同時也開放推特回應,主持人收到聽眾的推特說:「可不可以不要再播些會讓我流淚的歌,謝謝。」主持人還一本正經地說:「很遺憾,不行。」
二○○九年起,解決版權爭議的節目全部都放在網路上,供聽眾任意下載。你可以用自己喜歡的歌曲搜尋訪談,或從自己的偶像開始聽起。克絲緹說:「我的前任主持人說過,荒島唱片是廣播界裡最棒的工作,我想我很難反駁她。」身為聽眾,也很幸運有這些充滿熱情的主持人讓我們聽到那麼多名人的人生風景,也可以開始想像那些讓自己陷入音樂回憶的人生片段:如果有一天你被流放到荒島上,身上只能帶八張唱片,你會帶哪八張?
司康Scone
我曾經很討厭吃「司康餅」(scone),總想著又乾又沒味道怎麼會好吃。來到倫敦後,每次室友想烤東西,我都改點一些我的心頭好,比方說巧克力可頌布丁之類的。直到最近,室友在讀了強者我朋友妞仔的食譜後,決定不顧我的碎唸烤下去,一出爐我才發現自己大錯特錯。剛出爐的司康餅香氣四溢,配上表面光澤與中間自然產生的裂痕,本身就夠誘人了,掰開後抹上凝脂奶油與果醬,完全就是人間美味啊。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通常覺得東西難吃,可能只是剛好吃到做得差的,不要放棄治療,要再給自己一次機會啊。言歸正傳,我顯然沒資格講要如何做出好吃的司康餅,或哪裡可以買到好吃的司康餅,但我或許可以解開關於司康餅的幾大爭議(最好是)。
首先是發音,英國多數地方對此物的發音與gone相同;但美式發音則多偏向tone,兩者的區別大抵是scone跟scone的差別。
對英國人來說,發音這件事首先是地域上的差別,有時也免不了跟階級扯上關係,BBC的建議播報發音偏向gone,但妙的是兩種發音都覺得對方的發音比較天龍,這事恐怕還有得吵,如果再加上蘇格蘭腔(scoon,史庫恩)或是英格蘭東北腔(scown,史靠恩)就更熱鬧了。其次,關於司康餅的起源也是眾說紛紜,幾種說法分別是蘇格蘭地名(Scone,在司康鎮吃司康應該別有風味)、蘇格蘭蓋爾語(sgonn,一沱)荷蘭文(schoonbrood,好白麵包)或德文(Schönbrot,好麵包)演變而來。無論起源為何,英國最早的文字記載是一五一三年,諸多考據都跟燕麥烤餅(bannock)系出同源,在還沒有泡打粉的年代,司康是種中型的扁圓餅。一直要到泡打粉普及後,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模樣。
接下來談吃法,有些餐廳為求平整,直接用刀把司康餅切成兩半,後來看了各方資料才發現這是不恰當的,司康餅如果烤得好,中間會出現一個自然的裂縫,用手掰開才能讓凝脂奶油跟果醬塗得夠厚;而究竟先加果醬還是先加奶油?康沃爾郡吃法是先果醬再奶油,德文郡吃法是先奶油再果醬,後面會提到兩個郡的世紀之爭;奶油一定得加凝脂奶油,這是靠間接加熱與緩慢冷卻得到的乳製品,據敝宅的乳品供應商表示,他們都直接開一間房間低溫慢烤!萬不得已找不到凝脂奶油,才會用鮮奶油或是奶油。為此,某數學系教授還寫了一篇好笑的廢文,「證明」凝脂奶油比鮮奶油好。最後則是世紀之爭:Cream Tea(司康餅配茶的輕食下午茶)到底是來自德文郡還是康沃爾郡?康沃爾郡已經先下一城,拿到凝脂奶油的原產地名稱保護(PDO)。德文郡則不甘示弱,想要取得整套Cream Tea的原產地保護,目前戰爭還在持續中,有待後續觀察。
說實在,我本來沒有要寫得那麼宅,結果越看覺得越有趣,英國人怎麼都在這麼好笑的事情上面認真啊。可是換個角度看,不就是因為很重視這件事,才會想要在這些雞毛蒜皮的細節上面琢磨嗎?仔細想想,如果真的愛吃,是不是也應該用一樣認真到好笑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食物?而如果這樣的話,吃進莫名其妙化學物的機會,會不會也因此少一點?
夏令時間Summer Time
「時間有兩種,一種是人們的時間,往前走;一個是自己的時間,停留在最值得紀念的瞬間。」這是很久以前的戲劇演出《在那遙遠的星球,一粒沙》裏頭的句子,想一想,對某些人,某些事而言,時間止在那時那刻,再多的流淌也微不足道。
英國的時間也有兩種,一種叫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reenwich Mean Time, GMT),一種叫不列顛夏季時間(British Summer Time, BST)。前者指的便是「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當地時間。天文台離我們家不遠,在天文台外的地上有條「經度零度」的線,可以讓人兩腳分別踏在東西半球上。博物館裡頭展示了各種計時器的演進,還有「時間」這個概念的發展歷史,相當有趣。
而夏季時間,指的則是每年三月最後一個週日開始,到十月最後一個週日止的日光節約時間。夏季時間比格林威治時間早一個小時,所以BST即是GMT+1。台灣也曾經實施過日光節約時間,但是每年調時鐘的時間跟英國不一樣。
第一次經歷冬令調時鐘的時候非常困惑,不知道是怎麼調?什麼時候調?宿舍室友有一台收音機,恰好我們都晚睡,湊耳在喇叭旁聽廣播報時,原來該是週日凌晨一點的報時,就報成了凌晨兩點,眨著困惑但也睏倦的眼睛睡去,覺得次日的白天異常短暫。到了三月底那次就更奇妙了,日光一下子變得很長,得提醒自己調手錶,以免出門時遲到一個小時。不過手機、筆電這些電子產品都會自動調整,非常方便。某次三月調夏令時間時,我們正好去了比利時,比倫敦早一小時,也在同一天進入夏令時間,旅程中調了好幾次手錶。
不管時間怎麼調,每年三月底固定的碎碎念就是:「對啦對啦夏令時間,這氣溫哪叫夏日。」三、四月在倫敦偶爾還會下雪,羽絨衣也還沒得收,暖氣也不能停,這樣說是「夏天」,根本就是要亞熱帶的子民們,眼球運動預備起。差不多得要到了復活節前後,才覺得有些春意,當然也得吃吃巧克力蛋。然後五月有接骨木花(Elderflower)盛開,可以跟檸檬做成糖漿兌水,或是買明明是蔬菜卻常拿來做甜點的大黃(Rhubarb)做飲料;六月看溫布頓吃草莓配鮮奶油,或是買五鎊票去聽逍遙音樂會,我也老想著要在夏天去環形劇場看「仲夏夜之夢」,最好是晚場,這樣才能和劇名相互輝映。
夏天一到,酒吧裡的生意總是特別好,而地鐵上的醉漢也會多一些。海德公園裏也擺上躺椅,讓遊客可以躺著曬太陽。在春天整理花園的努力,也在夏天得到回報。只要是天氣晴朗的週末,家附近總可以聞到烤肉的味道。說實在,夏天到,感覺連路上陌生人都會友善一些。只是,倫敦的夏天常叫人失望地短,也難以捉摸。若以為晴天要延續數日,興奮地買好皮姆斯(Pimm’s)調酒來喝,過沒兩天就又雨又冷,足可提供人們對於天氣的談資。
小學放起暑假,大學則只剩下研究生還在埋頭苦幹(嚴格來說,英國的研究生是沒有暑假的),我倒是挺喜歡七、八月的校園,適合沉思,反而不愛在此時踏上牛津街人擠人。一直要到九月的第二個週末,BBC逍遙音樂會結束、倫敦市政府辦完泰晤士河嘉年華(Thames Festival),閒散慵懶歡樂的夏日才告結束。接下來,秋季野味上市,然後就又得做些安慰食物囤積脂肪,好迎接冬天了。
零工時契約Zero-Hour Contract
在英國,持學生簽證入境的非歐盟學生可以打工,但限制也不少。以攻讀學位的學生來說,現行規定是學期間(term time)可以工作的時數是每週不超過二十小時。聽過身邊的朋友有兼職的,較多是在學校裡工作,其中又以在圖書館居多。
零工時契約的形式,是指雇主跟員工簽約,以時數計薪,但是雇主並不保證固定給予各個員工多少工作時數。在此情況下,雇主得以視不同時機的需求彈性調整人力安排、節省人事費用;同時,受僱者也沒有答應、接受雇主指派工作的義務。聽起來,這樣的工作模式很有彈性,想工作的時候做,不想,或是不需要的時候就休息。對於假期有空的學生,或是找第二份外快的上班族而言,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在英國,無論公私部門,或是非營利組織,都使用這樣的契約方式,甚至白金漢宮每年固定夏季開放時所需要的多餘人力,也用這種合約找人。
問題就在於,往往制度在設計時都是用意良善,而落實上常會有意想不到的狀況。正如《衛報》的文章中所說,並非零工時契約有問題,問題出在濫用這個合約形式的雇主。正因為雇主不保證給予員工多少時數,使員工可能面臨本週工作爆量,但下週完全沒得做的狀況,對於需要養家活口,或是有貸款要繳的員工來說,十分不利。同時,也有公司發出班表的預告期太短,造成員工無法預期收入狀況,也無法安排其他份工作來補足收入。更有甚者,即便僱主不保證給予工作時數,卻禁止員工去找其他兼職。凡此種種,都是對受僱者極不合理的要求。二○一三年底,當時的商務大臣文斯.凱博(Vince Cable)宣布要對零工時契約做全面檢視,相關的新聞討論,一直到隔年六月都還可以見到。諮詢之後,零工時契約並不會被禁用,而必須杜絕其他不合理的附帶條件。
在倫敦生活這幾年也經歷過幾次大大小小的罷工,無論是地鐵,博物館、或是學校教師工會發起的罷工,生活上的不便當然有,但同時它也是促進大眾討論勞工議題的契機。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勞資關係也隨之進化(雖然看起來不像是往比較好的方向去)如果不是報紙、媒體窮追不捨的分析跟整理,我恐怕也不會曉得,原來零工時契約這樣的雇傭模式,會有如此多潛在的問題。勞工問題並非事不關己就不存在,其實種種議題都需要長期的關注,才有改變的可能。這也是在倫敦生活的幾年中,感受最深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