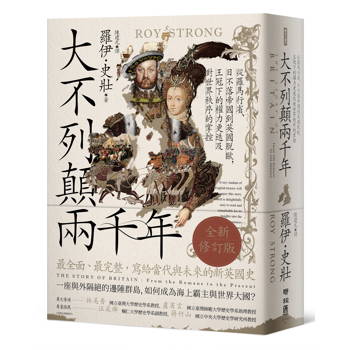內文選摘
1 不列顛島
不列顛是一座島嶼,對於要了解它的歷史而言,這個事實比任何其他事實都重要。它只有被征服過兩次,一次是在西元前五五年被羅馬人征服,另一次是在一○六六年被諾曼人征服。
征服者總是必須與被征服者進行對話,遲早會產生一個由雙方共同組成的社會。然而,從總體上看,這個國家其實是不斷地被那些具備足夠韌性的人們入侵,他們勇敢地面對不列顛周遭海域洶湧波濤的海洋。由於這種困難,無論是來自萊茵蘭(Rhineland)的部落,來自南方地中海的羅馬人,來自日耳曼的盎格魯—撒克遜人,還是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維京人,這些人群的數目總是很少。他們一旦到達這裡,就會被吸收到當地現有人口中。
這一簡單的事實,即任何來到不列顛的人都必須乘船經歷風雨顛簸的折騰,解釋了英國人作為一個民族的兩個主要特徵:內向和外向。英國人仍然珍視自己的島嶼,將其作為與世界其他地區分離並且不受侵犯的領土。今日搭飛機抵達英國,也不能消除這地方與外界截斷的感覺。即使是在英吉利海峽下面挖一條隧道,也無法消除一種與外部世界隔絕的感受,這也正塑造出,出了隧道之後,任何東西在態度、風格和理念上一眼就能被認出來是英國的。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的是,英國的疆域一開始就由它的地理條件所劃定。
與此同時,這也使得英國人成為了航海者和旅行者,他們為了理解外面的世界,不得不離開這個庇護所島嶼。學者和朝聖者穿越了歐洲和中東、上帝的使者跨越全球去改變未信者的信仰,發現者航行到最遙遠的海洋去尋找新的土地,而且成千上萬的英國居民移居海外去建立新的國家。英國四周被海洋所包圍,產生了一個人與人之間不得不相互容忍,但總體而言仍能接受彼此差異的民族。英國人天生就喜愛他們所認為的島嶼安全和由此帶來的生活安寧。這解釋了他們與生俱來的保守主義、妥協的能力、實用主義,以及他們在思想上許多具革命性的突破。我們歷史上出現許多天才,其中的原因之一必然是這座島上的幽閉恐懼症。以威廉.莎士比亞或艾薩克.牛頓為例,他們的思想為了尋求普遍性真理突破了島嶼的限制。
如果作為一個島嶼這個現實是其歷史的核心,那麼不列顛的地形和氣候也是如此。這是一個分為高地和低地兩個地區的國家。北部和西部有山丘和山脈,有些高達四千英尺,土壤貧瘠、雨量充沛且氣候寒冷。即使在今天,這個國家的這些地區仍然偏遠而難以進入,但在早些世紀,它們與外界幾乎是斷絕聯絡的。總的來說,他們很窮,但他們擁有礦產形式的財富:北威爾斯、德比郡、約克郡和安格爾西(Anglesey)的鉛,威爾斯的黃金、康沃爾(Cornwall)的錫,以及迪恩森林(Forest of Dean)的鐵。東部和南部是土壤肥沃的低地,是氣候溫和得多的河谷地帶,交通也更便利。它的財富是另一種類型的,穀物收成豐富的農田以及供綿羊與牲畜食用的茂盛綠地,這裡提供了肉類、皮革以及最重要的羊毛。
從一開始,不列顛的地理便已經定義了其內部歷史的中心主題:高地和低地之間;以及蘇格蘭、威爾斯、中部和南部之間的緊張局勢。這樣的戲碼在好幾個世紀的過程中不斷重演。然而,低地比不列顛其他地方更容易受到移民的影響,因為在地理位置上,低地便正對著幾乎所有移居者抵達時必須經過的海峽。當尤里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最終在西元前五五年決定征服該島時,他也帶來了橫跨已知世界的帝國文明。他在海峽對面看到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更加原始的文化,這個凱爾特人的文化可以追溯到三十多萬年前長線中的最後一支,不列顛在當時甚至還不是一座島嶼而是歐洲的一部分,有些獵人迷路走到這裡來,後來發現自己被創造了海峽的巨大地貌變化切斷了與歐洲的聯繫。
在長達四百年的時間裡,不列顛一直是羅馬帝國的一部分,直到羅馬人的軍團於西元五世紀初撤出;面對北方野蠻部落的襲擊,這個島不得不設法保全自我性命。在接下來的一千年裡,不列顛與歐洲大陸部分地區的聯盟將成為其歷史上的主要主題。後來,在十一世紀,諾曼人的第二次入侵將英格蘭與現代法國的大部分結合了起來。這個帝國在五百年當中時而擴張時而收縮,直到一五五八年時,最後剩下的前哨點加萊港也向法國國王投降。
在這個時代,美洲已經被發現,而人們第一次開始將注意力轉到西邊。在此之前,位於不列顛島之外西邊被注意的只有愛爾蘭,人們的目光都牢牢注視著東方。在這幾個世紀當中,不列顛處於已知世界的邊緣,羅馬在異教時代時是世界中心,而在隨後的基督教時代,耶路撒冷則是世界中心。然而,其偏遠的地理位置並不代表其重要性不高,它之所以受到侵略勢必是有原因的,也有潛力成為帝國維持其在海外力量的基地。在中世紀,英格蘭國王將統治西歐最先進的國家。但是當羅馬軍團啟航去征服不列顛島時,上述的一切都是未來才會發生的事情。
43 一個大國的誕生
威廉三世從來都不是位受人民歡迎的國王。他冷漠孤僻,而且待人生硬拘謹。他不具備任何能受到新臣民喜愛的特質。但他是位令人敬畏的政治家和將軍,這些特質也正是將他帶到英格蘭的主因。威廉三世從歐洲的角度看待這個島嶼,也因此改變了它的地位。自從伊莉莎白一世時代與西班牙的戰爭以來,英格蘭不曾在歐洲政治中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在查理二世統治下,這個國家已淪為宛如法國的附屬國。在詹姆士二世統治下,它選擇了孤立主義。現在這一切都要改變了,因為英格蘭與其商業、金融和海軍等龐大資源,全都要用來投入反對法國的龐大聯盟中,目的是要遏制法國的擴張政策,並且恢復權力平衡,在此體系中不會有某個國家可以支配其他所有國家。當戰爭剛爆發時,人們認為這只會是短暫的投入。沒有人能夠預料到它會將英格蘭捲入兩場大規模的戰爭,以及十九年的大規模戰鬥。沒有人能想到不列顛將會就此崛起成為世界大國。
有兩件大事深刻影響了這國家,而且影響力將會一路持續到十八世紀末,而這場戰爭便是其中之一。另一件大事則是革命協議,該協議從根本上改變了王權的性質。威廉三世之所以擁有王位繼承權,是因為他妻子是具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女王,而女王之所以繼承王位的部分原因則是當時沒有其他的選項存在。他們兩人共同統治,但實際上威廉三世掌握了所有權力。正如一位貴族所觀察的:「我認為今日我們的所作所為毀滅了英格蘭君主制度,因為我們是以投票的方式選擇君主。」威廉三世從未承認他的地位與他的前任有任何不同,但事實上兩者確實有所不同。國會通過的《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闡明了以下觀點:目前這個君主制度的存在是要遵守一些條件的。王室中止國會的權力現在被宣布為違法。沒有國會的同意,國王不能在承平時期維持常備軍。從此以後,所有天主教徒都被排除在王位繼承人選之外。人們希望這場革命能夠使得英格蘭國教會具備更大範圍的包容性,但這一希望最終以破滅告終,就像一六六○年發生的情況一樣。一六八九年五月通過的《寬容法案》(The Toleration Bill)只給予不服從國教者有限的信仰自由,對於他們二等公民的地位絲毫沒有改善。
輝格黨歷史學家將一六八八年呈現為有限君主立憲制演變的里程碑。令人意外的是,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發生,君主與政府仍然密不可分,大臣們繼續由君主選任。事實上,大臣們只有在得到王室寵信的情況下才能留任,他們也要依賴國會中受益於王室贊助的那些議員的支持。國王手上有大量的官職、養老金和其他津貼可供支配,這情況會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他對外交政策的控制權,實質上仍然不容他人置喙。
這兩次戰爭跨越了兩個統治時期,但與過去不同的是,新君主的上台並不預示著政策就將改變。威廉和瑪麗沒有孩子,在威廉三世於一七○二年去世後,王位傳給了威廉的小姨子安妮(Anne)。她是一個身材矮胖、心胸狹窄的三十七歲女人,特別喜歡閒聊和打牌,但是她並不欠缺政治敏感度。她全心全意地盡責與承擔起英格蘭國教會,並且沐浴在他人成就所散發出的光輝中。安妮和她的姊夫一樣,認為王室特權崇高無比,並堅決抵制任何侵蝕它的企圖。
然而,不列顛陷入了一場將近三十年的戰爭之中,不列顛在這場戰爭要與自羅馬帝國以來歐洲最強大的軍事機構對抗。有多達四十萬人做好了被武裝的準備,並且能夠在多個戰線上同時作戰。從一六八九年持續到一六九七年的九年戰爭,以及從一七○一年持續到一七一三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這兩場戰爭都是在削弱法國主宰歐洲的野心。這個野心尤其表現在:法國在哈布斯堡王朝最後一任國王查理二世駕崩的時候,宣稱擁有西班牙及其帝國的主權。一六八八年,路易十四入侵日耳曼地區,翌年年初,荷蘭對法國宣戰,這揭開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英格蘭、薩伏伊和日耳曼許多邦國組成大聯盟的序幕。一直到詹姆士二世入侵愛爾蘭,英格蘭的激情才被激發。
那次入侵引發了愛爾蘭天主教民族主義的高漲,導致長老派教徒逃往倫敦德里(Londonderry)和恩尼斯基倫(Enniskillen)避難。英格蘭軍隊在五月解救了倫敦德里,但在八月派遣的第二支軍隊卻以慘敗告終。次年,威廉三世本人入侵愛爾蘭,並在博因戰役(Battle of Boyne)中獲得大勝。即使這場大勝之後,威廉三世也需要一年多的時間完成對愛爾蘭的重新征服。英格蘭對愛爾蘭起義的報復,則是在此地展開將延續數個世紀之久的殘酷統治傳統。國會對所有公職人員重新執行了《檢覈法》,所有天主教徒和長老派信徒因此都被禁止參與政治活動。天主教徒尤其遭受了殘酷的法律懲罰,這實際上是將他們從地主階層中清除出去。愛爾蘭改由信奉愛爾蘭國教會的少數地主階級實施高壓統治,悲慘地淪落到宛如殖民地的附庸地位。
直到今天,在北愛爾蘭的新教徒中,威廉三世仍然是一個受人崇拜的人物。但是對威廉三世而言,整個事件只是一個距離遙遠且令人討厭的插曲,迫使他轉移了在歐陸上對抗法國人的精力。歐陸的戰場在西屬尼德蘭(現在的比利時),而戰爭往往是在每年夏季展開,其中包括小規模戰役以及長時間的圍攻。威廉三世的軍事行動並未特別順利,但在一六九五年他奪下了納穆爾(Namur)。路易十四在此戰役之後便準備談和,並於一六九七年簽署了《里斯維克條約》(Treaty of Ryswick)。除了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阿爾薩斯(Alsace)的一部分外,路易十四放棄了自一六七八年以來他所取得的一切。更重要的是,路易十四承認威廉為國王。
這份和約只解決了一些小問題,因為西班牙王位的繼承權仍然懸而未決。在隨後的幾年中,威廉三世和路易十四達成了兩項協議,即所謂的《兩份瓜分條約》(The Partition Treaties,一六九八—一七○○)。當這些內情於一七○○年被公諸於世時,輿論極為憤怒,而外交政策作為王室之特權的傳統也就此開始被削弱。威廉三世的聲望降至谷底,人們對他長期人在海外、戰爭的代價和軍隊的長期存在感到深惡痛絕。王位繼承的不確定性加劇了這種不滿,因為安妮唯一的兒子於一七○○年去世了。結果,一七○一年的《王位繼承法》將王位授予漢諾威選侯(Electors of Hanover,詹姆士一世之女伊莉莎白的後裔)。同年,病重的西班牙國王查理二世最終去世,把西班牙的王位留給了路易十四的孫子安茹的菲利普(Philip of Anjou)。法國國王立即毀棄《兩份瓜分條約》,而且也無視自己先前已承認威廉三世為國王,轉而答應要在詹姆士二世死後承認他的兒子為詹姆士三世。
這喚起了不列顛重新開戰的欲望,但這一次不是由威廉三世來領軍,他在此時已不再踏足沙場了。約翰.邱吉爾(John Churchill)被任命為英格蘭軍隊總司令,他後來被封為馬爾博羅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威廉三世不喜歡邱吉爾,儘管他很清楚後者所具備的潛力。然而,國王並未活著親眼目睹勝利,他在一七○二年初就去世了。他辭世時既不受人愛戴也無人哀悼。邱吉爾多年來一直在伺機而動,而新任女王的來臨(她的閨密是邱吉爾的妻子),讓他的地位扶搖直上。這位英軍有史以來能力最強的指揮官,將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這個舞台上大展才能。這位英俊的男子天生優雅、有魅力、有禮貌,是位完美的朝臣。他也有缺陷,他會為了自身利益不擇手段,而且對名利貪得無饜。然而,他是出色的軍事指揮官和戰術家,整場戰爭的節奏在他的領導下發生了巨大變化。馬爾博羅相信打仗的必要性,並開始調動他的部隊出其不意地襲擊法國軍隊,迫使後者開戰。他隨後取得了一系列傳奇般的勝利,這使馬爾博羅成為歐洲的英雄。法國軍隊於一七○四年在布倫海姆(Blenheim)遭受了兩個世代以來的首次敗戰,兩萬三千人傷亡,一萬五千人被俘虜,而且元帥也在其中。女王封邱吉爾為馬爾博羅公爵,並授予他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王家莊園,並在該莊園上興建了布倫海姆宮(Blenheim Palace)以紀念他的榮耀。
布倫海姆戰役開啟了後來一連串的勝利。一七○六年的拉米利斯(Ramillies)戰役導致了西屬尼德蘭的投降。兩年後是奧德納德(Oudenarde)戰役,而一七○九年則爆發馬普拉蓋(Malplaquet)戰役。在西班牙的戰爭就沒那麼順利了,英軍在阿爾曼薩(Almanza)被擊敗,但是那時法軍已經筋疲力盡了。馬爾博羅知道,只有箝制住法國的許多邊界—西班牙、日耳曼、荷蘭和義大利—才能徹底擊敗法國。他在箝制法國邊界的這件事情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盟國在獲勝之後便陷入爭吵。此外,國內開始出現厭戰情緒,這是對馬爾博羅不利的發展。安妮女王聽到奧德納德戰役的消息後說道:「哦,主啊,這一切可怕的流血何時才能停止?」馬爾博羅後來因莫須有的罪名被解職,而和平談判在一七一三年四月於烏特勒支(Utrecht)圓滿結束。
這是英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這要歸功於那位不受人歡迎的國王,他看到了英國在歐洲舞台上的重要性。在安妮女王去世的那一年(一七一四),英國已成為國際強國,這是英國在最偉大的中世紀國王之後便不曾達到的國際地位。任何歐洲大國都無法忽視她,英國也不再能夠對歐洲大陸置之不理。在整個十八世紀,維持各國勢力平衡確實成為了英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任務。這種情況的發生並不僅僅是由於威廉三世或政治家們的心血來潮,而是由於人們日漸意識到英國在歐洲所占據的重要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諸於媒體之發展。《出版許可法》(Licensing Act)於一六九五年被廢止,這意味著各種支持和反對戰爭的著作都能被印刷問世,供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閱讀;這讓公眾意識到英國對於歐洲無法置身事外,而且也因此方能確保自己的商業財富、海上力量或新教王位繼承不會受到威脅。
《烏得勒支條約》對路易十四有著具備實質效力的限制,他在一個祕密條款中保證,他將不再援助被流放的斯圖亞特家族。各國還一致同意,法國和西班牙的王位永遠不會合併。英國透過取得各地的特許貿易權開始形成一個新生的帝國:哈德遜灣、紐芬蘭、新斯科細亞(Nova Scotia)、阿卡迪亞(Arcadia)、聖克里斯多福島(St Christopher)、米諾卡(Minorca)和直布羅陀(Gibraltar)。英國藉此累積了巨大的商業優勢,特別是與西班牙帝國的貿易。
兩次戰爭都對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英國已經有兩個世紀沒有經歷過這種局面了。這是自十五世紀以來,英國軍隊首次連續好幾年在歐洲大陸上作戰,戰爭漫長而昂貴。第二次大戰牽涉到的地理範圍更是前所未見,包括在西班牙、荷蘭、日耳曼、義大利和西印度群島的作戰。在一七○六至一七一一年之間的最高峰時,英國軍隊(不包括軍官)約有十二萬人。曾令統治階級驚恐萬分的詹姆士二世軍隊,相比之下只有兩萬人。如同陸軍的擴張,海軍不僅在艦船數量上而且在品質和性能上都在提升。到了戰爭結束時,王家海軍已是歐洲規模、戰力最為強大的海軍。
1 不列顛島
不列顛是一座島嶼,對於要了解它的歷史而言,這個事實比任何其他事實都重要。它只有被征服過兩次,一次是在西元前五五年被羅馬人征服,另一次是在一○六六年被諾曼人征服。
征服者總是必須與被征服者進行對話,遲早會產生一個由雙方共同組成的社會。然而,從總體上看,這個國家其實是不斷地被那些具備足夠韌性的人們入侵,他們勇敢地面對不列顛周遭海域洶湧波濤的海洋。由於這種困難,無論是來自萊茵蘭(Rhineland)的部落,來自南方地中海的羅馬人,來自日耳曼的盎格魯—撒克遜人,還是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維京人,這些人群的數目總是很少。他們一旦到達這裡,就會被吸收到當地現有人口中。
這一簡單的事實,即任何來到不列顛的人都必須乘船經歷風雨顛簸的折騰,解釋了英國人作為一個民族的兩個主要特徵:內向和外向。英國人仍然珍視自己的島嶼,將其作為與世界其他地區分離並且不受侵犯的領土。今日搭飛機抵達英國,也不能消除這地方與外界截斷的感覺。即使是在英吉利海峽下面挖一條隧道,也無法消除一種與外部世界隔絕的感受,這也正塑造出,出了隧道之後,任何東西在態度、風格和理念上一眼就能被認出來是英國的。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的是,英國的疆域一開始就由它的地理條件所劃定。
與此同時,這也使得英國人成為了航海者和旅行者,他們為了理解外面的世界,不得不離開這個庇護所島嶼。學者和朝聖者穿越了歐洲和中東、上帝的使者跨越全球去改變未信者的信仰,發現者航行到最遙遠的海洋去尋找新的土地,而且成千上萬的英國居民移居海外去建立新的國家。英國四周被海洋所包圍,產生了一個人與人之間不得不相互容忍,但總體而言仍能接受彼此差異的民族。英國人天生就喜愛他們所認為的島嶼安全和由此帶來的生活安寧。這解釋了他們與生俱來的保守主義、妥協的能力、實用主義,以及他們在思想上許多具革命性的突破。我們歷史上出現許多天才,其中的原因之一必然是這座島上的幽閉恐懼症。以威廉.莎士比亞或艾薩克.牛頓為例,他們的思想為了尋求普遍性真理突破了島嶼的限制。
如果作為一個島嶼這個現實是其歷史的核心,那麼不列顛的地形和氣候也是如此。這是一個分為高地和低地兩個地區的國家。北部和西部有山丘和山脈,有些高達四千英尺,土壤貧瘠、雨量充沛且氣候寒冷。即使在今天,這個國家的這些地區仍然偏遠而難以進入,但在早些世紀,它們與外界幾乎是斷絕聯絡的。總的來說,他們很窮,但他們擁有礦產形式的財富:北威爾斯、德比郡、約克郡和安格爾西(Anglesey)的鉛,威爾斯的黃金、康沃爾(Cornwall)的錫,以及迪恩森林(Forest of Dean)的鐵。東部和南部是土壤肥沃的低地,是氣候溫和得多的河谷地帶,交通也更便利。它的財富是另一種類型的,穀物收成豐富的農田以及供綿羊與牲畜食用的茂盛綠地,這裡提供了肉類、皮革以及最重要的羊毛。
從一開始,不列顛的地理便已經定義了其內部歷史的中心主題:高地和低地之間;以及蘇格蘭、威爾斯、中部和南部之間的緊張局勢。這樣的戲碼在好幾個世紀的過程中不斷重演。然而,低地比不列顛其他地方更容易受到移民的影響,因為在地理位置上,低地便正對著幾乎所有移居者抵達時必須經過的海峽。當尤里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最終在西元前五五年決定征服該島時,他也帶來了橫跨已知世界的帝國文明。他在海峽對面看到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更加原始的文化,這個凱爾特人的文化可以追溯到三十多萬年前長線中的最後一支,不列顛在當時甚至還不是一座島嶼而是歐洲的一部分,有些獵人迷路走到這裡來,後來發現自己被創造了海峽的巨大地貌變化切斷了與歐洲的聯繫。
在長達四百年的時間裡,不列顛一直是羅馬帝國的一部分,直到羅馬人的軍團於西元五世紀初撤出;面對北方野蠻部落的襲擊,這個島不得不設法保全自我性命。在接下來的一千年裡,不列顛與歐洲大陸部分地區的聯盟將成為其歷史上的主要主題。後來,在十一世紀,諾曼人的第二次入侵將英格蘭與現代法國的大部分結合了起來。這個帝國在五百年當中時而擴張時而收縮,直到一五五八年時,最後剩下的前哨點加萊港也向法國國王投降。
在這個時代,美洲已經被發現,而人們第一次開始將注意力轉到西邊。在此之前,位於不列顛島之外西邊被注意的只有愛爾蘭,人們的目光都牢牢注視著東方。在這幾個世紀當中,不列顛處於已知世界的邊緣,羅馬在異教時代時是世界中心,而在隨後的基督教時代,耶路撒冷則是世界中心。然而,其偏遠的地理位置並不代表其重要性不高,它之所以受到侵略勢必是有原因的,也有潛力成為帝國維持其在海外力量的基地。在中世紀,英格蘭國王將統治西歐最先進的國家。但是當羅馬軍團啟航去征服不列顛島時,上述的一切都是未來才會發生的事情。
43 一個大國的誕生
威廉三世從來都不是位受人民歡迎的國王。他冷漠孤僻,而且待人生硬拘謹。他不具備任何能受到新臣民喜愛的特質。但他是位令人敬畏的政治家和將軍,這些特質也正是將他帶到英格蘭的主因。威廉三世從歐洲的角度看待這個島嶼,也因此改變了它的地位。自從伊莉莎白一世時代與西班牙的戰爭以來,英格蘭不曾在歐洲政治中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在查理二世統治下,這個國家已淪為宛如法國的附屬國。在詹姆士二世統治下,它選擇了孤立主義。現在這一切都要改變了,因為英格蘭與其商業、金融和海軍等龐大資源,全都要用來投入反對法國的龐大聯盟中,目的是要遏制法國的擴張政策,並且恢復權力平衡,在此體系中不會有某個國家可以支配其他所有國家。當戰爭剛爆發時,人們認為這只會是短暫的投入。沒有人能夠預料到它會將英格蘭捲入兩場大規模的戰爭,以及十九年的大規模戰鬥。沒有人能想到不列顛將會就此崛起成為世界大國。
有兩件大事深刻影響了這國家,而且影響力將會一路持續到十八世紀末,而這場戰爭便是其中之一。另一件大事則是革命協議,該協議從根本上改變了王權的性質。威廉三世之所以擁有王位繼承權,是因為他妻子是具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女王,而女王之所以繼承王位的部分原因則是當時沒有其他的選項存在。他們兩人共同統治,但實際上威廉三世掌握了所有權力。正如一位貴族所觀察的:「我認為今日我們的所作所為毀滅了英格蘭君主制度,因為我們是以投票的方式選擇君主。」威廉三世從未承認他的地位與他的前任有任何不同,但事實上兩者確實有所不同。國會通過的《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闡明了以下觀點:目前這個君主制度的存在是要遵守一些條件的。王室中止國會的權力現在被宣布為違法。沒有國會的同意,國王不能在承平時期維持常備軍。從此以後,所有天主教徒都被排除在王位繼承人選之外。人們希望這場革命能夠使得英格蘭國教會具備更大範圍的包容性,但這一希望最終以破滅告終,就像一六六○年發生的情況一樣。一六八九年五月通過的《寬容法案》(The Toleration Bill)只給予不服從國教者有限的信仰自由,對於他們二等公民的地位絲毫沒有改善。
輝格黨歷史學家將一六八八年呈現為有限君主立憲制演變的里程碑。令人意外的是,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發生,君主與政府仍然密不可分,大臣們繼續由君主選任。事實上,大臣們只有在得到王室寵信的情況下才能留任,他們也要依賴國會中受益於王室贊助的那些議員的支持。國王手上有大量的官職、養老金和其他津貼可供支配,這情況會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他對外交政策的控制權,實質上仍然不容他人置喙。
這兩次戰爭跨越了兩個統治時期,但與過去不同的是,新君主的上台並不預示著政策就將改變。威廉和瑪麗沒有孩子,在威廉三世於一七○二年去世後,王位傳給了威廉的小姨子安妮(Anne)。她是一個身材矮胖、心胸狹窄的三十七歲女人,特別喜歡閒聊和打牌,但是她並不欠缺政治敏感度。她全心全意地盡責與承擔起英格蘭國教會,並且沐浴在他人成就所散發出的光輝中。安妮和她的姊夫一樣,認為王室特權崇高無比,並堅決抵制任何侵蝕它的企圖。
然而,不列顛陷入了一場將近三十年的戰爭之中,不列顛在這場戰爭要與自羅馬帝國以來歐洲最強大的軍事機構對抗。有多達四十萬人做好了被武裝的準備,並且能夠在多個戰線上同時作戰。從一六八九年持續到一六九七年的九年戰爭,以及從一七○一年持續到一七一三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這兩場戰爭都是在削弱法國主宰歐洲的野心。這個野心尤其表現在:法國在哈布斯堡王朝最後一任國王查理二世駕崩的時候,宣稱擁有西班牙及其帝國的主權。一六八八年,路易十四入侵日耳曼地區,翌年年初,荷蘭對法國宣戰,這揭開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英格蘭、薩伏伊和日耳曼許多邦國組成大聯盟的序幕。一直到詹姆士二世入侵愛爾蘭,英格蘭的激情才被激發。
那次入侵引發了愛爾蘭天主教民族主義的高漲,導致長老派教徒逃往倫敦德里(Londonderry)和恩尼斯基倫(Enniskillen)避難。英格蘭軍隊在五月解救了倫敦德里,但在八月派遣的第二支軍隊卻以慘敗告終。次年,威廉三世本人入侵愛爾蘭,並在博因戰役(Battle of Boyne)中獲得大勝。即使這場大勝之後,威廉三世也需要一年多的時間完成對愛爾蘭的重新征服。英格蘭對愛爾蘭起義的報復,則是在此地展開將延續數個世紀之久的殘酷統治傳統。國會對所有公職人員重新執行了《檢覈法》,所有天主教徒和長老派信徒因此都被禁止參與政治活動。天主教徒尤其遭受了殘酷的法律懲罰,這實際上是將他們從地主階層中清除出去。愛爾蘭改由信奉愛爾蘭國教會的少數地主階級實施高壓統治,悲慘地淪落到宛如殖民地的附庸地位。
直到今天,在北愛爾蘭的新教徒中,威廉三世仍然是一個受人崇拜的人物。但是對威廉三世而言,整個事件只是一個距離遙遠且令人討厭的插曲,迫使他轉移了在歐陸上對抗法國人的精力。歐陸的戰場在西屬尼德蘭(現在的比利時),而戰爭往往是在每年夏季展開,其中包括小規模戰役以及長時間的圍攻。威廉三世的軍事行動並未特別順利,但在一六九五年他奪下了納穆爾(Namur)。路易十四在此戰役之後便準備談和,並於一六九七年簽署了《里斯維克條約》(Treaty of Ryswick)。除了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阿爾薩斯(Alsace)的一部分外,路易十四放棄了自一六七八年以來他所取得的一切。更重要的是,路易十四承認威廉為國王。
這份和約只解決了一些小問題,因為西班牙王位的繼承權仍然懸而未決。在隨後的幾年中,威廉三世和路易十四達成了兩項協議,即所謂的《兩份瓜分條約》(The Partition Treaties,一六九八—一七○○)。當這些內情於一七○○年被公諸於世時,輿論極為憤怒,而外交政策作為王室之特權的傳統也就此開始被削弱。威廉三世的聲望降至谷底,人們對他長期人在海外、戰爭的代價和軍隊的長期存在感到深惡痛絕。王位繼承的不確定性加劇了這種不滿,因為安妮唯一的兒子於一七○○年去世了。結果,一七○一年的《王位繼承法》將王位授予漢諾威選侯(Electors of Hanover,詹姆士一世之女伊莉莎白的後裔)。同年,病重的西班牙國王查理二世最終去世,把西班牙的王位留給了路易十四的孫子安茹的菲利普(Philip of Anjou)。法國國王立即毀棄《兩份瓜分條約》,而且也無視自己先前已承認威廉三世為國王,轉而答應要在詹姆士二世死後承認他的兒子為詹姆士三世。
這喚起了不列顛重新開戰的欲望,但這一次不是由威廉三世來領軍,他在此時已不再踏足沙場了。約翰.邱吉爾(John Churchill)被任命為英格蘭軍隊總司令,他後來被封為馬爾博羅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威廉三世不喜歡邱吉爾,儘管他很清楚後者所具備的潛力。然而,國王並未活著親眼目睹勝利,他在一七○二年初就去世了。他辭世時既不受人愛戴也無人哀悼。邱吉爾多年來一直在伺機而動,而新任女王的來臨(她的閨密是邱吉爾的妻子),讓他的地位扶搖直上。這位英軍有史以來能力最強的指揮官,將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這個舞台上大展才能。這位英俊的男子天生優雅、有魅力、有禮貌,是位完美的朝臣。他也有缺陷,他會為了自身利益不擇手段,而且對名利貪得無饜。然而,他是出色的軍事指揮官和戰術家,整場戰爭的節奏在他的領導下發生了巨大變化。馬爾博羅相信打仗的必要性,並開始調動他的部隊出其不意地襲擊法國軍隊,迫使後者開戰。他隨後取得了一系列傳奇般的勝利,這使馬爾博羅成為歐洲的英雄。法國軍隊於一七○四年在布倫海姆(Blenheim)遭受了兩個世代以來的首次敗戰,兩萬三千人傷亡,一萬五千人被俘虜,而且元帥也在其中。女王封邱吉爾為馬爾博羅公爵,並授予他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王家莊園,並在該莊園上興建了布倫海姆宮(Blenheim Palace)以紀念他的榮耀。
布倫海姆戰役開啟了後來一連串的勝利。一七○六年的拉米利斯(Ramillies)戰役導致了西屬尼德蘭的投降。兩年後是奧德納德(Oudenarde)戰役,而一七○九年則爆發馬普拉蓋(Malplaquet)戰役。在西班牙的戰爭就沒那麼順利了,英軍在阿爾曼薩(Almanza)被擊敗,但是那時法軍已經筋疲力盡了。馬爾博羅知道,只有箝制住法國的許多邊界—西班牙、日耳曼、荷蘭和義大利—才能徹底擊敗法國。他在箝制法國邊界的這件事情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盟國在獲勝之後便陷入爭吵。此外,國內開始出現厭戰情緒,這是對馬爾博羅不利的發展。安妮女王聽到奧德納德戰役的消息後說道:「哦,主啊,這一切可怕的流血何時才能停止?」馬爾博羅後來因莫須有的罪名被解職,而和平談判在一七一三年四月於烏特勒支(Utrecht)圓滿結束。
這是英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這要歸功於那位不受人歡迎的國王,他看到了英國在歐洲舞台上的重要性。在安妮女王去世的那一年(一七一四),英國已成為國際強國,這是英國在最偉大的中世紀國王之後便不曾達到的國際地位。任何歐洲大國都無法忽視她,英國也不再能夠對歐洲大陸置之不理。在整個十八世紀,維持各國勢力平衡確實成為了英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任務。這種情況的發生並不僅僅是由於威廉三世或政治家們的心血來潮,而是由於人們日漸意識到英國在歐洲所占據的重要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諸於媒體之發展。《出版許可法》(Licensing Act)於一六九五年被廢止,這意味著各種支持和反對戰爭的著作都能被印刷問世,供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閱讀;這讓公眾意識到英國對於歐洲無法置身事外,而且也因此方能確保自己的商業財富、海上力量或新教王位繼承不會受到威脅。
《烏得勒支條約》對路易十四有著具備實質效力的限制,他在一個祕密條款中保證,他將不再援助被流放的斯圖亞特家族。各國還一致同意,法國和西班牙的王位永遠不會合併。英國透過取得各地的特許貿易權開始形成一個新生的帝國:哈德遜灣、紐芬蘭、新斯科細亞(Nova Scotia)、阿卡迪亞(Arcadia)、聖克里斯多福島(St Christopher)、米諾卡(Minorca)和直布羅陀(Gibraltar)。英國藉此累積了巨大的商業優勢,特別是與西班牙帝國的貿易。
兩次戰爭都對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英國已經有兩個世紀沒有經歷過這種局面了。這是自十五世紀以來,英國軍隊首次連續好幾年在歐洲大陸上作戰,戰爭漫長而昂貴。第二次大戰牽涉到的地理範圍更是前所未見,包括在西班牙、荷蘭、日耳曼、義大利和西印度群島的作戰。在一七○六至一七一一年之間的最高峰時,英國軍隊(不包括軍官)約有十二萬人。曾令統治階級驚恐萬分的詹姆士二世軍隊,相比之下只有兩萬人。如同陸軍的擴張,海軍不僅在艦船數量上而且在品質和性能上都在提升。到了戰爭結束時,王家海軍已是歐洲規模、戰力最為強大的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