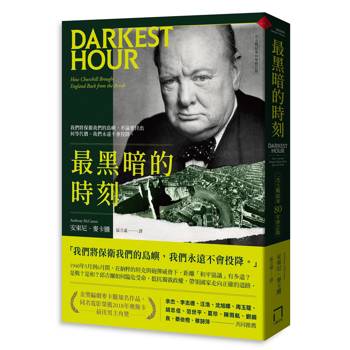第一章 分裂的下議院
英國國會的議事廳淹沒在一片譴責與咒罵之中。「滾,滾!」他們從二樓旁聽席大聲吼著;貴族與上議院議員們爭相探頭,想看得更清楚些。「下台,老兄!下台!」這是英國政治從未有過的景象。反對黨議員們把議事程序單捲成匕首狀,隔空戳向一個坐在發言箱前、衰老且暗地裡為病痛所苦的身影──他就是大不列顛的保守黨首相,納維爾.張伯倫。
但是張伯倫並不情願辭去首相的職務。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他完全沒有把握還有誰能接下他的位子。
英國進入戰爭已經八個月,而且進展非常糟糕。無論政治人物或民眾都在大聲疾呼,他們需要的不是隨便一個領袖,而是就像所有重大時刻都要求的那樣,英國人需要一個偉大的領導人:這個人要能發表唯有偉大領導者才能做出的談話,能打動、影響、說服、激勵與鼓舞廣大的人心,甚至能在民眾的心裡創造出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擁有的強烈情感。這些談話能催生行動,而且依照行動的明智與否,將決定結果是勝利還是慘痛的失敗。
而且對任何面臨重大危機的國家民族來說,他們或許還希望在領導人身上看到一種令人意外的素質,那就是:懷疑。這是一種極其重要的能力,使他能懷疑自己的判斷,能同時抱持兩種對立的構想,而且只在真能做到後才予以綜合,能擁有一種不獨斷的心態,並因此能與所有觀點保持對話。相反地,心態如果獨斷,能進行對話的對象就只剩下他自己一個人了。在這個時代裡,意識形態先行者對英國沒有好處。英國亟需的,是一位具有三百六十度視野的思想家。
如奧利佛.克倫威爾一六五○年在給蘇格蘭教會的信上寫道:「以耶穌的肺腑之名,我懇求你們,請想一下,你們也可能是錯的。」在這個前景難料的時刻上,考慮到英國面臨的議題如此重大,以至於整個未來都取決於下一步如何決策,那麼一個大問題就在於:要去哪裡找這樣一位領導者呢?
「不管從你的任何貢獻來說,你在這個位子上都已經坐太久了。走吧,拜託,讓我們跟你做個了斷吧!以上帝之名,請你走!」利奧.艾默里(伯明罕市的斯帕克布魯克選區的國會議員)在說完這話並返回座位時,獲得了雷霆一般的喝采:這是一九四○年五月七日星期二,如今聞名史上的「挪威辯論」的第一天晚上。這時下議院開會已經將近九小時。這是初夏一個暖和的傍晚,夜幕已經降臨。艾默里的話就像匕首一樣插在同為保守黨的張伯倫的側腹上。
英國這時是一個分裂的國家。內閣政府沒能團結議會,而是被各方強烈的主見與瑣碎的爭論來回撕扯,導致英國無論在陸地還是海上的戰事都遭遇災難性的失敗。在歐洲,法西斯勝出、民主走到盡頭的可能性,早已不是無法想像。
當晚在議事廳發生的這場著名辯論,起因是在五天之前種下的:五天前消息傳來,在首度遭遇納粹的激烈進攻之後,英國正在把部隊從挪威的特隆赫姆港撤出。艾默里,以及由索爾茲伯里勛爵領導的「監督委員會」的成員(由保守黨的下院議員與上院議員組成,目標是監督內閣政府負起責任),還有一個跨黨派的國會行動小組(目標類似,但是由自由黨議員克萊門特.戴維斯領導且包括工黨議員)於是強行召開了一場辯論,來討論這場首度遭遇納粹部隊的大挫敗,同時也試著讓領導人下台──他們覺得張伯倫已不符合他們與國家的期待。
張伯倫首先在五月七日下午三點四十八分對下議院就「戰事指導」發表演說;這是持續兩天的辯論的第一天。他的言談以及他嘗試進行的搶救工作,並沒有讓他的立場更有力量,也無法緩和各方對英國基本上即將撞船的憂慮。相反地,這只證實了他的疲倦與防衛心態,這樣的人只會加速國家陷入危機。帶著一臉的「傷心與低落」,如一位評論者日後所形容,他在辯論中苦苦支撐,而敵方還擊的言詞遠比他自己的更加響亮好記。這些言詞他再熟悉也不過了,因為那就是他自己提出來的:「為我們的時代創造和平!」(這是他一年前莊嚴的承諾)以及「錯過了公車!」(他曾指稱希特勒已經錯過了能在歐洲製造任何禍害的所有機會。)現在這些話就像手榴彈一樣在他自己的腳下炸開來了。
張伯倫在演說過程中,連所得到的那一點微弱的支持,如工黨的亞瑟.格林伍德所描述,都是「言不由衷的」。因為下議院的氣氛從未如此沉重:「人人都憂心忡忡,都感到不安──不,那不只是不安,而簡直是危疑恐懼。」
張伯倫返回座位後,保守黨議員海軍上將羅傑.凱斯爵士正好穿著全套軍禮服(這在下議院是聞所未聞的)戲劇性地進入議事廳,下議院突然一片寂靜。作為一名長期批評首相的人,凱斯痛斥著內閣政府「駭人聽聞的種種無能」。他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他親眼見證了政府的種種挫敗。
英國國會的議事廳淹沒在一片譴責與咒罵之中。「滾,滾!」他們從二樓旁聽席大聲吼著;貴族與上議院議員們爭相探頭,想看得更清楚些。「下台,老兄!下台!」這是英國政治從未有過的景象。反對黨議員們把議事程序單捲成匕首狀,隔空戳向一個坐在發言箱前、衰老且暗地裡為病痛所苦的身影──他就是大不列顛的保守黨首相,納維爾.張伯倫。
但是張伯倫並不情願辭去首相的職務。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他完全沒有把握還有誰能接下他的位子。
英國進入戰爭已經八個月,而且進展非常糟糕。無論政治人物或民眾都在大聲疾呼,他們需要的不是隨便一個領袖,而是就像所有重大時刻都要求的那樣,英國人需要一個偉大的領導人:這個人要能發表唯有偉大領導者才能做出的談話,能打動、影響、說服、激勵與鼓舞廣大的人心,甚至能在民眾的心裡創造出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擁有的強烈情感。這些談話能催生行動,而且依照行動的明智與否,將決定結果是勝利還是慘痛的失敗。
而且對任何面臨重大危機的國家民族來說,他們或許還希望在領導人身上看到一種令人意外的素質,那就是:懷疑。這是一種極其重要的能力,使他能懷疑自己的判斷,能同時抱持兩種對立的構想,而且只在真能做到後才予以綜合,能擁有一種不獨斷的心態,並因此能與所有觀點保持對話。相反地,心態如果獨斷,能進行對話的對象就只剩下他自己一個人了。在這個時代裡,意識形態先行者對英國沒有好處。英國亟需的,是一位具有三百六十度視野的思想家。
如奧利佛.克倫威爾一六五○年在給蘇格蘭教會的信上寫道:「以耶穌的肺腑之名,我懇求你們,請想一下,你們也可能是錯的。」在這個前景難料的時刻上,考慮到英國面臨的議題如此重大,以至於整個未來都取決於下一步如何決策,那麼一個大問題就在於:要去哪裡找這樣一位領導者呢?
「不管從你的任何貢獻來說,你在這個位子上都已經坐太久了。走吧,拜託,讓我們跟你做個了斷吧!以上帝之名,請你走!」利奧.艾默里(伯明罕市的斯帕克布魯克選區的國會議員)在說完這話並返回座位時,獲得了雷霆一般的喝采:這是一九四○年五月七日星期二,如今聞名史上的「挪威辯論」的第一天晚上。這時下議院開會已經將近九小時。這是初夏一個暖和的傍晚,夜幕已經降臨。艾默里的話就像匕首一樣插在同為保守黨的張伯倫的側腹上。
英國這時是一個分裂的國家。內閣政府沒能團結議會,而是被各方強烈的主見與瑣碎的爭論來回撕扯,導致英國無論在陸地還是海上的戰事都遭遇災難性的失敗。在歐洲,法西斯勝出、民主走到盡頭的可能性,早已不是無法想像。
當晚在議事廳發生的這場著名辯論,起因是在五天之前種下的:五天前消息傳來,在首度遭遇納粹的激烈進攻之後,英國正在把部隊從挪威的特隆赫姆港撤出。艾默里,以及由索爾茲伯里勛爵領導的「監督委員會」的成員(由保守黨的下院議員與上院議員組成,目標是監督內閣政府負起責任),還有一個跨黨派的國會行動小組(目標類似,但是由自由黨議員克萊門特.戴維斯領導且包括工黨議員)於是強行召開了一場辯論,來討論這場首度遭遇納粹部隊的大挫敗,同時也試著讓領導人下台──他們覺得張伯倫已不符合他們與國家的期待。
張伯倫首先在五月七日下午三點四十八分對下議院就「戰事指導」發表演說;這是持續兩天的辯論的第一天。他的言談以及他嘗試進行的搶救工作,並沒有讓他的立場更有力量,也無法緩和各方對英國基本上即將撞船的憂慮。相反地,這只證實了他的疲倦與防衛心態,這樣的人只會加速國家陷入危機。帶著一臉的「傷心與低落」,如一位評論者日後所形容,他在辯論中苦苦支撐,而敵方還擊的言詞遠比他自己的更加響亮好記。這些言詞他再熟悉也不過了,因為那就是他自己提出來的:「為我們的時代創造和平!」(這是他一年前莊嚴的承諾)以及「錯過了公車!」(他曾指稱希特勒已經錯過了能在歐洲製造任何禍害的所有機會。)現在這些話就像手榴彈一樣在他自己的腳下炸開來了。
張伯倫在演說過程中,連所得到的那一點微弱的支持,如工黨的亞瑟.格林伍德所描述,都是「言不由衷的」。因為下議院的氣氛從未如此沉重:「人人都憂心忡忡,都感到不安──不,那不只是不安,而簡直是危疑恐懼。」
張伯倫返回座位後,保守黨議員海軍上將羅傑.凱斯爵士正好穿著全套軍禮服(這在下議院是聞所未聞的)戲劇性地進入議事廳,下議院突然一片寂靜。作為一名長期批評首相的人,凱斯痛斥著內閣政府「駭人聽聞的種種無能」。他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他親眼見證了政府的種種挫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