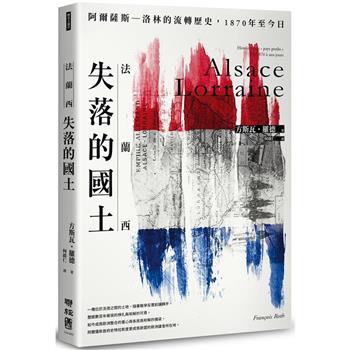第一章 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出現,是歷史的偶然?
德意志化措施
我們要如何說明將奪得領土進行德意志化這個策略的意義呢?首先,「奪取」這個字是法國人說的,依德國人的說法則是「回歸」,因為在他們的歷史裡,這塊土地有很長一段時間屬於德意志帝國,這段時間比法國擁有這塊土地的時間更久;再者,有四分之三居民使用的母語(Muttersprache)是各種日耳曼方言;對住在鄉村和小城市的居民而言,用俾斯麥的話來說──「法國皮相」,只是表象而已,只要刮開,「原有的德國本體」就會出現。要經過一或兩個世代,透過義務學校教育、男人一定要服的兵役、必要施政措施,透過工作關係,德意志語言和文化就會一點一滴重新回到應有的位置,這也是要將德語定為官方語言的原因。有兩項措施非常重要:一是1872年的語言普查,可以確定以德語作為大部分居民母語的地方,而對所有這些地區,德語就成為行政和學校使用的專用語言;二是國民義務教育(Volksschule),由俾斯麥-博倫頒布命令,男生必須接受義務教育直到14歲,女生則是到13歲,穆勒起草各不同年級的課程進行通告,迅速實施。由於部分教師選擇前往法國,因此在執行上要找到具有能力的人員成為最大困難。為了替代這些離開的教師,在洛林雇用盧森堡教師與一些德國教師,即使會讓督學的觀感不好,但是也讓一些在學校的修女留下。被稱為教師研習會的師範學校人事和課程被德意志化,西發利亞(Westphalie)神父亨瑞奇.尼格提特(Heinrich Nigetiet)在1871年來到梅斯,領導洛林教師研習會直到1906年退休為止。在法國,情況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阿爾薩斯和洛林出身的儲備教師相對較多,對教師人員都能進行定期補充。在以多數人講法語或是以法語為專門語言的地區,教師都能使用雙語,在學習開始初期是以法語作為讀、寫為主,稍後在大學課程才出現德語。
最後一堂法文課
「……阿默先生站上講台,用之前對我講話時一樣柔和而低沉的聲音,對我們說:『孩子們,這是我們最後一次上課。柏林方面下令,以後在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學校裡,只能教授德文⋯⋯新老師明天就會來。今天是你們最後一堂法文課,麻煩請大家專心上課。』這幾句話讓我感到不知所措。啊!這些傢伙,原來之前市政廳公布的事就是在講這個。
我的最後一堂法文課!我剛剛會寫一些字!就這樣我就再也沒法學習!一切就到此為止了!……
就這樣,阿默先生從這件事講到那件事,他開始跟我們講到法文,說法文是世界上最優美、最清晰、最嚴謹的語言:我們要好好記住這個語言,絕對不要忘了,因為即便一個民族被奴役,只要仍能保有他們的語言,就如同有了打開牢獄的鑰匙。接著他講授文法,我們也跟著讀課文。我竟意外地都能聽懂,他所講的,我竟然都覺得那麼簡單,一點都不難。我相信自己從來沒有這麼專心聽課。……
突然教堂中午的鐘聲響起,接著是唸《三鐘經》的時間。同一時間,普魯士士兵操練結束返營的號角聲,在我們的窗外響起……阿默先生臉色蒼白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在我的眼中,他的個子從來沒有這麼高大。『朋友們、朋友們,』他說著,『朋友們,我……我……』
但是有些事情讓他講不下去,他未能講完要說的那句話。
就這樣他轉身朝向黑板,拿起一支粉筆,用全身的力氣大大地寫下:『法國萬歲!』
然後他就這樣待著,把頭抵著牆,沒說話,用手勢向我們表示:
『下課了……你們走吧。』」
阿爾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
〈最後一堂課,一位阿爾薩斯小孩所寫〉
(La dernière classe, récit d’un petit Alsacien)
引自《星期一故事集》(Contes du lundi),
巴黎,1873年
初中教育從課程至人事,則達到完全的德意志化。文理中學的教師全都是德國人,在大學課程安排上,大學入學測驗要計入在文理中學的成績,依成績決定能否進入大學就讀。只有宗教機構能有本地人任職其中,但是這些人也受到嚴密監視,並且要聽從公部門指示。除了文理中學,還在主要城市成立一些提供現代課程的職業中學。
史特拉斯堡大學成為威廉皇帝大學(Kaiser-Wilhelm Universität),經過重組並提供相當優良的設備。阿爾薩斯人很快就絡繹不絕地前往就讀,而洛林人因為通過入學測驗的人數很少,前往就讀的人也少。
短暫的現象或是長久延續的目標?
對德國人而言,這些「既成事實」就是確定不變的,應該讓被兼併地區的人們接受,無論使用強制手段、德意志化,還是軟硬兼施,都要花時間來完成。在法國這邊,總統提耶和其後的繼任者都要執行《法蘭克福條約》,並且要對德意志帝國保持低姿態。可是公共輿論則不然,對於阿爾薩斯這塊「美好花園」屈服於俾斯麥「專制」之下,輿論都感到憤慨。
他們以最晦暗的筆法訴說著德國的存在,在這個主題上,有許多例子可舉,比如1878年有一篇刊載於《跨界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的文章,就將阿爾薩斯和洛林景象描繪得非常灰暗。
法國難道就這麼甘於接受「既成事實」?還是在被兼併地域內,鼓動想恢復失地者的情緒和行動,就像俾斯麥所說的,煽動「餘燼覆蓋下的星星之火」?在1870年代末,對戰爭餘悸猶存,沒有人想要看到情勢再度演變如斯。德國領導人想要靠著時間推進,讓「既成事實」能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