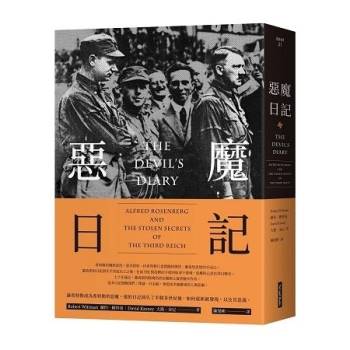1鍥而不捨
二次大戰終戰四年後,有個檢察官正在紐倫堡司法大樓可以容納六百人的法庭裡,等待最後判決出爐。這是最後一批遭美國政府起訴的納粹戰犯,檢察官羅伯。坎普納(Robert Kempner)為了起訴他們盡心竭力,現在只能等待結果。
坎普納時年四十九歲,他生性好鬥頑固,勤於利用情報網絡,喜歡施展計謀,終其一生總把下巴抬得老高,好像要敵人儘管放馬過來——他的敵人還真的不少。儘管坎普納的體型並不出眾,身高只有一百七十公分上下,頭頂漸禿,但擁有一種能讓人追隨他或敵視他的人格特質。喜歡他的人總認為他充滿領袖魅力、努力不懈,是個正義使者,但敵視他的人卻覺得他喜歡賣弄炫耀、固執己見,簡直像個鄉巴佬。
坎普納曾經與希特勒及納粹黨鬥爭了將近二十年,最後四年的較量舞台,是紐倫堡這個曾被希特勒的自大與盟軍的炸彈給摧毀的城市。他曾為了求生存而努力奮鬥,也曾為了他身處的世界大戰貢獻一己之力,而這戰鬥不懈的人生既是他的個人故事,也是那時代許多人的共同際遇。一九三○年代初期,坎普納還只是柏林市的一名年輕警政官員,他極力主張德國政府應該以叛國罪逮捕希特勒與其追隨者,以免他們毀了威瑪共和國,藉此才能夠阻止他們執行納粹黨的恐怖計畫。一九三三年,納粹取得執政權才沒幾天,坎普納這個猶太裔的自由派納粹政敵就被免去官職。一九三五年,他被短暫拘禁並遭蓋世太保偵訊,此後他逃往義大利再到法國,最後落腳美國,在那裡繼續他與納粹之間的鬥爭。他手握大量德國政府的內部文件,並控制著一個線民網絡,因此能幫美國司法部把在美國境內替納粹進行宣傳的人給定罪,而且他提供納粹情報的對象包括戰爭部、神祕的戰略情報局,以及胡佛(J. Edgar Hoover)局長麾下的聯邦調查局。
接下來他的人生轉折彷彿好萊塢劇本,他歸返故里幫美國政府起訴過去的敵人,那些人曾害他丟官,因為他的猶太血統而將他妖魔化,甚至剝奪他的德國公民資格,害他亡命天涯。
在戈林、羅森堡與其他第三帝國高層都在知名的國際大審中,遭到戰爭罪起訴後,坎普納繼續留在紐倫堡幫美國政府處理另外十二個案子,被起訴者是一百七十七名納粹同路人,包括多位利用集中營收容人進行非人道實驗的醫生、負責管理與處決集中營收容人的納粹親衛隊成員、因為強迫勞動而獲利的公司負責人,以及大戰期間在東歐各國負責屠殺平民的處決隊隊長。
由坎普納親自督軍的最後一個案子耗時最久,這編號十一號的案子外號叫作「部長級審判案」(The Ministries Trial),因為大多數被告都是柏林市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上各政府部會的高官。其中名氣最響亮的被告是外交部國務祕書恩斯特。馮。魏茨澤克(Ernst von Weizsäcker),戰時他不但為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鋪路,也有證據顯示,在他的親自批准之下,曾有六千多名猶太人從法國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最惡名昭彰的被告是納粹親衛隊高官戈特洛布。貝格爾(Gottlob Berger),他是一支殘暴行刑隊的指揮官。貝格爾曾在一封信裡這樣描述自己的行刑隊:「多殺兩個波蘭佬也沒什麼了不起,總好過漏掉了兩個沒殺掉。」最令人齒冷的被告莫過於那些銀行家,他們不但出錢蓋集中營,還將滅絕營受害者遺留下來堆積如山的金牙、珠寶與眼鏡全部儲存起來。
審判從一九四七年年底就已經開始,到了此刻,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終於要結案了。三位美國法官走進法庭,坐上位子後,開始高聲朗讀宣判書。宣判書內容總計有八百頁,要三天才能念完。法庭另一頭的納粹被告由憲兵們看守著,他們各個站得筆直,銀盔閃閃發亮,藉由耳機聆聽翻譯成德語的判決內容。最後,二十一名被告裡有十九人被判有罪,其中五人犯下了史無前例、由紐倫堡大審定義的「危害和平罪」。魏茨澤克被判入獄七年,貝格爾二十五年,三位銀行家則是被判五年到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對檢方而言,可說是大獲全勝。過去四年來,他們深入挖掘大量的納粹文件,偵訊過數以百計的證人,終於把最惡劣的被告定罪並送入監獄。他們也向世人昭示,德國政府的各部門與各層級都有大屠殺的共犯。就檢方的描述,如坎普納所言,第三帝國「犯下的罪孽罄竹難書」,檢方也因此強化了紐倫堡是「國際法的最後一道防線」這個歷史定位。他們以強而有力的論證來起訴戰犯。
坎普納與納粹黨鬥了那麼久,他的最高成就莫過於把這些人給定罪。
至少我們可以說,這「應該是」他的最高成就才對。
幾年之內,紐倫堡大審的聲譽就被毀了。
大審開始以來,無論是在德國與美國,都有人想將審判給汙名化。在這些批評者眼裡,起訴行動的核心價值並非伸張正義,而是報仇解恨,至於原本個性就令人討厭的坎普納,眾所皆知他偵訊犯人時無所不用其極,於是他也就成為顯現這次大審不公不義的指標人物。例如,坎普納曾經嚴厲偵訊前納粹外交官弗里德里希。高斯(Friedrich Gaus),期間還威脅高斯,說要把證物都交給蘇聯,讓其以戰爭罪起訴他。也曾有美國檢察官聲稱坎普納的策略「愚不可及」,恐怕會把「紐倫堡大審上的普通罪犯變成烈士」。另一位曾遭坎普納進行交互詰問的證人則表示,「他簡直像蓋世太保一樣兇狠。」
一九四八年,坎普納捲入一場激烈的公開論辯中,挑戰者是質疑審判過程不夠公正的德國新教教會主教特奧菲爾。烏爾恩(Theophil Wurm)。烏爾恩寫了一封公開的抗議信給坎普納,而其對此的回應是:會質疑紐倫堡大審的人,事實上都是「德國人民的公敵」。等到媒體大肆報導這次爭辯時,坎普納發現自己成為德國各大報的公審對象。他被譏諷為一心只想報仇、自以為是的流亡猶太人。
就連美國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也提出批評,因為在他的選區威斯康辛州裡有大量德裔美籍選民。麥卡錫反對起訴魏茨澤克,因為根據他的匿名消息來源指出,魏茨澤克於戰時幫美國在納粹政府裡臥底,貢獻頗多。麥卡錫說,紐倫堡大審阻礙了美國在德國的情蒐工作,並在一九四九年春天的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上指出,起訴魏茨澤克實在是「愚蠢至極」,他打算徹底追查此事。
「我認為,」麥卡錫表示,「本委員會應該搞清楚到底是哪些笨蛋——我是經過深思熟慮才用這字眼——在管理那個軍事法庭。」
所有案子都審判結束後,美國戰犯法庭總計讓一千多位納粹人士被判刑入獄。他們大都遭囚禁在慕尼黑附近的蘭茨貝格監獄(Landsberg Prison)。此時,許多西德人仍然拒絕接受盟軍軍事法庭的判決結果,認為那些納粹囚犯並非戰犯,而是被一個不公不義的司法體系所陷害。
一九四九年,西德選出立國後的第一任總理後,這個問題也成為主要的爭議點,而此時對蘇聯在歐洲的計畫感到不安的美國,也正努力重建原來的敵國,把西德打造成一個非軍事化的忠實盟國。
冷戰爆發後,現實的國際局勢很快便使得戰犯法庭檢察官的成就化為烏有。
美國駐盟國對德高級委員會專任委員在重新檢視判決結果後,於一九五一年釋放了三分之一被定罪的紐倫堡大審戰犯,除了五名死刑犯以外,其餘戰犯均獲減刑。到了該年年底,在「部長級審判案」後被坎普納關進監獄的所有納粹高官皆已獲釋。儘管美國認為減刑乃寬宏大量之舉,但德國人的解讀卻有所不同:他們認為美國人終於承認紐倫堡大審是不公不義的。坎普納也痛批這個決策。他說:「今天,我想公開向世人發出警訊:過早開啟蘭茨貝格監獄大門將導致極權勢力得以重返社會,對自由世界造成威脅。」
沒有人理會他的警告。美國政府高層因為現實的政治考量而做出讓步,到了一九五八年,幾乎所有戰犯都已經獲釋。
但坎普納並未就此放棄,而是繼續努力不懈。他曾浸淫在納粹戰犯的罪證文件裡四年之久,也很清楚,即便紐倫堡大審是在國際媒體的關注之下進行的,世人仍然並不了解納粹犯罪事實的全貌。
第三帝國的餘孽試圖掌握話語權,從修正主義的角度去改寫納粹時代的德國史,這讓他感到憤怒不已,因此訴諸媒體,展開反擊。坎普納投書《紐約先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許多德國政論作家的筆觸多少都帶有明顯的懷舊感,他們向德國民眾傳達的訊息是,要不是當年『元首』的行徑有點失控,他們應該還是會過得很好。」這是他完全無法接受的。許多右派媒體刊登希特勒如天使般的照片,還有軍國主義者主張,要不是希特勒插手軍務,害將軍們打敗仗,德國也不至於受到如此羞辱,也有納粹外交官開始為戰時的德國脫罪,這一切都令他感到悲哀不已。
他呼籲應該在德國出版紐倫堡大審上所提出的罪證。「唯有如此,才能對抗有人明目張膽在這剛萌芽的共和國裡,系統性地荼毒國民的心智。」
不過,就在寫出這一篇充滿開放精神的文章之前,坎普納卻做了一件與其訴求背道而馳的事:坎普納在紐倫堡大審結束後,將盟軍截獲的重要德國文件其中五份正本帶回家——而且,就算有任何複本存在,也沒有人知道它們的下落。
基於檢察官的權責,坎普納有權調閱任何文件,以供他準備起訴工作。他處理文件的方式曾經不只一次遭人質疑。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一日,文書檔案組主任曾在一份備忘錄裡寫道,坎普納的辦公室借走了五份文件,但並未歸還。「也許可以在此一提的是,這絕非本組首次在勸說坎普納博士歸還圖書館的書籍與文件上遭遇極大困難。」
一九四七年,坎普納在美國的檢方同僚間變得惡名昭彰,只因他對那份僅存的大屠殺相關文件之處置不當。當時,第二輪大審剛剛展開,坎普納重返紐倫堡不久後,即派屬下去調閱德國外交部的紀錄,那些文件從藏匿地哈茨山(Harz Mountains)山區搶救出來後,被送往柏林。某天,有位助理湊巧發現一份十五頁的文件,開頭是這樣寫的:「以下人員參與了有關猶太人最終處置問題的討論,討論地點位於柏林郊區大萬湖畔(Am Grossen Wannsee)五十六/五十八號,時間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這就是所謂的萬湖協議書(Wannsee Protocol),記述由萊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所主持的一場會議,他是希姆萊轄下的親衛隊國家安全部部長,會議議題是如何「撤離」歐洲猶太人。
文件被發現的幾個月後,美國檢察官班傑明。費倫茨(Benjamin Ferencz)坐在辦公桌後,看著另一位檢察官查爾斯。拉佛列(Charles LaFollette)衝進自己的辦公室,對他大叫:「我要殺了那個王八蛋!」拉佛列是另一個紐倫堡案件的負責人,工作是起訴納粹所屬的法官與律師。他已經知道有萬湖協議書這份文件,但坎普納不肯交出來。負責紐倫堡案件的許多檢察官之間存在著競爭關係,而坎普納想必是打算在自己的案子開庭時,才把協議書公諸於世。
費倫茨走到坎普納的辦公室去與他交涉,但坎普納否認自己扣住任何文件。費倫茨不肯放過他,又追問了一陣子後,坎普納才打開辦公桌的最下層抽屜,若無其事地問道,「你是說這個嗎?」
拉佛列很快就知道那份協議書對自己的案子有多重要了:第三帝國司法部也曾派代表出席那場重要會議。他立刻跑去找主任檢察官泰爾佛德。泰勒(Telford Taylor)告狀,要求泰勒「開除那個混蛋」!費倫茨跟了過來,並且幫坎普納講話。他告訴泰勒,要是開除了坎普納,那麼「部長級審判案」肯定就辦不下去,更何況坎普納也只是不小心把協議書擺在自己那裡而已。
「我的話沒有任何人肯信,」多年後費倫茨在寫給坎普納的信裡面這樣寫道。無論如何,泰勒終究還是讓他繼續承辦「部長級審判案」。
紐倫堡大審期間,並非只有坎普納把納粹檔案的正本挪為己用。終戰以來,截獲的文件在軍方各文件中心間流通,用飛機運往巴黎、倫敦與華府等地給情報單位進行判讀,也運往紐倫堡作為戰犯法庭的證物。這些檔案在歐洲各地來來去去,讓想要竊取紀念品的人有機可趁,他們的目標是蓋有無所不在的納粹黨口號「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字樣的納粹信紙,而且上面還要有某位重要人士的簽名。負責保管文件的人特別擔心紐倫堡大審的檢方人員,唯恐他們之所以調閱文件,是像某位陸軍軍官在備忘錄裡面所寫的,「與其說是想要伸張正義,不如說是受到記者般的好奇心影響。」另一位觀察者的結論是,紐倫堡檢方的文書檔案組在掌握紀錄流向方面非常不盡責。
有一份被弄丟的關鍵文件是希特勒的軍事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所寫的備忘錄,其內容顯示「元首」早在一九三七年就計畫要征服歐洲。為此,檢察官們在大審期間只能用一份公證過的複本來當作證物。監督終戰時被截獲的德國文件出版工作的史家曾問坎普納那份備忘錄的下落,他回想起自己曾看過,並表示,「正本也許被某個竊取文件當紀念品的人拿走了。」到了一九四六年九月,某個軍方文件中心的管理人員不再出借文件正本給紐倫堡大審的檢方,因為擔心他們不會歸還已經借走的一千份證物。
大審期間,紐倫堡司法大樓裡到處都是文件。一項一九四八年四月完成的調查顯示,「那些行政檔案、媒體底片與新聞稿、影片庫、法庭錄影帶、偵訊報告錄音帶、圖書館書籍與其他出版品、文件正本、影印的資料、文件複本、裝訂成冊的文件、審判摘要、囚犯檔案、偵訊檔案、偵訊檔案的摘要,還有全部法院及員工所做的證物分析抄本」,全部堆起來的體積超過六萬四千立方英尺。
東西多到官員們擔心有人在無意中把文件正本丟進垃圾桶。就像後來坎普納在回憶錄裡面寫道,當時的狀況真是「亂七八糟」,而他真可以說是趁亂胡作非為。
他說很怕那些可能有爆炸性威力的文件未獲妥善保存,所以才會放在自己那裡,以確保它們能好好發揮效用。他在回憶錄裡坦承,大審期間如果有任何「有興趣而且聰明的」研究者向他索取重要文件,他可能就直接把檔案放在辦公室的沙發上,然後在走出門時加上一句:「就當我沒看到。」
他的想法是,與其把「價值不菲的歷史資產」留給可能摧毀它們的政府官僚,不如就託付給值得信賴、志同道合的人,讓它們的內容有面世的機會。
大審後,所有截獲的德國文件正本理應歸還給軍方的各個文件中心,但坎普納想用他收集的文件來撰寫關於納粹時代的文章與書籍。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就在「部長級審判案」判決出爐的前幾天,坎普納收到一封只有一段文字的信函,發信人是檢方文書檔案組主任佛瑞德。尼伯蓋爾(Fred Niebergall):「茲以此函授權政治部會組副檢察長兼主任檢察官羅伯。坎普納博士,將德國紐倫堡戰爭罪大審期間使用的非機密性資料移往他處保留,供其進行調查、寫作、演講與研究。」此一通知非比尋常。後來,某位隸屬於軍情單位的律師甚至非常懷疑,認為以尼伯蓋爾的職務而言,應該不會簽署那種信函。
同一天,坎普納發信給紐約的達頓出版社(E. P. Dutton),附上一本書的提要,是他根據紐倫堡大審期間進行的偵訊工作及德國外交部的文件寫作而成,書名暫定為:「希特勒與他的外交官們」(Hitler and His Diplomats)他早在一月就把書寫好了,某位達頓出版社的編輯對他表達了興趣,並希望能獲知更多細節。
要到後來才會發現,這本書只是坎普納在一九四九年時的出版構想之一。
幾十年後,坎普納在回憶錄裡會解釋他為什麼要從紐倫堡帶走文件。「有一件事我很清楚。當我想寫點東西而得跟各個檔案庫聯絡時,雖然他們會很客氣地答覆我,但卻只會說找不到資料。所以我才會拿走。」
但他這一番說詞根本無法為自己開脫。坎普納其實是希望手裡握有獨家資料,這是其他書寫納粹時代的作家都沒有的重要優勢。
坎普納手握核准函,把他收集的紐倫堡大審文件全都打包,其中還包括他在擔任德國檢察官時代所累積的資料,全部寄回大西洋彼岸的費城郊區住家。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四日,總計超過八千磅的二十九個包裹抵達賓州鐵路的蘭斯唐恩火車站(Lansdowne s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