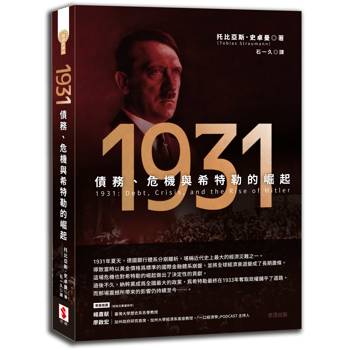第一章 孤掌難鳴的渡鴉
一九三○年一月,維也納經濟學家菲利克斯.索馬利(Felix Somary)前往海德堡大學,就全球經濟前景這一主題發表演說。當時,索馬利是最受世人敬重的分析專家之一。每當有危機逼近,政府各部門的首長、央行主管,以及企業領袖—從奧地利的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家族、德意志帝國銀行(Reichsbank)總裁哈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到隸屬德國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財政部長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都會徵求索馬利的意見。索馬利自稱是一名「政治氣象學家」,他主要是靠著擔任一家位於蘇黎世的小型私人銀行Blankart & Cie.的合夥人來維持生計。財富自由使他敢於對當前世界的概況直言不諱。
索馬利在海德堡的友人想要知道,近期爆發的華爾街股市崩盤事件,是否意味著歐洲地區即將迎來嚴重的經濟衰退。索馬利曾親自在紐約目睹黑色星期四(Black Thursday,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慘況,當日的股市市值在一天之內大跌超過十個百分點。投資人信心崩潰的情況令他感到擔憂,於是他立刻發越洋電報給他在蘇黎世的合夥人:「別讓客戶進場交易,危機才正要開始。」更令他感到震驚的,是歐洲在一個月之後的情況。短短數週之內,奧地利第二大銀行波登信貸公司(Bodencreditanstalt)便喪失清償能力,而比利時第二大銀行布魯塞爾銀行(Banque de Bruxelles)也因為股市崩盤,導致其所持有資產的帳面價值大幅降低。
索馬利向海德堡的聽眾們傳達了非常迫切的訊息:「我相信,維也納及布魯塞爾在十一月時所面臨的慘況,只不過是百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開端而已。這還只是開端,一切才剛揭開序幕,這場危機不會只持續幾週或幾個月,而是會影響我們好幾年的時間。波登信貸公司的垮臺與布魯塞爾銀行的重建不過有如夏季無聲的閃電,我們將會見證更大規模的倒閉潮。」
為什麼索馬利會這麼悲觀呢?在他看來,這兩家銀行所遭遇到的困難並非獨立事件,而是國際根本性失衡的徵兆,這些失衡將以混亂的方式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列強決定保留彼此對戰時債務的索賠權,並決心以高額的賠償金來懲治德國。
按索馬利的說法,這分協議便是導致日後釀下災禍的主因。「是什麼驅使我們步入危機的呢?是無法償還的鉅額債務。歐洲各國應該要向美國償還戰時債務,但是因為沒有人知道這筆資金調動要怎麼長期運作,所有的金額便以賠償債務為由,轉嫁給了德國。」
這一大堆的債務之所以還沒有壓垮德國政府,是因為有短期的私人資本流動在維持穩定。但是根據索馬利的看法,增加這些額外的貸款只是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無法償還債務的事實被短期借貸所掩蓋,而這些借貸的撥款額度從財務上的角度來看是站不住腳的。為了取得貸款,債務國被迫簽署高額利息同意書,同意其農業及工業領域必須支付遠高於其所得的超額利息。這整個體系的崩解,必然會發生在這整個環節之中最薄弱之處。」就連放款銀行也承受不住這場風暴的襲擊。「商業銀行(commercial banks)及專營抵押貸款的銀行(mortgage banks)是將其事業基礎建立在債務人的還款能力之上,同樣的道理,債權國的銀行也是將其事業基礎建立在債務國銀行的還款能力之上。」而無論是就哪一種情況來說,償付能力都是虛構的想像,整個國際金融結構就像是個搖搖欲墜的紙牌屋。
想要防止全面性的崩潰,所剩時間已不多,索馬利提出了警告:「把國家經濟體和國際經濟體拴在一起的這條鎖鏈即將崩裂的危險,比任何人所想像得都還要逼近。也許,隨著這場危機捲起的漩渦,賠款方案與國際政治債務最終都將不復存在,但是很有可能,就連國際私人債務也將遭受到前所未見的衝擊。」一旦局勢開始迅速惡化,德國的處境將會變得特別危險。「隨著危機越演越烈,德國會越來越難以為其短期債務籌措資金,撤回境外資金的風險將會越來越高,最終便將造成國際破產。」
索馬利斷定,如今只有一項策略可以讓整個體制重新取得平衡,那就是促成德法兩國的密切合作。「若是無法實行這項策略,我們將會見識到各國祭出完整的外匯管制機制、進出口禁令,最終迎來的也許不會再是通貨膨脹,而是另外一種會使得我們經濟結構變得更加支離破碎的結果,亦即銀行與公共財政的瓦解。」
一如我們所知,這項策略並沒有付諸實現,而事實也證明了索馬利(附圖1)的看法完全正確。華爾街股市崩盤、奧地利和比利時的銀行問題,並非只是暫時性的騷動,而是現代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的開端。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全球工業生產量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六,直到一九三七年仍未回升至一九二九年的水準。失業率上升至二位數,原物料及加工品的價格分別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六和三十六。全球貿易量實際減少了三分之二。另一方面,索馬利也正確指出了德國是在這整個環節中最弱勢的一方,德國的財政崩塌將會加速全球經濟的劇烈衰退。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間,德國的工業生產量減少了將近百分之五十。
失業率攀升至高於百分之二十,工業部門的失業率更是衝破了百分之三十。實質GDP的降幅大約為百分之二十五,人均實質GDP則下降了百分之十七。此外,正如索馬利所預測的,隨著危機逐漸擴大,賠償方案及戰時債務最終都被予以縮減或撤銷,德國積欠外國銀行的債務也一併遭到凍結。全球經濟體被分散成了數種貨幣陣營及貿易集團,為全球化的時代畫下了句點。
索馬利為什麼能夠如此準確地預料到經濟體系將會崩塌呢?
其身家背景是箇中原因之一。他曾就讀維也納大學,並曾擔任當代頂尖經濟學家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的助理。後來成為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在銀行家及政治顧問方面,擁有相當豐富的實務經驗。一九○五年,二十四歲的索馬利進入英奧銀行(Anglo-Austrian Bank)就業,這間位於維也納的銀行是由來自倫敦市的一群顯赫銀行家所成立,其中一位即為厄尼斯特.卡塞爾爵士(Sir Ernest Cassel)。索馬利在英奧銀行擔任常務董事的助理,因此每一筆重要的交易,他幾乎都有參與。當時在英奧銀行(Anglobank),主要的營業項目為東歐及巴爾幹半島的企業融資,為此,索馬利必須對該歐洲區域尤為動盪的政治及社會條件具備深厚的知識。一九○九年,索馬利以獨立講師、銀行家及德國政府顧問的身分前往柏林工作,使他對於歐洲政治及外交的內部運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索馬利和知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合擬了一分報告給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Emperor Wilhelm II),表態反對將戰事升級至擴大潛艇戰。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索馬利挽救了奧地利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鉅額家產,將之轉移到位於蘇黎世的小型私人銀行Blankart & Cie.。不久之後,索馬利便成為了這家銀行的合夥人。索馬利之所以能夠做出精準預測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對於迫在眉睫的大災難擁有很強的第六感。索馬利的友人—瑞士外交官卡爾.雅各布.布爾克哈特(Carl Jacob Burckhardt)在寫給奧地利作家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的信中說道:「有個古怪的傢伙你也認識,就是索馬利⋯⋯他是能夠預見危機的人;他在政治方面也很有遠見。我從他那裡聽到的預言全都成真了,有些預言更是以十足令人驚奇的方式實現的。」索馬利曾經對自己的兒子說過:「我可以從我的骨子裡感知到未來,而不是單憑知識去推敲。未來不是浮現在我的腦海,而是在骨髓。」索馬利如此神通廣大,然而他其實並不知道所謂的「內幕」。他所做的就只是收集各方資訊,再把一個個的點逐一連接成線而已。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國際之間的情勢明顯已劇烈失衡。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而德國是最大的債務國(圖示1.1)。比利時、法國、英國及義大利的外債結餘雖然是幾乎打平,但是這些國家的帳目仍須取決於德國向其支付賠款的意願與能力。一如《經濟學人》雜誌所做的評論,協約國列強與德國之間形成了一道枷鎖,被「政府間債務的龐大結構」給束縛在 一起。
一九三○年一月,維也納經濟學家菲利克斯.索馬利(Felix Somary)前往海德堡大學,就全球經濟前景這一主題發表演說。當時,索馬利是最受世人敬重的分析專家之一。每當有危機逼近,政府各部門的首長、央行主管,以及企業領袖—從奧地利的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家族、德意志帝國銀行(Reichsbank)總裁哈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到隸屬德國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財政部長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都會徵求索馬利的意見。索馬利自稱是一名「政治氣象學家」,他主要是靠著擔任一家位於蘇黎世的小型私人銀行Blankart & Cie.的合夥人來維持生計。財富自由使他敢於對當前世界的概況直言不諱。
索馬利在海德堡的友人想要知道,近期爆發的華爾街股市崩盤事件,是否意味著歐洲地區即將迎來嚴重的經濟衰退。索馬利曾親自在紐約目睹黑色星期四(Black Thursday,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慘況,當日的股市市值在一天之內大跌超過十個百分點。投資人信心崩潰的情況令他感到擔憂,於是他立刻發越洋電報給他在蘇黎世的合夥人:「別讓客戶進場交易,危機才正要開始。」更令他感到震驚的,是歐洲在一個月之後的情況。短短數週之內,奧地利第二大銀行波登信貸公司(Bodencreditanstalt)便喪失清償能力,而比利時第二大銀行布魯塞爾銀行(Banque de Bruxelles)也因為股市崩盤,導致其所持有資產的帳面價值大幅降低。
索馬利向海德堡的聽眾們傳達了非常迫切的訊息:「我相信,維也納及布魯塞爾在十一月時所面臨的慘況,只不過是百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開端而已。這還只是開端,一切才剛揭開序幕,這場危機不會只持續幾週或幾個月,而是會影響我們好幾年的時間。波登信貸公司的垮臺與布魯塞爾銀行的重建不過有如夏季無聲的閃電,我們將會見證更大規模的倒閉潮。」
為什麼索馬利會這麼悲觀呢?在他看來,這兩家銀行所遭遇到的困難並非獨立事件,而是國際根本性失衡的徵兆,這些失衡將以混亂的方式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列強決定保留彼此對戰時債務的索賠權,並決心以高額的賠償金來懲治德國。
按索馬利的說法,這分協議便是導致日後釀下災禍的主因。「是什麼驅使我們步入危機的呢?是無法償還的鉅額債務。歐洲各國應該要向美國償還戰時債務,但是因為沒有人知道這筆資金調動要怎麼長期運作,所有的金額便以賠償債務為由,轉嫁給了德國。」
這一大堆的債務之所以還沒有壓垮德國政府,是因為有短期的私人資本流動在維持穩定。但是根據索馬利的看法,增加這些額外的貸款只是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無法償還債務的事實被短期借貸所掩蓋,而這些借貸的撥款額度從財務上的角度來看是站不住腳的。為了取得貸款,債務國被迫簽署高額利息同意書,同意其農業及工業領域必須支付遠高於其所得的超額利息。這整個體系的崩解,必然會發生在這整個環節之中最薄弱之處。」就連放款銀行也承受不住這場風暴的襲擊。「商業銀行(commercial banks)及專營抵押貸款的銀行(mortgage banks)是將其事業基礎建立在債務人的還款能力之上,同樣的道理,債權國的銀行也是將其事業基礎建立在債務國銀行的還款能力之上。」而無論是就哪一種情況來說,償付能力都是虛構的想像,整個國際金融結構就像是個搖搖欲墜的紙牌屋。
想要防止全面性的崩潰,所剩時間已不多,索馬利提出了警告:「把國家經濟體和國際經濟體拴在一起的這條鎖鏈即將崩裂的危險,比任何人所想像得都還要逼近。也許,隨著這場危機捲起的漩渦,賠款方案與國際政治債務最終都將不復存在,但是很有可能,就連國際私人債務也將遭受到前所未見的衝擊。」一旦局勢開始迅速惡化,德國的處境將會變得特別危險。「隨著危機越演越烈,德國會越來越難以為其短期債務籌措資金,撤回境外資金的風險將會越來越高,最終便將造成國際破產。」
索馬利斷定,如今只有一項策略可以讓整個體制重新取得平衡,那就是促成德法兩國的密切合作。「若是無法實行這項策略,我們將會見識到各國祭出完整的外匯管制機制、進出口禁令,最終迎來的也許不會再是通貨膨脹,而是另外一種會使得我們經濟結構變得更加支離破碎的結果,亦即銀行與公共財政的瓦解。」
一如我們所知,這項策略並沒有付諸實現,而事實也證明了索馬利(附圖1)的看法完全正確。華爾街股市崩盤、奧地利和比利時的銀行問題,並非只是暫時性的騷動,而是現代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的開端。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全球工業生產量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六,直到一九三七年仍未回升至一九二九年的水準。失業率上升至二位數,原物料及加工品的價格分別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六和三十六。全球貿易量實際減少了三分之二。另一方面,索馬利也正確指出了德國是在這整個環節中最弱勢的一方,德國的財政崩塌將會加速全球經濟的劇烈衰退。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間,德國的工業生產量減少了將近百分之五十。
失業率攀升至高於百分之二十,工業部門的失業率更是衝破了百分之三十。實質GDP的降幅大約為百分之二十五,人均實質GDP則下降了百分之十七。此外,正如索馬利所預測的,隨著危機逐漸擴大,賠償方案及戰時債務最終都被予以縮減或撤銷,德國積欠外國銀行的債務也一併遭到凍結。全球經濟體被分散成了數種貨幣陣營及貿易集團,為全球化的時代畫下了句點。
索馬利為什麼能夠如此準確地預料到經濟體系將會崩塌呢?
其身家背景是箇中原因之一。他曾就讀維也納大學,並曾擔任當代頂尖經濟學家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的助理。後來成為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在銀行家及政治顧問方面,擁有相當豐富的實務經驗。一九○五年,二十四歲的索馬利進入英奧銀行(Anglo-Austrian Bank)就業,這間位於維也納的銀行是由來自倫敦市的一群顯赫銀行家所成立,其中一位即為厄尼斯特.卡塞爾爵士(Sir Ernest Cassel)。索馬利在英奧銀行擔任常務董事的助理,因此每一筆重要的交易,他幾乎都有參與。當時在英奧銀行(Anglobank),主要的營業項目為東歐及巴爾幹半島的企業融資,為此,索馬利必須對該歐洲區域尤為動盪的政治及社會條件具備深厚的知識。一九○九年,索馬利以獨立講師、銀行家及德國政府顧問的身分前往柏林工作,使他對於歐洲政治及外交的內部運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索馬利和知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合擬了一分報告給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Emperor Wilhelm II),表態反對將戰事升級至擴大潛艇戰。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索馬利挽救了奧地利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鉅額家產,將之轉移到位於蘇黎世的小型私人銀行Blankart & Cie.。不久之後,索馬利便成為了這家銀行的合夥人。索馬利之所以能夠做出精準預測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對於迫在眉睫的大災難擁有很強的第六感。索馬利的友人—瑞士外交官卡爾.雅各布.布爾克哈特(Carl Jacob Burckhardt)在寫給奧地利作家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的信中說道:「有個古怪的傢伙你也認識,就是索馬利⋯⋯他是能夠預見危機的人;他在政治方面也很有遠見。我從他那裡聽到的預言全都成真了,有些預言更是以十足令人驚奇的方式實現的。」索馬利曾經對自己的兒子說過:「我可以從我的骨子裡感知到未來,而不是單憑知識去推敲。未來不是浮現在我的腦海,而是在骨髓。」索馬利如此神通廣大,然而他其實並不知道所謂的「內幕」。他所做的就只是收集各方資訊,再把一個個的點逐一連接成線而已。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國際之間的情勢明顯已劇烈失衡。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而德國是最大的債務國(圖示1.1)。比利時、法國、英國及義大利的外債結餘雖然是幾乎打平,但是這些國家的帳目仍須取決於德國向其支付賠款的意願與能力。一如《經濟學人》雜誌所做的評論,協約國列強與德國之間形成了一道枷鎖,被「政府間債務的龐大結構」給束縛在 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