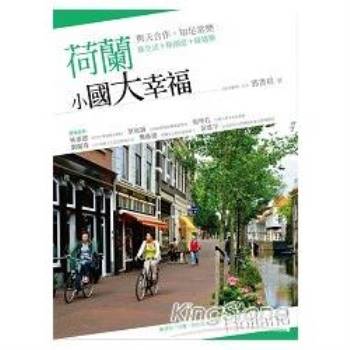02 與水共舞的浪漫風情
我和英國友人東尼,在錯綜複雜的阿姆斯特丹街頭閒逛時不慎迷失了方向。
「別堅持了,我們來問路吧 !」於是我開口向第一個迎面而來的路人,詢問中央車站的方向。
條條運河環繞中央車站
「中央車站?簡單得很。」擁有典型荷蘭外貌的高大路人,耐心地向我們說明:「我教你們一個祕訣:你們走到哪裡都會碰到運河對吧?只要往這些弧形河道的圓心前進,就會抵達中央車站了。你們難道不知道,阿姆斯特丹正是以這些半同心圓形狀的運河河道聞名的嗎?」
直到我回家補做了功課,才發現荷蘭首府阿姆斯特丹縱橫的運河水道, 原來規劃得如城市街道般驚人地整齊;而環繞在阿姆斯特丹城市外圍,長達一百三十五公里的環狀水線(Stelling van Amsterdam),更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 N E S C O)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建設。原來,我膚淺的眼光只顧著偷瞄紅燈區櫥窗內的性感女郎,殊不知腳下踩過的河道與橋樑,承載的是集結了前人血汗、令世人為之讚嘆的建築成就。
「人們只要聽說我是荷蘭來的,就立刻認為我是水上專家。」一名台夫特科技大學建築系的荷蘭交換生,來到人才濟濟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時如此感嘆。
擁有私人船隻不稀奇
荷蘭人所居住的這片與北海共生存的土地,可說是用運河、橋樑與堤防連結起來的,這樣的先天環境使荷蘭人的生活無可避免地與水息息相關。四通八達的水道,不僅形成了自古以來的防禦水線,同時也造就了完整的水運系統, 使第一大港鹿特丹成為歐陸重要轉運港;與此同時,這些縱橫水道也帶來了荷蘭獨有的各種水上風情與文化,這是其他立足於「正常」陸面上的國家人民無法想像的世界。荷蘭人似乎打定主意,要用「水」讓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荷蘭人甲:「你決定要買車還是買船了嗎?」
荷蘭人乙:「還在考慮。買車似乎比較實際,但是停車問題很麻煩,而且我一直想和其他人一樣,晴朗的時候就開船來趟愜意的運河之旅。不過話說回來,一年之中天氣好的日子又有多少呢?何況冬季一旦河面結冰,就哪裡也去不了??」
以上的對話,大概也只有在荷蘭才能聽到吧 !
事實上,擁有私人船隻的荷蘭人還不在少數。若你有幸住在靠河的區域, 這些運河內的船隻功能就像路面上的汽車一樣,不僅可以作為每日的通勤工具,也可以充當開派對的理想地點,而市政府也為船隻的停泊規劃出如路面停車格一樣的「停船格」。在首都阿姆斯特丹,除了私人船隻之外,還有各種觀光遊艇、任意上下(Hop On Hop Off)的運河巴士,甚至有同樣漆成小黃顏色的「計程船」(Water Taxi),讓河面交通的盛況毫不亞於車水馬龍的街頭。就連聖尼可拉斯(Sinterklaas,類似荷蘭版的聖誕老人)每年十二月進城時,搭的也不是馴鹿拉的雪橇,而是和隨從黑彼得(Zwarte Piet)們一同搭著小船從河港登陸,為孩童們帶來糖果和歡笑呢。
特別節日最怕「塞船」
至於每逢女王節(Koninginnedag,慶祝朱莉安娜女王的生日)等大型節日當天,阿姆斯特丹運河內便塞滿了大大小小的船隻,從放著震耳欲聾音樂的大型船趴,到三五好友自行聚會暢飲的小型動力船,硬是將全城的河道擠成名符其實的水洩不通。當其他城市飽受塞車之苦時,荷蘭人此時面對的則是「塞船」的畫面。不同之處在於,這些作為替代交通的船隻不僅減少了廢氣污染, 即使塞在綠意盎然的河道上動彈不得時,依舊為城市街頭添了一分詩情畫意。
不僅在阿姆斯特丹,荷蘭許多城市都擁有這般迷人的小橋流水風情。這些人造運河,在從前的歲月中一度扮演了重要的運輸功能。如今由於多數的小巧運河都不適用大型現代商船的行駛,這種水面貿易的繁榮景象如今已不多見, 而今日在許多古貿易城鎮留下的「計量所」(Waag)則成了歷史見證的建築。所謂的計量所,最初建造的目的是為了稱量貿易商船沿著運河載來的起司及農產品,因此計量所經常建於鄰近碼頭的地帶,或至少也是人力搬運可及的交易廣場。如今這些古蹟級的計量所已不再作為貿易秤量之用,而是成為現代音樂會的演出地點,或是十二月時聖尼可拉斯和小朋友相見歡的場所,或甚至如阿克馬或豪達(Gouda)等地,傳統的起司交易市場被刻意保留下來,做為娛樂觀光客的噱頭。
荷蘭四面八方通達的運河網絡為荷蘭人帶來了得天獨厚的水上綠生活。不過,要想來一趟浪漫的遊船之旅,除了坐擁前人留下的水道工程外,後人的經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試想,若人人喝完啤酒,便將手中的空罐順勢往河面扔去,這些美麗的運河很快就變得臭氣熏天。所幸,荷蘭人截至目前為止,只有將偷來的腳踏車扔進河裡的習慣(至少比扔垃圾好多了),不時也可看到市政府派出的河道清潔船在河面打撈廢棄物。青蛙王國的水面世界,今日也才得以繼續造福青蛙國民。
荷蘭水線化身觀光車道
實際上,這些規劃整齊、頗具觀光吸引力的運河,一度也扮演了重要的軍事防禦功能。早在正式的防禦水線出現之前,歷史上已記載荷蘭人故意開放堤防,使河川上漲或是使被侵略的土地淹沒,使敵軍無法入侵。
一五七四年的八○年戰爭期間,荷蘭奧倫治親王(Prince of Orange)矢志捍衛西班牙軍包圍的萊登城,當時也採取了利用運河水道的策略。親王下令擊破堤防,使大水灌注萊登城外土地,同時萊登市民在彈盡糧絕的狀態下,和西班牙軍整整僵持了三個月。最後終於在天候配合下,萊登城外河水暴漲,荷蘭援軍艦艇得以順利駛入。十月三日,西班牙王朝終於捨棄了這塊泡在爛泥中的沼澤地打道回府,而解放軍也總算及時帶來糧食,解救了飢腸轆轆的受困市民。
著名的荷蘭水線(Holland Water Line)就是這種破堤灌水的古老戰略現代版。在低窪運河處設置閘門,一旦受到敵人攻擊時,便引導河水淹沒鄰近土地,必要時還可以讓戰略艦艇長驅直入。而沿著水線的防禦碉堡則建造在較高的地勢上,漲水時便可成為防衛基地。這樣的戰略幫助了荷蘭人將西班牙王朝的勢力驅逐出境,也在許多重要戰爭中奏效,直到近代二次大戰時,開著轟炸機的德軍不再採取陸軍攻勢,荷蘭水線這才失去了效用。如今荷蘭境內多處的防禦水線,大多用來滿足荷蘭人的另一種愛好:觀光用環河單車道。
星形堡壘成林間明星
時至今日,當年沿著防禦水線建造的堡壘,多半成為與世無爭的寧靜小鎮,只有從前遺留下來的砲台和城牆等遺跡,回味著以往的歷史。而利用護城運河建造出的星形堡壘,便成了空拍圖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美麗記號。雖然歐洲各地都有星形堡壘的建築,但荷蘭的星形堡壘仍是數量最多,也通常最受觀光客歡迎。位於荷德邊境的布坦吉堡壘(Vesting Bourtange),同樣是當年奧倫治親王為抵抗西班牙軍所下令建造的戰略機地。如今的布坦吉堡壘形狀保存完整,從空中鳥瞰下來,兩道護城河勾勒出一枚鑲著邊框的星星圖案,夢幻的形狀彷彿置身童話世界。踩著單車繞行時,從前的防禦要塞,似乎也搖身成為掉落林間棲息的一顆明星。
另一座饒富趣味的四角星形堡壘盧沃瑞堡(Fort de Roovere),雖然不如擁有完整五角形的堡壘來得知名,但由於二○一一年荷蘭建築師的一道神來之筆,頓時吸引了建築界的注目。由於荷蘭政府近年致力於防禦水線的保存與觀光路線,盧沃瑞堡的護城河也需要一條聯外橋樑。由於不願破壞原本護城河的水線與防禦性質的歷史意義,荷蘭R O與A D建築事務所(RO and AD Architecture)設計出一道隱藏於水面下的隱形橋樑。從遠方望去,完全看不到橋樑的存在,而走進一看,水面竟如摩西過紅海般被分出一道小徑。這座暱稱為「摩西橋」的設計,橋體經過無毒處理的耐久環保材料,使今日的修復與昔日的風光,毫無衝突地共存一處。15獨立不遺世的北方威尼斯:羊角村
若說荷蘭北方的羊角村(Giethoorn)是座遺世獨居的世外桃源,可以說對,也可以說不對。
我頭一次造訪羊角村是在初春的平日週間。我和友人一同從阿姆斯特丹出發,一路換乘火車、當地巴士,最後還坐上必須打電話叫車的私家計程車, 才風塵僕僕抵達了這座遠離塵世的小鎮。但是我們完全沒有抱怨,因為當我們站在有如藍色小精靈居住的寧靜童話村落中間,看見那一座座沿著小河排列、庭園與外牆上裝飾著繽紛鮮花的尖頂蘆葦屋時,再沉重的旅途疲累都不足掛齒了。
夜間,大片的星空籠罩著河流匯聚的湖泊,四周只聽得見潺潺的流水聲和不知名的低頻蟲鳴。我拉著友人率性躺在橫跨運河的美麗小橋上,讓深沉的黑暗包裹著我們,周遭的微弱光源只來自頭頂上的月光,以及在河邊閃爍著暈黃燈光的低矮路燈。
我跟自己說,我願意再重返這個地方,多少次都可以。
第二次來到羊角村是觀光旺季的夏日,我帶著前來歐洲旅遊的家人踏上兩年前同樣的路程。美到令人屏息的蘆葦屋依舊,只是這回小小的村落塞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走在運河沿岸的蜿蜒小徑上,不時都得停下等待人們拍完照。而映著綠波的狹窄河道中,也壅塞著一艘艘供遊客體驗水上生活的搖槳船、獨木舟、電動船和撐篙平底船。我不禁小小抱怨起不該在旺季時到觀光勝地人擠人。
「人多沒關係,這麼美麗的地方,本來就值得讓更多的人看見呀。」我的母親倒是豁達地笑道。
所幸,在白天的擾攘過後,由於夜間所有水上活動不再營運,羊角村那股桃花源般的靜謐氛圍,終於在入夜時分再度降臨在我們周遭。
冬暖夏涼的蘆葦茅草
綠蔭盎然的羊角村建立於十三世紀,最常見的說法是,第一批來到這片沼澤地的農民,在開墾時發現許多羊角遺骸,推測這些山羊是溺死於一一七○年的洪水,因此該地便被命名為羊角村。
羊角村於是發展成一座美輪美奐的小鎮,至今的居民仍不超過三千人。據傳,剛來到這片泥濘窪地的是一群窮困農人,他們由於無法負擔磚瓦的價格,於是以濕地上隨手可得的蘆葦茅草搭建房舍,但乍聽之下寒酸的建材,實際上卻具有冬暖夏涼、防雨耐熱的優點。如今,羊角村已成為炙手可熱的觀光景點,蘆葦也翻身成為比磚瓦更高價的建材。這些原本是窮人住處的天然蘆葦屋,如今則是反諷地成為動輒要價數千萬台幣的富人別墅,這想必是最初迫於生活無奈的人們無法預料的未來。
儘管多少經過翻修,羊角村的建築造型基本上仍維持傳統的蘆葦屋頂樣式。這些完整保留的蘆葦屋少了城市僵硬的鋼筋水泥感,和周遭的天然風光和諧地融為一體,而當地居民也充分發揮荷蘭人酷愛綠化的習性,紛紛將自宅的獨立小屋四周整理成爭妍鬥豔的綺麗花園。
無車地帶的自在優遊
除了天然取材的建築造型外,羊角村更令人流連忘返的另一項主要原因, 在於這是個完全的「無車地帶」,這也是為何通往這個小村落需要如此大費周章的交通轉乘。從一開始,羊角村裡便沒有道路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數十道橋樑和運河裡的船隻,甚至許多美麗的蘆葦屋舍是座落在孤島上,必須越過唯一的聯外橋樑才能抵達。不難想像,羊角村便因此獲得了「北方威尼斯」的封號。雖然,今日沿著運河河道拓建了對荷蘭人而言同樣重要的腳踏車道,但依然沒有可供車輛通行的車道,人們若要運送大件貨物,只有船運一途。
少了車輛的廢氣與噪音,羊角村保留的是純淨的空氣,以及青蛙國人對「水」的一貫敬重。這座往來運輸主要靠水道進行的小村落,無疑為荷蘭人長期以來伴水而居的共存關係,再一次作了美麗見證。
綠波水面的美麗驚豔
我和家人投宿在標榜傳統蘆葦屋建築的私人民宿,享受在水光鳥鳴間醒轉的幸福感受。第二天,我們向民宿主人租了電動馬達操控的小船,準備來趟羊角村水道探密之旅。由於羊角村的特殊需求,這裡的民宿幾乎都備有船隻和腳踏車出租的服務。
我們先在水道裡打轉了一陣,對馬達小船的操縱稍為熟悉後,我們便沿著蜿蜒的運河排水前進,同樣穿梭在水道上的是悠哉游水的野鴨和互相點頭微笑的其他遊客。一邊喝著冰涼的啤酒,一邊徜徉在綠波水面上,我無法祈求更奢侈的享受。
這樣的悠閒享受一直到我們的小船穿過整座相連的內陸湖,發現怎麼開也開不回原來的村落時,我們才稍為驚慌了一陣。原來羊角村儘管迷你,四周連接的水道和湖泊卻是一片巨大的水道網絡,迷失方向的我們差一點就一路開到運河相通的另一座小鎮。
我們在繞行半天後總算開回民宿所在的河道,民宿主人已經騎著單車焦急地沿著岸邊小徑搜尋我們的蹤影。儘管早已超出我們租船的一小時期限,臉頰圓胖的民宿主人卻笑著說道:「不用加錢啦 !看到你們平安歸來我就放心了。」
或許這是民宿老闆的和氣生財之道吧,但我寧願這麼相信:正是由於這與世無爭的寧靜生活,讓居住在這可愛小村落裡的居民們,也擁有彷彿來自烏托邦世界的善良心境。
我和英國友人東尼,在錯綜複雜的阿姆斯特丹街頭閒逛時不慎迷失了方向。
「別堅持了,我們來問路吧 !」於是我開口向第一個迎面而來的路人,詢問中央車站的方向。
條條運河環繞中央車站
「中央車站?簡單得很。」擁有典型荷蘭外貌的高大路人,耐心地向我們說明:「我教你們一個祕訣:你們走到哪裡都會碰到運河對吧?只要往這些弧形河道的圓心前進,就會抵達中央車站了。你們難道不知道,阿姆斯特丹正是以這些半同心圓形狀的運河河道聞名的嗎?」
直到我回家補做了功課,才發現荷蘭首府阿姆斯特丹縱橫的運河水道, 原來規劃得如城市街道般驚人地整齊;而環繞在阿姆斯特丹城市外圍,長達一百三十五公里的環狀水線(Stelling van Amsterdam),更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 N E S C O)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建設。原來,我膚淺的眼光只顧著偷瞄紅燈區櫥窗內的性感女郎,殊不知腳下踩過的河道與橋樑,承載的是集結了前人血汗、令世人為之讚嘆的建築成就。
「人們只要聽說我是荷蘭來的,就立刻認為我是水上專家。」一名台夫特科技大學建築系的荷蘭交換生,來到人才濟濟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時如此感嘆。
擁有私人船隻不稀奇
荷蘭人所居住的這片與北海共生存的土地,可說是用運河、橋樑與堤防連結起來的,這樣的先天環境使荷蘭人的生活無可避免地與水息息相關。四通八達的水道,不僅形成了自古以來的防禦水線,同時也造就了完整的水運系統, 使第一大港鹿特丹成為歐陸重要轉運港;與此同時,這些縱橫水道也帶來了荷蘭獨有的各種水上風情與文化,這是其他立足於「正常」陸面上的國家人民無法想像的世界。荷蘭人似乎打定主意,要用「水」讓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荷蘭人甲:「你決定要買車還是買船了嗎?」
荷蘭人乙:「還在考慮。買車似乎比較實際,但是停車問題很麻煩,而且我一直想和其他人一樣,晴朗的時候就開船來趟愜意的運河之旅。不過話說回來,一年之中天氣好的日子又有多少呢?何況冬季一旦河面結冰,就哪裡也去不了??」
以上的對話,大概也只有在荷蘭才能聽到吧 !
事實上,擁有私人船隻的荷蘭人還不在少數。若你有幸住在靠河的區域, 這些運河內的船隻功能就像路面上的汽車一樣,不僅可以作為每日的通勤工具,也可以充當開派對的理想地點,而市政府也為船隻的停泊規劃出如路面停車格一樣的「停船格」。在首都阿姆斯特丹,除了私人船隻之外,還有各種觀光遊艇、任意上下(Hop On Hop Off)的運河巴士,甚至有同樣漆成小黃顏色的「計程船」(Water Taxi),讓河面交通的盛況毫不亞於車水馬龍的街頭。就連聖尼可拉斯(Sinterklaas,類似荷蘭版的聖誕老人)每年十二月進城時,搭的也不是馴鹿拉的雪橇,而是和隨從黑彼得(Zwarte Piet)們一同搭著小船從河港登陸,為孩童們帶來糖果和歡笑呢。
特別節日最怕「塞船」
至於每逢女王節(Koninginnedag,慶祝朱莉安娜女王的生日)等大型節日當天,阿姆斯特丹運河內便塞滿了大大小小的船隻,從放著震耳欲聾音樂的大型船趴,到三五好友自行聚會暢飲的小型動力船,硬是將全城的河道擠成名符其實的水洩不通。當其他城市飽受塞車之苦時,荷蘭人此時面對的則是「塞船」的畫面。不同之處在於,這些作為替代交通的船隻不僅減少了廢氣污染, 即使塞在綠意盎然的河道上動彈不得時,依舊為城市街頭添了一分詩情畫意。
不僅在阿姆斯特丹,荷蘭許多城市都擁有這般迷人的小橋流水風情。這些人造運河,在從前的歲月中一度扮演了重要的運輸功能。如今由於多數的小巧運河都不適用大型現代商船的行駛,這種水面貿易的繁榮景象如今已不多見, 而今日在許多古貿易城鎮留下的「計量所」(Waag)則成了歷史見證的建築。所謂的計量所,最初建造的目的是為了稱量貿易商船沿著運河載來的起司及農產品,因此計量所經常建於鄰近碼頭的地帶,或至少也是人力搬運可及的交易廣場。如今這些古蹟級的計量所已不再作為貿易秤量之用,而是成為現代音樂會的演出地點,或是十二月時聖尼可拉斯和小朋友相見歡的場所,或甚至如阿克馬或豪達(Gouda)等地,傳統的起司交易市場被刻意保留下來,做為娛樂觀光客的噱頭。
荷蘭四面八方通達的運河網絡為荷蘭人帶來了得天獨厚的水上綠生活。不過,要想來一趟浪漫的遊船之旅,除了坐擁前人留下的水道工程外,後人的經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試想,若人人喝完啤酒,便將手中的空罐順勢往河面扔去,這些美麗的運河很快就變得臭氣熏天。所幸,荷蘭人截至目前為止,只有將偷來的腳踏車扔進河裡的習慣(至少比扔垃圾好多了),不時也可看到市政府派出的河道清潔船在河面打撈廢棄物。青蛙王國的水面世界,今日也才得以繼續造福青蛙國民。
荷蘭水線化身觀光車道
實際上,這些規劃整齊、頗具觀光吸引力的運河,一度也扮演了重要的軍事防禦功能。早在正式的防禦水線出現之前,歷史上已記載荷蘭人故意開放堤防,使河川上漲或是使被侵略的土地淹沒,使敵軍無法入侵。
一五七四年的八○年戰爭期間,荷蘭奧倫治親王(Prince of Orange)矢志捍衛西班牙軍包圍的萊登城,當時也採取了利用運河水道的策略。親王下令擊破堤防,使大水灌注萊登城外土地,同時萊登市民在彈盡糧絕的狀態下,和西班牙軍整整僵持了三個月。最後終於在天候配合下,萊登城外河水暴漲,荷蘭援軍艦艇得以順利駛入。十月三日,西班牙王朝終於捨棄了這塊泡在爛泥中的沼澤地打道回府,而解放軍也總算及時帶來糧食,解救了飢腸轆轆的受困市民。
著名的荷蘭水線(Holland Water Line)就是這種破堤灌水的古老戰略現代版。在低窪運河處設置閘門,一旦受到敵人攻擊時,便引導河水淹沒鄰近土地,必要時還可以讓戰略艦艇長驅直入。而沿著水線的防禦碉堡則建造在較高的地勢上,漲水時便可成為防衛基地。這樣的戰略幫助了荷蘭人將西班牙王朝的勢力驅逐出境,也在許多重要戰爭中奏效,直到近代二次大戰時,開著轟炸機的德軍不再採取陸軍攻勢,荷蘭水線這才失去了效用。如今荷蘭境內多處的防禦水線,大多用來滿足荷蘭人的另一種愛好:觀光用環河單車道。
星形堡壘成林間明星
時至今日,當年沿著防禦水線建造的堡壘,多半成為與世無爭的寧靜小鎮,只有從前遺留下來的砲台和城牆等遺跡,回味著以往的歷史。而利用護城運河建造出的星形堡壘,便成了空拍圖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美麗記號。雖然歐洲各地都有星形堡壘的建築,但荷蘭的星形堡壘仍是數量最多,也通常最受觀光客歡迎。位於荷德邊境的布坦吉堡壘(Vesting Bourtange),同樣是當年奧倫治親王為抵抗西班牙軍所下令建造的戰略機地。如今的布坦吉堡壘形狀保存完整,從空中鳥瞰下來,兩道護城河勾勒出一枚鑲著邊框的星星圖案,夢幻的形狀彷彿置身童話世界。踩著單車繞行時,從前的防禦要塞,似乎也搖身成為掉落林間棲息的一顆明星。
另一座饒富趣味的四角星形堡壘盧沃瑞堡(Fort de Roovere),雖然不如擁有完整五角形的堡壘來得知名,但由於二○一一年荷蘭建築師的一道神來之筆,頓時吸引了建築界的注目。由於荷蘭政府近年致力於防禦水線的保存與觀光路線,盧沃瑞堡的護城河也需要一條聯外橋樑。由於不願破壞原本護城河的水線與防禦性質的歷史意義,荷蘭R O與A D建築事務所(RO and AD Architecture)設計出一道隱藏於水面下的隱形橋樑。從遠方望去,完全看不到橋樑的存在,而走進一看,水面竟如摩西過紅海般被分出一道小徑。這座暱稱為「摩西橋」的設計,橋體經過無毒處理的耐久環保材料,使今日的修復與昔日的風光,毫無衝突地共存一處。15獨立不遺世的北方威尼斯:羊角村
若說荷蘭北方的羊角村(Giethoorn)是座遺世獨居的世外桃源,可以說對,也可以說不對。
我頭一次造訪羊角村是在初春的平日週間。我和友人一同從阿姆斯特丹出發,一路換乘火車、當地巴士,最後還坐上必須打電話叫車的私家計程車, 才風塵僕僕抵達了這座遠離塵世的小鎮。但是我們完全沒有抱怨,因為當我們站在有如藍色小精靈居住的寧靜童話村落中間,看見那一座座沿著小河排列、庭園與外牆上裝飾著繽紛鮮花的尖頂蘆葦屋時,再沉重的旅途疲累都不足掛齒了。
夜間,大片的星空籠罩著河流匯聚的湖泊,四周只聽得見潺潺的流水聲和不知名的低頻蟲鳴。我拉著友人率性躺在橫跨運河的美麗小橋上,讓深沉的黑暗包裹著我們,周遭的微弱光源只來自頭頂上的月光,以及在河邊閃爍著暈黃燈光的低矮路燈。
我跟自己說,我願意再重返這個地方,多少次都可以。
第二次來到羊角村是觀光旺季的夏日,我帶著前來歐洲旅遊的家人踏上兩年前同樣的路程。美到令人屏息的蘆葦屋依舊,只是這回小小的村落塞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走在運河沿岸的蜿蜒小徑上,不時都得停下等待人們拍完照。而映著綠波的狹窄河道中,也壅塞著一艘艘供遊客體驗水上生活的搖槳船、獨木舟、電動船和撐篙平底船。我不禁小小抱怨起不該在旺季時到觀光勝地人擠人。
「人多沒關係,這麼美麗的地方,本來就值得讓更多的人看見呀。」我的母親倒是豁達地笑道。
所幸,在白天的擾攘過後,由於夜間所有水上活動不再營運,羊角村那股桃花源般的靜謐氛圍,終於在入夜時分再度降臨在我們周遭。
冬暖夏涼的蘆葦茅草
綠蔭盎然的羊角村建立於十三世紀,最常見的說法是,第一批來到這片沼澤地的農民,在開墾時發現許多羊角遺骸,推測這些山羊是溺死於一一七○年的洪水,因此該地便被命名為羊角村。
羊角村於是發展成一座美輪美奐的小鎮,至今的居民仍不超過三千人。據傳,剛來到這片泥濘窪地的是一群窮困農人,他們由於無法負擔磚瓦的價格,於是以濕地上隨手可得的蘆葦茅草搭建房舍,但乍聽之下寒酸的建材,實際上卻具有冬暖夏涼、防雨耐熱的優點。如今,羊角村已成為炙手可熱的觀光景點,蘆葦也翻身成為比磚瓦更高價的建材。這些原本是窮人住處的天然蘆葦屋,如今則是反諷地成為動輒要價數千萬台幣的富人別墅,這想必是最初迫於生活無奈的人們無法預料的未來。
儘管多少經過翻修,羊角村的建築造型基本上仍維持傳統的蘆葦屋頂樣式。這些完整保留的蘆葦屋少了城市僵硬的鋼筋水泥感,和周遭的天然風光和諧地融為一體,而當地居民也充分發揮荷蘭人酷愛綠化的習性,紛紛將自宅的獨立小屋四周整理成爭妍鬥豔的綺麗花園。
無車地帶的自在優遊
除了天然取材的建築造型外,羊角村更令人流連忘返的另一項主要原因, 在於這是個完全的「無車地帶」,這也是為何通往這個小村落需要如此大費周章的交通轉乘。從一開始,羊角村裡便沒有道路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數十道橋樑和運河裡的船隻,甚至許多美麗的蘆葦屋舍是座落在孤島上,必須越過唯一的聯外橋樑才能抵達。不難想像,羊角村便因此獲得了「北方威尼斯」的封號。雖然,今日沿著運河河道拓建了對荷蘭人而言同樣重要的腳踏車道,但依然沒有可供車輛通行的車道,人們若要運送大件貨物,只有船運一途。
少了車輛的廢氣與噪音,羊角村保留的是純淨的空氣,以及青蛙國人對「水」的一貫敬重。這座往來運輸主要靠水道進行的小村落,無疑為荷蘭人長期以來伴水而居的共存關係,再一次作了美麗見證。
綠波水面的美麗驚豔
我和家人投宿在標榜傳統蘆葦屋建築的私人民宿,享受在水光鳥鳴間醒轉的幸福感受。第二天,我們向民宿主人租了電動馬達操控的小船,準備來趟羊角村水道探密之旅。由於羊角村的特殊需求,這裡的民宿幾乎都備有船隻和腳踏車出租的服務。
我們先在水道裡打轉了一陣,對馬達小船的操縱稍為熟悉後,我們便沿著蜿蜒的運河排水前進,同樣穿梭在水道上的是悠哉游水的野鴨和互相點頭微笑的其他遊客。一邊喝著冰涼的啤酒,一邊徜徉在綠波水面上,我無法祈求更奢侈的享受。
這樣的悠閒享受一直到我們的小船穿過整座相連的內陸湖,發現怎麼開也開不回原來的村落時,我們才稍為驚慌了一陣。原來羊角村儘管迷你,四周連接的水道和湖泊卻是一片巨大的水道網絡,迷失方向的我們差一點就一路開到運河相通的另一座小鎮。
我們在繞行半天後總算開回民宿所在的河道,民宿主人已經騎著單車焦急地沿著岸邊小徑搜尋我們的蹤影。儘管早已超出我們租船的一小時期限,臉頰圓胖的民宿主人卻笑著說道:「不用加錢啦 !看到你們平安歸來我就放心了。」
或許這是民宿老闆的和氣生財之道吧,但我寧願這麼相信:正是由於這與世無爭的寧靜生活,讓居住在這可愛小村落裡的居民們,也擁有彷彿來自烏托邦世界的善良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