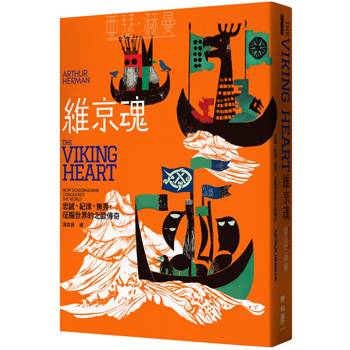1 諾斯人之怒
我主紀元七九三年六月的一個晴朗天, 英格蘭東北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島上修院中的三十多名修士,注意到海平面出現了一列船隻。
修士們認為來者為善,想必有幾位下了海灘去跟對方打招呼。他們的世界是和平的世界,遠離動盪,苦難不能及。他們全心全意地祈禱與冥想,慷慨的當地貴族將金銀珠寶捐獻給修道院,聊表虔心。海灘上的修士怕是沒注意到掛在船舷的盾牌,或是船艏的龍頭雕刻。
等到船隻一艘接著一艘靠了岸,剽悍的男子手持利劍與戰斧躍過船舷,林迪斯法恩眾修士才意識到自己大錯特錯。只是來不及了。
英格蘭史家達蘭的西默盎(Simeon of Durham)在《英格蘭諸王紀》(Historia Regum Anglorum)描述船上來人接下來做了什麼:「他們來到林迪斯法恩教堂,大搶特搶,破壞一切,用髒污的腳步踐踏聖所,挖開祭壇,搶走了聖教會的所有寶藏。他們殺害幾位弟兄,把幾位弟兄上腳鐐押走,不少人被他們扒光衣物、橫加羞辱,還有人被扔進海裡淹死……」
行兇者去時簡直跟來時一樣迅速,但傷害已經造成。林迪斯法恩之陷震撼了英格蘭與歐洲各地。一下子,基督教世界的每一個人都注意到了是誰幹下這件事──北方人。人們逐漸得知,他們來自遠方,來自當時仍撲朔迷離的斯堪地那維亞之地。時人稱呼他們北方人或諾斯人,還有許多不同的稱呼。現代世界稱他們為維京人。維京人憑藉自己在林迪斯法恩海岸的震撼登陸,宣告大駕光臨,成為接下來兩個世紀的文明之鞭。
林迪斯法恩突襲其實不是他們第一次出手。《盎格魯-薩克森編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記載,四年之前威塞克斯(Wessex)便曾遭到「北方人」襲擊──七八九年,僅僅三艘船構成的隊伍攻擊了波特蘭(Portland)的城鎮。一份來自七九二年的教會紀錄,提到英格蘭東海岸的默西亞(Mercia)為了防範「異教水手」──也就是同樣的斯堪地那維亞劫掠者──而修築防禦工事。
但林迪斯法恩遇襲一事,命中了基督教文明世界脆弱的核心,預示整個不列顛群島即將面對一場永無止境的燒殺搜刮。隔年,七九四年,盎格魯-薩克森的兩間修道院──紐卡斯爾(Newcastle)近郊的蒙克維茅斯(Monkwearmouth)與雅羅(Jarrow)修道院也遭到類似襲擊。到了七九五年,蘇格蘭愛奧那島(Iona)的聖高隆(Saint Columba)修道院,也成了教會中人口中「那些豪勇、憤怒、徹底的異教徒」的下一個受害者。
「異教」一詞並無不妥。直到今天,仍然無人知曉這第一批維京海盜的確切身分,也不知道他們的領袖是誰。但他們顯然視基督教禮儀、聖物之莊嚴於無物。事實上,維京人感覺正是要來找這些寶物,以及看管這些寶物的人,而且手段兇殘至極。打家劫舍,破壞祭壇與聖髑,殘殺百姓或者鬻之為奴──已經成了諾斯人四出劫掠時標準的犯案手法。他們必然深深刺傷了歐洲文明人的心,造成的恐懼無以名狀。一位顫慄驚恐的記事者寫道,諾斯人「如凶狠的狼群般由四面八方湧來,他們搶奪、撕扯、屠殺的可不只是馱獸、牛羊,甚至神父與助祭,以及大批修士與修女皆不能免」。
皇帝查理曼的側近之一,出身英格蘭的約克的阿爾坤(Alcuin of York)寫下這段令人不寒而慄的判斷:「我們如今落入異教徒的手中,此前不列顛未曾遭遇如此恐怖之行徑,也無人能逆料此等入侵居然會從海上而來。」西方公認最睿智的阿爾坤吐不出其他字句,只能引用《耶肋米亞先知書》(Jeremiah)第一章第十四節:「上主對我說:『災禍將由北方燒起,一直燒到這地上的一切居民。』」林迪斯法恩遇襲之後的數十年,人們自然相信耶肋米亞這話就是說給維京人的受害者聽的。
諾斯人兵分三路,從北國故鄉的三個不同地方出發──亦即今天的丹麥、瑞典與挪威。八三四年,也就是查理曼駕崩十七年後,維京人的襲擊已經發展為全面遠征,數十艘船隻形形色色,每年夏天都有斯堪地那維亞領袖率領隨從出海。諾斯人的劫掠隊伍有能力在具戰略地位的河口長期紮營,以此為根據地,讓船隻航向──甚至是扛向──更上游之地。
一夕之間,不列顛群島的每一所修道院、每一間教堂與每一處城鎮但凡位於海路可以到達的範圍,只要有任何財寶或可以搶奪的東西,就只能任由來自斯堪地那維亞的劫掠者所擺布──諸王、教宗或地方當局根本無從救援起。
丹人(Danes)短時間內次第攻陷倫敦(八四一年)、南特(Nantes)、盧昂(Rouen)、巴黎,甚至是位於高盧中央的土魯斯(Toulouse)。此時,瑞典入侵者已經逆流而上,深入窩瓦河(Volga),在諾夫哥羅德(Novgorod)建立聚落。他們攻佔基輔城,其中一名領袖留里克(Rurik)後來長期建都於此,襲擊、奴役周邊的斯拉夫居民。丹人入侵者在八四四年進攻西班牙的塞維利亞(Seville),然後把矛頭指向地中海的尼姆(Nîmes)與比薩(Pisa)。接下來二十年,維京入侵者從基輔出發,橫掃黑海地區。他們在八六○年推進君士坦丁堡,此時已有另一支無所畏懼的隊伍抵達哈里發的大本營──巴格達。
到了八七八年,英格蘭泰半遭到斯堪地那維亞人佔領,不列顛群島其餘地方也有許多地區落入他們手中。愛爾蘭與蘇格蘭顯然已經成了挪威殖民地。諾斯人罷手之前,甚至把活動範圍往西擴大進入大西洋,遠至北美洲。
十一個世紀之後,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寫下:「這些海盜就跟其他海盜一樣行徑卑劣。但是,當我們回想起他們的殘酷犯行,或是因為他們駭人聽聞的破壞與其他殘忍之舉而倒抽一口寒氣時,倒也不能忘記他們的紀律、堅忍、同袍情誼與武德,讓他們成為當時世界上最所向披靡、最大膽無畏的族群,無人能夠比肩。」
其實,維京人的大爆發愈想愈讓人吃驚。歷史上還未曾有哪一個地方人口如此之少(今日北歐只佔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一,當時甚至更少),卻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對人類文明造成如此深遠的衝擊。他們深受神話與傳說,虛構與非虛構文學,以及電視與電影所讚揚,自然也不讓人意外。無怪乎回首過去時,維京人似乎泛起超級戰士,甚至是超級英雄的光環。
但是,這些豪氣干雲、注定成就非凡的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北方人成就了什麼,而他們一開始為何會踏上改變世界的旅途? 這些問題不只史家傷腦筋。斯堪地那維亞對全世界(包括美國)的衝擊始終未減,對於現代想像也影響深遠。若想全盤理解這些衝擊與影響,就必須打通窒礙難解之處。開始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得先對維京人來自的土地有所認識。
* * *
從南方世界望向斯堪地那維亞的觀察家當中,羅馬博物學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是時代最早的一二人。老普林尼稱之為「自成一格的世界」。嚴酷環境帶來的苛刻考驗,逼得當地居民得膽識過人堅忍不拔才得以過活。從往北伸入北極圈的冰封山脈,到數不清的湖泊與冷杉、樺木林,再加上寒風掃過、湍流切穿的草原,斯堪地那維亞可說是一片地貌對比鮮明的土地。從挪威北岬(Northern Cape)到丹麥南境,斯堪地那維亞的長度達到歐洲南北的一半,總土地面積比不列顛、法國、西班牙三者相加還要廣大。即便如此,大部分的土地卻難以居住。
凡是說到斯堪地那維亞,許多人腦海中浮現的是從高峻壯闊的海岸山脈裂出的一處處深水峽灣,抵擋著北大西洋怒號的一座座成串小島嶼和礁岩。易言之,他們描繪的是挪威。斯堪地那維亞西海岸線確實多半如鋸齒狀的刀,某些峽灣甚至往內陸切入深達百餘英里。外海有一條由島嶼與礁岩構成的島鏈,稱為礁盾(Skerry Guard),為居民提供一段能遮風避雨的入海通道。因此,「挪威」(北道〔North Way〕)這個名字總讓人遙想數世紀以前,船隻(包括維京人的船)利用礁盾間的水道駛入大海的年代。
望而生畏的山脈主宰了大半個挪威,從西邊的海域拔地而起,然後緩緩沉入東邊的波的尼亞灣(Gulf of Bothnia),也就是分隔瑞典與芬蘭的海灣。維京人不愧是維京人,用造船術語給斯堪地那維亞山脈起了個綽號──「龍骨」。龍骨有一大部分高於林線,濃密的針葉林則覆蓋了餘下的大部分面積。挪威實際的可耕地,只有奧斯陸周邊與特隆赫姆(Trondheim)峽灣一帶的肥沃平原,佔總面積百分之三,而且至今猶然。其餘有四分之一為森林,不毛的山地超過三分之二,其中便包括哈當爾高原(Hardangervidda)──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劇碼之一便是在此地上演,甚至決定了戰爭的結果。
瑞典位於更東邊,國土比挪威稍大,達到十七萬三千八百六十平方英里(與加州大小相仿),西邊長期作為競爭對手的鄰國則是十四萬八千七百二十九平方英里。瑞典北部海岸線與挪威非常類似,崇山峻嶺,冰雪永覆。不過,南端的地貌卻一片開闊,有無數的湖泊與茂密廣布的森林;對於吃苦耐勞,願意在不時出現的泥淖與濕地間開闢農場或牧場的人來說,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但是,交替出現的湖泊與森林,也讓瑞典內陸在過去難以通行。芬蘭位於更東邊,地理類似瑞典,但族群有別。森林、湖泊與泥淖遍布,讓陸路交通窒礙難行。
斯堪地那維亞的第四部分,丹麥,不僅地形平坦得多,而且森林採伐面積相對較大。古早以前的丹麥擁有大片的針葉林,但在維京年代遭到砍伐。當時的丹麥和今天一樣,它那指向北邊的狹長半島──日德蘭(Jutland)半島──深入北海與波羅的海,幾乎觸及到瑞典的東海岸;日德蘭半島的南邊,則與歐洲大平原相連。而在斯堪地那維亞各部中,促成丹麥首先實現政治統一的原因之一,便是其相對開闊的地理形勢,而丹麥跟歐洲其他地方也因物理上的比鄰,讓斯堪地那維亞的這個地區在數個世紀中深受歐陸影響。
我主紀元七九三年六月的一個晴朗天, 英格蘭東北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島上修院中的三十多名修士,注意到海平面出現了一列船隻。
修士們認為來者為善,想必有幾位下了海灘去跟對方打招呼。他們的世界是和平的世界,遠離動盪,苦難不能及。他們全心全意地祈禱與冥想,慷慨的當地貴族將金銀珠寶捐獻給修道院,聊表虔心。海灘上的修士怕是沒注意到掛在船舷的盾牌,或是船艏的龍頭雕刻。
等到船隻一艘接著一艘靠了岸,剽悍的男子手持利劍與戰斧躍過船舷,林迪斯法恩眾修士才意識到自己大錯特錯。只是來不及了。
英格蘭史家達蘭的西默盎(Simeon of Durham)在《英格蘭諸王紀》(Historia Regum Anglorum)描述船上來人接下來做了什麼:「他們來到林迪斯法恩教堂,大搶特搶,破壞一切,用髒污的腳步踐踏聖所,挖開祭壇,搶走了聖教會的所有寶藏。他們殺害幾位弟兄,把幾位弟兄上腳鐐押走,不少人被他們扒光衣物、橫加羞辱,還有人被扔進海裡淹死……」
行兇者去時簡直跟來時一樣迅速,但傷害已經造成。林迪斯法恩之陷震撼了英格蘭與歐洲各地。一下子,基督教世界的每一個人都注意到了是誰幹下這件事──北方人。人們逐漸得知,他們來自遠方,來自當時仍撲朔迷離的斯堪地那維亞之地。時人稱呼他們北方人或諾斯人,還有許多不同的稱呼。現代世界稱他們為維京人。維京人憑藉自己在林迪斯法恩海岸的震撼登陸,宣告大駕光臨,成為接下來兩個世紀的文明之鞭。
林迪斯法恩突襲其實不是他們第一次出手。《盎格魯-薩克森編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記載,四年之前威塞克斯(Wessex)便曾遭到「北方人」襲擊──七八九年,僅僅三艘船構成的隊伍攻擊了波特蘭(Portland)的城鎮。一份來自七九二年的教會紀錄,提到英格蘭東海岸的默西亞(Mercia)為了防範「異教水手」──也就是同樣的斯堪地那維亞劫掠者──而修築防禦工事。
但林迪斯法恩遇襲一事,命中了基督教文明世界脆弱的核心,預示整個不列顛群島即將面對一場永無止境的燒殺搜刮。隔年,七九四年,盎格魯-薩克森的兩間修道院──紐卡斯爾(Newcastle)近郊的蒙克維茅斯(Monkwearmouth)與雅羅(Jarrow)修道院也遭到類似襲擊。到了七九五年,蘇格蘭愛奧那島(Iona)的聖高隆(Saint Columba)修道院,也成了教會中人口中「那些豪勇、憤怒、徹底的異教徒」的下一個受害者。
「異教」一詞並無不妥。直到今天,仍然無人知曉這第一批維京海盜的確切身分,也不知道他們的領袖是誰。但他們顯然視基督教禮儀、聖物之莊嚴於無物。事實上,維京人感覺正是要來找這些寶物,以及看管這些寶物的人,而且手段兇殘至極。打家劫舍,破壞祭壇與聖髑,殘殺百姓或者鬻之為奴──已經成了諾斯人四出劫掠時標準的犯案手法。他們必然深深刺傷了歐洲文明人的心,造成的恐懼無以名狀。一位顫慄驚恐的記事者寫道,諾斯人「如凶狠的狼群般由四面八方湧來,他們搶奪、撕扯、屠殺的可不只是馱獸、牛羊,甚至神父與助祭,以及大批修士與修女皆不能免」。
皇帝查理曼的側近之一,出身英格蘭的約克的阿爾坤(Alcuin of York)寫下這段令人不寒而慄的判斷:「我們如今落入異教徒的手中,此前不列顛未曾遭遇如此恐怖之行徑,也無人能逆料此等入侵居然會從海上而來。」西方公認最睿智的阿爾坤吐不出其他字句,只能引用《耶肋米亞先知書》(Jeremiah)第一章第十四節:「上主對我說:『災禍將由北方燒起,一直燒到這地上的一切居民。』」林迪斯法恩遇襲之後的數十年,人們自然相信耶肋米亞這話就是說給維京人的受害者聽的。
諾斯人兵分三路,從北國故鄉的三個不同地方出發──亦即今天的丹麥、瑞典與挪威。八三四年,也就是查理曼駕崩十七年後,維京人的襲擊已經發展為全面遠征,數十艘船隻形形色色,每年夏天都有斯堪地那維亞領袖率領隨從出海。諾斯人的劫掠隊伍有能力在具戰略地位的河口長期紮營,以此為根據地,讓船隻航向──甚至是扛向──更上游之地。
一夕之間,不列顛群島的每一所修道院、每一間教堂與每一處城鎮但凡位於海路可以到達的範圍,只要有任何財寶或可以搶奪的東西,就只能任由來自斯堪地那維亞的劫掠者所擺布──諸王、教宗或地方當局根本無從救援起。
丹人(Danes)短時間內次第攻陷倫敦(八四一年)、南特(Nantes)、盧昂(Rouen)、巴黎,甚至是位於高盧中央的土魯斯(Toulouse)。此時,瑞典入侵者已經逆流而上,深入窩瓦河(Volga),在諾夫哥羅德(Novgorod)建立聚落。他們攻佔基輔城,其中一名領袖留里克(Rurik)後來長期建都於此,襲擊、奴役周邊的斯拉夫居民。丹人入侵者在八四四年進攻西班牙的塞維利亞(Seville),然後把矛頭指向地中海的尼姆(Nîmes)與比薩(Pisa)。接下來二十年,維京入侵者從基輔出發,橫掃黑海地區。他們在八六○年推進君士坦丁堡,此時已有另一支無所畏懼的隊伍抵達哈里發的大本營──巴格達。
到了八七八年,英格蘭泰半遭到斯堪地那維亞人佔領,不列顛群島其餘地方也有許多地區落入他們手中。愛爾蘭與蘇格蘭顯然已經成了挪威殖民地。諾斯人罷手之前,甚至把活動範圍往西擴大進入大西洋,遠至北美洲。
十一個世紀之後,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寫下:「這些海盜就跟其他海盜一樣行徑卑劣。但是,當我們回想起他們的殘酷犯行,或是因為他們駭人聽聞的破壞與其他殘忍之舉而倒抽一口寒氣時,倒也不能忘記他們的紀律、堅忍、同袍情誼與武德,讓他們成為當時世界上最所向披靡、最大膽無畏的族群,無人能夠比肩。」
其實,維京人的大爆發愈想愈讓人吃驚。歷史上還未曾有哪一個地方人口如此之少(今日北歐只佔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一,當時甚至更少),卻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對人類文明造成如此深遠的衝擊。他們深受神話與傳說,虛構與非虛構文學,以及電視與電影所讚揚,自然也不讓人意外。無怪乎回首過去時,維京人似乎泛起超級戰士,甚至是超級英雄的光環。
但是,這些豪氣干雲、注定成就非凡的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北方人成就了什麼,而他們一開始為何會踏上改變世界的旅途? 這些問題不只史家傷腦筋。斯堪地那維亞對全世界(包括美國)的衝擊始終未減,對於現代想像也影響深遠。若想全盤理解這些衝擊與影響,就必須打通窒礙難解之處。開始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得先對維京人來自的土地有所認識。
* * *
從南方世界望向斯堪地那維亞的觀察家當中,羅馬博物學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是時代最早的一二人。老普林尼稱之為「自成一格的世界」。嚴酷環境帶來的苛刻考驗,逼得當地居民得膽識過人堅忍不拔才得以過活。從往北伸入北極圈的冰封山脈,到數不清的湖泊與冷杉、樺木林,再加上寒風掃過、湍流切穿的草原,斯堪地那維亞可說是一片地貌對比鮮明的土地。從挪威北岬(Northern Cape)到丹麥南境,斯堪地那維亞的長度達到歐洲南北的一半,總土地面積比不列顛、法國、西班牙三者相加還要廣大。即便如此,大部分的土地卻難以居住。
凡是說到斯堪地那維亞,許多人腦海中浮現的是從高峻壯闊的海岸山脈裂出的一處處深水峽灣,抵擋著北大西洋怒號的一座座成串小島嶼和礁岩。易言之,他們描繪的是挪威。斯堪地那維亞西海岸線確實多半如鋸齒狀的刀,某些峽灣甚至往內陸切入深達百餘英里。外海有一條由島嶼與礁岩構成的島鏈,稱為礁盾(Skerry Guard),為居民提供一段能遮風避雨的入海通道。因此,「挪威」(北道〔North Way〕)這個名字總讓人遙想數世紀以前,船隻(包括維京人的船)利用礁盾間的水道駛入大海的年代。
望而生畏的山脈主宰了大半個挪威,從西邊的海域拔地而起,然後緩緩沉入東邊的波的尼亞灣(Gulf of Bothnia),也就是分隔瑞典與芬蘭的海灣。維京人不愧是維京人,用造船術語給斯堪地那維亞山脈起了個綽號──「龍骨」。龍骨有一大部分高於林線,濃密的針葉林則覆蓋了餘下的大部分面積。挪威實際的可耕地,只有奧斯陸周邊與特隆赫姆(Trondheim)峽灣一帶的肥沃平原,佔總面積百分之三,而且至今猶然。其餘有四分之一為森林,不毛的山地超過三分之二,其中便包括哈當爾高原(Hardangervidda)──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劇碼之一便是在此地上演,甚至決定了戰爭的結果。
瑞典位於更東邊,國土比挪威稍大,達到十七萬三千八百六十平方英里(與加州大小相仿),西邊長期作為競爭對手的鄰國則是十四萬八千七百二十九平方英里。瑞典北部海岸線與挪威非常類似,崇山峻嶺,冰雪永覆。不過,南端的地貌卻一片開闊,有無數的湖泊與茂密廣布的森林;對於吃苦耐勞,願意在不時出現的泥淖與濕地間開闢農場或牧場的人來說,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但是,交替出現的湖泊與森林,也讓瑞典內陸在過去難以通行。芬蘭位於更東邊,地理類似瑞典,但族群有別。森林、湖泊與泥淖遍布,讓陸路交通窒礙難行。
斯堪地那維亞的第四部分,丹麥,不僅地形平坦得多,而且森林採伐面積相對較大。古早以前的丹麥擁有大片的針葉林,但在維京年代遭到砍伐。當時的丹麥和今天一樣,它那指向北邊的狹長半島──日德蘭(Jutland)半島──深入北海與波羅的海,幾乎觸及到瑞典的東海岸;日德蘭半島的南邊,則與歐洲大平原相連。而在斯堪地那維亞各部中,促成丹麥首先實現政治統一的原因之一,便是其相對開闊的地理形勢,而丹麥跟歐洲其他地方也因物理上的比鄰,讓斯堪地那維亞的這個地區在數個世紀中深受歐陸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