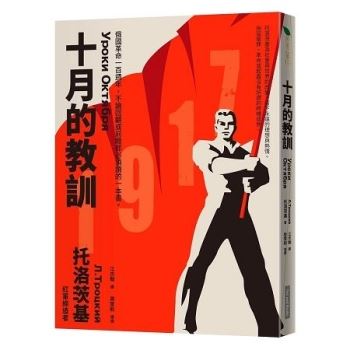必須研究「十月」
我們在十月革命(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中幸運成功,但就出版而言,十月革命就不大好運了。時至今日,我們仍然沒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夠呈現十月政變(переворот)的大致情形,指出其政治與組織上最關鍵的重點。不僅如此,甚至連直接說明政變的準備工作和政變本身的各個方面的第一手資料──而且還是最重要的檔案── 至今都尚未出版。關於十月革命之前的時期,我們出版了許多革命史與黨史的檔案和資料;關於十月革命以後的階段,我們出版的資料也不在少數。然而,對於「十月」(Октябрь)的關注則少得太多。在政變達成之後,我們好像認定,無論如何,將來都沒有再重複的必要。我們似乎以為,研究「十月」、其直接的準備、實現以及鞏固階段最初幾週的各種情況,對後續建設的迫切任務將不會有任何直接的益處。
然而,如此的評價──即使不見得是有意的──不僅大錯特錯,而且在國族上太過狹隘。就算我們無需重複十月革命的經驗,也絕不表示我們不能從中學習。我們是「國際」的一分子,而其他各國無產階級的「十月」任務皆仍有待解決。過去一年,我們有相當令人信服的證據,足以說明,即便是西方較為成熟的共產政黨,也未能完全吸收我們的十月經驗,甚至對其事實方面全然無知。
的確,有人會說,研究「十月」、出版相關的資料必然會挑起往日的分歧。然而,這樣的觀點根本不值得一提。一九一七年的意見分歧的確深刻,而且絕非偶然。不過,在多年之後,如今若試圖以此作為武器,攻擊當時犯了錯的人,也未免太過低劣。倘若因為微不足道的個人考量,而對十月政變最重要的、具有國際意義的問題沉默不語,就更令人無法容忍了。
過去一年,我們在保加利亞遭遇了兩次慘重的失敗:首先,黨因為固守教條、宿命論的思維,錯失了革命行動的絕佳時機(詹科夫六月政變之後的農民起義);然後,黨為了修正錯誤,投入九月的起義,卻未能完備政治和組織上的先決條件。保加利亞的革命應該成為德國革命的序曲。不幸的是,保加利亞糟糕的序曲在德國本土的發展更是惡劣。去年下半年,我們在那裡見到了經典的例子:如何錯過絕無僅有、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情況。相同地,去年保加利亞和德國的經驗至今仍未得到夠完整、夠具體的評價。針對德國的事件發展,本書作者在去年已經做了概略的論述。後續發生的一切皆證實了該論述完全正確。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任何人嘗試過提出其他的說法。然而,概述是不足的。關於去年在德國發生的事件,我們需要確切且包含豐富事實資料的圖像,才能非常具體地解釋極為慘重的歷史性挫敗的原因。
不過,由於至今仍然未能掌握十月政變在政治和策略方面的細節,我們很難分析在保加利亞和德國發生的事件。我們自己都尚未釐清我們達成了什麼,又是如何辦到的。在「十月」之後,一陣情緒激昂,彷彿歐洲的事件都會自然發展,而且如此匆促,以至於沒有時間在理論上吸收十月的教訓。然而,若少了能夠領導無產階級政變的黨,這次政變根本不可能發生。無產階級無法藉由自發的起義取得政權:就連在工業、文化高度發展的德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勞動者的自發起義也僅只將權力轉交到了資產階級手上。有產階級之所以能夠掌握自另一個有產階級手中奪得的政權,仰賴的是自身的財富、「文化素養」(культурность),以及與舊的國家機器之間無法盡數的關係。而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其政黨無可取代。一九二一年中,各共產政黨成形、建設的階段才真正開始6。「十月」的任務推遲了,關於「十月」的研究也跟著退到一邊。過去一年,我們才又再度面臨無產階級政變的任務。該是收集全部的文件,出版所有的資料,並且著手研究的時候!
當然,我們知道,每個民族(народ)、階級,甚至每個黨派,大都從自身的慘痛經驗中學習。但是,這絕不代表其他國家、階級和黨派的經驗無關緊要。少了對法國大革命、四八年革命7和巴黎公社的研究,即使具備一九○五年的經驗,我們也永遠無法實現十月政變。畢竟,我們也是憑藉著過往革命的總結,延續其歷史路線,才成就了我們的這個「民族」經驗。接著,在反革命時期,人們始終致力研究一九○五年的教訓和結果。然而,對於一九一七年成功取得勝利的革命,我們卻沒有做這樣的工作,甚至未及其十分之一。的確,我們所面對的既不是反動的年代,亦非流亡的處境。但今日我們所能支配的力量和資源絕對不是那艱苦的年代所能相比。我們必須做的,不過是清楚而明確地將研究十月革命訂定為黨和整個「國際」規模的任務。全黨──尤其年輕一代──都必須循序漸進地研究「十月」的經驗。這個經驗是對過去偉大而不容質疑、反駁的審視,敞開通往未來的大門。去年德國的教訓不只是重要的提醒,更是嚴肅的預警。
是的,有人會說,即使非常認真地研究了十月政變的過程,也不能確保我們在德國的黨獲得勝利。但這般毫無根據的說法本質上是庸俗的空談,無法使我們前進一步。的確,光是研究十月革命不足以為其他國家取得勝利,不過,有時候,一切的先決條件皆已齊備,獨缺目光遠大、有決心、明白革命的規律和方法的黨的領導。去年在德國的狀況即是如此。這樣的情形也可能在其他國家再度發生。若想要研究革命的規律和方法,在現階段,沒有比十月的經驗更重要、更深刻的材料了。倘若歐洲各個共產政黨的領導者未能批判地研究十月政變的歷史,檢視所有的具體細節,就如同軍事指揮官在當今的狀況下準備迎接新的戰爭,卻不研究最近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中戰術、策略和技術方面的經驗。這樣的指揮官將來必定會使部隊遭受失敗。
黨是無產階級革命最基本的工具。就我們的經驗── 即便只考量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的一年時間──以及在芬蘭、匈牙利、義大利、保加利亞、德國的附加經驗而言,可以判定,在由革命的準備工作轉向對政權的直接爭奪的過渡階段,黨的危機無法避免。這幾乎是不容爭議的定律。一般來說,每當黨的路線面臨重大的轉捩點,危機便會出現──不論是作為轉折的序曲,或其後果。這是因為在黨的發展過程中,每個時期都有其特殊之處,需要一定的運作技能和方法。策略的轉向意味著在這些技能和方法上或大或小的斷裂,這就是黨內摩擦和危機最直接的根源。列寧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寫道:
面臨歷史驟變,即便是先進的政黨,往往也要經歷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無法掌握新的局面,重複過去正確、但今日已經不具任何意義的口號。這些口號「突然」失去了意義,正如同歷史的劇變之「突然」發生。
危險亦由此而來:如果轉變太過劇烈或迅速,而在前一個階段,黨的領導機構內又累積了太多因循保守的消極分子,那麼縱使準備工作已經持續了數年或數十年,黨也無法在最緊要的關頭實現其領導。黨為危機所摧殘,而運動則從旁經過──步向失敗。
革命政黨必須承受來自其他政治勢力的壓迫。在發展的每個階段,黨總是尋求與之抗衡、反擊的方法。當黨面臨策略上的轉折,內部因而發生重組和摩擦,反抗的力量便會削弱。所以,因應策略改變之必要而生成的黨內團體經常可能遠遠逾越其出發點,成為各種階級傾向的支柱。簡而言之,如果政黨無法與自身階級的歷史任務一齊前進,便會成為──或有可能成為──其他階級的間接武器。
若就每個重要的策略轉變而言,以上的論述正確無誤,那麼這樣的觀點也就更加適用於大的戰略轉變。政治上的策略(тактика),如同軍事上的概念,我們指的是主持個別行動的技術;而戰略(стратегия)則是取勝──亦即掌握政權──的藝術。戰前,在第二國際時期,我們通常不大區分上述的差異,只局限於社會民主策略的概念。這並非偶然──社會民主包含議會、工會、市政府、合作社等策略。至於整合一切力量和資源── 各式軍力── 以求克敵制勝的問題,事實上並不在第二國際時期的考量之內,畢竟當時爭取政權並未成為實際的任務。在長時間的間隔之後,一九○五年革命才首先使無產階級鬥爭的根本或戰略問題浮上檯面。如此一來,這場革命為俄國的革命社會民主人士──即布爾什維克──確保了極大的優勢。一九一七年,革命戰略的大時代開始了,最初在俄羅斯,接著遍及整個歐洲。當然,戰略不會將策略排除在外:工會運動、議會工作等問題也並未從我們的視野消失,而是有了新的當代意涵──成為取得政權的綜合鬥爭中的從屬方法。戰略凌駕在策略之上。
若說策略的轉向往往導致黨內的摩擦,那麼因戰略改變而引發的衝突該是多麼強烈而深刻啊!最急遽的轉折便是,當無產階級政黨自準備、宣傳、組織與煽動,轉而投入政權的直接爭奪和對抗資產階級的武裝起義,黨內所有猶豫不決的、懷疑的、妥協的、屈從的──孟什維克的──都會起來反對起義,為自己的反對立場找尋理論說法。他們會在昔日的對手──那些機會主義者──那裡找到現成的論述。我們將不只一次目睹這樣的現象。
二月至十月期間,黨以對群眾極為廣泛的煽動與組織工作為基礎,在關鍵的戰役前夕,最後一次審視、選擇武器。在十月間以及十月以後,這項武器在偉大的歷史行動中通過了考驗。如今,在「十月」之後,幾年過去,評價關於一般的革命──包括俄國革命在內──的不同觀點,卻又迴避一九一七年的經驗,就像研究徒勞無益的經院哲學,而絕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分析。如此的作為無異於練習爭論各種泳式的長處,卻怎麼也不看看河裡正在以那些方法游泳的人們。檢視革命觀點最佳的方式莫過於在革命中實踐──正如同驗證游泳方法最好的機會,便是當泳者躍入水中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