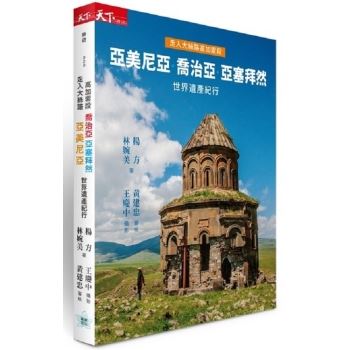1
凡湖&亞拉拉山
亞美尼亞是古烏拉圖王國(Urartu, 860 –590 BC)的主要繼承者,西元前九世紀烏拉圖興起於亞美尼亞高原,成為亞述帝國(2500–609 BC)北方的強鄰。烏拉圖的版圖以今土耳其東部的凡湖(Lake Van)為中心,也稱凡王國,或因亞拉拉山而稱作亞拉拉王國。相傳亞拉拉山是諾亞方舟最終的停泊之處,亞美尼亞人自認是諾亞的傳人,因此這一山一湖就成了亞美尼亞最重要的精神象徵。亞美尼亞素有「三湖之國」的雅號,從烏拉圖、阿爾塔克西亞至巴格拉圖尼王國都領有凡湖、思凡湖以及今伊朗的烏爾米亞湖。阿爾塔克西亞王國最盛時領土曾一度橫跨裏海與地中海,至今這依然是亞美尼亞人最津津樂道的歷史。
凡湖是土耳其最大的湖泊,面積約3800平方公里,是思凡湖的三倍大,兩湖相距不到200公里,而亞拉拉山就位在兩湖的正中間。凡湖東岸的凡城(Van)曾是烏拉圖以及巴格拉圖尼所屬的法斯普拉坎(Vaspurakan, 908–1021)等朝代的首都,此後凡湖一帶歷經拜占庭、塞爾柱與鄂圖曼統治,至20世紀結束前,亞美尼亞人在凡城仍佔約60%的多數,在整個凡省人口中也佔四分之一。
一次大戰期間,俄國以協助獨立相誘,慫恿凡城的亞美尼亞人發動叛變,俄軍兩度佔領凡城,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俄軍匆匆退出戰事,鄂圖曼收復凡城後55,000亞美尼亞居民悉數遭到屠殺。鄂圖曼戰敗後簽訂色佛爾(Sèvres)條約接受協約國的苛刻條件,鄂圖曼帝國把亞美尼亞傳統領域的六個州中最東的三個州劃給戰後獨立的亞美尼亞共和國,亞美尼亞還取得黑海的出海港特拉布宗(Trabzon)。不過亞美尼亞從未實際上得到這些領土。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拒絕履行色佛爾條約,對鄰國發動獨立戰爭,再度佔領凡城,殘存的亞美尼亞居民遭到徹底驅離。蘇聯1920年併吞南高加索三國後,另與土耳其簽訂卡爾斯條約,原來根據色佛爾條約屬於亞美尼亞的凡湖以及亞拉拉山,都變成土耳其的領土;亞美尼亞人重歸故土的美夢就此破碎,成為深埋內心的永恆遺憾。
今天凡城約有60萬人口,以庫德人佔多數,城西距凡湖約1公里處突起一塊高百餘公尺的狹長岩層露頭,稱為凡石(Rock of Van),古烏拉圖王國最大的堡壘遺跡—凡堡(Van Kalesi / Van Fortress)即建在凡石之頂,東西綿延1.2公里,俯瞰著南面被亞美尼亞人視為第一個首都的圖西帕(Tushpa),即凡城的前身。堡壘的基座是玄武岩,上部則以厚重的土磚疊砌,作為首都堅強的防禦據點,烏拉圖之後的歷代地區強權幾乎都曾入主凡堡,現存的建築大都是鄂圖曼時期遺留,真正可溯及烏拉圖時期的遺跡是登山步道旁殘存的階梯狀牆基。
凡石最高點略偏西的南面筆直峭壁有一處鑿入山壁的洞穴,是建立艾瑞布尼城寨的烏拉圖國王阿格什提一世(Argishti I, 786–764 BC)的陵墓,漆黑的洞內有若干墓室和壁龕,洞口兩側的石壁則刻滿了楔形文字銘文,記載他的生平與功勳。東面的山壁還有幾個不知名的墓穴,供遊客攀登的狹窄階梯步道也是鑿山壁而成,僅在危險處的外側加裝簡陋的金屬護欄,因此不免有幾分驚險。
前五世紀波斯帝國的薛西斯一世(Xerxes I, 486–65 BC)在凡石南面山腳下的一處山壁上刻下三種文字(古波斯、巴比倫、埃蘭)的銘文,高出地面20公尺—這是古波斯帝國勒石銘勳宣揚國威的典型遺跡,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朗西北部名列世界遺產的比斯希頓(Behistun)銘文,出自薛西斯一世之父大流士大帝(Darius I, 522–486 BC),凡石的這一件是現存唯一位在伊朗境外的古波斯帝國銘文,保存狀況極佳。凡石之南緊鄰老凡城,經歷1915至1920年間的戰爭破壞與屠殺清洗,這座百年前曾有八萬居民的城市只剩不明顯的土堆、牆基、幾截宣禮塔與教堂殘跡,倒是南面兩座16世紀的清真寺已經修復得十分光鮮。
凡湖周邊一度教堂、修道院林立,如今倖存且可觀的卻是寥寥無幾。巴格拉圖尼王朝最大的王國法斯普拉坎921年在凡湖南端的阿赫塔馬爾(Aghtamar)島修道院建造聖十字教堂,作為法斯普拉坎王室教堂及主教駐地,13至19世紀再陸續擴建了前廳等建築。最具特色的是聖十字教堂外牆連續的聖經故事等生動的浮雕,包括大衛王挑戰巨人歌利亞等,風格則匯聚了波斯、阿拉伯與伊斯蘭等外來影響。一次大戰後教堂內外都遭到嚴重的破壞,2005年土耳其政府斥資大修,2007年以博物館的方式重新開放。
亞拉拉山高5137公尺,是土耳其第一高峰,峰頂距亞美尼亞的亞拉拉省邊界僅30公里,整個亞美尼亞西半部都看得到;東南面的小亞拉拉山高3896公尺,從亞美尼亞這一邊望去,大亞拉拉山永遠在右邊。自古以來亞拉拉山被亞美尼亞人視為聖山而禁止攀登,1828年俄土戰爭後俄國取得亞拉拉山,次年一支歐洲登山隊才首度征服頂峰;1840年活火山亞拉拉山最後一次爆發,造成極大的災難。雖然一個世紀來的搜索調查都未能證實諾亞方舟的蹤跡,但這絲毫不影響亞美尼亞人身為諾亞後代的自豪。
亞拉拉山是亞美尼亞最重要的精神象徵,許多國家以星月或十字架作為國旗的主題,而亞美尼亞國徽始終以亞拉拉山為中心,蘇聯時期還曾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抗議;離散亞美尼亞人不論身在何處,家裡總有一張亞拉拉山的相片,至今亞拉拉山和亞美尼亞的形象依然緊緊相連,象徵著亞美尼亞人的苦難以及失去的故土。這使土耳其官方似乎不自覺地排斥起自己的最高峰,竭力避免觸及亞拉拉山的形象,因此一般人在圖片裡看到的大亞拉拉山幾乎都位在右邊。亞美尼亞人固然喪失了亞拉拉山的所有權,不過專利權看起來依然歷久彌堅。2
亞美尼亞流散社群
哪一個民族的語言自成一個語族、擁有獨特的書寫字母、信仰專屬的一神教教派、散居世界各地的人數遠多於國內人口,而且不論身在何處都依然保留語言、文化與民族認同,歷經千餘年而不被同化?
答案不是尤太人,是亞美尼亞人。
目前全球約有1100–1200萬亞美尼亞人,其中只有三成居住在亞美尼亞與納卡地區,亦即流散社群(diaspora)的規模接近800萬人,和尤太人不相上下*。俄羅斯(225萬人)、美國(150萬人)與法國(45萬人)是亞美尼亞人的三大客居國,其次是喬治亞、阿根廷、黎巴嫩、伊朗、波蘭、烏克蘭、德國、奧地利、巴西、加拿大等。
亞美尼亞歷史悠久、傳統領域極為遼闊,歷代不斷遭受侵略與佔領,長期被不同的強權瓜分併吞,因此早在四世紀即已出現相當的流散社群,不過現有的流散社群主要在20世紀初的大屠殺之後才開始形成。相較於其他民族,亞美尼亞人的流散之路更為曲折坎坷,1915年鄂圖曼帝國的亞美尼亞人大量逃離世居之地,1923年法軍撤出敘利亞,再度造成難民潮。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後,領土只剩亞美尼亞傳統領域的十分之一,比台灣還小,而且大部分是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山地,人民出走有增無減;1991年蘇聯解體,新獨立的亞美尼亞共和國經濟凋敝,又導致大約百萬移民離鄉背井。
亞美尼亞人是中東國家「必備」的少數民族,中東的基督教會也幾乎全是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的天下,阿拉伯或波斯基督徒都說亞美尼亞語、讀亞美尼亞語聖經。伊朗與戰前的敘利亞都各有超過25萬亞美尼亞使徒教派基督徒,佔黎巴嫩人口4%的亞美尼亞人還在國會擁有六個保障席次,而敘利亞的阿勒坡(Aleppo)與黎巴嫩的安佳(Anjar)都是亞美尼亞流散社群中心。
耶路撒冷是基督教、伊斯蘭教、尤太教三大一神教的共同聖地,但舊城在這三區之外還多出一個「亞美尼亞區」,一旁的全球基督徒朝聖之所—聖墓教堂則由羅馬天主教會、希臘正教會與亞美尼亞使徒教會三方共管。宗教不但凝聚了亞美尼亞民族,也反映出這個民族不凡的影響力。
許多現居歐美的亞美尼亞人都是一路從中東地區輾轉而來,飽嘗顛沛之苦。亞美尼亞移民落腳之後努力適應並積極參與當地社會,他們經常對當地經濟貢獻卓著,也頗具政治遊說與動員能量。他們開辦學校、文化中心、教會以及各類公益組織,教育和傳播媒體是維繫凝聚力、免於被同化的。一個保加利亞笑話對亞美尼亞人的描述最為傳神:「只要把三個亞美尼亞人放在一起,他們就會立刻蓋一座教堂、建一所學校,再辦一份報紙。」
大部分的流散亞美尼亞人至今已傳到第四代,即使他們從未見過祖國,卻依然能說母語。不過不少人改了名字,因為亞美尼亞姓氏既長又難唸、難記,在某些國家還有受到歧視之虞。亞美尼亞人在歷史上和尤太人一樣都以經商見長,也以傑出的工匠技師聞名,今天則在居住國的不同領域出人頭地。亞美尼亞是俄國教育水準最高的少數民族,在藝術、科學、運動、政軍領域皆人才輩出,包括被譽為世界最偉大西洋棋王的卡斯帕洛夫(Garry Kasparov),以及米格機的設計人米高揚(Artem Mikoyan 1905–70)等。亞美尼亞人也在美國的企業/科學界、法國的藝術/運動界、土耳其的語言學/建築界等領域大放異彩,同時還出了不少頂尖政治人物,包括法國前總理巴拉杜(Édouard Balladur 1993–95)、美國前加州州長(George Deukmejian 1983–91)等。
凡湖&亞拉拉山
亞美尼亞是古烏拉圖王國(Urartu, 860 –590 BC)的主要繼承者,西元前九世紀烏拉圖興起於亞美尼亞高原,成為亞述帝國(2500–609 BC)北方的強鄰。烏拉圖的版圖以今土耳其東部的凡湖(Lake Van)為中心,也稱凡王國,或因亞拉拉山而稱作亞拉拉王國。相傳亞拉拉山是諾亞方舟最終的停泊之處,亞美尼亞人自認是諾亞的傳人,因此這一山一湖就成了亞美尼亞最重要的精神象徵。亞美尼亞素有「三湖之國」的雅號,從烏拉圖、阿爾塔克西亞至巴格拉圖尼王國都領有凡湖、思凡湖以及今伊朗的烏爾米亞湖。阿爾塔克西亞王國最盛時領土曾一度橫跨裏海與地中海,至今這依然是亞美尼亞人最津津樂道的歷史。
凡湖是土耳其最大的湖泊,面積約3800平方公里,是思凡湖的三倍大,兩湖相距不到200公里,而亞拉拉山就位在兩湖的正中間。凡湖東岸的凡城(Van)曾是烏拉圖以及巴格拉圖尼所屬的法斯普拉坎(Vaspurakan, 908–1021)等朝代的首都,此後凡湖一帶歷經拜占庭、塞爾柱與鄂圖曼統治,至20世紀結束前,亞美尼亞人在凡城仍佔約60%的多數,在整個凡省人口中也佔四分之一。
一次大戰期間,俄國以協助獨立相誘,慫恿凡城的亞美尼亞人發動叛變,俄軍兩度佔領凡城,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俄軍匆匆退出戰事,鄂圖曼收復凡城後55,000亞美尼亞居民悉數遭到屠殺。鄂圖曼戰敗後簽訂色佛爾(Sèvres)條約接受協約國的苛刻條件,鄂圖曼帝國把亞美尼亞傳統領域的六個州中最東的三個州劃給戰後獨立的亞美尼亞共和國,亞美尼亞還取得黑海的出海港特拉布宗(Trabzon)。不過亞美尼亞從未實際上得到這些領土。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拒絕履行色佛爾條約,對鄰國發動獨立戰爭,再度佔領凡城,殘存的亞美尼亞居民遭到徹底驅離。蘇聯1920年併吞南高加索三國後,另與土耳其簽訂卡爾斯條約,原來根據色佛爾條約屬於亞美尼亞的凡湖以及亞拉拉山,都變成土耳其的領土;亞美尼亞人重歸故土的美夢就此破碎,成為深埋內心的永恆遺憾。
今天凡城約有60萬人口,以庫德人佔多數,城西距凡湖約1公里處突起一塊高百餘公尺的狹長岩層露頭,稱為凡石(Rock of Van),古烏拉圖王國最大的堡壘遺跡—凡堡(Van Kalesi / Van Fortress)即建在凡石之頂,東西綿延1.2公里,俯瞰著南面被亞美尼亞人視為第一個首都的圖西帕(Tushpa),即凡城的前身。堡壘的基座是玄武岩,上部則以厚重的土磚疊砌,作為首都堅強的防禦據點,烏拉圖之後的歷代地區強權幾乎都曾入主凡堡,現存的建築大都是鄂圖曼時期遺留,真正可溯及烏拉圖時期的遺跡是登山步道旁殘存的階梯狀牆基。
凡石最高點略偏西的南面筆直峭壁有一處鑿入山壁的洞穴,是建立艾瑞布尼城寨的烏拉圖國王阿格什提一世(Argishti I, 786–764 BC)的陵墓,漆黑的洞內有若干墓室和壁龕,洞口兩側的石壁則刻滿了楔形文字銘文,記載他的生平與功勳。東面的山壁還有幾個不知名的墓穴,供遊客攀登的狹窄階梯步道也是鑿山壁而成,僅在危險處的外側加裝簡陋的金屬護欄,因此不免有幾分驚險。
前五世紀波斯帝國的薛西斯一世(Xerxes I, 486–65 BC)在凡石南面山腳下的一處山壁上刻下三種文字(古波斯、巴比倫、埃蘭)的銘文,高出地面20公尺—這是古波斯帝國勒石銘勳宣揚國威的典型遺跡,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朗西北部名列世界遺產的比斯希頓(Behistun)銘文,出自薛西斯一世之父大流士大帝(Darius I, 522–486 BC),凡石的這一件是現存唯一位在伊朗境外的古波斯帝國銘文,保存狀況極佳。凡石之南緊鄰老凡城,經歷1915至1920年間的戰爭破壞與屠殺清洗,這座百年前曾有八萬居民的城市只剩不明顯的土堆、牆基、幾截宣禮塔與教堂殘跡,倒是南面兩座16世紀的清真寺已經修復得十分光鮮。
凡湖周邊一度教堂、修道院林立,如今倖存且可觀的卻是寥寥無幾。巴格拉圖尼王朝最大的王國法斯普拉坎921年在凡湖南端的阿赫塔馬爾(Aghtamar)島修道院建造聖十字教堂,作為法斯普拉坎王室教堂及主教駐地,13至19世紀再陸續擴建了前廳等建築。最具特色的是聖十字教堂外牆連續的聖經故事等生動的浮雕,包括大衛王挑戰巨人歌利亞等,風格則匯聚了波斯、阿拉伯與伊斯蘭等外來影響。一次大戰後教堂內外都遭到嚴重的破壞,2005年土耳其政府斥資大修,2007年以博物館的方式重新開放。
亞拉拉山高5137公尺,是土耳其第一高峰,峰頂距亞美尼亞的亞拉拉省邊界僅30公里,整個亞美尼亞西半部都看得到;東南面的小亞拉拉山高3896公尺,從亞美尼亞這一邊望去,大亞拉拉山永遠在右邊。自古以來亞拉拉山被亞美尼亞人視為聖山而禁止攀登,1828年俄土戰爭後俄國取得亞拉拉山,次年一支歐洲登山隊才首度征服頂峰;1840年活火山亞拉拉山最後一次爆發,造成極大的災難。雖然一個世紀來的搜索調查都未能證實諾亞方舟的蹤跡,但這絲毫不影響亞美尼亞人身為諾亞後代的自豪。
亞拉拉山是亞美尼亞最重要的精神象徵,許多國家以星月或十字架作為國旗的主題,而亞美尼亞國徽始終以亞拉拉山為中心,蘇聯時期還曾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抗議;離散亞美尼亞人不論身在何處,家裡總有一張亞拉拉山的相片,至今亞拉拉山和亞美尼亞的形象依然緊緊相連,象徵著亞美尼亞人的苦難以及失去的故土。這使土耳其官方似乎不自覺地排斥起自己的最高峰,竭力避免觸及亞拉拉山的形象,因此一般人在圖片裡看到的大亞拉拉山幾乎都位在右邊。亞美尼亞人固然喪失了亞拉拉山的所有權,不過專利權看起來依然歷久彌堅。2
亞美尼亞流散社群
哪一個民族的語言自成一個語族、擁有獨特的書寫字母、信仰專屬的一神教教派、散居世界各地的人數遠多於國內人口,而且不論身在何處都依然保留語言、文化與民族認同,歷經千餘年而不被同化?
答案不是尤太人,是亞美尼亞人。
目前全球約有1100–1200萬亞美尼亞人,其中只有三成居住在亞美尼亞與納卡地區,亦即流散社群(diaspora)的規模接近800萬人,和尤太人不相上下*。俄羅斯(225萬人)、美國(150萬人)與法國(45萬人)是亞美尼亞人的三大客居國,其次是喬治亞、阿根廷、黎巴嫩、伊朗、波蘭、烏克蘭、德國、奧地利、巴西、加拿大等。
亞美尼亞歷史悠久、傳統領域極為遼闊,歷代不斷遭受侵略與佔領,長期被不同的強權瓜分併吞,因此早在四世紀即已出現相當的流散社群,不過現有的流散社群主要在20世紀初的大屠殺之後才開始形成。相較於其他民族,亞美尼亞人的流散之路更為曲折坎坷,1915年鄂圖曼帝國的亞美尼亞人大量逃離世居之地,1923年法軍撤出敘利亞,再度造成難民潮。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後,領土只剩亞美尼亞傳統領域的十分之一,比台灣還小,而且大部分是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山地,人民出走有增無減;1991年蘇聯解體,新獨立的亞美尼亞共和國經濟凋敝,又導致大約百萬移民離鄉背井。
亞美尼亞人是中東國家「必備」的少數民族,中東的基督教會也幾乎全是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的天下,阿拉伯或波斯基督徒都說亞美尼亞語、讀亞美尼亞語聖經。伊朗與戰前的敘利亞都各有超過25萬亞美尼亞使徒教派基督徒,佔黎巴嫩人口4%的亞美尼亞人還在國會擁有六個保障席次,而敘利亞的阿勒坡(Aleppo)與黎巴嫩的安佳(Anjar)都是亞美尼亞流散社群中心。
耶路撒冷是基督教、伊斯蘭教、尤太教三大一神教的共同聖地,但舊城在這三區之外還多出一個「亞美尼亞區」,一旁的全球基督徒朝聖之所—聖墓教堂則由羅馬天主教會、希臘正教會與亞美尼亞使徒教會三方共管。宗教不但凝聚了亞美尼亞民族,也反映出這個民族不凡的影響力。
許多現居歐美的亞美尼亞人都是一路從中東地區輾轉而來,飽嘗顛沛之苦。亞美尼亞移民落腳之後努力適應並積極參與當地社會,他們經常對當地經濟貢獻卓著,也頗具政治遊說與動員能量。他們開辦學校、文化中心、教會以及各類公益組織,教育和傳播媒體是維繫凝聚力、免於被同化的。一個保加利亞笑話對亞美尼亞人的描述最為傳神:「只要把三個亞美尼亞人放在一起,他們就會立刻蓋一座教堂、建一所學校,再辦一份報紙。」
大部分的流散亞美尼亞人至今已傳到第四代,即使他們從未見過祖國,卻依然能說母語。不過不少人改了名字,因為亞美尼亞姓氏既長又難唸、難記,在某些國家還有受到歧視之虞。亞美尼亞人在歷史上和尤太人一樣都以經商見長,也以傑出的工匠技師聞名,今天則在居住國的不同領域出人頭地。亞美尼亞是俄國教育水準最高的少數民族,在藝術、科學、運動、政軍領域皆人才輩出,包括被譽為世界最偉大西洋棋王的卡斯帕洛夫(Garry Kasparov),以及米格機的設計人米高揚(Artem Mikoyan 1905–70)等。亞美尼亞人也在美國的企業/科學界、法國的藝術/運動界、土耳其的語言學/建築界等領域大放異彩,同時還出了不少頂尖政治人物,包括法國前總理巴拉杜(Édouard Balladur 1993–95)、美國前加州州長(George Deukmejian 1983–9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