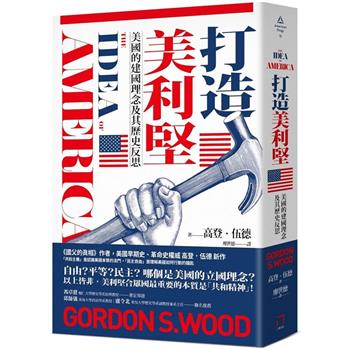第二章 美國革命的羅馬傳承
我們常常聽說大西洋世界(Atlantic world)的十八世紀末是「民主革命時代」,但其實我們應該說這個時代是「共和革命時代」比較恰當,因為推翻古代君主體制的是共和主義及共和原則,而不是民主思潮。
這是西方歷史上一個驚人的時刻,至今我們還活在其後續效應中。存在數世紀之久的君主制一夕遭到推翻,共和政府代之而起。時至今日在全世界的諸多角落,共和政府早已變得很自然且正常,對於十八世紀發生的歷次共和革命,我們已經很難感受當時它們的創新與激進性質。在十八世紀時,君主制對絕大多數人而言仍是標配,正如我們所處時代的一些事件所證明的,由單一權威從上而下統治龐大而多樣的國家,總是有其益處。君主制有它的歷史根源,歐洲的諸王曾經花了幾個世紀來鞏固他們的權威,統治不受控的貴族與多樣的民族。聖經也曾為王權背書,例如古以色列人就曾說過:「我們定要一個王統治我們,使我們像列國一樣,有王治理我們,統治我們,為我們征戰。」
自有歷史紀錄以來,大西洋世界和其他地方的大多數人民都生活在君主的統治下。但既然如此,為什麼到了十八世紀,這些君主都突然被共和革命推翻了呢?一七七六年亞當斯還感慨地說:「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在那麼短的時間裡,突然抹除他們心中對君王的崇拜、對驕傲貴族的愚忠?」如果改變無法避免,為什麼取代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是共和主義而不是別的?除了建立共和制度外,那些舊政權或許可以嘗試政治及憲政改革,世襲制度或許可以做些調整,王位繼承或許也可以換人。像是英國經歷過一六八八至八九年的光榮革命,一七一四年也進行過憲改,但都沒有取消君主制,他們只是換個人當國王,對他們的國王增加一些規定,如此而已。但除此之外,事實上英國在十七世紀曾經短暫實驗過共和主義,結果卻是場災難,換來的是一個獨裁政權。若這樣的話,怎麼還會有人想要再實驗一次呢?十八世紀確實也有過一些自封的小共和國,譬如瑞士有些「邦」(cantons),義大利有些「城邦」(city-states),荷蘭有些「省」(provinces),但這些小共和國經歷各種階段的混亂之後,最後都一一衰敗,對於西方世界一些廣土眾民的國家而言,上述根本就是錯誤示範。那為何像是英屬北美殖民地持續擴張的各省,或是構成法蘭西舊政權的那些混合體,卻還想要仿效共和制度呢?
共和制度的典範
在這個君主制當道的文化中,卻有一個共和模範值得仿效。這個共和政體在榮耀中做到別人只能期待、巴望的事,它就是古代的羅馬。十八世紀的人對於過去並沒有很大的興趣,唯有古典時代(antiquity)是個例外。沒有其他現代人如此投入古典的過往。十八世紀的一些讀書人都熟知雅典、斯巴達、底比斯(Thebes)等古代的共和國(有個美國人說這幾個名詞早就成了陳腔濫調),但再怎麼熟,都沒有對羅馬那麼熟。對於羅馬,大家再耳熟能詳不過,孟德斯鳩就曾說過:「古羅馬這麼愉快的話題,大家都不會厭倦。」吉朋(Edward Gibbon)會以古羅馬為題撰寫他偉大的史書,一點都不奇怪,他在自傳中就寫說:「不管學童還是政治家都很熟悉羅馬。」在十八世紀,說一個人「讀過書」,意思就是熟知羅馬。洛克也說過,在當時懂拉丁文「對紳士來說是絕對必要的」。
如果說十八世紀歷次的共和革命背後有什麼文化源頭,那就一定是古羅馬(這裡指共和時代的羅馬),以及源自其歷史的各種價值觀。古羅馬的傳承使得十八世紀末明顯的「共和主義轉向」成為了可能。如果十八世紀的「啟蒙」真如彼得.蓋伊(Peter Gay)所說是「現代異教的興起」(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那麼,古典共和主義就是這支現代異教的教義。啟蒙是人們對古代產生了興趣,而對古代產生興趣就是對共和主義產生興趣。古典時代當然也能夠為君主制提供一些有意義的訊息,不過若是古代世界,尤其是羅馬,能夠告訴十八世紀一些啟示,其中主要的部分或隱或顯都跟共和主義有關。
如果說啟蒙時代是發現了人的幸福及社會繁榮的源頭,那麼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研究羅馬共和從興盛以迄於衰敗過程背後所發生的種種。因此法國和美國的革命分子對古代的視角是有選擇性的,他們會集中觀察古代的政治道德和社會基礎,以及諸如社會墮落和腐敗等情事。由於十八世紀的人相信「類似的原因永遠會在政治、道德、物質世界帶來類似的結果」,所以古典時代的歷史無可避免就成了實驗室,人們會在實驗室解剖驗屍已經敗亡的共和國(尤其是羅馬),從而產生一支判斷政治體質是否健康的科學,美國人參考關於自然界的醫學,說這是「政治病理學」(political pathology)。
拉丁文學黃金時代的著作吸引了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人們,因為前者專注於歷史循環論和羅馬共和的衰頹史。這些作品出現在共和國開始傾頹到奧理略(Marcus Aurelius)在位期間,也就是西元前一世紀中葉至西元二世紀中葉約兩個世紀之間。西塞羅、薩盧斯特、李維、維吉爾、塔西陀等羅馬拉丁文學作家,連同希臘的普魯塔克,拈出的政治及社會方面的共和理想與價值,後來對西方文化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這些拉丁文作家在羅馬共和最偉大的年代開始傾頹或已然傾頹的時代寫作,以想像中秩序井然、充滿純樸及田園詩歌美德的共和國早期,彰顯他們所見羅馬共和的腐敗、奢侈與混亂,嘗試解釋共和國頹危與敗亡的原因。
這種古典理想及價值後來被義大利文藝復興翻新,變成了「公民人文主義」(civic humanism),或又稱作「古典共和主義」(classical republicanism),流傳到現代早期歐洲,到了十七、十八世紀又漸為一個更深且更廣的階層內的大眾周知。不過這些大眾看到的並不是原初、無光澤的古典時代,他們看到的往往是那個早已消失的共和國經過折射後的形象,是馬基維利和文藝復興傳達給他們的古典過往和古典價值。英語世界有些人確實懂拉丁文,可以直接閱讀古代作家的作品,但是絕大部分人都偏好湯瑪斯.高登(Thomas Gordon)的《薩盧斯特》及《塔西陀》、貝澤爾.肯尼斯(Basil Kenneth)的《羅馬古典時代》、華特.莫伊爾(Walter Moyle)的古典時代淺談、查爾斯.羅林(Charles Rollin)的通俗歷史、湯瑪斯.布萊克威爾(Thomas Blackwell)的《奧古斯都宮廷回憶錄》、奧利佛.高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羅馬史、愛德華.孟塔古(Edward Wortley Montagu)的《古代共和國的興衰省思》等翻譯本、通俗讀本或二手研究。因此在十八世紀時,歐洲(尤其是英國)的君主制文化已經徹底浸淫在這些共和論述及其傳達的古典價值中,並且至少在這個程度內具備了共和思想。
君主體制下的共和主義伏流
君主制的毀壞以及被共和制取代雖是在十八世紀,但其原由其實早在幾個世代前就已存在,因此君主制不是一次就被共和制完全取代。一七七六年的獨立宣言沒有取代君主制,一七八九年召開三級會議沒有取代君主制,就連一七九二、九三年國民議會宣布處決路易十六,成立共和國,也都沒有取代君主制。改變是在這些事件前就已逐漸發生。十八世紀大部分時候,古典共和價值開始啃食君主制,漸漸地、不停地腐蝕君主制。共和主義滲入了大西洋世界的每一處,由內部侵蝕君主制社會,消磨傳統人們對於王權的支持,最後終於在法國、北美撕去了君主制的「神聖」面貌。這時大衛.休謨就觀察到:「君王之名已不足以令人尊敬;再說什麼君王是上帝在世上的代理人,再給君主什麼曾經很嚇人的頭銜,現在都已成了笑談。」
當然,法國和英國接受這種古典共和價值的程度並不一,而且「共和主義者」(republican)這個字依舊還有貶義,是掛在對手頭上的東西,目的是即使不損害他的信譽,也會損害他對王室的忠誠。不過,可觀的其實是大西洋兩岸英法兩國的讀書人,在實質上(非僅名義上)接受共和思想的程度。很多思想家,譬如孟德斯鳩、馬布里(Gabriel Bonne de Mably)、盧梭等人儘管欣羨古羅馬,但卻認為法國太大,難以建立共和國。但也有人,譬如說羅蘭夫人(Mme. Roland),就坦承說閱讀普魯塔克「使我變成了共和主義者,在我心裡激發那曾經賦予共和主義一些特質的力量及驕傲。此外他還激發了我對公共道德及自由真切的熱忱。」大部分人都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共和主義者,可是像《南卡信使報》(South Carolina Gazette)的編輯彼得.提摩西(Peter Timothy),有一次因為刊登《加圖來信》而被人視為共和主義者,遭到外界聲討,他卻回應說:「除非美德和真理是共和主義獨有的」,否則他不是「共和主義者」。
這種古典理想,這種詹姆斯.湯姆森(James Thomson)在他的輝格風詩詞〈自由〉(Liberty)中呈現的「古老羅馬美德」,後來就成了大西洋兩岸不滿的英國人和不快的法國人拿來發聲的手段,出言反對他們自身所處君主制世界的奢侈、自私與腐敗。雖然這些知識分子、批評家訴求共和原則及古典價值,反對主流君主制世界的做法和價值觀,但他們卻少有人會因此籌劃革命,試圖推翻君主制。他們會尋求改革及振興社會,開導及改善君主制,不會想砍國王的頭。對這些批評者和其他許多人(包括殖民地一些良善、忠誠的國王陛下臣民)來說,古典時代的共和主義在他們運用下也只是相對於君主制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雖然很少人會指名援引,但是古典共和主義代表著對抗、批評十八世紀君主制世界弊病的信念與價值。
君主制與共和主義價值就這樣肩並肩並存在這一支文化中。很多優秀的君主制擁護者,其中包括英國不少優秀的托利派人士,在實質上(非僅名義上)採納了共和主義的理想及原則,渾然不知他們這樣的做法長期下來的政治涵義。一些政治信念互異的讀書人,雖然很少講到那些字眼,卻都同聲讚揚古典共和主義的精神、道德、自由、友誼及責任感,以及美好的農業社會憧憬。古典共和主義作為一套價值觀、歷史解釋、生活方式、對自由及開明的追求,實在太全面而普遍,很難認為是要顛覆君主制,反對君主制。
但這一支古典共和主義並不是一股在英國或歐洲文化邊緣打轉的小小渦流而已,而是自成一股大潮流,和主流的君主制匯流,而且還影響了其色彩、調性、方向。所以十八世紀的共和主義並沒有取代君主制,而是改變了君主制,有時候甚至難以辨別它跟君主制的區別。共和主義所代表的,當然不只是一套以民選為本的政治體制。事實上,共和主義完全不能簡約為一種「政體」。在佛朗哥.文圖里(Franco Venturi)筆下,共和主義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套古典理想與價值,和君主制完全相容。共和主義已經和「歷史上它曾經採取的各種形式區隔,愈來愈成為可存在於君主制中的一套理想。」
所以,這種源自於古羅馬拉丁文作品的共和主義絕對不是受困於地下的意識形態,只是邊緣知識分子在地窖裡開開會說說而已。實際情形是,連君王本身都參與了這一股對古典時代的膜拜風潮。英王喬治三世曾對著畫家班傑明.韋斯特(Benjamin West)唸出李維羅馬史的一段話,然後建議畫家把「雷古魯斯離去」(The Departure of Regulus)這個故事繪成畫作,來作為犧牲小我的愛國心表率。約克大主教也曾經要求韋斯特畫出塔西陀傳記中的一個故事。鼓吹古典共和主義最為熱烈的,莫過於英法的許多貴族。照理說,他們的特權來自於君主制,本來應該是最親近君主制的。一七八五年,曾經有一群貴族蜂擁至巴黎的沙龍讚嘆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嚴肅的古典派繪畫《荷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Horatii),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促成君主制日後的傾頹、他們自己後來的沒落。詹姆斯.湯姆森一七三○年出版了由維吉爾衍生而來的田園詩集《四季》(The Seasons),這本詩集獲得了王后、十名公爵、三十一名伯爵暨伯爵夫人、很多同儕和他們的子女的贊助。同樣的,這些公親貴族也不怎麼意識到他們這樣讚頌簡樸農村及其純樸美德,形同在催促他們所賴以存在的君主制價值走向潰敗。康尼爾斯.米德頓(Conyers Middleton)曾經在他的《西塞羅的生平》(Life of Cicero, 1741)當中說:「不論出身如何,如果不是透過自己的功勳贏得尊嚴,任何人都無尊嚴可言。」他這樣說的時候,如果連「宣布放棄自己與生俱來之權利,匍匐在羅馬人腳下」的世襲貴族都熱烈贊同,我們就知道當時整個文化中的共和情緒有多高亢。「激進時尚」(radical chic)一詞可不是二十世紀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