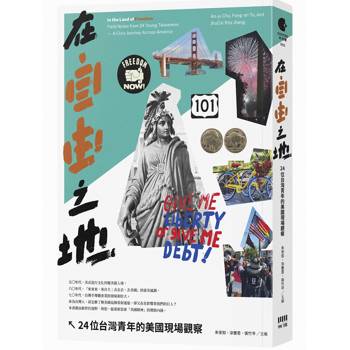以紀念塑造宏偉──DC紀念建築群
兩座紀念堂
華盛頓這座城市的整齊、秩序與無處不在的仿古建築,總會讓我感覺到這座城市仿若是被規劃著,彷彿在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已經構思好接下來兩百年的發展一般。國家廣場中的三座主要建築(林肯紀念堂、獨立紀念碑、國會山莊)雖然都是在不同的年代落成(分別是一九二二、一八八四、一八○○年),但他們的選址確實互相影響著。獨立紀念碑坐落於白宮與國會山莊的交界點;而林肯紀念堂最終的選址也是考慮到三者可以互相串聯,形成價值與景觀的軸線。甚至我們可以這麼理解:國家廣場中的三個主要建築,恰好體現了美國很重要的價值:民享(forthepeople)、民有(ofthepeople)、民治(bythepeople)。
來自台灣的我們,肯定對林肯紀念堂與中正紀念堂的相似性感到好奇。兩者似乎只有建築形式與裡面住的人有所不同,其餘的設計與空間安排似乎都遙相呼應。而這的確是事實,中正紀念堂的建築師楊卓成在設計伊始就有參考林肯紀念堂,目的當然是將蔣中正類比成林肯一般的偉大人物。除了形式與精神上的相似,更有趣的呼應是人們運用這些地方的手段。六十二年前金恩博士就是站在林肯面前的階梯上,向全美國以至全世界說出他最為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而台灣的許多民主化衝撞也同樣選在中正紀念堂,從兩岸對歌到野百合這裡始終是大家的聚集地。不僅因為廣場的功能,更因為它作為威權象徵很顯眼,只要挑戰這片場域的性質,事實上就是在挑戰威權本身。林肯紀念堂的每一處細節似乎都啟發了中正紀念堂,或者你可以說,楊卓成仔細地考究了林肯紀念堂的設計細節,然後再搭配中國文化與蔣介石的個人元素創造出了中正紀念堂。
例如紀念堂從倒映池(reflectingpool)到林肯面前是八十七階,恰巧等同於葛底斯堡演說中的開頭:「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而中正紀念堂中從民主大道(曾經的瞻仰大道)到主堂體內的蔣中正雕像共需八十九階,恰符合其過世時的年紀。
而林肯雕像背後所鐫刻之墓誌銘:「IN THIS TEMPLE AS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FOR WHOM HE SAVED THE UNION THE MEMORY OF ABRAHAM LINCOLN IS ENSHRINED FOREVER.」在中正紀年念中則體現於刻在其坐像下方所謂之「總統遺囑」及背後三個標語「倫理、民主、科學」。兩面的《葛底斯堡演說》與就職宣言則由蔣中正的兩句話「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所取代。
除了蔣中正的個人形象,中正紀念也有許多融合中華傳統與黨國精神的設計,例如從前的御路上的龍成為黨徽,四角的建築與八面的屋簷則指代四維八德。兩座紀念堂的建築形式上雖然千差萬別,但核心精神並無二致,都是對當權者理想世界的重現。美國國父與眾多政治人物都憧憬於古希臘、羅馬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具體體現在美國體制、選舉制度、首都建設甚至是拉丁文的應用上。從建築形式上而言,林肯紀念堂一定會令人聯想到殘存的帕德嫩神廟;而號稱中華文化正統的國民黨政府,則是不斷運用傳統中國元素深化自己作為正統代言人的身分,而所有模仿中山陵與紫禁城的所有設計細節也正是在此一脈絡下出現的。
或許他們的建設者未曾想過,金恩博士會在林肯紀念堂前高聲疾呼自由的早日到來,期盼共敘兄弟情緣,期盼最偏執的州也能擁抱改變;而中正紀念堂會成為民主化浪潮中用以挑戰黨國威權的場所,從國會改選的路跑開始到八九年的兩岸對歌活動以及後來的野百合學運,每每先輩們想要挑戰不公不義,破除威權,這裡都成為他們的不二之選。於林肯紀念堂,金恩博士的演說告訴我們平權遠不是一次改革就能帶來得;於中正紀念堂,前輩們運用反威權去告訴執政當權者,這片土地是屬於人們的,是不由得黨國強加定義的。當我們仔細分析威權的形塑,便會巧妙地發現,為了達成威權或者紀念的目的,都可以被反過來使用成為反抗威權或紀念另一個人的絕妙設計。
以中正紀念堂而言:為了瞻仰而設的空間反倒成為對抗爭的集會場所,當威權的空間被主動或被動地「允許」存在對抗性的活動或者物件,曾經昂揚的威權就會蕩然無存。就像雕塑被推倒可以象徵革新,一片曾經威權的地方變成民主的中心,自然會代表著社會的改革。對我來說,中正紀念堂與林肯紀念堂在建築與形式上無異,都是一種個塑造崇拜與敬仰的場所。往大的說,華盛頓與歐洲許多君主制國家首都別無二致,但帶給人們的感受卻是不同的,差別在哪呢?
我的答案是:體現的精神、紀念的人、紀念的事蹟。
這也提點我們一件事情,同樣的工具,可以帶來徹底不同的效果。現今我們對中正紀念堂之所以可以大家批評正是因為台灣民主化了,可如果今天仍然生活在威權之中,所有在美國用以形塑正面典範的作用,都可能會被用來形塑蔣氏王朝的合法性。
同理,華盛頓每一處的建設都可能用來形塑權威,但就是在細節處的觀點不同(如開放或封閉),崇拜的價值不同(君權或自由)而產生最終感知上的差異。或許事情真的就只在一念之差,好的念頭與壞的念頭都可以用一樣的東西實現,這無疑是值得我們警醒的
在異鄉繁茂開展的根系──美東夏令會(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East Coast)
在美國說台語
這是我第一次,在海外的集體聚會裡,聽見台語多於國語。午餐時,我用破碎的台語和陌生的長輩搭話,沒想到引來了熱烈的回應。也許是因為我們來自台灣的高中生太稀有,他們格外珍惜與我們的對話。
在自由交流時間中,我認識了何明聰先生。他頭髮花白、聲音洪亮,完全聽不出已經年過六十。他說他是宜蘭人,在成大求學,後來到了美國。當我告訴他我來自台南女中時,他眼睛一亮,像是記憶重新啟動。美國地大,只有住得近的人才有機會見面。對我這個短暫的旅人來說,這樣的共鳴就已足以動人,更何況是久未回台的他們呢?
何明聰先生說他曾走過中國的上海、蘇杭甚至拉薩,從中逐漸理解到台灣與中國是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我們也向他詢問台美人社群大多使用台語的理由,他便說到對他們而言國語是屬於外省人的語言,國語運動帶來的不只是語言的單一化,更抹去了一部分部分人們心中的台灣,取而代之的是三民主義、黨國體制等等不屬於這塊地原生認同的事物,所以當移居美國後終於可以自由使用台語──那不只是母語的重拾,更是一種自我身分的重建。
也有一位奶奶在分享時流露出深深的遺憾。她說當初來美國後,擔心孩子學不好英文,也覺得台語在這裡沒用,就沒教他們講。現在孩子們長大了,對台灣的記憶也逐漸模糊,她才體會到那不只是語言的斷裂,更是文化傳承的斷點。這不再僅只是語言的選擇,而是政治與認同的重建。也有人笑著說,他們講台語,是不想被中國人聽懂。這句玩笑話背後,是清晰的界線: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是台灣人。
我開始覺得,台美人這個群體,就像台灣的縮影。五十年來,他們將來自島嶼的歷史與記憶投射在美國這塊自由之地上。從人權保障、民主運動到台美關係正常化的倡議,他們不斷嘗試讓世界理解台灣。他們與台灣的距離也許因世代差異漸行漸遠,但對這座小小多山的島嶼,仍抱有深刻的牽掛。
在與幾位第二代台美青年交談中,我發現他們對台灣的記憶與我們非常不同。他們多半沒住過台灣,對台灣的想像來自父母的片段敘述、新聞裡中國威脅台灣的消息,或是在地夜市的珍珠奶茶與臭豆腐。他們對台灣有感情,卻也常帶著距離。他們說自己是「Taiwanese-American」,但更多時候,其實更像是在當美國人。然而,與台灣社會不同的是,台美人社群在語言認同上反而更堅定。也許正是距離與流離,讓他們更急於抓住台語這條唯一能證明「來自台灣」的文化線索。在台灣,台語仍常被視為「家庭語言」,甚至在都市逐漸式微,而在海外,它卻成了整個社群的旗幟。我也在想,如果未來的我們離開台灣,是不是也會慢慢遺忘語言與記憶?
一位自稱第二代台美人說自己從小就知道美東夏令會的存在,但父母從來沒帶他來參加。直到自己成年後,才開始主動接觸這個社群。他半開玩笑地說,對不少台美家庭來說,這其實不只是文化交流的場合,也是一種「相親場」,不少父母仍希望孩子能和台裔結婚,語言、價值觀、飲食與親族關係仍是一個家庭選擇的重要依據。
更有趣的是,他現在回頭為台灣地方政府工作,負責招募台裔青年回台工作。他坦言,台灣人才流失嚴重,但diaspora回流又不易,因為語言、文化、甚至對台灣生活節奏的適應,都形成斷裂。他說不少第二代台美人只會英文,或少數會台語,對中文甚至一點概念都沒有。語言成了阻礙,也是距離。
然而,與台灣社會不同的是,台美人社群在語言認同上反而更堅定。也許正是距離與流離,讓他們更急於抓住台語這條唯一能證明「來自台灣」的文化線索。在台灣,台語仍常被視為「家庭語言」,甚至在都市逐漸式微,而在海外,它卻成了整個社群的旗幟。過去我對台語的理解,頂多是考台語文競賽、上學期末的校定課程,說實話,我也曾覺得這門語言有點「沒用」。但在夏令營的這幾天,當我發現有人費心幫我查出名字的台語發音,用白話字一筆一筆寫下來,我第一次感覺台語好像不是別人的東西,而是我身分的一部分。也許這次旅程,不只是參訪美國,而是也重新讓我走進自己的過去,走進我們來自的那座島。
這段經歷讓我理解,「島嶼的身影」不只是地理的投射,而是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的延續。即使在萬里之外,語言仍成為一條回家的線索──當我用破台語試著開口時,也是在回應那條無形的連結。
兩座紀念堂
華盛頓這座城市的整齊、秩序與無處不在的仿古建築,總會讓我感覺到這座城市仿若是被規劃著,彷彿在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已經構思好接下來兩百年的發展一般。國家廣場中的三座主要建築(林肯紀念堂、獨立紀念碑、國會山莊)雖然都是在不同的年代落成(分別是一九二二、一八八四、一八○○年),但他們的選址確實互相影響著。獨立紀念碑坐落於白宮與國會山莊的交界點;而林肯紀念堂最終的選址也是考慮到三者可以互相串聯,形成價值與景觀的軸線。甚至我們可以這麼理解:國家廣場中的三個主要建築,恰好體現了美國很重要的價值:民享(forthepeople)、民有(ofthepeople)、民治(bythepeople)。
來自台灣的我們,肯定對林肯紀念堂與中正紀念堂的相似性感到好奇。兩者似乎只有建築形式與裡面住的人有所不同,其餘的設計與空間安排似乎都遙相呼應。而這的確是事實,中正紀念堂的建築師楊卓成在設計伊始就有參考林肯紀念堂,目的當然是將蔣中正類比成林肯一般的偉大人物。除了形式與精神上的相似,更有趣的呼應是人們運用這些地方的手段。六十二年前金恩博士就是站在林肯面前的階梯上,向全美國以至全世界說出他最為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而台灣的許多民主化衝撞也同樣選在中正紀念堂,從兩岸對歌到野百合這裡始終是大家的聚集地。不僅因為廣場的功能,更因為它作為威權象徵很顯眼,只要挑戰這片場域的性質,事實上就是在挑戰威權本身。林肯紀念堂的每一處細節似乎都啟發了中正紀念堂,或者你可以說,楊卓成仔細地考究了林肯紀念堂的設計細節,然後再搭配中國文化與蔣介石的個人元素創造出了中正紀念堂。
例如紀念堂從倒映池(reflectingpool)到林肯面前是八十七階,恰巧等同於葛底斯堡演說中的開頭:「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而中正紀念堂中從民主大道(曾經的瞻仰大道)到主堂體內的蔣中正雕像共需八十九階,恰符合其過世時的年紀。
而林肯雕像背後所鐫刻之墓誌銘:「IN THIS TEMPLE AS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FOR WHOM HE SAVED THE UNION THE MEMORY OF ABRAHAM LINCOLN IS ENSHRINED FOREVER.」在中正紀年念中則體現於刻在其坐像下方所謂之「總統遺囑」及背後三個標語「倫理、民主、科學」。兩面的《葛底斯堡演說》與就職宣言則由蔣中正的兩句話「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所取代。
除了蔣中正的個人形象,中正紀念也有許多融合中華傳統與黨國精神的設計,例如從前的御路上的龍成為黨徽,四角的建築與八面的屋簷則指代四維八德。兩座紀念堂的建築形式上雖然千差萬別,但核心精神並無二致,都是對當權者理想世界的重現。美國國父與眾多政治人物都憧憬於古希臘、羅馬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具體體現在美國體制、選舉制度、首都建設甚至是拉丁文的應用上。從建築形式上而言,林肯紀念堂一定會令人聯想到殘存的帕德嫩神廟;而號稱中華文化正統的國民黨政府,則是不斷運用傳統中國元素深化自己作為正統代言人的身分,而所有模仿中山陵與紫禁城的所有設計細節也正是在此一脈絡下出現的。
或許他們的建設者未曾想過,金恩博士會在林肯紀念堂前高聲疾呼自由的早日到來,期盼共敘兄弟情緣,期盼最偏執的州也能擁抱改變;而中正紀念堂會成為民主化浪潮中用以挑戰黨國威權的場所,從國會改選的路跑開始到八九年的兩岸對歌活動以及後來的野百合學運,每每先輩們想要挑戰不公不義,破除威權,這裡都成為他們的不二之選。於林肯紀念堂,金恩博士的演說告訴我們平權遠不是一次改革就能帶來得;於中正紀念堂,前輩們運用反威權去告訴執政當權者,這片土地是屬於人們的,是不由得黨國強加定義的。當我們仔細分析威權的形塑,便會巧妙地發現,為了達成威權或者紀念的目的,都可以被反過來使用成為反抗威權或紀念另一個人的絕妙設計。
以中正紀念堂而言:為了瞻仰而設的空間反倒成為對抗爭的集會場所,當威權的空間被主動或被動地「允許」存在對抗性的活動或者物件,曾經昂揚的威權就會蕩然無存。就像雕塑被推倒可以象徵革新,一片曾經威權的地方變成民主的中心,自然會代表著社會的改革。對我來說,中正紀念堂與林肯紀念堂在建築與形式上無異,都是一種個塑造崇拜與敬仰的場所。往大的說,華盛頓與歐洲許多君主制國家首都別無二致,但帶給人們的感受卻是不同的,差別在哪呢?
我的答案是:體現的精神、紀念的人、紀念的事蹟。
這也提點我們一件事情,同樣的工具,可以帶來徹底不同的效果。現今我們對中正紀念堂之所以可以大家批評正是因為台灣民主化了,可如果今天仍然生活在威權之中,所有在美國用以形塑正面典範的作用,都可能會被用來形塑蔣氏王朝的合法性。
同理,華盛頓每一處的建設都可能用來形塑權威,但就是在細節處的觀點不同(如開放或封閉),崇拜的價值不同(君權或自由)而產生最終感知上的差異。或許事情真的就只在一念之差,好的念頭與壞的念頭都可以用一樣的東西實現,這無疑是值得我們警醒的
在異鄉繁茂開展的根系──美東夏令會(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East Coast)
在美國說台語
這是我第一次,在海外的集體聚會裡,聽見台語多於國語。午餐時,我用破碎的台語和陌生的長輩搭話,沒想到引來了熱烈的回應。也許是因為我們來自台灣的高中生太稀有,他們格外珍惜與我們的對話。
在自由交流時間中,我認識了何明聰先生。他頭髮花白、聲音洪亮,完全聽不出已經年過六十。他說他是宜蘭人,在成大求學,後來到了美國。當我告訴他我來自台南女中時,他眼睛一亮,像是記憶重新啟動。美國地大,只有住得近的人才有機會見面。對我這個短暫的旅人來說,這樣的共鳴就已足以動人,更何況是久未回台的他們呢?
何明聰先生說他曾走過中國的上海、蘇杭甚至拉薩,從中逐漸理解到台灣與中國是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我們也向他詢問台美人社群大多使用台語的理由,他便說到對他們而言國語是屬於外省人的語言,國語運動帶來的不只是語言的單一化,更抹去了一部分部分人們心中的台灣,取而代之的是三民主義、黨國體制等等不屬於這塊地原生認同的事物,所以當移居美國後終於可以自由使用台語──那不只是母語的重拾,更是一種自我身分的重建。
也有一位奶奶在分享時流露出深深的遺憾。她說當初來美國後,擔心孩子學不好英文,也覺得台語在這裡沒用,就沒教他們講。現在孩子們長大了,對台灣的記憶也逐漸模糊,她才體會到那不只是語言的斷裂,更是文化傳承的斷點。這不再僅只是語言的選擇,而是政治與認同的重建。也有人笑著說,他們講台語,是不想被中國人聽懂。這句玩笑話背後,是清晰的界線: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是台灣人。
我開始覺得,台美人這個群體,就像台灣的縮影。五十年來,他們將來自島嶼的歷史與記憶投射在美國這塊自由之地上。從人權保障、民主運動到台美關係正常化的倡議,他們不斷嘗試讓世界理解台灣。他們與台灣的距離也許因世代差異漸行漸遠,但對這座小小多山的島嶼,仍抱有深刻的牽掛。
在與幾位第二代台美青年交談中,我發現他們對台灣的記憶與我們非常不同。他們多半沒住過台灣,對台灣的想像來自父母的片段敘述、新聞裡中國威脅台灣的消息,或是在地夜市的珍珠奶茶與臭豆腐。他們對台灣有感情,卻也常帶著距離。他們說自己是「Taiwanese-American」,但更多時候,其實更像是在當美國人。然而,與台灣社會不同的是,台美人社群在語言認同上反而更堅定。也許正是距離與流離,讓他們更急於抓住台語這條唯一能證明「來自台灣」的文化線索。在台灣,台語仍常被視為「家庭語言」,甚至在都市逐漸式微,而在海外,它卻成了整個社群的旗幟。我也在想,如果未來的我們離開台灣,是不是也會慢慢遺忘語言與記憶?
一位自稱第二代台美人說自己從小就知道美東夏令會的存在,但父母從來沒帶他來參加。直到自己成年後,才開始主動接觸這個社群。他半開玩笑地說,對不少台美家庭來說,這其實不只是文化交流的場合,也是一種「相親場」,不少父母仍希望孩子能和台裔結婚,語言、價值觀、飲食與親族關係仍是一個家庭選擇的重要依據。
更有趣的是,他現在回頭為台灣地方政府工作,負責招募台裔青年回台工作。他坦言,台灣人才流失嚴重,但diaspora回流又不易,因為語言、文化、甚至對台灣生活節奏的適應,都形成斷裂。他說不少第二代台美人只會英文,或少數會台語,對中文甚至一點概念都沒有。語言成了阻礙,也是距離。
然而,與台灣社會不同的是,台美人社群在語言認同上反而更堅定。也許正是距離與流離,讓他們更急於抓住台語這條唯一能證明「來自台灣」的文化線索。在台灣,台語仍常被視為「家庭語言」,甚至在都市逐漸式微,而在海外,它卻成了整個社群的旗幟。過去我對台語的理解,頂多是考台語文競賽、上學期末的校定課程,說實話,我也曾覺得這門語言有點「沒用」。但在夏令營的這幾天,當我發現有人費心幫我查出名字的台語發音,用白話字一筆一筆寫下來,我第一次感覺台語好像不是別人的東西,而是我身分的一部分。也許這次旅程,不只是參訪美國,而是也重新讓我走進自己的過去,走進我們來自的那座島。
這段經歷讓我理解,「島嶼的身影」不只是地理的投射,而是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的延續。即使在萬里之外,語言仍成為一條回家的線索──當我用破台語試著開口時,也是在回應那條無形的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