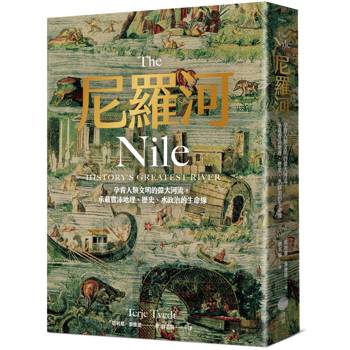一、旅程開始
羅馬城外的馬賽克鑲嵌畫
在羅馬城外約三十五公里處,有一座不起眼的考古博物館;位於博物館的四樓,有一幅以尼羅河為題的馬賽克鑲嵌畫,其已有兩千年的歷史,寬近六公尺,高超過四公尺,是從幾個不同的制高點生動地描繪出這條河及其沿岸的生活景象:頂部為非洲意象,底部則重現了地中海的場景。
雖然觀者必須隔著一道保護繩,保持一段距離觀賞這幅馬賽克鑲嵌畫,但還是能看出這幅以石灰漿黏著彩繪石頭所拼成的圖案是何其多彩與清晰。然而,這幅《帕萊斯特里納馬賽克鑲嵌畫》(Palestrina Mosaic)真正的獨特之處,在於河流和生活於河岸旁的人們,是以一種全然現代透視法的方式被描繪出來,彷彿創作者是從飛機上看著尼羅河。事實上,這幅藝術品也是一個極具表現力的史料:它凸顯了這條河從古至今一直是社會的命脈與中心,並闡明了地中海地區擁有一部「以水寫成」的大陸史。
這幅馬賽克鑲嵌畫描繪出尼羅河在沿岸居民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同時也闡述了這條河如何成為歐洲文化和宗教歷史的一部分。它使我們想起了遙遠的過去,當時尼羅河被奉為聖河,由宏偉寺廟中的祭司所祭拜,不僅在埃及境內的沿岸地區,就連在歐洲也是如此。這幅作品的起源來自於從埃及傳播至希臘與羅馬世界的「尼羅河與伊西斯(Isis)崇拜」,這是一種嶄新、獨立的信仰,是一種探討死亡與重生的神祕宗教,其有著壯觀的遊行與儀式,而尼羅河水在其中扮演著核心角色。英國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擁有著眾多伊西斯雕像。伊西斯是大自然的守護神、主掌生育與豐收的女神,她的左手提著一罐神聖的尼羅河水,這是救贖的重要媒介。兩千年前,信徒們就是提著這種裝有尼羅河水的罐子穿越平原和地中海以北的山谷,說明尼羅河水罐與後來歐洲教堂的領洗池(baptismal font)之間有著深厚的歷史關聯。
這幅馬賽克鑲嵌畫的創作時間,大約是尼羅河以及它所衍生出的伊西斯信仰,在與中東傳來的新宗教基督教成為重要競爭對手的幾百年前。當時,人們對尼羅河及其眾神崇拜,在進入基督教時代之後仍長年持續;聖馬可(Mark the Evangelist)在基督升天數十年後的一個復活節,於現今埃及的亞歷山卓(Alexandria)殉道,他正是死於伊西斯信徒之手。他們以繩索套住聖馬可的頸部遊街示眾,最後斬首。直到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伊西斯與尼羅河信仰才隨之消失,而這片一度孕育出廣為流傳的神祕宗教之尼羅河三角洲,則成了早期基督教的中心。
羅馬城外這幅尼羅河馬賽克鑲嵌畫代表了一段「洲」與「國家」之間的區別,以及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的漫長歷史。這條河的名字透過西元前七○○年至六○○年之間的希臘詩人海希奧德(Hesiod)與歐洲產生了關聯,當時的埃及、尼羅河三角洲與希臘都是地中海文化的一部分。海希奧德稱這條河為Neilos,因為這些希臘字母替換成數字的總值是三百六十五,亦即代表「一切」的意思,而這個名字似乎就是為了強調這條河被大家視為一切。這幅馬賽克鑲嵌畫提醒了我們,尼羅河谷是人類走出非洲前往地球每一個角落的主要路線之一,同時,一些已知的原初農業社會就是沿著這條河岸發展起來的,此外,也是拜這條河流所賜,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強大的古文明才得以誕生。
除此之外,這幅馬賽克鑲嵌畫描繪的是一場宗教儀式,但也能解讀成對尼羅河作為地中海文化一員的禮讚。它展現出與羅馬皇帝凱撒對這條河相同的「迷戀」:據說只要有人能告訴凱撒這條河的源頭在哪裡,他就會立即讓出整個埃及。那麼,究竟每年夏天,這個埃及最熱、最乾燥的時期,這些從熾熱的沙漠中大量湧現、將這地區變成地球上最肥沃土壤之一的水,是從哪裡來的呢?直到歐洲中世紀晚期,這條河的神祕面紗都籠罩在奇異的、神話般的臆想中。文獻中說這些水是從天堂和金色的石階上流下來的。因此,尼羅河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神聖的彰顯。十四世紀最偉大的法國編年史家之一讓.德.瓊維爾(Jean de Joinville)在一三○五年至一三○九年間出版的《聖路易傳》(Histoire de Saint Louis)中做出一個當時很普遍的結論:「沒有人知道這些水源自何處,難不成這是上帝的旨意?」
到了歐洲啟蒙運動勝利後,則出現了一種不同且更有科學依據的尼羅河浪漫主義。而在十九世紀,沒有哪個地理問題比尼羅河源頭所在位置更被廣受討論。一個半世紀前,尼羅河流域成為全球某些冒險家和探險家最傳奇的科學調查舞台,例如:英國的亨利.莫頓.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英國的大衛.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英國的約翰.漢寧.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沒那麼知名但家境富裕的荷蘭女性探險家亞麗珊卓琳.提內(Alexandrine Tinné),以及一位當年知名的挪威長跑健將,都在尋找這條河流的源頭。事實上,這些歐洲地理學家、探險家、水文學家和英國水資源規畫師所繪製的尼羅河地圖,就是一部殖民征服與現代科學在非洲凱旋前進的歷史。
然而,這幅馬賽克鑲嵌畫將這條河的景象凍結在兩千年前的這一瞬間,並從這瞬間起一秒復一秒、一日復一日、一代復一代地從非洲內陸涓涓流入密不透風且不見天日的原始森林,轟然自火山峭壁傾瀉而下,奮力湧出巨大的內陸湖泊,蜿蜒流經全世界最大的沼澤,並穿越全球最乾燥的沙漠。亙古不變的河道與水流的脈動持續形塑社會發展與轉型的條件,這條河永遠是神話締造與權力鬥爭的主角。
這幅馬賽克鑲嵌畫完成時,尼羅河三角洲這個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區之一,已先後經歷了波斯人、亞歷山大大帝和凱撒軍隊的征服。後來,阿拉伯人征服了尼羅河,十字軍也來過。接著,拿破崙率領他的軍隊登上三角洲,打了一場「金字塔戰役」(The Battle of the Pyramids);英國人則以開羅為軸心點,建立了他們的尼羅河帝國,從地中海到這條河的源頭,也就是被稱為「非洲心臟」的地方,整條尼羅河在歷史上頭一遭,也是唯一一次處於被單一權力支配:倫敦的控制。自七世紀以來,生活於尼羅河沿岸的居民一直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在非洲大陸爭霸的中心,同時,尼羅河流域也是國際援助體系中最經典的「虛構與刻板印象的溫床」。而到了第三個千禧年時,尼羅河流域的某些地區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這使得援助時期所描繪的無助非洲形象顯得有些過時了。
本書與帕萊斯特里納馬賽克鑲嵌畫所象徵的是同一個傳統,亦即:全世界都著迷於這條河流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這是一部關於文明發展的史書,也一部由全世界最長河流所敘述的遊記,同時,它也是一部對現代「水資源政治」(hydropolitics)和非洲發展的研究,以及這些變化如何像是透過棱鏡般反映出許多現代世界最核心的發展特徵。但最重要的是,本書是一條生命線的傳記,這條生命線把近五億人綑紮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如今共享這條河的十一個國家,沒有一個能逃脫。
先前我已寫過關於尼羅河歷史的書籍,如:從河流在英國控制時期的《英國時代的尼羅河》(直譯,The Nile in the Age of the British)到後殖民時代的《後殖民時代的尼羅河》(直譯,The River Nile in the Post-Colonial Age)。此外,我還出版了關於該地區的書目調查(共五卷)以及有關該地區援助時代的書籍。至於本書則試圖以不同的焦點與更長的時間軸,將我無數次縱橫整條河道旅程中所學到的一切、我從亞歷山卓到盧安達吉佳利(Kigali)的深夜咖啡館桌上永無止境的討論、多次與專家和國家元首以及部長的深入訪談,並耗費數年在三大洲的檔案館中尋找與該地區和尼羅河相關的史料,全部連結起來。
現在和未來幾年在尼羅河上及沿岸所發生的事,將對該地區乃至全球政治產生巨大影響。在撰寫本書之際,這條河流在大自然與社會中正在經歷其漫長歷史中最具革命性的轉變。正是在如今這個戲劇性、瞬息萬變、難以捉摸的時代,歷史知識變得更為重要;一個人如果不了解過去,註定會誤判現在。
本書的章節架構宛如一場沿著尼羅河出海口航向源頭的旅程。唯有如這條河本身的心跳般緩緩且有條理地沿著它逆流而上、走訪各地,才能揭開它的祕密,並了解它在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意義。
羅馬城外的馬賽克鑲嵌畫
在羅馬城外約三十五公里處,有一座不起眼的考古博物館;位於博物館的四樓,有一幅以尼羅河為題的馬賽克鑲嵌畫,其已有兩千年的歷史,寬近六公尺,高超過四公尺,是從幾個不同的制高點生動地描繪出這條河及其沿岸的生活景象:頂部為非洲意象,底部則重現了地中海的場景。
雖然觀者必須隔著一道保護繩,保持一段距離觀賞這幅馬賽克鑲嵌畫,但還是能看出這幅以石灰漿黏著彩繪石頭所拼成的圖案是何其多彩與清晰。然而,這幅《帕萊斯特里納馬賽克鑲嵌畫》(Palestrina Mosaic)真正的獨特之處,在於河流和生活於河岸旁的人們,是以一種全然現代透視法的方式被描繪出來,彷彿創作者是從飛機上看著尼羅河。事實上,這幅藝術品也是一個極具表現力的史料:它凸顯了這條河從古至今一直是社會的命脈與中心,並闡明了地中海地區擁有一部「以水寫成」的大陸史。
這幅馬賽克鑲嵌畫描繪出尼羅河在沿岸居民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同時也闡述了這條河如何成為歐洲文化和宗教歷史的一部分。它使我們想起了遙遠的過去,當時尼羅河被奉為聖河,由宏偉寺廟中的祭司所祭拜,不僅在埃及境內的沿岸地區,就連在歐洲也是如此。這幅作品的起源來自於從埃及傳播至希臘與羅馬世界的「尼羅河與伊西斯(Isis)崇拜」,這是一種嶄新、獨立的信仰,是一種探討死亡與重生的神祕宗教,其有著壯觀的遊行與儀式,而尼羅河水在其中扮演著核心角色。英國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擁有著眾多伊西斯雕像。伊西斯是大自然的守護神、主掌生育與豐收的女神,她的左手提著一罐神聖的尼羅河水,這是救贖的重要媒介。兩千年前,信徒們就是提著這種裝有尼羅河水的罐子穿越平原和地中海以北的山谷,說明尼羅河水罐與後來歐洲教堂的領洗池(baptismal font)之間有著深厚的歷史關聯。
這幅馬賽克鑲嵌畫的創作時間,大約是尼羅河以及它所衍生出的伊西斯信仰,在與中東傳來的新宗教基督教成為重要競爭對手的幾百年前。當時,人們對尼羅河及其眾神崇拜,在進入基督教時代之後仍長年持續;聖馬可(Mark the Evangelist)在基督升天數十年後的一個復活節,於現今埃及的亞歷山卓(Alexandria)殉道,他正是死於伊西斯信徒之手。他們以繩索套住聖馬可的頸部遊街示眾,最後斬首。直到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伊西斯與尼羅河信仰才隨之消失,而這片一度孕育出廣為流傳的神祕宗教之尼羅河三角洲,則成了早期基督教的中心。
羅馬城外這幅尼羅河馬賽克鑲嵌畫代表了一段「洲」與「國家」之間的區別,以及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的漫長歷史。這條河的名字透過西元前七○○年至六○○年之間的希臘詩人海希奧德(Hesiod)與歐洲產生了關聯,當時的埃及、尼羅河三角洲與希臘都是地中海文化的一部分。海希奧德稱這條河為Neilos,因為這些希臘字母替換成數字的總值是三百六十五,亦即代表「一切」的意思,而這個名字似乎就是為了強調這條河被大家視為一切。這幅馬賽克鑲嵌畫提醒了我們,尼羅河谷是人類走出非洲前往地球每一個角落的主要路線之一,同時,一些已知的原初農業社會就是沿著這條河岸發展起來的,此外,也是拜這條河流所賜,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強大的古文明才得以誕生。
除此之外,這幅馬賽克鑲嵌畫描繪的是一場宗教儀式,但也能解讀成對尼羅河作為地中海文化一員的禮讚。它展現出與羅馬皇帝凱撒對這條河相同的「迷戀」:據說只要有人能告訴凱撒這條河的源頭在哪裡,他就會立即讓出整個埃及。那麼,究竟每年夏天,這個埃及最熱、最乾燥的時期,這些從熾熱的沙漠中大量湧現、將這地區變成地球上最肥沃土壤之一的水,是從哪裡來的呢?直到歐洲中世紀晚期,這條河的神祕面紗都籠罩在奇異的、神話般的臆想中。文獻中說這些水是從天堂和金色的石階上流下來的。因此,尼羅河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神聖的彰顯。十四世紀最偉大的法國編年史家之一讓.德.瓊維爾(Jean de Joinville)在一三○五年至一三○九年間出版的《聖路易傳》(Histoire de Saint Louis)中做出一個當時很普遍的結論:「沒有人知道這些水源自何處,難不成這是上帝的旨意?」
到了歐洲啟蒙運動勝利後,則出現了一種不同且更有科學依據的尼羅河浪漫主義。而在十九世紀,沒有哪個地理問題比尼羅河源頭所在位置更被廣受討論。一個半世紀前,尼羅河流域成為全球某些冒險家和探險家最傳奇的科學調查舞台,例如:英國的亨利.莫頓.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英國的大衛.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英國的約翰.漢寧.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沒那麼知名但家境富裕的荷蘭女性探險家亞麗珊卓琳.提內(Alexandrine Tinné),以及一位當年知名的挪威長跑健將,都在尋找這條河流的源頭。事實上,這些歐洲地理學家、探險家、水文學家和英國水資源規畫師所繪製的尼羅河地圖,就是一部殖民征服與現代科學在非洲凱旋前進的歷史。
然而,這幅馬賽克鑲嵌畫將這條河的景象凍結在兩千年前的這一瞬間,並從這瞬間起一秒復一秒、一日復一日、一代復一代地從非洲內陸涓涓流入密不透風且不見天日的原始森林,轟然自火山峭壁傾瀉而下,奮力湧出巨大的內陸湖泊,蜿蜒流經全世界最大的沼澤,並穿越全球最乾燥的沙漠。亙古不變的河道與水流的脈動持續形塑社會發展與轉型的條件,這條河永遠是神話締造與權力鬥爭的主角。
這幅馬賽克鑲嵌畫完成時,尼羅河三角洲這個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區之一,已先後經歷了波斯人、亞歷山大大帝和凱撒軍隊的征服。後來,阿拉伯人征服了尼羅河,十字軍也來過。接著,拿破崙率領他的軍隊登上三角洲,打了一場「金字塔戰役」(The Battle of the Pyramids);英國人則以開羅為軸心點,建立了他們的尼羅河帝國,從地中海到這條河的源頭,也就是被稱為「非洲心臟」的地方,整條尼羅河在歷史上頭一遭,也是唯一一次處於被單一權力支配:倫敦的控制。自七世紀以來,生活於尼羅河沿岸的居民一直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在非洲大陸爭霸的中心,同時,尼羅河流域也是國際援助體系中最經典的「虛構與刻板印象的溫床」。而到了第三個千禧年時,尼羅河流域的某些地區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這使得援助時期所描繪的無助非洲形象顯得有些過時了。
本書與帕萊斯特里納馬賽克鑲嵌畫所象徵的是同一個傳統,亦即:全世界都著迷於這條河流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這是一部關於文明發展的史書,也一部由全世界最長河流所敘述的遊記,同時,它也是一部對現代「水資源政治」(hydropolitics)和非洲發展的研究,以及這些變化如何像是透過棱鏡般反映出許多現代世界最核心的發展特徵。但最重要的是,本書是一條生命線的傳記,這條生命線把近五億人綑紮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如今共享這條河的十一個國家,沒有一個能逃脫。
先前我已寫過關於尼羅河歷史的書籍,如:從河流在英國控制時期的《英國時代的尼羅河》(直譯,The Nile in the Age of the British)到後殖民時代的《後殖民時代的尼羅河》(直譯,The River Nile in the Post-Colonial Age)。此外,我還出版了關於該地區的書目調查(共五卷)以及有關該地區援助時代的書籍。至於本書則試圖以不同的焦點與更長的時間軸,將我無數次縱橫整條河道旅程中所學到的一切、我從亞歷山卓到盧安達吉佳利(Kigali)的深夜咖啡館桌上永無止境的討論、多次與專家和國家元首以及部長的深入訪談,並耗費數年在三大洲的檔案館中尋找與該地區和尼羅河相關的史料,全部連結起來。
現在和未來幾年在尼羅河上及沿岸所發生的事,將對該地區乃至全球政治產生巨大影響。在撰寫本書之際,這條河流在大自然與社會中正在經歷其漫長歷史中最具革命性的轉變。正是在如今這個戲劇性、瞬息萬變、難以捉摸的時代,歷史知識變得更為重要;一個人如果不了解過去,註定會誤判現在。
本書的章節架構宛如一場沿著尼羅河出海口航向源頭的旅程。唯有如這條河本身的心跳般緩緩且有條理地沿著它逆流而上、走訪各地,才能揭開它的祕密,並了解它在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