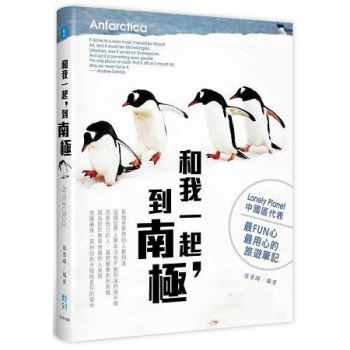穿越風急浪高的德雷克海峽是對旅行者的巨大考驗,忍受了種種折磨後,第一座冰山出現,然後第一次坐上橡皮艇,第一次登陸,然後看到企鵝、冰山、冰川,你會豁然發現,飛了那麼遠,暈船那麼辛苦,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就像是我們船上的探險隊隊長康拉德說的:「如果風浪真的特別大,在地獄般的兩天行程之後,回到了風平浪靜的比格爾海峽,你會想,再也不想到南極來了。但是,當你看到眼前這樣的美景、平靜的海灣、可愛的企鵝、澄澈的藍天、那麼多鯨,經歷了這樣的旅程,你就會忘掉德雷克海峽,這容易得很。」
確實,這容易得很。
格拉斯水道,晨光從濃密的雲層中掙扎出幾道光,便輕易讓海面上波光粼粼起來,遠處的雪山在雲霧之間正若隱若現,路過的冰山姿態各異,一隻海燕展翅飛過洪荒。
天堂灣,滿天的雲彩只在船的正前方地平線附近留出一線藍天,天上的一抹藍色被清澈的海水倒映出這中間的一塊。那藍色在雪山映襯下閃著光芒,猶如打開一扇大門,那門,通往藍色天堂。
拉美爾水道,天空中沒有一絲風,水面上是大塊大塊的浮冰。船從冰塊之間緩緩凌波微步般劃過,兩岸是似乎觸手可及的冰山、冰川,水面是冰山的完美鏡射,鏡面純粹而令人恍惚,整個世界彷彿靜止,360 度的雪山冰川。
有這樣幾幅畫面,誰還會去想德雷克海峽?何況,這樣的畫面,還有很多很多……
我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登陸,那是在南設得蘭群島上的半月島。登陸的一剎那是那麼不真實:企鵝就在登陸點旁邊悠哉悠哉地整理羽毛,梳妝打扮,引吭高歌,旁若無人。這裡是帽帶企鵝的聚居地。第一次在野外看到這麼多企鵝,除了聽到「太可愛啦」的聲音此起彼伏,看到生命和生命、生命和自然之間如此的和諧,那感覺只能是感動。那天是一個典型的南極天,天空陰沉著,雲層如同在展示自然的灰度可以有多少層次,從淺灰、中灰,一直到深灰,一位黑白攝影師夢寐以求的層次感就這麼大大方方、完完全全地展示在眼前。光線透過雲層,微弱地漫射著。翻過一個小山坡,對面的海灣裡是淡藍色的冰山。雪花在空中適時地飛舞,企鵝們在亂石之間忙碌,遠處一頭皮毛海豹仰臥在雪地上。眾人默默地在雪地裡走著,有時候被震撼的結果不是交頭接耳,而是一時失語,如果實在找不到合適的詞語來形容這裡,形容此時心裡的感受,那就沉默吧。
而真正出人意料的是,之後的每次登陸、每次環遊,都能讓人感到不同的驚喜。
就像是我們船上的探險隊隊長康拉德說的:「如果風浪真的特別大,在地獄般的兩天行程之後,回到了風平浪靜的比格爾海峽,你會想,再也不想到南極來了。但是,當你看到眼前這樣的美景、平靜的海灣、可愛的企鵝、澄澈的藍天、那麼多鯨,經歷了這樣的旅程,你就會忘掉德雷克海峽,這容易得很。」
確實,這容易得很。
格拉斯水道,晨光從濃密的雲層中掙扎出幾道光,便輕易讓海面上波光粼粼起來,遠處的雪山在雲霧之間正若隱若現,路過的冰山姿態各異,一隻海燕展翅飛過洪荒。
天堂灣,滿天的雲彩只在船的正前方地平線附近留出一線藍天,天上的一抹藍色被清澈的海水倒映出這中間的一塊。那藍色在雪山映襯下閃著光芒,猶如打開一扇大門,那門,通往藍色天堂。
拉美爾水道,天空中沒有一絲風,水面上是大塊大塊的浮冰。船從冰塊之間緩緩凌波微步般劃過,兩岸是似乎觸手可及的冰山、冰川,水面是冰山的完美鏡射,鏡面純粹而令人恍惚,整個世界彷彿靜止,360 度的雪山冰川。
有這樣幾幅畫面,誰還會去想德雷克海峽?何況,這樣的畫面,還有很多很多……
我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登陸,那是在南設得蘭群島上的半月島。登陸的一剎那是那麼不真實:企鵝就在登陸點旁邊悠哉悠哉地整理羽毛,梳妝打扮,引吭高歌,旁若無人。這裡是帽帶企鵝的聚居地。第一次在野外看到這麼多企鵝,除了聽到「太可愛啦」的聲音此起彼伏,看到生命和生命、生命和自然之間如此的和諧,那感覺只能是感動。那天是一個典型的南極天,天空陰沉著,雲層如同在展示自然的灰度可以有多少層次,從淺灰、中灰,一直到深灰,一位黑白攝影師夢寐以求的層次感就這麼大大方方、完完全全地展示在眼前。光線透過雲層,微弱地漫射著。翻過一個小山坡,對面的海灣裡是淡藍色的冰山。雪花在空中適時地飛舞,企鵝們在亂石之間忙碌,遠處一頭皮毛海豹仰臥在雪地上。眾人默默地在雪地裡走著,有時候被震撼的結果不是交頭接耳,而是一時失語,如果實在找不到合適的詞語來形容這裡,形容此時心裡的感受,那就沉默吧。
而真正出人意料的是,之後的每次登陸、每次環遊,都能讓人感到不同的驚喜。